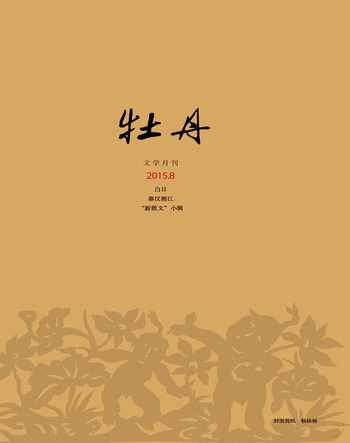嫁姑
王宏哲
我是被鸟叫声吵醒的。
我想不起来那是一种什么鸟,于是手扒着窗框朝院子里看。院子里亮汪汪的,早被阳光挤满了。我看见那些站立着的树、走动着的鸡和狗都披了一身阳光,一个个喜气洋洋,好像在等待着什么好事情。可是,除了几只跳来跳去的麻雀,我并没有发现别的什么鸟。我看见院子里杨树榆树的叶子嫩生生,绿汪汪的,而窗口那棵柿子树好像刚刚吐了一点儿芽,细细小小的,显得怯生生的。
我怀疑我是不是听错了,或者是在我梦里有一只鸟在叫。我朝院子里喊,我说:“妈,我听见有一只鸟在叫。”
我母亲正在院子里扫地。她把那块地扫得白光白光的,然后往上面铺一张很大的芦席。她说:“是喜鹊,喜鹊刚刚在柿子树上叫。”我一边套上衣服往炕底下溜,一边对我母亲说:“我还以为是我在做梦哩。”
母亲朝我笑了笑,阳光把她照得明灿灿的。她抬手朝灶房指了指,我看见她手腕间亮晃晃地划过一道光。我知道那道光一定是母亲腕上的银镯子发出的。母亲说:“饭给你在锅里留着,快吃去。”
我吸溜吸溜地喝完了一碗包谷粥,又狼吞虎咽地吃完了一个玉米面馍。我听见了我爷爷在牲口圈里和红马说话的声音。我爷爷当了大半辈子的饲养员,他似乎能看出红马心里在想什么,每次给它添料的时候总会嘟嘟囔囔地说几句啥。红马像是听懂了爷爷的话,它蹄子在地上踩出哒哒的几声响,嘴里还发出一连串咴咴的嘶叫声。
我跑到院子里朝牲口圈看,爷爷手里提着一只水桶正准备要往井台跟前走,一扭头就和我的目光相遇了。爷爷说:“才起来,你这么爱睡懒觉,将来上学了咋办呀?”我说:“我还没上学呢,要是上学了我就不睡懒觉了。”我爷爷朝我笑了笑就朝井台跟前走。
爷爷把那桶水绞上来后,就提着朝一棵白杨树跟前走。走到跟前他停住了脚。爷爷扭过头对我说:“树,去到灶房把瓢拿来。”我说:“拿瓢做啥呀?”他说:“咱把院子里的树浇一浇。”
我和爷爷把院子里的几棵树齐齐浇了一遍,浇到柿子树的时候,我特意多浇了一瓢水,我爷爷说:“为啥要给柿子树多浇些水?”我说:“柿子树是我姑姑栽的,柿子树叶子才长出来,早上还有喜鹊在柿子树上叫。”我爷爷在我的头上摸了摸就笑了。
我姑姑前年和民兵队在南山修水库,回来说南山的柿子树可多了,一到秋天到处是一嘟噜一嘟噜红红的柿子,随便摘一颗,软软的,甜甜的,别提有多好吃了。姑姑的话把我说得心里痒痒,我对她说:“我想吃柿子,你给咱也栽一颗柿子树。”我姑姑说:“好,你听话我就给咱也栽一颗柿子树。”去年春天,她就真的从南山带回了一颗柿子树,细细的,比我的胳膊粗不了多少,也不高,好像离房檐还差一截。我就有些失望了,我说:“这么小的树也能结柿子?”我姑姑说:“当然能,再小的树都会长,长大了就会结柿子。”可是,除了长出一些又黄又瘦的叶子,这棵树去年连一个柿子也没结。
我仰头看着树顶,觉得那些水似乎已经顺着树干爬上了树梢,而那些嫩芽芽就像是一张张张开的小嘴巴,吱溜吱溜地喝饱了,喝胀了,晒着暖洋洋的阳光正在悄悄地往大长。
我这样想着,禁不住就笑了。
我刚嘿嘿笑了一声,就听见我母亲在喊我,她说:“树,去门口看看你六娘来了没。”我答应着就朝院门口跑。刚跑到门口,我就看见六娘和我翠霞嫂子正一前一后地走过来。她们穿戴得整整齐齐,笑嘻嘻的,一边走一边还在小声地说着话。
我六娘和我翠霞嫂子走进院子的时候,我母亲已经在席子上铺展开的一张被里子上絮棉花。她挽起了袖子,手腕上的银镯子明灿灿地发着光;她的身上头发上沾了一些白棉絮,笑吟吟地抬起头与我六娘和我翠霞嫂子打招呼。六娘一眼就看见了我母亲手腕上的银镯子,六娘说:“我的爷呀,你咋舍得把我三妈留给你压箱底的宝贝都戴出来了,这不是故意让我眼红嘛?”我母亲说:“我四娘给你留的好东西不知道比这金贵多少了,你还会眼红这;甭说了,赶紧的,快干活,我都等你小半天了。”六娘看了看翠霞嫂子,又看了看我母亲裂开嘴就笑了。六娘说:“五嫂真个是急性子人,我收拾了锅案喂了猪紧赶慢赶地往来跑,没想到你已经干开了。”翠霞嫂子一边在衣袋里取针线,一边朝着我母亲说:“就是的,我五娘拉开的这阵势,哪里像是嫁小姑子,倒是比嫁姑娘还上心呢。”母亲噗嗤一声就笑了,说:“胡哒哒啥,四条被子呢,我不着急一天能缝完?干活,干活。”我六娘和我翠霞嫂子麻利地挽起袖子脱了鞋,和我母亲一起蹲坐在席子上絮棉花,缝被子。
我在一边蹲着看,想起来昨天晚上母亲和父亲说过的话。母亲对父亲说:“四条被子呢,得找人帮忙一起缝。”父亲当时正抽着旱烟想心事,说:“找人就找人,隔壁的杨花,对门子的改娃都是巧手人。”母亲翻了父亲一眼,说:“你懂个啥,缝婚被可不是随便谁都能缝的,得是浑全人。”父亲把煙袋从自己的口中取出来,说:“我还真把这事给忘了。”
我在芦席旁边蹲着,我看着六娘和翠霞嫂,我没看出她们比杨花和改娃多了啥,也没看出杨花和改娃比她们少了啥。翠霞嫂问我看啥呢?我说:“你和六娘是浑全人,我想看看啥是浑全人。”六娘和翠霞嫂子就都笑了,六娘说:“六娘和你翠霞嫂子是浑全人,到时候你娶媳妇我们也给你缝被子。”我从地上站了起来,我说:“我不要媳妇,我不娶媳妇,我娶媳妇做啥呀?”我母亲我六娘我翠霞嫂子都笑了,她们的笑声清清脆脆的,惊吓得榆树上的麻雀哄地一声飞散了。
我在院子玩了一会儿,我又跑到街道上疯跑了一阵。等到我再回到家的时候我看见六娘和翠霞嫂子已经不见了,芦席上也光光净净的,不知道那些缝好和没缝好的被子都上哪去了。我听见我母亲在灶房擀面的声音,我还闻见了炒熟的大葱香喷喷的味道。我在灶房探了一下头,问她上午是不是吃面条?我母亲冲我笑了笑,说:“嗯,你不是早就念叨着要吃粘面,今天咱就吃粘面。”我母亲一说吃粘面,我喉咙里的唾沫就溢满了。好多时候,我母亲中午总是苞谷面打搅团,黏黏糊糊的盛一大碗,浇了酸酸的浆水用筷子夹成块吃。我觉得我都吃得反胃了,我老缠着让我母亲叫擀粘面。我说谁谁家中午吃粘面,人家面里还有炒菜呢;我说谁谁家也常吃粘面,人家面里还有豆腐呢。听了我说的这些话,母亲只是笑一笑,说:“吃饭穿衣看家当,人家吃啥叫人家吃去。”可是我母亲隔三差五在打搅团前会给我爷爷另外擀一碗汤面,说:“你爷爷不一样,他年纪大了,还有胃病。”我爷爷每次端着面碗总会把我叫到跟前让我吃几条。其他吃面的机会,一般是我父亲或者我姑姑谁要出远门了,我母亲才会擀一案子面,我母亲说:“吃粘面吧,出远门呢,耐饥。”
我母亲对我说中午吃粘面,我就想起了我早上听到的喜鹊叫,没想到喜事这么快就降临了。我喜气洋洋地转身又要往院子跑,母亲把我叫住了,说:“别跑了,你烧锅,锅开了就下面。”烧锅就烧锅,只要能吃碗粘面烧锅算什么。我往锅灶前一坐往里面塞了一把柴,把风箱拉得呼哒呼哒响。
第一锅面捞出来刚刚递到我爷爷手里边,我就听见父亲在院门口喊:“树,快把门槛提起来。”我从灶房跑到门口,看见父亲的上衣在肩膀上搭着,脸上红堂堂,汗涔涔的。他一手扶着架子车辕,另一只手正在抹着脸上的汗。我麻利地拿掉了門槛,父亲猫着腰把架子车拉进了院子。我爷爷端着碗走过来看,我母亲端着一碗刚刚调好的面也跑过来看。我看见架子车上是两口红色的木箱子,上面画着一朵梅花,有两只喜鹊落在花枝山,尾巴高高的翘起来,脖子长长地伸着,张着嘴,好像在互相说着话。我母亲把饭碗给我父亲手里一递,说:“红底子花喜鹊,好看又喜庆。”说完又把头转向了我爷爷,说:“大,你看咋样?”我爷爷说:“好着哩,好着哩。”我父亲挑了一筷子面吞进嘴里,含混不清地说:“当然好了,两袋麦子换的,还能差?”
吃完中午饭,我母亲和我六娘我翠霞嫂子继续在院子里缝被子,我爷爷背上一个竹筐出门去给牲口打草,我父亲急急火火的,一撂下碗就不知道干什么去了。我在堂屋里围着那两口新木箱子前前后后地看。木箱子被我父亲架在一个长条凳上,上面还蒙着一张塑料布。我把那层塑料布揭去之后,一股子淡淡的油漆的味道就迎面往我的鼻孔里钻,往我的心肺里钻,让我滋生出一种从未有过的新鲜感。我忍不住在箱子上摸了摸,又歪着脑袋从几个不同的角度瞅着箱面上的梅花和喜鹊。神奇的是,我不论从哪个角度看,梅花的花枝都是对着我,喜鹊的眼睛也都好像在看着我,好像它们不是画上去的,而是长上去的,飞上去的。我看着看着就有些不安生了。我先是找来一根树枝照着箱子上的喜鹊在地上画,接着我干脆找来一支铅笔在一张纸上画。我吭吭哧哧乐此不疲地画了几乎一下午,可是,对着箱面上的喜鹊一看,不像不像,一点儿都不像。
我就丢了纸笔兴味索然地往院子走。
那时候,一缕夕阳投射到院子里,到处都是橙黄色的光。我母亲和我六娘我翠霞嫂子就在那样的光线里说笑着,正把那些缝好的红红绿绿的被子抱在怀里往屋子里走。我听见六娘说:“四床被子,四床新棉花缎面被子,可以了,可以了。”母亲笑着说:“一辈子就这么一回,再咋也不能让娃受委屈。”我翠霞嫂子把头扭向了我母亲,说:“不委屈,委屈啥呢;我三婆在无非也是这样,够可以了。”
翠霞嫂子说的三婆是我奶奶。我奶奶是前年不在的。翠霞嫂子一提她我母亲就不说话了。我看见她眼睛里亮汪汪的,好像是担心眼泪流出来,故意抬起头看了一会儿天。
晚上我们已经吃过饭好久了,还不见我姑姑回来。我母亲已经到院门口看了几遍,说:“说好的傍晚时回,现在天已经黑实了。”父亲坐在凳子上没有动,他朝外边看了一眼,说:“再等会儿。”我母亲就拿眼睛剜我父亲,说:“就你心大,这么晚了,一个大姑娘在外边你能放心?”我爷爷咳嗽了一声,说:“没事,那么大个人了,没事。”爷爷话刚一落,就听见院门吱扭扭响,紧接着,我姑姑背着一个鼓鼓囊囊的提包站在了屋子里。我姑姑穿着一身新衣服,一条粗黑粗黑的长辫子在背上垂着,脸上汗涔涔红扑扑的。她黑亮黑亮的大眼睛朝屋子里每个人看了看,把包往炕上一扔,说:“累死了,累死了,跑一天把脚都磨破了。”我往我姑姑的脚上看,看见她正把脚上一双黑油油的新皮鞋往下脱。我说:“皮鞋皮鞋,我姑姑穿的是皮鞋。”我说着就把自己的脚往我姑姑刚刚脱下的皮鞋里塞,我姑姑像是猛不防被蝎子蜇了一下,尖着嗓子说:“不敢不敢,小心弄坏了。”我姑姑越是这样说,我越是要把脚往里塞。我姑姑急得一只脚在地上跳着冲我母亲喊:“姐,你看你娃,你看你娃。”我母亲笑吟吟地从我手里抢过皮鞋抹了抹上面的灰,放到了炕沿上,对我姑姑说:“看啥,还不是你们平时惯的,赶快收拾先吃饭。”我姑姑说她已经吃过了。她哗啦一下拉开了提包,我看见包里花花绿绿的,是一堆新崭崭的衣服。我姑姑在那堆衣服里摸啊摸,最终摸出了一瓶酒。是那种绿玻璃瓶子红标签,脖子细长细长的酒。我姑姑手握着酒瓶给我爷爷递,说:“西凤酒,这是他买的。”我姑姑把“他”说得有些含混,脸上的肌肉好像还不经意地动了下。我爷爷拿着酒瓶在鼻子上闻了闻,交给我母亲让收拾好。我姑姑又从那一堆衣服里挑出了一件淡蓝色的衣服让我母亲试。姑姑说:“这是正宗的的确良,样子也不错,姐,你试试。”我母亲接过衣服手在上面摸了摸,说:“这瓜女子,给你买衣服呢,你给我胡买啥。”我姑姑忙着在包里翻检着没顾上接我母亲的话。我父亲蹲在一边嘿嘿地笑。我攥住我姑姑的衣襟说:“我的呢,我的呢,也没见给我买个啥。”我姑姑从包里取出了一个绿书包,说:“还能忘得了你;这是给你的,今年你上学了用得上。”姑姑又给了我一把花花绿绿的水果糖。我剥了一颗含在嘴里,甜味立即跑遍了全身。
我姑姑把她包里的那一堆衣服收拾好后,就和我母亲我父亲说着话。我姑姑说她这边主要的东西都置办齐了,还剩点儿零碎的她捎带着买。我母亲说被子缝好了,箱子今天也买回来了,家里该置办的也置办得差不多了。我父亲磕了磕烟袋朝门外的黑夜瞅了一眼,就叹了一声气,说:“唉,过不了几天就成人家的人了。”我父亲这话一说完我母亲就拿眼睛瞪他,母亲说:“看你说的,这是啥话?”我父亲摇着头没吱声。我姑姑好像有啥话还想说,我看见她一下一下地朝我父母脸上瞅,嘴唇一动一动地却没有声。终于,姑姑好像下了决心,我看见她抬起头坐直了,说:“还有件事。”我姑姑停顿了一下,说:“我想买一台收音机;南头春娥出门时都有收音机。”我姑姑话一说完,脸上就布满了不安。我爷爷把烟锅子在地上梆梆梆地磕了几下,说:“要那东西做啥,不能吃不能喝的;先去睡觉,睡觉。”
我父亲母亲先起身走出了屋子,我姑姑往出走时犹犹疑疑的。我看见她把那条粗黑的辫子朝后边一甩,低着头,步子迈得慢慢吞吞地。
我一晚上都搂着那个新书包,满脑子都是摆在堂屋的那两个红箱子和我姑姑包里的新衣服。去年秋天,一个穿戴整齐的小伙子来到了我们家,几个和我姑姑从小玩到大的姑娘藏了他的鞋,跟他要糖吃;我还看见我姑姑给了他一方花手帕,他给了我姑姑一个红纸包。那以后,我姑姑就让我叫他“姑父”。
我父母显然也醒着,我看见他们房间的灯还亮着,我母亲小声地说:“现在这些娃有福成啥了,光被子就四五套;咱结婚那时候都有啥?连炕上的被子都是借人家的。”我父亲叹了一声气,说:“那时候恓惶么。”说完了,我父亲像是想起了啥,说:“幸亏咱妈还留着她的宝贝,要不你真的是啥都没有了。”我母亲说:“难得咱妈的一片心,自己没钱看病都不舍得拿出来;咱妈还说叫我将来把这个给他孫子媳妇呢。”我听见我父亲叹了一声气,好久没有再说话。后来,我听见我母亲说:“按说现在是好些了,可再买一部收音机还是有些紧。”我父亲说:“可不是咋,买箱子已经把两袋麦子都卖了。”我母亲好半天没接话。再后来,我听见我母亲说:“要不然,要不然再拉一袋子麦子卖了去?”我父亲像是被火烫了一下,提高了声音说:“不行,不行,离麦收还有两三个月,到时候拿啥填肚子呀!”
我母亲又叹了一声气。
我侧过身望着窗外,看见月光把院子里的树照得清清楚楚,风一吹,杨树榆树的叶子在轻轻地动,而那棵柿子树静悄悄地,我好像看见那些嫩芽在月光里舒展开,正在默默地,欢快地生长着。
第二天我醒来的时候,看见爷爷在喂红马,姑姑正蹲在井台边洗衣服。那条又黑又粗的长辫子在姑姑背后一晃一晃的,额前垂下的一绺头发也扑闪扑闪的,太阳一照就在脸上留下了一些明明暗暗的影子。我叫了一声姑姑,问我父亲母亲去哪了。姑姑放下手里的衣服,抬手撩一撩额前的头发,说:“出去了,早上一起来就出去了;你自己到灶房去吃饭去。”我看见她眼泡肿胀着,声音也显得有气无力的。
我跑到村南头的老戏楼去耍了。老戏楼只有在过年过会时会唱上几场戏,平时闲着,就成了我们疯玩的好地方。我去的时候,早已经有一帮孩子在哪里大呼小叫的玩抓特务的游戏了。我先是在一边嘻嘻笑着看了一会儿,后来也加入其中了。我拿了一截树枝在手里当成枪,我举着我的那杆“枪”把那个扮成特务的家伙撵得四处躲。
晌午的时候,我已经玩得一头的汗,身上也脏兮兮的,全是土。更可恶的是,我裤子靠近屁股的地方不知被谁撕烂了,明晃晃地露着一坨子肉。起初的时候我并没在意,只是感觉凉飕飕地。后来,有好几个人看着我笑,我用手一摸我就知道咋回事了。我捂着屁股,说:“我不玩了,我回呀。”他们笑得更厉害了,有谁还在带头喊:“大白沟子二升面,过来过去叫人看。羞,羞,把脸抠,抠个渠渠种豌豆……”
我捂着屁股走到家门口,听见姑姑和母亲正在兴高采烈地说着话。我咚咚咚地跑进院子,看见我爷爷在地上圪蹴着抽旱烟,我母亲和我姑姑正围着一个木匣子收音机这儿摸摸哪儿瞅瞅地说着话。我母亲说:“我专门去看了,这个比春娥那个还要大。”我姑姑脸蛋红扑扑地,眼睛明明亮亮地,说话的声音似乎一颤一颤地。我姑姑说:“就是的,就是的,不光比春娥那个大,样子也比她的好。”我母亲说:“只要你喜欢就好。”我姑姑说:“喜欢,喜欢。”就把一个开关摁了一下,紧接着,一阵欢快的歌声就响了起来:“雪山升起的红太阳,拉萨城内闪金光。翻身农奴巧梳妆。阿爸和女儿逛新城呀……”
我父亲就是在这一阵歌声中走进来的。他把头上的草帽往墙上一挂,看着柜子上的收音机就呆住了。他看了看我姑姑,又看了看我母亲,就拉着我母亲的胳膊往外面走。我怯生生地跟出去,担心父亲是不是生气了。父亲把母亲拉到了榆树后面,一只手朝屋子里指了指,说:“咋回事?”母亲朝屋里子望了一眼,说:“娃想要,不买我心不安。”我父亲瞪着我母亲,说:“哪来的钱?”我母亲撩了一撂额前的头发没说话。我父亲就瞪着眼睛在我妈身上上上下下地看。最后,他抓住母亲胳膊抬起来看了看,说:“你的镯子呢?”母亲挣脱了父亲的手,说:“你小声点儿,戴那有啥用?我不戴了。”
这时,母亲发现了站在一边的我,撇下父亲拉着我的胳膊说:“弄啥去了,一身的土,裤子还烂了个洞,快脱下来我给你洗。”
我姑姑好像把收音机的声音放大了些,我听见收音机里的那一对父女唱得更欢实了:“今日的拉萨真漂亮,多亏了党的好主张唉,他领导我们当了家,雪山上升起了红太阳哇,照得我们心里暖又亮,幸福的万年长哇……”
以后的几天,我发现不断有亲戚到我们家来,村里的人也一拨一拨地到我们家来。他们大多不空手,有的拿一个新脸盆,有的拿一条新被面,还有的拿一个新镜子或者新衣架。我发现那几天我们家里堆了那么多的新东西,那么多的新东西让人感觉心里喜洋洋地。我看见我爷爷我父亲母亲热情地和他们打招呼,亲热地和他们说着话。有一天,我们家还在院子里摆了几桌席,我爷爷我父母端着酒杯敬了这个敬那个,人人脸上都带着笑,人人都说着暖心的话。我也高兴得不得了,一会儿跑到这个桌子抄几口菜,一会儿又跑到那个桌子拣几片肉。我翠霞嫂子就笑着斥责我,说:“少吃些,把肚子留着明天好好吃。”
第二天早上我早早就被叫起来了。我看见我六娘我翠霞嫂子还有不少亲戚把屋子里挤得满满当当的。我母亲特意用香皂给我洗了脸,又给我换上了一身新衣服。我六娘拿来了一个木盒子。我六娘说:“等会儿走的时候你就抱着这个木盒子,这可是你姑姑的家当,抱好。”我翠霞嫂子说:“到了谁要都不能给。”我说:“我谁都不给。”我翠霞嫂子又加了一句,说:“也不是不给,他给了你封儿你才给。”我不知道封儿是啥,我六娘说:“封儿就是用红纸包着的钱。”我说:“哦,抱盒子还有钱。”
过了一会儿,我听见外面有鞭炮响,我看见让我叫姑父的那个小伙子胸前挂着一朵大红花领着一帮人进了我们家。我看见我父亲把那对木箱子和几条新被子还有人们送来的东西往我家的马车上装,我看见那个让我叫姑父的人领着我姑姑上了他带来的马车。那辆马车上扎了个棚子,上面蒙着一张大红的被面,显得喜气洋洋,红红火火的。我姑姑穿着一身红衣服,头上还蒙着一个红盖头。我姑姑上了那辆马车后,我也被抱到那辆马车上去了。我和我姑姑紧挨着坐着,我把手里的木盒子抱得紧紧的。
我和我姑姑坐着的马车在前,我家的马车由我家的红马拉着跟在后。我们走过街巷,走向村口,两边净是笑着打招呼的人。
我们在一个叫清水头的村子停下来,我看见有一户人家的院门口挂着两个圆圆的红灯笼,好多人面带笑容地在门口围成了一圈。我听见又是一阵噼噼啪啪的鞭炮声,好多声音在喊着:“看新媳妇,看新媳妇。”我看见有人揭开了车棚上的帘子,我看见那个让我叫姑父的人抱着我姑姑在一阵哄笑声中朝屋里走,我抱着木盒子在后面跟着。
酒席吃到了半下午,我感觉我的肚子都快要撑破了,可是,看见白生生的馒头香喷喷的大肉我还是禁不住想动筷子。我翠霞嫂子就笑我,说:“你再吃小心裤带就撑破了。”我说:“没事,我把裤袋早放松了。”大家就都笑我,说:“娃今天吃美了。”我确实吃美了,面条,白馒头,大肉,这些东西我好像好久好久都没敞开吃了。
吃完饭,大家都起身准备往回走,我说:“等一下,我去叫上我姑姑。”我翠霞嫂子一把牵住了我的手,说:“瓜娃,你姑姑出嫁了;出嫁了就成了人家的人了,你连这都不懂?”听翠霞嫂子这么一说,我鼻子一酸,眼泪就流下来了。
一连几天我都呆在家里,哪里也不想去。我把我姑姑给我买的新书包拿出来看了几次,我把兜里装着的那天给我的封儿摸了又摸,我在我姑姑的房子里一待就是一整天。
这一天我正坐在门槛上发呆,我听见母亲在院子喊:“树,树,快来看,快来看。”我慢吞吞地出了房门,看见我爷爷我父亲母亲都在院子里站着,阳光把每个人身上照得亮汪汪的。我母亲手指着柿子树对我说:“你看,开花了。”
我看见柿子树上的叶子不知道什么时候长得绿汪汪的,还开满了一朵朵黄灿灿的柿子花。我仰着头,阳光迎面照下来,一股子清香直往我的心肺里飘。
责任编辑 婧 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