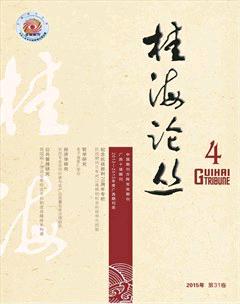战时广西在高校内迁中“翘板”作用的成因分析
韦升鸿 唐凌


摘 要:抗战时期的广西,被视为高校内迁西南大后方的“翘板”及中转、补给的重要基地。广西这种战略地位的形成并非偶然,而是存在着历史的必然。国内与广西战争形势的变化,是广西“翘板”作用形成的根本原因;广西地理位置与交通建设布局特点,为广西“翘板”作用的发挥奠定了基础;国民政府与广西省政府的政策导向差异,进一步推动了广西“翘板”作用的形成。由此展开分析,可形成对战时广西的地位、作用及贡献的客观认识。
关键词:抗日战争;广西;高校内迁;成因;地位与作用
中图分类号:K26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1494(2015)04-0021-07
抗战初期,广西作为抗战大后方的重要省区,吸引部分高校内迁办学,这些高校在广西分布较为集中,大批知识分子、社会精英随着内迁高校转移到广西。在广西期间,各院校在省政府的协助下,得以租借或使用多处房屋,并征购田地新办校址,广西省当局甚至直接拨款帮助内迁院校重建校舍。当地居民则积极配合政府所为,对高校从事抗战宣传活动、教学科研活动等以有利支持。在当地政府及民众的帮助下,各高校充分发挥所长,协助办理地方教育与师资培养等工作。战时的广西,对于各高校保存办学力量,进一步寻求更为安全的避难所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为抗日战争的胜利做出了贡献。桂南战役爆发后,广西部分沦为战区,驻留广西的高校纷纷迁往贵州、云南、四川、重庆等地。豫湘桂战役,更使整个广西沦为战场,包括本省高校在内的众多教育机关,被迫迁往西南各省。由此,广西被视为战时高校内迁的“中转站”,是高校内迁西南大后方的“翘板”,战时广西的战略地位独特而重要。
一、战时广西遭遇日军两次入侵,战争局势复杂多变,导致高校驻留广西时间较短,这是广西“翘板”作用形成的根本原因
受战局恶化的推动,高校迁桂呈现迁入快、迁离也快的特点。据不完全统计,战时在广西的内迁高校总计有15所,其中,包括外省迁来的高校11所,本省参与内迁的高校4所。而在这11所外省高校中,驻留广西直至抗战胜利的仅1所,即私立无锡国学专修学校,其余外省高校留桂时间均不长。大部分高校入桂是在武汉、广州沦陷前后。武汉会战历时4个月,日军消耗巨大,为开战以来不曾有过,日军其为策应武汉方面作战,企图切断我国对外联络,在华南沿海集结大量兵力,于1938年10月12日在大亚湾强行登陆,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相继攻陷淡水、惠阳、石龙等地,广州很快陷落[1]。武汉、广州沦陷后,原本迁移湘、赣等地的高校被迫再次西移,广西成为当时高校内迁的重要去向。一方面,湘桂铁路修通,极大地改善了广西与湘、赣等地的陆路交通;另一方面,桂、粤两省间拥有发达的水运系统,廉价的水运是当时高校内迁的首选。此外,广西省内当时并无战事,且各方面建设取得显著成绩,特别是教育事业的发展引人关注,被称为国内“模范省”,广西省政府积极招贤纳才,吸引了部分高校迁入办学。各高校则视广西为内迁的重要去向,适应了战时形势的发展。同时,广西距离战区较近,为防万一,一些高校还是做了内迁西南省区的备选方案。如当时的中山大学,计划在广西龙州设校,而就在师生赶往龙州途中,校方又决意迁往云南澄江。缘何高校迁桂会出现这样的现象?这从战时形势的变化可略知一二。
抗战期间,广西曾遭日军两次入侵,第一次是1939年11月日军由钦州湾登陆,12月相继攻占南宁、昆仑关等地,战事波及桂南多个县市,广西部分沦为战区。一年后,日军退出桂南地区,广西又恢复抗战初期的大后方地位。第二次是在1944年9月,日军为冲破英、美等国海上封锁,打通大陆交通线,发动豫湘桂战役,广西的桂林、柳州、南宁等地成为日军争夺重点,整个广西沦为战场。从这个意义上看,战时广西并非严格意义上的大后方,而是部分阶段具有大后方的性质。这也从另一层面反映了战争局势的复杂多变。在这样的战时环境里,高校要维持办学是异常艰难的。如国立同济大学在1938年7月迁至广西贺县八步,按原计划应于当年11月10日开学上课,但师生“到八步一个多月,天天都在跑警报,躲空袭,根本无法上课”[2]。于是在广州沦陷后,国立同济大学举校迁往云南昆明。实际上,当时的昆明作为西南大后方的重要城市,遭遇敌机轰炸不曾减少。西南联大成立前,敌机已对大后方各城市进行轰炸,昆明各中小学奉命疏散,联大得以借助各中小学原有校舍办学。这期间,联大校舍多次遭轰炸,学生在空袭期间,一面抱着书籍笔记疏散,坚持课业;一面还要协助校方修葺被毁校舍[3]。可见,躲空袭、跑警报是内迁高校在各地普遍面临的问题。高校内迁广西大部分集中在1938-1940年期间,此时正值桂南会战爆发前后,敌机为协助桂南战事,对广西各地进行狂轰滥炸。据统计,1938-1942年的5年间,广西共遭受空袭达615次,造成人员伤亡总计达9191人,仅1939年和1940年这两年,广西各地遭受的空袭就有485次,造成的人员伤亡达6777人①。由此推知,迁桂高校遭遇敌机空袭的次数是比较集中且频繁的,这与高校迁桂的时间密切相关,频繁的空袭破坏足以使高校整个教学秩序陷于混乱。高校在频繁的搅扰下无法维持课业,仅处于维持生存层面的需要,这对于追求发展、服务抗战建国需要的众多高校而言是难以接受的。因而,部分高校迁桂不久,又决意迁往更为深入的西南大后方省区,以寻求更为安定的办学环境。如私立武昌华中大学于1938年内迁广西,在桂林短暂维持办学,后因桂林屡遭敌机轰炸,部分校舍被毁,校方考虑到学校已不能继续正常上课,乃举校迁往云南,以求一劳永安[4]。办学环境的安全与稳定,成为当时许多内迁高校的共同追求,虽在战时条件下是难以实现的,却也成为高校不断内迁的动力所在。
如果说敌机的空袭破坏,是战时影响高校维持正常办学与发展的罪魁祸首,战事的迫近,则是直接威胁高校生存需要的魔鬼。桂南战役的爆发,是迁桂高校面临的特殊困境,这是内迁西南地区各高校不曾遇到的问题。广西战事趋紧,使得部分仍在此坚持办学的高校焦躁不安,校内师生纷纷呼吁迁往他地办学。以内迁宜山的浙江大学而言,学校在敌机频繁空袭之时,未曾有再迁校的考虑,桂南战役发生后,学校直接面临生存的威胁。特别是南宁沦陷后,校内学生自治会决议,要求“立即停课,筹备迁移”,并以此要求校长做出答复。校务会议则认为日寇虽取得南宁,但并无北上迹象,目的无非要切断我国际交通线,若敌人确有进占宾阳,学校方才停课,“书籍、仪器等不得已时即留存小龙乡,女生由校车送至相当地点,男生步行”[5]。可见,宾阳是否沦陷,已成为浙大衡量宜山能否继续维持办学的标准。从中也反映了内迁高校对战时形势的发展极为关注。高校内迁办学,在缺乏有效指示和通讯的情况下,不得不以自身的标准去判断战时形势的发展,实事求是,因地制宜,充分利用身边的资源优势维持其生存与发展的需要,这是高校面临战局多变情况下的必然选择。战争是推动高校迁桂的主要原因,同时,战争又成为迫使高校快速迁离广西的主导力量。正是由于战争形势难以预测,造成高校在广西的焦躁不安、去留难定。一旦战事的发展超出高校的预想,越过其判断战时形势的底线,再次迁校就成为无可争议的选择。这也是广西在高校内迁西南大后方的历史中“翘板”作用形成的根本原因。
二、广西在地理区位优势、水陆交通布局等方面便于高校观望形势、进退腾挪,为广西“翘板”作用的发挥奠定了基础
广西地处中国南陲,古时向称贫瘠之地,苗蛮之区,开化迟缓。广西受限于地理条件,交通阻塞,经济发展向属不易。广西四境,“东与东南均界广东,自思乐县以至贺县;东北界湖南,自贺县以至三江县;北连贵州,自三江县而至西隆;西北接云南,起西隆而至镇边;西南与安南毗连,起镇边而迄思陵;自安南因中法条约改隶法属后,遂成国境,而广西亦成为南国屏藩,边陲重地。”[6]地理区位及战略意义突出。以交通建设而言,昔日广西交通多依赖内河水运,公路运输与铁路运输起步较晚。但其“东连湘水,南控交趾(今越南地),西接滇、黔,北越五岭之地”[7],交通位置极为重要。广西境内河流众多,东西走向与南北走向交错贯注,且水量丰富,“河道适航条件好,具有江河纵横天然成网、终年不冻、干支直达、江海相通、河床稳定和含沙量少等优点。河流呈叶脉状分布较均匀,广西2/3以上的县城(市)位于江河边,对综合利用水运有利。”[8]2如“西江航运干线(百色—广州段),自西向东横贯广西14个县市,是一条仅次于长江的黄金水道。连接云、贵、桂3省的红水河、榕江和连接中、越两国的左江,通航历史悠久,在未修筑铁路和形成公路网的年代,历来是滇、黔、桂边陲地区最主要的交通命脉,现仍不失为西南地区物资出海便捷的水上大通道。”[8]2可见,在现代交通系统出现之前,广西因特殊的地理区位,发达的内河航运,早已成为滇、黔等西南省区对外交流的重要门户。
民国时期,广西交通建设颇为繁盛,特别是新桂系执掌广西后,政局较为稳定,各方面建设均获相应发展。新桂系当局根据本省地理位置优势、运输需求等实际情况,在交通建设上,尽量满足三方面需要:地方自身运输需要,国内整体运输需要,国际中转运输需要[9]。公路方面,从1937年7月至1945年8月,广西“为适应抗战期间大后方军运及国际援华物资运输需要,赶筑了沟通邻省和沟通越南的公路969公里。”[8]18如桂穗路的修筑,“豫湘桂战役期间,其不仅是联络桂林、芷江两个空军基地的捷径,更是沟通湘、黔、桂、川的交通要道,战事紧迫之时,地方财团和交通公路总局均拨巨款抢修。”[8]23-25当时,广西对外联络主要有7条干线:一是柳州六寨线:该线由柳州经宜山、河池、南丹而至六寨,出省境而入贵州,经独山、都匀而达贵阳,由贵阳经川黔公路可通重庆,东接湘黔公路可通长沙,西由滇黔公路可通昆明,是当时我国西南省际交通最重要的干线之一;二是柳州黄沙河线:该线由柳州经榴江、修仁、荔浦、阳朔、桂林、灵川、兴安、全县而至黄沙河,出省境而入湖南,经零渡、祁阳而达衡阳,北上可达长沙,南下可达韶关,向东可通浙、赣、闽诸省,为当时我国西南和东南各省联络干线,也是高校迁桂的主要路线之一;三是南宁镇南关线:该线由南宁经思乐、明江、宁明、凭祥而至镇南关,出省境而入越南,可接越南铁道达河内,与滇越铁路相通;四是南宁禄丰线:该线由南宁经武鸣、果德、田东、恩隆、百色而至云南禄丰,出省境入云南后,经富川、砚山、文山而达开远,接通滇越铁路,北可至昆明,南可达河内,为滇桂两省交通干线;五是南宁东罗线:由南宁经吴村而至东罗,入粤省而达钦州,上可接通贵州、云南,是广西出海最短路线,也是西南各省出海捷径;六是南宁梧州线:该线由南宁循邕柳路(南宁—柳州)而至宾阳,折向东南经贵县渡江,经兴业、玉林、北流、容县、岑溪而至梧州戎圩,为横贯广西南部的干线,由梧州可循西江水道而达广州;七是南宁柳州线:该线由南宁经宾阳、迁江而至柳州,为广西中部干线。广西公路,南部以南宁为中心,北部以柳州为中心,呈放射状分布,与南宁相衔接的有邕镇(南宁—镇南关)、邕钦(南宁—钦州)、邕色(南宁—百色)、邕柳(南宁—柳州)等诸线,与柳州衔接的有柳武(柳州—武鸣)、柳宜(柳州—宜州)、柳桂(柳州—桂林)等诸线[10]149。此外,自荔浦东行,经平乐、钟山、望高、西湾、八步而达贺县的公路,由望高有支线以通富川,八步有支线以通公会,平乐有支线以通恭城。而荔浦往北可达桂林,西接柳州,为联络广西东部矿区与省内各大城市间的要道。以各公路干线为支撑,辅以多条支线,广西在省际联运上,构建了黔桂运输、粤桂运输、湘桂运输、滇桂运输网络。特别是粤桂运输,水陆兼俱,历史悠久;湘桂运输方面,“1937年1月湘桂签订了《客货联运合约》,这是当时国内省际第一个客货联运合约”;黔桂运输与滇桂运输为适应战时需要均获相应完善与发展[8]195-198。总之,广西公路交通,在新桂系统治期间发展迅速,建成里程之长已位居全国前列[10]149-150。
铁路方面,广西铁路建筑,清末至民国初期,路权多为法国控制,法国把广西作为掠取西南各省经济的门户,“法国对广西铁路的计划,以安南为根据地,吸收西南各省的经济利益”[10]68-71。由此,同龙铁路(同登—龙州)的修建展延至百色、南宁二地。“钦渝铁路(钦州—重庆)更经百色至昆明,与滇越铁路汇合,北展入川以达重庆,如此滇越、邕同、钦渝三线联合,可使西南各省打成一片”,特别是“钦渝铁路联络粤、桂、黔、滇、川五省,对我国西南的经济开发意义重大。”[10]71-72可见,广西早期的铁路建设,在布局上除开发本省需要,还重在联络西南各省。客观上为广西铁路后续建设奠定了一定基础。如1937年广西始建湘桂铁路,为应抗战需要,广西在原有基础上,将湘桂铁路展筑至安南同登,与安南铁路衔接,完成国际铁路运输干线的建设[10]68。
抗战爆发后,沦陷区难民、机关、学校及工厂等纷纷内迁广西,或借道广西辗转贵州、云南、四川、重庆等大后方,这与广西地理位置、交通基础、建设布局等密不可分。高校内迁入桂可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为武汉会战至桂南会战期间;第二阶段为桂南会战至豫湘桂战役爆发前。高校迁桂后,主要分布桂东、桂北、桂东北等地,如图1和图2所示。
由如图1和图2可知,高校在广西的分布,与高校内迁入桂的来向有关。高校迁桂主要有两条路线:陆路由湘桂铁路沿线进入;水路则沿西江水道进入。这些高校入桂后,即是沿这两条路线的各支线而分布。此外,高校集中分布广西部分县市,一方面,与桂南战役的影响不无关系,桂南战役的爆发,直接堵住了高校往桂南的去向,使高校沿柳州—桂林一线分布两侧;另一方面,与这些地区在地理区位、交通建设上便于高校随时观望形势、进退腾挪密切相关。高校所迁驻的县市,均是广西开发较早的地区,如桂林、柳州、梧州为广西四大城市中的三个,经济发展与交通建设自不必多言。其他县市的交通建设亦各有特点,如宜山居于黔桂公路之上,战时成为流亡内渡,机关迁入的集中地,其“当黔桂之孔道”②,且“雄跨龙江之上,控黔而保粤”③。龙州则为“广西边防之重心,交通为军事上之要略,历任边帅未雨绸缪之地”,战时更为广西国际交通运输线的重要关口[11]。融县在交通方面,“濒临柳江,上通湘黔,下达梧粤,交通之便,于斯为盛,其交通之设备,自不容缓。”④三江之地,“当黔楚之交,一水可通梧粤,虽塞居山僻,而枢纽四省,其重要尤有不可忽视者”⑤。其境内青龙界,又名青林界,“为三江与湘省绥宁县交界地,素有‘湘桂屏藩之称。石门塘,石壁陡峻,须筏始通,为天然关隘,1943年桂穗公路经此,来往行人,毋须通渡矣。”⑥桂东贺县,“其城市以贺街八步商业最为繁盛,水路有二,一曰临江,上通钟山富川;一曰贺江,由桂岭大宁至贺街下游,与临江合流,下达信都。陆路由贺街至八步通汽车,连通贺城、信都与梧州,交通便利。”[12]从这些地区交通建设的特点来看,高校内迁于此,实是适应了抗战形势发展需要的必然选择。
总之,广西在水路、公路、铁路交通建设上,与粤、湘、黔、滇等省及越南国际线形成密切的交通网,广西交通网络经过历史的锤炼,在民国时期获得进一步完善与发展。作为抗战时期沟通我国西南大后方的交通枢纽,同时也是国际援华运输线的关键所在,广西在地理区位、交通建设方面,充分显示其特殊的战略地位,并藉此为战时由沦陷区退出的难民、学校、机关、工厂等内迁提供了极大便利。因而,这些交通网的构建,为广西在高校内迁西南大后方中“翘板”作用的发挥奠定了基础条件。
三、国民政府将广西置于高校内迁安置的边缘,广西省政府则积极扶持高校内迁安置,政策导向差异是广西“翘板”作用形成的推助器
战前,我国高等教育集中分布于华北、华东、华南等少数大城市,中、西部地区高等教育发展较为滞后。“战前国联调查团对我国大学已有批评,认为地理分配不合理,课程不切合中国需要,内容支离分裂,教授资格冗杂,教学方法偏于注入,建议改进。”[13]19全面抗战爆发后,敌人对我国高等教育机构恶意破坏,迫使大部分高校被迫内迁办学,国民政府则借此契机对高等教育强化管理,并对高校区域分布不均衡做出调整,以适应西部开发及大后方建设的需要。1938年4月,教育部颁布《战时各级教育实施方案纲要》,规定“对于全国各地各级学校之迁移与设置,应有通盘计划,务与政治经济实施方针相呼应”[14]。由此开始对高校进行有计划地迁移。以西南地区而言,国民政府将高校集中安置四川、云南、贵州等省区,据统计,此三省在战时“共接收内迁高校64所,占内迁高校总数的47%,是战时高校内迁的最大集中地。”[15]特别是国民政府西迁重庆后,内迁四川的高校为数更多,“四川一省在战时接收的内迁高校就有37所,占总数的38%,是战时接收内迁高校最多的省份”[16]。国民政府这样的安排,一方面是为适应战时形势的需要;另一方面与川、滇、黔的区位、建设基础等密切相关。此外,还应充分考虑国民政府与西部各省的关系,其大致可分以下几种:“1.中央势力已经完全或基本控制的,如陕西、甘肃、四川、贵州;2.中央势力在形式上已经进入,但实际上对省政难以插手,如宁夏、青海、云南;3.中央势力几乎完全不能进入,如新疆(抗战后期纳入中央势力范围)、西康、广西、西藏。”[17]受国民政府中央势力范围影响,对西部省区的战略开发,仍是有所偏重的,高校内迁安置即是例证,国民政府战时对大后方的建设重点也可为证。
然而,当战事燃及华中、华南等大部地区之时,国民政府对高校内迁已不能全面顾及。如陈立夫战后回忆所述:“教育部对于这许多专科以上学校的迁移、接济、决定迁设地点,筹措应变及经常费用,……无时不在紧急应付情况之下。”[13]16-17政府对高校内迁计划赶不上变化,部分高校由此选择根据需要自主迁移,广西在武汉、广州沦陷后开始有高校内迁办学,而这些高校迁桂之举,并非出于国民政府的政策安排。如国立浙江大学在迁桂之前,教育部有令:“必要时可迁贵州安顺”,而对迁校经费却不予照顾⑦。因而,当战事迫近时,浙大选择了内迁广西宜山暂住,并在此后的一年多均在宜山维持办学。国民政府在民族抗战当前,只得承认已成事实。而国立同济大学,经多次迁移,校内经费捉襟见肘,但因在贺县办学频遭敌机空袭,仍有再迁打算。教育部部长得知后,立刻划拨经费助同济迁校,竺可桢回忆:“遇同济教授朱君,知同济原订12月1日开学,后以敌机时赴八步,故于12月初正式决定移大理,学生等分批出发。当初全校只余5千元,故翁之龙遂赴重庆教部,但未几款即到校,计发三个月经费及迁移费2万5千元,每教员薪水在50下者发60。”⑧前后对比可知,教育部对高校迁桂与离桂的态度截然不同。浙大内迁贵州遵义、安顺办学之时,教育部部长陈立夫亲自到校视察,以示慰问和欢迎。显然,国民政府已将广西置于高校内迁安置的边缘。
究其原因,新桂系与国民政府当局长期存在尖锐矛盾,即是其一。“全面抗战爆发后,蒋桂虽不计前嫌,由对抗变为合作,但矛盾并没有消除,两者表面上精诚合作,暗中却进行激烈的控制与反控制斗争。”[18]李宗仁曾言及左右:“蒋介石是不能容我们的,横竖是利用我们,不过借抗战之名来削弱和他对立的地方力量,将来还是要搞统一独裁。蒋介石这个人最不可靠,他绝不会相信我们。”⑨蒋桂的貌合神离,某种程度上影响了教育部对高校迁桂的政策扶持,国民政府更多表现为对迁校已成事实的被动接受。国民政府为加强对战时高等教育的控制管理,教育部不可能全力扶持内迁院校在中央势力范围以外长期维持办学,更不可能促使内迁入桂院校在桂系统治范围内构建稳固的社会基础。
对新桂系而言,一方面,为增强自身“反控制”的力量,多方拉拢各民主党派及进步人士,并为此营造一种自由、民主的文化环境,使广西在战时汇聚了众多知名团体与文化名人,广西建设研究会的建立、桂林抗战文化城的形成等均是例证;另一方面,广西政治、经济、教育、文化等各项建设蒸蒸日上,急需引进各方面人才,高校迁桂给广西招揽人才提供了难得契机,因而,省政府积极扶持各高校迁桂办学。如内迁广西宜山的国立浙江大学,在广西省政府的协助下,获得文庙、标营、湖广会馆等房屋和空地,并在此基础上扩建校舍。由此,“凡讲艺之堂,栖士之舍,图书仪器之馆,校长百执之室,以至庖蝠之所,电工之厂,游息树艺之场,莫不具备。于是五院之师生千余人,皆得时讲贯于其中。”⑩又如内迁桂林的江苏省立教育学院,在院长高阳和俞庆棠先生带领下,于1938年初迁抵桂林,“学院先是借用广西大学部分校舍进行复课,嗣后由广西省政府拨款在桂林七星岩附近修建临时校舍三所,并租用部分民房、庙宇与祠堂作为师生宿舍。”[19]此外,迁桂的私立无锡国学专修学校在桂林穿山获得300亩建校用地,使学校可以稳定办学,这与广西当局的有力支持不无关系。
广西省政府对高校迁桂的态度积极,其热情举动充分表明,省政府有意挽留内迁高校在桂办学,并希望能与各高校在地方教育等方面进行更多合作。广西在成人教育、师资培养等方面,与迁桂高校多有合作,如选送中学史地教师进入国立浙江大学史地系第二部就学11,将民众教育交予江苏省立教育学院协助办理等[20]。而后又将本省《国民中学教学科目及各学期每周各科教学时数表》,委托江苏省立教育学院予以修正,最后制定成《广西省国民中学教学科目及每周教学节数表》,使广西在国民中学的教学安排上更为科学12。这些都对高校充分发挥所长,协助地方建设,稳固高校在地方办学的社会基础具有重要意义。广西省政府的主动招引,与国民政府对高校迁桂的不作为态度截然不同,两者政策导向的差异,是影响高校在广西办学去留难定的重要原因。实际上,贵州在战时是“国民党反动派严密控制下的‘模范省,民主人士和进步力量的活动均受党团特工监视,浙大学生和遵义人民的共同斗争都处于不利情况”13。据统计,1940年,“仅在川黔两地的高校中,两个月内因莫须有的‘思想罪而遭逮捕的学生,即有33名之多”,在国民党的党化教育与特务控制下,内迁院校处境艰难[21]。这与战时广西相对自由、民主的文化氛围形成鲜明对比。由此看来,抗战前期,广西对部分高校而言,确实是个良好的去向。但许多内迁高校与国民政府存在直接或间接的利益关系,甚至部分院校依赖于国民政府的经费扶持,广西始终只是战时环境下临时避难之地。何况广西在战时遭遇日军两次入侵,省内形势复杂多变,社会环境极不稳定,高校在此面临生存的威胁,这是促使其迅速迁离广西的关键。
综上所述,国内抗战形势的迅速发展,迫使部分高校内迁入桂,而广西战事趋紧,又迫使各高校很快离桂。在此过程中,战争始终发挥着主导性影响。此外,广西在地理区位、交通建设布局等方面为高校迁移提供了极大便利,打下良好基础。国民政府与广西省政府对迁校的政策导向差异,影响着这些高校迁移计划的制定和去向选择,形成对高校迁移的推助器。因此,战时高校内迁入桂过程虽与抗战相始终,但不可就此认为,高校迁移始终处于一种被动的地位,这无疑是比较片面的分析。战争的影响是客观存在的,但还应考虑高校自身的主观动因,战事始兴之际,多数高校难舍故地,然而抗战已成现实,出于自身生存的需要及抗战建国的责任,高校内迁也会有主动应战的策略。如李絜非所言:“我们将近七百师生,是自信有安定后方的天职。”14内迁的各高校为支持前方抗战、建设大后方所作的各项贡献也证实了这一点。从这个意义上看,战时高校内迁是由最初的被动迁移而慢慢转为主动应对的。惟有深入分析高校迁移动向与选择,才能从整体上把握高校内迁过程,进而实事求是地认识各地在高校内迁中所发挥的作用。因此,战时的广西在高校内迁西南大后方中发挥“翘板”作用,并非偶然,实属历史的必然。
注释:
①广西省政府统计处编印:《广西年鉴》(第三回,下),1948年,第1357-1359页。
②⑩《国立浙江大学宜山学舍记》,此碑为浙江大学校长竺可桢所撰,立于文庙校址(浙大教务处,现为市公安局),已佚。载于李楚荣著:《宜州碑刻集》,广西美术出版社,2000年,第55-56页。
③《修城记略》,此碑刊于清乾隆三十二年(1767年),为何熊所撰。何熊,浙江钱塘举人,乾隆二十六年任宜山县知县。载于李楚荣著:《宜州碑刻集》,广西美术出版社,2000年,第14页。
④黄志勋修,龙泰任纂:《融县志》(卷一),成文出版社,1936年,第186-187页。
⑤魏任重修,姜玉笙纂:《三江县志》(卷一),成文出版社,1946年,第494页。
⑥魏任重修,姜玉笙纂:《三江县志》(卷一),成文出版社,1946年,第89-90页。
⑦⑧浙大在筹备迁桂之时,“教育部以为在此打折扣时期,又加浙省协款来源断绝,而浙大尚有余款,势必加以减饬,至少亦不得增加。”校方只得主张“薪水打六折而经费发七成”,“停止购进仪器、书籍”等(引自竺可桢著《竺可桢全集》第6卷,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2005年,第578页)。可见,教育部不但没有因迁校而予以经费照顾,反而有缩减校内经费补助的意向。
⑨李任仁:《回忆广西建设研究会》,摘自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广西壮族自治区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广西文史资料选辑》(第四辑),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广西壮族自治区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发行,1963年,第78页。
11《电饬选送史地教师入国立浙江大学史地系第二部就学》,教导字第4930号代电,引自《广西省政府公报》,1941年,第1107期,第5-6页。
12《自费肄业中等学校学生贷学金章程》,引自《广西省政府公报》,1940年,第965期,第9-10页。
13周开德:《遵义县革命文化史料选·壮歌行》,遵义县革命文化史料征集办公室编,1992年,第329页。
14李絜非:《浙大西迁纪实》,1939年,第2页。李絜非是国立浙江大学内迁的主要负责人,参与了国立浙江大学内迁的整个过程。
参考文献:
[1]何应钦.八年抗战之经过[C]//沈云龙.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79辑.台湾:文海出版社,1966:54-55.
[2]李法天,李奇谟.抗战期间同济大学内迁回忆片段[C]//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西南地区文史资料协作会议.抗战时期内迁西南的高等院校.贵阳:贵州民族出版社,1988:71-77.
[3]陈明章.国立西南联合大学[M].台北:南京出版有限公司,1981:2-6.
[4]吴醒夫.华中大学迁滇梗概[C]//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西南地区文史资料协作会议.抗战时期内迁西南的高等院校.贵阳:贵州民族出版社,1988:99-100.
[5]竺可桢.竺可桢全集:第7卷[M].上海: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2005:209-210.
[6]方光汉.广西[M].广州:中华书局,1939:2-3.
[7]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C]//贺次君,施和金.中国古代地理总志丛刊.北京:中华书局,2005:4797-4798.
[8]广西壮族自治区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广西通志·交通志[M].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1996:2.
[9]陈 晖.广西交通问题[M].长沙:商务印书馆,1938:2-4.
[10]陈正祥.广西地理[M].上海:正中书局,1946:149.
[11]龙州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龙州县志[M].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1993:40-42.
[12]黄成助.贺县志:卷四[M].台北:成文出版社,1967:247.
[13]陈立夫.战时教育行政回忆[M].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73:19.
[14]教育部教育年鉴编纂委员会.第二次中国教育年鉴[M].上海:商务印书馆,1948:8-9.
[15]张根福.抗战时期的人口迁移——兼论对西部开发的影响[M].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2006:98-99.
[16]徐国利.抗战时期高校内迁概述[J].天津:天津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1996(1):57.
[17]马 烈.抗战时期国民政府开发西部的重大政治举措[J].江苏教育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1):67.
[18]谭肇毅.桂系史探研[M].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05:287-288.
[19]童润之.俞庆棠先生与江苏省立教育学院[C]//苏州大学(原江苏省立教育学院)校友会.人民教育家俞庆棠与江苏省立教育学院.苏州:苏州大学出版社,1987:16-17.
[20]苏州大学(原江苏省立教育学院)校友会.艰苦的探寻——江苏省立教育学院校友回忆录[C].苏州:苏州大学出版社,1989:148-153.
[21]侯德础.抗日战争时期中国高校内迁史略[M].成都:四川教育出版社,2001:236-238.
责任编辑 莫仲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