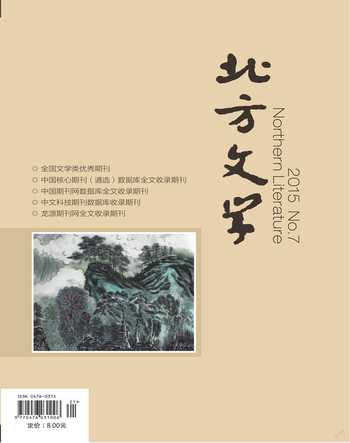《天注定》
李沙
摘 要:中国第六代导演贾樟柯的创作风格向来独树一帜,新片《天注定》又一次以独特的链条结构为叙事方式,以社会突然暴力新闻为素材,充分展现暴力本身,摈弃了以儒家思想影响下的传统电影叙述中的隐忍人物形象,消解了中国传统文化中重视个人对集体的价值观和集体对于个体的价值认同,着眼于刻画小人物在社会中孤立无援的状态与游离于大时代大背景下的生存状态。
关键词:传统文化;贾樟柯;天注定;暴力
贾樟柯的电影《天注定》亮相戛纳电影节,再一次向世界证明了中国导演的实力。对于中国电影界来说,这无疑是一大惊喜——贾樟柯大胆地将触角伸向了国内导演不敢触及的反映现实社会暴力与矛盾的电影题材。
《天注定》取材于四个真实的新闻事件,分别为山西胡文海连环杀人案,周克华案,邓玉娇事件和富士康员工自杀事件,与之前的《海上传奇》和《二十四城记》纪录式的电影不同,将四个毫无关联的犯罪事件串联起来,把各自独立的新闻事件组合成一部完整的电影,用叙事化的镜头语言构筑事件,四个小人物在故事里相互交织,几个事件重新排列组合,形成一个整体的连环套索。尽管在有限的时间中,四个故事的讲述稂莠不齐,如第四个故事,流水线工人跳楼自杀的动机明显在片中没有做恰当的过渡性铺垫,但从结构上来看,影片打破了单一的封闭的叙事结构,以重塑不同偶然性事件的方式对传统叙事结构进行反叛。
影片不仅在结构上与传统叙事方式有较大不同,还以狂欢式的暴力镜头对传统风格进行反叛,以独特的人物形象重置和叙事内容表达方面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消解。虽然在《天注定》这部影片中,吸取了一些传统的戏曲作为叙事的隐喻性线索,在题目上也借鉴了传统的宿命论中人命本是天注定的观点,但影片以个人化的暴力突发事件入手,其影片内核对中国传统的文化却是一种彻底的叛逆。
一、侠义人物形象的重置
贾樟柯在谈到这部电影的创作过程时,提出《天注定》是一部“现代侠义电影”,在许多方面是对导演胡金铨的一种致敬。《天注定》与其他武侠片相比,它着眼于重新构建古人与现代人的关系,而这种关系的纽带便是“侠义”,而所谓的武侠动作场面却非真正意义上的武侠电影,而是“贾樟柯式”的侠义风格,这种人物设置时对传统侠义形象的重置,对于传统意义上的武侠意义进行了消解,颠覆了“侠之大者”的侠客形象。在《天注定》中,贾樟柯的侠义人物不仅是村里游手好闲的大海和游侠一般混迹南北东西的三娃,最突出的是插足他人婚姻的小玉“女侠”形象的塑造,从造型上来说,演员赵涛以高耸的马尾辫出场,是完全符合古代侠客在头饰上的造型风格;在屡次受到村干部性骚扰之后,小玉忍无可忍,拔刀相向,其招式与动作都与古代侠客如出一辙。
在贾樟柯以往的电影中却没有这种剑拔弩张式的张扬,“侠义”表现在观念层面,而《天注定》中,导演将“侠义”只是停留在人物的动作行为上,将潜藏在影像结构层面的侠义情怀变化为外在表现,这些侠客在品行上并不是完美的、高尚的,导演消解了这些人物身上的责任感与使命感,而是以暴力行动来表现侠客在行侠仗义时的心理状态和行为招式,在暴力之中,英雄形象被突然建构起来又突然间崩塌,豪情表现在暴力爆发时的冲动,施暴结束后又转为无可奈何的洒脱。导演通过人物所表现出的扭曲的侠义精神,传达着当今社会人们心中英雄形象的倒塌和日常生活安全感的缺失。
二、抛弃人物在沉静中的隐忍
中国内地第四代以及第五代导演深受中国传统文化中儒释道精神影响,在影像风格上追求一种满承禅意的温柔敦厚的性情,擅于展现富有诗意的文人气质,传统的儒家观点强调以礼抑情,以义抑利。从中国第二代导演如费穆,蔡楚生到第五代导演张艺谋,儒家思想对中国国内电影导演的风格确立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人物塑造方面往往以隐忍坚韧的主角形象为主,人物性格沉静而悲情,在带有传统文化色彩的大背景下展示民族性的命运悲剧,如《神女》《小城之春》之类影片,人物在不幸的命运中咀嚼苦难,以隐忍的方式完成个人悲剧命运的涅槃。《天注定》也注定与众不同,以一次暴力镜头的狂欢方式瓦解了传统审美中的平衡感,反抗儒家思想对于国民性格的压抑,人物不再长期在痛苦中挣扎,痛苦只被缩小成一个个症结:大海已过不惑之年却没有娶妻生子,而且身患糖尿病;三娃居无定所无法回头,面对妻子与孩子一阵阵的陌生;小玉插足他人家庭,又在寻求真情的道路上迷失方向;年轻的打工仔始终逃离不掉同乡的追打……这些苦难被还原成日常生活中被忽略的情绪,甚至看起来可有可无,与此相反,当人物在这些症结恶化成危机感时,暴力气氛被营造得浓墨重彩,原始的暴力冲动在瞬间宣泄而出,在大海举着枪逼迫刘会计写下村长和焦老板的贪污事实时,观众早已在过去电影中形成了思维定式,认为在刘会计的反叛喝令下,大海会犹豫再三放下猎枪,但贾樟柯并不是循规蹈矩之徒,大海的情绪如同脱膛而出的子弹般一发不可收拾,见恶毙恶,在焦老板的车中,用封闭的狭小的空间完成了人物内心欲望的宣泄,在鲜血四溅的时刻,大海嘴角扬起一丝笑容,一反宋代的理学家宣扬的“存天理,灭人欲”,也彻底打破“乐而不淫,哀而不伤”的中庸美感意识。
大海看似“舍身取义”的行为,实则没有为乡亲们取得一丁点有效利益,相反,大海这种在集体之中带头以忽视个体生命来寻求集体公平的行为,非但没有唤起集体反抗意识,个体反而在矛盾中迷失理性,贾樟柯在片中将现实全盘摊出,大海杀死了贪污乡亲们共同财产的焦老板,那些污染环境的工厂没有关门,矿难还是时有发生,那些共同财产没有回到百姓手中,而是落在了焦老板夫人的手里,杀光违背公平的人又能怎么样?问题得不到解决,受到惩罚的,最终还是苦难者本身。
就在接二连三的暴力狂欢之后,观影者反而会对片中人物产生了不自觉的同情,这也就基于导演敢于反叛儒家传统根深蒂固的中庸人格特征,打破理想的人物性格建构,反颂扬道德意识下的正面人物诉求,反传统文化中“节制”与适可而止,为暴力发生所做的冲突仅仅是表象,暴力过程及施暴者的心理状态才是导演的立足点,暴力者即是施暴者,也是暴力的受虐者。突发的暴力事件只是表象,人的孤立无援,社会善恶模糊化,人无法在沉静中继续通过隐忍来完成自我救赎,暴力成为最终无可奈何的宣泄方式。
三、游离在集体之外的孤独个体
中国第六代导演在成长过程中经历了中国社会变革的历程,也目睹了中国大多数人民脱贫致富的过程,他们的影片几乎都着眼于社会变迁中的小人物的状态,普遍关注社会发展中的重大社会问题和新闻事件。贾樟柯作为第六代导演的领军式人物,从早期的《小武》《站台》《三峡好人》到近几年的《二十四城》《海上传奇》《天注定》,都带有贾樟柯独有的纪录片式电影风格和对小人物生存的终极关怀。
儒家文化重视个人对家庭,国家,民族的责任义务,把个人价值置于社会价值之中,强调群体意识对个人的影响。而贾樟柯的电影似乎从一开始就另辟蹊径,他电影中始终展现着小人物与大事件或大背景下生存事件之间的关系,与第五代导演在电影中对民族主义的中国性情表达截然不同的是,贾樟柯的电影更靠近意大利新现实主义电影,他擅长于将现实事件与电影中人物的生活经历对接在一起,如在《任逍遥》中,主人公小济在听闻全国人民因申办奥运会成功欢呼雀跃时,却将自己置身于欢呼声之外,这种巧妙的对接所传达出的小人物在主流社会中的孤独感在《天注定》中一脉相承,在第三个故事中,小玉(赵涛饰演)在平板电脑中看见了关于动车脱轨事件的新闻报道,面对如此重大的社会问题,普通人只能通过一句脏话和“这是怎么回事”来消解社会隐患对人们生活带来的不安全感,导演运用电影植入新闻的方式,形成了一种个体与社会互动的叙事张力,这些事件在人物内心影响着人物的情绪与命运走向,成为人物命运的预告式结局,小人物和大事件有意识的对应使得小人物的生存孤独和无奈感更加凸显,增强了电影的讽刺和暗示效果。
四、象征表达对传统意向的反叛
值得一提的是,贾樟柯向来钟情于运用外向型的象征表达,这种表达在以往的电影中也有所体现。在纪录式电影《海上传奇》中,赵涛饰演的行走人看似可有可无,而这个角色恰恰是导演画外音的无声化与情感的形象化表达。在影片《天注定》中导演将形象化语言附加在几个动物和物件上,第一段故事中乌金山村口的毛主席雕像与农用车上的圣母玛利亚画像在此相遇交错,格格不入的画面感,导演用符号化语言表达出政治化元素,影射当前社会潜在的危机。在之后的剧情中还出现了三娃拜鬼神,小辉和莲蓉拜隔着铁门的佛像,雨中的佛陀,导演不再冷眼旁观,而是将自己的主体意识直接通过这些外向化的形象符号摄入影片之中,道破了当下社会底层人们信仰缺失的尴尬处境,这种信仰迷失,正是在儒家等级观念影响和政治权力膨胀的背景下的产物,导演对于这种由古至今根植在人民心中的痼疾宣泄出来,对于传统的反抗也通过镜头语言直接表达出来。
在佛家思想之中,将人生现世指向虚无,认为生命本身是一种苦难,在贾樟柯的电影之中,常出现表现众生常态的镜头,《二十四城记》中工厂里麻木呆板的父子俩,《站台》之中听着演唱欢呼雀跃的人们,在《天注定》中,依然表现出芸芸众生对于生活的麻木妥协。不同的是,导演运用许多动物做隐喻,表现出牛毛般民众承受的欺压却不知反抗的愚昧心理。马,蛇,牛,鱼,这些动物在传统意象中或凶猛,或奸诈,或勤劳,而在影片之中,成为百姓生存状态鲜活的写照,这些动物的隐喻突破了传统文化意象之中的含义,而是将其苦难化,悲观化。
而过分强调这些动物对应主角的隐喻则过于生硬刻意,虽然叙事在象征层面有了进一步表达,而过于外化式的动物、元素象征则又将影片内核直白化,但这种主观化刻意强调了消极的价值观,过度突出对于传统思维的叛逆心理,尤其是第三个故事中,灵蛇在小玉身边经过,以及蛇女对于小玉的怜悯都充满了民间异教色彩,不免有调动西方观众的好奇心的嫌疑。这些动物在影片的叙事安排中过于严密,有时甚至与画面互相矛盾,显得刻意,做作,有失影片的真实感。
贾樟柯的电影以独特的方式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批评和反叛,使得他的作品中人物从集体意识回归到自我意识。虽然身在中国社会这一大背景下,贾樟柯也难以完全脱离儒家思想对其电影中小人物与大社会的关系判断的影响,无法全然摈弃传统意识下的“命中注定”思维,但他能够从个体角度开始探索个人在集体中认同感的缺失对于个人命运的导向性,从小人物事件着手,探究出人性在反抗或暴力之下的自我救赎之路。
参考文献:
[1]毛亚楠.我关注的不止是暴力本身——导演贾樟柯谈《天注定》[N].检察日报,2014.
[2]周华.简论贾樟柯电影中的侠义情怀[J].新闻爱好者,2012.
[3]尤宇翔.贾樟柯《天注定》:在信仰缺失的年代,重寻人与世界的连结[J].电影评介,2014.
[4]李泽厚,刘纲纪.中国美学史[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
[5]贾樟柯.贾想:贾樟柯电影手记[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