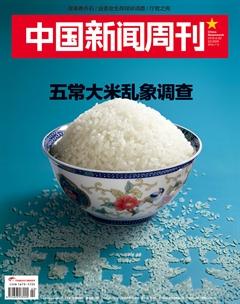“沉默”的业主
舒可心
法律、法规和政策的宽松甚至推动,并未使业主组织数量发生飞跃的变化。这背后既有外部环境的制约,也有业主群体自身的局限
改革开放和商品房制度,使得从1981年开始,中国有了第一批商品房业主群体(1981年9月,深圳东湖丽苑216套商品住宅交付使用)。从这一天起,城市管理就多出了一个新的群体——业主。他们对外反抗垄断机关、发展商、物业服务企业的侵权,对内防止互相侵犯权利。这些博弈导致各种形式的冲突不断,这就使得发展商、物业服务企业和政府不得不思考如何管理和解决这些冲突。
“以汉治汉,以旗治旗”
1991年,中国第一个业主组织的诞生(1991年3月,有190套住宅的深圳市天景花园成立了全国第一个业主管理委员会),是因发展商当初设计小区住宅和商铺用电容量分配的失误,指挥物业服务企业,利用业主群体的力量向政府电力部门转移施加压力,从而解决问题的战术胜利。但同时也开启了解决诸如“增设休闲椅和果皮箱、管理费构成等问题”的“业主自治”序幕。
这种建立以“业主”命名的组织,既从形式上与现代发达国家接轨,实际上也可以从制度设计上符合中国历代政府的执政方法。例如清代北京的旗人住宅和汉人住宅机制,就有“以汉治汉,以旗治旗”的理念和体系。这里的“以”是“利用”的意思,即利用汉族人管理汉族的住宅,而不是让汉族人自己决定自己的住宅如何使用和管理。
随后的1994年《深圳经济特区住宅区物业管理条例》中,名义上的“业主大会及管委会”便正式纳入这部地方法规之中。但该条例同时规定,“区住宅管理部门应会同开发建设单位及时召集第一次业主大会,选举产生管委会”,从而剥夺了业主们自己召集第一次业主大会的权利;还规定“管委会可聘请派出所、居民委员会等有关单位的人员担任管委会委员”。通过这种人员部署,实现对管委会产生过程和运行过程的控制。
这种做法,其实就是利用业主身份的人士组成的“委员会”,管理业主群体的“以汉治汉”的管理模式。这个委员会中各个委员的产生,与中国所有的居民委员会委员的产生过程如出一辙——候选人由政府挑选和确认,经过“选举”流程,最后被政府登记(委任)。所以仅仅是从名义上冠以“业主”或“居民”而已,实际主导者还是政府。
立法轨迹
由于业主身份的委员们毕竟更关心小区楼宇、设备、环境的管理这些价值因素,很难随时与政府愿望保持高度一致,这便导致业主管理委员会的“异化”——“我的财产我做主”的愿望便越来越强烈。
但这时的“我”是相对政府而言,主要是管委会几个业主身份的委员,不再愿意由政府有关部门做主而顽强地尝试自己做主。但这个阶段,仍然是业主中的精英分子觉醒和有强烈做主愿望的阶段。
时至2002年10月份,国务院法制办分别在《人民日报》和《法制日报》上公布了《物业管理条例》的草案全文,面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它不仅是中国第一个全国性的物业管理条例,同时也是中国第一部面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的行政法规。
此时,商品房制度在中国已经走过了20个年头,期间积累了大量的业主群体。仅一个多月时间,就整理出大小修改意见4000多条。这些修改意见中,有近一半被吸收采纳,从此也树立了中国公民参与立法的里程碑。
立法者们在过去10多年也看到,“业主管理委员会”等少数业主精英组成的小团体,很容易反过来侵犯业主利益甚至腐败和滥权,便在这部行政法规中确立了以业主和业主大会为组织核心,业主委员会仅仅为“执行机构”的组织模式,取代了以业主管理委员会或业主委员会为核心的业主组织模式。此外,业主组织活动监管模式也从由政府操办,变成了由居民委员会“监督”和“指导”。
随后,经大量业主公民参与意见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的出台,更加扩大了业主组织的自主地位。以国家最高阶位的法律地位,确定了业主可以决定包括“自行管理”和“聘请其他经理人”的物业管理模式,终结了《物业管理条例》只能由物业服务企业管理小区的行业垄断状态;立法确立业主大会、业委会可以成为业主诉讼的对象,从而给业主提供了一条法律程序化的救济渠道,从而实现对业主组织侵犯业主利益的威慑作用;立法还明确了政府对业主组织建设的服务职责,即从《物业管理条例》的“监督”“指导”转为“指导和协助”。
至此,中国住宅小区业主权利的立法和组织立法,除了业主组织在民商事活动中的法律地位的行政配套法规外,基本上已经完成。
“业委会”困境
法律环境似乎基本保障了业主组织的设立和运转,各地业主组织建设的困难程度也越来越低,政府、发展商、物业服务企业阻碍业主组织的个案也越来越少。特别如北京市在2010年推出的《物业管理办法》及相关配套文件,确立了发展商承担前期物业管理责任,即没有建立业主组织并向业主组织交接物业共用部分前,建设单位不得向业主收取物业服务费。甚至在2011年9月,北京市住建委、民政局、社会办联合下发《关于推进住宅区业主大会建设的意见》,计划到“十二五”期末,北京市争取实现有物业管理的住宅区业主大会全覆盖。
但是,这些法律、法规和政策的宽松甚至推动,并未使业主组织数量发生飞跃的变化。截至2013年9月的北京市建委官方统计数字,北京市只有956个小区建立了业主组织,占全市小区总数的26.56%,甚至还低于2011年有关新闻报道的数字,当年这一比例为28.3%!
究其原因,当然是多方面的。业主组织领袖们普遍认为,原因主要是政府中抵制业主自治的公务员和一些发展商、物业公司利益驱动导致;一些研究法律的人士认为,中国法律对业主组织建立的门槛过高,直接阻碍了业主组织的建立。
15年以来,本人从亲自参与组建和运行本人所在商品房小区的业主组织,到先后协助全国范围近百个小区业主组织的建设,认为更主要的原因来自业主群体自身。
业主组织与政府、军队、学校等组织性质完全不同,前者是“自组织”而后者是“他组织”。中国几千年的历史中,只有当饥饿或群体感染愤怒到极端严重的情况下,才会产生如农会等自组织。除了宗教之外,极少有和平状态的自组织活动。解放以后,每个人都生活在他组织当中,使得国民的自组织能力丧失殆尽。
在已经建立业主组织的小区中,绝大多数个案的组织动力都来自外部——发展商造成的普遍房屋质量问题,或物业服务企业管理水平普遍严重下降。这就应了中国的成语:多难兴邦。只有在灾难的情况下,民众才被激励起来,一哄而起。而一旦和平了,则一哄而散。
抛开组织的对外侵略目的,仅从组织对内的作用分析,则在中国民众看来,组织的作用只是用来抵抗已经或立即到来的灾难;但在西方民众的观念中,组织的作用则是防御那些未知的、但可能随时发生的小风险以免酿成大灾难。这种文化的差异,自然就导致中国的业主群体的行为模式,只要自己还能忍受,就弯腰承受,内心想着“天塌下来有大个顶着”。
这种观念带来了另外一个现象,就是即便外力迫使组织产生,也是少数组织领袖成为既得利益者,要么当官,要么发财。而多数人只是为他们做嫁衣、做筹码、当炮灰。业主委员会委员的腐败和滥权现象,就是这种文化的反映。它反过来更严重地教训着有一丁点组织热情的个体,使他们望而却步。这就使得组织建立和维系更加困难,需要更深重的压迫和更持久的积累才能组织起反抗。
不参与,是中国国民在公共事务中表现出的文化特征,也是历史上几乎所有参与者一般都无好下场的反映。“出头的椽子先烂”“枪打出头鸟”等谚语,时时深刻地提醒着每个中国人。经济体制改革开放后,“撑死胆大的、饿死胆小的”这种另一极端的唯利是图的冒险精神,也刺激了一些人为自己的利益或为群体的利益而奋斗。
成长的周期
那么,中国业主组织的前景到底如何呢?下图也许能够清晰地描绘出一些前景。
图中描述的是在不同的周期:
无组织的业主群体内部的组织动力(向上)与外部负面压力(向下)的关系,它导致业主组织建立的可能。
形成组织后的业主群体,内部的负面(成员的不参与、腐败等)与外部负面压力(均向下)和内部组织动力(向上)之间的关系,当负面压力过大时则导致组织逐步涣散直至散伙。
第一阶段,是孕育期。业主群体逐渐形成,发展商、物业服务企业对业主侵权的机会最大,往往侵权行为也最严重。这个时候,被压抑的业主们便爆发出组织起来的动力并最终组织起来。
第二阶段,是婴儿期。组织起来的业主们,具有了抵抗外部压力的能力,使得外部压力减小。但内部治理能力的压力(如无法提高业主们的参与热情和不能防止腐败等),又逐步瓦解组织自身。
第三阶段,是成长阶段的睡眠期。再次陷入无组织的业主群体,尽管不用被组织自身的内部管理问题所困扰,但外部压力自然会越来越大,直至再次刺激业主组织动力,使得业主们再次组织起来。
第四阶段,是成长阶段的觉醒期。再次组织起来的业主们,一般会总结上次组织治理中的经验和教训,找到解决自身问题的方法、对策。令组织能正常运转较长的时间。
第三、第四阶段也许会重复几次,但每次都不是与前次简单地复制而是自主治理水平能力的逐渐提高。
最后达到的阶段就是组织的成年期,随着全国成千上万不同小区业主组织对相同或类似问题(业主冷漠、领袖腐败)解决方案的互相学习,随着国家对相关瓶颈问题的立法对策的完善,最终业主群体会普遍地以组织的形式常态化存在。尽管组织治理过程中的内部压力永远都会伴随组织自身,但业主们已经找到了解决这些负面压力的办法,可以在这种压力不至于令组织涣散时,就令其终结。
用于对付业主们冷漠的办法主要有:国家法治大环境的改善;邻里间友爱、互助观念的逐步加强;降低参与(例如投票、开会等)的难度和技术门槛,将目前动辄几千户业主的小区降低至合理的300户左右;从竞争为社区服务转向抽签轮流为社区服务制度的创立和运用,也会随着社会经济发展产生人们智慧的其他结晶,不断激发业主们的参与热情。
用于对付业主领袖们滥权、腐败的办法主要有:建立监督机制;保障每个业主监督权利的行使;建立对领袖罢免相对容易的机制;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富有创造力的人们还会建立我们现在还不能想象到的其他各种机制。
伴随着建筑物自身的寿命导致其价值的降低,业主组织也自然会到老年期,甚至业主组织随建筑物的报废而寿终正寝。但业主组织的最重要作用,其实就是通过向组织成员筹集资金,对大厦进行维护,以使其尽可能延长大厦本身的寿命,即保护每个业主的财富价值。
当然,即便在公民自主治理为立国之本的美国,也并不是所有的业主群体都能很好地组织起来和正常运转。好比谁都知道一把筷子不容易被折断,但没有外部力量,一堆筷子并不会自动地成为一把!因此,政府对业主组织的指导和协助,是提高社区“自稳定”机制的重要“外部力量”。业主组织自我运转得越好,对侵权的随时自救能力就越大,侵权方就越收敛,冲突就越少产生,居民生活就越安逸,社区就越和谐,就越不需要政府的干预和操心。来自每个社区的 “自稳定”“自和谐”等 “自适应”力量,就将成为社区乃至社会的主要力量。稳定,就不再是政府的工作目标,而是社会、社区、公民们的自我诉求。其实,那一天并不遥远,只要我们开始做起,只要我们相信群体内部的力量会被外部力量激发起来这种自然规律,只要我们有一点社会责任感地去注意呵护、培养业主群体中的自组织力量的成长,这一天就会更快地到来。
一位前中国领导人说过:“我一直认为,这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但是要相信,群众能管好一个村,也能管好一个乡,也能管好一个县,这需要一个过程。”我在后面加一句:也能自己管理好自己的社区。
(作者为知名物业管理专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