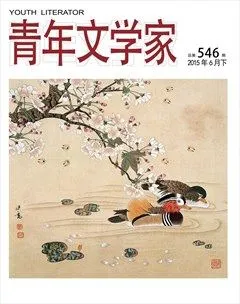《一位女士的画像》之戏剧化解读
摘 要:亨利·詹姆斯的长篇小说《一位女士的画像》因其多面性带来了多种诠释的可能。本文拟从社会学家戈夫曼的戏剧理论的角度对《画像》作一新的诠释,呈现作品中以女主人公伊莎贝尔的婚姻为中心,所上演的一出精彩表演,以期对舞台上各种角色作一个通透的展现,并勾勒出伊莎贝尔悲剧经历背后的根源。
关键词:《一位女士的画像》;亨利·詹姆斯;戈夫曼;戏剧;表演
作者简介:黎蕾(1991-),女,汉族,四川资阳人,西南大学文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是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具体小方向是中外文学与文化。
[中图分类号]:I1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5)-18-0-03
美国的著名小说家亨利·詹姆斯(1843-1916)的早期代表作品《一位女士的画像》(以下简称《画像》)历来为读者和评论家所关注,女主人公独特的形象和追求、精密的构思和语言、欧美文化融合与碰撞的体现等都引起人们极大的兴趣,因此该作品的多面性带来了多种诠释的可能。本文拟从社会学家戈夫曼的戏剧理论的角度对《画像》作一新的诠释,呈现作品中以女主人公伊莎贝尔的婚姻为中心,所上演的一出精彩表演,以期对舞台上各种角色作一个通透的展现,并勾勒出伊莎贝尔悲剧经历背后的根源。
戏剧并非仅仅在正式的舞台上演。戈夫曼的戏剧理论正是从这一视角,剖析了社会中各个场域所发生的一幕幕真实戏剧。他就他独特的戏剧语言对社会中人与人交往的行为进行分析,“充分肯定了社会体系这一剧作者及其剧本期望对表演者的决定性作用,也即承认社会结构对个人行为的制约性。”[1]就《画像》这部作品来看,各个主要人物极好地印证了戈夫曼的戏剧理论,在角色扮演的互动中,构织出了一幅戏剧表演的生动图画。
一、转变:从观众到表演者
伊莎贝尔作为小说主人公,在作品里其实是由远及近地出现的。伊莎贝尔本在美国,小说开篇是在英国的花园山庄,杜歇先生、拉尔夫以及沃伯顿勋爵在闲聊,在谈话中杜歇先生提到了他夫人即将带回国的侄女伊莎贝尔,至于这个侄女具体什么样,老人并没有给出明确的答复,只在妻子的电报中知道她“颇能自主”。这引得拉尔夫和沃伯顿勋爵兴趣颇浓,以至于伊莎贝尔到花园山庄后,他们对她的兴趣和好奇也丝毫没有减弱,但伊莎贝尔似乎并不把注意力放在要成为他人注目的焦点上,她更喜欢的是平静地、默默地观察着周围的人和事物,她“给人留下了一个印象,仿佛她经常在感受和思考着什么。”[2]可以说,这时的她是一个没有真正融入英国生活的观众,她在乐此不疲而赏心悦目地观看着英国的人情世故。然而她的本质并未发生改变,她仍然是奥尔巴尼那个善良、求知欲强的少女,姨妈带她在欧洲的游历并没有让她的本性变得更复杂,但无疑她现在面对的却是一个更加复杂的环境。
由于她的美好和独特,戈德伍德和沃伯顿勋爵都成为了她的追求者,但是她对他们的热情都予以了回绝,这更清楚地显示了她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她最珍视的是她的自由,于是她不可避免地走近梅尔夫人和奥斯蒙德设下的圈套。根据戈夫曼的理论,“在表演同一常规程序时相互配合的任何一组人”[3]被称为“剧班”。梅尔夫人和奥斯蒙德就构成了一个剧班,在他们精心搭建的舞台上进行表演,而他们邀请的观众便是伊莎贝尔。
首先要提的就是梅尔夫人,她是引诱伊莎贝尔落入陷阱的关键人物,没有她的帮助,伊莎贝尔不可能和奥斯蒙德结婚,而她的关键作用便归根于梅尔夫人这位表演者的“双重身份”以及她高明的“印象管理”技术。所谓的“双重身份”就是她既是伊莎贝尔“亲切的”朋友,又是奥斯蒙德的共谋者。然而实际上,她只是在表面上假装和伊莎贝尔在同一个剧班,事实上却仅和奥斯蒙德构成一个剧班,善良单纯的伊莎贝尔正是由于没有认清这一点而掉以轻心。伊莎贝尔经过杜歇夫人的介绍认识了这位“模范女性”,第一次见面便被她深深吸引,接触之后更是“喜欢她到了极点。”[2]因此在伊莎贝尔眼里,梅尔夫人这样可爱的朋友引荐的人也一定是很可爱的。
经过梅尔夫人的引荐,奥斯蒙德相当于得到了一张优秀证明书,于是他开始了他绝妙的表演。奥斯蒙德极力让伊莎贝尔产生一种印象,即他是一个平静、有独特艺术品位与才能、有伟大父爱、虽贫穷但高尚的孤独者。他的一切在伊莎贝尔眼里都是与众不同却符合她自由理想的。但是这都缘于他极佳的“印象管理”技术,他在她面前这样表演:
“难道你从没有过什么计划吗?”
“有过,几年以前我定了一个计划,一直奉行到今天。”
“这一定是一个很有趣的计划。”伊莎贝尔直率地说。
“一个很简单的计划。那就是尽量平静无事。”
“平静无事?”姑娘跟着问道。
“不寻烦恼——不用努力,也不必奋斗。听天由命。清心寡欲。”他说得慢条斯理,每句话之间都停顿一下,那对聪明的眼睛注视着伊莎贝尔的眼睛,露出一种决心开诚布公的神气。[2]
后来的事实证明,奥斯蒙德完全不是一个听天由命、清心寡欲的人,他对伊莎贝尔的控制、对女儿个人意志的剥夺(集中体现在帕茜的婚事上)都证明了他是一个利欲熏心的人。他在追求伊莎贝尔的时候所展现的都是他精心谋划的表演,意在给其造成一种幻觉印象,以娶得伊莎贝尔,获得她丰厚的财产。
梅尔夫人和奥斯蒙德这个“剧班”中,他们两人身上都有一些共同的特点,就是他們气质的混杂性。对于梅尔夫人,伊莎贝尔刚开始以为她是法国人,后来又觉得她像德国人,或是奥地利人,唯独没有想到她居然是美国人。其实这正说明她善于用欧洲优雅的风尚来伪装和修饰自己。在周围人看来,她几乎没有缺点,周身散发着优雅的气质和光芒。然而她只是用她通过经验获得的东西为自己编织了一件美丽的华服,以掩盖她的狡诈和野心。而奥斯蒙德则更精于这种伪装:他的“眼神显得既呆滞又犀利,既聪明又迟钝,具有观察者和梦想者的双重气质。至于他的国籍和出生地,你会觉得很难确定,那些使人一猜就着,变得索然无味的表面特征,他一概没有。如果说他血管里有英国人的血液,那么大概也已经掺进了法国人或意大利人的杂质。”[2]单从表面来看,这些表演者是几乎不可能被一眼看穿的,他们都戴上了面具,还搭配使用了道具,这使他们的演出大获成功,取得了伊莎贝尔这位观众的认可。伊莎贝尔和奥斯蒙德结婚后,梅尔夫人和奥斯蒙德的剧班没有解散,伊莎贝尔却和奥斯蒙德也组成了一个“剧班”,她从观众渐渐变成了表演者。
在梅尔夫人和奥斯蒙德表演的前前后后,其实一直存在着“剧班共谋”,它一般发生在“后台区域”,与前台相对,是不能轻易被观众看到的,然而却反映着剧班的真实情况,由于没有观众的观看,表演者可以轻松卸下面具,展现最本我的一面。小说里的后臺区域表现地并不明显,但仍能从为数不多的叙述中看出奥斯蒙德的自私和对女人的轻蔑,他对梅尔夫人称伊莎贝尔是“一件合适的外衣,”[2]然而在他对梅尔夫人的谈话中可以看出,他已经把梅尔夫人这件“不合适的外衣”从心头远远抛掉了。
实际上,伊莎贝尔并非从未窥见他们后台区域的模样,这是他们疏忽的地方,也是使她产生怀疑的开始。一次,伊莎贝尔从外归来,看到奥斯蒙德和梅尔夫人在谈话,让她感到诧异的是他们的不正常状态:奥斯蒙德坐着,作为客人的梅尔夫人却站着,但是双方没有丝毫的不自在,那种聚精会神的面对面注视的场景像一幅画般定格在她的眼眸中。其实这就恰似观众闯入戏剧后台的情况,事发突然让双方都感到震惊。在1996年由《画像》改编的电影《淑女本色》里,导演简·坎皮恩在其中添加了很多展现后台区域的镜头,使潜存的台词外化,让观众能更容易地把握情节走向和人物性格,却失掉了小说静默的艺术魅力,殊不知“空无隐含着幽深的意境,沉默潜藏着巨大的效能。”[6]这部作品的电影观众比小说读者要少很多自我创造的乐趣。
二、痛苦的面具人
与伊莎贝尔结婚后,奥斯蒙德已经得到了她的财产和一个对帕茜很善良的继母,并进而妄想也让她成为一个百依百顺的妻子。这源于他极强的控制欲,“渴望成为妻子的‘上帝,主宰她的一切。”[4]就戈夫曼的理论来说,他即是想成为他与伊莎贝尔这个剧班的中心,完完全全地取代伊莎贝尔来发声。这对于把自由作为人生信条的伊莎贝尔来说是一种极大的痛苦,但她没有选择向其他人诉苦,因为她要强的个性和决心承担后果的勇气和自尊感不允许她这样做,最终这让她罩上了一层面具,这表现在她婚后与关心她的人的交往上,她不得不做的违心的表演。
《画像》中有三位男子与伊莎贝尔有情感上的纠葛:沃伯顿勋爵、拉尔夫和戈德伍德。他们都在她结婚之后拜访她,主要原因就是看看她过得幸福与否。而她对此无一例外采取了伪装,这种伪装和梅尔夫人以及奥斯蒙德的是不同的,本意是善意的。由于拉尔夫曾经劝她不要嫁给奥斯蒙德但她没有听从,伊莎贝尔便在他面前就“始终戴上了假面具。”[2]拉尔夫发现,她永远试图给人一种特别值得羡慕的印象。她颇费心思地向他隐瞒一切,“在他们的谈话中,她永远拉上了幕布,打开了屏风。”[2]至于沃伯顿勋爵和戈德伍德,她也采用同样的策略,然而在她这一副高贵妇人的面孔下,是一颗得不到安慰的挣扎的心灵。不过后来当他知道拉尔夫对她的馈赠和关怀后,她在他面前最终还是扯下了面具,做回了真正的自己。
在帕茜的婚事这件事上,伊莎贝尔体现了她的矛盾性。这反映出她所扮演的角色与她内心自由之追求的矛盾。作为奥斯蒙德的妻子,她认为她有义务去努力从丈夫的角度考虑,但同时她又觉得这涉及帕茜的自由选择,而这是恰恰相对立的。这一点上,正如有的学者指出,“伊莎贝尔对自由的追求体现出一定的矛盾性:在追求自由和知识的同时,她并不反对社会的正统权威强加在女性身上的传统价值及道德规范。”[5]此外伊莎贝尔身上也体现了奥斯蒙德极强的控制力,她在这种影响下越来越倾向于从奥斯蒙德的角度来看问题,正像拉尔夫所说,“她代表着吉尔伯特·奥斯蒙德。”[2]她考虑着奥斯蒙德想让帕茜嫁给沃伯顿勋爵的计划,对帕茜传达她爸爸的旨意,询问沃伯顿勋爵的意见。然而由于她内心对自由渴求的火苗没有完全熄灭,因此在这个过程中她一直摇摆不定,停顿、怀疑成为了她最常见的心理活动,从而使其在行动上表现出的是一种犹豫和斟酌,所以导致奥斯蒙德和梅尔夫人对她表示了不公正的愤怒和谴责。我们知道,表演戏剧的表演者对他所扮演的角色必须要肯定,绝不怀疑自己的台词,最好能理解角色人物的心声,这样讲出来的台词才能铮铮作响,深入人心。倘若表演者对自己的角色本身产生了怀疑,对其行动和目的的正确性和合法性感到动摇,他的表演也就不干脆,会变得拖沓而生硬。伊莎贝尔由于其心底对自己作为奥斯蒙德的妻子——更确切地说是作为他的传声筒和工具——的角色性质的不认同使她的这一表演使命没有完成,没有达成“同一剧班”的奥斯蒙德和梅尔夫人的希望,遭到了合作者的谴责。(戈夫曼将这种剧班内部的合作称为“剧班共谋”)
三、物化的道具和突破隔离的局外人
正如魔术师表演魔术时需要一顶帽子才能变出兔子来,表演者在舞台上也经常需要使用道具,最高超的表演者奥斯蒙德在为伊莎贝尔上演好戏的时候也自有他独特的道具。这里且不说他所运用的优雅外表、艺术收藏品,仅分析一个特别的道具。这个道具就是他的女儿,帕茜。帕茜在《画像》中被形容为一张白纸,纯洁无暇、天真善良,然而她最大的特点还是她的服从性。因此她被物化成为了她父亲的道具。奥斯蒙德在伊莎贝尔面前表演的时候就充分运用了这个“道具”,通过他对待和谈论他女儿的方式,他极力给她塑造一种慈父的印象,在伊莎贝尔称赞他的女儿可爱的时候,他立马展现了他博大的父爱:“‘啊,吉尔伯特·奥斯蒙德像充满感情似的叫了起来,‘她是天国的一位小天使!她是我最大的幸福!”[2]以至于这些表演给伊莎贝尔这位观众产生了美妙的印象,她给他的生活构织了一幅美好温馨的画卷:“他生活在美丽如画的风景中,生活在拾级而上的山顶上,生活在整齐的意大利花园的碧草清泉中,他与他的女儿相依为命,那种既一往情深、又无可奈何的、奇异的父爱,像大自然的雨露一样,灌溉着他生活中的不毛之地。”[2]此外,由于帕茜在修道院习得了良好教养、性格也温顺友好、对伊莎贝尔颇有好感,因此小姑娘本身也对伊莎贝尔产生了吸引力,客观上也促使伊莎贝尔做出错误的决定。
除了表演者、观众、道具等要素,小说中值得一提的还有“局外人”的作用,这就是指奥斯蒙德的姐姐——格米尼伯爵夫人。在奥斯蒙德和梅尔夫人对伊莎贝尔施行他们的诡计的时候,伯爵夫人一直看在眼里,但她却没有提醒和警告伊莎贝尔,这源于她的角色定位。整件事她并没有参与,在奥斯蒙德和梅尔夫人要求她保持缄默后,她乖巧地闭上了口。戈夫曼对此做了说明:“我们常会发现,当互动必须在局外人面前进行时,局外人会知趣地以一种不感兴趣、事不关己、不予注意的方式行动,这样,即使没有墙壁或距离来获得身体的隔离,至少还可以通过习俗来获得有效的隔离。”[3]伯爵夫人作为局外人表现出了一副事不关己的姿态,为奥斯蒙德和梅尔夫人的表演提供了稳定的环境,从而保证了表演的顺利进行。然而眼看着婚后的伊莎贝尔一步步地越陷越深、痛苦不堪,伯爵夫人最终突破了局外人的角色,打破了“前台区域”与“局外区域”的壁垒,勇敢地站到了伊莎贝尔一边,揭穿狼狈为奸的奥斯蒙德和梅尔夫人的表演,拆穿他们伪装的假面具,才使得伊莎贝尔终于醒悟,使其得以果断启程看望病重的表哥。由此可见,舞台上下的角色并非一成不变,随着舞台背景的变化、情节的更迭、角色心理的转换,他们的角色可能也会发生变化,比如从观众变为表演者的伊莎贝尔和由远处的局外人转变为热心的“剧组成员”的格米尼伯爵夫人。
参考文献:
[1]青连斌.世界是一个大舞台[J].学习时报,2006.
[2]亨利·詹姆斯.一位女士的画像[M]项星耀,译.人民文学出版社,2013.
[3]欧文·戈夫曼.日常生活中的自我呈现[M]冯钢,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
[4]吴彩亚.万花丛中的毒蛇——评《一位女士的画像》中的吉尔伯特·奥斯蒙德[J].苏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8(4).
[5]陈丽.伊莎贝尔的自由观——亨利·詹姆斯的《一位女士的画像》[J].外国文学研究,2002(1).
[6]魏新俊.空白、沉寂、未言——解读《一位女士的画像》中的‘另类语言艺术[J].周口师范学院学报,2013(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