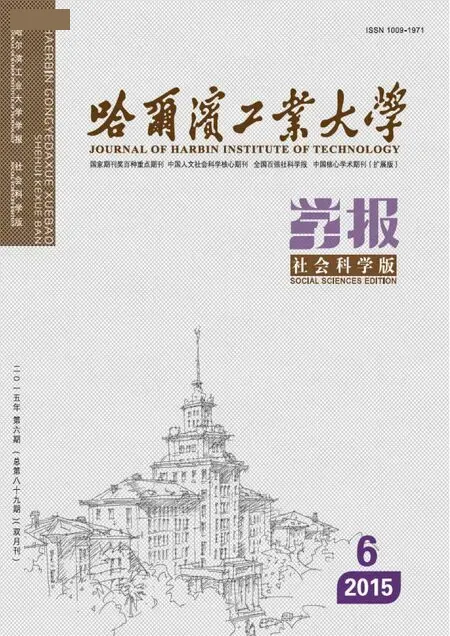社区内的权力关系重构
赵丽娜
(江苏科技大学 公共管理学院,江苏 镇江212003)
我国单位制解体后,社区承载了人的日常生活,直面人的需求,调节人的行动。作为生活展开的具体平台,居民应当成为社区运行中的核心主体和权力拥有者,即社区中应当存在这样的互动过程:“人们在社会结构的限制下,在一定的空间中行动;同时,人们可以创造和改变空间以表达自己的需求和欲望”[1]。且由于人在社区中的主体性和核心性,“合理的社区存在应是以独立于‘国家’和‘市场’之外的一个‘公民社会’存在。而这个社会应是在不违背法制之下的一个自治空间”[2]。对此,我国于2002年的中共十六大上,明确提出“完善居民自治,建设管理有序、文明祥和的新型社区”[3]。这说明社区的良性运转依赖于自治基础上的内部权力在主体间的合理分配和平衡,这是将社区建设成为生活空间而非单纯居住空间的必要条件,也是建立起有效关系网络和形成居民归属感的必要条件。也就是说,这样的一个空间,社区秩序的建构不仅仅是一个外部力量介入的结果[4],以内部居民为中心展开的社区内不同行动者之间的互动及互动基础上的权力关系的结成,对社区秩序建构而言更加重要。
然而,大量事实表明,目前社区运行还没能够以“自治”为基础,这导致了社区成为独立于其真实主体“人”之外的一个机构设置,而不是生活性的“空间实体”,其直接后果不仅仅是社区预设的服务功能无法实现、居民现实需求无法得到满足,更使得我国新改革观的推行受阻。我们看到,“新改革观”尤其“把改善人民生活作为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关系的结合点”的提出,客观要求社会治理要以人的生活为导向并进一步调整。而社区作为人生活的真实场域和政府的神经末梢,它的治理状态直接反映也影响了社会治理的进程及方向。我国城市社区治理过程中的权力主体的外部性特征,使得居民主体缺位导致公民参与性差,并引发了社区内部关系网的脆弱性和某种程度上的敌对性,进而致使整合性缺失。于是,社区无法成为真正意义上的生活空间,更多地体现为“空壳“下的形式主义运转,其社会性难以建立,其对社会整体发展的消极影响不言而喻。因此,在国家对于社会治理的空前重视以及构筑宏观治理体系的背景下,社区治理成为一个时兴而现实的议题[5]。基于此,可以说研究如何重新建构社区内的权力关系具有重要意义。本文正是在此背景下展开。
一、社会转型提出居民占据社区权力主体地位的客观要求
在社会转型过程中,经济的转型和政府角色的转型共同规约了城市社区运行的新条件是居民的参与及自治热情。应当说,城市社区运行中社区居民公共事务参与的迫切性是我国社会转型的结果。
经济体制的转型导致社区角色转变,进而提出了居民参与社区事务的现实需求。曾经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社区仅仅作为“居住空间”而存在,人们生活中繁杂的需求由“单位”予以解决,此时社区是一种地域性的空间概念。但是,随着经济的转型,“强单位”关系逐渐解体,政治认知上大量的“单位”人向“社区”人转化,原来由单位承担的责任逐渐转移到社区。人们现实生活中的各种需求直接面向了城市社区,于是,社区不再局限于单纯的“居住空间”,而成为了“生活空间”。这种生活空间“超越了单纯的地理界定……而变成了一种蕴含精神性的存在”[6]。“我们在空间中居住、描绘自我、消磨生活和时间、创造历史。这个空间是多样繁杂的[7]”。因此,伴随经济结构调整城市居民生活的社区化直接提出了其参与到社区事务中的现实要求。为了获取更好的生活满足,他们不仅需要表达自身的需求,而且要求能够监督与制约社区内其他权力集团的运行[8]。
政府职能转变直接呈现了社区居民在社区运转中的主体权力地位。2004年,提出“努力建设服务型政府”。此后,“服务型政府”的建设广泛铺展开来。2008年3月,在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再次强调:“健全政府职责体系,全面正确履行政府职能,努力建设服务型政府。”随着“服务型政府”建设的展开,政府由原来的管理者转向服务者,这意味着政府的功能由以往大包大揽转向公共产品的供给及社会引导和协调上。在社区层面,政府的职责应当定位于公共产品及服务的供给及内部关系的协调、整合。而服务显然因需求而存在。对于社区而言,作为居民与政府联系的中间纽带,其面向群众的服务与居民真实需求的契合程度直接表征了服务型政府的建设水平与阶段。这就要求转变传统的“社区强势行政管理与社区参与的低迷状态”[9]53-57,激励居民参与到与政府的协商、互动中,并成为社区治理中的重要主体。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居民对社区工作的评价被用作衡量社区治理效应[10]。
二、社区现实运行中的权力主体单一性及其后果
在社区运行中的恶性循环模式,导致居民难以介入社区运行中。管理权的外部性导致居民主体的参与性缺位。虽然早在198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居民委员会组织法》就已规定:“居民委员会是居民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的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11]”。这导致社区事物决策权来自社区外部的行政部门而非内部的民主决议。直接的结果是社区工作人员的向上负责。在社区管理与运转的实践过程中,社区工作人员的主要任务没能真正落实到为满足内部居民的生活需求而提供各项服务与帮助上,他们绝大部分的工作任务是完成上级指派性行政工作。这些工作往往是上级政府为了进行各项行政统计或事物性责任而分派的,与社区居民的现实需求关系并不密切。大量的工作时间用来作为上级政府部门的“腿”去行动,导致“社区居委会承担条条块块的行政负担逐年加重,城市基层社区已被同化为一个‘行政社会’,无暇顾及自治事务以及向居民提供公共服务和管理”[12]。
上级政府在决定社区具体工作时,基本思维模式是自上而下的,即社区工作人员的一切职责是由上而下下达的,社区向居民主体提供的服务事项均由决策部门内部讨论决定,这就导致居民在社区工作中被边缘化。由于缺乏畅通、有效的自下而上的意愿表达途径,作为真正的服务对象,社区居民不仅没能够成为社区工作的受益主体,而且也无法有效参与到社区决策过程中。甚至可以说,在事物决定过程中,居民的权利处于被排斥状态。这种单向运行模式直接的结果是没有将居民纳入决策体系内部,使得居民对社区而言由应然的主体变成了实然状态中的“他者”。也正是由于“我们的基层政府不是真正的服务型政府,仍然缺乏社区居民正常表达利益需求的渠道、途径及解决机制,给社区的和谐稳定带来极大的威胁”[9]53-57。
大包大揽的政府职责定位实际将政府禁锢在了一个无法脱身的牢笼中。政府不停地疲于应付各种微观层面工作而难以将自己解放出来进行宏观调控与指导。缺少了解居民需求的实践工作而造成的单向思维,加之长期的大政府运行模式,导致在社区层面政府无法客观而正确地衡量自身职能,也缺少推进社区内部权力合理分配的基础认知,从而也切断了居民参与的热情和市场进入的可能性。因此,社区的服务供应与居民需求几乎无法契合。2010年对哈尔滨市P区的社区工作进行调查的结果也证实了社区服务供需错位的真实状况。
从需求情况来看,针对社区居民的问卷调查结果中,对“您认为下面所列事项中,实用性最强的服务事项是什么?”这一问题的回答结果如表1所示:

表1 社区居民认为实用性最强的服务事项
从表1可以看出,目前社区居民认为各种事项的咨询服务实用性是最强的。这个调查结果再一次证实了上面老年人服务在社区居民需求中的强烈性。
从供应情况来看,2458份有效社区工作人员工作日志整理结果如图1所示:

图1 社区工作人员工作事项频率统计
从图1可以看出,社区提供的服务中发生频率最高的是“其他”服务事项(发生频率332次),这其中针对居民服务的事项68项(包括了送对联、走访上访户、对居民进行慰问等),剩余的所有其他服务事项(263项)都是上级指派性的工作,包括开会、画图、整理好人好事、工作述职、登记动迁、维修电脑等等。在问卷设计中,考虑到有上级指派的工作,我们设立了“辅助调查”(即辅助上级部门或其他部门展开社区内的问卷发放,入户调查等工作)这一选项。那么将“辅助调查”和“其他”项中从非居民需求的服务加重发现,在2468个事项中,非居民服务性工作的总量为328项。在事项分类中,计划生育和社区党建工作在某种程度上也是上级指派的,而社区党建工作172项,人口与计划生育工作134项。由此可以认为,社区工作中完成上级指派给你工作的内容约634项,占据了所有服务事项四分之一多。这说明社区工作人员很大的一部分时间被上级指派的工作占据。并且在图1中可以看到,缺少居民们迫切需要的医疗服务。
目前社区的服务提供和居民对服务的需求之间的契合性并不好,社区的工作安排并没能够完全从社区居民的需求出发进行配置,这也说明社区服务与居民之间出现了鸿沟。
三、公民社会原则下的社区权力重构路径
权利主体的单一性和政府的大包大揽导致社区运行中服务供应的无效性。而这,无论是对整体社会治理而言还是对服务型政府建设而言,都是一个阻碍因素。权力关系的重构是解决这些问题的有效途径。我国有学者指出,要走出“行政社区”,构建“公民社会”[13]。倡导在建设自治社区、探寻民众的社区事物参与实现方式时,“公民社会”应当成为首选原则。原因在于其对底层民众的关怀、对人合理自主性的倡导、对自治社区独立性的肯定而能够形成支撑社区空间内在实体的丰盈。实现这一原则下的权力重构必须实现如下转变:
(一)将权力的分配由“政府”一元主体转向“政府——公民”二元主体
“公民社会的精髓之一在于鼓励社会共同体成员参与公共政治生活,尽管每一个人在其中并不同等地参与”[14]。而这一权利分配格局的形成有赖于两个方面:“一是国家对社会公共空间的让渡和社会赋权;一是公众对公共空间的争取和公民精神的培养”[15]。就我国目前的社区运行状况而言,国家权力的让渡和向社会转移是首要的。只有权力的让渡才能够为居民参与提供必要的空间,才能够为居民参与创造可能性,进而才能够刺激居民的参与欲望与参与主动性。因此,二者应当存在一个先后的关系,但是时间的间隔尚需进一步合理设计。
(二)将权力主体由外部转往内部,实现由他治向自治的转变
伴随着“政府——公民”的二元权力主体确立,同时要进行权力内部性的转化。一方面,在二元主体确立时,居民的参与性需要得到法律的保障和内部的一致认可。只有居民有效参与才能够确保居民真实需求的表达和实现,才能够实现社区空间的“自治”性,才能够建立起“公民社会”原则下与政府相对应的独立社会。另一方面,政府要转变对社区居民的身份认知,将其由政府管辖的“他者”变成政府服务下的“我们”。只有能够完成这样身份外部性向内部性的转化,才能够真正确立政府的“服务意识”,从而确保在二元权力主体的运作过程中,找到最佳的目标结合点。
(三)将权力主体的结构关系由管理与被管理转向协作
“在公民社会里,组织具有一定的自主性和自主性利益”[16]。“组织是:(1)怀有某种目的的人群;(2)群体中相互作用的人群;(3)运用知识和技能的人群;(4)有某种结构的活动整体,即在特定关系模式中一起工作的整体”[17]。以公民社会为价值原则的社区,权力主体中的每一方都可以称为组织,包括:以公共利益为工作目标的政府组织;以群体生活利益为目标的居民组织。这些组织在不危害他人利益的前提下应当是具有自主性的,同时在权利体系中彼此间的关系应是合理自主范围内的相互协调和监督的,而非一方独大的模式。政府权力一方独大产生的社区运行问题已经鲜明体现,而居民群体一方权力独大的问题可以想见:由于社区内的居民所想到的是本区域范围内的群体利益,不具有更宏观意义上的公共性和利他性,而且社区居民不具有公共产品供应的能力,因此当居民群体一方权力过大时直接的后果可能是不同社区间的冲突及内部“熵”的不断增长。
总之,我国社会转型的宏观背景直接提出了社区权力结构体系中居民群体作为参与方介入社区管理和服务供给的工作安排中。但是现实的城市社区运行机制明显滞后于社会的现实要求,由于当前我国城市社区管理中的一元权力主体现状,导致了社区居民生活需求无法得到良性的满足,也导致社区居民与政府间的关系产生错位。为了推进社区的发展,必须进行权力的重构,而有价值的制导性原则是“公民社会”的原则,在这一原则的规约下,社区应当转向“政府——公民”二元分配的权利结构,并且政府与居民间的关系需要由他者转向我们。
可以说,社区是生成公民社会的微观社会空间,而公民社会也是推进社区发展的指导性原则。在“公民社会”的制导下,社区能够真正建设成为有归属感的“生活”空间。同时,社区权利关系重构还具有更宽层面的拓展意义,包括:政府解放,制度转型实践成功,为建设“福利性社会”提供更多的时间与财务支持。社会结构重新安排,使得金字塔型的政府向扁平型社会结构的转变,人、政府、其他组织之间是平行互动的相互建构关系。人呈现真正的自我价值。人最高的价值需求是能够感受到被尊重。当社区秩序重构后,由于参与性的提升,自我建议的回馈渠道畅通,人的被尊重感增加。这样人作为核心的发展才有了实质性的体现。
[1]陈伟东,舒晓虎.社区空间再造:政府、市场、社会的三维推力——以武汉市J社区和D社区的空间再造过程为分析对象[J].江汉论坛,2010,(10):130-134.
[2]黄晓星.社区运动的社区性[J].社会学研究,2011,(1):41-2.
[3]十六大报告“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局面”[G]//江泽民文选: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554.
[4]陈薇.空间——权利——社区研究的空间转向[D].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8:4.
[5]王处辉,朱焱龙.社区意识及其在社区治理中的意义——基于天津市H和Y社区的考察[J].社会学评论,2015,(1):44-58.
[6]HENRI L.The Production of Space[M].New Jersey:Wiley-Blackwell,1992:1-3.
[7]SOJA E W.Postmodern Geographies:The Reassertion of Space in Critical Social Theory[M].Merseyside:Verso Books,1989:17.
[8]陈柳钦.城市社区功能研究[J].重庆工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10):57-64.
[9]贾秀兰.论社区转型与社区运行机制的重建[J].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6).
[10]陈捷,呼和·那日松,卢春龙.社会信任与基层社区治理效应的因果机制[J].社会,2011,(6):22-40.
[11]徐祖荣.社区治理中的政府定位——以杭州市为例[J].城市问题,2006,(6):79-83.
[12]李晓壮.城市社区治理体制改革创新研究——基于北京市中关村街道东升园社区的调查[J].城市发展研究,2015,(1):94-101.
[13]陈云松.从“行政社区”到“公民社区”——由中西比较分析看中国城市社区建设的走向[J].城市发展研究,2004,(4):1-5.
[14]李友梅.社区治理:公民社会的微观基础[J].社会,2007,(2):159-169.
[15]周永康.社会控制与社会自主的博弈与互动:论社区参与[J].西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7):98-103.
[16]潘修华.论中国公民社会组织政治参与的建设问题[J].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9):31-36.
[17]朱国云.组织理论:历史预流派[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1997: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