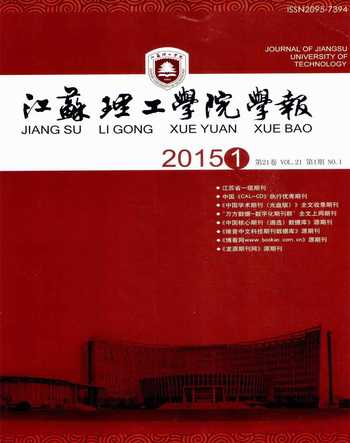试论作为世界观的语言对翻译的制约
解薇
摘 要:语言反映一种世界观,持不同语言的人,其思维方式和世界观亦不同,这种差别在东西方语言之间的翻译中表现得尤为突出。汉语重意念,偏向于综合思维和形象思维;印欧语言重形式,偏向于分析思维和抽象思维。翻译的艰难就在于要跨过另一种语言的樊篱,真正成为另一个民族的说话人,获得这个民族人与人之间对话的无限可能性。
关键词:语言;世界观;翻译;文字
中图分类号:H315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2095-7394(2015)01-0013-04
法国翻译学家乔治·穆南在《翻译的理论性问题》一书中提到欧洲新洪堡特派关于语言与世界映象的观点:每种语言都以其特有的方式表现客观世界,即使是相似的两种语言,也不可能以完全相同的方式分析同一客体,语言即代表一种逻辑,代表一种世界观。因此,从一种语言跨越到另一种语言,同时,也意味着逻辑形式与世界观的转变。这一论断无疑将对翻译的限度问题产生影响。
一、“言”为其“观”
法国哲学家马松-乌尔色认为:“任何一个人类社会的逻辑推理方式都受其语言句法的影响。”马塞尔·柯恩也指出:“每个民族的语言句法都揭示了这个民族的逻辑。”[1]48对此,布龙菲尔德举出古希腊语法和哲学的例子:“古希腊人只研究他们自己的语言,他们认为希腊语的结构代表了人类思维甚至世界秩序的普遍形式。所以他们进行语法分析,并用哲学术语将其提出,但仅仅局限于一种语言。”[1]49本韦尼斯特更是明确指出,亚里士多德等人提出的逻辑概念,不过是将希腊语特有的语言概念转换成哲学术语罢了。马丁内在《语言的任意性》一书中也说道:“我们将看到,我们所说的语言对个人世界观的决定作用达到了何种程度。”[1]50
语法学家们一般认为,语言的形式就是语法的变格变位形式。洪堡特则认为,语言形式不是来自外部交流的需要,而是来自内部认知的需要,语言的作用是将特定民族的人所感知的经验材料分类或范畴化,从而将世界纳入一种特定的秩序。它决定了人与事物的关系、人对事物的态度以及人对世界的认识。“每一种语言都包含着一种独特的世界观……人从自身中造出语言,而通过同一种行为,他也把自己束缚在语言之中;每一种语言都在它所隶属的民族周围设下一道樊篱,一个人只有跨过另一种语言的樊篱进入其中,才有可能摆脱母语樊篱的约束。”[2]76正因为每一种语言都包含着某一民族特有的概念和思考方式,所以接触外语就是接触一种新的世界观,或者在已经形成的世界观里建立一个新的立足点。翻译的艰难就在于要“跨过另一种语言的樊篱”,真正成为另一个民族的说话人,获得这个民族人与人之间对话的无限可能性。
海德格尔曾经以希腊词physis来说明翻译的限度。希腊人称存在事物为physis,这个基本的希腊词通常被译作“自然”,它来自于拉丁语对physis的翻译:natura。然而,“希腊人不是通过自然现象了解physis,而是通过其他途径:通过对存在的一种基本性的诗与理智的体验,他们发现,他们不得不称之为physis的东西。正是这一发现,才使他们得以窥见严格意义上的自然”[3]77。在希腊语中,physis不仅指天、地、动物、植物,还指人和人类历史,以及“从属于命运的众神本身”,指“受其支配出现的力量以及受这种力量支配的存在”[3]78。一经翻译成natura,physis的本义就被狭隘化了,其哲学涵义也被曲解了。海德格尔认为,这种曲解同样存在于其他语言对希腊哲学的翻译。语言具有人性意义,说不同语言的人具有不同的民族性;语言是“存在的家园”,不同民族的人居住在完全不同的“家园”中。因此,不同民族语言之间的翻译,其误解和遮蔽时不可避免的。尤其在面对东西方语言之间的翻译时,这一困难表现得更为突出。
二、“形”“意”之别
汉语与所有的印欧语言之间存在着显著的差异,中国的语言文字在世界上独一无二,自成体系。洪堡特认为,汉语将其语法元素的主要功能付之于意念作用,也就是思维,只剩下为数不多的虚词、小品词和语序来组织语法形式,需要靠敏锐的心智来捕捉和补偿语法形式的缺乏,完成言语中的形式链接。[4]230这种特点使得汉语只需凭语言本身来充分表达思想,而不必借助于语法形式。
试以玛格丽特·杜拉斯的小说《英国情人》中的一个片段为例,来比较一下原文与汉译的不同。
Le recoupement ferroviaire a permis de découvrir que les trains qui transportaient ces débris sont passés,quelle que soit leur destination,en un même lieu,à savoir,le viaduc de Viorne.Etant établi quils ont été projetés dans les wagons à partir du garde-fou de ce viaduc,il est donc probable que le crime a été commis dans notre commune.
从铁路交会的情况来看,我们发现带有这些残骸的列车,不管其目的地是哪里,全都经由一个地方,这个地方便是维奥纳的高架桥。鉴于这些肢体残骸是越过高架桥栏杆抛进车厢的,这次凶杀案的案发地点很可能便在我们镇上。
首先,从形态上来说,汉语的词没有形态的变化。汉语名词和形容词没有阴阳性、单复数之分。撇开“性”的概念不谈,“数”的概念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语境,或者通过附加数量词、助词等词汇手段来表达。语段中某一名词是否暗含复数,有时需要靠上下文来判断,这就是一个意念问题。汉语动词更加不存在变位、时态、语态和语式的变化,这些概念主要也是靠词汇手段来表现的。如法语原文使用“quelle que soit leur destination”这一虚拟式来表示让步关系,汉语译文则通过“不管……都……”这组关联词来补偿这种语式的空缺。同样地,法语中表示假设、推测、推想、疑虑、疑惑、惋惜等情态的语式也可以通过汉语中的副词如果、倘若、也许、即使、本该、理应等来表达。可见,法语的语法结构主要表现为词的形态变化(名词、代词、形容词的性数变化,更重要的是动词的变位、时态、语态和语式变化),以及“主语+动词+宾语或表语+补充成分”的提挈性搭配。而汉语的词并不具备形态变化的功能,汉语的主语也并非不可或缺,主语与谓语之间的关系相对松散,不存在固定的主谓宾结构,更不存在性数一致的问题。更多情况下,主语只是一个话题,其余部分则是表述话题的述题,话题和述题都是某种意念的组合,与法语规范的句子结构有很大的区别。
再从语义上来讲,法语的形态标记对句法结构有着很强的提示功能,而句法结构又对语义起到了极大的提示作用。不管是多么冗长繁复的句子,只要抓住形态标记和关联词,就可以分析出句法结构,进而获得句义。例如,上述法语原文的第一句话,这是一个相对较长的句子,但只要抓住变位动词a permis和关系代词que,就掌握了句子的主要结构,再加上从句和补充成分,就能分析出句义。语言的形态机制为译者提供视觉上的句法结构提示,使译者凭借句法结构分析出语义结构,形成从句法结构到语义内容的模式。而汉语不具备充足的形态标记,不能为译者提供视觉上的句法结构提示,汉语的语法是隐含的,句法结构是模糊的,所以译者通常是先获得意义,根据意义来建构语法结构,并以这个结构为参照,转换为目的语,形成从语义内容到句法结构的模式。关于东西方语言的这种结构差别,周方珠在《翻译多元论》一书中说到:“英语是以抽象字母为基础的表音文字,而汉语则是以象形文字为基础的表意文字:前者的句法结构侧重形合(hypotaxis),后者的句法结构侧重意合(parataxis);前者结构缜密严谨,各个部分之间通过关联词丝丝入扣地连成整体,后者结构松散灵活,各部分的连接靠的是语义与逻辑。因此,英汉互译中首先要解决的便是形合结构与意合结构的相互转换。”[5]38
正如洪堡特所言,“每一种语言都包含着一种独特的世界观”,因而汉语与印欧语言的差别也反映在思维方式上。语言和思维是人类表现原始生活经验的两种方式。一个民族的原始生活经验决定了该民族的语言表达方式,而语言表达方式又同时规定了该民族的思维方式。就原始思维的发生而言,语言的选择就意味着思维方式的选择。当然,思维方式反之又对语言表达方式产生影响。东西方思维方式的差异主要表现为:综合思维与分析思维之别,以及具象思维与抽象思维之别。从上文法语与汉语的对比中可以看出,法语注重形态的变化、结构的严谨,从词形、句法结构入手分析句义,环环相扣,体现出典型的分析思维;而汉语结构松散,没有词形的变化,着眼于整体而非局部,着眼于功能属性而非具体结构,要理解其句义,不能靠层层分析,而要靠总体感悟,这就是综合思维。法语等欧洲语言的文字是以抽象的拉丁字母组成的表音文字,加之尚思的古希腊哲学的影响,便逐渐形成了抽象的思维模式;汉字以象形为基础,凸现简单的物象,或在象形的基础上辅以符号,体现了具象思维的模式。译者除了关注原文的语境内涵,还要照顾到东西方语言在思维方式上的差异。
三、“言”“文”之争
语言离不开文字,文字不仅是记录语言的手段,更是看待语言的一种方式。汉字与印欧语系的文字看待其各自语言的方式是不同的。孟华在《汉字:汉语和华夏文明的内在形式》一书中将人与人之间的交流定义为两种范畴:有声性和在场性属于“言”的范畴,无声性和不在场性属于“文”的范畴。印欧语系的表音文字有声性强,是偏重于“言”的符号系统,而汉字等表意文字无声性强,是侧重于“文”的符号系统。一种文字以“言”的方式来看待自己的语言,即为“言本位文字观”,以“文”的方式来看待自己的语言,即为“文本位文字观”[6]15-20。表音或表意,言本位或文本位,不是一种纯偶然的历史选择,而是不同民族的文化传统与实践的体现。言本位和文本位本质上就是一种文化,一种世界观。“文的方式与传统、稳定、典籍、精英、雅文化、官方意识形态有关,言的方式与现实、变化、面对面交流、大众、俗文化、民间意识形态有关。”[6]3
被视为西方文化之骄傲的拉丁字母,其产生与演变经历了古埃及的象形文字——中东腓尼基字母——古希腊字母——拉丁字母这样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当古埃及象形文字被腓尼基人借用为表音字母时,象形字体中的表意动机和意象就被切断了,变成了一个抽象的记音符号系统。“当人们开始用一个书写符号代表一个音位时,他们不过是把自己对语言系统的直觉知识变成自觉知识。”[7]370也就是说,表音文字是为语言而创制的,是对语言进行分析的产物,是一种自觉的符号创制。与之相反,汉字是由本文化内部产生的,从未受其他文明的影响,它不是为汉语而创制的,不是语言分析的产物,而是视觉符号与听觉符号综合的结果,不像表音字母那样依附于语言。“当文字与意义联系的时候,它的图像性增强,成为一种超时空的不完全依附于口语的自立的体制。……维系了中华民族几千年言语异声的统一,传承了文明古国一代代绵延不息的文化。”[8]58
汉语表意文字相对于印欧表音文字的特殊性,及其所包含的文化与世界观的差异性,也成为制约翻译限度的一个重要因素。关于这一问题,曾有汉学家作过尝试和探索。埃兹拉·庞德将汉字分解成图画元素,并神往于由此发现的意象。如《论语》中的一句“学而时习之,不宜说呼”,“习(習)”字可以分解成“羽”和“白”两个元素,庞德抓住羽毛的意象,将这句话译为:“学习中季节飘飘飞去,不也是一件高兴的事吗?”诚然,这不是准确的翻译,但不失为一项有意义的尝试。对这个句子,汉学家乔治·肯尼迪(George Kennedy)的解读则更为机智,他说到“习”字前面还有个“学”字,这样重复的意思是指:除非不断地付诸力行,否则学习就是徒劳。[9]35
四、结语
洪堡特关于语言与世界观的看法对今天的翻译理论与实践仍有着深刻的启示。语言在其本质上具有人文性,人的根本属性是其语言性,语言对于人的世界观具有根本意义。不同的语言作为不同民族的生存世界,是人类文化的巨大财富,但语言深刻的民族性对文化之间的相互了解又是巨大的障碍。于是,翻译就显得尤为重要了。德国学者伽达默尔认为,译者必须首先成为源语言的一个“说话人”,而成为“说话人”就意味着他必须获得源语言中人与人之间对话的无限性的内容。因为一种语言形式平面地交换为另一种语言形式后,源语言的背景和言外之意都消失了,这些潜在的元素只存在于源语言中,拒绝异族语言的代替。在这个意义上,翻译的限度也就是语言的民族性的限度。
参考文献:
[1]Georges Mounin.Les problèmes théoriques de la traduction[M].Paris.Gallimard,1963.
[2]姚小平.洪堡特——人文研究和语言研究[M].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95.
[3]海德格尔.人,诗意地安居——海德格尔语要[M].郜元宝,译.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1996.
[4]Wilhelm von Humboldt.On Language[M].trans,Peter Heath.Cambridge.CUP,1989.
[5]周方珠.翻译多元论[M].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2004.
[6]孟华.汉字:汉语和华夏文明的内在形式[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
[7]弗罗姆金,罗德曼.语言导论[M].沈家煊,译.北京: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1994.
[8]申小龙.人文精神,还是科学主义?[M].上海:学林出版社,1989.
[9]张隆溪.道与逻各斯[M].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6.
责任编辑 徐 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