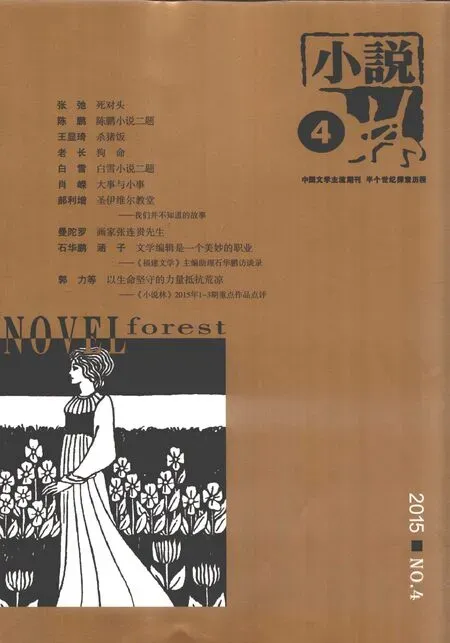白雪小说二题
私密空间
——起初,相识在未来。
将来,我的客厅要涂成苹果绿——原来银白这么刺眼。
女人默默的沉思。
仰头,
第一重天是镶嵌了花岗岩的特殊金属网,
第二重天是翻滚的熔岩,
第三重天是海绵和水雾,
第四重天是清冷的湖波和透明眼球的鱼,
第五重天是沙漠,荆棘和蝎子,
第六重天是风,晚霞,雨和苍穹,
第七重天是星和微粒。
她站在螺旋楼梯上,周围是银光闪烁的四壁,楼梯连接黑质白章的大门和地板。楼梯上,大厅里,空无一人,那些把她带到这里的人,也不知什么时候消失了。可能是在她四下打量,或者走神、想客厅的时候。
为什么带她来这个地下室?
她迈下最后一级台阶,“当”,鞋跟撞击地面。
没有回声,因为房间太大,到处都很光滑,没有颜色,没有秘密。
“你好。看来,你是来得早的。”一个男人的声音在她耳边响起,她惊愕地转过身。
他,西装革履的人。温和地微笑着,模样不难看。
莫名其妙的,她的心情忽然愉快起来,轻松到没留意这种心情的变化。她说:“这里好静,似乎全世界都烟消云散了。”没必要问名道姓,宛如老友重逢。
他说:“是的,不过很快就会热闹。这里将塞满人。”
她笑着问:“为什么?”
他伸出手,一只手指慢慢地按在她微微张开的嘴唇上,低声说:“嘘——这是秘密。”
他看到她眼中的疑惑和失落。她被陌生人带进沙漠,钻进连绵沙丘下,这个她一辈子都梦想不出的地方。她必须知道前因后果。
光线从隐秘之处散射而出,弥漫在空气中,照亮她微俯的头,鲜红的水果香甜钻进他的中枢神经,循着气息,他找到她柔软的发丝,更加柔软的脸和一滴孕育在眼睛里的同样柔软的泪珠。
他的心软了,酸了。他说:“以后,你会住在这里——这里,其实是个避难所。所以还会有很多人,都住在这儿。会非常拥挤,他们将让这里塞满人,多一个人,就多一种延续物种的希望。

插图:王艺雯
“因为,有外太空的不明生物即将袭击我们。以我们目前的科学手段还不足以消灭他们,除非,我们引爆所有的核弹,跟它们同归于尽。不过,首脑们会秘密地留下生命种子,将来出去重建家园。你是被选中的,你该感到庆幸。”
她说:“那我的父母,爷爷呢?”
他用力握紧她的手。
她说:“还有我的朋友。我的狗,就要生宝宝了。”
他说:“其他人到来的时候,千万不要跟他们说,我告诉你的话。这里是不能骚乱的。另外……我也是有父母的。”
没有钟表,不知道过了多久。
他们坐在地板的白色方块上,她靠着他。
她说:“我的那套《追忆似水流年》还没看完,它放在床头柜上,台灯边,还有一杯我喝了一半的茶,不倒掉,再过几天一定会长霉。”
他说:“普鲁斯特,没必要看完。一段一段地看就可以。虽然以后的事怎么安排还没有具体通知,但我想,很快就会步入正轨。”
她说:“这么说,一切都已经决定了?这就是命运。”
他说:“不要再想过去了。你将开始一种全新的生活,这样想,不是很兴奋吗?”
她惆怅地说:“如果,我们是在咖啡厅认识的。你可以到我家做客。我的小狗不认生,对朋友都很亲热。而且我会做很好吃的黄瓜汤。”
他笑着说:“我只会做煎蛋吐司,经常炸糊。”
她也笑了,说:“其实,我的厨艺也不好。哦,对了。我的客厅的墙是淡蓝色的,我一直想把它涂成绿色。”这里的墙到处闪动银色荧光,除了地板上寂寞阴沉的黑色方块,只有他们的投影是丰富多变的灰色。
他问她,说:“以前,你是做什么工作的?”
“不要说过去了。”她转过脸,望着螺旋楼梯说,“为什么还没有人来?”
他说:“等到塞满人的时候,你就不会这么问了。全球有一百亿人口。他们要仔细挑选。”
她说:“为什么挑上我?”
他说:“我不在最高决策层,我只负责地下的事。不过,如果是我,我挑人的原则将是只挑瘦子。胖的占的空间大。”
她觉得他的玩笑很惨淡,她说:“好吧,除了这个大厅,还有什么?能不能让我看看我的房间。也许我会放点小东西。”
他严肃地说:“没有房间。除了大厅,还是大厅,我们不能浪费空间。”
她说:“这样的大厅遍布全球,彼此相连?应该,又能保障有效隔离,免得某个地方出意外。在我们头顶,是沙漠。另一个大厅的上方,也许是繁忙的巴黎地铁。”她心想,很快就不会繁忙了。可是真的没有个人空间吗?
她说:“我想跟爸爸妈妈死在一起。我想出去。”
他同情地说:“你决定不了什么。”
她咬住嘴唇,流露出无限哀愁。
他心血来潮,解开衬衣纽扣,掏出一个坠在银丝项链上的古香古色的心型小盒子,打开,金丝绒上躺着一颗银耳钉。他捏起耳钉,轻手轻脚地给她戴在耳垂上,说:“你在上面。出生,读书,上班,下班,在某个特别时刻死去。你真的以为你的生活掌握在你的手里吗?你不过能决定下午茶买小圆饼干,还是长面包而已。好了,你来的一定很匆忙,什么都没带来,不过,女孩子到什么时候都需要一点小首饰。”
突然,他像是想起了什么,拽着她,把她领到大厅一侧,掀起一块地板,露出一个圆圆的窄洞,洞底是片朦胧的白光。
他急促地说:“快点跳下去,快点。”
她却问他:“你要我去哪儿?”
他说:“这下面是一个比较舒服的大厅,安排在那的人比较少,而且还摆有植物。我让你去是滥用职权了。不过,大家都是陌生人,没人会盘问你的。要是有人问,你就说,一开始就被带去下面。”
她失望地说:“不过是地下室的地下室。”
他为她思维的迟钝而恼火,说:“那里要舒服得多。一旦有人来了,我就不能这么方便地送你去那里了。”
她眼波闪躲着,低声说:“你什么时候去?”
他说:“我不能去,我要在这里维持秩序。这儿很快会乱成一锅粥。”
她固执地说:“那我也不去。”
她话音未落,他已经抓住她的肩膀,把她提起来,扔进洞口,她的身子在迅速滑落,仿佛砸在牛顿头上的苹果,同时心灵产生一种奇妙的悬浮感,飞舞着在空气里签名留念的花瓣,四周,白色、银色和浅灰的亮点被瞬间拉长,成了一条条流线。她只听见他的声音追着她坠落。
“记住我。”
她不能给他画上小圆圈,不能休止,因为他还在说话,应该是告诉她他的名字。只是那声音变成了毫无意义的——
“嗡嗡嗡,嗡嗡嗡……”
也许她明天又能见到他,露出真正的老朋友式微笑,也许在几个月以后,也许几年。
她,还在飘浮中降落。槐花在湿润的晨风中飞旋。
她记得放射污染要五十年才能消除。到了重见天日的时候,她已经是老太婆了。而他,看起来比她大很多——不知道他们是不是能活到那一天!
而且,不知道那些乘坐太空船来的奇怪生物是不是真能被消灭?
她明白了,他已经跟她的亲朋好友一样,在她的生活中消失。
他的笑,优雅的绽放,随即成为过去。
时间是一条线
——建元十八年,大将吕光领兵七万出西域,伐龟兹。
这个男人从混乱嘈杂的梦中醒来,吸一口阴凉、略带霉味的空气,才突然感到胸口热辣辣的刺痛,接着,左腿也开始疼起来,腿骨的深处仿佛有一把冰锥在搅动。尽管墙壁上凝结着点点露珠,他却觉得自己的灵魂更潮湿更沉重……男人闭上眼睛,试图回到梦中,但是只看到一些支离破碎、毫无理性的画面,血腥的屠杀和永远无法听见的哀嚎。不对,这怎么是梦呢?昨夜,也许是前夜,该死的昏迷和石屋中的昏暗光线让他失去了时间感,一伙暴徒冲进他的家园,大肆劫掠,他一定是在自卫中受了伤。这时候他才意识到眼睛酸涩肿痛,左眼比右眼更甚。于是他放弃了从梦中占卜前途的打算——门,忽然开了。
清甜干爽的微风扑面而至,门口站着一个体态轻盈的少女,手里抱着一个水罐,她略一低身提起放在脚边的另一个水罐,迈步走进小屋。注意到男人睁开的眼睛,少女来到床边,谦恭地问候他,
“恩主,您已经醒过来了。”她用一块小手帕为他擦拭脸庞和干裂的嘴唇,小心翼翼地掬一捧泉水喂他喝。四周一片沉寂,没有鸟鸣也没有虫声,他知道他们正身处沙漠之中,永恒的疾风让任何人、任何生物都无法留下足迹。
事实上这个用于紧急避难的小屋就是他修建的,小屋北边,一座大沙丘之后有一眼很隐蔽的泉水,她就是去那儿取回了宝贵的水,可是他们显然没有食物。
男人问:“没有其他人逃出来吗?”“不用太担心,他们都是骁勇的战士,懂得怎么保护自己,也许他们正在跟您会合的路上。”她回答。
表面上他是位经营武器买卖的突厥商人,在龟兹住了很多年,无论是南来北往的大客商还是皇亲国戚都是他的座上宾。为了保护财产,他自然要养一些死士。武器商人的身份是个绝佳的障眼法,掩盖了他的突厥间谍的真实身份。这些死士的真实用途就是为了刺杀那些亲汉人的官僚,以保障西突厥在西域的利益。当龟兹王白纯表现出畏惧汉人势力的倾向时,他开始策划刺杀龟兹王,只不过吕光的大军比他更迅猛。战争的动荡也让那些亦商亦盗的驼队骚动不安,袭击他的会是土匪吗?
她慢悠悠地说:“那些人中虽然混有各族战士,但统领是个汉人,而且训练有素,绝不是普通土匪。”汉人虽然攻伐龟兹,但他们更恨突厥人。她的声音就像每天晨祷时为他读佛经那样澄澈婉转。她用一罐水为他清理伤口,涂上止血的药膏后,静静地坐到墙角。床边水罐里的波纹在晃动中渐渐平息。
“吕光刚刚攻下龟兹,军政要务数不胜数,怎么会对我这个小小的商人感兴趣呢?”
“恩主,我认为是童向吕光告发了您,童还是白纯的鹰犬时就怀疑您了。”
屋外的沙漠一定是烈日当空,因为他感到门口吹进来的风开始变得燥热。她走过去关上石门,又抱膝坐在墙角。
“恩主,您需要食物和疗伤的药膏。我可以为您潜回龟兹。”
“不行,太冒险了。”没有群鸟婉转的低唱,也没有风声。
她十三岁那年,刚学会表演完整的小天舞,也是这样一个晴朗的日子里,在花园的砖石空地上刻苦练习。闪亮的红丝带嵌进她柔密厚实的黑发,朝霞般闪耀的绯红小袄和漂白的细棉布裤子勾勒出鹤一般纤细优雅的身姿,乌黑的小皮鞋在地板上踏出轻快的节奏。
清晨的玫瑰花苞啊!我怎么忍心采摘?可是,当你娇艳怒放的时候,是否已被他人劫掠?
与那个时候的饱满鲜艳相比,她变得沉静而略显忧伤了,脸部线条显露出成年将至的柔韧棱角,妩媚的性格也已经取代了年少张扬。
她站起身走向门口。
“你要去哪?”
“恩主,我要回龟兹。我并没有长着一张突厥人的脸,骗过守门的士兵,不是什么难事。我会很快回来的。”
当她走到门口的时候,男人盯着她的背影问:“你什么时候回来?”
她在昏暗中停下来,缓缓地转过身,说:“今天早晨我在泉水边遇到两个汉军的探子,我把他们都杀了,尸体埋在沙子里。但是很快就会有更多的汉军来搜查。我们会在饿死前被吕光斩首的。您的伤势很重,无法移动,不管怎样已经踏上了黄泉路。而我还年轻,请放我走吧。”
他并没有觉得震惊,也没有丝毫哀伤愤怒,她说的都是事实,如果她没有想到这些,就不是他精心培育的珍宝了。那种骄傲地向朋友们炫耀,但绝不会任人染指的珍宝。
“我们是主仆,师生、父女和恋人。我深知你的话合情合理,但是在这终结的时刻,请陪在我身边吧!我无法独自面对死亡。”他努力看清她,心里闪烁着时隐时现的希望。
她再次来到他身边,从荷包里拿出一支干枯的绛红色玫瑰,放在他胸口。已经没必要再说什么,她干净利落地走出石屋,扬长而去。
童与一位少年英武的汉人将军来到石屋的时候,男人还是不能挣扎着坐起来,他只能躺着对他们说:“你们想要抓住的那个我的手下,她对我说,她要回龟兹。不过我相信她藏在沙漠深处,但不会离泉水很远,她一定是背着我另外建了自己的藏身地。快去追她,你们一定能抓住她。”说了太多的话,他再次感到焦渴,忍着剧痛大口大口地喘息。童和汉人将军旋即去追她了,只留下几个士兵看守石屋。
她在劫难逃。
十年前,她来到他家,那时大雨倾盆而下,她站在雨中,虽然撑着一把伞,不合体的衣裳还是被打湿了,湿衣服紧裹着她瘦弱如芦苇的小身躯,因而凸显得头格外大,头发也是湿的,一绺一绺贴着颅骨。雨,为周围的胡杨树以及稍远的楼宇雉堞涂上灰暗,城市像坟墓般沉寂。那时的她是那样渺小,特别吸引他的,是她两颊处从粉白皮肤里泛出的嫩红,那么鲜明刺眼,让他想起在沙漠城市中极其珍贵的新鲜桃子。
那天的雨罕见的猛烈,他记得很清楚,青灰的雨云之上是交错急驰的亮白云团。
作者简介:白雪, 女,1979年4月出生于承德。2000年毕业于中央民族大学油画系。曾发表过小说《河面的光斑,河底的泪》《渡/渊》,诗歌《呓语》《草与湖》《几滴雨,之后》《水滴包裹音符》《寒玉》,书评《了解日本学界关于中日战争责任认识的一本好书》《吴亮与真实状态中的画家们》《形味结合——说说张丹阳鉴赏沉香的审美特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