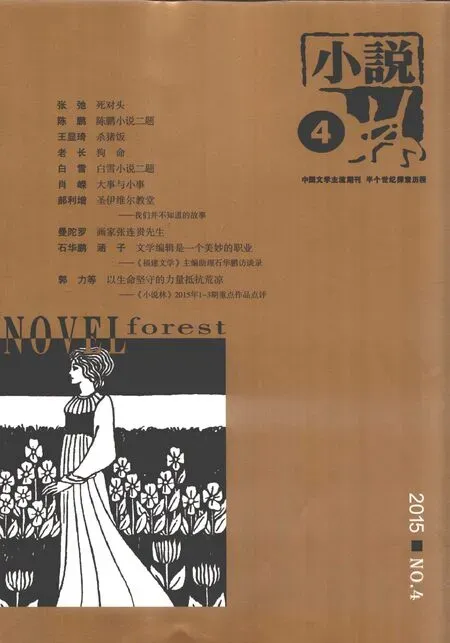杀猪饭
一
朱老者是一个神经病。
他紧紧地握住手中白森森的杀猪刀,目光空洞,口里念念有词,几个有劳力的汉子死死地压住在案桌上挣扎咆哮的大猪,等待朱老者手举刀落。
空气又湿又冷,但是壮汉们的身上都在蒸腾着一股热气,他们不再年轻,但看上去仍旧劳力十足。朱老者一只手拿着锋利的钩子,狠狠地钩进猪的嘴里,用力往上一提,那颗沉重的头颅便高高扬起,被钩子刺破的上颚流出了掺杂着黏黏的口水的血液。朱老者刀尖用力一挺,深深地刺进了猪的喉咙里,一阵悲惨的长鸣,一股滚烫的血液。这是一年到头的酬谢,一年里最重大的盛宴。
猪的血已经流得差不多了,几只鸡在拼命地争抢着洒在地上浓浓的血液。调皮的孩子们正趁大人不注意的时候上前去揪揪猪尾巴,摸摸猪蹄子,但是马上又被忙碌的人们伸出的一只有力的大手,狠狠地一推,怒吼道:“滚过去!”
朱老者突然丢开了手中的刀,缩到了院坝里的一张桌子下。点一杆叶子烟,“吧嗒吧嗒”地抽着,嘴中念念有词。
“我家儿子就是前年出去的那个嘛。”朱老太的脸上洋溢着难以言表的自豪。“大城市,去的是大城市。今年回家要带我家的孙孙来过年。”朱老者的孙孙现在正端着半碗被风吹得又冷又硬的洋芋,紧紧地靠在朱老太的怀里,怯生生地看着自己的爷爷。而朱老太则紧紧地搂着自己的孙孙,嘴里不断地骂:“天啊天,我朱家是造些哪样孽,你个老不死的这样还不如死了痛快啊。”
“讲这个鬼崽崽前年和我家儿媳妇把小的那个丢给我们两个老的就出去了,出去听到讲又给我生了个小孙孙,今年回家过年。我家大的孙孙三岁了。没见过的那个孙孙也有一岁了。”朱老者抹了一把嘴角的白沫,像是对众人说,像是自言自语,又好像跟谁促膝交谈。
朱老太后背上,一个小孩正在甜甜地睡着。
几个人硬生生地把朱老者从桌子下扯了出来,“别碰我,别碰我。你们这些死猪崽,老子要杀你们一刀一个,你们被老子宰了,又回来索我的命,给老子滚!”
“你个老不死的快滚回家去,别在这丢人了。”朱老太跟在一帮人的身后,边骂着朱老者边抹着眼泪,院坝里几个择菜的老女人扔开了手中的菜,赶紧上前扶住了随时都会瘫软的朱老太,大孙孙已经一屁股坐在了泥泞的地上,半碗冷洋芋全部洒在地上,几只鸡在拼命地啄食。
朱老者被拽进家中的火炉旁边坐下,几个人又是端茶又是拍背。原来热闹的大院坝里现在空无一人,两条瘦弱的黑狗用舌头舔食着鲜红的血旺子,几只灵活的老母鸡跳到死猪的身上,一嘴一嘴地啄着,就像是一次依依不舍的送别。一个女人在慌乱中抱起了朱家的大孙孙:“朱姨妈,你家孙孙滚倒了,快抱回家换裤子。”朱老太从朱老者身边一下子蹦了起来,神色慌张,“哪点,在哪点?”那个人把人抱到她面前时,朱老太的大巴掌已经落到她孙孙的屁股上,“短命儿,我看你家这一大家子要把我折磨死。”边骂边打,背上的小孙孙惊醒,大哭,面前的孙孙又冷又疼,大哭!
“我的儿啊。”朱老者一屁股从凳子上坐到了地上,拼命地哭着。几个男人去拽着朱老者,几个女人也去拉着朱老太。“别打了,快带回家去换衣服了。”几个人又拉又拽,硬生生地将朱老太拉回家中。
这边的朱老者也慢慢地安静了下来,只是口中还是默默地念着——“你们这些猪崽,滚远一点儿,被我杀了现在又来索我的命,还说我儿子死了,你们这些猪崽,想吓唬我,说我儿子像我骗你们上案桌一样被别人骗出去打工,说我儿子像你们被我杀一样被城里的人杀了,你们这些猪崽,你们……你们……”老者白眼一翻,两腿一蹬,重重地摔在地上。“行了,看来能安静一会儿了,扶床上睡吧。”几个人连拉带拖,将老者拽上了一张脏兮兮的床上,他手上的猪血还来不及洗,已经干成了一块一块的,慢慢地往下掉。一张一张的,红红的。
“回去吧回去吧。朱大爷睡着了。大家回去干活吧,一会儿又吃不上饭了。”人们又回到了大院坝里。踢跑了添旺子的狗,吓飞了啄猪的鸡。男人们拴好了杠子,担在猪肚子下面。女人们重新捡起筐里的蔬菜。
“哎!造哪样孽。朱伯伯和朱伯妈这辈子人这么好,怎么就这样呢?拖起两个孙孙,朱伯伯还变成这样了,这个日子要怎么过?”人们在自己手中的活路里闲聊,在闲聊里回忆,回忆朱老者的过去。
“朱老者是一个猪妖。”一个年龄和朱老者差不多大的人说,他还一边用绳子将粗粗的杠子拴得死死的,“我和他一起屙尿拌泥巴玩到大。我记得小时候他身体不好,经常生病,发高烧,还经常学猪叫,那时候我们都是七八岁吧。”老人一边套着绳子,一边说着。其他的人也是一边用心地干着活,一边用心地听着。“他爹他妈没办法,请个先生给他跳大神,先生说他在阴间的时候阎王爷是打算让他投猪胎的,孟婆给他熬汤的时候也熬的是猪要喝的汤,但是在进轮回道的时候他拼死挣扎,结果投错了胎,进了投人胎的轮回道,才成了人。”
“哎,我说,听说这头猪以前爬过树。是吗?老五,你家猪会爬树吗?”一个胡子有些发白的汉子说,然后人们放声大笑。
“你们这些没有见过世面的小老者,敢笑我?算算老子也比你们大好几岁,不晓得尊重老人。我讲来你们不信?当时我就在场,那个先生说他抢了本来要投人胎的那个人的轮回道,那个人不愿意投猪胎,现在还在缠着朱老者,先生让他家去拜祭一个杀猪的,咱村那时候也没有杀猪的,他爹他妈就带他走了好几十里山路,去拜对面寨子的那个朱老三当干爹,也改姓叫朱,叫朱克星。你们还别说,回来后这小子就好了,不生病了,能吃饭了,身体还越长越壮。后来他家又请了那个先生给他看了一回,先生说被他抢轮回道的那个人投胎成猪,已经没什么大事了,但是事事因果轮回,尽量不要让他和猪有什么牵连。
“哎,农村人家,哪能离得了猪呢?他爹他妈见他身体慢慢的好了,也没有过细地注意,后来还把他送到对面寨子朱老三那里学杀猪。”
说话间那头死猪已经被人们抬到了前门一个土包包上,那里燃了一团跳跃着的火焰,火上放着一锅滚烫的开水,那是烫猪用的,一个干瘪的瓢,一把生锈的菜刀,一瓢热水往猪的身上一浇,用刀刮着被热水烫过的地方,猪毛便大片大片地开始往下掉。那个老人停下来点了一杆叶子烟,歇一口气,人们也都各自埋头做着自己的活路。
前院,朱老太牵着一个,背着一个,从远处一步一步地走来,眼角还零星着几粒黄黄的眼屎。女人们看见走来的朱老太,你看着我,我看着你,不知道如何是好。
“那个老不死的睡着了?”朱老太很勉强地挤了一下笑容,皱纹瞬间堆积在脸上,她拢了拢鬓角的白发。“哎,那两个走了之后他就这样了,发病了就乱喊,一会儿又是猪要他的命,一会儿又是儿子儿媳要回来看他的。我看他啊,日子不长了。”朱老太说话时感觉自己的喉咙哽哽的,不自觉地憋出了几滴干干的眼泪。
“伯妈,不要这样说了,你和朱伯伯都是好人,要好好地活。”
“哪样子好人,好人会有这个报应,不晓得我们上辈子是造个哪样孽啊!当年那两个短命的要出去打工,他死活不同意,最后两爷崽差点儿提起刀满寨子追起来砍。那短命的来求我借他们车费钱,帮他们带孙孙。我看没办法了,他们实在是想出去了,在家里坐不住了,就把卖鸡卖菜存的一点儿钱全部拿给他们,三更半夜地煮点儿粑粑给他们吃,送他们走的。第二天那个鬼老者起来发觉人走了,就是骂,哪样难听骂哪样,骂又有什么用,人都走了,孙孙还是要带,庄稼还是要做。”
人们全神贯注地盯着朱老太,手中的活还是在灵巧地进行着,刮洋芋皮,洗白菜,切葱葱。她们细心地听着朱老太的诉说,她们也在用心地完成自己手中的事情。
“你家儿子和儿媳为哪样铁心要出去呢?你家田地这么多,还要带两个孙孙,他们怎么能丢得开手嘛?”
“就是怪他家的干亲家嘛。”朱老太把刮好皮的洋芋扔进脚边的水盆中,又捡起另一个洋芋接着刮。“前年这个鬼老者家的干侄儿来这边拜年,穿得油光满面的,还提一些花花绿绿的东西来送我们,我家儿看到就问他是在哪点做活路,怎么会找到这么多钱,想和他一起去做。他讲是在城里,一个服装厂,一个月四千多,包吃包住,现在还缺人,要去的话过完年就和他一路去。
“我家儿一听心就热了,晚上就和他爹商量,要我们两个老的帮他们带孙孙,他们出去打工。他爹讲我们老了,家里田地又这么多,他们在家做田地也饿不死,两个娃娃也还小,没有爹妈在身边造孽得很,还是不要出去了。我那憨包儿讲死讲活不听,要出去,他爹也是犟,提把菜刀砍在桌子上,讲要出去就一刀把他砍死再走,那憨儿看他爹这架势就不敢讲了。自己悄悄地就出门了,也不晓得去哪了,反正一晚上没有回家。”
二
一只脏兮兮的猪瞬间变得白白净净,刮猪毛的人用那厚实的巴掌狠狠地拍了猪两下,“啪,啪!”
“行了,抬上案桌吧。”
于是又是一阵骚动,结绳抬杠,手忙脚乱;几个不知轻重的小孩又是上前去扯扯猪耳朵,揪揪猪尾巴。
“滚过去!”大人们恶狠狠地推这些小孩一把,然后蹲下身子,将粗粗的杠子担在自己的肩上。“来!一、二!起!”一声沉闷的声音从喉咙里憋了出来,借助这股憋着的劲儿,四个有劳力的壮汉把一头肥硕的猪抬起来,放在案桌上,开膛破肚。
“老人,你家那几个儿子今年要来家过年嘛?”杀猪匠一手拿着杀猪刀,一手拿着钢刀杆,将手中的刀磨得“哗哗”作响。
“他们啊!”那老人一边用棕叶搓着绳子,一边说,“他们去年送朱老者家儿子儿媳的骨灰来家,今年就不来家过了。”
“他们是怎么晓得朱老者家儿子儿媳死了的啊?”
做活路的人们紧紧地盯着那个老者看,手中的活还是井井有条地进行着。那老人不昂头看众人期待的眼神,只是自顾低头编着自己的绳子,不时吐一口浓浓的痰。
“我记得是前年,晚上了,我都洗好脸洗好脚准备去歇了,朱老者家儿子着急忙慌地跑来找我家那个,两个就在我家里悄悄地讲了一晚上,我睡去了,也不晓得是讲些哪样。第二天朱老者家儿子才自己回家去,我家那个就来找我,话都不说,就跪在我的面前,我还以为是出哪样事了。我讲你这个狗日的有屁快放,老子又没有死,你跪老子干什么啊。他说他要出去打工,今天晚上和朱老者家的儿子一路走,我听到他这么讲我就晓得那天晚上朱老者家儿是来约他出去打工的,我讲老子还以为是好大个事,要去就去,孙孙我们两个老的帮你带,你们两口子放心地去,那憨儿看到我没有反对,一下子就从地下蹿起来,急急忙忙地去喊媳妇收拾东西。”
“人家朱老者提起刀讲只要他儿敢踏出家门半步就把他砍死,为什么你这么爽性就同意你家儿出去?”
“我家那个短命儿在家里什么都不做,一天就是打他媳妇,老子喊都喊不住。是啊,他要出去就让他出去,管不住了,要滚哪里让他滚得了,他死在外面也不关老子的事了。”
说话间猪的头已经被卸了下来,胸膛和肚子也已经被划开,像是披着一件没有扣上扣子的外衣,心肺肠子都裸露在外面,冒着一股腥臊的热气。杀猪匠的刀在猪的身上自如地游走,掏心挖肺,不一会儿工夫,猪的内脏已经被清理干净了,只剩下了一个空空的外壳。杀猪匠用一块油腻的毛巾擦着猪肚子里面残存的血水,袖套和毛巾上都附着了一层厚厚的油,滑滑的,亮晶晶的。
那老人拿着水瓢往地上的水盆里舀了半盆水,然后把冒着腥热气息的猪大肠放进盆里,一层白白的油沫马上就漂了起来,几个人看见来连忙上来搭手帮忙,理顺,然后捏着肠子的一头,用力地往另一头挤,胀得鼓鼓的肠子,瞬间瘪了不少,粪便不断从另一头涌出,冒着热气,几条黑狗上来抢食。盆里散发令人作呕的气味,但是人们不受丝毫的影响,兢兢业业地做着事,津津有味地听着话。
“短命儿收拾好东西,我在院坝里磨刀准备去割草,他一笑一笑地过来喊我,爹啊,你看要出去了,我不可能走路去嘛,这个……我当时看到他的那个样子太想一刀把他整睡起算了,打个啥工,他妈的在家都养不活自己,赶后老子想了想算了,给他吧,反正出去是死是活老子是不管了,我把刀丢开去家里摸得两千块钱给他装起去,他笑眯眯地讲爹啊,这个钱回家过年就还你啊,我讲你狗日的养好自己就行了,老子不要你的钱。”
老人说到这里手里用力一捏,一股黏稠的粪便从猪大肠里喷涌而出,喷到了一条狗的眼睛上,那狗“嗷,嗷”地叫着跑开了,其实应该不疼,只是被吓的。
“那天啊。”杀猪匠抬起头,用尖尖的刀在一块猪肉上刺了一个洞,然后用棕叶编的绳子套进去,递给旁边的人提回家去腌腊肉。“那天我是去朱老者家干什么去了,忘记了,和他在家里坐半天,不见他家儿子,我还问你家那个今天哪去了,怎么来半天没有看到啊,还想喊他来喝酒啊。”说话间他又取下一块猪肉,刀工精湛,手指灵活,不在朱老者之下。
“朱老者还讲不晓得是去哪儿了,这两天这个短命儿要出去打工,老子看到他敢走出家门半步我把他的脚杆打断,我讲还是年轻人嘛,出去见见世面也是好的,只是那个鬼老者犟嘛,不同意就是不同意。我回家第二天就听到讲悄悄地跑了,晚上趁朱老者睡着悄悄跑的。”
那只肥硕的猪被肢解得只剩下后腿了,杀猪匠的尖刀在猪肉里肆意游走,忽然发出一声刺耳的响声,杀猪匠感受到了一阵阻力,他把尖刀拔出来,换成了一把重重的砍刀,“啪,啪,啪”。一下一下地砍在猪坚硬的骨头上,肉渣飞跳,有几粒落在了他的脸上,他并不在意,依旧低头做自己的事。
“是啊,”老头直起身来,用油光锃亮的手卷了一杆叶子烟,吧嗒吧嗒地抽着,“老了,多弯哈腰杆就酸得不行了。”他吐了一口烟圈,看着水上漂浮的油脂,几个人还在七手八脚地搓洗着。“那天晚上半夜三更的,我家那点儿把我喊醒,讲要走了,我讲现在黑灯瞎火的,要走也等天亮再走嘛。朱老者家儿和他家儿媳妇讲要趁晚上他爹睡着才能走,我看到没得办法就把他们送到寨子口,还把家里的电筒拿给他们了,害我改天跑去又买一个,好几十块钱啊。”
三
腊月的风刮过没有枝叶的树林,冷飕飕的。狭小的院坝里只剩张案桌,一条银白色的水迹一直延伸到臭水沟里,几个小孩追着一个被吹胀了的猪尿泡玩耍,上面沾满了煤灰。杀猪的壮汉们已经歇工了,他们摆开了一张桌子,一副扑克牌,一罐包谷酒,已经有人喝得满面通红,还有的已经蜷缩在桌子下面,胡言乱语了。
朱老者在主人家的床上舒服地睡着了,他呼吸均匀,表情安详,清澈的鼻涕不自觉地流出来,沾在花白的胡须上。
现在最热闹的地方应该就是厨房了吧,炉火正旺,油锅滚烫;菜刀与菜板接触发出的声音像一首交响乐,这是新年的前奏。
“打我,就是打我!”朱老太一边把干净的菜整齐地码在菜板上,一边愤愤地说。“醒来后这个老不死的晓得儿子出去就要打我,用煤棒打,用耍鞭棍打,用火麻抽我的脚。边打边骂,骂我是败家的婆娘,一直骂,连小的也骂。小孙孙吓得哭,声音都哭哑了,哭得咳出血了,不管,也不准我管。高声大气地骂,不准管,那个杂种都不管的小杂种你管个啥,等他干啥,我看爱打工,打工连家都不要,滚!边打边砸东西,家里的锅碗瓢盆,全部砸烂,只有那个黑白电视舍不得砸,不然是真的全部砸烂。”朱老太说得很平淡,好像经历这事的不是她,她把菜板上的菜切得很碎,下刀又快又狠,并且不用眼睛看着切,切得非常的均匀。
“打过了,打累了,自己喝点饿肚酒就去睡觉,我背起小孙孙去我哥家住了一场,家里的东西全部被打坏了,我火重得很,我懒得管他,自己背起孙孙就走了。住一场回来,锅碗瓢盆全部重新买了,家里整得好好的。看到我回来,眯笑眯笑的,我懒得和他讲话,我想到我实在生气得很,他把饭做得好好的,我也没有去吃,带起小孙孙就去睡觉。他不敢来睡,自己悄悄地在板凳上坐了一晚上,第二天天不亮背起箩箩就割草去了。”
“朱伯伯也是下得去手。”主人家把朱老太切好的菜放进锅里,“人都走了,你打就打得回来嘛。”
“他就是发疯,找不到人出气拿我出气。现在好了,发疯发疯都发成真的了,这个日子要怎么过哦。”朱老太长长地叹口气,把菜刀往菜板上狠狠地剁了一下。
“朱伯娘别这么讲嘛,寨子里这些能帮的会帮到你的嘛,日子还是会好好地过的。”
说话间最后一道菜已经出锅了。
“安桌子,吃饭了。”一声张罗,院子里的人们收起了牌和酒,喝得蜷缩的人也已经差不多醒酒了,现在又端端正正地坐在桌子边,满满的又是一碗包谷酒。
猪血煮白菜,白片煮青菜,炒瘦肉,四季豆,炒洋芋,炸花生米。
杀猪饭吃的菜也是不多的,但是每年每户人家都要杀猪,都要吃杀猪饭,吃的时候也都是高高兴兴,热热闹闹的。
“朱伯娘,要不要喊朱伯伯起来吃点啊?”
“不用,喊起来不一定要发什么疯,等我带点儿回家给他吃就好。不用管他。”
“好,那我们就不管了。先吃先吃。”主人家热情地招呼着,人们又说又笑地吃着,不一会儿,划拳的吆喝声便响了起来。
原来每年的杀猪饭,主人家都要提前通知朱老者,寨子里的人们都知道他会杀猪,杀猪好,都知道他杀猪时猪不叫,不挣扎,都是乖乖地仰着头等他杀,村里人已经很久都没有听见杀猪时猪那种撕心裂肺的嚎叫了,一切都是因为朱老者。
朱老者疯了,他的手艺还在,但是他不让猪嚎叫的神奇魔法不在了。
去年杀猪,朱老者已经把猪牵引上了案桌,一切就像原来一样,蠢笨的猪并没有感受到死亡的降临,乖乖地仰着头等着朱老者下刀,这时候院坝口出现了两个衣着光鲜的人,他们手里捧着两个黑黑的盒子,沉沉地低着头。
“两个短命怎么回来了,来家也不先通知一声。”
朱老者听见主人家的声音,朝着院坝口望去,是去年和自家儿子一路出去的那两口子,那个老者嘴里骂的短命儿,没有看到自家的儿子和儿媳,他立即把眼神收了回来,手中的刀利落地捅进了猪的咽喉里。
“嗷!”案桌上的猪嚎叫了,吓住了在场的所有人,接下来开始挣扎,它滚下了狭窄的案桌,它压在朱老者的脚上,那把尖刀还在它的咽喉里没有取出来,它拼命地甩着那颗硕大的头颅,鲜红的血洒在四周,洒在朱老者的身上。那头肮脏的猪翻滚着,像一台压路机一样,它从朱老者的身上碾压过去,它那满是脂肪的肚子压住了朱老者的脸,朱老者感觉自己呼吸困难,他也无力地挣扎着,想要把这头又重又脏的猪从他的身上推下去,他的鼻子被猪压平了,他的嘴被压得无法闭拢,他的舌头舔到了软软的猪肚子,他舔到了猪肚子上腥咸味的猪屎,他现在憋得满脸通红,满脑子都通红。
院坝里乱作一团,人们一拥而上,你抓猪脚,我拽猪尾巴,都想把猪从朱老者身上挪开。但是手忙脚乱的,大家的劲儿没法往一处使,那猪纹丝不动,朱老太在一旁高声喊着,“天!快去帮他嘛,快去帮嘛。这是造什么孽啊!”她手脚并用,又是跳又是蹦的。她的喊叫让营救队伍更加的混乱,她不像是一个指挥官,也不是一个加油助威的拉拉队员,她的旁边有几个妇女扶着,生怕她不注意脚下一滑,摔个四脚朝天。
热腾腾的猪血从咽喉里汹涌地喷出来,形成一条小河,还未开始奔涌,就被开裂的土地全部吸收。猪的挣扎幅度越来越小,叫声也从开始的狂嚎变得越来越低沉,最后只是有在喉咙里虚弱的“哼哼”声。朱老太的手脚却越来越活跃,声音越嚎越大,最后索性一屁股坐在地上,手挠脚蹬,喊叫变成哭嚎,任周围的人如何拉拽劝说,喊声依旧。
猪已经慢慢地失去热气,人们也从慌乱中慢慢地镇定下来,几个人合伙喊着“一二,一二”的号子,三两下便把朱老者从猪的身子下面拉出来。
“让开!让开!让开!”朱老太连滚带爬地移到了朱老者身边,“天!你个死老鬼的你不能死啊。你死要我和孙孙怎么办?”
“朱伯娘,朱伯娘!”几个人生拉硬拽地把朱老太扶起来,她满身都是油腻腻的血水。“你先让开,我们把伯伯扶到火边去。”
人们把朱老太拨弄开,抬着半身是血半身是泥的朱老者进家去了。两个归乡的年轻人显然是被这样的场面吓住了,他们脸色苍白,神色紧张,手里捧着两个盒子一直站在院坝口,沉沉地低着头。直到人们把朱老者救出来接近家的时候,他们才缓缓地迈开步子,跟着进家了。
“朱伯伯!朱伯伯!”
“朱老者!朱老者!”
“老朱!老朱!”
人们手忙脚乱地用自己的方式呼唤着昏迷的朱老者。
“让开,让我来!”那个从小和朱老者一起长大的老者拨开众人,先是一瓢冷水泼在他的脸上,然后用自己长长的指甲掐进朱老者的人中,一道深深的痕迹出现在鼻子下面,还有一些淡淡的血迹。然后他又把一个巴掌放在朱老者的胸口上,另一只手一拳一拳地狠狠捶在朱老者的胸口上。
“咳、咳!”朱老者一阵猛烈的咳嗽,然后剧烈的颤抖之后,他直直地坐起身,吐了一口浓浓的带有些血丝的痰。“怎么了?我怎么了?猪呢?我杀的猪呢?”
“没事就好了,刚才你杀的猪一下子跳起来,差点把你压死了,快先歇口气,要喝茶不喝啊?”人们有的拍背有的端茶,朱老者摆摆手,静静地坐着喘气。“刚才我好像看到有两个人?”
“朱伯伯!”朱老者的话还没有说完,人群后面传来一声哭腔。人们的目光纷纷转向后面,两个年轻人一起跪下,跪着挪到朱老者面前,眼泪一滴一滴地打在地上,形成了四道湿湿的痕迹。
“你们干什么啊?来家不先和老子打招呼,先哭哭啼啼地跪这个朱老者干什么啊?”那老者显然不满意被自家的儿子忽视,但是这话之后自己的儿子依旧没有理睬他。
“朱伯伯,你家……你家……”还没说完就把两个骨灰盒捧在朱老者面前,泣不成声。
朱老者两眼一翻,一口脓血吐在两个黑黑的盒子上面,“嘭”的一声,两个盒子被朱老者打翻,白色的粉末洒了一地,朱老者也应身倒地,不省人事。
“哇!”有孩子哭了,屋里的人循声望去,那个孩子被捆在跪地的男人的背后,这个孩子是谁的呢?现在没有人关心了,因为在孩子破嗓大喊的那一声后,朱老太也软绵绵地倒在地上,屋里一阵哄乱。孩子放声大哭,两个归乡的人一直跪着,迟迟不肯起身,眼泪鼻涕止不住地流着。
“快去喊隔壁寨子的医生来看。”
“快起来,是怎么了,先起来再讲,别跪了,起来。”
“天!是造哪样孽?”
“滚过去,别在这挡脚手。”
“快把这条狗打出去,它在舔地下的白粉粉。”
“这个是些哪样嘛,还要不要嘛,要就去拿把扫把来扫起,到时候一个踩来一个踩去的一会儿踩不得要。”
屋里像一锅粥,屋外只有一头猪,悠闲地睡着,死死地睡着,好像是对屋里人们忙乱的一种嘲笑。
四
朱老者神智清醒,他闻到外面的包谷酒的香气,猪肉的香气,花生米的香气;他听到外面的声音,划拳的声音,说笑的声音,酒杯相碰的声音,劝酒劝肉的声音。
他感觉自己好饿,他想起身去和他们吃饭,去喝酒。
“朱老者。”他听见有人喊他,“来!来!来!”他看见有人向他招手,他下床走出去,看到一个狭小的车间,猪肉如林,机器轰鸣,空气中充斥着令人作呕的气味,一群穿着破旧的油腻腻的工作服满眼血丝的人低头不知疲倦地工作着。高墙上的小窗户不注意让几缕阴沉的阳光漏了进来,苍白的灯泡发出的光亮照在缓慢转动的扇叶上,阴影随着扇叶的移动而移动,笼罩在每一个工人的脸上。朱老者努力地看,却看不清;努力去听,却沉寂无声;努力去闻,满屋子猪肉的气息却让他这同猪打了一辈子交道的屠户呕吐不止。他感受到自己儿子的气息,他只是想寻找他们的身影,但他只能感受到,不能真真切切地看到。
“别打!别打!不敢了,再也不敢了!老板!”他听到一阵骚乱,但是依旧看不清每一个人的脸,只能依稀看到两个被一群壮汉打得满地打滚的人,“别打……别……”他们不断地挣扎着,哀求着,嚎叫着,扭曲着,像是案桌上已经被钩子钩住嘴巴的猪,此时的嚎叫已经没有作用,狠心的屠夫只会在适合的时机再补上致命的一刀,然后你不再痛苦。
被打的两个人嘴里流着肮脏的血,他们鼻青脸肿,手里拿着两大块又青又紫的猪肉。“不敢了,别打,再也不敢了,别打……”他们不断地哀求着,不断地把手里的猪肉往嘴里塞,黏黏的口水掺在血水里一直往外流,他们的嘴被腐烂的猪肉塞得满满的,他们大口大口地咀嚼着,嘴里发出“呜呜哇哇”的声音。
他们的眼睛变得直勾勾的,身体慢慢地坚硬了,停止了挣扎,停止了咀嚼。还有大半块来不及咀嚼的猪肉塞在他们的嘴里。
“拖下去吧!”
他们显然是死了,尸体在地上划出了两条血迹,这是他们留在世上的唯一痕迹。
“看到没有,这就是不好好干活,偷吃东西的下场,快点干活!”
工人们在死亡中沉沉地低着头颅,默默地干活。有的人趁着监工不注意的时候用浮肿的手撕下一块腐烂的猪肉,放进嘴里,不敢咀嚼,生生地吞下肚里。
朱老者惊得一身冷汗,他蹲在地上,感到自己胃里一阵扭曲,他想呕吐,但是除了几下干呕,他什么也没有吐出来。
“鬼老者,滚回去!看什么看啊!”他听到自己的后面有人对他咆哮,一回头,一根棍子狠狠地敲在他的头上,他感到自己的身子迅速地往下掉,就像是从一栋很高的楼上往下掉一样。
醒来时四周黑暗,一口井,黑洞洞的,看不见底,看不见水,他使劲地摇了几下头,对着黑洞洞的井口出神地望着。慢慢地,他看见了一个人影,很模糊,慢慢地,他越看越清楚。
他看见了,他看见了他自己,他看见自己被两个人身兽面的人押着,那里有三口井,他看见那两个兽人要把自己丢进中间的那口井。他使劲地挣扎着,挣扎着,他挣脱了那两个人的束缚,但他还没缓过神来,就失足掉进了左边的那口井里,那两个兽人满脸惊恐,小声地商量着什么,最后他看见他们的脸上浮出了一丝微笑,然后不知道去哪了,过了一会儿,他们又押着另一个人过来。
“对不住你了,本来猪是要你前面那个人当的,但是他劲儿太大,掉进你的轮回道中,为了不被阎王怪罪,只能拿你替他去当猪了。”
“不要,我不要。这是你们的失职,不关我的事,我不要当猪。”被押着的人惊慌地挣扎着,比刚才的朱老者还要凶猛,两个兽人死死地架着他的胳膊,对他拳打脚踢,他依旧死死地挣扎,但是一切无效,他被两个兽人丢进了中间的那口井中。
“朱克星,你来了!”朱老者四周变成一个大殿,烟雾升腾,大殿上坐着一个面目狰狞的人,旁边的一个小鬼样的人手捧生死簿。
“朱克星,年六十四急火攻心至疯,年六十五卒。前世投胎抢猪小四轮回道,在世为人随意屠杀猪灵,现打入畜生道,永世为猪,受人屠戮,不得翻生。”
院坝里,年轻的屠户把锋利的尖钩狠狠地钩进肥猪的嘴里,黏稠的口水混夹着淡淡的血水,一路淌到案桌上,散发出淡淡的腥咸气息。汉子们七手八脚的压住案桌上的肥猪,屠户鹰爪一般的左手用力一提,肥硕的猪头高高地昂起,他右手一挺,白森森的刀子插进肥猪咽喉。霎时间,猪嚎震天,血喷如泉!
作者简介:王显琦,男,汉族,贵州省安顺市人,1993年12月出生。哈尔滨师范大学文学院政务文秘专业2012级学生。
——璧山区建立三级院坝会制度推进基层治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