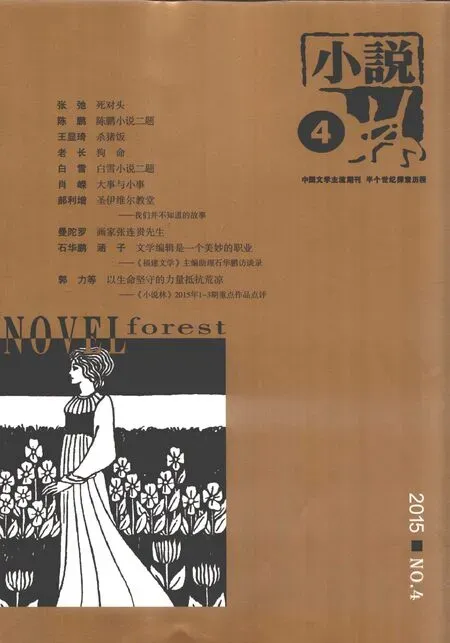想象力创造现实
陈鹏
显然,这两个小说是我旺盛想象力的分泌物。当我于2012年写下《乌蒙》或稍早时期写下《奶牛住进我们家》《宋代美人》《开往糖厂的末班车》乃至更早一些的《巴西海藻足球队》那样的小说之后,在我所尊敬的何凯旋大兄的提醒之下,我突然发现,小说写作当然可以照着这条路子往下走——以我十余年记者生涯的真实遭遇提供燃料,再用过剩的想象力点燃它,亦能完成一个写作者所谓的“现实观照”。按照老博尔赫斯的说法,小说家的想象力总能胜任更加广阔的现实世界,甚至,小说家的“想象现实”(或虚构现实)比现实还要真实;比起作家的想象力,现实世界不过是一条拖在身后的影子。
小说凭什么不能这么写?
《记者手记之审讯》写得很累。由大量对话充斥的小说通常难写,不信各位试试看。而《记者手记之审讯》的难度还在于审讯者的突如其来以及被审讯者马六交代的匪夷所思的现实体验,它们看起来荒诞不经,可谁能否认,很多事件的似曾相识不过是我们“活着”的体认之一?写它的时候,我天马行空地放任着自己的想象力,尽管我干记者以来碰上的很多事情早已超出了想象——问题来了,当超出想象的荒诞一而再再而三地成为“常识”,你还有什么理由指责我的小说“荒诞”?这个小说的内核其实是马六本人无处诉说的悲凉——在一场荒诞不经的由极小事件引爆的浩劫中,他一再遭到亲生父母的抛弃,只能独自面对黑暗甚至死亡。这太可怕了。“审讯”反倒是一次倾诉的良机,但结局的吊诡似乎又让这场倾诉丧失了“意义”……马六的命运,再次被悬置起来。
至于《牛奁》,一起看似更加荒诞的“坠落”导致了男主角内心的急剧震荡,那个坍塌的大地洞肯定有象征和隐喻在焉,可我的本意是,那就是一个地洞而已;重要的不是坍塌,是坍塌之后,是男女主角的同居爱情或日常生活,真的像表面上看起来的那么稳固吗?答案,大概是否定的。我的想象力告诉我,肥胖的女主角必然坠到楼下,而不是像马六的父母那样飞到天上。不由自主地向下,无论对于爱情,还是对于生活,都是合适的吧……
是的,我放任着并且相信着我的想象力。
这类小说极有可能成为双刃剑——解构现实的同时也伤及自身,成为某些人,尤其是某些文学卫道士们狠狠挞伐的对象,口实无非是,卡夫卡或博尔赫斯式的小说,由他们去写就足够了,何必东施效颦、出乖露丑?瞎编,谁不会呢?这样的指责义正词严,而且,你真的很难推翻他们——建构于现实基础上的现实主义,你怎么可能推翻?除非你是火星人。但我想说的是,如果一个写作者不遵从自己的内心冲动,如果不愿意换一个哪怕是看起来荒诞不经的视角大量“现实”,如果他始终削尖脑袋非要为了现实主义而现实主义,那样的写作,永远无害,却又多么无趣啊。我想借助记者手记系列表达的,无外乎小说当然可以是“轻”的,是胆大妄为无所不能的,但其内在,它应该也必须忠实而严格地传达我们对现实的种种质疑、批判与反思;小说的一大功能无非是提供一个有效故事,但如果小说家不仅仅提供故事,还任意折叠故事、弯曲故事和变形故事,它所呈现的现实难道不是我们更熟悉的现实?而在那样的“非现实”语境中,我认为,才更接近我们活脱脱的日益魔幻的当下——我从来不觉得二十一世纪的中国社会现实比之马尔克斯、胡安·鲁尔福们的现实更像现实,相反,它们无限接近虚构,接近所谓“魔幻现实主义”的源头,它们敦促你脑洞大开、想象的汁液不断分泌,以一种荒谬而真切的方式成为认知当下和自身的基本出发点。为此,我倒真想看看,将我们熟悉的现实拆散重组,现实究竟会急剧下坠,还是飞走消失?
放任想象力的挑战在于,写作的过程自由而畅快,但故事或叙述的边界又是如此的苛刻,两者怎样和谐共存,对写作者提出了高难度挑战,谁也无法保证你的挑战成功还是失败了,但,唯其“真诚”和“真实”,我为我的投入深感幸福。
还有更多更好的天马行空的小说构思呢,就待在我脑子里,我会一个一个写出来。有的确乎很现实,但大多数仍然“超现实”。我越来越发现,比起现实,我更乐于信任我想象的现实——它太不着边际啦,简直是一匹无法无天的野马。我真不知道我还能干出点什么来。再次感谢优秀的《小说林》,让我如此的任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