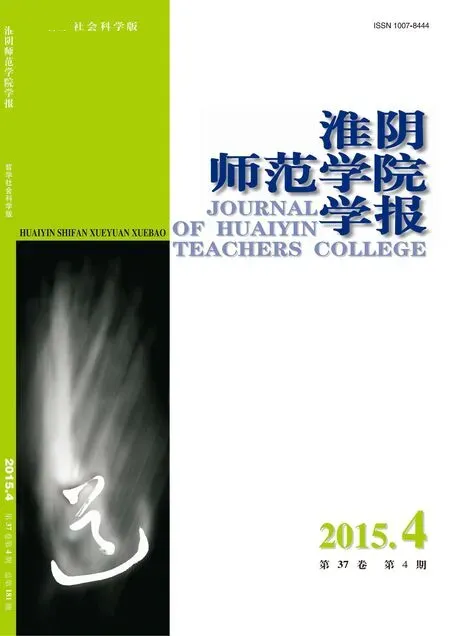从《左传》的人物称谓看其编纂过程
唐明亮
(南通大学范氏诗文研究所,江苏南通226019)
读《左传》,会发现作者对人物称谓的使用时而统一,时而混乱,往往名、字、谥号、职官、封邑混用,甚至在同一事件中不断变换称谓,若不借助杜注,读者根本不明其中的人物关系。学者对此早有感触,章学诚指出:“尝读《左氏春秋》,而苦其书人名字,不为成法也。夫幼名,冠字,五十以伯仲,死谥,周道也。此则称于礼文之言,非史文述事之例也。左氏则随意杂举,而无义例;且名字谥号以外,更及官爵封邑,一篇之中,错出互见;苟非注释相传,有受授至今,不复识为何如人。是以后世史文,莫不钻仰左氏,而独于此事,不复相师也。”[1]393章氏所言现象属实,但其产生之由,恐非《左氏》作者一人为之。细读其中人物称谓之变化,并非杂乱无章,却有一定规律。这种规律,因国、因人而异,或是作者在引用各国史料时逐渐产生的。归纳其中人物称谓的变化规律,庶几可以探索出《左传》的编纂过程来。
一、对周天子与鲁国人物的称谓
首先看对周天子的称谓。《左传》记周天子之事,多数都有经有传,在《春秋》经中能找到相对应的记载。但在称谓上二者有同有异,《春秋》只称周天子为“天王”,而《左传》中却有“王”与“天王”两种称谓,先看其相异处:
《春秋经》隐公七年:冬,天王使凡伯来聘。
《左传》:冬,王使凡伯来聘,还,戎伐之于楚丘以归。[2]52-55
《春秋经》文公元年:天王使叔服来会葬……天王使毛伯来锡公命。
《左传》:元年春,王使内史叔服来会葬。公孙敖闻其能相人也,见其二子焉……王使毛伯卫来锡公命。叔孙得臣如周拜……[2]508
《春秋》称周天子为“天王”,《左传》称“王”。这种称谓上的差异,在僖公十三年、昭公二十三年、二十六年皆可见。凡《春秋》称“天王”处,《左传》皆称“王”。在这些史料中,二书对于其他人物的称谓也不同,如《春秋》之“叔服”,《左传》称“内史叔服”;《春秋》之“毛伯”,《左传》称“毛伯卫”。除了人物称谓不同外,《左传》对于每一事件的记载,都比《春秋》要详细得多,除了事件本身以外,《左传》作者还补充了很多后续发生的事情。这些后续发生的史事,并不是针对经文而作的解释,而只是史事的延续。如“还,戎伐之于楚丘以归”一句,并不能解释《春秋》中“天王使凡伯来聘”。“公孙敖闻其能相人也”一段话,也不能作为对经文“天王使叔服来会葬”的解释,这说明,二书根本是两个不同版本的鲁史,并不存在解释与被解释的关系。
然而又有几处相同的地方,存在着解释与被解释的关系:
《春秋经》隐公元年:秋七月,天王使宰咺来归惠公、仲子之赗。
《左传》:秋七月,天王使宰咺来归惠公、仲子之赗。缓,且子氏未薨,故名。天子七月而葬,同轨毕至;诸侯五月,同盟至;大夫三月,同位至;士逾月,外姻至。赠死不及尸,吊生不及哀,豫凶事,非礼也。[2]8
在这一则史料中,《左传》与《春秋》对周天子均称“天王”,不仅如此,叙述的文字也完全相同,从“缓……非礼也”的解经语中也可以看出这一点,这段补充文字并非史料,而是对经文的解释。对于这段解经语,赵光贤先生在《左传编纂考》中指出:“人未死而先去送助丧之物,这是大悖情理的事,恐怕周天王不会糊涂到这种地步。”[3]57这些解释的荒谬之处,学者们也已指出其成因。王和先生认为这是后代经师为了将《左传》改成解经的形式而附益进去的,因为“这位解经者对于《春秋》的基本内容都并不熟悉,也许仅仅是依据《礼记》的说法,就轻易添加了这么一段话”[4]。
可见,《左传》中的文字完全是对《春秋》的抄袭,所谓解经只是一种形式。由于没有更多史料的补充,经师们便妄加解释,以致破绽百出。因此,在对周天子的称谓上就与《春秋》一致。类似的抄袭还见于桓公十五年:
经:天王使家父来求车。
传:天王使家父来求车,非礼也。[2]141
这是经师们对史事实在无法解释了,便加了一句“非礼也”的解经语,也是为了把《左传》作成解《春秋》的传。由此可以断定,《左传》对于周天子也有特定的称谓——“王”。凡称“天王”处,都是经师们直接抄袭《春秋》的文字,在抄袭的过程中,没有将《春秋》中的称谓转换成《左传》中的称谓。
在对鲁国卿大夫的称谓中,也有同样的现象出现。《春秋》对于鲁国未受分封的卿大夫称“公子某”,如“公子友”“公子翚”,对受封的卿大夫称谓方式是“氏+名”,如“季孙行父”“叔孙侨如”等,非常有规律。而《左传》对鲁国卿大夫的称谓规则,有时与经文相同,有时又不同。以季氏家族为例,家族第一代,《春秋》中只称“公子友”,而《左传》中却有“季友”“公子友”两种称谓。先看与《春秋》称谓相同的传文:
其一:
《春秋经》庄公二十七年:秋,公子友如陈,葬原仲。
《左传》:秋,公子友如陈,葬原仲,非礼也。原仲,季友之旧也。[2]236
其二:
《春秋经》僖公元年:冬十月壬午,公子友帅师败莒于郦。获莒拏。
《左传》:冬,莒人来求赂。公子友败诸郦,获莒子之弟拏。非卿也,嘉获之也。[2]277
其三:
《春秋经》僖公三年:冬,公子友如齐涖盟。
《左传》:冬,公子友如齐涖盟。[2]285
以上三则传文,除了或多或少加了一些解经语之外,所叙述的内容基本上与《春秋》完全一致。虽然这里的解经语是否合理,我们无从判断。但从形式上看,它们与前面的抄袭手法非常相似。应该也是经师们抄袭《春秋》之后附益进去的。另有几处无经之传与《春秋》称谓不同:
《左传》庄公三十二年:……问于季友。僖公元年:公赐季友汶阳之田。[2]279
可见,在无经之传中,季氏之始祖称作“季友”,这应该是《左传》对该人物本来的称谓,但改造成解经之传后,又多出了经师们从《春秋》中抄来的称谓“公子友”。因此,《左传》中凡称“公子友”处,其内容均与《春秋》经文相同或非常相似。经师的抄袭方式有解经的,有不解经而直接抄袭的,也有依据其他史料略作补充的,但都没有将《春秋》的称谓转换为《左传》中的称谓。
在对鲁国其他卿大夫的称谓中,二书同样存在着称谓上的差异。如对季平子的称谓,《左传》多称谥号:
昭公九年:冬,筑郎囿,书,时也。季平子欲其速成也……[2]1312
昭公十二年:季平子立,而不礼于南蒯……[2]1335
昭公十六年:公至自晋。子服昭伯语季平子曰……[2]1382
另外,“季平子”之称谓还见于《左传》昭公十七年、二十五年、定公元年、五年。这些史料都呈现出相同的特点,都是无经之传。这应该是《左传》作者对鲁国卿大夫特定的称谓方式,其他各家卿大夫,如叔孙氏、仲孙氏、臧氏等,也都是称谥号而不称名。但也有几处不称谥号而称“季孙意如”,凡带有“季孙意如”这一称谓的史料都与《春秋》完全相同,有些地方还掺入了解经语:
《春秋》昭公十三年:晋人执季孙意如以归。
传:晋人执季孙意如。[2]1342
《春秋》昭公十四年:十有四年春,意如至自晋。
传:十四年春,意如至自晋,尊晋罪己也。尊晋、罪己,礼也。[2]1363
《春秋》昭公三十一年:季孙意如会晋荀跞于适历。
传:季孙意如会晋荀跞于适历。[2]1510
这一称谓的变化同样是经师们抄袭《春秋》改造《左传》的结果,内容上完全相同。在经师们没有将《左传》改造成解经之传前,作者对季平子其人只有谥号“季平子”这一种称谓,这是作者对鲁国卿大夫的称谓方式。而“季孙意如”这一称谓,则是《春秋》经的称谓方式,经师们直接抄袭《春秋》原文补充《左传》的痕迹很明显。抄袭的方法,与其他地方对《春秋》经文的抄袭完全一致,都是直接抄袭或者加上解经语略作改造。可以看出,《春秋》和《左传》本是两个不同版本的鲁史,两位作者对于鲁国人物各有固定的称谓,经师们在改造《左传》的过程中,将《春秋》作为补充的史料来使用,目的是把原始的不解经的《左传》,改造成一个新的解经的《左传》,但却没有统一两书在称谓上的差异。因此,对同一人物便出现不同的称谓方式。
二、对他国人物的称谓
对周天子和鲁国人物,《左传》作者有自己的称谓方式,在后来不断增益的过程中,又掺入了《春秋》中的人物称谓方式。除此以外,还有对其他各国人物的称谓方式,这些人物称谓总的看来是十分混乱的,但按照国别来分,在一定的时间段内也是有规律的。
1、晋国。《左传》对晋国卿大夫的称谓有谥有名,以赵氏为例,自赵衰以后,对于家族的大宗或族长,谥号与名并用,如赵宣子赵盾、赵庄子赵朔等;而对小宗或侧室,多称名,如赵同、赵婴齐、赵获等,但从不称字或职官。
就大宗而言,在人物第一次出场和对外战争中,作者多称名。僖三十二年,“以叔隗妻赵衰,生盾”。这是赵盾第一次出场,作者不称之为赵宣子。此后,文六年、七年、九年、十二年、十四年的多次战争中,也只称“赵盾”而不称“宣子”,在其他的战争中作者也是习惯称呼双方统帅的姓名。因此,这应该是《左传》作者的称谓习惯,目的是为了将史事叙述得更加清楚。因为名是一种特指,而宣子的谥号在晋国则有多人,如韩宣子、知宣子。但在其他史事中,作者对赵盾的称谓常常名与谥混用。如宣二年:
秋九月,晋侯饮赵盾酒,伏甲将攻之……初,宣子田于首山……宣子使赵穿逆公子黑臀于周而立之……赵盾请以括为公族……冬,赵盾为旄车之族。[2]659-666
赵盾弑君之事在《公羊传》《谷梁传》《史记》三书中均有记载,对赵盾只称名,而不称谥,可见这三书作者对人物是有固定称谓的。而《左传》作者在对赵盾弑君及其后所发生的一系列事件的记述中,时而称“赵盾”,时而称“宣子”,初读者若不借助杜注,只能凭推测来断定二者的关系实为一人。类似的情况还出现在文十四年:
晋赵盾以诸侯之师八百乘纳捷菑于邾。邾人辞曰:“齐出玃且长。”宣子曰:“辞顺而弗从,不祥。”乃还。[2]604
这种变换称谓的记述方法无形中给读者增加了阅读的困难,宋子然在谈到《左传》中的这类史料时说:“用一个人或事物的异名别称互相代用,固然不至改变原意,问题在于这种异名别称并不为人所共知,如果随意乱用,杂然并陈,势必令人迷惑不解,给阅读带来困难。”[5]340按常理来说,作者完全没有必要将史料写得让读者读不懂,因此,这一定不是作者的初衷,而是在转引的过程中产生的。对晋国卿大夫国内活动的记载,应出自晋国史书。因为晋国史官对本国人物是非常熟悉的,所以,在著史过程中对于人物可任意选择不同称呼。这些人物,在当时都非常著名,应该是人所共知的。只有在这种情况下,称谓的变化才不会造成阅读的困难。甚至到了《左传》作者所处的时代,也不会造成阅读的困难。因此,晋国史官以及《左氏》作者均无意去统一称谓。但时代愈后,文意的不解就慢慢加深了。
据此,我们可以推测,对他国卿大夫称名,是《左传》作者的称谓方式;先称名而后称谥,名与谥混用,是晋国史官的称谓习惯。《左传》作者在编写晋国史时,有改有不改。凡某一事件中对人物一直称名,应是《左传》作者用自己的语言编订改造后的史料。若某一事件中对人物称谓是名与谥号混用,则是直接摘抄晋国的原始史料。这一推定,在其他各国史料的引用中也可以得到进一步验证。
2、楚国。以楚国国君为例,《春秋》经对楚国国君只称其爵位“楚子”,而《左传》作者对楚国国君的称谓也是前后不同,有时称其爵“楚子”,有时则称“王”。“子”的爵位,是西周时期周成王册封给楚国的,《史记·楚世家》载:“周成王……封熊绎于楚蛮,封以子男之田。”[6]1691到春秋时期,中原各国对楚国国君的称谓是固定下来了,只称“楚子”①郭沫若《周代彝铭中无五服五等之制》、杨树达《古爵名无定称说》都曾指出。,而“王”则是楚君自称。在中原地区,只有周天子才有资格使用这种称号。而处于边陲的楚、吴、越等国,却不受此种规定之约束,常常僭称“王”。鲁桓公六年(公元前706年),楚武王熊通请周王室尊其王号遭到拒绝,自陈曰:“成王举我先公……蛮夷皆率服,而王不加位,我自尊耳。”[6]1695于是自上尊号为“王”,从此便一直以王自称。从传世的考古材料中,也可得到印证。“《楚王腾邓仲埔钟》和《楚王领钟》均系楚王所作……再有春秋早期的《中子化盘》提到‘用保楚王’,和《王子午鼎》的器主都是楚国王子。”[7]但这一称谓没有得到中原各国的承认。鲁国史书《春秋》就一直称“楚子”。
根据这样一种称谓习惯来看,《左传》作者对于楚国国君应当只称“楚子”而不称王,但实际上书中对楚君的称谓则是二者混用。例如:
冬,楚子为陈夏氏乱故,伐陈。谓陈人无动,将讨于少西氏。遂入陈,杀夏征舒,轘诸栗门,因县陈。陈侯在晋。
申叔时使于齐,反,复命而退。王使让之曰:“夏征舒为不道,弑其君,寡人以诸侯讨而戮之,诸侯、县公皆庆寡人,女独不庆寡人,何故?”对曰:“犹可辞乎?”王曰:“可哉。”曰:夏征舒弑其君,其罪大矣,讨而戮之,君之义也。抑人亦有言曰:牵牛以蹊人之田,而夺之牛。牵牛以蹊者,信有罪矣;而夺之牛,罚已重矣。诸侯之从也,曰讨有罪也。今县陈,贪其富也。以讨召诸侯,而以贪归之,无乃不可乎?王曰:“善哉!”吾未之闻也。反之,可乎?对曰:“可哉!吾侪小人所谓取诸其怀而与之也。”乃复封陈,乡取一人焉以归,谓之夏州。故书曰:“楚子入陈,纳公孙宁、仪行父于陈。”书有礼也。[2]713-716
这一段文字中,对楚君前后都称“楚子”,而中间则称“王”,变化颇为奇怪,若不结合上下文,对于第一段中的“楚子”和第二段中的“王”是否为同一人,都无法判断。这种人物称谓的突然转换,实际上是作者在转述史料和引用史料过程中没有兼顾到前后文的结果。第一段“冬,楚子为陈夏氏乱故,伐陈。”一句,是作者对阅读到的史料的转述,在转述过程中,按照中原地区的习惯,称楚国国君为“楚子”。而第二段则是直接摘抄自楚国的原始史料,对其中“王”的称号没有作相应改动。第二段最后一句“故书曰:‘楚子入陈,纳公孙宁、仪行父于陈。’书有礼也”,则是后代经师为了将《左传》改为解经之传而作的附益之词。经师自认为楚庄王此举为义举,值得称赞,但同时又无法解释楚庄王之举符合怎样的“礼”,于是便抛下“书有礼也”一句空话作为解经语。
由此可见,《左传》作者在对楚国史料的引用中,也是有改有不改。凡对楚君称“王”处,当是直接引自楚国的史料,而称“楚子”处,一是作者自己对楚国历史事件转述时产生的,二是经师们为了改造《左传》而直接抄自《春秋》的。但是,在转述和直接引用过程中,作者对于楚国国君的称谓没有作相应调整,因而产生了前后称谓差异。
3、郑国。郑国史官对于本国卿大夫,也有特定的称谓习惯。在大多数的历史事件中,对于参与其中的人物,都只称字。如襄十九年:
郑子孔之为政也专。国人患之,乃讨西宫之难,与纯门之师。子孔当罪,以其甲及子革、子良氏之甲守。甲辰,子展、子西率国人伐之,杀子孔而分其室。书曰:“郑杀其大夫。”专也。子然、子孔,宋子之子也;士子孔,圭妫之子也。圭妫之班亚宋子,而相亲也;二子孔亦相亲也。[2]1050
此事件中所有人物均只称字,即便有两人的字同为“子孔”,也不改称名加以区分,只有在会盟、朝聘等重大场合称名。以印氏家族印段为例:印段在《左传》中共出现七次活动,其中六次出现在朝聘会盟的场合中,因此均称名。只有襄公三十年的一次历史事件中称字。这一称谓习惯,从某一家族数代人的称谓中都能够得到验证。
以郑国良氏为例,《左传》中共记载了良氏家族四代人,列表如表一[8]1335:

表一
这一家族中,始祖子良在《左传》中一直都是称字,二代子耳也一直称字,只在一次会盟中称名:
十一月己亥,同盟于戏,郑服也。将盟,郑六卿公子騑、公子发、公子嘉、公孙辄、公孙虿、公孙舍之及其大夫、门子皆从郑伯。晋士庄子为载书……[2]968
此称名处,与印段称名的场合相同,说明会盟称名、常事称字是郑国史官的称谓习惯。可以推测,这些史料都是取自郑国史官之手。四代良止因事迹不详,不便讨论。唯独对于第三代良霄的称谓,变化颇大。多数情况下都是称其字——伯有,但是竟有四处称名,分两组列举如下:
襄二十六年:六月,公会晋赵武、宋向戌、郑良霄、曹人于澶渊以讨卫,疆戚田。[2]1115
襄二十七年:五月甲辰,晋赵武至于宋。丙午,郑良霄至。[2]1129
这一组的两则史料中,为什么会突然称其名了呢?参照《春秋》经文便知,这两处实际上是抄自《春秋》,应该也是后代经师们为了解经而从《春秋》经文中抄来的称呼。若将另外两则史料与经文对比,更能坚定这一推定:
襄十一年《春秋》经:楚执郑行人良霄。
《左传》:九月,诸侯悉师以复伐郑。郑人使良霄、大宰石如楚,告将服于晋……楚人执之,书曰“行人”,言使人也。[2]990
襄三十年《春秋》经:郑良霄出奔许,自许入于郑,郑人杀良霄。
《左传》:书曰“郑人杀良霄”。不称大夫,言自外入也。[2]1177
从这一组史料中可以明确看出,经师们改《传》以解《经》的手法是多么明显!以伯有、良霄称呼观之,对于伯有其人,《左传》作者本来是直接引用郑国的史料称其字“伯有”。但后来经师在将《左传》改为解经之传时,又抄了《春秋》经中“良霄”这一称谓,因此,便出现了名与字两种不同称谓。因此,传文凡称“伯有”处,都是无经之传,凡称“良霄”处,都有经有传。
4、宋国。《左传》中对宋国卿大夫多称名,如:
文七年:公子成为右师,公孙友左师,乐豫为司马,鳞矔为司徒,公子荡为司城,华御事为司寇。[2]556
文十六年:华元为右师,公孙友为左师,华耦为司马,鳞鱹为司徒,荡意诸为司城,公子朝为司寇。[2]620
这种称谓习惯在襄公以前一直是比较统一的,顾栋高《春秋大事表》统计宋国卿大夫十三家一百多人,在襄公以前的历史事件中,称字的仅有子鱼一人[8]1305-1334。但在鲁襄公以后的宋国史料中,对人物的称谓就比较混乱了。称字有之,称官职有之,乐氏一家就忽然出现五个人常称字,还有多处混用的情况,如定公九年:
九年春,宋公使乐大心盟于晋,且逆乐祁之尸。辞,伪有疾。乃使向巢如晋盟,且逆子梁之尸。子明谓桐门右师出,曰:……[2]1571
这段史料对宋国卿大夫称谓极其混乱,乐大心、乐祁、向巢是称名;子梁、子明是称字;桐门右师是称官职。其中“子梁”是乐祁的字,“桐门右师”是乐大心的官职,均为同一人的不同称呼。在同一事件中对人物不断变换称谓,于宋国最多。若不借助杜注,读者完全不知所云。杨树达在分析这种现象时说:“《左氏传》于同一篇中称举同一人者,名字号谥,错杂不恒,几于令人迷惑,斯为极变化之能事者……然作《左氏传》意在求美,后人之误解与否,非所计及,其求美之意之切,亦可推见矣。”[9]43依杨氏之说,作者不断变换称谓,为的是使历史的叙述语言更加优美。然从以上所引这段文字中,着实体会不出优美来。再者,史家以此种方式追求文辞优美,以致阻隔文意,不仅于后代史书中从未见过,就先秦典籍中也无可稽考。一种合理的解释是,由作者直接传抄宋国的原始史料造成了人物称谓的复杂性。因为只有宋国的史官,才有可能对宋国众多人物的称呼达如此熟悉的程度,可以任意使用人物称呼而无需统一修改。因此,可以推测,宋国史官对人物的称谓实无一定标准。这可能和宋国世族众多,政局不稳,官职变换不定有关系。《左传》作者在处理宋国史料时,也是有改有不改。襄公以前的人物称谓都作了统一修改,按照自己对他国卿大夫的称谓习惯,全称名。而襄公以后的,可能是没来得及修改而直接引用了宋国的原始史料,因此人物称谓显得比较混乱。
此外,对于齐、卫、楚诸国卿大夫的称谓,也各有特点。齐国卿大夫多称谥与名,偶尔称字,如高敬仲傒(谥与名混用)、高止子容(名与字混用),但绝不称其官职。卫国卿大夫只称谥与名,如石成子稷、石共子买,但绝不称字。楚国卿大夫多称名与字,如斗谷於菟字子文,又有称封邑、官职和名,如申(封邑)公(官职)斗班、芋(封邑)尹(官职)无宇,但绝不称谥号。这些应该都是《左传》作者在传抄各国史料时,对各国史官称谓习惯的保留。不过,对于一些特殊人物的历史记载,作者在编纂过程中对史料作了精心处理,并不照抄原始史料。在人物称谓上改用自己特定的称谓。
三、对特殊人物的称谓
《左传》作者对各国的人物称谓,虽然因为对各国史料的摘抄,造成五花八门的景象,但是对于某些特殊人物的称谓则相对固定,全不遵循各国史官的习惯。例如齐国管仲、郑国子产、晋国叔向、宋国子罕等人。从前文的分析总结中可以看出,春秋时期各国史官都有各自的称谓习惯,几乎没有对某一人物始终用固定的称谓。那么,这种对某一人物的固定称谓,一定是经过作者统一改造过的。《左传》作者在编纂史料过程中,将原来不统一的人物称谓改为固定的人物称谓,说明作者对这些史料都作了精心改造,对这些人物给予了特别的关注。
对于管仲,作者几乎只称名,在称谓上非常固定。这说明作者在记述管仲的事迹时注意到了称谓的统一性。
对于郑国子产,其事迹颇多,自襄公十九年子产立为卿至昭公二十年子产去世,几乎每年都有子产的事迹,并且对于每个故事中子产的行动、语言都记载得极其详细,可以说,《左传》中再没有哪个人的事迹比子产的事迹更多更详细了。全书记载子产事迹百余条,几乎都称字。但也有四处称其名“公孙侨”,这四处都是在朝聘会盟场合:
襄二十二年:夏,晋人征朝于郑。郑人使少正公孙侨对曰:……[2]1065
昭元年:六月丁巳,郑伯及其大夫盟于公孙段氏,罕虎、公孙侨、公孙段、印段、游吉、驷带私盟于闺门之外,实薰隧……晋侯有疾,郑伯使公孙侨如晋聘,且问疾。[2]1215
昭六年:楚公子弃疾如晋,报韩子也。过郑,郑罕虎、公孙侨、游吉从郑伯以劳诸柤。[2]1278
这种称谓的变化符合郑国史官的称谓习惯,因此,关于子产的这几则史料极大可能是来自郑国的原始史料,而其他史料则是经过作者编订的。
对于其他特殊人物,《左传》作者也都有固定的称谓。如晋国叔向。根据前文所总结的晋国史官称谓习惯,于卿大夫多称名与谥号,但是对于叔向,仅称名一次,其他事件中均称字。这种称谓,应当不是来自晋国史书中的称谓,而是《左传》作者自己对叔向的特定称谓。
同样,对于宋国子罕也是如此,宋国史官对卿大夫均称名,而对子罕仅称名(乐喜)一次,其他事件中均称其字“子罕”。另外,除了宋国子罕之外,郑国也有个子罕。作者在叙述二人故事时,特别加以区分。对宋国子罕只称“子罕”,而对郑国子罕则称“郑子罕”,以示区分。但对于其他同名人物,作者多数情况下都不加区分,如子孔,郑国有两个子孔、楚国有一个子孔,作者均只称子孔。由此可以看出,宋国的子罕在作者心目中是个特别的人物。
这些人物的固定称谓,在《左传》中不能不说是一个很特别的现象。除了称谓比较固定外,这些人物还有其他一些共同点:
第一,这四个人物,每个人出现的年代跨度都较大。管仲初次出现于庄公九年,最后一次出现于僖公十七年;宋子初次出现于襄公六年,最后一次出现于襄公二十九年;子产初次出现于襄公八年,最后一次出现于昭公二十年;叔向初次出现于襄公十四年,最后一次出现于昭公十五年。《左传》中除鲁国人物外,将一人之事迹分割于几十年中来叙述,而前后称谓几乎无变化,仅此四人。这说明这四人的称谓是经过作者统一修改过的。
第二,进一步设问,作者为什么会对这类人物给予极大关注呢?从这些人物的史料中可以看出,他们的言行有两个共同点:一是好作预言,且极为准确。除管仲外,其他三人都有预言。如襄公八年,郑人侵蔡得胜,举国欢庆,年纪尚幼的子产却预言说:“小国无文德,而有武功,祸莫大焉。楚人来讨,能勿从乎?从之,晋师必至。晋、楚伐郑,自今郑国不四五年,弗得宁矣。”后来情况果如子产所言。孩童能对国家大事有如此独到的先见之明,实在罕见!叔向预言最多,且准确率很高。管仲虽无预言,但他对政治事件发展态势的分析是有远见的,能将政治危机消灭于萌芽之中,亦可视为另一类型的预言。反观《左传》作者所作的预言,与此类预言的形式完全一致。同类相求,也许是作者关注这类人物言行的一个重要原因。二是这些人物都特别推崇儒家的德、礼、仁、义,其中以德与礼两种伦理最受推崇。管仲曰:“招携以礼,怀远以德,德礼不易,无人不怀。”叔向曰:“(天道)在其君之德也。”这些儒家的伦理观念,也是《左传》作者所推崇的,作者似乎是以他们的言行来宣扬儒家思想,视其为隔代知音。因此,对这些人物的史料,作者在撰写时非常详细,倾注了极大的力量,所以,人物称谓也是统一的。
第三,从书中对这些人物的评论,也可以找出他们的共同点。如:
对管仲:
君子曰:“管氏之世祀也宜哉!让不忘其上。《诗》曰:‘恺悌君子,神所劳矣。’”[2]342
对叔向:
仲尼曰:“叔向,古之遗直也……三言而除三恶,加三利,杀亲益荣,犹义也夫!”[2]1367
对子产:
仲尼闻是语也,曰:“以是观之,人谓子产不仁,吾不信也。”……及子产卒,仲尼闻之,出涕曰:“古之遗爱也。”[2]1422
对子罕:
君子曰:“‘彼己之子,邦之司直。’乐喜(按:即子罕)之谓乎?‘何以恤我,我其收之。’向戌之谓乎?”[2]1136
从以上的评论中可以看出,《左传》作者对于四人的认识都是正面的,褒赞的。从书中的记载来看,作者总是会对其褒赞的人物用墨较多,着力较大,而于此四人最甚。管仲是恺悌君子,叔向是古之遗直,子产是古之遗爱,子罕是邦之司直,因为他们的高尚品格和人格魅力,吸引作者将其事迹记录下来。这些事迹的篇幅和故事叙述的连贯性,都甚过对那些小人物的描写,因此,有理由相信这些史料都是经过作者改造的。在编纂过程中,作者使用的是自己对这类人的特定称谓,而不是直接抄自原始史料,使用他国史官的称谓习惯。
四、结语
关于《左传》的编纂过程,赵光贤先生与王和先生已撰系列论文,从叙事的连贯性、预言、历法、解经语等方面找出了大量有力的证据,证明《春秋》《左传》本为两书。那么,从《左传》的成书到后来被篡改附益为解经之传,到底留下了多少痕迹证据呢?人物称谓的复杂可算作一证。
从以上的分析中可知,春秋时期各国史官在撰写历史时,对本国人物都有各自的称谓习惯,而《左传》作者对各国人物也有自己的称谓习惯。在引用这些史料时,作者对于原始史料中各国不同的称谓习惯,有改有不改,既保留了各国史料中史官的称谓习惯,也用自己的语言改造了一部分史料。后代经师在传授《左传》的过程中,又抄袭另一版本鲁史——《春秋》——的内容以补《左传》,以造成解经的假象,但没有协调好称谓问题,因而也有《春秋》作者的称谓习惯混入《左传》,由此造成人物称谓的大混乱。因此,《左传》中的人物称谓,依其来源,可分为三类:
一是作者在引用原始史料时,直接摘抄他国史官对各国人物的称谓习惯,未加改动。
二是作者本人对人物的特定称谓。这一特定称谓又分为三类:1、对周天子和鲁国人物,作者的称谓都是固定的,不随意称名称字,改变称谓。结合鲁史《春秋》经来看,鲁国史官对本国人物大体上是使用固定的称谓的;2、对他国人物的特定称谓。这些人物的言行符合儒家德、礼、仁、义之伦理,又都有高尚的品格和非凡的魅力,吸引了作者极大关注,视其为个人理想的践行者。因此,作者在撰写他们的史料时并不是直接摘抄原始史料,而是作了细心的编纂,人物的称谓在作者编纂史料的过程被统一修改成固定称谓;3、在转引史料和叙述过程中,对他国国君以下的人物均称名。
三是后代经师在改造《左传》以解《春秋》时,直接抄自《春秋》的。
据此可以推定,《左传》一书的形成至少经过了三个阶段:对各国史料的摘抄,对特定人物史料的改造,以及后代经师们在传授过程中附益进去的文字。随着对《左传》一书越来越深入地解读,应该会有越来越多证据的支持。
[1] 章学诚.文史通义校注[M].北京:中华书局,1985.
[2] 杨伯峻.春秋左传注[M].北京:中华书局,1981.
[3] 赵光贤.《左传》编纂考[M]//中国历史文献研究集刊:第 1、2 集.长沙:岳麓书社,1980.
[4] 王和.《左传》中后人附益的各种成分[J].北京师范大学学报,2011(4).
[5] 宋子然.中国古书校读法[M].成都:巴蜀书社,2004:340.
[6] 司马迁.史记[M].北京:中华书局,1959.
[7] 王世民.西周春秋金文中的诸侯爵称[J].历史研究,1983(3).
[8] 顾栋高.春秋大事表[M].北京:中华书局,1993.
[9] 杨树达.汉文文言修辞学[M].北京:中华书局,198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