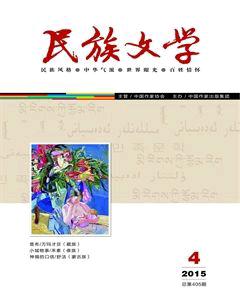从前的树
周碧麟
去年腊月回到乡下,母亲对我说,准备把屋后的柿子树砍掉做柴烧,砍树的人都请妥了。我很吃惊,说:为什么不能留下呢?母亲说,柿子没人要,变不成钱。树太高了,柿子摘不下来,掉在地上烂得到处都是,树大了荫田,庄稼长不好,不如砍了做柴,还可以烧上半个冬天。我不赞成母亲的意见,做柴半个冬天就烧没了,这棵树可是已经长了好几十年!想想这是我们家仅剩的一株果树,也是我们村子仅存的几株柿子树,砍了,孩子们要吃柿子,哪里去找呢?于是我与母亲商量,田荒了由我来补偿,柿子弄不下树我会回来帮忙,留下柿树会多个念想,母亲只好作罢。幸亏回家及时,为这棵比我年纪大许多的树挽回了一条性命。我想,只要能力所及,无论如何,我得把这相伴我童年和青春岁月仅有的一棵树保住,也算是对祖辈的慰藉。至于到泥菩萨过河的时候,那只好由它去了。
我的家乡是柿树之乡,过去,每家每户都有几株大柿树。柿树肯活肯挂果,小树苗不要几年就繁果满枝,就像邻家阿香,几天不见,小鼻涕娃就怀上了崽。一到秋天,柿叶由青变红,然后一片片落下,藏在叶间的柿子便像新娘揭了红盖头,红灯笼高高挂起,村庄到处一簇簇、一团团火红,收成好,枝条常被压断。家里有闲人,就把柿子“叉”下来做成柿饼。“叉”柿子颇费精力,先要备一根长竹竿,把竹竿头削成鱼尾状,剖开一个小口,缠上绳索或是捆上细铁丝,叉竿就做成了。柿子树性脆,用叉竿咬住小树枝轻轻一扭,柿子就被连枝带叶绞下来。晴天的时候,在树下架好梯子,用绳子吊一只竹筐,不一会儿就会叉上满满一筐,很是热心。青涩的柿子叉下来,用清水浸泡三四天,就不涩了,叫泡柿子,味道也不错。要做柿饼,得等到秋天柿子成熟,刮皮,翻晒,好天气半个月才能成形,如遇雨天,辛劳就全报废了。做柿饼是极要耐心极麻烦的活儿,无怪乎母亲对这事不太热心。在生活困难的年月,柿饼是很珍贵的礼品。
曾有人尝试用柿子酿酒。我一直很困惑,青涩的柿子里怎么会出酒呢?可柿子酒还真有酒味,但毕竟比粮食酒差得远了,酸酸的,酒精度低,口感差,喝了还上头。即便如此,依然供不应求,没办法,有人就好喝这一口。父亲把青涩的柿子叉下来卖给酒厂,能换回几个买煤油和食盐的钱,因此对栽柿树也就有些兴趣。
我少小的时候,老屋周围还有许多树,多是祖辈植下的。记得我家大门前稻场坎边有四棵树,一棵柿子树,另有三棵厚朴树,都长得高过屋顶了。厚朴树皮是名贵中药材。厚朴树有挺直的树干,银灰色的树皮,宽大的叶片。大风吹过,树叶们也慷慨热烈,似掌声稀里哗啦,营造出一种极清平和谐的氛围。秋天树叶全落,只有枯瘦的秃枝在寒风中抖索。春天,枝条会变成一枝枝生花“妙笔”伸向天空,像要写出漫天锦绣文章。渐渐,广玉兰一样银白色的花朵挂上枝头,白花退去,又长出玉米样的苞子来。三棵厚朴树比肩而立,像士兵出操,白花竞放,是我家门前的一道风景。有一年,父亲得了一场重病,在公社卫生所医治,医生为他挽回了一条命。为谢救命之恩,父亲就把这三棵树全捐给了卫生所。他亲手砍下这几棵树,剥下的皮宽大如席。父亲把树皮展开,用大石头压平,待树皮全部风干,然后亲自送到卫生所。至于那棵柿子树,改革开放以后,生活好了,还有谁喝柿子酒呢?柿子变不成钱,父亲就把它砍掉了。柿树是什么时候訇然倒地,我在外乡谋生,不得而知。
稻场角的东西两侧还有两棵歪脖子枣树(家乡的枣树似乎全是歪脖子),是我祖母栽下的,在我记事的时候就有了大碗粗细。枣树枝条苍劲,一副饱经沧桑的模样。枣树总是比别的树生长节奏慢上一拍,春风过后,万木薰然,别的花木早已花团锦簇,枝繁叶茂,只有枣树依然不动声色,慢条斯理。桃花开过,枣树始有米粒大小的白花绽出,像一树眨着眼睛的小星星。枣花微露芬芳,引来蝶翻蜂舞,一时枝头好不热闹!花开时节是蜂蝶们的节日,秋天果熟是孩子们的节日。每到枣子成熟的季节,我就爬上枣树,像松鼠一样闪转腾挪,在枝叶间寻找最红的果实。枣子丰收的时候,我们还会把枣子打下来,煮熟,晒干,用糖蜜了,放到过年吃。
那年我家筑水泥稻场,为了让场地平整规则,父亲提议把枣树砍掉。那时我已经大了,并不留恋那几颗枣,只是觉得祖上种下的,可惜了,因而反对。父亲只好斧下留情。可枣树不服老,依然保持着旺盛的活力,枝条不断延伸,粗大的虬根拱出地面,把新修的水泥稻场顶得稀烂,无法打场,我不得不痛下决心。荒唐而又荒凉的年月,饥饿伴随我的童年,果树实在有恩于我们,之后好长时间,我都心存愧疚。而水果当不得饭,长在集体田里的果树影响庄稼生长,都被斩树除根了。
父亲栽过许多树,不过父亲栽树一定是从实用出发。物质匮乏的年月,生存是第一要务,人会变得极为现实。父亲喜欢栽几种树,一是杉树,这是一种极好的用材树,材质轻,质地细腻,耐腐蚀,有韧性,不走形,无论是做房子还是做家具,都是上好的木材。那时候的政策是,只要经公社批准,而且砍一栽三,就可自栽自用。父亲把房前屋后田边山边都栽上杉树,我家做房子,为我姐做嫁妆,以至于后来我参加工作后使用的木箱衣柜,全是用父亲栽的杉树。到现在,那些树蔸还在生出像模像样的杉树,就像父亲的后代生生不息。父亲还爱栽梧桐树和构树,梧桐树皮可以打草鞋,构树叶可以喂猪,树皮还能卖钱。
后来父亲又热衷于栽杜仲。杜仲树的皮和叶子有蚕丝一样坚韧的白丝,故又名丝绵树。杜仲树皮是名贵中药材,有两年,杜仲皮突然价格飙升,就像前些年炒作君子兰。发财梦让人疯狂,幼小的树苗也被残忍剥皮。人们认定栽种杜仲是致富的最好途径,上级号召把好田好地都拿来种杜仲。十年过去了,杜仲苗都有水瓶粗细,以往肥沃的土地成了荒草丛生的树林,树可以剥皮卖钱了,可这时杜仲竟成了没人要的贱物。十年的土地收益,十年的精心养护,十年的希望与梦想,到头来全都化为泡影。我家的杜仲树做了柴禾,父亲的心在滴血。市场真是太诡谲了!谁说得清十年之后世界会是什么样子呢?
扎根农村是我们那一代人的理想,对于未来,我那时一片茫然,我想,这辈子大概也就这样终老山寨了。因此,我学着兴家理业。有一天,我在别人家山林中发现一株小柏树,像毛笔,像宝塔,冬天枝叶不凋,姿色不减,我以为栽在家门口一定极出风景,于是把它移植过来。这树还真给我长脸,没几天都长得高过人头。正在有人称赞树长得好的时候,有人说了,长青树是栽在坟前的,栽在家门口不吉利。生老病死是自然规律,吉凶祸福乃生命应有之义,干树何事?后来我远走他乡,再回家时发现那棵树真的不在了,我知道为什么,自然不再追问。趋吉避凶是人之本能,自然现象往往会拿来比附人事。山上有些树完全靠种子落地生根,自然繁衍,如松树山棕树。这是两种不发芽的树,乡里人认为栽这样的树会影响后代繁衍,有“先人栽棕,后人不凶(多)”的说法。自生自灭,终老山林,其实是一种幸运,也算一种境界。
在我们村,从前有很多大树,千年古松、百年银杏都有。大炼钢铁的时候,用大树炼铁,铁没炼成,树被砍光,田园荒芜了,老人饿毙了!农业学大寨中,旱改水,坡改梯,凡不利于耕作影响粮食收成的大树均被铲除,斧锯所向,无一幸免。“木秀于林,风必摧之,行高于人,众必非之”,无知者无畏,名木大树也会遭人觊觎。我外公家一棵板栗树,粗细要四个人合抱,每年能收上千斤板栗,公社刘部长一声令下,板栗树就被锯成了公社的楼板。砍倒那棵大树实在不是件容易事,还专门请铁匠打了丈把长的锯条,十多个人忙活三四天,才把大树放倒。据说,大树锯到一半,锯子口上流出了殷红色汁液,像人血。还有一棵神樟,有一千多年寿命了吧,据说已经成仙,树上终年披红挂彩,树下终日香烟缭绕,鞭炮声不绝于耳。“文革”中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再也没有人敬香,大树就被砍下做成了供销社柜台,一进供销社大门,满屋都有樟木的奇香。而去年,最后一株百年银杏向村人依依道别,被城里人以两万元的高价买走了。大树进城是树的不幸,与其喧嚣,勿宁寂寞。
去年,我去了江西婺源。在晓起村,二十多棵千年神樟郁郁葱葱,隐天蔽日,让我深深震撼。我不知道这些神樟是如何逃过千百次的劫难,我对晓起人油然而生深深的敬意和羡慕。一代又一代精心呵护,实际是一代又一代的文化传承,这些樟树纵览岁月风云,阅尽人间沧桑,成为晓起人的物质和精神财富。长阳麻池是一座古寨,而今又焕发了生机与风采。那里有百年古建筑,千年的民俗民风,还有贺龙当年留下的革命遗迹。在当年苏维埃政府门前,有一株要几人才能合抱的银杏树,老人说,这是贺龙当年拴马的地方。这株银杏,成为历史的见证和革命文化的载体,几十年来,供人们怀念与景仰。如果没有树,泰山、黄山还有风采吗?孔林、苏杭园林还算文化吗?善待大树,不仅是我们对自然的一种态度,对后代的一种责任,也是人类对自身的一种观照。一个没有大树的村庄,文化根基一定不会很深,一个不爱种树的民族,究竟能够走出多远?走在乡村土道上,或是走进农家院落,我们常常会为偶尔见到一株大树而惊奇赞叹,大树就是一张文化名片。人们在城里置了新房,除了人,一切都是新的,家中没有十年以上的东西,甚至连一本书也找不到。虽有一些美其名曰文化的饰物,没有融进骨髓深入灵魂的物事,算什么文化?只是附庸文化的摆设而已。
树木可以禁受千百年恶劣自然环境的考验而顽强生存,却是无法逃过人类的斧锯加害。我周围有几位朋友,英年早逝了,令人扼腕。朋友阿陈正值人生盛年竟得了不治之症,他感叹道,人想要活到六十岁,居然还不容易!人犹如此,树何以堪!活过百年千年的大树,曾经历过多少世态炎凉、雨雪风霜,人之于自然,理应存有敬畏之心。有句谚语叫先人栽树,后人乘凉。给后人留些福祉,让他们生活得比我们更好些,这是我们的愿望,也是我们的责任。得到他们的怀想、敬重与感戴,则幸莫大焉!
责任编辑 安殿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