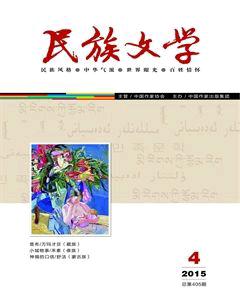代课教师
徐文
一
我去乡中学报到的那一天,村里最喜欢给人保红媒的刘大爷说:“啊哈,你小子没白写,终于写出个半拉老师来。”
刘大爷说我没白写,写出个半拉老师来,是指我爱写个新闻、通讯、故事、散文、诗歌、小说什么的,经常在市里县里的报刊、电台发表或播送。因为这个,我们乡十里八村的人都觉得我很了不起似的。这一下我去了乡中学当代课教师,大家都以为我是靠这个发的家。其实不然,我是参加了乡中学的统一命题考试。说实在的,光靠考试也不行,全乡二十几名高中毕业生,都来竞争那两个代课老师名额,并且考试后只有校长一个人批卷,分数不公开,校长说谁考得好,录取谁,就是谁。那时就已实行校长负责制了。
后来,我想我能被幸运地录取,一是我语文卷答了个满分(自我检查而得之),再就是我在乡政府工作的远房的表兄领我去校长家,给校长送了十瓶两元钱一瓶的酒,这酒起了不可忽视的作用。
说到半拉老师,指的就是代课老师。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不知什么原因,学校里忽然缺了那么多的老师。直到九十年代初,我们那的乡下中小学还有二三百人的代课教师。这些人千方百计、拼死拼活地想要自己一辈子都站在那泥砖砌就的讲台上吃粉笔灰,其中的酸甜苦辣和所付出的代价,可以说是各种各样的。
二
我们那所乡中学,坐落在山脚下,有一趟红砖灰瓦的教室,还有一趟老师学生混住的宿舍是泥墙灰瓦房,已有些破烂。一个操场很大,在跑桃花水和雨季时,山上下来的水就将这里变成待插秧的稻田,附近人家养的白鹅子和花鸭子都喜欢来这里嬉戏,学生们就不能做第六套广播体操,只好把做广播体操的时间用来在教室里连疯带闹。
因为我的写作水平,校领导让我教初一(一、二班)的语文。第一堂课,教导处于主任带着我去一班的教室。从办公室到教室的路上,于主任一句话也没说,夹着听课笔记,大步流星地走在我的前面。要到教室门口了,只听得里面像一窝吵翻了的蜂子。于主任一脚跨进教室,屋里的喧噪戛然而止。我跟进来,发现学生们脸有恐惧之色。于主任看看学生们,说:“这是新来的韩平老师,从今天开始,他教你们班的语文课。”说完,找个学生缺席的空座坐下。我也许天生就是当教师的料,我没有一点畏惧和失措,大大方方地喊了一句:“上课!”
学生中一人喊起立。我像老教师一样,环视整个教室,看有没有没站好的学生。这时,我发现墙角的一个座位上,还坐着一个女生,戴着眼镜,泰然自若,而她身边的那个女生站得笔挺。我顿时很生气,这是我第一天的第一节课啊!为了树立一个严肃的师表形象,我平静而坚定地说:“后面戴眼镜的那位女同学,请你对老师礼貌一点,站起来!”她愣了一下,但是却没有站起来,同学们的目光刷地一下都随着我的目光向后射去。几个调皮鬼立刻忍俊不禁,咬着嘴哧哧地笑。这时,戴眼镜的女生白净的脸一下子红到脖子根,腾地一下站起来,一双热辣辣的目光直直盯着我。我一下子觉得有点过分,不过,马上又有一种胜利感。我拿出极平静的语调说:“同学们请坐。”
这节课轻松自然地上完了,自以为很不错。下课回办公室的路上,于主任边走边对我说:“你的课上得不错,教态自然,教学语言也比较精炼、生动……只是……”
我慌忙点头哈腰,说:“于主任,我有什么错误您尽管批评指导,我初中时是您的学生,现在也是您的学生,将来还是您的学生。”于主任立定,站好,指着走到我们前面去的那个课堂上不起立戴眼镜的女学生,说:“她不是学生,是苟校长的千金,是去年来咱学校代课的教师,叫苟艳,她教初一三、四班的语文,所以才去听你的课,只是没有通知你。”
我听懂了于主任的话。一个篮球被学生当成足球踢,飞起来,正中我的面门,我手里的教科书和粉笔撒了一地。
三
我懵懵懂懂地回到办公室的时候,上课的铃声又响了,我差点和出来的苟艳撞个满怀。苟艳用白眼珠看了我一眼,急忙走了。我回头看她脑后那根辫子一摇一荡,心里竟稍微轻松些了。
我们语文组五名老师,四名代课的。只有教初二(三、四班)的丁老师是正式的,是两年前救了一名落水儿童上面特批的转正名额。丁老师三十九岁,长脸,脸很白,白头发也多,打眼一看是那种工于心计的白面书生,是我们语文组组长。
此时,屋子里就丁老师一人在。我这一节没课。我说:“丁老师没课?”他说:“嗯。”我坐在办公桌前,可怎么也不得劲,有点手忙脚乱的。我终于忍不住说:“我上第一节课就捅了马蜂窝了。”丁老师用一双布满血丝的红眼睛扭头看我,我如此这般地把整个过程说了。丁老师听完,苦笑一下,问:“你吃什么粮?”我说:“供应粮。我爸原来是被下放到这里来的,一九七○年去世了。”丁老师头也没抬地说:“是供应粮就行。”我很茫然,但心里又有点莫名地熨帖。他又问:“你有没有对象?”我说:“还没有。家里太穷,草屋很矮很破。”丁老师都没看我一眼,竟然低头出屋走了。
我傻愣愣望着丁老师的背影,真有点摸不着头脑了。
我一直想找个机会向苟艳道歉,解释一下,可苟艳总不给我机会,只要我们两个人在办公室里,她肯定要离开。大家都在一起时,我又不好意思。就这样,转眼一个星期过去了。周六下午学生放假,学校每周六都要开一次例会。在例会上,于主任主持,评完了一周的卫生先进班级,苟校长开始讲话。苟校长特能讲,据说也是语文教师出身,他从中央会议精神一直讲到省里、市里、县里、乡里,最后到学校。把大家都讲困了,最后苟校长说:“咱们大家的眼睛要明亮些,确切地说,我们领导的眼睛是明亮的。像新来的韩平老师,当然我没听过他的课,不过据讲,这个小青年课讲得不错,很有水平,我们要向他学习……”
散会了,大家从校长办公室各自搬着自己的椅子出来,有好几名年轻的男女教师都用一种异样的眼光瞅我,我被那些乱七八糟的眼光看得很不自然,慌乱地低下了头。
四
我觉得生活里充满了阳光。我那双在庄稼地里先磨成血泡后磨成了茧茬的双手,捏了一个星期的粉笔就变得细嫩多了。
星期一上午,我下了第二节课回到办公室,就见办公室的窗前围了不少学生,趴着窗户往里看。我进了屋才知道,教初三语文的金来民老师和教初二(一、二班)的江东海老师吵起来了。在我们语文组,虽然丁老师是组长,但学术权威还是金老师。金来民是县城重点高中毕业,纯牌的大学漏,许多问题大家还要请教金老师的。我们这些人不到万不得已的情况下,是不敢得罪他的。
此时两个人越吵越凶,最后竟然揭起短来了。
金来民说:“你好?你偷学校的柴禾回家烧!”
江东海气得眼镜直抖:“我烧学校的柴禾是我没时间上山割!你呢?骚炮一个!去年你领着李春霞去做人流,你把学生的肚子搞大了,你怎么不说?”
金来民的脖筋暴起:“你……你不是人!”
门被当的一脚踹开了。苟校长怒气冲冲撞进来指着这二人的鼻子骂:“你们是想滚回家啦!还像个教师样子吗?”两个人立刻就像撒了气的皮球一样,哑了,瘪塌塌低下了头。
苟校长又冲着丁组长喊:“你,这个组长,怎么不管?还带头卖呆!太不像话!”
丁老师搔搔头,细声慢语地说:“校长,他们两位的火力太猛,谁也插不进去。”
苟校长又冲着我和苟艳厉声道:“你们愣着干什么?去把学生赶走!”
窗上尽是扁鼻子和黑眼珠。
我和苟艳出去把他们赶跑。
我和苟艳回到办公室的时候,校长和吵架的两位已不在,大概去了校长室。丁老师还一个劲地磨叨:“这何苦来,犯不上,都公事……这何苦来,低头不见抬头见的……”
苟艳问怎么回事,丁老师才说了事情的原委。
原来,上节课江老师任班主任的二年一班是体育课,体育老师不太高兴,就让全班自由活动。金老师正在自己的班级讲着课,突然,一个女学生啊地尖叫一声从座位弹起来,把大家吓了个半死。金老师过去一看,女生桌子上爬着一只拳头大小的癞蛤蟆。金老师一抬头,看见窗外有个学生的脑袋一晃,再看见那没有玻璃的窗洞,就什么都明白了。金老师追出去,逮住这个学生,不分青红皂白,就是两耳光子。就这样,那学生就去找班主任江老师告状,江老师就挑金老师没通知他,就把他的学生打了的理,金老师说江老师的学生太少教……一来二去,两个老师也打起来了。
丁老师说完,苟艳说:“都不是好东西,不就是为了争去年那个先进教师的名额吗?再刷人的时候都得刷掉!”
我看看苟艳,觉得她的话挺有权威性似的。苟艳看我一眼,脸有些红。
下午放学的时候,我发现我的教案下面压着一张纸条,我张开,见写道:韩老师,放学以后,请你到学校前山上的那片杨树林里等我。苟艳即日。
我有些纳闷,她一直不跟我说话,却突然约我去杨树林,这到底是什么意思呢?我想不去,可又抗拒不了那诱惑,还有点惧苟艳,准确地说是惧苟艳她爹,我这个臭代课的生杀大权就握在他们父女手里。
夕阳那一抹淡黄的余光从山背后折射过来,树林里弥漫着大山特有的潮湿气息,光线暗淡,蒙蒙,挺梦境的。我倚在一棵杨树下,等苟艳。
过了一会儿,苟艳在我身后说:“你真够呆的,我来得比你早,就在那边等你。”
我说:“啊,让你久等了。苟老师,上次我实在……”
“算了,算了!过去的事还提干什么!我今天约你来不是和你说过去那些破事的!”苟艳撅着嘴,把脸扭向一边。
我心里长长地舒了口气。我小心翼翼试探问:“你今天……”她转过头,火辣辣的目光直视着我,坚定地说:“我爱上你了,想跟你处对象……”
我脸腾地红了,喃喃着说不出话来,这的确太突然了。
苟艳说:“你不要说什么了,我舅都跟我说了,他说你行。他看上的人不多。”
“你舅是谁?再说是你看上我了?还是你舅看上我了?”
“丁老师是我舅。要说人就是怪,你第一节课让我掉链子,可我一见你就产生了强烈的好感。我舅也说你将来会有出息,我舅会看相算命呢。”
我说不出话来。我们的语文组长丁老师竟然是苟艳的舅舅,这一点我怎么就不知道呢?在一起工作快半年了,我竟然一点都没觉察到,愣是没看出一点蛛丝马迹。我此时真不知道是该痛恨自己的呆傻呢,还是应该羡慕嫉妒苟艳家族的高智商呢。
苟艳盯着我。
我细细打量苟艳,她穿了一套乳白色的运动衫,胸口的拉链半开着,露出的皮肤是少有的白,那张圆脸也挺美。她今天头发也好像刻意梳理了,显得特别光滑,扎着马尾辫子,还戴了一个绿色的发卡,浑身上下都透着一股青春蓬勃的气息。我脸红心跳低下了头,因为我很自卑,我家里很穷,我这个代课老师,随时都会被赶回田里去种庄稼。苟艳给我的幸福,让我这个穷小子发蒙,真是天上突然掉下个大馅饼,把我砸得不知所措。但是,我潜意识里知道,我的前途、理想、跳出农门的命运,就掌握在苟艳她爹苟校长的手里,当然更掌握在苟艳手里。
我鼓足勇气抬起头,眼里闪着水雾看着苟艳。
我憋了半天要说出的话,突然被几声脆生生的鸟叫打断了,几只归巢的鸟喳喳地叫起来,飞回它们那垒在树尖上温暖的窝里。我和苟艳也情不自禁牵起了手,都没有说话,红着脸低着头走出那片杨树林。
五
一连几天,语文组办公室里都给人一种沉闷压抑的感觉,谁都不说话,甚至都很少瞅对方一眼。只有我和苟艳时常对视一下,两道兔子一样的目光,忽闪忽闪的。
我去听了苟艳一节课,那节课讲的是简单的复句。苟艳的水平太一般,这一点让我心里多少有点失望,但似乎也没有太防碍我心中爱情的生长。这几天,我的办公桌上常常放着苟艳给我带来的好吃的,有很多都是我没吃过的小食品,但我知道,那些五花八门的小食品,应该都是从县城的副食商店里买来的,而我们这个乡政府所在地的小镇副食商店里是没有那些东西的。
按常理,我应该再主动约苟艳一次,可我一直憋着一股劲。你是校长的千金,我不能显得太巴结。但实际上,我内心深处潜藏着的是自卑,我内心十分清楚,我的心里有一道坎,还没有迈过去。苟艳似乎看出我的这种心理,也不提出和我幽会,我们俩都暗地里较着一股劲。
一个星期三的下午,县教育局来人了,又碰巧苟校长出门了,就轮到教导处于主任接待。下午第一节课还差十分钟下课,下课铃就响了,紧接着广播通知:各位教师马上到教导处开会。大家慌慌张张来到了教导处,还没坐稳,于主任就说:“临时召集大家,开个紧急会议,县教育局的马科长带人到我校来检查工作。他们提出就听一节课,听完还要赶回县里。这样,就决定听江东海老师的课,上什么课都可以,讲新课或上复习课都行。”于主任说完,大家的目光都粘在江东海老师的脸上。只见江老师的嘴唇哆嗦了好几下,才发出音来:“为什么非听我、我的课?”
于主任说:“你的课还怕听吗?你已经是有五年教龄的代课教师了!”江老师说:“那实在要听就听吧,反正也没有什么准备。”
江老师这一节课讲得太平常,没有几处闪光的地方。总体来说是一节失败课。面对全校教师外加教育局的两位领导,他显得十分紧张。下课的时候,他的脸上淌着汗水,不知道是累的还是紧张造成的。
也没有评课,教育局的两位领导就匆匆地走了。
大家都觉得这件事十分反常。我们回到语文组,大家你一嘴我一嘴地瞎猜起来。最后谁也弄不明白教育局这两位的葫芦里卖的什么药。大伙乱猜时,只有金来民不说话,只是不经意间在嘴角的皮肤里面抽动着几缕压抑不住的似有得意的笑丝来。
最终还是苟艳挺不住了,她说要去问问于主任,恰巧于主任推门进来了。没等于主任说话,苟艳就发问:“于主任,为什么非要听我们语文组的课?”于主任笑着说:“马科长点名要听江老师的课。”江老师迫不及待地问:“为什么?有转正名额吗?”于主任说:“他们啥也没说。”江老师拍摸着自己的头,一副丈二和尚想摸自己头的架势。
我突然发现,金来民的眼里掠过一道得意而狡黠的贼光,我预感到不祥。
果不出我所料,第二天上午,苟校长到我们语文组专门给我们开会。苟校长开门见山地说:“咱们语文组要团结,有问题不要往上面捅。咱们学校代课的多,年轻人多,大家没有考上大学就来吃这碗饭,都不容易,互相帮着点。反过来说呢,咱们作为代课老师,也都要有上进心,要抓紧提高业务水平和教学能力,得对得起学生,这是个良心活。我刚才接了教育局一个电话,对我校江东海老师的讲课情况,给予严厉的批评,并要求辞退该人,他们另派一个人来。”
苟校长说完开始点烟。江老师蔫巴了,像霜后的茄子,他那比实际年龄要老得多的脸上全是苦涩和失落。正赶上他上完一节课回来,头发和脸上粘着黑白相间的粉笔灰,像一个疲劳而颓废的粉刷工人,特别是当他听完苟校长的话,更像一个突然知道自己患了癌症的人,满脸都是死亡前的沮丧和绝望。这时候,丁老师接过话来说:“王八蛋,算个什么东西,有能耐冲我老丁来。”事到如今,大家的心里都明白了八九分。
江东海用袖子抹了一下头上的汗,说:“苟校长,我干了五年整六年头了,我回去种地也种不明白呀……”
我说:“不能辞江老师。”
苟校长说:“金来民,你说江老师这种情况怎么处理好?”金来民说:“江老师虽然水平不高,可很认真,不该辞退,只是局里……”金来民说到这,乜斜着江东海。
苟校长说:“我们研究过了,决定让江老师教韩平那两个班,韩平接江老师的班,韩平水平也较高。”
我慌忙说:“我能行吗?”
苟艳说:“有什么不行的?”
苟校长说:“我们相信你。”
丁组长说:“这样比较好。”
六
转眼之间,长白山区的秋天来了,山区的秋挺有层次,山上尽染着五颜六色。天蓝了高了许多。挣扎了一年的果实终于成熟了。我们这所乡镇学校每年都放秋收假。
苟校长说今年年头好,就放了一星期假,老师和同学们都回家帮忙秋收。再开学的时候,每个学生要交五元钱勤工俭学费。我回到离学校三十里外的家中收秋。
放假第三天,我正在山坡上割玉米,娘顶着一头乱糟糟的头发在田头喊我:“小子,有个姑娘来找你。”
我一看,原来是苟艳站在娘的身边。苟艳穿了一套红色棉纶运动衣,被秋日靓丽清爽的阳光一照,像一棵饱满的高粱。我的脸红了。我的心里很热。我又一次被幸福的突然袭击打了个措手不及,因为我没想到苟艳会到我家来找我。虽然我们俩确定了恋爱关系,但是在学校期间,我们俩都是在秘密中进行。我估计,我们俩的事情,也许只有苟艳她舅——也就是丁老师会知道一点。她的突然袭击,我觉得她是来看我的家庭状况了,而我一想到自己贫穷的家庭,就觉得特别对不起苟艳,对不起她给我的爱情。我猛转过身,又拼命割起玉米来,娘又喊:“小子,有个姑娘找你……”
苟艳说家里没事,就来帮我秋收。
我心里一直很虚,不敢碰苟艳的目光。
秋天的黑影下来了,该收工了。我坐在玉米堆上喘气。
苟艳坐在我身边。我觉得她似乎冷得发抖。
苟艳说:“哥!”声音也发抖。
我说:“啊?”
苟艳:“哥!”
我说:“嗯。”
苟艳:“哥……”
我说:“唉……”
我拥住苟艳暖而软的身子,心里突然着了火一般。我们的嘴像婴儿寻找乳头,很快就接上了,这是我第一次吻。我们相恋了半年,最多是拉拉对方的手。今天我们在金秋的黑土地里,在金黄的玉米堆上,肆无忌惮地吻了,仿佛是两头饥渴很久的牛疯狂地找到了汩汩流水的泉眼,拼命地吸吮,都要把对方吸到自己的骨髓里。
月儿出来了,我们不再吻了,相拥着躺在玉米堆上。苟艳说:“月亮好圆哪!”
我却说:“也有不圆的时候。”
苟艳:“哥,你能永远爱我吗?”
我低声说:“能。”
苟艳:“哥,你要是转了正,能不能嫌弃我呀?”
我这回声音洪亮而坚定地说:“不能。”
苟艳:“哥,我是农村户口,吃农村粮转正的希望太渺茫了。你吃供应粮,我爹会帮你的。”
我疑惑:“你是农村粮?”我一直以为苟艳是吃供应粮的。
苟艳:“俺家就我爹自己是商品粮,我娘是农村户口,子女就低不就高。”
我心里发虚,而表面却显得很不在乎地说:“其实吃什么粮无所谓。”
苟艳看我一眼,较真地说:“那不对。吃农村粮你干得再好也转不了正,吃商品粮就有机会转正,至少也办个全民合同工。”
我内心深处当然渴望着转正,但是我不愿在此情景谈论此事,尤其不愿和苟艳谈论这个话题。一同苟艳谈论这个话题,我的心中就老出现苟校长的影子,这让我产生一种莫名的不舒服。
我拉起苟艳,往家里走。
我说:“我的一篇散文在省报发表了。”
苟艳一下抱住我巴叽巴叽亲我的脸。
“这是真的吗?这也是转正的有利条件啊!”
我的情绪一下子被破坏了,心里堵得慌。我没有再说什么。此刻的天渐渐黑下来了,田间的小路蒙蒙看不清,几只秋虫有一声无一声地枯叫着,好像唱着一首歌颂黄昏的曲子。远处的山是无意的泼墨,近处的山是空洞的剪影。从远处的村庄传来狗懒懒的吠声和牛疲惫的哞叫,扯拽着庄稼人生活的调子……
我突然觉得我梦想的美好世界离我好远好远,人生变得空洞而孤独。此时此刻谁会知道我这个怀揣着强烈的跳出农门的穷人家的孩子,正拖着在田地里劳作一天变得疲惫不堪的身躯,懵懵懂懂走在回家的田间小路上,身边还有一个急切希望我转正的女孩子,她把赌注下到了我的身上,谁知道她会赢呢还是会输呢?谁知道她赢了能得到什么,输了又会失去什么呢?
到了村口,苟艳一把拉住我,吓了我一跳。苟艳站定,在黑暗里说:“哥,你真的以为我是来帮你秋收的吗?”
“那是……”
“告诉你,咱们再开学的时候,要刷掉一个代课的。县教育局要派来一个人,听说是教育局长的堂兄弟。没有办法,刷人就得考试,我怕你数学考不好,就把我爹出的数学题给你偷来了。”“你这……”
“考语文、政治、数学三科,我想你其他两科没问题。你一定要好好考,也给我爹留下个好印象。”
代课老师被刷掉回家,尤其是考试刷掉的,惨了,在四乡八邻里人脸丢尽,简直是再无法做人!还有,当老师养成了嘴勤身子懒的臭毛病,如何养活老婆孩子,没老婆孩儿的自己也够活的。况且,从此后跳出农门的希望再也不会有了,如真的被刷掉回家,就等于在这块黑土地上被判了死刑。谁不渴望着能转正,一辈子都有个铁饭碗,那是出息啊,那是乡亲们认为坟地里冒青烟的事啊!
我仿佛是在大海里抓到了一根救命的稻草,紧紧地握着试题,心里乎地一热,一下子爱得苟艳好深。我说不出话来,我钉在那里,不是望着黑暗中的苟艳,而是望着不远处村中人家那显得昏黄的灯火,我的眼里慢慢流出两行咸咸的热泪……
七
假期很快就结束了。上班的第一天,全校十八名各科的代课教师就进行了一次考试。年龄最大的四十五岁,代了快二十年的课了,也有才毕业的高中落榜生。苟校长亲自监考,整个考场里弥漫着浓浓的烟雾。几位资格老一点的代课老师,不时地还说几句笑话,大家都称这样的考试为:“运动战”。从有了要刷人要考试的风有意无意中从苟校长的牙缝里挤出来又通过各种渠道刮出去开始,一直到考完试批完卷,刷掉一些人又新考来一些人之后,这段时间,每一位代课老师的神经都绷得紧紧的,一个个提心吊胆,然后是溜须拍马,送礼拉关系,绞尽脑汁,耍尽手腕,想尽各种各样的办法动用一切能够想到的关系,真是八仙过海,各显神通。我们这些代课老师之所以这样,这是没有办法的事,为了维护保住自己那个可怜的社会地位,为了跳出农门,为了不再像父母那样面朝黄土背朝天,为了生存和前途,也只有打掉牙往肚子里咽,委屈求全。
奇怪的是,这次考完试一个星期了,苟校长也没有公布人事变动。送礼多的和送礼少的都捏了一把汗,想问苟校长还不敢,这是历年来的规矩。出题苟校长一人出,考试苟校长亲自主考,批卷还是他一人,谁考的不好就刷谁也是他一句话。
又一个星期三的下午,苟校长把我叫去,让我星期四早晨坐早车去县教育局取资料,这样的差使一般人是捞不到的,过去都是教音乐的王艳老师去取,据说王艳和苟校长的关系很暧昧。现在我能轮到这样的差使,足以说明苟艳在她爹面前为我说了不少好话,使了不少劲。
星期四下午,我取了资料坐晚车回到学校,已经下班了。但在教育局时,一位姓李的副局长要我给苟校长捎个口信,让苟校长第二天坐早车去教育局一趟,我只好硬着头皮去苟校长家。
苟校长家大红门楼,三间大瓦房,炫耀着他在这个乡里的地位和权势。我叫开大门,是苟艳来开的门,她一见是我,一惊,脸一红,又一笑,说:“快进来。你刚回来吗?”我说:“校长在家吗?我给他带来个口信……”我本想说完了就走,苟艳却一把把我扯进大门里,嗔怪地说:“你真是的,进屋跟我爹说,在这里说有啥用?我又不是校长。”我脸一红,瞅了苟艳一眼,只好进了屋。
苟校长见我,很热情,亲自倒水,亲自让烟,我好紧张,连说不会喝水不会抽烟。第一次和表哥一起来送酒走后门,我不太紧张,如今紧张也许是因为同苟艳的那层关系。我心快气短地把口信复述一遍,再就说不出话来了。苟校长问一句答一句,全是问答式的,很不自然,很别扭。我的额上开始冒汗。实在坚持不住了,我提出要走,苟校长和他老婆都要留我吃了饭走,我哪敢,急急慌慌地走了。一推门,正和外面进来的一个人撞了个满怀,认真一看,是金来民一手拎着鸡,一手拎着酒和大包食品,我更不好意思了,特别尴尬,脸也红成鸡冠子色儿。而金来民却冲我十分自然地笑了笑,然后对我身后的苟校长说:“校长,听说你今天不太舒服,来看看你。”苟校长打着哈哈说:“你这臭小子尽费心,快进屋,快进屋……”
苟校长把我送出了大门就急忙回去了。我心里想:苟校长真不舒服了吗?鸡能补身子,酒呢?
八
又到周六下午的例会了,评完卫生先进班级之后,苟校长点上一支烟,狠狠地吸了一口,说:“我们又来了一位老师,县教育局派来的,是重点高中毕业,吃商品粮,叫林光。大家欢迎林光老师!”大家都勉强拍了几下巴掌。苟校长又接着说:“大家都知道,我们学校一个萝卜一个坑,按理应该再辞掉一个,但是,快放寒假了,就维持这几个月,过年开学再说吧。林光暂时先任教导干事。”
大家都长出了一口气,不管怎样还有几个月的奋斗时间。同时大家又觉得很新奇,这个学校还从来没有过教导干事,教导干事干什么呢?管他呢,反正上面给开资。
天快黑了才散会,大家都感觉到有些冷。是啊,冬天就要来了,外面好像在飘雪。
散会后,苟艳说:“今晚乡里放电影,我七点在乡政府门前等你。”
于是,我和苟艳第一次在众人的场合肩挨肩地看了一场电影。尽管那晚下了第一场雪,露天电影场还是有好多人。
不知什么时候,金来民从我和苟艳的身后,将一把伞递给了我们。
九
放寒假了。我在家里呆了些日子,等得挺苦,苟艳一直没上我家来。我去苟艳家找她,苟艳不在家,苟校长说她去辽宁的亲戚家串门去了,我也不敢多问苟校长,只能心中失落,精神萎靡不振地默默离开。那时,我们那里还只是在传说中听说有什么BP机和大哥大,我们的主要联系方式还是靠写信,极特殊情况才会去单位校长室或者去邮局打电话、发电报。
过了几天,我又去了一次苟艳家,苟艳还是没有从亲戚家回来,依然不在家。苟校长一个人在家,我张了几下嘴,鼓足勇气想问问苟校长苟艳什么情况,但是我那好容易鼓上来的勇气都被苟校长冷漠的目光驱散了,我只能在心里一遍又一遍地咀嚼思念苟艳的痛苦。
被痛苦折磨了十多天,我终于下定决心不再去苟艳家了,我把心思都用到了一部中篇小说的创作上。
十
转眼间,新的学期又开始了,但苟校长让人捎给我的口信是:不要到学校上班了。
只一个口信就令我足信了。其实,这个消息对我们这些代课教师来说,虽然是狠毒了一些,但也是最终的结局。我们这些平民子弟们,大部分也都预算到了这种命运。
我把办公桌的钥匙捎到学校,并捎信说,办公桌里的一条新毛巾和几本小说,都给苟艳就行了。
我在炕上躺了三天。
苟艳一直没有来找我,也没给我捎来任何口信,也没有一封安慰或者解释的书信,仿佛突然从人间蒸发了,但我知道,她还在学校里代课,还站在那令我恋恋不舍、朝思暮想的讲台上。不知道为什么,我躺在家里的土炕上,就如大病一场,但我想的却不是苟艳,也不是和苟艳那些浪漫的爱情。我心里想的竟然是苟艳她爹——苟校长,想的是那用红砖和黄土砌就的还有坑洼的讲台,想的是那些比我小不了几岁的农家中学生们,想的是那红砖灰瓦的教室,想的是那一下雨就积水的操场……
第七天,我的一个得意门生和几个同学来看我,从他们那里我才得知,江东海也被刷掉了,这学期共刷掉了三位。
我问:“不知江老师怎么样?”
他们七嘴八舌地说,江老师刚被刷掉的时候,没敢跟家里和村里人说,他还是天天上班,到了学校以后,他就藏在学校前面的那片杨树林里,呆呆地往学校的操场上看。后来的几天,他就不偷偷摸摸了,低着头天天到学校前的山上走,来来回回地走,我们都不敢靠近他,有点怕他……
我的心在抽搐,我忘了自己,很为江老师担忧。
学生们看出了我的心思,又说:“这几天好了,他可能要做买卖了。”
“金来民呢?”我低声问。
“听说他要转正了,是县教育局的一个副局长给办的。”
“林光呢?”我突然想起最后来的林光。
“林光老师啊,最有故事了,他的酒量可大呢,常把苟校长给喝醉。他教我们历史,他可有闹呢,有一节课,他讲到现代史中‘地主那节,他讲:地主在‘文化大革命时可吃了亏,叫红卫兵好揍。我们学生都笑,他以为我们没听明白,又强调补充说:真的,揍得可厉害了……”
他们又叽叽喳喳笑起来了。
我却怎么也笑不出,眼里发酸。我知道同学们说的是真的,因为我多少了解一些林光,他是上面有人,派来的,虽然也是代课,但他的背景和我们却截然不同。所以,无论他素质多差,多么不适合来做老师这个工作,都可以顶掉我们这些代课多年的人。
十几年后,我听说,林光在学校代课一年多就主动辞职不干了,他做了房地产老板,发达了,成为当时全县数一数二的有钱人。但是他当年从县城空降到我们学校来当代课老师,又只干了一年,自己主动辞职,这在我们看来简直是不可思议,是我们这个中学自古以来没有发生过的事情。更重要的是,他当时白瞎了一个比我们命还值钱的代课名额,活生生地毁了我们其中某一位爬出农门的大好前程。
十一
可能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人生轨迹,你偏离了自己的轨迹,拼掉青春也好,拼了自己的老命也好,最终还是要回到你注定的轨道上来。你费尽心机苦苦强求的东西,往往是很难得到,而你无意插下的那棵翠柳,却荫蔽了你的一生。我的幸运是,在我和苟艳谈恋爱期间写的那部中篇小说在省文学权威刊物发表了,引起县文化局的重视,文化局原打算调我到文化馆当创作员,无奈我是临时工、待业者,不是什么所谓的正式工,没有干部的身份,即使再有能力也没办法调入文化馆坐上那能够吃上皇粮的椅子。文化局王局长也爱好文学,他很同情我,可怜我的处境,最后费了一番周折,把我推荐到县城一家国有企业写材料,厂长答应给我先招工后转干。
到县城两个月,给苟艳写了两封信,都没有收到回信。
后来有一个家乡来的人说,苟艳已经结婚了,是跟金来民。我听了这个消息,心里虽然不是滋味,但是没有五雷轰顶的感觉。我不知道我和苟艳之间的这场恋爱,算不算是一场真正的恋爱。我总觉得苟艳对我的主动追求,对我的热心帮助,和我在玉米堆上的狂吻,到后来的突然消失,直到最后的无声无息……这一切,让我一直觉得是那么梦幻,那么空灵,又那么遥远。
但是我的内心深处,还是有什么东西在蠕动,我知道那是关于苟艳的。我心中还是不愿意相信苟艳会和金来民结婚,所以,我还是抱着一种说不上是什么样的心态,寻找机会打听苟艳是否真的和金来民结婚了。
终于有一天,我在县城最大的那个十字街路口,遇到了我曾经的直接领导也是苟艳的舅舅丁老师,他是来县城公安局开会的。我很纳闷,丁老师来公安局开会?学校出什么事儿了?丁老师跟我说,他改行了,转行到乡派出所了。他说,你也知道,在乡中学当个老师,能有什么出息?待遇也低,是苟校长在县里托人帮他改了行。我那时还不知道一个乡派出所的民警究竟有什么样的实权,也不清楚丁老师改行后还会遇到什么样的问题,这一切都不是我想知道的。
最后,我迫不及待地向他询问苟艳和金来民结婚的消息,丁老师不再看我,低着头告诉我说,那是真的。
责任编辑 安殿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