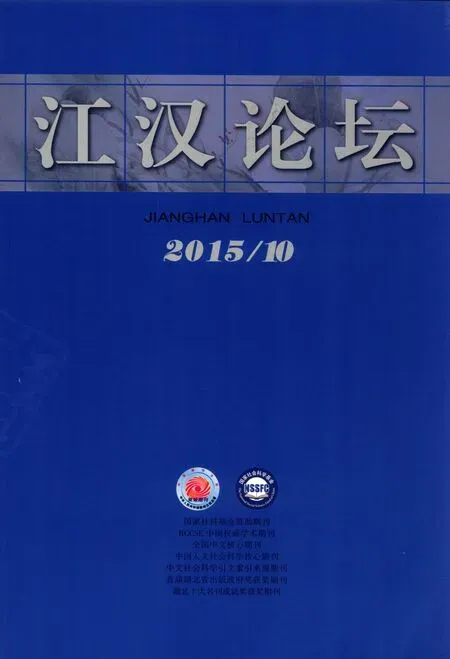《论语》中的“道德”
臧宏
哲学
《论语》中的“道德”
臧宏
国内外学术界大都认为《论语》是一部讲道德的书。这是一种严重的误解或曲解。《论语》讲“道德”,不是它的直接目的或最终目的,它是通过“道德”来说明它要说明的根本问题——生命本体的。通过对《论语·学而》篇的“吾日三省吾身”章,“弟子入则孝出则弟”章、“贤贤易色”章、以及《公冶长》篇的“十室之邑”章、《为政》篇的“道之以政”章进行分析解说,我们可以很清楚地得到结论,即《论语》不是讲人间“道德”的书,而是讲生命本体的书,是讲人的“大觉悟”、“大智慧”的书。
《论语》;道德;仁;孝弟;生命本体
国内外学术界大都认为《论语》是一部讲道德的书。我认为,这是一种严重的误解或曲解。《论语》中确实讲了大量的关于“道德”的话,也出现过不少单独使用的“德”字。但是,绝不能据此得出“《论语》就是讲道德的书”这个结论。因为《论语》讲“道德”(即伦理学说的道德规范和道德品质),不是它的直接目的或最终目的,它是通过“道德”来说明它要说明的根本问题——生命本体(即“明德”,或“知”)的。它单独使用的“德”,也不是世间所说的“道德”,而是指“天”之“德”或“道”之“德”,亦即王阳明所谓的“良知”。
《论语》中讲到“道德”的地方,多与“省”、“学”、“德”、“仁”等字相连,实际上都是为了说明生命本体的。因此,要恰当地评价“道德”的价值,必须将它和“省”、“学”、“德”、“仁”等字联系起来进行考察,分清世间道德和生命本体之间的区别与联系,准确地把握二者在治理社会和国家过程中的作用。以下择取重要的、典型的几章加以解说。
一、《学而》篇“吾日三省吾身”章
该章的原文是: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
这是孔子学生曾子说的一段话。曾子,姓曾,名参,字子舆。为学注重内求,处事谨慎。“四书”之一的《大学》的作者。孔子去世后,“儒分为八”,曾子是其中一派的导师,故亦称他为“子”。
“省”字是这一章的关键。在曾子那里,这个“省”字,既不同于现在说的“反省”、“检讨”、“检查”等概念,也不同于基督教说的“忏悔”,更不同于曾国藩家书中写的那些道德自责之类的话。“省”的本义就是“明”,就是曾子在《大学》中说的“大学之道,在明明德”的第一个“明”字。“三省吾身”的“三”,表示多数的意思,“三省吾身”,就是孔子说的“学而时习之”,就是不断地体验生命之本体。“明明德”的第一个“明”字是使动词,后面的“明德”是名词,朱熹将其解为“知”。明明德即通过不断地实践体验,使“明德”“明”,让“良知”自然地到来,而不是用概念来讲什么叫“明德”。“明明德”,也可以叫做“知知”,即对生命本体的“觉悟”。有的学者称“明明德”的“明”为“反思”,但又认为这个“反思”与西方哲学的“反思”不同:“东方文化所说的反思,主要是对角色意识的清除,客观运动不可能直接反映为意识,必有层层角色意识为障碍,使得意识映象成为一种扭曲的折光,只有当人不断剔除这种角色意识的干扰,主客观才能接近。”①那么为什么曾子要提出不断地反思“忠”、“信”、“传”呢?我认为,根本的原因是东方文化尤其是中国传统文化,对人们的唯一要求便是对生命本体的“觉悟”,而这种“觉悟”又是一个无穷无尽的过程,要实现它,必须要有路标。这里说的“忠”、“信”、“传”,就是这种路标。生命的本体是无形无相的,它要靠这些路标来显示;如果没有这些路标,那它就成了不可捉摸、不可思议的东西了。我这样说,是符合于曾子的本意的,他在《大学》中说:“古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很显然,在曾子那里,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都是“明明德”的手段、方法,而孔子及其嫡传弟子们,为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确立的一些基本原则,就都是“修身”(即“修心”、“明心见性”或达到“生命本体”)的一些路标。
然而,又不可把这些路标绝对化,要看到它们是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变化的。在巫术图腾时代,路标主要是诚敬鬼神,用鬼神解释一切现象。孔子则否定这样的路标,要人们“敬鬼神而远之”,带头不讲“怪、力、乱、神”,并提出一种新的路标,这便是“吾道一以贯之”的“忠恕”,即强调“忠”于自己,“恕”于自己,也就是强调以人为本。比如“忠”,作为一种道德规范,其具体内容是随着时代、环境、对象的变化而变化的。曾有人问孟子,武王伐纣算不算弑君?孟子答,吾未见武王弑君,只见武王杀了一个匹夫。在这个意义上岳飞就是由于固守一个“忠”的道德概念,不仅丧失了自己的生命,而且断送了宋人抗金的大业,即违背了真正的“忠”——当时的民族统一大业。因此,绝对化地理解概念,那怕是道德概念,也会给人带来灾难,甚至可以杀人,岳飞之死,就是一个实例。
二、《学而》篇“弟子入则孝”章
该章的原文是:子曰:“弟子,入则孝,出则弟,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行有余力,则以学文。”
这一章分两段:从“弟子入则孝”到“而亲仁”为一段,“行有余力,则以学文”,为另一段。
第一段主要是对入门者说的。这段中的“入则孝”的“孝”,“出则弟”(通“悌”)的“弟”,“谨而信”的“信”,“泛爱众”的“爱”,都是入手处,不是归宿处,意思就是通过它们可“亲仁”。“仁”是生命的本体,但“亲近”于“仁”却不是“仁”本身,故还不能说是最终的目的。
不过,这段话对我们来说,还是有其意义的。第一,在孔子那个时代,“孝弟”作为一种不可怀疑的伦理道德原则,在被孔子着力地提倡之后,就彻底避免了中国文化岔入到一神尊崇的西方中世纪式的等级社会,这是中国人的一大幸事。第二,孝弟,这种亲爱关系,是人类应有的自然属性,孔子巧妙地利用了这种自然属性,来清除巫术图腾时代留下的“鬼神”在人们头脑中的统治地位,从而为自己提出的以人为本的“生命观”扫清道路。这无疑是对中国文化作出的一大贡献。第三,孔子为什么能够最早地看到以人为本的新的生命观产生的必然性?为什么能够最早地从以神为本的生命观中摆脱出来?为什么在2500年前就能够提出后他2000年才提出的平等观呢?这显然是和孔子最先识透了人的生命的本来面目分不开的。而西方文化之所以在14世纪才进入以人为本的生命观,之所以从鬼神文化走出来又立即落入一神尊崇的铁板一块的等级社会,一直摆脱不了鬼神——上帝的幽灵,之所以对生命的认识存在着极大的盲目性,把生命与人的肉体混为一谈,恰恰是由于他们没有真正地识透生命的本来面目。董子竹说得好:“在生命的本来面目面前,一切必然是平平等等。人作为生命的载体,生命给予每个人的不会多一点,也不会少一点。中国的平等观是从这里生发出来的,和西方的平等观有质的区别,如果孔子不了解生命本质力量的存在,仅凭学识文化,无论如何不可能超越历史,提出二千年后才能提出的观念。”②但是,话要说回来,对生命本来面目的把握,是离不开“内省”的。而本章和“吾日三省吾身”章一样,也是讲“内省”自我的。“入则孝,出则弟,谨而信”,从贴近当时的生活而言就是一个“诚”字。这是中国文化内省自心的魂。还是董子竹说得好:“不是追求孝、悌、信,而是问自己,孝、悌、信时是否是‘真诚’的。我此时是否是为孝而孝,还是真孝?我此时为悌而悌,还是真悌?我此时是真信,还是为信而信?在这一点上千万不要自欺欺人,任何‘偷心’不可有。当然,绝对没有‘偷心’也是不可能的。但只是要在内省中及时发现自己有‘偷心’。真发现了,也就是‘诚’了,更不必另找一个‘诚’。”③这是“内省”的第一要义。其第二要义,是孔子说的“泛爱众,而亲仁”。所谓“泛爱众”,其核心只是“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即“欲明明德于天下”,就是爱天下。“而亲仁”是对“泛爱众”的进一步的解释,是说“于众皆当泛爱,但当特亲其众中之仁者”④。正如前面说过的,孔子所说的“仁”,实属于生命本体的范畴,如“在亲民”,就是生命本体使百姓都有“明德”,都能明“明德”,这就是“仁”,生命的本体赋予个体以生命,此谓之“仁”。所以孔子从不轻言其哪一个弟子达到了“仁”的境界。孔子高标“仁”,正说明他是希望在现实生活中,人们都应该把自己的生命的行为和生命的本来面目结合起来思考。
第二段的“行有余力,则以学文”,也是极其重要的一个指示。它告诉我们,《论语》中的“学”,包含有学生命本体和学知识二层意思。“行有余力”的“行”,就是孔子说的“吾十有五而志于学”的“学”,“学而时习之”的“学”,亦即学生命本体之“学”。“则以学文”的“文”,多数注家都说是“文献”之“文”,“学文”,就是学知识。孔子不反对学知识,但主张以“知天”、“体仁”、“明心”、“明明德”为前提。“行有余力,则以学文”,就是说的这个意思。它强调要为“明心”、“觉悟”而学,认为,当不知“内省”己心之前,千万不要到处乱“学”,更不能为某种功利,比如为沽名钓誉而学,为挣钱而学等等。
“行有余力,则以学文”,在中国历史上影响很大,其意义是不可估量的。正是它,在中国民间形成了“望子成龙”的民风;正是它,使《大学》说的“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落到了实处;正是它,为下层子弟进入上层打开了一个通道;正是它,使中国“士阶层”(知识分子)的成长有了社会基础,因为在孔子那里,以家庭为单位的“则以学文”实是一切人都有的权利。中国古代的政治制度与别国相比,并无多少先进性可言,但中国“士阶层”的独立成熟,则是世界文明的奇迹。中国的“士阶层”是欧洲的骑士、日本的武士不可比拟的,前者“替天行道”,后二者则唯上是从。
最后,必须指出,我们今天学习这一章,绝不能着眼于它提出的那些只适用于当时生存环境的社会道德教条,而是要学习孔子是怎样通过这些“道德”来把握生命本体的,以及生命本体在当前又可能体现出什么样的“生命观”来。
三、《学而》篇“贤贤易色”章
该章的原文是:子夏曰:“贤贤易色;事父母,能竭其力;事君,能致其身;与朋友交,言而有信。虽曰未学,吾必谓之学矣。”
这是孔子学生子夏说的一段话。子夏姓卜,名商,字子夏。他虽家境贫寒,但有气节,具有临难不苟、临危不惧的气慨。和前章一样,本章也分两段,从“贤贤易色”到“言而有信”为第一段,“虽曰未学,吾必谓之学矣”为第二段。
第一段的首句“贤贤易色”,南怀瑾的解释很通俗,就是“看到好的人事能肃然起敬”(《论语别裁》)。董子竹对之解释得更深刻,他在《论语正裁》中解释本章时说:“‘贤其贤’正是由于有‘明德’。不是生命之知,不是人的独特的生命之知,我们就不知什么是‘贤’,当然也就不会‘贤其贤’了。贤其贤的能力是生命本来的,贤的标准也是生命在展示自己的过程中确立的。我们的判断,实是随着生命的展示过程而发展。正因为如此,我们个体的生命只是‘宇宙——生命’系统的一个表现形式,能在别的生命个体身上表现出来的‘贤’,也必然会在我的身上表现出来,只不过现在在我身上还未表现,所以才会引动我的感触,觉其贤而肃然起敬,如果我根本不知其‘贤’为何物,我怎么会感动呢?”董子竹在这里所说的“生命之知”,指的是“明德”,所说的“人的独特的生命之知”,指的是“明明德”。“明德”为一切生命体所具有,而“明明德”则为人所独有。动物的“明德”只求与自己的本能相对应,而人的“明明德”,则可以对事物作出是非、善恶、真假、美丑、贤愚等等的判断,二者是完全不同的。还要看到,董子竹强调“贤其贤的能力是生命本来的,贤的标准也是生命在展示自己的过程中确立的”,是在告诉我们,人们对“贤”肃然起敬,也就是对生命本质力量自身的肃然起敬。因为前者是后者的表现形式,是由后者决定的。
“贤贤易色”的后面三句,是关于“贤”的举例,什么是“贤”?子夏举了三种“贤”的例子:“事父母,能竭其力;事君,能致其身;与朋友交,言而有信。”这些话容易理解,“事父母”、“事君”的“事”字,作动词,事奉的意思。“能致其身”,即能献身的意思。因为“致”字有“委弃”、“献纳”等义。事父母尽力,事君献身,与友交诚信,是孔子时代常见的“贤”,子夏作为典型例子举出来,是可以理解的。但是,我们不能认为这三者就是“贤”的全部内容。要知道,时代不同,“贤”的内容也会跟着变化,我们今天的人,也是可以对科学家、艺术家、教育家、管理家……乃至一切有利于社会进步的人和事“贤贤易色”的。把“贤贤易色”的对象限制死了,就无法“止于至善”了,即无法把握生命的本来面目了。
第二段的“虽曰未学,吾必谓之学矣”是本章的重点。如果解这一章,把重点放在“事父母”、“事君”、“交友”这三点上,那就本末倒置了,人们很可能因此认为子夏讲的是纯道德的东西。何谓“虽曰未学”?有两层意思:一层是说,事父母尽力、事君献身、与友交诚信,只是达到“明明德”、“知天命”的手段、方法,而不是“明明德”、“知天命”本身,所以只能说是“未学”,即未达到“明明德”、“知天命”。请大家记住,在孔子那里,“学”主要是指学“明明德”(“大学之道,在明明德”),主要是指学“知天命”(“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五十而知天命”)。另一层是说,我能知他“贤”,却不能知他在哪儿“用心”、在哪儿着力时,当然不知他是“学”了还是“未学”,也就是不知他是否明了“明德”、知了“天命”。那么何谓“吾必谓之学”呢?这和“虽曰未学”是联系着的,就是说,虽然“事父母”等三句话,本身不是“明明德”、“知天命”,但它们是达到“明明德”、“知天命”的方法,可以使我们达到“明明德”、“知天命”;只要“我”经过“事父母”、“事君”、“与朋友交”,并超越它们,达到了“明明德”、“知天命”,就可以说它们是“学”。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我知它们“贤”,且“贤贤”,即“贤其贤”,我自己也就是“贤”了,所以“吾必谓之学”。见贤为贤,并能肃然起敬,这本身就是“学”了。
为了加深理解,还要强调几点。第一,《学而》篇,自第五章,即从“道千乘之国”开始,到本章结束,都是讲的儒学的修身、齐家、治国等基本观点,因此要把这几章联系起来理解。比如本章就是接上一章的,更进一步强调“内省”以“诚”的重要性。学文,必是从“内省”之“诚”学起,有了一定的“觉悟”之后,再去学习文化,否则,就会迷失方向。第二,不要就道德讲道德,也不要空谈“明明德”、“知天命”,而要把二者结合起来。要知道,孔门提出的许多道德原则,一是为了适应当时那个社会,即为了摆脱鬼神迷信,二是为了“明明德”、“知天命”。如果你把孔子提出的道德原则研究透了,你就会发现,其中暗藏着许多对生命本体的认知。为什么儒学中的许多思想,至今还会被人提倡?其原因正在于此。孔子的学说,永远是“叩其两端而竭焉”的,一方面,它是“明德”、“至善”,另一方面,又适合当时的时代要求,舍弃任何一端,都可能错解孔子博大精深的思考。第三,要牢牢抓住“虽曰未学,吾必谓之学矣”这个重点,除了对之再作深入的探讨外,更重要的,是要正确把握“虽曰未学”与“吾必谓之学”这二者的关系,切不可割裂它们。如果割裂了,那“虽曰未学,吾必谓之学矣”,就变成了对“贤”的赞扬,这就与主张主客一体、知行一体的东方文化的观点,相去甚远了。
四、《公治长》篇“十室之邑”章
该章的原文是:“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不如丘之好学也。”
将这章译为现代汉语就是:(孔子说)“十户人家的小地方,其中必有和我一样忠信的人,但没有像我这样好学的。”
这一段,孔子明确地把道德修养和“学”作了严格的区分。这对今天的许多人,包括许多研究国学的人来说,都会觉得不可理解。因为在他们看来,儒家学说和“伦理道德学”是一码事。
《论语》中,有近40处讲到了“学”,而且主要是讲学“明明德”、学“知天命”、学“致良知”的。如“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吾十有五而志于学”、“君子不重则不威,学则不固”、“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有孔颜者好学”、“好仁不好学,其蔽也愚;好知不好学,其蔽也荡;好信不好学,其蔽也贼;好直不好学,其蔽也绞;好勇不好学,其蔽也乱;好刚不好学,其蔽也狂”等等,这些“学”字,都不是讲学知识、学文化、学道德的,而是讲学生命之本体的。本章讲的“不如丘之好学也”的“学”字,也是如此。《论语》中讲的“学”和“好学”的“学”,只能是“大学之道,在明明德”的“致良知”,亦即“觉悟”。
我认为,相比之下,在历代的注家中,以明人李卓吾和藕益道人智旭对本章的解释为最好。李卓吾说:“正欲满天下都好学也。”⑤藕益在《藕益大师全集·四书藕益解·论语点睛补注上》中说:“孔子之忠信与人同,只是好学与人异。好学二字,是孔子真面目,故颜渊死,遂哭云:‘天丧予!’”这是对“好学”的最好的解释。何谓“好学”?好学者,好“知天命”,好“体仁”之谓也。孔子认为,在他的弟子中,只有颜回是“好学”的人,因为他能“三月不违仁”。颜回死,他痛哭,说是“天”要毁灭他,实际上是说,颜回不在了,也就是上天使他少了一个能知天命的人。
在今人中,我认为,对“好学”解释得比较好的,是安德义。他说:“孔子的‘好学’表现在许多方面:①好学的态度:‘学而不厌,诲人不倦’。②好学的内容:‘就有道而正焉’。③好学的对象:‘圣人无常师’。④好学的时间:‘乐以忘忧,发愤忘食,不知老之将至’。⑤好学的方法:‘温故而知新’、‘学思结合’等等。”⑥
而在古代的注家中,朱熹对“好学”的“学”字的解释,值得注意。他在《论语集注》中说:“忠信如圣人,生质之美者也。夫子生知而未尝不好学,故言此以勉人。言美质易得,至道难闻,学之至则可以为圣人,不学则不免为乡人而已。可不勉哉?”⑦他把“圣人”和“至道”当作“好学”的内容与对象,这是正确的,但他仅仅将“好学”的“学”当作动词,当作扩大“忠信”道德美质的一种手段或方法,则是与孔子的本意不合。在孔子那里,“学”是名词或动名词,即指“明明德”、“知天命”、“致良知”。
我们来看今人是如何解释“好学”之“学”的。先看李泽厚的解释。他说:“又一次强调‘学’。‘学’当然包括学习文献、历史、知识以及各种技能,同时更指积极实践的人生态度和韧性精神。它始终是动态的,当然不止于静态的忠、信品德。”⑧于此我们看出,“后来居上”这句话并非是绝对真理。李泽厚对“学”的解释,与李卓吾、藕益相比。非但不是“居上”,反而是大大地倒退了。谁都知道,在这里,孔子明明是把“学”放在“忠信”之上的。否则,他就不会讲“不如丘之好学也”这句话了。无独有偶,不只是李泽厚这样来解释“学”字,就是发行量很大的《论语译注》的作者杨伯峻,又何尝不是如此呢?他比李泽厚更干脆,直接地把“学”字译成了“学问”。应当看到,如李、杨这样解释“学”字,是今天学术界的大多数,他们二位只不过是代表而已。
更为有趣的,是钱穆对本章的评论:“按:本篇历论古今人物,孔子圣人,人伦之至,而自谓所异于人者惟在学。编者取本章为本篇之殿,其意深长矣。学者其细阐焉。又按:后之学孔子者,有孟轲、荀卿,最为大儒显学。孟子道性善,似偏重于发挥本章上一语。荀子劝学,似偏重于发挥本章下一语。各有偏,斯不免于各有失。本章浑括,乃益见其闳深。”⑨这样来解“学”字,明显不妥。孔子说他“吾十有五而志于学”,学什么?学“知天命”,因为他说他是“五十而知天命”。以孔子的这个话为准,那钱穆的“评论”就不免有些偏颇了。孟子、荀子不过是随历史进程各讲各自领略的“天命”罢了。中国历代的知识精英,大都以“觉悟”为终生追求。这个追求,经过孔子及其弟子之手的发扬光大,已成了一个光荣传统。这是中国文化的基本价值所在。
五、《为政》篇“道之以政”章
该章的原文是:子曰:“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
本章分两段,前三句为一段,后三句为另一段。
先解释第一段。“道之以政”的“道”,通“导”,引导的意思。“之”,指“民”,百姓。“政”,指各种强制性的政治手段和政策措施。此句可直译为:以各种强制性的政治手段和政策措施引导民众。“齐之以刑”的“齐”,作动词,使整齐、规范或一律。此句可直译为:以固定一律的刑法为标准判断民间是非。“民免而无耻”,是说采用“道之以政,齐之以刑”的治理的方式,民众会使用巧计逃避而不以为耻。这里的“免”是“避免”、“逃避”的意思。就像善于逃避猎手的野兔一样。杨润根在其《发现论语》中说:“‘免’的本意也许正是指一只兔子的迅速逃避猎手的行为及其结果:使自己免于危险与灾难。这里‘免’(逃避)的对象是‘政’和‘刑’。”⑩这里的“耻”,指人的内心的一种羞愧之感。
再解释第二段。“道之以德”的“德”,本义是“得”。“德”、“得”是不可分离的,但“德”又不只是“得”。当代的一些学者把“德”的实际涵义分为孔子之前与孔子之后两类,认为在孔子手中,“德”已经变成民的“品质”、“品德”之类的道德概念了。这是对孔子学说缺乏深入研究的缘故。他们不知,“德”就是《大学》所说的:“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这段话的最后一句的“虑而后能得”的“得”。因为它和“定”、“静”、“安”、“虑”一样,都是“知止”的结果。“知止”,就是“知止于至善”,就是“知天命”、“明明德”、“致良知”,一句话,就是对“天德”的“觉悟”。必须明确,“德”是对“天”(即“宇宙——生命”系统)来说的,而“得”则是对“人”来说的。人本无“德”,人之“得”乃“天”之所赐,“天”让你“得”,你才能“得”,“天”不让你“得”,你什么也“得”不到。“齐之以礼”的“礼”,主要是指外在的礼仪。“有耻且格”的“格”,杨伯峻的注释比较好。他引《礼记·缁衣篇》说:“‘夫民,教之以德,齐之以礼,则民有格心;教之以政,齐之以刑,则民有遯心。’这话可以看作此言的最早注释,较为可信。此处‘格心’和‘遯心’相对成文,‘遯’即‘遁’字,逃避的意思。逃避的反面应该是亲近、归服、向往,所以用‘人心归服’来译它。”⑪把“格”解释为“归服”,这与孔子的原意相符合。综合以上的解释,可将这一段今译为:以“天之德”引导民众,又以外在的礼仪规范民众,民众不但有羞耻之心,而且会从内心认同而归服。
李卓吾对本章的眉批是:“由今以思古也,亦对症而下药也。”⑫此话何意?李泽厚试图对之作出解释,他在对本章所作的“记”中说:“这仍然是用远古氏族习惯法规(“德”“礼”)来比较当时的行政法规(“刑”“政”)。强调的仍然是心理悦服的重要。为什么‘免而无耻’不好,因为只能管个外在行为而不涉及内心世界,此离巫术礼仪要求身心同一,内外均诚远矣。孔子之后,孟子由‘性善’讲‘四端’,发展了孔学内在心理面;荀子强调‘礼乐刑政,其实一也’,则甩开了心理方面,重视建立制度规范。一个发展了宗教性道德而回归神秘经验,一个发展了社会性道德而走入政治——法律。以后道法家占了上风,抛弃了远古氏族的格局。但由于长期的农业小生产和血缘关系作为社会结构主要支柱的保存,汉代强调‘孝’,伦理与政治在专政帝国的政治体制下,又以新形态混而不分。到宋明理学,更在理论上被推至顶峰,在实践中也如此。‘大公无私’、‘成仁取义’、‘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等等宗教性道德笼罩了包括政治在内的一切。正因为中国的‘政教合一’的特征是这种泛道德主义,它比非理性的宗教信仰、教义更难与世俗性政治事务相分离。”⑬李泽厚的这一番话,引起了董子竹的关注。董对之评价道:“李泽厚把儒家‘达天之德’的追求,追踪到原巫术礼仪的身心同一,内外均‘诚’,这是极有远见的,也是极准确的。他对孟子与荀子的分野也是极准确的。”这是对李氏所作的肯定方面。另一方面,董子竹也指出了李泽厚的不足,他说:“李泽厚氏一生受历史唯物主义熏陶至深,所以有上文的至论。但是,他不是十分了解古文化。李泽厚的根本失误,只在于他不知轴心时代经典作家对原巫术神秘经验的伟大升华,达到了人类理性的顶峰。正如我们过去讲过的,孔子的天命观,既超越了鬼神天命观,也不是经典物理学的天文历相气候的自然天命观,孔子、老子、释迦探寻到了生命本体的生命观。虽然今天的人对此觉悟的不多,但世界的进步,自然科学的进步正在证明着这种天命——生命观念的正确性。”⑭董子竹对李泽厚的批评,才真正抓到了李卓吾的那个眉批的真谛。“由今以思古也”的“古”,指何而言?不是别的,正是孔、老、释所探寻到的“生命本体的生命观”,它才是对治百病的良药,世间所说的道德修养、道德规范的治理作用,岂可与它相提并论?
六、结语
从以上对《论语》中讲人间道德问题的主要篇章的解说中,我们可以得到哪些启示呢?第一,一定要弄清楚《论语》为什么要大讲道德问题,亦即《论语》大讲道德问题的原因与意义何在?应当说,这个问题是不难回答的。谁都知道,在孔子的时代,不讲道德,就不能摆脱鬼神为中心的生命观的束缚;就不能建立起以人为中心的新的生命观;就难以理解“天之德”这个生命本体的本义。因为本体无形无相,只有通过“道德”这个具体的人与人之间的伦理关系,才能具体地把握。尤其要指出的是,在当时,儒家着重提倡“孝弟”道德,是与人们之间的亲情之自然属性相符合的,也就是说,是符合孔子时代最广泛的社会基础——农耕文明为基础的村社家族文化的实际的。在当时,它是最大的政治,其作用几乎与本体之“仁”相媲美。所以,只有大举“道德”的例子,才能说服人,使更多的人了解生命的本来面目。也就是说,在当时大讲道德的意义或价值,主要在于它是体认“天之德”即生命本体的一个手段、一个环节,或者说,它是认识生命本体这个无穷过程中的一种路标。
第二,一定要弄清楚人间道德与生命本体之间的区别与联系。前面解说的《论语》的五章都是讲这个问题的,《论语》讲人间的“道德”,总是与“省”、“学”、“德”、“仁”等字相连,其用意亦在于此。从前面的解说中我们看到,人间的“道德”与生命的本体之间,确实既存在着联系的一面,又存在着区别的一面。夸大联系或区别都会混淆人间道德与生命本体之间的界限,都会给人类社会带来不好的后果。《论语》中对人间道德的论述,不是康德的“先天道德律令”,“而只是‘诚’的一种表现形式,只是‘致良知’之‘诚’的前期准备。千万不要混淆了这种学习的具体次第:从道德中进入,再从道德中走出。关键不是说自己是否有道德,而是看自己是真道德还是假道德,或是以道德沽名钓誉”⑮。后人往往不明此理,夸大了二者的联系,把二者混为一谈,以为圣人对道德的强调,就是说圣人完全具备了“天”之“德”或“道”之“德”,甚至认为这是圣人对人类的要求。朱熹就是这样认为的,他要求学“圣人”、学”圣人”所具备的“天”之“德”或“道”之“德”。这样,使得一些学国学的人往往强行去作,结果是人格扭曲,精神分裂,最后导致假道学的大肆泛滥。
第三,上述诸章的解说告诉我们,一定要划清《论语》使用的道德语言与康德、牟宗三所说的“先天道德律令”和“道德主体”之间的界限。各种文化都有自己的表述系统。《论语》的表述系统,基本是用“伦理道德”和“天”之“德”、“道”之“德”的语言进行表述的。但是,他表述的不是今天说的“伦理道德学”,与康德的“先天道德律令”、牟宗三的“道德主体”也有本质上的不同。二者从名词或概念上可能相近,但毕竟是两个完全不同的体系。在康德那里,“道德”是纯精神的东西,与生命的物质存在、宇宙万相的存在没有任何关系。《论语》中的“天”、“天道”、“天命”、“天德”,则是囊括一切,物质、精神、宇宙、万物,全是一体思考。这个区别,是必须要搞清楚的,否则,就会导致巨大的混乱。而牟宗三就是在弘扬中国传统文化过程中的混乱的制造者,其原因就在于他把根本不同的体系变成了一个,把康德哲学亦即启蒙主义的东西拿过来,用中国“心学”进行重新包装,并名之曰“现代新儒家”。这种包装,不仅有极大的欺骗性,更重要的是他完全错解和歪曲了儒家文化。如他把孟子的“四端”当成了“先天道德律令”并依此提出了自己的“道德主体”论,就是明显的例证。
牟宗三的“道德主体”论,完全是拾康德“先天道德律令”或“先天意志”的牙秽。康德的“先天道德律令”或“先天意志”,认为“道德”是每个生命先天就有的观点是根本站不住脚的,是经不起驳斥的,马克思主义仅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这个理论的角度,就把他驳倒了、否定了。其实,道理很简单,在客观的历史过程中,不同的阶级有不同的道德,不同的民族有不同的道德,不同的宗教有不同的道德,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道德。尤其重要的是,任何道德都是在具体事情中表现出来的,而具体事情又是千差万别的,又永远是黑格尔说的绝对的“这一个”。既然是绝对的“这一个”,人们之间人就不可能有“道德”的公约数。没有“道德”之间的公约数,也就不存在什么“先天道德律令”或“先天意志”。康德的这个观点,是建立在抽象的逻辑理性的思维方式的基础之上的,这也是西方人特有的思维方式。而他把这种思维方式运用到哲学上,运用到伦理学上,则完全是时代的悲剧。牟宗三对建筑在这种思维方式基础之上的“先天道德律令”的观点崇尚有加,视为圭臬,并用中国的“心学”进行包装,从而提出的“道德主体”论,只能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严重歪曲,只能给中国国学的弘扬增加麻烦,制造混乱。李泽厚是最早对现代新儒家特别是牟宗三提出批评的人,历史的实践越来越证明他的批评是正确的,在这方面,我们应该向他学习!
注释:
①②董子竹:《论语正裁——与南怀瑾商榷》,长江文艺出版社2007年版,第15、24页。
③⑭⑮董子竹:《论语真智慧——兼就教于钱穆、李泽厚先生》,长江文艺出版社2012年版,第22、45、23页。
④⑨钱穆:《论语新解》,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2年版,第10、138页。
⑤⑫李贽:《四书评》,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57、33页。
⑥安德义:《论语解读》,中华书局2007年版,第138页。
⑦朱熹:《四书章句集注》,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83页。
⑧⑬李泽厚:《论语今读》,安徽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第144、51页。
⑩杨润根:《发现论语》,华夏出版社2003年版,第29页。
⑪杨伯峻:《论语译注》,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12页。
(责任编辑胡静)
B222.2
A
1003-854X(2015)10-0041-07
臧宏,男,1933年生,江苏宿迁人,安徽师范大学政治学院教授,安徽芜湖,241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