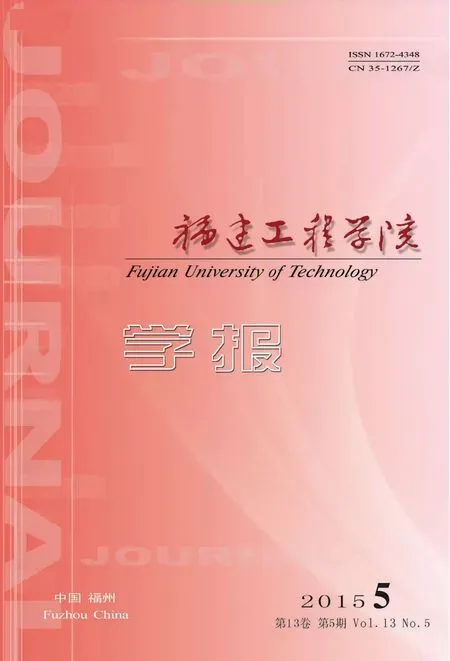《庄子》的修辞语境观及其实践
陈启庆,林秀明
(1.莆田学院文化与传播学院,福建莆田351100;2.福建信息职业技术学院思政教学部,福建福州350003)
《庄子》的修辞语境观及其实践
陈启庆1,林秀明2
(1.莆田学院文化与传播学院,福建莆田351100;2.福建信息职业技术学院思政教学部,福建福州350003)
重温经典,发现2000多年前的庄子,已经在修辞语境观及其实践方面取得了非凡的成就。一方面,庄子明确提出了话语建构应切合时代与社会环境、修辞活动要因人而异、修辞活动要切合接受者的心理等主张,在言与境合方面有较为成熟的理论认知与理论提炼,并能切实地身体力行;另一方面,庄子还自觉地、创造性地营造虚境、梦境等言说环境以有效地言道与传道,在设境显旨方面也有熟练的实践。庄子的修辞语境理论及其实践,将为我国当代语境学建设提供丰富的传统营养与资源。
《庄子》;修辞语境;言与境合;创境显旨
修辞语境也叫言语环境,指的是人们“使用语言的环境或者说修辞行为过程中所关涉到的各种因素”[1]。在修辞行为中,无论是话语建构,还是话语理解,都与修辞语境息息相关。正因此,修辞语境愈来愈受到当今人们的普遍关注与重视,并且成为了当代修辞学、语用学以及其他语言学科的重要理论之一。然而,今天当我们重读《庄子》这一经典时,我们却惊讶地发现,无论是对修辞语境的理论认知,还是对修辞语境的稔熟操作,庄子都无愧于一位语境学的行家里手!
一、“义设于适”:言与境合
咸池九韶之乐,张之洞庭之野,鸟闻之而飞,兽闻之而走,鱼闻之而下入,人卒闻之,相与还而观之。鱼处水而生,人处水而死,彼必相与异,其好恶故异也。故先圣不一其能,不同其事。名止于实,义设于适,是之谓条达而福持。(《至乐》)
由于事物各自的禀性不同,所以彼此的喜好有别,因此凡事不可“一其能”“同其事”,亦即不可一成不变、一概而论,而应当“义设于适”。这里,“义”与“宜”相通,可引申为当然之则,“适”则有合宜或适合特定情景之意。所以“义设于适”,也就是当然之则的运用应合乎具体的情景。[2]就言语行为而言,便可理解为:特定的言语活动应当与特定的情景相一致,具体的话语建构应当与具体的语言环境相统一,只有这样才能获得理想的修辞效果。
(一)“不可与庄语”:话语建构应切合时代与社会环境
在《天下》篇中,庄子对自身的言说方式与表达特点作了自我揭示,即“以谬悠之说,荒唐之言,无端崖之辞,时恣纵而不傥,不以觭见之也。以天下为沈浊,不可与庄语。”在此,庄子明确地告诉人们,《庄子》的话语建构之所以不用“庄语”——不用严正的话,而更多地采用“谬悠之说”“荒唐之言”“无端崖之辞”之类的话语形式,是因为“天下沈浊”——因为自己所处的时代、所生活的社会环境沉沦堕落、混浊不堪。反之,在一个“沈浊”无序的社会里,人们的言语交际、言语活动如若采用“庄语”的形式,反而是无益而且不当的。可见,在庄子看来,如何言说、建构怎样的话语形式,应当与时代背景、社会环境紧密联系,换句话说,时代与社会环境往往影响并制约着修辞主体的话语表达与话语建构。
众所周知,庄子生活的战国中期,正是社会进入快速变革时期,周初以来的礼乐制度风光不再,宗法制政治、经济、军事体系纷纷土崩瓦解,诸雄争霸加剧,弱肉强食,整个社会岌岌可危:
方今之时,仅免刑焉。福轻乎羽,莫之知载;祸重乎地,莫之知避。已乎已乎。临人以德!殆乎殆乎,画地而趋!迷阳迷阳,无伤吾行!吾行郤曲,无伤吾足。(《人间世》)
庄子认为处于无道社会的人们生存非常不易,处世非常艰难,时时需要小心留意,生活其中能够免遭刑罚已属不易,幸福更是比羽毛还轻,没有谁能够真正去享受它;灾祸比大地还重,没有谁能够回避它。不要去做什么努力,用道德去教化别人更是危险。在庄子看来,在一个“福轻乎羽”“祸重乎地”“仅免刑焉”这样无序与无道的社会里,任何言语行为与修辞活动不但充满艰难,而且充满艰险。也正是从话语建构应当切合时代与社会环境这一语境观出发,庄子自然地把那种言语活动与特定时势相背离的修辞行为视为不合时宜,并予以讥讽与挞伐。
颜渊东之齐,孔子有忧色。子贡下席而问曰:“小子敢问,回东之齐,夫子有忧色,何邪?”
孔子曰:“善哉汝问!昔者管子有言,丘甚善之,曰:‘褚小者不可以怀大,绠短者不可以汲深’。夫若是者,以为命有所成而形有所适也,夫不可损益。吾恐回与齐侯言尧舜黄帝之道,而重以燧人神农之言。彼将内求于己而不得,不得则惑,人惑则死……”(《至乐》)
不难看出,这里孔子所担心的正是颜回那种不合时宜的言语行为——在齐侯面前或“言尧舜黄帝之道”或“重以燧人神农之言”。
然而,孔子自己又如何呢?在庄子笔下,孔子的言语行为与修辞活动比起颜回来常常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
孔子谓老聃曰:“丘治《诗》《书》《礼》《乐》《易》《春秋》六经,自以为久矣,孰知其故矣:以奸者七十二君,论先王之道而明周、召之迹,一君无所鉤用。甚矣夫!人之难说也,道之难明邪?”
老子曰:“幸矣,子之不遇治世之君也!夫六经,先王之陈迹也,岂其所以迹哉!今子之所言,犹迹也。夫迹,履之所出,而迹岂履哉?”(《天运》)
孔子也总想凭借自己对《诗》《书》《礼》《乐》《易》《春秋》六经的熟谙,以期说服列国君王采纳他的治国之道与政治主张,可惜在现实中却屡屡碰壁。对此,老子一针见血地指出,孔子的劳而无功完全在于自身的不合时宜——言说内容完全脱离了社会现实。在老子看来,孔子所谓的“先王之道”“周召之法”乃至于“六经”,对于当时的社会现实而言,都不过是过时而落后的主张,就好比人走路留下的足迹与鞋子是完全两样的,如果硬要加以推行,那便是逆时代而动,反时势而行,其结果只能是以失败而告终。
(二)“宋人资章甫而适诸越”:修辞活动要因人而异
《逍遥游》中记录了这样一件事:“宋人资章甫而适诸越,越人断发文身,无所用之。”其意是:北方的宋国有人贩卖帽子到南方的越国,越国人不蓄头发满身刺着花纹,没什么地方用得着帽子。宋人由于不了解越人的生活习惯,结果闹出了笑话。做生意如此,与人交际、修辞活动又何尝不是这样?在庄子看来,言语交际与言语活动同样要了解对象、分析对象并根据对象的不同特点因人而异、区别对待,而不可千篇一律、千人一面、一副面孔、一个腔调,如此才能达到应有的修辞效果与修辞目的。正所谓“在什么山头唱什么歌”,面对不同的对象时,该不该言说、何时言说、言说什么以及如何言说等,这些都是言说者在具体言说活动中必须注意与思考的问题。《人间世》开头叙述的三个故事——“颜回之卫”“叶公子高使齐”“颜阖傅卫灵公太子”——便是对这一语境认知的有力证明与示范:庄子假借孔子与蘧伯玉之名告诫人们,尽管都是臣子与君王之间的相处与交往,尽管在相处与交往中无一例外地都充满着或伤身或害命的危险,但庄子认为在面对不同的交往对象时,还是应当分别对象、区别对待,而不可强求一致。为此,我们看到,在面对年少专断的卫君时,孔子提醒颜回应“先存诸己后存诸人”,教给颜回的方法是“入则鸣,不入则止”,是“心斋”;当相处与交往的对象换成齐侯与楚王时,孔子给叶公子高的指点则是“为人臣子者,固有所不得已。行事之情而忘其身,何暇至于悦生而恶死!夫子其行可矣。”而当交际对象变成卫灵公太子时,蘧伯玉开给颜阖的交往之方又随之而变:“彼且为婴儿,亦与之为婴儿;彼且为无町畦,亦与之为无町畦;彼且为无崖,亦与之为无崖。”庄子正是借此以告诫人们,由于不同个体在年龄、阅历、学识、性格等方面存在着差异,因此,在与不同的人进行言语交际时,也理应采取不同的交谈方式及其言说策略,唯有如此,才能取得最佳的言说效果,也唯有如此,方是理想的言说之道。
(三)“亲父不为其子媒”:修辞活动要切合接受者的心理
庄子认为世人存在的一种普遍心理是“与己同则应,不与己同则反;同于己为是之,异于己为非之。”因而,“亲父不为其子媒。亲父誉之,不若非其父者也。”这是“非吾罪也,人之罪也”,即接受者心理作用的原因。所以要“藉外论之”,要借助“他者”来言说自己的主张。而这不正说明庄子对当时世人接受心理的高度把握与重视?也正是有了这样的把握,并出于交际效果的考虑,庄子认为修辞活动还应注意接受者的反映、充分考虑并尊重接受者的接受心理。因为,这是取得理想交际效果的又一必要条件。
《徐无鬼》中,徐无鬼在与魏武侯的交谈与交往时,虽然始终都没有说及“诗书礼乐”或“金板六弢”等为君之道与治国之方,所谈论的也只是关于如何相狗与相马之类的无关紧要的话题,然而魏武侯听后却“大悦而笑”。从某种意义上说,徐无鬼能够取得这次言语交际的成功,便在于他牢牢抓住了魏武侯接受心理的结果。
《田子方》中的文王,可谓是参透接受者接受心理的另一典型人物:
文王观于臧,见一丈夫钓,而其钓莫钓;非持其钓有钓者也,常钓也。文王欲举而授之政,而恐大臣父兄之弗安也;欲终而释之,而不忍百姓之无天也。于是旦而属之大夫曰:“昔者寡人梦见良人,黑色而髯,乘驳马而偏朱蹄,号曰:‘寓而政于臧丈人,庶几乎民有瘳乎!’”诸大夫蹴然曰:“先君王也。”文王曰:“然则卜之。”诸大夫曰:“先君之命,王其无它,又何卜焉!”
显然,这是文王利用接受者的接受心理巧妙而又富有成效地实施了一次修辞行为:文王在一次臧地游历途中,看到一老者似钓非钓,就想推举他来管理政事,但如果采用强行推动的做法,则势必引起大臣乃至于父兄们的不安甚至阻挠,于是便假借“先君之命”,从而便轻而易举地解决了这一难题。对文王的这一做法,颜渊深感不解,认为凭借文王作为君王的身份,又何必多此一举呢?然而,颜渊的这一疑问却也恰恰暴露了他对接受心理在交际中的作用的一无所知。相较而言,还是孔子看出了文王的用心:“彼直以循斯须也”,即他只是顺着众情于一时就是了。
应当指出的是,在《庄子》中,所有“籍外论之”——借“他者”言说的修辞现象均是庄子对接受者接受心理与修辞效果充分考虑的结果。
二、“无何有之乡”:设境显旨
在修辞活动中,修辞语境固然影响并制约着言语行为,但这并不意味着修辞主体只能一味地被动适应。事实上,修辞主体在修辞活动中同样有较大的灵活性与能动性,即修辞主体完全可以根据交际的需要,主动地创造有利于修辞行为的修辞语境。当代修辞学家王希杰先生就曾说过:“语境是客观地存在着的,但是交际者也可以临时地创造语境。”[3]无独有偶,陈汝东先生也认为:“鉴于修辞行为与语境因素之间的互动关系,修辞过程中,修辞者不但可以积极利用语境因素,而且还可以能动地调动各种语境因素甚至创设语境,利用话语或其他条件,使语境适应修辞需要。”[1]
世所公认,庄子是先秦时期创造寓言故事的第一大家,而这一个个寓言故事,不也分明是庄子所创造的一个个气象万千、奇异非凡的修辞语境吗?不仅如此,我们甚至可以说庄子在创设语境方面已经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境地。那么庄子创造这一系列千奇百怪的寓言其修辞意图何在?显然,庄子并非借此炫耀自己的超凡想象,也并非借此来眩人耳目。为了找出其中的答案,这里我们特拣出庄子笔下的虚境与梦境作一考察。
(一)虚境
纵观《庄子》笔下各圣人、神人、至人居住或游历的处所真可谓是异彩纷呈——有“六极之外”“无何有之乡”“圹埌之野”,有“冥伯之丘”“昆仑之虚”“黄帝之所休”,有“尘垢之外”“无极之野”“六合之外”,等等,不一而足。
这些居所、处所,究竟地在哪里?所在何方?假如有人想从考古的角度对此予以考究,其结果只能是无功而返,因为,这些地理空间事实上都不是实有——现实的存在,而均是庄子创设的“无有”——虚拟之地、虚构之所。那么,庄子又为什么要虚构出如此之多的“无何有之乡”呢?或许从下面这个故事中我们会找到答案:
市南宜僚见鲁侯,鲁侯有忧色。市南子曰:“君有忧色,何也?”
鲁侯曰:“吾学先王之道,修先君之业;吾敬鬼尊贤,亲而行之,无须臾离居。然不免于患,吾是以忧。”
市南子曰:“君之除患之术浅矣!夫丰狐文豹,栖于山林,伏于岩穴,静也;夜行昼居,戒也;虽饥渴隐约,犹且胥疏于江湖之上而求食焉,定也。然且不免于罔罗机辟之患,是何罪之有哉?其皮为之灾也。今鲁国独非君之皮邪?吾愿君刳形去皮,洒心去欲,而游于无人之野。南越有邑焉,名为建德之国。其民愚而朴,少私而寡欲;知作而不知藏,与而不求其报;不知义之所适,不知礼之所将。猖狂妄行,乃蹈乎大方。其生可乐,其死可葬。吾愿君去国捐俗,与道相辅而行。”
君曰:“彼其道远而险,又有江山,我无舟车,奈何?”
市南子曰:“君无形倨,无留居,以为君车。”
君曰:“彼其道幽远而无人,吾谁与为邻?吾无粮,我无食,安得而至焉?”
市南子曰:“少君之费,寡君之欲,虽无粮而乃足。君其涉于江而浮于海,望之而不见其崖,愈往而不知其所穷。送君者皆自崖而反。君自此远矣!故有人者累,见有于人者忧。故尧非有人,非见有于人也。吾愿去君之累,除君之忧,而独与道游于大莫之国。方舟而济于河,有虚船来触舟,虽有惼心之人不怒。有一人在其上,则呼张歙之。一呼而不闻,再呼而不闻,于是三呼邪,则必以恶声随之。向也不怒而今也怒,向也虚而今也实。人能虚己以游世,其孰能害之!”(《山木》)
这里,市南宜僚为鲁侯开出除患的办法是“与道相辅而行”“独与道游”。那么,“道”在何方?又当如何得“道”?为此,市南宜僚进而告诫鲁侯说,当以“虚己”之心,去“无人之野”“建德之国”“大莫之国”得“道”。而“无人之野”“建德之国”“大莫之国”同样并非实有之地,乃是庄子所创造出来的“无何有之乡”——“道居之所”“道之境域”。如此,“无何有之乡”不正是呈现无有之道体的最佳语境吗!
除此之外,这“无有”之境,无疑还具有消解并破除世人那种对号入座式的“是执”之心的作用,进而由忘言而得意。无奈,鲁侯凡心太重且道心太浅,总念念不忘“彼其道远而险,又有江山,我无舟车”“彼其道幽远而无人,吾谁与为邻?吾无粮,我无食”等实有,不免让人遗憾。而鲁侯终将未能得“道”也便在意料之中了。
(二)梦境
古人认为,梦是神灵的启示或预兆,因而中国古代特别重视对梦的阐释,为此,各种圆梦、解梦或释梦的所谓占梦术也便应运而生。据记载,占梦术早在西周时期就已流行,周天子还专门设有占梦官为天子和诸侯占梦。《诗经·小雅·正月》就有“召彼故老,讯之占梦”的诗句,《周礼·春官》也有“(太卜)掌三梦之法,一曰致梦,二曰觭梦,三曰咸陟”的记载。而这些实际上也从一个侧面说明了中国古人对梦的一种认知:虽然虚幻,但却是实在的;虽然神秘,但却是可信的。庄子对此可谓了如指掌且熟谙此中的奥妙,也因此,庄子总是屡试不爽,常常或假借梦境来言说,或创设梦境来传道。上引《田子方》篇中文王正是假借先君托梦之事顺利地请来臧地老者以辅助自己管理国家政事,而且没有遭到丝毫反对与阻拦。又如:
庄子之楚,见空髑髅,髐然有形,撽以马捶,因而问之,曰:“夫子贪生失理,而为此乎?将子有亡国之事,斧钺之诛,而为此乎?将子有不善之行,愧遗父母妻子之丑,而为此乎?将子有冻馁之患,而为此乎?将子之春秋故及此乎?”于是语卒,援髑髅,枕而卧。
夜半,髑髅见梦曰:“子之谈者似辩士。视子所言,皆生人之累也,死则无此矣。子欲闻死之说乎?”
庄子曰:“然。”
髑髅曰:“死,无君于上,无臣于下;亦无四时之事,从然以天地为春秋,虽南面王乐,不能过也。”
庄子不信,曰:“吾使司命复生子形,为子骨肉肌肤,反子父母妻子闾里知识,子欲之乎?”
髑髅深矉蹙頞曰:“吾安能弃南面王乐而复为人间之劳乎!”(《至乐》)
世人究竟应当如何面对“生”“死”,究竟应当持有怎样的生死观?对此,世俗社会往往有一个根深蒂固的观念,这就是“好死不如赖活”,在这一观念支配下,其结果便是“贪生怕死”。然而,庄子的看法却相反。庄子认为,世俗社会的这一“心魔”,恰恰不利于“养生”,更不利于“乐生”。为此,庄子提出了“生死一如”的观点。这里,庄子正是通过“髑髅见梦”这一梦境的营造,也正是通过这一“梦”的言说,形象而俏皮地把“生不如死”的理念寄寓其中,从而对世俗观念作了彻底颠覆,不仅节省了许多逻辑论证的口舌,而且又大大地强化了“言后之效”。
有学者说过:“任何一种理论的自我修正、话语更新,都同时面对着传统资源和当下的学术前沿。赋予理论以现实形式的,是当下的创造,也是传统的馈赠。”[4]回眸历史,重温经典,一方面,我们惊讶于两千多年前的庄子对语境的理论认知已然达到如此的深入与系统,另一方面,我们更为庄子那种开创性的设境、造境实践而啧啧称赞。同时,我们也有理由相信,庄子的这些语境观及其实践,也定会为我国当代语境观、语境学更加茁壮成长提供丰富的传统营养与资源。
[1]陈汝东.当代汉语修辞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30,364.
[2]杨国荣.《庄子》哲学中的名与言[J].中国社会科学,2006(4):38-42.
[3]王希杰.修辞学通论[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1996:340.
[4]谭学纯,朱玲.广义修辞学[M].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2001:4.
(责任编辑:许秀清)
The theoretical cognition on the rhetorical context and practices in“Chuang Tzu”
Chen Qiqing1,Lin Xiuming2
(1.College of Culture and Communication,Putian University,Putian 351100,China;2.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Science Department,Fujian Polytechnic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Fuzhou 350003,China)
Re-reading classical Chinese work“Chuang Tzu”reveals that Chuang Tzu had attained extrodinary achivements in the theoretical cognition on rhetorical context and his rhetorical practices over 2000 years ago.He claimed that rhetorical formulation should cater to the times and the social environment,the rhetorical activities should vary with people and suit the psychology of the receptors.He had amature theoretical cognition and theorectical refinement and he himself put his cognition in his practices.Meanwhile,he consciously and creatively created vacantand dreaming contexts for his discourse context to effectively communicate and disseminate his thoughts and ideas and had skilled in his context designs.His theory on and practices in the rhetorical contextwill provide rich traditional nutrition and resources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contemporary context.
“Chuang Tzu”;rhetorical context;contextmatching;context creation
H13
A
1672-4348(2015)05-0409-05
10.3969/j.issn.1672-4348.2015.05.001
2015-07-21
陈启庆(1965-),男,福建仙游人,副教授,文学硕士,研究方向:汉语修辞学与汉语语用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