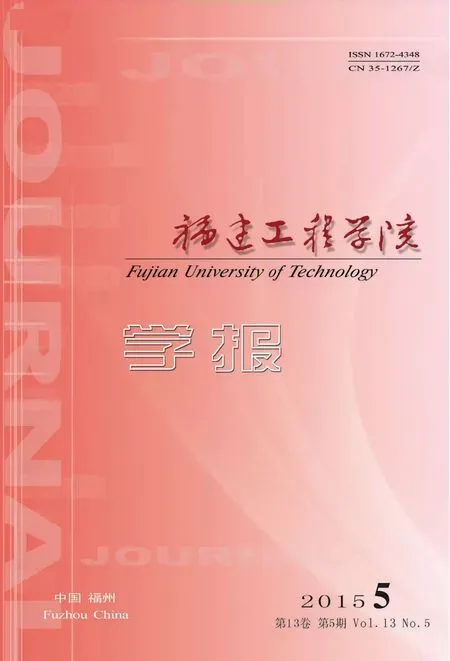建国后毛泽东国际话语传播的环境、主题及启示
吴贤军
(福建工程学院人文学院,福建福州350118)
建国后毛泽东国际话语传播的环境、主题及启示
吴贤军
(福建工程学院人文学院,福建福州350118)
中国和平发展的势头,越来越引起西方国家利用话语表述施加各种软遏制。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代领导集体的核心,毛泽东建国后曾多次在外事场合就国际形势发表观点,并有力地加强了中国国际话语传播的影响力。从政治传播学的视角,整理和分析《毛泽东文集》中的相关文本,能够表明其对不同历史时期的国际话语环境变化有着清晰而准确的判断,对国际话语主题、风格进行了有益的定位。当前,中国要构建更有利的外部舆论环境,正需要借鉴毛泽东国际话语在内容、表述和目标上的认识实践。
毛泽东;国际话语;话语表述;政治传播
法国哲学家福柯曾说过:“知识(话语)激发了活动,而不是禁锢了活动,诱导了思想,而不是禁锢了思想,引发了话语,而不是打断了话语。”[1]218可以说,正是言语的修辞、主体和风格等内在特性,在国家领导人所置身的国际政治背景中产生意义,才使得国际传播和国家形象以主体意识和权力渗透的方式展现了出来。在当今相对和平的国际环境下,随着各类主体、利益之间交叉和作用的不断深化,大国间的话语往往成为集中反映国家意志、展示国家影响的手段,容易受到国际社会的关注。然而,西方国家长期以来不断运用多种话语内容和话语平台来压制中国发出的不同声音,从而使中国长期面临“话语困境”。
作为大国领导人和知名政坛人物,毛泽东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后的27年里曾经多次就国际问题发表谈话,其中不少谈话的对象都是国际人士。这些谈话中的内容已经被众多毛泽东思想的学者研读和分析,但基于中国的话语输出而对文本进行的研究却并不多。针对毛泽东同志建国后的重要外交谈话具有施加话语权力的特点,可以通过对《毛泽东文集》第六卷、第七卷、第八卷(均为人民出版社1999年出版)中的40多篇谈话文本进行分析,并结合毛泽东的外交和国际战略思想,探讨毛泽东的国际话语传播及其背后的成因,以求对当前中国如何争取国际政治话语权提供借鉴。
一、毛泽东就国际话语环境的基本认识
建国后到20世纪70年代的20年左右时间里,随着国际政治格局波谲云诡地变化,毛泽东对于国际话语环境的认识有着一个逐渐变化的过程,其运用国际话语的意识也逐渐增强,按时间划分,可以中苏同盟关系的破裂为标志,分为前后两个阶段。
(一)“一边倒”的国际话语环境
20世纪50年代初的中国,奉行的是“一边倒”的外交政策,这一时期毛泽东的涉外谈话相对比较单一,主要体现在两大主题:一是站在社会主义阵营的立场上,反对美帝国主义。二是关于朝鲜战争的正当性话语。前者具有代表性的有《驳斥艾奇逊的无耻谣言》,后者主要体现在《朝鲜战局和我们的方针》一文中。但在这段时期里,毛泽东认识到部分国家具有同中国外交接触的可能性,也试图从一些对中国相对友好、反共色彩不那么浓厚的国家里打开局面。例如,在1954年7月7日同《英国工党代表团的谈话》中说“美国所谓反共,不一定是真的,而是要把它当作题目来做文章,以达到它另外的目的”,[2]339这时的毛泽东相信广大中间地带国家不一定都会认同美国的反共话语。
从50年代中期开始,毛泽东的外交谈话日渐增多,且受到国际话语环境制约的程度明显减轻,更易于表现出一种符合中国自身利益和意志的言说。尤其是在1954年的日内瓦会议和1955年的万隆会议之后,毛泽东逐渐认识到在第三世界国家中更多地争取有利于中国形象的舆论支持是完全可能的,因而也开始尽可能用话语来团结一些第三世界国家。在同印度总理尼赫鲁、缅甸总理吴努、泰国经济文化代表团等的谈话中都可以看出,其话语对象的重心已经调整到不结盟运动中的代表性国家和地区。苏联共产党二十大后,赫鲁晓夫对斯大林作出了全盘否定,苏联对待中国的大国沙文主义倾向亦越发明显,在一系列问题上都表现出以“老子党”自居的态度。毛泽东在这一时期国际问题的谈话中,明显将如何看待斯大林,以及如何处理中苏关系作为话语的重要着眼点。例如,在部分文章中,毛泽东提到“要从本国的实际出发来进行革命实践”“每个民族都有自身的长处和短处”“对苏联、斯大林的问题要辩证地来看待”[3]24等一系列的话语主张。当然,此时中苏关系尚未全面破裂,中国仍然在国际上自视为社会主义大家庭的成员,所以对苏联展开话语对抗和争夺并不被毛泽东认为是主导性谈话内容。甚至在不同场合,他还尽量微妙地将社会主义世界中的话语环境解读为同志、家庭之间的争吵。例如,在接见南斯拉夫共产党代表团时,他仍然秉持着“支持苏联作为中心,这对社会主义运动有利,尽管你们不同意”这样的观点。
(二)“两个拳头打人”和“一大片”的国际话语环境
60年代初,伴随着中国与苏联(中苏)大论战和关系的全面破裂,苏联“变成修正主义”与已有的打倒“美帝国主义”一样都成为中国官方的既定话语。在《毛泽东文集》中,我们对这一时期毛泽东的谈话研究,明显发现强化了革命输出的话语。或许,这一时期的毛泽东不愿意对外国友人多谈对苏联的态度,而是将眼光主要放在了广阔的“中间地带”。相比之下,除了在1964年初《赫鲁晓夫不好过》这篇谈话中表达了“大闹天宫”的姿态之外,其他的谈话更多地体现在向第三方势力,即“一大片”亚非拉国家的靠近上。毛泽东此时最为看重在“中间地带”国家中争取道义和舆论支持,他更加意识到国际话语权力的重要性,这一时期堪称是其国际话语实践最为成熟的阶段。毛泽东认为,在政治、经济、军事实力都空前不足,两个超级大国虎视眈眈的现实面前,中国必须尽可能地团结更多朋友。他对话语权的思考和实践也侧重在三个层面:一是对亚非拉民族国家的独立革命的话语支持;二是对所谓的美国苏联盟友国家内部反抗运动的话语鼓动,如《日本人民的斗争影响是很深远的》《中法之间有共同点》等篇谈话;三是在对话中注重谈论当时西方世界出现的社会主义、和平主义的运动和思潮,尤其善于抓住一些资本主义国家的国内矛盾来作文章。其中有代表性的例子是,这一时期美国国内爆发了黑人反对种族歧视的“民权运动”,1963年8月9日《人民日报》就发表了毛泽东主席的关于《支持美国黑人反对种族歧视斗争的声明》一文,将黑人的抗议活动视为美国被压迫人民反对统治阶级的伟大抗争。该时期的话语实践,体现了毛泽东本人将国际意识形态话语权斗争、民族解放话语权斗争、冷战双方阵营内部话语权斗争以及国内阶级利益话语权斗争充分结合的深刻战略思想。
60年代末至70年代初,国内“文化大革命”高潮的逐渐淡去,毛泽东对于国际关系和国际政治的思考日趋冷静。虽然这一时期他的对外谈话数量有所减少,但却展现出务实性的话语转向。一方面,更加重视对外宣传的有效性,提出了不少改进对外宣传方法的重要观点;另一方面,则侧重于减少话语的进攻性,逐步淡化对资本主义国家的敌视和不满色彩,进而为中国与美国、日本展开对话进行话语尝试和铺垫。尤其是1970年12月18日就尼克松的谈话,他说道:“我欢迎尼克松上台。为什么呢?他的欺骗性也有,但比较地少一点,你信不信?”[4]436,这表明要以一种国家利益为重的实用主义风格,为打破阻碍中美两国关系的坚冰做努力。
纵观建国后毛泽东的对外交往谈话,每个时期的特点都不是绝对的,例如对亚非拉国家的肯定和友谊往往贯穿于多个时期。此外,由于对国际环境风云变化需要有微妙的判断,其言说主题往往会针对不同对象、不同时局而突然调整。但总体而言,毛泽东作为伟大的政治家、外交家,对于新中国所处的险恶舆论环境以及自身话语权弱小的现实有着十分清醒的认识,只是在遵循总体国际话语规则的前提下,让中国适度参与了国际议题的讨论和设置。
二、毛泽东给予国际话语主题的充分定位
福柯认为,掌握话语权的人就能够掌握社会规范。毛泽东意识到中国作为一个大国,其主动发声的国际话语必然会对国际社会就中国的看法和行为产生一定影响。因此,他较为注重在谈话过程中对话语主题和风格两方面进行定位,从而展现中国最高领导层对国际话语空间的介入姿态。
(一)革命的话语定位
角色定位是话语分析理论的重要视角,毛泽东一直以来将中国视为世界社会主义革命的重要组成力量,所以建国后主动赋予了中国以社会主义革命的主力军、反帝国主义的支持者的角色定位。尤其是面对50年代末至60年代初风起云涌的民族解放运动,更是将自己视为民族解放的引导者。例如,在同非洲青年代表谈话时,他说“非洲人要依靠自己的力量来解放非洲”[4]8;在同越共领导人长征谈话时,他说“不能只做和平取得胜利的打算,要设法使得革命阵营的国家占绝大多数”[3]16;在同巴西记者谈话时,他说“打老虎要讲究拳法,要一拳一拳的打,不能大意”[3]405。此外,更广义地看,他甚至将日本等资本主义国家人民对美国的不满视为反对帝国主义的民族民主革命的一部分,从话语上将日本工人同美帝国主义及其在日本的代言人——“岸信介一伙人和垄断资本集团”对立起来。这种革命的话语定位,尽管较为激进,却在某种程度上契合了部分国家、民族争取独立、民主、自由、和平的呼声,在当时的国际舞台上有一定市场。正是在这种革命的声援中,他塑造出了中国作为弱小国家和被压迫人民坚定盟友的国际地位和形象。
(二)团结的话语定位
毛泽东同志的国际统一战线思想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时期就初步形成,[5]125-130建国之后,这种思想的发展更强烈地影响了其对于国际关系的思考和论述。我们可以看到,在其外交性的谈话中多次强调了具有“团结”意义的话语,包括团结、平等、合作等等。这种团结的话语针对不同的言说对象,还可以分为四种类型。一是谈中苏以及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但这种话语在60年代以后就基本不提了;二是同一些国家的共产党领导人谈话,会从全世界无产阶级联合上谈反对帝国主义,包括1959年3月会见美国共产党中央书记杰克逊、1959年10月会见澳大利亚共产党总书记夏基时都提到各国兄弟党的相互支持;三是在同亚非拉国家领导人的谈话中提出了弱小国家要团结一致,反对美帝国主义的话语。毛泽东一直坚持中国与弱小国家的共同点要远大于分歧,例如在1954年10月同尼赫鲁的多次谈话中,他就强调“中国和印度在受外国欺侮、热爱国家方面的感情是一致的”,“我们东方人有团结起来的感情,有保卫自己的感情”。[2]361在他看来,哪怕是中国与亚洲邻国,其领土的争议也不会非常大,在共同的敌人面前都不会是根本矛盾。就像他在《中尼边界要永远和平友好》的谈话中说的那样:“我们同印度吵了一年架,但还是朋友。朋友吵架是常有的,夫妇之间、兄弟之间都吵架。”四是到了60年代末期,毛泽东还在与美国、日本、西欧客人的谈话中说到了一种发达国家民众与中国团结起来反对本国统治集团的可能。这种超越了国家界限来谈团结,虽然未必符合实际,但却是对中国话语影响力的倍增。
(三)谦虚的话语定位
话语权力的重要内涵就在于语言形成的威慑力和感染力,正因为话语权是通过反映主观意识的话语来表达和运用权力,而不是通过冰冷的刀枪,所以总是沾染着文化、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因素。[6]12-13话语的谦逊往往会避免咄咄逼人的态势,而用更加委婉、风趣的表达来说服对方,可以达到更好的传播效果。毛泽东同志在对外谈话方面就十分注意这一点,他曾就对外宣传问题告诫道:“第一,要注意不要强加于人;第二,不要宣传外国的人民运动是由中国影响的,这样的宣传易为反动派所利用,而不利于人民运动。”[4]432而他自己的言语中也时刻注意既保持谦逊的语调,又尽可能利用一些话语修辞来表情达意。例如,对于当时有些小国受到美帝国主义的鼓动,宣扬中国可能会对外侵略,毛泽东幽默地说:“你们回去以后,请告诉你们的下一代,将来中国如果翘尾巴,翘到一万公尺以上,就批评它。”[3]124他还对南斯拉夫代表团说道:“中国作为大国要非常谨慎小心,要避免盛气凌人,要‘夹紧尾巴做人’。”[3]123可以说,正是这种对待各国人士一律友好、谦虚的态度,赢得了众多小国、弱国对于中国话语及毛泽东本人的尊重。
(四)自信的话语定位
正如谦虚的话语反映出中华民族千百年来温文尔雅、内敛含蓄的文化底蕴一样,自信的话语也正是毛泽东本人性格特征的最好写照。尽管当时新中国诞生不久,但在毛泽东的国际话语中我们不难发现对和平或正义战争的自信,对中国人民的自信。例如,他曾经多次在各个国际谈话场合从战略上论证一个观点:即帝国主义都是纸老虎,弱者可以战胜强者。他也曾在同11个社会主义国家代表谈话时说:“世界上有人怕鬼,也有人不怕鬼。”[4]51此外,在同蒙哥马利元帅谈论世界局势时,他会毫不掩饰对英法挑战美国领导权的欣赏;在印尼苏加诺总统希望中国主动提出“入联”时,他会坚定地说:“中国进入联合国,就像《雁荡山》一样,要飞进去,也就是说,我们要打进去。”[3]142谦虚和自信构成了毛泽东国际话语中的双重定位,正因为毛泽东本人具有这种充满着辩证法思想,“一张一弛,文武之道”般巧妙的政治艺术,才能使中国的国家话语权力软硬兼施地得以展现。
三、毛泽东话语实践对当前国际传播的几点启示
当前中国的国际话语权构建,就国家层面上看还主要停留在媒介和载体上,似乎把国际话语权等同于国际传播权。而毛泽东时代,尽管中国对外传播媒介还很弱小,传播手段也较为落后,但中国在世界上的话语影响力却能与日俱增。通过剖析毛泽东的话语传播实践,我们更加认识到,话语是思想内容的载体和表现,只有真正树立起中国国际话语的内在自信,才可能根本改变所处的话语弱势地位,传递出更有力的中国声音。
(一)要善于传播既有的先进思想和经验
对中国或对世界其他国家而言,毫无用处的话语体系无论建构得多么完美都难以“行之久远”。[7]73毛泽东的谈话之所以能够有助于中国在国际上占据话语高地,恰恰是因为毛泽东个人深刻的思想内涵,以及他对治国、治党、治军方面的丰富创见。值得一提的是,毛泽东领导共产党及人民军队进行武装斗争的经验,对于广大还处在反帝和民族解放进程中的亚非拉人民而言,尤为具有影响力。例如,在1956年3月的同长征、艾地的谈话、1960年10月同埃德加·斯诺的谈话中,我们都可以看到谈话对象不仅十分关注毛泽东军事思想的现实意义,对于《毛泽东选集》也认真进行了阅读和理解,这充分说明毛泽东思想作为当时一种为实践证明了的先进理论,展现了蓬勃的生命力,经过有意识的介绍,理论优势很快就能形成话语优势。后来,我国政府也专门设立了《毛泽东选集》翻译领导机构。这一大型中译外工程包括东语、西语两大翻译团队,涉及语种达30多种。从1949年至1988年,经由中国国际图书贸易总公司向境外发行的外文版《毛泽东著作》共39个语言版本,图书更是达到2 300多种、3 447万多册。[8]国际话语权力不同于现实的国家实力,其改变的往往是话语对象的价值观,而要改变对方的价值选择,就必须提出更重要、更有吸引力的价值成果。中国共产党十八大以来,新一届领导人身体力行,主动对国际社会的关切予以话语回应,特别是《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等书籍在海外的热销热议,更展现出其对自身观点和中国发展的理论自信。然而,国力大幅提升的中国话语权力有限的现状依旧没有改变,根源在于缺乏西方国家那种人文社会科学对已有经验的总结。正如有学者指出的,中国的崛起必须有原创性的基础理论,特别是必须提出世界性的新“主义”,这样才能弥补“拿来主义”的严重不足,也才能在与全人类的共同进步中实现自身的现代化。毛泽东的国际话语实践,正是对这种观点的重要例证,也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后再形成理论输出的最好写照,启示着我们应当自信地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中国道路优越性进行传播与推介。
(二)要着力于产出合理而深刻的概念
话语生成能力强大所导致的话语资源丰富,对于一国话语权的构建具有决定性影响。在毛泽东的国际谈话中,尽管他本人对具体“问题”的分析不多,但却能够通过具有个人风格的思考,形成对概念和话语的推陈出新。最具代表性的是他在1963年谈话中所提出的“两个中间地带”论,以及1974年同赞比亚总统卡翁达谈话时提出的《关于三个世界的划分问题》。无论是“两个中间地带”,还是“三个世界”的提法,由于较为合理地反映了当时的国际力量对比,准确进行了时代发展态势的判断,因而在广大反抗帝国主义霸权和反对美国与苏联冷战的国家和人民中广为认同。近年来,中国在国际上尚未形成具有影响力的崭新概念,如“和平崛起”之类的提法应者寥寥。相比之下,早在上世纪50年代就提出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等话语还更有影响,并仍然得到沿用。然而,冷战结束以来,西方学者、政客却提出了一系列重要的国际关系理论话语,如“历史的终结”“文明冲突论”“民主和平论”“第三条道路”“全球治理”等等。这种话语逆差表明:毛泽东的国际话语实践的重要意义在于,话语的生命力离不开概念创新。应该基于学术理论和现实对策的有效结合,大胆提出解释现状的话语范畴,无论是“新常态”“中国梦”,还是“命运共同体”“大块头”“APEC蓝”。只要力争提出形象而富有说服力的概念,就会产出深受国际舆论欢迎的新表述。
(三)要敢于对国际话语权力体系进行挑战
打破旧的国际格局,建立更为平等的国际秩序,这是中国人民和曾经的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的共同愿望。然而,帝国主义国家依仗知识优势、文化优势和媒体优势,牢牢掌控着国际议题的主导权。尤其是在新中国成立之初,美国就通过对中国“应当放弃侵略政策”“强大起来会称霸”等负面宣传,妄图抹黑中国,甚至挑起亚洲邻国对中国的误解和猜忌。毛泽东敢于直面这种话语攻击,主动而坦诚地阐明中国的态度,不被其“牵着鼻子走”,避免陷入其国际话语陷阱。一个典型的事例是:1955年万隆会议召开后,新中国的国际形象迅速上升至一个高度,不少亚非国家希望中国能够“先入联,再驱蒋”,从而站到反对帝国主义的国际舞台最前沿。联合国是当今世界最主导的话语平台,且民族国家争取加入联合国正是二战后国际话语权力下的游戏规则。但毛泽东却敢于反其道而行,打破现行游戏规则。在1956年9月与印尼总统苏加诺的谈话中,毛泽东指出:“只要在联合国里有一个小小的台湾,我们就不进去。我们一万年也不进去”;“我们要借这个题目做文章。我们天天要求进入联合国,但是我们不讲时间”;“有些人讥笑我们,说中国人总是慢慢来。我们恰好就是这一条”[3]145。后来事实证明,正是这种对国际话语秩序的挑战,才为中国始终坚持台湾问题的原则立场,并且在东西方两大阵营之间争取战略主动创造了条件。当前,中国经济实力的增强极有可能促成话语优势的构建,但要完成两者之间的转化,却不是一帆风顺的。
以中国发起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亚投行)来打破世界金融权力体系为例,就存在着与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亚洲开发银行等原有话语权平台的博弈问题。中国只有坚定目标和信心、遵循公认规范、积极倡导合作,才能真正被视为提供公共产品的负责任大国,受到国际上的广泛认可。
《毛泽东文集》六、七、八卷中关于国际问题或同国际人士谈话的文章多选自《毛泽东外交工作文选》,由于谈话覆盖面有限,仅对其展开研究难以全面概括建国后毛泽东的国际话语实践全貌。但是,基于文本的修辞学、语用学研究,依然能够使我们理清毛泽东国际话语权力观的大致思想轮廓。总而言之,毛泽东同志不仅具有丰富的政治修辞技巧、深刻的辩证法思想、成熟的国际战略思维而且能科学运用马克思主义原理。面对当前新一届国家领导人在国际上主动施展外交新举措,增强话语内容、理念的影响和创新表达方式的新态势,借鉴毛泽东的国际话语传播策略,有助于进一步打破西方国家的话语软遏制,更好地参与国际政治领域话语权力构建。
[1]米歇尔·福柯.规训与惩罚[M].刘北城,杨远缨,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7.
[2]毛泽东.毛泽东文集:第六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
[3]毛泽东.毛泽东文集:第七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
[4]毛泽东.毛泽东文集:第八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
[5]胡为雄.建国后毛泽东国际统一战线理论的发展和演变[J].毛泽东思想研究,2013(2):125-130.
[6]张志洲.中国国际话语权的困局与出路[J].绿叶,2009(5):12-13.
[7]张首映.话语体系建构三题议[J].人民论坛,2012(4):73.
[8]张生祥.《毛泽东选集》的传播为中国拓展国际话语空间[N].中国社会科学报,2013-11-27(3).
(责任编辑:许秀清)
The communication environment,topics and im p lications of M ao Zedong’s international discourse post the founding of PRC
Wu Xianjun
(School of Humanities,Fujia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Fuzhou 350118,China)
The trend of China’s peaceful development has prompted western countries’increasing soft inhibition/suppression via discourse expressions.As the core of the first leadership in China post the founding of Peoples’Republic of China(PRC)in 1949,Mao Zedong used to comment on the international affairs of China and the world in different occasions,who significantly strengthened the influential power of the Chinese international discourse.An analysis of the texts in Mao Zedong’Selected Works is conducted in the perspective of political communication,which demonstrates that Mao had a clear and accurate judgment on the international discourse changing environment and had well grasped the topics and styles of his international discourse.To construct a more favourable international opinion environment,it is critical thatwe draw on the experience of Mao’s international discourse in content,expression and target.
Mao Zedong;international discourse;discourse expression;political communication
A841.3
:A
:1672-4348(2015)05-0437-05
10.3969/j.issn.1672-4348.2015.05.007
2015-03-27
福建省教育厅2013年A类社科项目(JA13220S)
吴贤军(1982-),男,福建福州人,讲师,博士,研究方向:公共关系、政治传播、文化产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