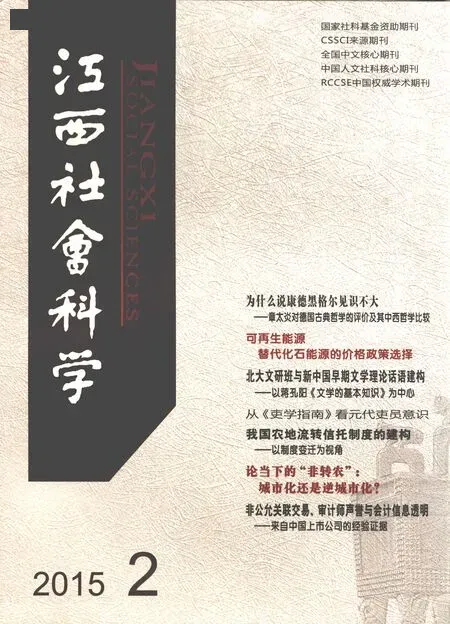“晶体模式”小说与卡尔维诺的深层矛盾
陈曲
“晶体模式”小说与卡尔维诺的深层矛盾
陈曲
卡尔维诺提出小说的“晶体模式”,这被认为是后现代小说家对19世纪现实主义小说形式上的反思,在结构、内容上都颠覆了对小说的传统观念。然而“晶体模式”不仅仅是卡尔维诺小说的总结,更是他对认知、世界、宇宙思考后的总结。晶体模式有着卡尔维诺更为深层的追求,然而这种深层追求中充满了矛盾。无限小包蕴无限大,以及赋形和对秩序的追寻有着深刻的内在矛盾性。这种矛盾性引领他走向更为幽深的思想探索以及小说探索。
晶体模式;赋形;秩序;自我;客体
陈 曲,中国人民大学人文学院博士生。(北京 100872)
伊塔洛·卡尔维诺(Italo Calvino,1923—1985),意大利当代最有影响的小说家,被称为“作家们的作家”。他曾为诺顿讲坛准备《未来千年文学备忘录》,以小说家的睿智提出对小说未来发展形态的勾勒。其中“精确”的特质中暗含他推崇的小说模式——晶体小说。以往的研究者关注的是晶体模式在小说形式方面的创新,认为其是后现代小说的一种创新模式。的确,在晶体模式中包含卡尔维诺对19世纪现实主义小说线性构思的反叛,然而,卡尔维诺之所以提出“精确”特质以及晶体模式,有着更为深层的考虑。这里不仅仅是一个小说形式的问题,它涉及卡尔维诺对世界的思考向度。晶体模式背后暗含卡尔维诺思想中的深层矛盾。
一、“晶体模式”的提出
卡尔维诺提出文学上的“晶体模式”,源于他对水晶的独特偏爱,代表了他对“精确”的理解。在《未来千年文学备忘录》里,他提出了五个小说特质,其中一个关键特质就是“精确”。他提出“精确”的缘由有几点:一,卡尔维诺深感现代社会人类正在经历一场语言与形象的瘟疫。语言与形象变得模糊没有棱角,变得枯燥乏味,再也不能给人一种清晰精确的感觉。犹如一个用旧的器物,使得一切形式的历史都变得没有特色、枯燥乏味、模糊不清、没头没尾。而解决方法只有使用精准的言辞,细心琢磨词汇之间、语言之间、思想之间细微的差异。二,专注于无限小的这一个“精确”,目的是为了通过这个无限小反观无限大。精确地刻画每一个有限,最终是为了掌握无限。而最能将这两方面完美体现的便是“晶体”。由于思维无法直接面对无限,所以必须先精确地掌握无限小,用思维给有限赋形。而晶体具有精确的晶面和折光能力,是完美的模式,它既体现了有限、有序,同时因为它的晶面连缀、叠加,形成一个网络,可以按自身结构自我生成,趋向无限,这就使有限把握无限成为可能。于是卡尔维诺选它作为一种象征。
很显然晶体模式的提出背后隐含两个人类长久的追求:一,通过有限去认识无限;二,对秩序的情有独钟。或者说这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卡尔维诺曾说:“有时候我写历史,努力把精力集中在历史上,结果发现我感兴趣的不是历史而是别的东西。确切地说,我感兴趣的不是某个具体的东西,而是我要写的东西以外的一切东西。是我选择的那个题目及其全部可能的变体、异体之间的关系,是这个题目的时空可能包括的一切事件……为了与这种顽念斗争,我尽力缩小我要讲述的范围,然后把这个范围分成有限的一些范围,再把这些有限的范围分成更小的范围……我被无限小所包围,先是陷入无限广阔之中,现在又陷于无限微小之中。”[1](P337)由无限大到无限小的转换发生了。卡尔维诺是具有野心的作家,他想描写一切,然而直接面对无限是不可能的。保罗·泽利尼在《无限简史》中把无限大翻转过来并将它融化于无限小之中。而卡尔维诺所认为的晶体结构就是这一设想的结果。晶体是有限并有序的,如果这一设想正确,通过晶体就可以接近无限大,接近宇宙,并解释宇宙。然而问题依然没有解决:无限小如何包蕴无限大,从无限小中如何把握或窥见无限大?这要从卡尔维诺的宇宙观看起。他深受卢克莱修和奥维德的影响。从奥维德那里,他得到“同一性”的概念,即事物具有同一性和亲属性的关系。“同一性”既提供变形的可能,同时也提供微小包蕴无限的可能。休姆指出:“卡尔维诺经常描绘知识用它最基本的形式,发现相似性,不管是领地是动物学或词源学或宇宙学或文学,我们划分了一个新的现象,主要通过它们与另外已经知道的,并将之放入一个活动话语或知识网络的相似性。卡尔维诺希望这种相似性和同一性可以给自我知识。”[2](P158)并说:“一个相似的或小的宇宙在一个层面上呼应大的宇宙。”[2](P163)因此,卡尔维诺寻找意义又是在一个大范围内消减找到或建立微观宇宙,这样的象征,作为连接个体与大系统的方式。例如,在《帕洛马尔》中,帕洛马尔在观察海浪时,不是运用目光的连续性来观察一片大海,而是用不连贯的目光,来切割海浪,仅仅观察一个浪头,他想从这唯一的浪头中得到对海浪的认识。在观察草坪时,他局限自己的视域,将草坪分割成一个又一个子集,然后仅仅对一个子集进行观察。这个与博尔赫斯的“无穷后退”的理论有些相似。例如小说《阿莱夫》中的阿莱夫,直径大约为两三厘米,但宇宙空间都包罗其中,体积没有按比例的缩小,每一件事物都是无穷的事物。这也就是卡尔维诺强调精确的原因,精确与平淡、没有棱角相反,而我们唯有用精确来尝试把握无限,如莱奥帕尔迪一样。而什么是精确最完美的象征,他找到水晶。卡尔维诺通过这个逻辑完成有限把握无限的反转,想借用水晶每一个镜面去折射出无穷。而这种想法也是人类亘古不变的野心,以有限自我去认识无穷。
二、对秩序的追寻
晶体完美的几何构造让人沉浸在一个充满秩序、逻辑整一、因果完美合一的世界中。休姆认为卡尔维诺的宇宙有两种形式的外表。一种是微尘:粒子,可分离的,分开的单位。另一种是以大海为代表的混沌,它将微粒吞噬在流体或黏糊中。卡尔维诺同时也承认自己对几何图形、对称、排列与组合比例的偏爱。事物的无序是他难以忍受的。无序代表混乱、漩涡、无意义、死寂、厌烦。混乱可能威胁到自我。他常常以四种形式来表达这种无序:海洋,漩涡,数量繁多和迷宫。这四种无序的象征,卡尔维诺努力与之抗争。因为与之相反,有序代表秩序、意义、生存。他偏爱给事物以有序的形式,而在这种为事物划分和分类的过程中,便得到意义。这也就是他在1962年那篇著名的有关挑战迷宫论文中要阐明的。他说:“一方面,当今需要一种面对复杂现实的态度,来抗拒一种简单化的观点。我们今天需要的是尽可能详细的一张迷宫的地图。另一方面,面对迷宫的迷惑,在迷宫中失去自我,代表了没有出口的人的真实境遇。”[2](P76)他刻画了两种文学选择:一种是绘制迷宫的地图,诚实地呈现出口的迷失,并努力寻找出口;另一种,他们声称没有出口,并认为生活本来就是一场没有出口的迷宫。而卡尔维诺属于前者,迷宫地图的绘制者。他要打破这种无序使一切变得有序起来。有序是通过思维和视觉为事物划为和分类完成的。卡尔维诺认为目前语言和形象的瘟疫使得一切形式的历史都变得没有特色,枯燥乏味,模糊不清,没有始末。这就是一种熵的状态,是一种混乱无序的状态。生活失去形式,使他感到不安。文学是解决这一问题的唯一办法,用语言的精确对抗无序,他把文学放在一个至高的地位。文学是思维的结晶,它是意义的来源,是赋形的工具。赋形是为了让世界变得有序。在这个时期的卡尔维诺看来,秩序是意义的保证。人生而去追寻秩序,也其实是对意义的追寻。然而在这个混乱的年代,我们首先要做的便是对混乱世界的规划,赋形使其变得有序。
三、对赋形的反思
这里有一个明显的悖论:即有限的人如何能包蕴无限,有限的自我如何能给事物赋形?这种赋形是否具有合法性?众所周知,自我问题是一个西方哲学由来已久的问题。奥古斯丁认为“自我”是“是”、“思”、“时”三者的结合。然而在笛卡尔的“我思故我在”中,自我失去了“时”的界定。笛卡尔依靠记忆试图保证自我的同一性,然而假设世界发生混乱,那么记忆便无法起作用,自我的同一性和连贯性也将无从实现。而由此以降,康德、黑格尔、胡塞尔等都没有填补上“自我”这个时间缺口。他们在超越时间的基础上建立先验自我,来保证自我的完整性。人力求成为给一切存在者以尺度和准绳的存在者。然而按照休谟的话来说,心灵是“处于永远流动和运动之中的直觉的集合体或一束知觉”,自我在同一时间内或在不同时间里是没有单纯性可言的,无法保持同一性。自我的确定性是无法论证的,或者说自我本身就是一个成问题的主体。哲学界却忽视这一点,将自我绝对化、先验化。而早在古希腊的智者学派,就已经对人的限度进行限制,在那里没有任何一种主观主义。然而,自柏拉图,尤其是笛卡尔等人的努力,人最终成为以自身为准绳的立法者。正如海德格尔所说:“笛卡尔形而上学的任务就成为:人的解放——走向作为自身确定的自我规定的自由的解放——创造形而上学的基础。然而,这个基础不但本身必然不是一个确定的基础,而且,由于禁阻了来自其他区域的任何尺度,它同时必然就要有这样一种特性,即:所有的自由的本质通过这个基础而被设定为自我确定性了。”[3](P110)于是问题便出现了,成问题的自我却要成为有效性的标准,那么所延伸出来的意义,真理也面临着合法性危机。现代哲学开始这种反思。人们开始放弃知识论的经典追求,放弃普遍绝对的知识追求。维特根斯坦开始寻求改变:他认为词语没有什么固定的意义,只是人们赋予它们意义,没有本质性的东西存在于语言背后,同时提出常识或者说世界图式。“它给我们看事物的方法,给我们的研究工作提供了形式。”[4](P221)而自身是无根据的。它不是演绎出来的,而是先验世界的架构。世界图式不是理论假设而是理论前提。有意思的是,他认为世界图式是可变的,多元的。那么这样一来还存在确切的知识吗?人们面对世界的认识最终会陷入迷惘,世界图式不正是自我局限的提示。而这种反思几乎萦绕海德格尔的全部作品中,包括他对科学的论证:“在科学的研究所扩展和固定化中发生了什么呢?无非是保障了方法对于总是在研究中成为对象的存在者(自然和历史)的优先地位。”[3](P86)哲学上的反思在科学上也得到印证。随着海森堡在物理学上的发现以及哥德尔在数学上的发现,科学终于赶上哲学的预言:理性有着不可避免的限度。海森堡的测不准原理表明这个世界本质性的混乱。物理学家冯·鲍利说:“我们因观察一个实验装置A而毁掉B,或者选择B而毁掉A。但是,我们不能选择它们当中一个也不毁掉。”[5](P38)这充分说明我们无法认识事物的全貌,事物的全貌永远在我们认知范畴之外。当我们以为达到对某个事物的认知时,不过只是看到事物的一个方面。人的有限性显露出来。“熵”概念的提出,更让人类面对这团热云显得无能为力。这里有两点是对秩序追求的反击:一,自我的混乱及有限性无力认识世界的秩序,即使认识的秩序也不过是自我膨胀的结果。二,这个世界本身就是无序的,毫无秩序可言。追求秩序无异于缘木求鱼。
这样一个思想背景,卡尔维诺应该是了然于心的。然而为何他还执着于晶体?他曾经说过:“在整个图案中宇宙变成一团热云,不可挽回地陷入熵的漩涡之中,但是在这个不可逆转的过程内部,却还存在一些有序的区域。”[1](P337)正是因为这些有序的区域激发他人文的情怀,试图与混乱、无意义对抗。他的不信教身份更加剧这种对抗的决绝。在他的世界里不存在宗教救赎,而在面对这样一个无意义的混乱世界唯一的出口就是决死地对抗。在《看不见的城市》中可汗试图从一些城市的规则中找到支撑整个帝国的规律,然而梦想终究落空。看来卡尔维诺了解对世界进行框限赋形最终会以失败告终,但他还是选择坚持。观察不能提供一种完全的知识,没有完美的模式,但他明显鼓励我们无论如何坚持观察。他尝试着对迷宫的描绘,对宇宙的构筑。就像休姆所说:“我们需要体系,是因为它是我们意识的本质,把他们从混乱中分类。”[2](P163)对卡尔维诺来说活着就意味着成为意识、思考,如果失去意识,那就等于死亡。如果我们懈怠,虚无混乱就不再仅仅是我们生活的背景。所以他试着与之抗争,以一种近乎悲剧的姿态。
四、自我与客体的和解
我们明显地感觉到卡尔维诺对理性的热衷,然而卡尔维诺的内心并不平静,在其晚期的作品《帕洛马尔》里,卡尔维诺有了新的思索。这个时期对秩序的追寻已经转化为如何解决自我与客体的矛盾上来。随着这个矛盾的升级,原有的带有乐观态度的对意义、秩序的追寻,开始转向对自我这个作为认识基点的怀疑。在《帕洛马尔》里,帕洛马尔先生自始至终都在通过这个自我试着去认知世界。他沿用哲学上的一些方法。第一步,他借用现象学方法,“回到事物本身”。在胡塞尔看来,我们实际上无法认识事物本身,我们的意见永远都是主观的,因此对待事物唯一正确的态度就是悬置判断。但应注意到,回到事物本身并不是指自然事物,而是指在意识中被意指的东西。胡塞尔说:“每一种远处给予的直观都是认识的合法源泉,在直观中原初地……给予我们东西,只应按如其被给予的那样,而且也只在它在此被给予的限度之内被理解。”[6](P84)突破经验科学的思维方式的成见回到我们的原始直观中来。然而这样一来一切事物都还原成了意识存在。这种极端的先验主义立场很难保证我们对事物和真理的客观性。卡尔维诺在帕洛马尔身上的实践同样以失败告终。第二步,以语言为媒介来认识世界。然而帕洛马尔在经过种种努力后,发现语言的限度。不是在认识世界,反而是认识的解体。完全依靠语言,依靠语言的描述跟解释,往往会破坏或限制原有的意义结构,甚至使我们跌入到无限解释,类似于德里达所说的分延之中(解读文本不过是顺着文本给定的踪迹暗示另一些踪迹的过程,即从这一文本到另一文本,然后再进入更大的文本群,而这一从踪迹到踪迹的过程永无止境)。在卡尔维诺看来,这个过程便是意义失落的过程,而促成这一结果的根本原因是人的有限性,以及由人所操纵的语言的有限性。通过前两个步骤,我们发现卡尔维诺对秩序以及赋形不再那么执着。他通过具体的个人去验证哲学上的思路,最终发现行不通。对晶体所代表的秩序与严谨出现动摇。人对世界的认识或赋形,不是解决问题的方式,反而是对物的打扰。赋形是思想对物的强暴。秩序是被设计出来的,是人把自己的陈述转嫁在世界自身的结构上。我们与世界相遇,既不需要去求索,也不需要去设计。所以在最后一步,卡尔维诺企图将自我从世界中分离出来。这里卡尔维诺已经完全扬弃主观主义立场,用理性给自然赋形,必定会走向主观的泥沼。他发现自我不再是认识世界的工具、通道,而成了与世界沟通的障碍。然而对自我的完全扬弃是不可能的。即便他在《帕洛马尔》中作了类似的想象性描述:“那么,把自我排除在外,又怎么进行观察呢?观察时使用的眼睛是谁的呢?一般认为,我仿佛站在窗口向外看的人,站在眼睛后面观察展开在眼前的广阔的世界,这么说有个开向世界的窗户了。窗户那边是世界,这边是什么呢?这边也是世界……既然窗户外边是世界,窗户里边也是世界,那么‘自我’就成了窗户,世界就是通过自我观察世界。世界为了观察它自身需要借助帕洛马尔先生的眼睛及其眼镜。”[1](P300)卡尔维诺充满诗意的语言描述去除自我的过程,可发现完全摈弃自我似乎无法实现。自我是我们存在的依据,你不能像去除一个物件一样将自我去除。问题仍在继续!卡尔维诺由之前的主体为世界赋形,到认识到主体的有限性,再到对主体存在的厌倦。那么该如何摆脱这一厌倦,这一困境?
海德格尔也似乎在着手解决这个困境。他认为我们面对大自然时,应该是以守护、仔细倾听的方式。在海德格尔看来,真理在苏格拉底之前的时代不是确定的,它指的是一个使存在者敞开的过程,这个过程中始终存在保留与显现的状态。存在本身是变异的,而非同一。然而后来的哲学家不愿意这种变异存在,他们需要确定的真理。比如柏拉图,他创造了理式,而被认为是真理的本质。知觉是一种看,这种看要能正确符合看的东西。真理不再是作为存在者本身的基本特征,而是正确的看,它因此成了人对事物的态度。真理变成了正确性,成了理智符合事物的真理观。所以对意义的追寻也许就是自身对世界粗暴的干预。所以我们需要的是倾听而不是追寻。有意思的是卡尔维诺在《帕洛马尔》中有着相似的描述:“无穷无尽的、哑口无言的事物之中,一种召唤、一种表示或一个眼色出现了,某种事物脱颖而出,要意味什么……意味什么呢?意味它自己。一种事物被其他事物盯着而感到满意时,说明它意味着它自己而不是别的什么,说明它周围的事物都以为着他们自己而不是别的什么。”[1](P301)此时,卡尔维诺想给万物以生命,使它们从人的意志的压制下,解放出来,获得自身张显和喘息的机会。同时这种呈现又因人的注意或者说观察而满意(也就是使自我呈现有了意义)。卡尔维诺在这里用了一个极为巧妙的词汇“穿过”,来界定人与物的关系。人仅仅穿过万物,不定义万物,同时人自身也需要万物的存在。卡尔维诺与卢克莱修作了最终的拥抱。卢克莱修最伟大之处就是将自己隐身于万物,他的诗歌如同万物自己的诗歌,而不是写出来的,这就是卢克莱修一劳永逸地向人类证明了的。
五、走向更高的层面
这个时候主体似乎与世界达成和解。主体与世界不是对立的,而是和谐的。从对主体的无限彰显——晶体模式,到承认主体的有限,再到主体融入世界之中。主体从一个明确的存在变得越来越稀薄,以前的问题似乎不成问题,没有了主体,何谈与世界对立,一切不过是世界之中而已。人来自于尘归之于尘。于是在卡尔维诺最后谈到了“死”。帕洛马尔在活着的时候试着去学会死亡。而承认“死”此时此刻就是可能,便已经是承认“此在”的最大的有限性。比人更原始的是人的此在的有限性。人之死,也许是与世界最大的和解。有趣的是卡尔维诺让学着死的帕洛马尔先生在这一刻真正死亡了。世界岿然不动,依然如故地进行着。
在这里,人的故事结束了,然而宇宙还存在着。卡尔维诺在接受采访中这样说道:“而追求和谐的欲望来自对内心挣扎的认知。不过偶然事件的和谐幻象是自欺欺人的,所以要到其他层面寻找。就这样我走向了宇宙。但是这个宇宙是不存在的,纵就科学角度而言。那个是无关个人意识,超越所有人类本位主义排他性,期望达到非拟人观点的一个境遇。在这个升空过程中,我既无惊惧失措的快感,也未曾冥思,反倒兴起一股对宇宙万物的使命感。我们以类原子或前银河系为比例的星系中的一环:我深信不疑的是,承前启后是我们行动和思想的责任。我希望有哪些片段组合,亦即我的作品,感受到是这个。”[7](P121)卡尔维诺最终以小说家的智慧去化解所有人世的问题。小说天马行空的模式给了卡尔维诺最大的自由,在这里他不必拘泥于任何先在条件,用想象摆脱所有人类本位主义。这也可以解释在卡尔维诺的小说里,人的存在越来越稀薄。同样这样的一个状态也许是卡尔维诺提出的小说“轻逸”特质的最终状态。摆脱人类的沉重感,穿上柏尔修斯的飞行鞋,以最大的自由升空。所有的矛盾在这个过程中不是化解了,而是其存在的前提消失了。卡尔维诺用小说思考,或者思考与小说共同流淌,离开任何一方,都是无法成立的。而他提出的“晶体模式”以及其背后的思索也为主张“非个人”化倾向的后现代小说打开一个更开阔与深沉的空间。
[1](意)卡尔维诺.卡尔维诺文集[M].吕同六,张洁,译.北京:译林出版社,2001.
[2]Kathryn Hume.Calvino’s Fictions:Cogito and Cosmos.Oxford:Oxford Press,1992.
[3](德)马丁·海德格尔.林中路[M].孙周兴,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4.
[4](英)维特根斯坦.论确定性[M].张金言,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
[5](美)威廉·巴雷特.非理性的人——存在主义哲学研究[M].杨兆明,艾平,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
[6](德)胡塞尔.纯粹现象学通论[M].李幼蒸,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2.
[7](意)卡尔维诺.巴黎隐士[M].倪安宇,译.台北:时报文化出版企业股份有限公司,1998.
【责任编辑:彭民权】
I106.4
A
1004-518X(2015)02-0098-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