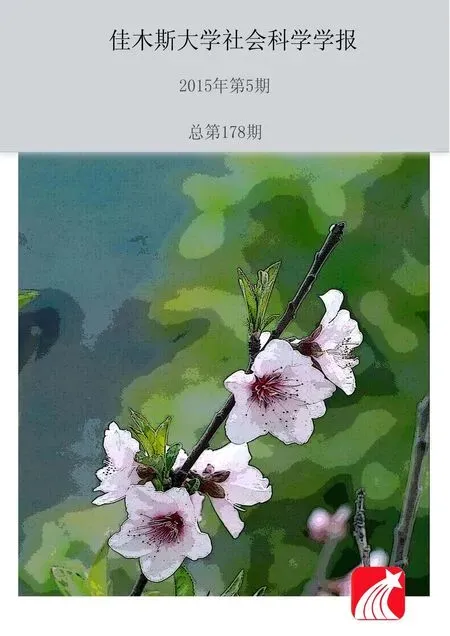王夫之诗学思想的基本原则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9882(2015) 05-0095-04
① [收稿日期]2015-08-12
[作者简介]陈雪雁(1980-),女,上海人,博士,同济大学哲学系博士后,研究方向:先秦哲学、古典诗学。
王夫之在诗学批评上常有创见,以往并未得到足够重视。现代学界的确较为重视其创见,但往往局限在文艺批评领域。从审美维度来审查船山的诗学思想,或不是那么贴合作者的初心。今天,如果推进对船山诗学的还原式理解,是否有进一步厘清作者的学术旨趣和学术关切的需要?纵观船山诸种诗学论著,我们可见他的一些基本诗学原则,这些原则贯穿了他所有的诗学解读。
一、《诗》诗关系论:诗《诗》一如,《诗》为诗本
船山既有《诗广传》、《诗经稗疏》这样的诗经学著作,也有《诗译》、《夕堂永日绪论》这样的诗话式著作,还有《古诗评选》、《唐诗评选》、《明诗评选》这样的诗歌选集与评论性作品,更有持续一生的诗歌创作。在船山这里,诗经学、诗学与诗歌创作是一气贯通的。
“仲淹之删,非圣人之删也,而何损于采风之旨邪?故汉、魏以还之比兴,可上通于《风》、《雅》;桧、曹而上之条理,可近译以三唐。元韵之机,兆在人心,流连泆宕,一出一入,均此情之哀乐,必永于言者也。故艺苑之士,不原本于《三百篇》之律度,则为刻木之桃李;释经之儒,不证合于汉、魏、唐、宋之正变,抑为株守之兔罝。”(《诗译》)
王通的删诗续经活动,虽然不能比拟孔子的六经编纂工作,但仍有可取之处。一方面,王氏的工作彰显了人心、世道与时事之变。唯有真正的基于当下情状,诗的风化和风刺才是对现实有效用的。另一方面,只要从作为诗歌本源的人心人情和作为诗歌的本旨的诗教风致来考察,所有后世之诗都可上通《诗经》。《诗经》是诗合法性的根源,也是诗歌评判的首要标准。
“四言之制,实维《诗》始。广引充志以穆耳者,《雅》之徒也。微动含情以送意者,《风》之徒也。……是知匪风匪雅,托无托焉。自汉以降,凡诸作者,神韵易穷,以辞补之。故引之而五,伸之而七,藏者不足,显者有余,亦势之自然,非有变也。”(《古诗评选·评谷风赠郑曼季》)
“呜呼,知古诗歌行近体之相为一贯者,大历以还七百余年,其人邈绝,何怪四始、六义之不日趋于陋也!”(《唐诗评选·评北山》)
“古今有异词而无异气。气之异者,为嚣,为凌,为荏苒,为脱绝,皆失其理者也。以是定诗,《三百篇》以来至于今日,一致而已。”(《古诗评选·评杂诗》)
诗体虽有变迁,但这种变迁并无损诗的“一致”和“一贯”,后人之变,乃时势所造,并无损诗旨。也因此,《诗》、诗之间可以上下通达,互相观照。在船山,不知《诗》者,亦无从知诗也。论《诗》则其对后世诗学的引导和影响自然地在论者的视域之内;论诗如不能追溯、推进到《诗》,则有盲词之嫌。他的《诗广传》论《诗》时常下及于汉、魏、唐、宋的诗人诗作,三种《诗评选》多从《诗》道和风雅之旨的接续与断裂臧否诗人诗作,《诗译》的每一条都在《诗》、诗之间流转,皆证也。这种《诗》与诗关系的一如绝不囿于被狭义化了的文学和美学之中,这也是船山诗学的特质之一。虽然诗旨未发生根本变化,皆以风、雅为宗,但仍有古今、正变的问题。这与船山对诗的根本界定有关,如果说知道《诗》、诗一贯是论诗之本的话,理解《诗》、诗之变正是诗以用世的方式。他说:“《易》有变,《春秋》有时,《诗》有际。善言《诗》者,言其际也。寒暑之际,风以候之。治乱之际,诗以占之。极寒且燠、而暄风相迎,盛暑且清、而肃风相报。迎之也必以几,报之也必以反。知几知反,可与观化矣。”(《诗广传·大雅》)“《诗》有际”展现的是诗和世界的关系,“有际”是以正变论《诗》诗之变的内在依据。诗从细微中见精神,及时呈露时变和世变的端倪和征兆,变皆“兆在人心”,“诗者象其心而已矣”。(《诗广传·周颂》)由人心之几而知人世之治乱盛衰;观诗知人心、时世之变,从而可正人心、拨世乱。人世有变,诗自然也因世变而变,如此,诗承《诗经》之道应世事、人心而生,由诗而知治乱、风雅之盛衰与诗道之正变并以之用世。“物必有所始,知始则知化”(《唐诗评选·评赋得浮桥》)《诗》为诗本,诗是《诗》化,船山诗学理解的出发点便是《诗》诗之间的变与不变。变者是时与际,一贯者是世变和人心的相接及其所成就的诗之政教。他常用“诗亡”来说诗,皆就诗对人心和政教的败坏而言。《诗》有衰亡之虞,因其可能背离人心的自然生发与人情的本然呈露。诗有衰亡之危,因其可能违背《诗经》所指引的诗情和诗教之路。《诗》与诗的一贯性统合在诗对人心人情的诉求上。
二、诗、经、乐的关系定位
首先,诗属乐语,诗教即乐教。在《夕堂永日绪论序》中,他先以“涵泳淫泆,引性情以入微”为乐教之用,又言“乐语孤传为《诗》。诗抑不足以尽乐德之形容,又旁出而为经义。经义虽无音律,而比次成章,才以舒,情以导,亦所谓言之不足而长言之,则固乐语之流也。二者一以心之元声为至。……明于乐者,可以论诗,可以论经义矣。”其中,乐教分乐语和乐德两部分,乐语为形,乐德为本;乐语外显者,乐德内蕴,言乐语则乐德自在其中。乐教之传有二,一为诗,二为经义。当诗不能完全成就乐德之教时,诗旁出而为经义,则经义天然渊源于诗教之用。诗与经义皆兼有乐语和乐德的规定性,相较而言,前者更重乐语之形,后者重乐德之显。“钩略点缀以达微言,上也。其次则疏通条达,使立言之旨晓然易见,俾学者有所从入。又其次则搜索幽隐,启人思致,或旁辑古今,用征定理。三者之外,无经义矣。”(《夕堂永日绪论》)经义或阐发微言,或发明经之大旨或启思明理,简言之,经义意在显教。经义既是诗乐之教的流行,又是经典的发用,这看似有些抵牾的双重规定在船山这里并不矛盾。“诗以道性情,道性之情也。性中尽有天德、王道、事功、节义、礼乐、文章,却分派与《易》、《书》、《礼》、《春秋》去,彼不能代《诗》而言性之情,《诗》亦不能代彼也。” [1](p5110)经典为尽性之学,且各有其尽性的路径。经义虽是诸经之学的开显,强调的却是经典与人心的契合,是人心之发,且“韵以之谐,度以之雅,微以之发,远以之致”,其恰是以乐教“涵泳淫泆,引性情以入微”的方式显经的。将经义与诗合而论之,船山注重的是:诗,作为乐语乐教及经典尽性之学之一端,有其独特由情入性的进路。船山在论诗时,始终有经义、乐教、经典作为思想参照的背景。诗教乃是凸显了言志之端、弱化了声、律、永之维的乐教。然而弱化并不是取消,也因此,他强调乐语、长言、声情、结构等形式化、方法性之物。同时,教显于形式之中,他也从未曾忽略作为形式、方法之本的政教意蕴。
从六经之分出发,船山反对“诗史”说,他有一个理由:“夫诗之不可以史为,若口与目之不相为代也,久矣。”“司马、班氏,史笔也;韩、欧序记,杂文也;皆与经义不相涉。经义竖两义以引申经文,发其立言之旨,岂容以史与序记法搀入?……要之,文章必有体。体者,自体也。”(《夕堂永日绪论》)史无涉乎作为诗教之显的经义,自然也无涉于诗,这种无涉根于六经之体、六经之义与六经之用的分别。如此,诗不能用史笔,以史的方式要求诗,是违背诗乐之语和诗乐之教的。船山认为以“诗史”评判诗歌,正是诗不成诗并失其外显之形与内蕴之教的表现,正因他始终坚持从经典和乐教的角度看诗的形教声情。
三、诗为政为教,以政教为旨
诗、乐、六经皆为“世教”之方,上文讲到乐语和乐教的关系,语以显教是船山的根本立场,他说:“长言永叹,以写缠绵悱恻之情,诗本教也”,“骀宕人性情,以引名教之乐者,风雅源流,于斯不昧矣”,(《夕堂永日绪论》)“诗之教导人于清贞而蠲其顽鄙”。(《诗广传》),以诗抒情,从而使人能贞其情,是诗为教的方式。“心术坏,世教陵夷矣。”(《夕堂永日绪论》)人心与世间政教相互作用,政教的败坏源自人心的败坏,人心的清明自然会导向政教的清明。诗从治情入手,正人之心,也是诗为政的方式。
但我们看一下船山对杜甫的批评:
子山则情较深,才较大,晚岁经历变故,感激发越,遂弃偷弱之习,变为汗漫之章,偶尔狂吟,抒其悲愤,初不自立一宗,以开凉法。乃无端为子美所推,题曰“清新”,曰“健笔纵横”……凡杜之所为趋新而僻,尚健而野,过清而寒,务纵横而莽者,皆在此出;至于“只是走踆踆”、“朱门酒肉臭”、“老大清晨梳白头”、“贤者是兄愚者弟”,一切枯管败荻之音,公然为政于骚坛,而诗亡尽矣。清新已甚伤古雅,犹其轻者也。健之为病,“壮于頄”,作色于父,无所不至。故闻温柔之为诗教,未闻其以健也。健笔者,酷吏以之成爰书而杀人。艺苑有健讼之言,不足为人心忧乎? [2](p4826)
此处表面看来是在讨论诗的写作手法即所谓的“健笔”问题,然船山将“健笔”与“温柔”相对言,以“之为诗教”作结,且该段中屡言“汗漫”、“不可以诗论”、“诗亡尽”、“澌灭尽”、“一皆诗”等等,如此,他的关切点最终当落在诗之为诗和诗之为教上。健笔是对虞子山因个人际遇而有的“感激发越”“抒其悲愤”之作的评价。一般而言,健笔一指直接揭露现实时事,一指酣畅淋漓的直抒悲愤。他批评中举例的诗句,多被目为史笔,或誉为有诗史之风者。他将健笔解作健讼,即官吏文书写作的方式。他以《春秋》为“史氏之言”和“圣人之刑书”,则《春秋》既是史学之开端,也是刑名之初起,言刑则史在其中。他称唐宋诗人为“法吏”、诗作为“刑名体”皆是以此为健笔与诗史说的流弊。在这段引文下,船山还论述了上文谈及的诗与其他经典和文体的体用之异。以上三点,皆可证健笔与诗史的渊源,求为诗史则必为健笔。求为健笔则以史笔和讼词来正人,此非诗教作用于人心的方式。情有淫贞,此激越之情“作色于父”显然是淫情,故不得温柔敦厚之教,人心可忧。
“周至吉甫而《雅》亡,汉讫曹植而诗亡,唐之中叶,前有杜、后有韩、而和平温厚之旨亡。衰而骄,骄而衰不可振。衰中于身,其身不令;衰中于国,其国不延。” [1](p143)诗为尽情尽性之学,性情不得其正,则身不能正,身不正则政不正,政衰则国亡。“周于利而健于讼,虽免于亡,其能国乎?”淫情健笔,国虽存而不国,诗虽在而犹亡。诗亡指诗不能呈现、通达与匡正人情,这同时意味诗教和诗政的不可能。
萧度《古近体诗评选总序》云“考其所评选诗钞,与尼山自卫返鲁正乐删诗之意,息息相通。”刘人熙《古诗评选序》言“于孔子删诗之旨,往往有冥契也。”船山诗评的序言皆将其评诗之行与孔子删诗相比照。船山在《诗译》首条言“王通续六经”事且给予了肯定评价,则他本人未必没有这种续经的自觉意识。孔子删《诗》作《春秋》诸种经典编纂之行意在通过经典之教而正政,船山也有明确的正教而正政的意识。他有非常鲜明的以诗为教和以诗为政的意识。例如,他很注重从政治分期和诗学思潮角度论诗之好坏,坏的诗是诗不宗经的,且使政治败坏、诗教亡故。
四、诗为性情之学
上面所有论述都落实到人心和人情上,这也是《诗经》区别于其它经典的特质。故而船山屡言“诗言志”和“诗达情”。船山早期的《四书引义》多以心有定向言志,志指向的是人心之正。《诗广传》有志、意与情、欲之辨,既重情志之别,又有情志之通。《古诗评选·谷风赠郑曼季》中他以情论国风、以志言雅同样注重二者之异同。晚年在《尚书引义》中他又以“贞淫”论志,而贞淫是《诗广传》论情的重要指标,则有以情言志的倾向,重情、志的一贯与融合。在船山的诗论中,诗达情显然是使用更为广泛、更为基础的一个提法。
诗达情,意味着诗要指向和成就的是一个诸情可达、人我可通、达情尽性的世界。首先,诗是“广通诸情”的。喜怒哀乐、兴观群怨诸情是相通的,故而可以哀景写乐,以乐景写哀,有可兴则必于所兴而可观,有可怨则于可怨处可群。诸情的通达也使得诗可由“微中”而至“深远广大”。其次,诗是一个我和人、君子与小人可以感情相互通达的所在。船山言:
君子与君子言,情无嫌于相示也。君子与小人言,非情而无以感之也。小人与君子言,不能自匿其情者也。将欲与之言,因其情而尽之,不得其情、不可尽也。将欲与之言,匡其情而正之,苟非其情、非所匡也。言之而欲其听,不以其情,嫌于不相知而置之也。言之而为可听,不自以其情、彼将谓我之有别情而相媢也。故曰“诗达情”。达人之情,必先自达其情,与之为相知,……不自匿而已矣。 [3](p43)
我们如何使人知己?我们如何知人?我们如何相知?我们如何进入共同生活?表面上这种人与人的相接、相交、相知、相感成就于人的视听言动,然而视听言动之事是人的情动和人与人之间情接的外在表现,故而我们因情而有之间的通达与感动。诗达情,正是以诗来生成一个向自我和他者开放的世界。在这个诗意世界中,情感得以以其本然方式呈现;在这种呈现中,真诚的情感相互触动,真实的自我相互抵达,通过感情的感染、匡正与治理来安顿人心和人得以实现。我们将自己之情真实地展现于人前,大白于天下,从而人与人之间因情而相感、相匡。不以其情,则人不能相知相通。
夫上不知下,下怨其上;下不知上,上怒其下。怒以报怨,怨以益怒,始于不相知,而上下之交绝矣。夫诗以言情也,胥天下之情于怨怒之中,而流不可反矣,奚其情哉!且唯其相知也,是以虽怨怒而当其情实。如其不相知也,则怨不知所怨,怒不知所怒,无已而被之以恶名。 [3](p34)
对相知的强调是基于诗情“可群”即诗情之于共同体的建构的意义,在王夫之的“四情”说中,他特别强调“平情说出,群怨皆互”,即在情的自然呈现中,群与怨同时抵达。不能达成群的怨自然不是合乎情理之怨。基于不相知从而不能群的怨,或有“诬”之嫌,在《卫风》的解读中,他就格外注意“诬上行私不可止”与卫风之亡和卫国之亡的问题。
诗所要达之情,是因实情可怨而怨,当怒而怒之情,而非因不相知而产生的怨怒之情。这种怨怒之情的表达,恰使天下之情旁流而不能纳入正轨,因此会导致诗情、人情和政教生活的败坏。因相知而相恶,因相恶而相怨怒是诗可达之情。由于不相知产生而彼此相恶,相恶而又怨怒加之,则不是诗想要抵达的情感。无论是相知还是不相知,怨怒的表达仍是有限度和界限的。他说:
“恶、怒,不相为用者也。怒之、又从而恶之,是终无释也。苟恶之又以怒加之,将不择其所可胜矣。……又何足以刺人?赵壹之褊,息夫躬之忿,孟郊张藉之傲率,王廷陈丰坊之狂讦,学《诗》不择而取《相鼠》者乎?” [3](p28)
恶其事自然有怨、怒之情的发生,但在诗的表达中,不能采用恶、怒叠加的方式,否则也会导致情的旁流和泛滥。怨怒的表达还涉及到“诅”和“讦”的问题。使人知其怨怒之情,是使人相知的方式,同时也是讽谏他人的方式。船山言:
“可以群者,非狎笑也。可以怨者,非诅咒也。”(《古诗评选·评中山孺子妾歌》)
长庆人徒用谩骂,不但诗教无存,且使生当大中后直不敢作一字。(同上,评《和谢豫章从宋公戏马台送孔令谢病》)
至理不讦,讦即不成诗矣。(《明诗评选·武夷曲次晦庵棹歌》)
诅咒、攻讦、谩骂不是诗相知、相群、动人心的方式。为讼为诅,无法达成情的相互通达和人的相互感化。情能相知,诗才能以情教人。
再次,达情是为了尽性。王夫之首先明确了性情的相属关系。“诗以道性情,道性之情也。性中尽有天德、王道、事功、节义、礼乐、文章,却分派与《易》、《书》、《礼》、《春秋》去,彼不能代《诗》而言性之情,《诗》亦不能代彼也。”(《明诗评选》)情乃性之一维,诗安顿的便是性中之情。与一般理学家的性情论不同,船山明确提出“我情自性”,“性之情者,性所有也……流于情而犹性也。尽其性,行乎情而贞,以性其情也。”(《诗广传》),情属于性,“行乎情而贞”,人能自贞其情,正是情其情或曰尽情的方式,而尽情又是“性其情”进而“尽性”的路径。固然,他说君子尽性,但同时他提出一个关于尽性的境界划分。“故圣人尽心,而君子尽情。心统性情,而性为情节。自非圣人,不求尽于性且或忧其荡,而况其尽情乎?”(《诗广传》)唯圣人为能尽心即同时尽性与尽情,即便是圣人,尽性也是不易的。而君子以性其情作为尽性的方式行走在尽情之路上。然而,他又说:“何言乎情为至?至者,非夫人之所易至也。圣人能即其情、肇天下之礼而不荡……情,非圣人弗能调以中和者也。”,“圣人达情以生文,君子修文以函情”。对圣人来说,尽情是境界;对君子来说,尽情是功夫,诗则是君子尽情及性的路径。“可性可情,乃三百篇之妙用。盖唯抒情在己,弗待于物,发思则虽在淫情,亦如正志,物自分而己自合也。呜呼,哭死而哀,非为生者。圣化之通于凡心,不在斯乎?”(《古诗评选》)诗实质上是通过可情的方式可性的。性情还有上下隐显问题的问题,“情受于性,性其藏也,乃迨其为情、而情亦自为藏矣。藏者必性生,而情乃生欲,故情上受性,下授欲。受有所依,授有所放”,性情有上下授受关系,其中,性隐而情显,由情而性显,达情可尽性。情本身也是自藏而隐的,故而有“文以白情”“修文函情”之说,君子以诗的方式显情于天下,同时治天下之情。
“诗以道情,道之为路也。诗之所至,情无不至;情之所至,诗以之至;一遵路委蛇,一拔木通道也。”(《古诗评选》)
诗给情以道路、空间、方向,因情而生,缘情而止。但此情应是自白于天下之贞情。诗情论又奠基于诗之为诗、诗之为经、诗之为教、诗之为政等之上,并且是成就后者的内在动力。船山通过诗情论想要抵达的是性命之学和政教之道。
从上述四原则出发反观船山的诗学思想,则很难单纯的以审美、抒情、文学的字眼来该遍其创见,这些原则其实构成其所有理论的内核,也因此,许多学人在以审美意识论船山之后,或多或少都要指明船山有过度强调诗教的立场。但当诗教是最为根本的坚守时,我们如何可以剥落之而言其他?船山诗学当然可归之于文学,因为他有很清晰的文学自觉,如他常将“诗人”“艺苑之人”挂在嘴边,并以此作为诗当何为和诗人当何为的出发点。但不能否认其文学源于经学,并始终深深植根于经学,其诗学在很大程度上是其《诗》经学式展开、延展、发用、流行。船山诗学无疑也是抒情诗学,但抒情并非仅仅限于审美性的情感抒发或宣泄,恰恰是要有度有节,有所正有所止的白情于天下,而非囿于私人的意欲。这种达情是注重情感的感化通达之意并进而达成政教之境的。而且,诗达情不仅要导向人的情感之正,并由之而可尽性知命,可以说船山的抒情诗学也必然是尽性之学。船山诗学当然也是审美诗学,但这种审美的发生源于诗教根源处的乐语形式之美和乐教成就性情之美。王夫之作为明末清初最具思想深度的大思想家,其诗学思想也极为深邃与精妙,若限于现代学术建构,可能和其思想的精义失之交臂。
——探《船山之尊生尊气与尊情才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