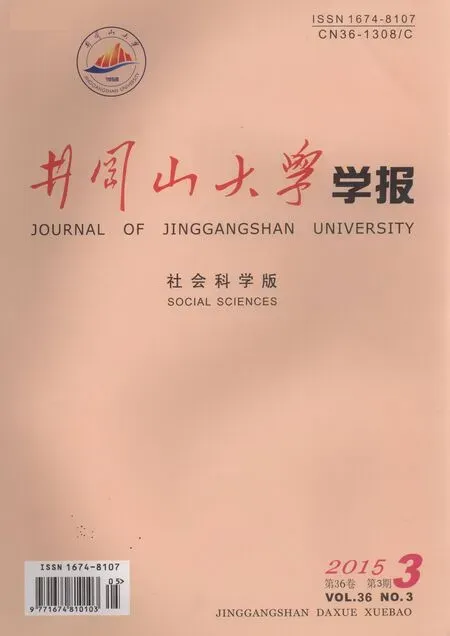论新世纪江西女性作家小说的地域特征
刘云兰
(井冈山大学人文学院,江西 吉安 343009)
文学的地域性是文学与生俱来的内在品质。何为文学的地域性?“在通常的理解中,地域性是一个空间性的概念,包含了一个地方的地理、文化、民俗等。然而对作家而言,地域性远远超过了空间范畴,空间被无限拉伸和延长,时间与历史充盈了这个空间,使得这种包容了无限时空的地域蕴藉出巨大的能量,展现出某种决定性的意义。 ”[1](P72)因此,文学的地域性不单纯指自然地理区域上的分布状态,也包括在历史的进程中形成的人的多种精神因素,是“时空合一与内外兼顾”的多维形态,是某一地域独特的自然环境、生活习俗、言语传承、风土人情、文化心理、神韵风采、心灵默契等因素在文学作品中的综合体现,它不仅包括区域范围这一外在意义层,更重要的内涵是指某一人类群体在一定区域内长期生存及其发展演变过程中所形成的具有文化特质的时空环境。
江西自古就是文风鼎盛之地,拥有丰富的历史文化资源,诸如以南昌的豫章文化、九江的码头文化、抚州的临川文化、景德镇的陶瓷文化、吉安的庐陵文化、赣南的客家文化、龙虎山的道教文化、苏区的红色文化等等。这些文化滋养了江西作家,成为了他们追求文化共同体的资源。新世纪江西女性作家立足江西历史,努力挖掘江西文化资源以讴歌江西人民的坚韧精神为已任,创作出一批具有浓郁地域特色的作品。她们的作品在自然地理空间的构造、富有地域特征的人物形象塑造以及人文环境的建构方面呈现出强烈的地域特色、情感认同与文化诉求,从而显现出独特的审美风格和艺术价值。
一、自然地理空间:具有原生态美的江西山水风光
自然地理环境是地域文学区别于其它文学的首要标识。法国的丹纳在《艺术哲学》中明确提出影响文学的三大要素是“种族、时代、环境”。清末民初的刘师培在《南北文学不同论》中,从语言声音的南北差异论及艺术风格的南北地域特性,认为:“大抵北方之地,土厚水深,民生其间,多尚实际。南方之地,水势汪洋,民生其际,多尚虚无。民尚实际,帮所作之文,不外记事、析理二端。民尚虚无,帮所之文,或为言志,抒情之体。”[2](P82)在他看来,自然环境对地域文学的影响起着决定性的作用。的确,文学的地域性,首先以特定地域特点的自然地理环境为标识,它离不开对那些具有地域特色的山川河流、季节气候和特殊的地貌特征等自然环境因素构成的特定空间的描写。
新世纪江西女作家们将具有江西地域特征的山山水水直接融入作品中,使之成为人物生活环境的写照。她们笔下的自然地理环境几乎都有现实生活的原型,南昌、赣州、吉安、万寿宫、青云谱、桃花巷、松柏巷、系马桩、赣江、三清山、青原山、明月山等江西地名多次在作品中出现。唱山歌的姑娘、潺潺的小溪、韵味十足的江西采茶戏、青翠的毛竹、柔美的油茶树、古老的樟树、赣南的围屋、照明的松光、可口的毛栗子、铺着青石条的巷子……,这些具有浓郁江西特色的人物、景物成为小说的主要描写对象和人物活动的背景。吉安籍女作家安然的作品大多以吉安这座城市为背景来安排故事,在《少女姚窕》中有对吉安十字街的描写。在《陀螺的舞蹈》中有对原吉安师专的介绍:师专远离市区,后升为师院。师专与市区分别有 “山上”、“山下”之称。无独有偶,那些生活在吉安市区的人对原“吉安师专”的称呼也是如此。而《水月亮》中的竹城,就是吉安城的写照。例如,小说中写道:“沿江路上有一棵三百多年的大榕树,旁边还有德克士、好街坊、画院、居民住宅区等”[3](P21)。 这些描写与现实相吻合,读者可凭此画出一幅地图来吉安进行探访。《水月亮》中还提到了南昌幼儿园发生的事情:“衣蓝说她们中秋发了三盒乔家栅月饼,一百块钱。月饼一点也不好吃,钱又太少了。衣蓝接着说南昌一家幼儿园发生大火事故后,她整天上班都提心吊胆,不敢不小心。”这段文字提及“南昌”以及所在地曾经发生的重大火灾事故,与现实一致。此外,彭学军在《北宋浮桥》中写道:“赣江上有一座浮桥,叫北宋浮桥。……既是浮桥就没有桥墩,一溜大木船并排串着,从江的这边到那边,然后铺上木板,就成了桥。由于年代的久远,木船的油漆早已剥落,露出黑褐色的木纹,上面的铺板也腐烂、断裂了好些,有的地方缝隙宽得能掉下孩子的一条腿。但孩子并不害怕,过桥时还有意把桥面跺得嗵嗵响,弄得桥一悠一悠的,很好玩。 ”[4](P110)这正是赣州贡江上古浮桥的写照。当然,进入文学作品中的自然环境已不是纯粹的外在之物,更多的是承载了地域人文精神、文化认同之物,它们已成为地域文学特有的甚至为恒定的环境标识。
俗话说: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一个地域里的人有大致相近的饮食习惯。新世纪以来的江西女性作家善于将本区域内人们习以为常的食物写进作品中,使作品充满了赣地风情。在她们的小说中,多次出现“枣糕”、“南瓜子”、“乔家栅的月饼”、“江西炒粉”、“霉菜扣肉”等江西人常食之物。阿袁在《蝴蝶的战争》中写陈小摇买了藜蒿,放在水房里一根一根洗,再在走廊里就着腊肉炒。“藜蒿”是鄱阳湖里的一种草,“藜蒿炒腊肉”是南昌的特色菜。阿袁还在《姹紫嫣红》中写了“荠菜虾仁”、“肉末雪里蕻”等菜肴。在《女人的幸福》中写用冬笋、火腿、菌菇一起煨汤的江西人冬季常用煮汤方法。饮食是人类最本能的需求,一个地方的饮食是当地文化代代传承的结晶,最具地域色彩。文学作品中对饮食的描写更多地保留了生活原貌,通过这些生生不息地流传的饮食等元素,可折射出当地的生存环境、经济状态、思想文化、民俗心理、文化特征等,从而成为考察地域文化的活化石。
新世纪江西女性作家无论对自然环境的设定还是对饮食等方面的描写都较少进行加工改造,而是以写实的形式进行再现,追求人物活动空间环境的原生态美,最大限度地为作品中的人物生存活动空间环境保持原生态状貌,为人物创设了特有的人际生态圈和人文气场。因而,她们的作品中存留了环境中最具地域特色的东西,体现了中国文化的“天人合一”思维方式和价值哲学,饱含着较高的美学理想。中国文化和文学自古代以来就强调取法自然,与自然相融相生。新世纪江西女性作家所追求的也是人与自然的“相安”、“相谐”,注重表现中国文学的自然性特征。生态美的审美理想在经济飞速发展的时代显得尤为重要,正如生态文学家贝特在《大地之歌》里指出的,生态作品的目的是为了展现理想的自然生存,状态,为我们提供“想象的自然状态,想象中的理想的生态系统;阅读它们,陶醉于它们的境界,我们便可以开始想象另一种与我们现状不同的栖居于大地方式”。[5](P250-251)它是解决“全球一体化”和“人的物化”弊端的一剂良方。
二、人物形象塑造:地地道道的赣味人情事故
弗罗斯特曾说:“人的个性的一半是地域性。”[6]地域文学中所塑造的人物形象都带有地域色彩与烙印,他们是当地民众的形象代言人,是地域文化承载和体现的又一实体与符号,也是人们阅读文学、认知地域文化的又一标识。由于江西境内的地形地貌为:“六山一水二分田,一分道路和庄园。 ”[7](P9)这就造成了江西长期以来都以农业为主要的社会生产方式,养成了江西人勤奋务实、淳朴善良的性格特征。另外,由于历史上江西是儒学鼎盛之地,传统的儒家思想在人们头脑中根深蒂固。因此,江西人大多安土重业,注重节俭,为人恭谨,崇尚礼教、忠义节烈、坚韧执着。但又因为山多水远,与外界缺少交流,在尊崇儒雅之风的同时也有一点拘谨和呆板。早在南宋时,朱熹与陆九渊在争辩中就曾多次谈到“江西之学”与江西人性格特点的内在关联性,“江西山水秀拔,生出人来便要硬做”[8]、“江西人好拗,人说臭他须要说香。 ”[8]其说法虽有所偏颇,但也道出了江西人一些本质性的特征。这种淳朴、善良、忠贞、坚韧而又有些执拗、狭隘的人物性格经过历史的传承与现实的嬗变积淀下来,得到大多数江西人认同,成为江西作家笔下人物的性格基础。
进入新世纪以来,面对市场大潮的冲击和理论界各种思潮的困扰,江西女性作家尽管作品内容不一,风格各异,但她们有着相似的审美趣味、价值观念、思想情感等,她们的情感认同一致。在物欲横流的时代,她们不媚时,不沉沦,不玩感官,不单纯写两性爱欲,而是坚守传统,赞美美好的人性与人情,将写作视角伸向社会,书写普通人、边缘人尤其是底层女性的生存境况,表现她们在物欲横流社会中坚持自我、不畏世俗、追求精神高洁的思想境界。例如安然《水月亮》中的布裙子,辞去了大上海令人羡慕的工作,回到家乡和好友开了一家手磨咖啡吧。在咖啡吧中,不迁就客人的爱好,宁愿得罪客人也要坚守不准打麻将和不卖茶水的经营原则。她不顾世俗压力与中年男子麻零相爱,但当她得知麻零不能原谅出轨妻子的真心悔过时,义无反顾地离开了他,即使自己遍体鳞伤也决不回头。布裙子的性格柔中带刚,爱憎分明,心地纯净。布裙子身上这种执拗、清高、自我的性格得到许多江西女性作家的认同。在陈蔚文的小说《向往高尚生活》中,苏玉贤虽然是一名酒厂女工,但在婚后的十多年里一直向往高尚的精神生活。她曾以个体户的身份组织过女性沙龙,讨论文学与人生的话题。她置家庭和婚姻而不顾,为了出版一本诗集自费去大学中文系做旁听生,目的就是为了把它寄给她中学时曾暗恋过但现已结婚的语文老师。这种精神爱恋,是一种明知无望而希望的执着,令人心酸,但纯净美丽。王晓莉笔下的林方(《和“史努比”相爱》)、何青蓬(《渡海中》)和倪思红(《倪思红》)共同的特征是柔顺而坚韧。她们面对无常的生活困境,是孤独无援的弱者,无力反抗,只能屈从命运的安排,但她们不麻木不沉沦,内心敏感而细腻,在庸常的生活中始终保持着自己的尊严。
柔弱只是女性性格的一面,许多女性为了自己心中的信念和实现自己的精神追求,面对苦难她们不屈从,坚贞执着,体现出刚毅果敢的性格另一面。胡辛《怀念瓷香》中用“瓷”来象征女性坚贞自尊的性格。经过千锤百炼煅烧而成的瓷,精美高贵,宁可粉身碎骨也不变质。小说中的几位女性有着瓷一样的秉性,高贵美丽,她们执着于对纯洁爱情的追求,敢于向不合理的社会抗争,即使碎成一片片,也依然故我,永远保持一颗纯真之心,以不卑不亢态度对待生活中的一切。在温燕霞的长篇小说《红翻天》中,江采萍、刘观音、周春霞、马丽等执着于自己对革命信念的追求,她们与恶劣的社会环境和自然环境进行不屈不挠地抗争。面对敌人对苏区惨无人道的“清剿”,她们机智勇敢地与敌人周旋,化解了一次次的危机,她们中也有人逃跑过,但坚定的信念支撑着她们走下去,有的即使身陷囹圄也坚贞不屈,她们在战争的熔炉中已锻造成了坚定的革命战士。“这些红土地上的女性,她们的性格中既有沉静和抗争的忧伤,也有坚贞和决绝的纯粹,更有厚道与自然的淳朴,性格内核的复杂性与多元性赋予了她们独有的魅力,她们以多姿的气质与醇美的品格凸显了江西地域女性独具的地缘精神。 ”[9](P76)
文艺作品中对地缘精神的认同也是人类的共性,正如美国当代著名学者本尼迪克·安德森在《想象的共同体》中指出的:“‘共同体的追寻’——寻找认同与故乡——是‘人类的境况’本然的一部分”[10](P19)在安德森看来,任何民族都是一种想象的共同体,有着集体的认同感;民族认同包括自我的认同与“他者”的认同;“民族”的想象和出生地、肤色等一样个人无法选择,它能在人们心中召唤出一种强烈的历史宿命感,使人们在“民族”的形象之中感受到一种真正无私的大我与群体生命存在。没有群体归属感的艺术作品犹如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失去艺术的生命力。
三、文化地域建构:醇厚的赣文化底蕴
人文环境,主要指由饮食、服饰、建筑等及以语言等为载体的精神产品构成的、与人的精神意志关系更密切的环境。从宏观方面来看,体现为一个地区的文化内涵与集体无意识心理;从微观角度来看,主要体现为某些社会生活现象、生活场景和民俗世相,它们从不同的层面、不同的角度凝聚、折射了当地民众特殊的文化心理和文化现象,成为当地民众精神文化特征的表征。
江西拥有丰富的历史文化资源,从历史的维度上来看,儒家文化占主导地位,道家、佛家文化与儒家思想共存。儒家思想深深地影响了江西人,赣地先贤多为正统的儒者,在人生追求上,崇仰并实践“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儒学信条,积极入世,匡时救弊,刚健有为,奋斗不息;在品格情操上,坚守正直、清廉的风范。虽然儒家思想为正统之道,但道教、佛教精神则更多地成为民众心灵的一种超现实的寄托。江西历史上徐孺子、苏云卿、张位、朱耷等人的归隐意识和行为所积淀下来的隐文化,深含的是一种远离喧嚣世界,坚守个人独立精神追求的意识和淡泊心态,表现出一种对现实俗世的逃离,这种思想对江西普通民众的处世方式与价值观念的形成影响较深。例如,安然小说《水月亮》中隐含着若有若无的佛意与禅味,作品中多处出现以佛家寺庙作为背景环境:河洲上的尼姑庵、林小羊栖身的山门圣庙、明月山的净居寺、沙滩上被遗留的《金刚经》等物件,使作品蒙上了一层虚无和宿命的纱雾。小说的情节设置也与宗教密切关联:林小羊婚姻受挫后选择剃度出家,麻零遭到妻子的背叛后开始研究禅,而他与布裙相知相爱也是由禅入手的。此外,陈蔚文的小说《惊蛰》、《流光》、《悬念》中也多处涉及到来世超生得好报等佛教思想和宗教对人精神的操纵作用的问题思考。《惊蛰》中的开芝得知丈夫有外遇后不找家人而是找居士小安,小安劝她念佛,她每天虔诚地烧香念《般若波罗蜜多心经》,还想通过让丈夫廖志看《了凡四训》受到感召重新变好。“纹了眉毛眼线的师兄告诉她,有个修行法可以改善夫妻不睦。每天在佛前顶礼叩头一百零八个,若无佛堂,也可面向配偶所在方向,边磕头,边忏悔自己过去对配偶曾经不忠的罪业——即使你今世对配偶并未犯过不忠的过错,根据因果原则,你也应该这么去做,去修!因为有因才有果,无因必无果!今世他(她)对你不好,必然是过去你对他(她)不好。今世他(她)对你不忠,必然是过去你对他(她)不忠! ”[11](P13)宗教成为人们解决生活困境的一剂良方。佛家、道家的许多价值观念成为了普通民众表达自身文化诉求、建构自身文化空间的重要依据。
文化的积淀可以说是地域文学的一种隐性存在,而一定的民间习俗及某些社会现象、生活场景则是识别地域元素的显性标识。正如美国学者本尼迪克特所言:“‘特定的习俗、风俗和思想方式’,就是一种‘文化模式’,它对人的‘生活惯性与精神意识’的‘塑造力’极大,甚至令人无可逃脱。 ”[12](P5)文化在漫长的历史延续和发展过程中,逐渐转化为当地原住民的集体无意识的深层心理,它通过现实生活中具体的生命个体的语言、行为活动、思维方式等体现出来。因此,地域风貌、习俗信仰、人情世相等是判断作品地域特征的重要元素。在新世纪的江西女作家中,温燕霞的小说大多以赣南为场景,以客家人的生活为主要题材,客家妇女的信仰、禁忌、操守、服饰、饮食、爱情等在小说中得以充分体现,从而使她的小说有着沉甸甸的文化内涵,呈现出浓郁的地方色彩。在小说《我的1968》中,写到客家女出嫁的哭嫁习俗:新娘子出嫁时一定要大哭一场并在伴娘的拖拽下才能出门(以示不舍娘家之意)。出门时喜娘要将掺杂了枣子、豆子、花生的白米撒在新娘子前行的路上,一边撒,一边赞(表达“早生贵子、家庭和睦”的祝愿)。由于这些民俗既负载着对人物行为动作、心理活动的描写,同时又传递着特定地域的风俗习惯,共同组成了小说的文化背景,使小说焕发出一种独特的人文精神光彩。胡辛在创作时也非常重视作品人文环境的地域特征,在小说 《怀念瓷香》中,胡辛从文化人类学的角度出发,以艺术的方式为我们呈现了一部瓷都的历史。孝女跳窑出祭红的传说、高岭婆婆的传说、青花仙女的传说、郑贵妃与青龙缸、张太后与蟋蟀瓷罐、徐皇后与永乐瓷的故事在作者笔下娓娓道来,所传达的一部陶瓷史就是一部女性的历史,女性同样创造着历史的文化诉求。
文学是人学,而生活在特定历史时间和空间中的人均受到某个特定历史环境和地域文化的浸染。因此,文学作品总是避免不了要承载地域文化信息,作家在创作中有意或无意地书写着某一地域所特有的文化,表现其地域审美模式的某些本质特征,从而使其作品具有了区别于其它作品的地域文化意义。瑞士心理学家荣格把艺术看成是集体无意识的表现,是人类集体心灵深处的回声,是原始意象和原始幻觉的象征。荣格认为,只有表现集体无识及其原型的艺术才能突破个人局限而唤醒所有的力量,维护现代人的完整人性,才能帮助人类返回神圣的家园[13](P360)。 因此,表达一定地域内民众的文化诉求,是文艺的职责所在,也是地域文化的重要体征。
四、结语
进入21世纪以来,江西女性作家们扎根本土,将女性写作与社会历史相结合,关注底层女性的命运,书写她们在复杂社会生活中的爱情、欲望、身体以及婚姻等。她们的作品善于通过个体命运的沉浮来折射社会、历史以及人类生活的发展轨迹,表现普通民众对地域文化的情感认同与精神诉求,带有鲜明的赣文化特色,有其独特的审美风格和存在价值。但是,她们的作品在对地域文化特色的表现时对深层文化本质内涵挖掘还不够深入,尚需进一步深入其中,多一点人文思索与关怀,以增强地域文化的内在活力和自觉意识。我们相信,在她们的不懈努力下,不久的将来,她们的辛勤耕耘一定会硕果累累。
[1] 梁海.苏童小说与江南地域文化[J].当代文坛,2012,(3).
[2]程千帆.程千帆全集·文论十笺[M].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
[3] 安然.水月亮[M].北京:中国工人出版社,2004.
[4] 彭学军.北宋浮桥[M].北京:现代出版社,2013.
[5] Jonathan Bate.The Song of the Earth[M].Cambridge,MA: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00.
[6] 沈苇.尴尬的地域性[N].文学报,2007-03-15.
[7] 余悦.江西民俗[M].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2004.
[8] 李超.元人吴澄的江西地城父学观[J].兰州教育学院学报.2010,(6)
[9] 何静.素手青条上红妆白日鲜[J] .山东文学,2012,(3).
[10] (美)本尼迪克·安德森.想象的共同体[M].吴叡人 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
[11] 陈蔚文.惊蛰[J].上海文学,2012,(3).
[12] (美)露丝·本尼迪克特.文化模式[M] .王炜,等 译.北京:三联书店,1988.
[13] 马新国.西方文论史[C].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