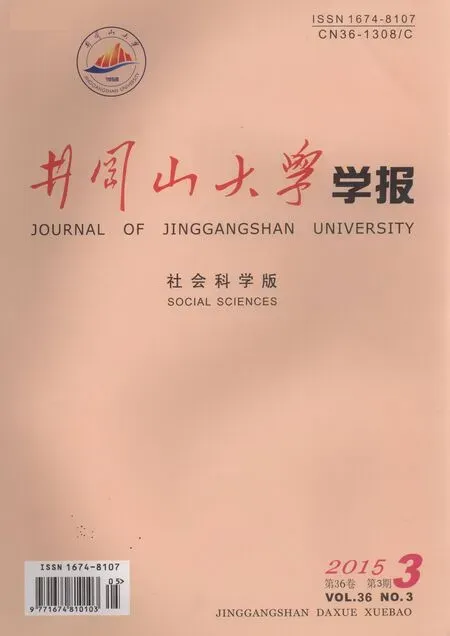中国现代主义思潮的“颓废性”嬗变
李洪华
(南昌大学中文系,江西 南昌 3 30031)
现代主义思潮在中国现代文学发展过程中一度被贴上西方资本主义“颓废”的标签,即便是经过上世纪80年代以来“重写文学史”浪潮的重塑,人们对现代主义思潮的“颓废性”习惯经验在艺术层面上有了很大程度的“矫枉”,但在思想来源方面仍然没有得到很好“厘清”。大家对现代主义思潮曾经在中国的“风光”有了越来越多的“共识”,但是对其为何由启蒙大众、引领人生的“宠儿”嬗变为落后、反动、颓废的“弃儿”的问题,并未得到很好的解决。文章试图在还原历史语境的基础上,对中国现代主义思潮“颓废性”嬗变的过程及缘由作一管窥。
一、启蒙文化语境中现代主义思潮的“浪漫化”倾向
“五四”时期,新文化先驱们是循着先“立人”后 “立国”的思想路线选择和接受外来文化思潮的。正如鲁迅所指出:“角逐列国是务,其首在立人,人立而后凡事举:若其道术,乃必尊个性而张精神。 假不如是,槁丧且不俟夫一世。”[1](P51)在思想启蒙的文化语境中,现代作家对反叛传统、张扬个性的现代主义思潮表现出“浪漫”的热情。这一“浪漫化”倾向主要表现为,“中国作家对于西方现代主义文学的兴趣还不在于具体作家和具体技巧,而在于现代主义反映的现代意识。”[2](P143)
众所周知,“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实绩主要体现在新文学的成功上,而新文学的成功显然与西方现代主义文学思潮的影响密不可分。现代主义文学思潮所彰显的现代性首先是与一切传统猝然决裂的“新的意识”和“人类思维的新状态”[3](P96)。五四作家对西方现代主义思潮的应和也更多地表现在思想意识层面。五四伊始,首倡“文学改良”的胡适便是在美国意象主义的启发下提出了新文学的“八事”主张。陈独秀参照“现代欧洲文艺”高举“文学革命”大旗时所注重的是它们的思想意识,他说:“西洋所谓大文豪,所谓大作家,非独以其文章卓越时流,乃以其思想左右一世也。”[4]在这些“大文豪”、“大作家”中就包括梅特林克和霍普特曼等象征派作家。鲁迅在译介安特莱夫、陀思妥耶夫斯基、厨川白村等俄、日现代派作家作品时,尤其注重思想意识层面,他称厨川白村等的著作有“天马行空似的大精神”,是“萎靡锢蔽”的中国所需要的[5](P232)。 五四时期现代主义思潮的积极倡导者茅盾则更明确指出:“介绍西洋文学的目的,一半是欲介绍他们的文学艺术来,一半也为的是欲介绍世界的现代思想——而且这应是更注意些的目的,而在尚未有成熟的‘人的文学’之邦像现在的我国,翻译尤为重要;否则,将以何者疗救灵魂的贫乏,修补人性的缺陷呢?”[6]
“五四”时期,现代作家并没有对现代主义思潮进行合理的命名,而常常以“新浪漫主义”来指称现代主义,但对新浪漫主义的认识和运用却相当模糊和混乱。茅盾在《我们现在可以提倡表象主义吗?》中并未把表象主义(即象征主义)归入新浪漫主义,而是认为它“是承接写实之后,到新浪漫的一个过程”。而在《为新文学研究者进一解》中却认为,新浪漫主义主要由“心理派的小说家”和“象征派的诗家”组成[7],把象征主义的霍普特曼和浪漫主义的罗曼罗兰等人都归入新浪漫派之中。田汉认为,新浪漫主义“重主观直觉情绪”,是“以罗曼主义为母,自然主义为父所产生的宁磬儿”[8]。海镜则在《后期印象派与表现派》中把象征主义、未来主义、表现派等都归入新浪漫主义。正如沈起予在20世纪30年代总结新浪漫主义历史特征时所指出,20年代以来人们提倡 “新浪漫主义的范围实很漠然”,“似乎凡是代表世纪末的、主观的、颓废的、享乐的、神秘的精神等的东西都可以放进去”[9](P216)。可见,五四作家对于现代主义的“浪漫化”态度一方面是因为对现代主义思潮缺乏准确、深刻的认识,另一方面也说明了他们所关注的是现代主义的思想意识而不太注重它们的艺术形态,这在他们的创作中也得到体现。
作为新文学的“主将”,鲁迅“超越了他那一代人的那种常见的感受力而跨入了西方现代主义文学的门槛”,他早期创作的《呐喊》、《彷徨》和《野草》等作品充满了广泛的象征和孤独的体验,被认为是 “已经发展到象征主义阶段”[10](P232), 后期的《故事新编》大量运用荒诞、夸张、变形的手法有意制造“间离”效果,“主要是现代主义——确切地说是表现主义的产物”[11]。然而,鲁迅是从现实主义的意义上接近和运用现代主义的。他借鉴安特莱夫“含着严肃的现实性以及深刻的纤细,使象征印象主义与写实主义相调和”[12](P185); 仿效陀思妥耶夫斯基“将人的灵魂的深,显示于人”[13](P103);学习菊池宽“竭力的要掘出人间性的真实来”[14](P228)。与鲁迅不同,“狂飙突进”的创造社成员主要是在浪漫主义与现代主义之间徘徊。热爱泰戈尔、惠特曼和歌德等浪漫派的郭沫若同时也表现出对表现派的“共感”,他说:“当时流行着的新罗曼派和德国新起的所谓表现派,特别是表现派的那种支离灭裂的表现,在我的支离灭裂的头脑里,的确得到了它的最适宜的培养基”[15](P81)。 郭沫若不但对德国的表现主义“寄以无穷的希望”[16](P98),而且还毫不犹豫地把 “新罗曼主义”作为创造社今后发展的“方针”[17]。郭沫若早期诗歌、戏剧和小说所表现出的“生底颤动,灵底喊叫”,既是浪漫主义的情感宣泄,也是表现主义的“自我表现”。对此,郑伯奇指出,郭沫若“受德国浪漫派的影响最深”,而“新罗曼派和表现派更助长了他的这种倾向”[18]。田汉的早期剧作大多具有浓厚的象征色彩,演绎抽象的生命主题,努力表现出象征主义倾向,但其剧作所体现出的“人生艺术化”戏剧观和带有虚幻色彩的理想主义,在美学倾向上正如有研究者所指出,“仍然是以浪漫主义间以象征主义手法来传达作家的艺术救世理想的”[19](P108)。
置身乡土中国的五四作家是怀着对现代民族国家的憧憬进行文化启蒙的,因此,他们在接近西方现代主义时明显地表现出浪漫化的“拿来主义”倾向。他们虽然“在某种程度上,同样具有西方美学的现代主义那种艺术性的反叛意识,但他们并未抛弃对科学、理性和进步的信心”,他们反对的不是 “包藏在日增月涨的物质文明中的虚伪和粗鄙”,而是植根于落后乡土社会中的专制和愚昧,他们不是厌倦“浪漫的人文主义”,而是在思想启蒙过程中表现出现实的责任和浪漫的热情。
二、左翼文化语境中现代主义思潮的嬗变
“五四”时期,先进知识分子在追求现代性的过程中,参照的对象是西方现代文明,选择的路径是文化启蒙,实施的方案是反封建。正是在这种注重思想启蒙的文化语境中,中国现代作家在引进西方现代主义思潮时,关注的是其反传统的现代性和先锋性,而悬置了包含其中的颓废性,或者说颓废主义和唯美主义因素并没有妨碍他们拥抱现代性的热情。他们甚至把现代主义中的恶魔主义和虚无主义看作是现代社会的精神代表,并从中汲取合理的现代性内涵。周作人认为,波特莱尔“貌似的颓废,实在只是猛烈的求生意志的表现,与东方式的泥醉的消遣生活,绝不相同。所谓现代人的悲哀,便是这猛烈的求生意志与现在的不如意的生活的挣扎。这挣扎的表现可以为种种改造的主义,在文艺上可以为弗罗倍尔的艺术主义,陀思妥也夫斯奇的人道主义,也就可以为波特来耳的颓废的‘恶魔主义’了”[20]。田汉则说,波特莱尔的“诗境常为死,为颓唐,为腐肉,为败血,为磷光”,这种“恶魔主义”代表了“近代主义”的精神[21]。茅盾甚至认为,“所谓颓废派……于外面形式上看来,似乎不好,但是平心而论,也有可用之处,因为他的这种奇怪感想,全是反动的不平的思想所做成;他要求社会进步,而偏为社会所束缚,愤世故的悖逆,便发出许多狂言反语,他的形式虽然消极,其实却是积极,对于人类尚不致有坏的影响”[22]。
然而,上述状况在“文学革命”转向“革命文学”的20年代后期发生了变化。五四以后,知识分子的现代性诉求发生了由文化启蒙向社会革命的转变。在新的文化语境中,注重阶级分析和提倡社会革命的马克思主义很快成为现代知识分子革命救亡的新思想武器,现代主义思潮也随之由启蒙时代的“宠儿”沦为革命时期的“弃儿”,逐渐被左翼文艺界指斥为资产阶级腐朽、堕落的艺术,而遭到清算和批判。
在“文学革命”转向“革命文学”的过程中,以郭沫若、田汉、茅盾等为代表的五四作家在转向革命文学的同时,对曾经热情倡导的现代主义展开了清算和批判。1924年,郭沫若在译完日本著名马克思主义学者河上肇的《社会组织与社会革命》后表示,“今后打算把自我表现的文学无限期地搁置起来,而从现在起就把文学当作一种武器”[23](P10)。转向后的郭沫若对自己过去的文艺思想进行了清算,他批判曾经寄予“无穷希望”的现代主义是“幻美的”、“自我表现的”、“个人的”、“自由主义的”、“资产阶级的”、“反革命的”文艺,把它置于革命文学的反面。他宣称,“在欧洲今日的新兴文艺,在精神上是彻底同情于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的文艺”[24](P28),他感谢马克思主义把他从“半眠状态”、“歧路的彷徨”和“从死的暗影里救出”[23](P10)。 与热情易变的诗人相比,田汉的“左”转要迟缓一些。1928至1929年间,当郭沫若、冯乃超、王独清等曾经主张现代主义的创造社同仁高举“革命文学”的大旗时,已经脱离创造社另起炉灶的田汉仍然带领着南国社四处巡演他的 “新浪漫主义戏剧”。直到一年后,当左翼思潮磅礴到来时,曾经推崇并标榜新浪漫主义的田汉发生了“左”转,发表了七、八万字的长文《我们的自己批判》,对过去“误入歧途”的思想和艺术倾向进行了深刻的自我反省和批评:“在这个时代”,“演这样艺术味极浓厚的戏”,是“反时代”、“不民众”的,“惭愧得很。那时我们所能给的并不是无产大众对于新社会创造的理想,而仅仅是当时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底动摇与苦恼”,“过去的南国热情多于卓识,浪漫的倾向强于理性,想从地底下放出新兴阶级的光明而被小资产阶级底感伤的颓废的雾笼罩得太深了”。田汉在对自己和南国社 “仔细的清算与不断的自己批判”后,决心“将以一定的意识目的从事艺术之创作与传播,以冀获一定的必然的效果”,“新的戏剧得为新时代的民众制造新的语言与新的生活方式”[25]。时人回忆,田汉这一“诚恳的自我批评在当时的文化界引起了很大的震动”[26]。转向后的田汉积极投入左翼文艺运动,创作出一批富有时代感和革命性的现实主义剧作,彻底告别了新浪漫时期的唯美主义感伤色彩。1925年,曾经大力提倡“新浪漫主义”的茅盾发表了《论无产阶级艺术》。在这篇著名的长文中,茅盾在对无产阶级艺术进行全面阐述的同时,从意识形态层面对现代派艺术进行了的清算和批判。他认为,“无产阶级艺术对资产阶级——即现有的艺术而言,是一种完全新的艺术”,而“未来派、意象派、表现派”等曾经的“最新派”,是“旧的社会阶级在衰落时所产生的变态心理的反映”,是“变态的已经腐烂的‘艺术之花’,不配作新兴阶级的精神上的滋补品”[27]。然而,与那些批评和攻击他的创造社和太阳社成员不同的是,茅盾并没有把无产阶级艺术狭隘化,也没有在艺术层面上全盘否定现代主义。他认为,虽然现代主义艺术 “不配作新兴阶级的精神上的滋补品”,但是“各种新派艺术的诗式当然有其立足点,未便一概抹煞”,因为“人类所遗下的艺术品都是应该宝贵的;此与阶级斗争并无关系”[27]。
20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在日益高涨的左翼思潮的影响下,施蛰存、戴望舒、杜衡、刘呐鸥、穆时英等现代派群体也表现出鲜明的“左翼”倾向(戴望舒和杜衡还一度加入“左联”),在他们创办和经营的《无轨列车》、《新文艺》、《现代》等现代派杂志上,表现出现代主义和左翼兼容并举的编辑倾向。在创作上,他们也明显地表现出关注社会现实、描写底层民众生活和无产阶级斗争的左翼倾向,如施蛰存的《追》、杜衡的《机器沉默的时候》、戴望舒的《我们的小母亲》和穆时英的《南北极》等作品。穆时英一度甚至被誉之为“普罗文学之白眉”[28]。但是,刘呐鸥、施蛰存、戴望舒、杜衡、穆时英等现代派群体在倾向左翼的同时并没有放弃对现代主义先锋艺术的探索,他们对左翼思潮的态度也与左翼文艺界有很大的不同。在施蛰存、刘呐鸥等人看来,“新兴”的无产阶级普罗文学和“尖端”的资产阶级新流派都是文学的新潮,在艺术的本质上并没有什么两样,他们“高兴谈历史唯物主义文艺理论,也高兴谈弗洛伊德的性心理文艺分析”[28]。刘呐鸥甚至借翻译藏原惟人的《新艺术形式的追求》提出,普罗艺术不能只停留在“意识形态的内容”层面,而应该从“心理内容和艺术形式”上对“未来派,立体派,构成派,新写实派等的艺术”进行批判的吸收,“接受这些艺术形式的拍子,力学,正确和单纯”[29]。 然而,现代派关于现代主义和左翼思潮兼容并举的主张并没有获得左翼文艺界的认可。左翼批评家们指责他们的创作是“金融资本主义底下吃利息生活者的文学”,“他们只是张着有闲的眼,从这崩坏中发现新奇的美,用这种新奇的美,他们填补自己的空虚”[30]。对于左翼阵营的批评和责难,现代派群体表现出既要在思想上不甘落后又要在艺术上自由追求的矛盾和焦虑,二者之间关于艺术与政治关系的认识分歧,在左翼运动的高潮时期终于以“论争”的形式公开化,这在关于“第三种人”和“软”、“硬”电影的两次论争中都有不同程度地体现。苏汶、施蛰存、戴望舒、刘呐鸥、穆时英等坚持自由主义的文学立场,信守文学的真实性、艺术性和个性主义;而左翼批评界坚持普罗主义的文学立场,主张文学的社会性、阶级性、革命性和集团主义。这场关于文学与政治关系的论争在某种意义上可以看作是坚持艺术现代性的现代主义思潮与坚持革命现代性的左翼思潮的一次正面“交锋”。
三、现代主义思潮“颓废性”嬗变的溯源
作为一种世界性的文艺思潮,以现代性为本质诉求的现代主义在共时性和历时性的不同维度上都包含着各种不同的甚至相互反对的思想主张和风格倾向,其中既有颓废唯美的象征主义,也有左翼进步的表现主义;既有投靠法西斯政权的意大利未来主义,也有支持共产主义运动的苏俄未来主义。正因如此,卡林内斯库在分析现代性问题时指出,颓废和进步的因素是紧密地包含在现代性范畴之中的,“以至于如果我们想作出概括,就会得到一个悖论式的结论:进步即颓废,反之,颓废即进步”,“高度的技术发展同一种深刻的颓废感显得极其融洽”,颓废与进步和繁荣相生相随[31](P166)。 实际上,美学上的“颓废”最初并没有意识形态倾向的贬义色彩,“颓废风格只是一种有利于美学个人主义无拘无束地表现的风格,只是一种摒除了统一、等级、客观性等传统专制要求的风格”[31](P183)。因此,在追求个性解放的五四时期,周作人、田汉、茅盾等人并没有对现代主义思潮中的颓废因素感到任何不适,反而把象征主义中以恶、丑为美的恶魔主义和悲观厌世的虚无主义看作是近代主义的精神代表和现代人的悲哀表现,从中汲取合理的现代性内涵。然而20年代中期以后,曾经以先锋姿态和现代意识倍受五四作家注目的现代主义思潮在左翼作家的视野中逐渐失去了此前的“先锋性”与“合理性”,现代主义思潮中的颓废性因素被上升到意识形态领域遭到批评和否定。
现代主义思潮在中国经由先锋到颓废的 “变奏”,美学上的“颓废”概念被左翼文艺界长期上升到意识形态领域贬义化运用,除了国内的社会政治原因和现代主义艺术的自身因素外,还主要与作为中国左翼文艺思潮直接来源的俄、日左翼文艺思潮密切关联。
苏俄文艺论战时期,激进的革命文学团体对包括现代主义思潮在内的文化遗产采取了简单粗暴的否定和批判态度。转向革命的未来派马雅可夫斯基等人甚至宣称要把普希金、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勃洛克、索洛古勃等文学前辈和同时代的现代派作家 “全都从现代生活的轮船上扔出去”。波格丹诺夫等无产阶级文化派在鼓吹极左的“无产阶级文化”理论时也主张彻底否定文化传统,认为无产阶级艺术“只能在新的基础上发展”,要“与资产阶级文化决裂”[32]。20世纪20年代初,盛行日本的福本主义主张 “要创立有明确阶级意识的无产者集团的组织”,“必须在联合之前,首先彻底地分裂”,“使一切非马克思主义思想如工联主义、折衷主义得到彻底的清除”[33](P75-76)。 其后,苏联的“拉普”和日本的“纳普”所开展的无产阶级文学运动强调辩证唯物主义为唯一正确的创作方法,否定之前的现实主义、浪漫主义和现代主义,排斥现代派同路人作家。
以俄、日为师的中国左翼文艺界在上述激进思潮的影响下,大力倡导革命文学,提出要“干干净净地把从来所有的一切布尔乔亚意德沃罗基(笔者注:Ideoloige思想意识的音译)完全地克服,牢牢地把握着无产阶级的世界观——战斗的唯物论,唯物的辩证法”[34]。因此,他们理所当然地认为,现代主义是“旧的社会阶级在衰落时所产生的变态心理的反映”,是“变态的已经腐烂的‘艺术之花’,不配作新兴阶级的精神上的滋补品”[27]。不止是苏俄和日本激进思潮的庸俗社会学主张和虚无主义态度深刻影响到中国左翼文艺界,使之对五四新文学传统中的现代主义产生态度上的根本性转变,而且列宁、普列汉诺夫、卢纳察尔斯基和日丹诺夫等革命领导人或早期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家对待现代主义的态度也同样影响了中国左翼文艺家们现代主义“颓废观”的形成。
作为无产阶级革命的导师,列宁一方面反对激进革命文学团体对待文化传统的虚无主义态度,认为“即使美是‘旧’的,我们也必须保留它,拿它作为一个榜样,作为一个起点”[35](P106)。 但是,列宁所重视的艺术传统是现代主义以前的普希金、托尔斯泰、果戈里等的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传统,而不是资本主义后期的现代主义先锋派艺术。列宁反对颓废派的神秘主义和取消主义倾向,并把颓废主义的特征概括为“狂欢烂醉状态”[36](P24),他甚至表达了对现代主义的反感:“我不能把表现派、未来派、立体派和其它各派的作品,当作艺术天才的最高表现。我不懂它们。它们不能使我感到丝毫偷快。 ”[35](P434)俄苏早期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家普列汉诺夫和卢那察尔斯基的文艺思想是中国左翼文论最重要的思想来源,鲁迅、冯雪峰、瞿秋白等都先后翻译过普列汉诺夫和卢那察尔斯基的重要文艺论著,因而他们关于现代主义思潮的观点和态度对中国左翼文艺界有着更为直接的影响。在《无产阶级运动和资产阶级艺术》和《艺术与生活》等著作中,普列汉诺夫对现代主义的艺术特征、历史演变、思想基础和社会根源进行了集中论述。他认为,西方现代主义从为艺术而艺术变成了为金钱而艺术,是衰落时期的艺术,所反映的社会关系体系也是衰落的,因而称它为颓废派的艺术是最适合不过的;现代主义艺术的基本特征就是离奇的形式和贫乏的思想。他忧虑俄国许多知识分子迷醉于西方资产阶级精神危机时代的哲学思想和审美趣味,并且还进一步渗透到许多无产阶级的同情者之中,与社会主义奇妙地混起来,从而造成思想上的混乱[37](P837-868)。 与列宁和普列汉诺夫一样,卢那察尔斯基反对现代派艺术上的颓废主义和形式主义,他说,“不论是象征主义的迷雾,还是令人眼花缭乱的未来主义的焰火都不行”,他希望“革命给艺术以巨大的影响,说得简单一些,把艺术从颓废主义的最坏的艺术种类那里,从形式主义那里拯救出来”[38](P313)。
20世纪二、三十年代,对中国左翼文艺界产生影响的还有苏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家高尔基、沃罗夫斯基、日丹诺夫等人。高尔基曾对现代主义的神秘主义和颓废主义进行了严厉的批判。在他看来,现代主义作家“傲慢不逊地卖弄他们自己病态的稀奇古怪的玩意,这些玩意使他们变成从平常的眼光看,是一些自命不凡的可笑的人;从精神病医生的眼光看,是一些有精神病的人;从社会学家的眼光来看,是一些不仅艺术上、而且道德上的无政府主义者;从所有这三种眼光看来,颓废主义者和颓废派是一种有害的、反社会的现象,是一种必须与之斗争的现象”[39](P2-3)。 沃罗夫斯基则一度把现代主义等同于颓废主义来揭示其对革命的消极作用。他说颓废派文学是“资产阶极真正的产物,是它所产生、也是它为了自我慰藉所需要的腐烂了的果实”,以安德烈耶夫为代表的悲观主义和以索洛古勃为代表的享乐主义不是把革命描写成只能造成混乱和破坏的残酷而无意义的反叛,便是以色情和淫荡来消磨人们的斗志并卑鄙地污蔑革命者的形象。因此,颓废派文学实质上都是“消灭革命”的[40](P174-179)。
总之,20世纪20年代中期以后,在“启蒙”转向“革命”的文化语境中,现代主义思潮在中国由“先锋”到“颓废”的变奏,与俄、日极“左”文艺思潮和俄苏早期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的影响是息息相关的。虽然苏俄革命文学派别之间存在各种分歧和矛盾,但是他们在文艺思想上表现出类似的革命功利主义或庸俗社会学倾向,大多从文艺为政治服务的角度强调文艺的阶级性和革命性,大多把美学领域的艺术问题进行社会学层面的简单化处理,从而对现代主义思潮持批评与否定态度。这种对待文艺尤其是对待现代主义思潮的态度与方法对中国左翼文艺界产生了深远影响。实际上,虽然作品意义、作家思想、阶级属性和经济基础存在一定的联系,但是它们之间绝不是简单的必然的对应关系。无数文学史实证明,作品的意义大于作家的思想,而作家的思想并非是所属阶级的机械反映。正如恩格斯所指出,“更高的即更远离物质经济基础的意识形态,采取了哲学和宗教的形式。在这里观念同自己的物质存在条件的联系,越来越错综复杂,越来越被一些中间环节弄模糊了,但是这一联系是存在着的”[41](P253)。而在艺术的评价标准上,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更是把“美学观点”置于“史学观点”之前视为“非常高的即最高的标准”[41](P561)。虽然普列汉诺夫等人对现代派艺术产生的社会基础和心理根源进行了深刻的分析。但是,现代派艺术的产生除了这些主要条件之外,还有许多复杂因素,譬如现代技术、生活节奏和战争动乱对人们生活方式、心理状态和审美趣味的改变等。更何况,现代主义思潮本身就充满了复杂的矛盾和冲突,不仅派别繁多,而且在各派之间以及每一派别内部都存在着艺术思想和创作方法上的千差万别。显而易见,我们对现代主义思潮的“颓废性”习惯经验不但要从艺术层面进行 “矫枉”,而且还应从思想来源方面进行“厘清”。
[1] 鲁迅.文化偏至论[A].鲁迅全集:第 1 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
[2] 陈思和.七十年外来思潮影响通论[A].鸡鸣风雨[M].上海:学林出版社,1994.
[3]麦·布鲁特勃莱.现代主义的称谓和性质[A].现代主义文学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
[4] 陈独秀.现代欧洲文艺史谭[J].青年杂志,1915,(3).
[5] 鲁迅.《苦闷的象征》引言[A].鲁迅全集:第 10 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
[6] 茅盾.新文学研究者的责任与努力[J].小说月报,1921,(2).
[7] 雁冰.为新文学研究者进一解[J].改造,1920,(9).
[8] 田汉.新罗曼主义及其他[J].少年中国,1920,(6).
[9] 沈起予.什么是新浪漫主义[A].文学百题[M].上海:生活书店,1935.
[10] 李欧梵.现代性的追求[M].北京:三联书店,2000.
[11]严家炎.鲁迅与表现主义——兼论《故事新编》的艺术特征[J].中国社会科学,1995,(2).
[12] 鲁迅. 《黯淡的烟霭里》译者附记[A].鲁迅全集:第 10 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
[13] 鲁迅.《穷人》小引[A].鲁迅全集:第 7 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
[14] 鲁迅.《三浦右卫门的最后》译者附记[A].鲁迅全集:第 10 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
[15] 郭沫若.创造十年[A].郭沫若全集:文学编 12 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2.
[16]郭沫若.自然与艺术——对表现派的共感[A].文艺论集[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
[17] 陶晶孙.忆创造社[A].牛骨集[M].上海:太平书局,1944.
[18]郑伯奇.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三集导言[M].上海: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公司,1935.
[19]唐正序,陈厚诚.20世纪中国文学与西方现代主义思潮[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2.
[20]周作人.三个文学家的纪念[N].晨报副刊,1921年11月14日.
[21] 田汉.恶魔诗人波陀雷尔的百年祭[J].少年中国,1921,(4),(5).
[22] 沈雁冰.什么是文学——我对于现文坛的感想[J].学术演讲录,1924,(2).
[23] 郭沫若.孤鸿[A].郭沫若全集:第 16 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2.
[24] 郭沫若.革命与文学[A].郭沫若论创作[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3.
[25] 田汉.我们的自己批判[J].南国月刊,1930,(4).
[26]阳翰生.纪念左联成立五十周年大会上的发言[A].左联回忆录[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0.
[27] 沈雁冰.论无产阶级艺术[N].文学周报,1925-05-02,1925-05-17,1925-05-31.
[28] 施蛰存.我们经营过三个书店[J].新文学史料,1985,(1).
[29] 藏原惟人.新艺术形式的追求[J].葛莫美 译.新文艺,1929,(12).
[30] 适夷.施蛰存的新感觉主义——读了《在巴黎大戏院》与《魔道》之后[J].文艺新闻,1931,(33).
[31]卡林内斯库.现代性的五副面孔[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2.
[32] 凯尔仁采夫.与资产阶级文化决裂[J].艺术与文化(苏),1920,(6).
[33]艾晓明.中国左翼文学思潮探源[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
[34] 李初梨.怎样地建设革命文学[J].文化批判,1928,(2).
[35]列宁.列宁论文学与艺术[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
[36] 列宁.列宁全集:第 10 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5.
[37]普列汉诺夫.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第5卷[M].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1987.
[38]卢那察尔斯基.卢那察尔斯基文集:第2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
[39] 高尔基.高尔基论文学[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
[40]沃罗夫斯基.文学批评论文集[M].莫斯科:苏联国立文学出版社,1956.
[4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