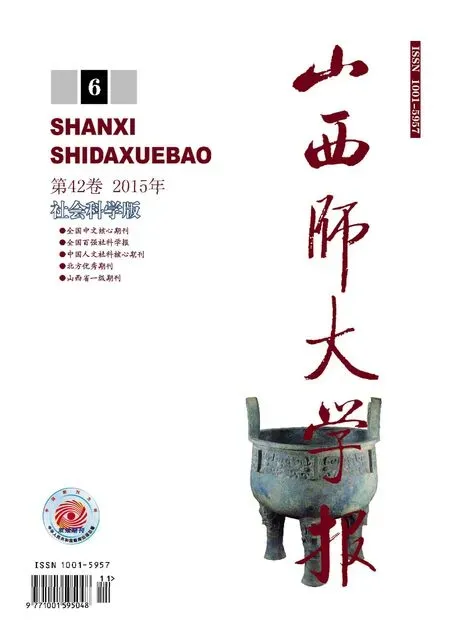论先秦“故实”观的史学生活意义
王 灿
(河南科技大学 人文学院,河南 洛阳 471023)
先秦时期是中华文化的起源期,在中国历史上非常重要,因而关于先秦史学的研究一向极受重视,出现了很多有启发性的成果。而历史思想研究又是先秦史学的重要方面,包括“殷鉴”观念、“法先王”思想等在内的种种观念,现有研究成果颇多。然而在《国语》等先秦文籍中还存在着以“故实”(即“可效法的成例或先例”)为行事依据的普遍观念,其在史学生活*“史学生活”,即人类与“史学”相关的精神生活,是与“语言生活”、“文学生活”等并列的“精神生活”概念。本来“历史生活”一词更为合适,然而考虑到“历史生活”一词以前多被理解为“过去的生活”,故用“史学生活”代替。等方面的意义,尚未引起学界的足够重视,值得专文深入剖析。
一、“故实”观概述
先秦古籍《国语》中数次出现的“故”字值得注意:
哀姜至,公使大夫、宗妇觌用币。宗人夏父展曰:“非故也。”公曰:“君作故。” 对曰:“君作而顺则故之,逆则亦书其逆也。”[1]147(《国语5鲁语上》)
里克对曰:“非故也。君行,太子居,以监国也;君行,太子从,以抚军也。今君居, 太子行,未有此也。”[1]268(《国语5晋语一》)
上引《国语》段落的意义在于:它不仅指出了“故”有“值得效法的正面史例”这一易被忽视的重要含义,而且指出当时人们都具有遵循“故”或者建立(正确)“故”的意识。而《国语》中还有些地方从不同侧面对“故”的这一意涵和用法都做了注脚:
宣王欲得国子之能导训诸侯者,樊穆仲曰:“鲁侯孝。”王曰:“何以知之?”对曰: “肃恭明神而敬事老;赋事行刑,必问于遗训而咨于故实,不干所问,不犯所咨。”王曰: “然则能训治其民矣。”[1]23(《国语5周语上》)
庄公如齐观社。曹刿谏曰:“不可。……今齐社而往观旅,非先王之训也。……君举必书,书而不法,后嗣何观?”[1]144—147(《国语5鲁语上》)
“问于遗训”与“咨于故实”,“先王之训”与“君举必书,书而不法,后嗣何观”都互相阐释,有力地证明了“故”或者“故实”作“可效法的成例、惯例”之意,而且是当时社会语境中重要而固定的用法。这在先秦时期的其他古籍中也有明显表现,譬如,《逸周书》言:“好变故易常者,亡。昔阳氏之君,自伐而好变,事无故业,官无定位,民运于下,阳氏以亡。”[2]380把“故”和“故业”并用,从上下文清晰可见其“可效法的往事、惯例”之意;为人们所熟知的“持之有故,其言之成理”[3]89—91之“故”,更是把“故”作为“持”的前提。而段玉裁《说文解字注》对于“古”的解释是“按故者,凡事之所以然。而所以然皆备于古……展转因袭,是为自古在昔矣。……凡古之属皆从古”[4]88。可见“故”或者“古”的本意即“先例”。如果说《说文》对“古”的解释还只能间接说明“故”的本意,那么,其对“故”的直接解释就更有说服力:“凡为之必有使之者。使之而为之则成故事矣。引伸之为故旧。故曰古,故也。墨子经上曰:故,所得而后成也。”[4]123可见,“故”即“故事”亦即“故实”即“可效法的成例或先例”。尤其所引《墨子5经上》之“故,所得而后成也”,更是强调指出“可效法的成例才能做成今事”之意(“故”在此处易被误解为“原因”),《墨子》注者孙诒让做了准确的剖析。[5]309
不仅从字面上考证是如此,从古代思想史上看同样有迹可循。中国最早典籍《尚书》首篇《尧典》起首即言:“曰若稽古。”有学者径直解为“追述”“查考”古事[6]5—6,即“从古事中寻求可效法之事”。又如孔子曾言:“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7]2483其意同样强调了对“古”(即“故”)的重视。而众人皆知的“温故而知新”之“故”,按照相当多古代学者的看法,正是“故实”之意——“故”应是“古也,已然之迹也”,相应的,“新”乃“今也,当时之事也”,学者列举古注中的诸多证据,足可证成此说。[8]94—95因此可证明,先秦时期古人在行事施政时普遍存在着要遵循前代可遵循的成例这一原则,即“咨于故实”的观念,可概之为“故实”观。
先秦时期的“故实”观,即使在后世也一直占据重要地位,在各种文献中皆有折射和反映。如在颇有“疑古”“疑经”倾向的东汉学者王充笔下,他也仍然对“故实”的作用毫不怀疑。[9]1178—1179南朝颜延年的一篇与王融的同名文章《三月三日曲水诗序一首》中就使用了“故实”一词,并且,后世注者李善在注中本身就以引用“故实”的方法来反复说明“故实”之重要。[10]646中国古人对于“故实”观的认可可见一斑。
总之,发源于先秦时期的“故实”观深刻影响了整个中国古代,已成为中国传统文化思想宝库中的重要内容。
二、“故实”观是重要的历史观念
上述凡事强调“咨于故实”的观念,是一种强烈而突出的历史意识,这点毋庸置疑。因为,“咨于故实”的实质就是通过对往事和经验的追溯,把它和今事进行比较,以作为今日举措的根据,所以这种对往事的面向就决定了其中必然包含着史学生活的强烈意味,而“历史”亦因之时刻返照于“现实”之中,此乃中国古人一种独特的史学生活。因而,“故实”观首先应属一种历史观念,一种史学方面的精神生活。简言之,属于史学生活中的历史观念。
但是,先秦时期还有一种很明显的历史观念——“先王”观念或言“法先王”思想,即以效法、遵循先王遗规、以先王为行事执政楷模的观念意识。如果不加辨别,“咨于故实”观念似乎与“法先王”思想并无二致。其实二者仍有明显分野。不可否认,“先王”观念亦有其对往事和古人的面向,那么,这与“故实”观是否同一呢?答案应该是否定的,其原因有以下几点:其一,“先王”观念与“故实”观的具体内容不同。前者的核心在于对“先王”的人格、行事及效仿,将其对象限定在“先王”上,但是,“故实”观的内涵却超过“先王”的范围,凡是以往之事,皆在其范畴之内,而不仅限于“先王”之事,这点前文已有例证和论述。其二,“先王”观由于“先王”在上古时期的中国兼具君、师、圣人身份,故而带有更强烈的宗法乃至宗教意味,而“咨于故实”却更强调其作为治道和行事的依据,带有浓厚的实用理性主义色彩。一言以蔽之:“故实”观表现了效法“事例典范”的历史意识,而“先王”观念则本质上属于效法“人格典范”的历史观念。
另外,在发源于先秦时期的历史观念中,“殷鉴”思想(或言“历史鉴戒观念”)也是重要的一种,它与“故实”观的关系亦应加以辨析。从汲取历史经验教训这一角度而言,“故实”观表现出古今连续的历史意识。因为,只有承认历史是连续、有其相同点而非断裂、无相同点这一前提,才能把古事和今事相联系,否则,“故实”观就没有意义,而“殷鉴”思想也是建立在历史的连续性、统一性、相似性这些前提之上的,否则,前代历史对于后世也根本不能产生鉴戒作用。[11]6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故实”观与“殷鉴”思想有相通之处,但二者也有不同。虽然二者皆含有以古代之事作为当前行为依据之意,但是,“殷鉴”思想重点在于寻求经验教训亦即“鉴戒”,而“故实”观却更着眼于“成例”本身存在与否。换言之,“殷鉴”观指向“当下”,“故实”观指向“过往”。正是因为“故实”本身就带有今之“典范”“依据”的意义,因此按照“故实”观,在先秦时期的中国,“当下”能否做某事的依据,在某种意义上却是存在于“历史”即“故实”之中的。
三、“故实”观产生的原因及其影响
从上文清楚可见,先秦时期的“咨于故实”是普遍存在的。另一个很重要的问题随之产生:何以中国古代的“故实”观如此强大而传承久远?这应该从整个中国原生本土文化的根本特性上去寻找答案。
首先,这与中国上古时期文化发生之初就缺乏西方那样的宗教和宗教团体以及宗教生活有关。有学者指出:“唐虞夏商……没有与政权并峙的教权,如埃及式的僧侣,犹太式的祭司,印度式的婆罗门,在中国史上还未发见有与之相等的宗教权力阶级。中国古代君主都是君而兼师的;他以政治领袖而兼理教务,其心思当然偏重在人事。中国宗教始终不能发展到唯一绝对的大神观念。当然亦是教权不能凌驾政权之上的原因。在宗教上的统一天国尚未成熟之前,政治上的统一帝国已经先建立起来;因此宗教的统治,便永不能再出现了。 ”[12]86正是由于没有像西方那样的超越性宗教,不能以教义作为最高行为准则,出于经验理性的原因,中国古人特别重视以过往的故实作为行事、施政的榜样和规范。
其次,先秦时期“故实”观的强大,还与中国经验理性的发达和重视史学生活紧密相关。李泽厚先生早已指出:“不是先验的、僵硬不变的绝对的理性(rationality),而是历史建立起来的、与经验相关的合理性(reasonableness),这就是中国传统的‘实用理性’,它即是历史理性。因为这个理性依附于人类历史(亦即人类群体的现实生存、生活、生命的时间过程)而产生,而成长,而演变推移,具有足够的灵活的‘度’。……‘实用理性’不以自身为自足的最高鹄的,相反,它清晰地表明自己作为人类生存的工具性能:在实用中证实理性对于人类生存确乎是有用的和有益的。‘实用理性’不是先验的理性,也不是反理性,它只是非理性的生活中的实用合理性。它是由历史所建构的。”[13]90李先生指出的这种“与经验相关的合理性”和“中国传统的实用理性”,完全可以用来理解“故实”观——“故实”不就是在“实用中证实理性对于人类生存确乎是有用的和有益的”吗?“故实”观不就是“依附于人类历史”并“由历史所建构”的吗?因而,正是由于西方式宗教观念的淡薄和实用理性主义的生活观念,凡事必“咨于故实”的观念才会深入古代先民的人心,而成为一种习惯性的重要观念意识。
再次,从事实上言,肇端于先秦的“故实”观也确实有其人类精神生活上的充分合理性。因为,过往的礼俗制度、惯例、规则之所以能被人们所记载、信从、遵守,多是因为已经被历史事实证明了它的合理性。这正如梁漱溟先生早已指出的:“……给予古今礼俗制度各以其历史上适当的位置,肯定多于否定。大抵一种礼俗制度的兴起畅行皆基于其时代需要与环境可能而来,有利于有秩序地进行其社会生产和生活;虽则今天看它不免愚拙幼稚乃至横暴残忍,却总是当地当时人们的创造表现,有行乎其不得不行者在。”[14]684而且,还有学者进一步指出,正是因为“故实”已经被相对于“当下”更久远的时间、比“当时之人”更多的古人的经历所证明为正确而可效法,所以它就理所当然地成为后世之人的参照:“历经数代人的实验和尝试而达致的传统或成就,包含着超过了任何个人所能拥有的丰富经验,因此关于这些规则系统的重要意义,人们或许可以通过分析而发现;但是即使人们没有透彻认识和把握这些规则系统,亦不会妨碍它们有助于人们的目的的实现。”[15]16“数代人”的经验,当然比“一代人”的想法更经得起时间的检验,更何况是数十代乃至百代呢!
最后需要补充说明的是,先秦时期的“故实”观,与中国特有的“礼法”制度等紧密相关。不仅如此,它还与英国等国家的先例制度有很多相似之处,实际上带有习惯法的意味。归根结底,它实际上是一种经验理性主义的历史观和制度观,强调“法在王上”,并且主张遵循保守、慎重、经验及平和演进的理念,对保持社会政治的稳定和有序进步以及限制君权起到了非常关键的作用。然而,随着君主专制的不断加强,荀子实变古之“隆礼重法”实为君主专制下的“礼法”过渡,为“法礼”,而法家则纯变为“法”,在本无至上神的中国,“先王”之礼法的权威,被迫让位于当世之王的“法令”,“循礼”和“咨于故实”的观念,虽然仍有遗存,但实际上已被弱化、边缘化和口号化,从而使得君主的权力失去了被限制的空间。后世,“故实”观与“法先王”思想一样,难免其逐渐式微的命运。在秦朝以后的君主专制政体之下,即使仍有遗存,但它已经成为君主专制统治的点缀,只是一种潜在而微弱的君权限制观念。对“故实”观的反动和摒弃,其极端情形就是秦朝的“以法为教,以吏为师”制度,这实际上就是把君主专制权力作为全体国人的唯一行动准则,君权变得独大和独断。
因而,在中国历史上,“故实”观未能如英国那样得于“天时”之利,一直保持较为强大的力量。更由于后世君主专制主义统治的严酷,而使得后世中国社会实际上沿着如同法国大革命那样的暴力路线演进,不断改朝换代。一旦新的政权建立,则又不得不利用儒家思想这一经验理性主义的渊薮进行统治,即奉行“阳儒阴法”的统治策略。在这种情况下,包括“故实”观、“法先王”思想、先秦礼法思想在内的种种思想资源,虽然表面上仍被尊崇,但实际上都不能如先秦之时那样有足够的影响力,不能对专制君主形成更大的制约。由于君主专制与儒家思想的内在矛盾,“故实”观念总是被压制。当思想和政治上的专制演变到极端的地步时,又会造成新的历史断裂和新政权的产生。在历史悠久的中国,这就造成了一种“兴衰周期律”的刻板印象。这种由于背离经验理性造成的社会历史的断裂,是一种应予深刻反思的现象。可以说,与“礼崩乐坏”这一理由一样,“故实”观的逐渐式微,亦应是后世儒家学者何以艳称“三代”、称其为“天理”流行,并贬秦朝以后为“势利世界”的重要原因之一——因为“三代”时的“天理”和“礼法”或“礼乐”制度就存在于“故实”之中。至于“故实”观在法律制度方面的意义,限于篇幅,另撰文探讨。
[1] 徐元诰撰.国语集解[M].王树民,沈长云点校.北京:中华书局,2002.
[2] 黄怀信.逸周书校补注译[M].西安:西北大学出版社,1996.
[3] (清)王先谦撰.荀子集解[M].沈啸寰,王星贤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88.
[4] (汉)许慎撰.说文解字注[M].(清)段玉裁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
[5] (清)孙诒让撰.墨子间诂[M].孙启治点校.北京:中华书局,2001.
[6] 顾颉刚,刘起釪.《尚书》校释译论[M].北京:中华书局,2005.
[7] (清)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5论语注疏[M].北京:中华书局,1980.
[8] 程树德撰.论语集释[M].程俊英,蒋见元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90.
[9] 黄晖撰.论衡校释(附刘盼遂集解)[M].北京:中华书局,1990.
[10] (梁)萧统编,(唐)李善注.文选[M].北京:中华书局,1977.
[11] (德)黑格尔.历史哲学[M].王造时译.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1.
[12] 梁漱溟.中国文化要义[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
[13] 李泽厚.人类学历史本体论[M].天津:天津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
[14] 梁漱溟全集:第7卷[M].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86.
[15] (英)哈耶克.自由秩序原理(上册)[M].邓正来译.北京:生活5读书5新知三联书店,199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