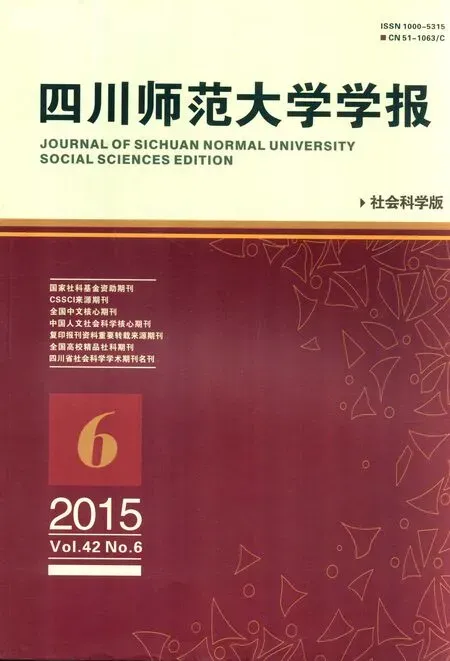河伯神话流变考释
李 进 宁
(四川师范大学 文学院,成都610066)
关于河伯神话的源流问题,学界长期聚讼纷纭,莫衷一是。王孝廉[1]、李立[2]等学者主张夏族集团说,何光岳[3]、林河[4]等主张东夷集团说。造成这种分歧的原因,主要是河伯神话在流传过程中出现的一些带有浓郁民族和地方特色的不同称谓,如冯夷、冰夷、无夷等。我们拟从文化和文献角度对河伯神话源流略作梳理,以就教于方家。
一 河伯史实考
文献载有河伯族人与其他民族的冲突和战争。《初学记》引《归藏》说:“昔者,河伯筮与洛伯战而枚占,昆吾占之:不吉也。”[5]48河伯族人为了拓展生存空间和掠夺更多人口,打算进攻洛伯族人,但战前卜筮的结果对己方不利。《竹书纪年》记载,夏帝芬十六年,“洛伯用与河伯、冯夷斗”[6]20。洛伯族人与河伯、冯夷二族联盟发生战争,反映了当时诸族中原逐鹿的历史事实。可知,有夏之时,河伯族已居于河洛之地,并且为争夺生存空间进行殊死搏斗。随后河伯族的势力逐步增强,其他部族如殷侯亦曾假借“河伯之师”讨伐与自己不共戴天的有易族,“殷主甲微假师于河伯以伐有易,灭之,遂杀其君绵臣也”[6]22。这说明此时的河伯族人已经具有一定的经济、军事实力以及强大的号召力和影响力。
那么,河伯族是原始土著还是异地来客?河南二里头遗址的考古发现解决了这一长期悬而未决的历史问题。考古专家根据相关出土文物的碳-14测定,确认曾经生活于此的河伯族具有明显的夏文化特征,而出土陶器等文物则具有大汶口文化的身影[7]。众所周知,发现于山东泰安的大汶口文化已被认定为新石器时代的文化遗存,是典型的东夷文化的代表。因此,据出土文物和传世文献综合考察,可以确定二里头文化是夏文化和东夷文化交流与整合的产物,而东夷文化的传播者应当是经过战争和联姻而占据河洛的河伯族人。他们凭借武器精良和英勇善战,获得了河洛的控制权,并且不失时机地把自己的风俗习惯、文化信仰等移植于此。另据何光岳考证[3]267-285,在夏代之前,河伯族人曾帮助大禹在黄河下游治水,并赢得广泛称誉和尊敬,河伯族人因此乘势一路向西,把自己的势力扩大至河洛之地。在经历无数次冲突甚至厮杀之后,“最终两族之间达成和解并结为秦晋之好,繁衍生息于河、洛之地”,这种“和亲”联姻方式促成了他们之间暂时的和谐稳定局面[8]149。于是,河洛一家,相安无事。但是,随着河洛文明的继续发展,东夷族一个分支——有穷夷羿携弓负箭由黄河下游沿河而上,摧城略地,势如破竹。在激烈争夺之后,夏后太康失国,而与之辅车相依的河伯族也岌岌可危。随后,有穷夷羿乘胜强掠河洛之地,追杀河伯并霸占其妻洛嫔。屈原《天问》对此疑虑重重:“帝降夷羿,革孽夏民。胡射夫河伯,而妻彼洛嫔?”[9]99这段历史的文献记载,在人们的心目中逐渐分化和变异:一方面,以这段历史为原型,在河伯原有图腾崇拜的基础上,于口耳相传的过程中演绎出曲折动人的神话故事;另一方面,遭到重创的河洛之民作鸟兽散,奔走呼号,他们铭记先祖的荣耀与辉煌,怀抱生的希望与信念,沿着陌生路途寻找自己的安身之所,诉说先祖的英雄业绩和对故土的留恋,形成了对列祖列宗的遥祭。
商周之际,河伯族人对周部族立国抚民功勋卓著,赢得了周王朝的信任和器重。周穆王时,河伯酋长掌管着周王朝祭祀河神的大任。“天子授河宗璧,河宗伯夭受璧,西向沉璧于河,再拜稽首。”“河伯号之帝曰:穆满,女当永致用时事。”[10]204河伯酋长在周王的授意下召集王公大臣向天言事,在神圣肃穆的祭祀仪式中表达“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11]797的家国理念。因此,王夫之认为“河伯,古诸侯,司河祀者”[12]53,是符合历史事实的。日本学者白川静也称:“河伯的祭祀原先好像是一个拥有特定传承的氏族的一种特权,被视为能够支配自然节奏的特定山川的信仰和祭祀。经常是和一个特定的氏族结合在一起,这些掌山川信仰与祭祀的特定氏族即是所谓的神圣氏族。”[13]100因此,当时的河伯族在国家特权的庇荫下获得了长足发展。
二 河伯神话考
学术界认可“河伯之说,本远古相传神话”[14]69的观点。纵观河伯族的发展历程,不难发现图腾化时代早已离他们远去,因而仅从称名上已无从寻找到自然神的踪迹。《初学记》引《援神契》释河伯曰:“河者水之伯,上应天汉。”[5]119根据约定俗成的解释,“伯”具有阳性特征,“河伯”当为阳性神。据此可推测河伯族已进化至父系氏族社会。他们或许率先脱离东夷集团走向更为广阔的生存空间,凭借其发展优势,在河洛之地称雄一方。
但是,太康失国,有穷夷羿对河伯族人进行了无情的杀戮。面对死亡的挣扎、心灵的创伤,原始思维和万物有灵观念极易激起他们对逝去灵魂的追忆,他们通过曲折离奇的神话传说渲染诠释先祖功勋,体现永志根本之意。王逸在注解《楚辞·河伯》时所引古老传说最具说服力:“河伯化为白龙,游于水旁,羿见射之,眇其左目。河伯上诉天帝,曰:‘为我杀羿。’天帝曰:‘尔何故得见射?’河伯曰:‘我时化为白龙出游。’天帝曰:‘使汝深守神灵,羿何从得犯?汝今为虫兽,当为人所射,固其宜也,羿何罪欤?’”[9]99河伯化为白龙,被夷羿射瞎左眼,诉诸天帝,天帝没有为他伸张正义。这则流传于南方的神话故事,已经具备非常完整而生动的故事情节和文学色彩。不仅如此,这则神话故事还传达其他一些信息:河伯是水中神灵的守护者,它已经脱离了自然神的“虫兽”之类,达到了神话发展的较高形态。我们还可以溯源而上,寻找更为古老的演变原型。西汉刘向《说苑·正谏》记载:“吴王欲从民饮酒,伍子胥谏曰:‘不可。昔白龙下清泠之渊,化为鱼,渔者豫且,射中其目,白龙上诉天帝……’”[15]237这可视作王逸注说的渊源。《庄子·外物篇》亦称:“宋元君夜半而梦人被发窥阿门,曰:‘予自宰路之渊,予为清江使河伯之所,渔者余且得予。’元君觉,使人占之,曰:‘此神龟也。’”[16]933可见,关于河伯的神话在周时流传甚广。由于吴楚神话和庄子所记均有“鱼”、“鳖”等水族形象和“渔者”的身影,这样河伯神话原型便更加清晰地展现在我们面前。先秦其他文献关于河伯故事的记载亦甚夥。《晏子春秋》载:“齐大旱,景公召群臣问曰:‘寡人欲祀河伯,可乎?’晏子曰:‘不可。河伯以水为国,以鱼鳖为民,彼独不欲雨乎?祀之何益。’”[17]56此处河伯具有“主雨”的神性,对河伯的祭祀表现了人们冀神赐福的功利目的。虽然晏子极力反对祀河伯,却反映了自然神的客观存在。另外,齐国勇士古冶子杀鼋和《韩非子》所记“河伯,大神也”[18]218均具此种性质。即使河伯的侍从也具有水族类的标识。《古今注·鱼虫》载:“鳖名河伯从事。”[19]128《初学记》引《南越记》曰:“乌贼鱼,一名河伯度事小吏。”[5]742从以上记载可知,人们认为“鱼”“鳖”乃河伯魂附之物,而诸多水族之属前簇后拥,伴随左右,则表明河伯具有动物的某些特征,这为我们把河伯定位为自然神提供了依据。
赵辉认为:“神话在不同的历史阶段表现为不同的形态。它有一个由动物神到半人半神、再到人格神的发展历程。”[20]75河伯与“鱼”的关系,我们也可以视其为河伯族人的自然神话。这也恰恰验证了王孝廉所说:“古代人最初信仰的神,是他们生活周边的敬畏或具有实益的动植物和自然现象,其后随着人的自觉意识的提高,人们所祭祀的神也逐渐由完全的动植物等转化为半人半兽的神。”[21]45《尸子》所描写的河神即为人面鱼身,具有半人半神的神格特征。“禹理水,观于河,见白面长人,鱼身,出曰:吾河精也。”[22]167《酉阳杂俎》亦载:“河伯人面,乘两龙,一曰冰夷,一曰冯夷。又曰人面鱼身。”[23]77这些记载说明,河伯除了具有鱼的特性,还有人的性格和面貌,实现了从纯动物向人面鱼身的过渡。这是神话形态的一种飞跃,是古人思维模式的重大转变与革新,是人类文明的进步与升华。
由上可知,春秋战国时期的河伯神话已经广泛流传并深入人心,而且其神格已经摆脱原始意义的神话色彩,具有了人的思想和情感。《庄子·秋水》曰:“秋水时至,百川灌河……河伯欣然自喜,以天下之美为尽在己。”[16]561河伯与海神若的一番辩论,体现了智者之思。而真正把河伯形象在历史和神话基础上进行艺术加工并糅合在一起的当是楚人屈原。屈原因谗见疏,被贬于湘、沅之地,目睹世俗所祭,遂作《河伯》以寄哀怨之情和鸿鹄之志。“与女游兮九河,冲风起兮横波。乘水车兮荷盖,驾两龙兮骖螭。登昆仑兮四望,心飞扬兮浩荡。日将暮兮怅忘归,惟极浦兮寤怀。鱼鳞屋兮龙堂,紫贝阙兮朱宫。灵何为兮水中,乘白鼋兮逐文鱼。与女游兮河之渚,流澌纷兮将来下。子交手兮东行,送美人兮南浦。”[9]76-78河伯与南浦女乘上水车,驾驭螭龙,逍遥自在地神游昆仑之墟,而后闲庭信步于龙堂朱宫,此种闲情逸致表现了诗人在河伯形象上所寄寓的某种理想或情愫。然而,南浦送别,执手相看泪眼,不免使河伯徒增几分忧伤和落寞。诗人通过对河伯内在神性和外在形象的描绘,完成了河伯人格化和理想化的蜕变。这样,屈子笔下的河伯神话已经具有人格神的特质,标志着它已步入了高级形态神话的发展阶段。
三 冯夷、冰夷、无夷等神话传说考释
从文献记载看,“河伯”还有多种称谓,如冯夷、冰夷、无夷等,这些称谓应当存在内在联系。《山海经·海内北经》载:“昆仑虚南所,有氾林方三百里。从极之渊深三百仞,维冰夷恒都焉。冰夷人面,乘两龙。一曰忠极之渊。”[24]369这里的“冰夷”具有人面、乘两龙的神态特征,说明它已经发展到了半人半神的自然状态;所居之地为“从极之渊”,从地理特征看,应在阳纡和陵门山一带,即今渭河下游和黄河河曲一带,它应是当地的水神。那么,这个半人半神的冰夷又是如何产生和发展演变的呢?
李立认为:“在先秦文献所记载的河神话传说中,有河伯神话,有冰夷传说,河伯与冰夷相合者并不多见。”[25]52可见,冰夷神话传说自成体系。但如果对“冰夷”称名略作分析,不难发现其与“河伯”具有同质性。先看“冰”字。许慎《说文解字》:“冰,水坚也,从仌,从水。”[26]240我们把“冰”与“冯夷”的“冯”的语源学结构做一比较。《说文解字》:“冯,马行疾也。从马,冫声。”[26]200左边两点是“冰”,做“冯”的声部。检《宋本广韵》“冯”“冰”同属下平十六“蒸”韵之“凭”韵部[27]179,古音中两字是极为接近的。因此,《山海经》中的“冰夷”极有可能就是“冯夷”。再看“夷”字。“夷”字蕴含着浓郁的地域性和族源性色彩。《周礼》:“东方曰夷,被发文身。”[28]2637《大戴礼记》:“东辟之民曰夷。”[29]162《说文解字》:“夷,东方之人也。”[26]8《竹书纪年》亦载,天下九夷彼此消长,荣衰于中原与边疆,“后芬发即位,三年,九夷来御”[6]19。《后汉书·东夷传》:“夷有九种:曰畎夷、于夷、方夷、黄夷、白夷、赤夷、玄夷、风夷、阳夷。”[30]2807从文献看,九夷形成于山东半岛,随着东夷逐渐强大,东夷一些支族陆续迁移至周边区域,甚至于黄河上游,最后畛域渐消,文化信仰也融合于华夏族。“夏侯氏太康失德,夷人始畔……武乙衰敝,东夷浸盛,遂分迁淮、岱,渐居中土。”[30]2808由此可知,冰夷即为冯夷,与河伯同出东夷。关于冯夷的神话传说流传也颇广,如《淮南子》:“昔者冯夷、大丙之御也,乘云车,入云蜺,游微雾,骛怳忽,历远弥高以极往。”[31]8《水经注》引《括地图》称:“冯夷恒乘云车驾二龙。河水又出于阳纡凌门之山,而注于冯逸之山。”[32]3这里的冯夷“乘云车,驾二龙”与冰夷“人面,乘两龙”异常接近,因此郭璞注《山海经·海内北经》曰:“冰夷,冯夷也。”故我们更有理由相信“从极之渊”就是冯夷(冰夷)神话传说产生和流传的发源地。当然,随着民族融合、文化交流,使它在独立发展的同时,也逐渐融入他族文化。这进一步说明,部族文化的相互渗透和兼容,仍然裹挟着最初的地域风貌和原始文化内涵。正如李诚所说:“神话传说的特点之一,即在于流传过程中,几乎任何一个故事都会产生一些异说、歧说。但是既然产生于一个母体或母本,也就有极大可能在典籍和口头传说中不知不觉留下其内在的可能是带有规律性的共同点和联系。”[33]8所以,诸多典籍多以“冯夷”称代“冰夷”。如《楚辞·远游》:“使湘灵鼓瑟兮,令海若舞冯夷。”[9]8《庄子·大宗师》:“冯夷得之,以游大川。”[16]8这种称名一旦形成,便深入人心,在流传中很难从部族的记忆中抹去,这种半人半神的神格给予我们无尽的想象和深思。
关于“无夷”,学界一般认为它是东夷集团所属方国——当时生活于黄河下游的部族“蒲夷”的别称。《山海经·北山经》:“又北五百里,曰碣石之山。绳水出焉,而东流注于河,其中多蒲夷之鱼。其上有玉,其下多青碧。”[24]118《西山经》:“冉遗之鱼,鱼身蛇首六足,其目如马耳。”[24]73郝懿行《山海经笺疏》:“《太平御览》九百三十九卷引此经作无遗之鱼,疑即蒲夷之鱼也,见《北次三经》碣石之山下;蒲、无声相近。夷、遗声同。”[24]74据此,“无夷”或即“蒲夷”。当蒲夷之民沿河西迁之后,也把自己部族的信仰带到了河渭之地。《穆天子传》:“戊寅,天子西征,骛行至于阳纡之山。河伯无夷之所都居。是惟河宗氏。”[10]58这一方面说明河伯无夷称名上已经统一、无夷文化信仰已经隶属于河伯文化的事实;另一方面说明穆王西征时曾经到达河伯无夷所居的阳纡山,而这里正是河伯无夷祭祀河源的圣地,也是他们通向传说中的昆仑山的必经之地。《淮南子》:“禹之为水,以身解于阳纡之河。”[31]1317据“河伯无夷”之连称,可知此时的民族风俗和文化信仰已经完全融合并同化于河伯文化信仰。
综上,冯夷、冰夷、无夷等部族在民族融合之前均有一个相对独立的发展时期,他们散居于黄河沿岸,形成不同的神灵崇拜和神话传说。虽然名称各异,情节有别,但他们又都从属于东夷集团,拥有大体相同的神灵观念。正如何新所说:“在原始先民的文化中,神话并不是一种单纯想象的虚构物,一些或有趣或荒谬的故事。神话本身构成一种独立的实体性文化。神话通常体现着一种民族文化的原始意象,而其深层结构,又转化为一系列观念性的母体,对这种文化长期保持着深远和持久的影响。”[34]289因而其神灵的神态特征和生活习性,大都与黄河相关,这些自然神可以视为其方国的起源神。白川静总结道:“当时散布在黄河及其支流的民族,各有各自的洪水神话与祭祀的水神及各别的祭河仪式。”[13]100随着东夷西进、西夏东上步伐加剧,以及兼并战争愈来愈频繁、民族融合步伐越来越快,丰富多彩的民族文化逐渐融为一体,如河伯冯夷、河伯无夷等称谓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发展而来的。
四 河伯神话与其他神话的整合与发展
河伯神话源远流长,在长期的民族迁徙、斗争和联姻中逐渐形成了以河伯文化信仰为主、其他诸夷文化信仰为辅的兼容并包的格局。这不仅有利于多民族国家的祭祀活动,而且有利于部族的多元发展。我们所看到的河伯形象更多地体现了华夏各族由原始野蛮走向文明开化、由多神走向一神、由分散走向统一的历史趋势。史实证明,禹夏之时,河伯诸神话已经出现了重组与整合的端倪。如《竹书纪年》:“洛伯用与河伯冯夷斗。”[6]20《穆天子传》:“阳纡之山,河伯无夷之所都居。”[10]58这些记载说明冯夷及无夷族已经迁徙至中原腹地,在族际间的文化交融中,占绝对优势的河伯文化以其强大的吸引力和包容性,覆盖了冯夷和无夷的文化信仰,出现了二者连用的称名。这种联合方式在共同发展中保留了各自的特质,他们共同承载了不同的文化积淀。这是黄河流域各部族相互斗争和融合的结果,也是他们在经济或文化方面共通和互补的迫切需要,更是社会发展不断前进的必然选择。
经过多次民族大融合,河伯文化得到了长足发展,在夏、商、周三代较为正式的国家祭祀中,河伯神往往作为国家整体概念上的主宰神灵出现在祭祀场合,俨然成了一个国家同宗共祖的标志。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中国早期神话一个明显的特点:即神话演变中的那种巨大的内聚力,它以神格为中心,将其相似和相关的内容加以改造而向它聚合。但是,后来随着社会的发展,神话人物逐渐定型化,功能越来越明确,那种模糊性、交叉性逐渐消除,代之以职能性的专职神的产生。”[35]87这种趋势一直延续到秦并天下,随着诸侯咸服,天下合一,始皇帝命令祠官按照常奉次序祭祀天地诸神,其中有“水曰河,祠临晋”之称,这里用“河”代替带有地方色彩的“河伯”或“冯夷”,使之更具整体概念意义,显得更为庄重和神圣。到汉宣帝时,更具抽象意义的“四渎神”被正式列于国家祭典。这样,长期以来具有恤民安国之称的骄子形象的河伯逐渐退出历史舞台,隐去曾经耀眼的光环,落拓于乡间野舍,最终在佛道的巨大影响下华丽转身:或附于惩恶扬善的娑竭龙王之身,接受民间的祷告和朝拜;或离开神话传说的桎梏而羽化登仙,在虚无缥缈的天国寻找自己的神龛。诚如宋赵彦卫所说:“《史记》西门豹传说河伯,而《楚辞》亦有河伯祠,则知古祭水神曰河伯。自释氏书入中土有龙王之说,而河伯无闻矣。”[36]178从河伯在中原的发展情况看,这种说法具有一定的历史根据,也是合乎历史逻辑的。然而,河伯冯夷神话的仙话化则是在道家及道教思想的改造下完成了历史使命。
秦汉魏晋时,道家仙术蔚然成风,人们试图通过对古代神话故事的改造,来演绎羽化登仙、长生不老的人生。因此,他们对河伯冯夷神话进行了删改和增补。首先,将尚未完全人格化的神改造成形神兼具的人,这些神祇拥有了名姓和籍贯。其次,由原来半人半神改造成不食人间烟火的仙人形象。《后汉书·张衡传》李贤注引《龙鱼河图》:“河伯姓吕名公子,夫人姓冯名夷。”[30]1925《楚辞》王逸注引《抱朴子·释鬼》:“冯夷以八月上庚日渡河溺死,天帝署为河伯。”[9]78又引《清泠传》:“冯夷,华阴潼乡隄首人也。服八石,得水仙,是为河伯,一云以八月庚子浴于河而溺死,一云溺死。”[9]78《搜神记》卷四:“弘农冯夷,华阴堤首人也。以八月上庚日渡河溺死,天帝署为河伯,又《五行书》曰:‘河伯以上庚辰日死。不可治船远行,溺没不返。’”[37]8这些记载向我们展示了河伯冯夷仙话的形变及演化过程:他是弘农华阴人,也就是冰夷神话传说的发源地,他或溺河而死成为水仙,或修行得道服药成仙。在道教的大力改造和重组中,河伯冯夷终于得道成仙,顺利完成了由神话传说向仙话的过渡。这样,具有浓厚仙话色彩的河伯冯夷终于跳出了神话传说的藩篱,走向了新的历史舞台。为了抬高河伯神的地位,道教还给它安排了神位。《真灵位业图》曰:“太清右位:河伯。”[38]84《历代神仙通鉴》卷十五:“黄河:澄静尊神河伯。”[39]848河伯的使者也被《神异经·西荒经》描写成白衣玄冠如风似飞:“西海水上有人乘白马,朱鬣白衣玄冠,从十二童子,驰马西海水上,如飞如风,名曰河伯使者。”[40]96至此,神话中的河伯形象在人们虔诚的祷告中堂而皇之地走向了仙话世界。
五 结论
由上述考证可知,河伯神话传说的发生发展及逐渐淡出人们视野的过程,正是人类社会从万物有灵的图腾崇拜到历史意识和主体意识逐渐觉醒的过程,它昭示着原始信仰的终结和宗教热情的冷却,也说明“人类由多神崇拜到一神崇拜,由对自然神的崇拜到祖先神的崇拜,又由祖先神的崇拜发展到对本族英雄的崇拜,是同生产力和社会发展相适应的”[41]138规律。同样,在夏、商、周三代由河伯族人所主导的以河神为尊的国家祭祀,也是这种规律的客观反映。不可否认,入主中原前,河伯神话传说是从东夷集团裂变而生,充其量它只是原始意义上的自然神话,是万物有灵观念的产物。但是,当它走向中原腹地,同其他部族密切联合形成了新的共同体之后,也就形成了新的民族意识和文化信仰,尤其是举族生死存亡之际,更能激起他们的民族认同感,因而又形成了半人半兽或者完全意义上的人格神的神话。
纵观典籍所记,河伯化为白龙遭射以及屈原所刻画的“乘水车、驾两龙”的河伯形象,冯夷“乘云车、驾二龙”与冰夷“人面、乘两龙”的神态勾勒,均有着相似的特质和容貌,不得不使人认为他们就是融各部族神话传说于一身的河伯神话。而那些不同的称名,则反映了他们在重组、整合与发展过程中,并非简单地以一种文化取代另一种文化,而是两个或数个不同文化圈的文化元素的交融与组合。因而,从社会发展规律来看,河伯神话的进一步发展和流传就是华夏各民族彼此融合与发展的缩影。随着秦朝一统天下和佛教进入中土,各种意识形态也在相互碰撞中寻找着自己的归宿,由于统一的多民族文化信仰的共同需要,河伯的宗主地位遭到了质疑、排挤,进而被更具抽象意义的“四渎神”所取代。
[1]王孝廉.中国的神话与传说[M].台北:联经出版社,1977.
[2]李立.文化整合与先秦自然神话演变[M].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02.
[3]何光岳.东夷源流史[M].南昌:江西教育出版社,1990.
[4]林河.《九歌》与沅湘民俗[M].北京:三联书店,1990.
[5]徐坚.初学记[M].北京:中华书局,1962.
[6]李民,等.古本竹书纪年[M].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89.
[7]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二里头工作队.河南堰师市二里头遗址中心区的考古新发现[J].考古,2005,(7).
[8]李进宁.论“河伯”形象的文化意蕴[J].文艺评论,2014,(10).
[9]洪兴祖.楚辞补注[M].北京:中华书局,1983.
[10]山海经·穆天子传[M].郭璞注,张耘点校.长沙:岳麓书社,2006.
[11]《十三经注疏》整理委员会.十三经注疏·毛诗正义(上)[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
[12]王夫之.楚辞通释[M].北京:中华书局,1975.
[13]〔日〕白川静.中国神话[M].王孝廉译.台北:长安出版社,1983.
[14]刘永济.屈赋通笺[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1.
[15]向宗鲁.说苑校证[M].北京:中华书局,1987.
[16]郭庆藩.庄子集释[M].北京:中华书局,1961.
[17]吴则虞.晏子春秋集释[M].北京:中华书局,1962.
[18]王先慎.韩非子集解[M].北京:中华书局,1998.
[19]崔豹.古今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
[20]赵辉.楚辞文化背景研究[M].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1995.
[21]王孝廉.水与水神[M].北京:学苑出版社,1994.
[22]李守奎,李秩.尸子译注[M].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3.
[23]段成式.酉阳杂俎[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
[24]袁珂.山海经校注[M].成都:巴蜀书社,1992.
[25]李立.文化整合与先秦自然神话演变[M].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02.
[26]许慎.说文解字[M].北京:中华书局,1963.
[27]陈彭年,等.宋本广韵[M].北京:中华书局,1982.
[28]孙诒让.周礼正义[M].北京:中华书局,1987.
[29]王聘珍.大戴礼记解诂[M].北京:中华书局,1983.
[30]范晔.后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65.
[31]何宁.淮南子集释[M].北京:中华书局,1998.
[32]陈桥驿.水经注校证[M].北京:中华书局,2013.
[33]李诚.屈赋神话传说三题[J].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89,(6).
[34]何新.诸神的起源(第一部)[M].北京:中国民主法治出版社,2008.
[35]熊良智.《楚辞》后羿形象思考[J].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0,(6).
[36]赵彦卫.云麓漫钞[M].北京:中华书局,1996.
[37]干宝.搜神记[M].汪绍楹校注.北京:中华书局,1979.
[38]陶弘景.真灵位业图校理[M].王家葵校理.北京:中华书局,2013.
[39]徐道.历代神仙通鉴[M].沈阳:辽宁古籍出版社,1995.
[40]张华注.神异经[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
[41]潜明滋.中国古代神话与传说[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