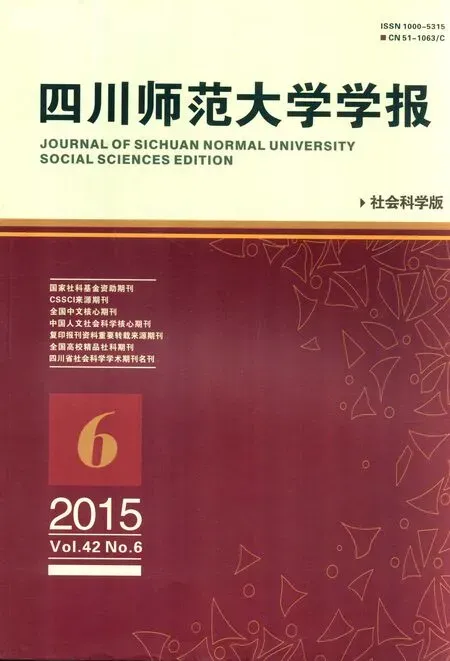日本法西斯统治与大政翼赞体制
张 东
(东北师范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长春130024)
日本法西斯曾给中国人民带来了沉重灾难,国内学术界对日本法西斯的思想源流、意识形态统制、右翼法西斯主义团体思潮及行动等方面已做了深入的批判性研究,揭示了近代天皇制的军国主义传统和军部在法西斯统治中的主导作用①。但遗憾的是,对于日本法西斯统治的内在构造——大政翼赞体制,却鲜有深入探讨。本文即从日本大政翼赞体制的产生及其与明治宪法的关系来考察、辨明大政翼赞体制的实质,以期深化对日本法西斯的认识。
一 大政翼赞——对政党政治的反动与否定
1932年5月,犬养毅内阁辞职,元老西园寺公望推荐海军大将斋藤实组阁,八年的政党政治告终。由于腐败、政策无力及选举舞弊等,此时政党主导政治的正当性急剧减弱,民众对政党的态度十分消极,“腐败案件也常引起社会关注,中央及地方议会的宪政精神变弱,国民对议会的感情日渐消退”[1]339,“政友会与民政党好像突然间就成了国民之仇敌”[2]15-16。
从斋藤实内阁开始,政府常标榜举国一致和政治革新,因此也被称为“举国一致内阁”。所谓“革新”,主要在于两个方面。一是调整内阁与议会关系,保障国策决定的独立性。以后藤文夫为代表的新官僚与军部联合,填补政治空白,力求避免政治变动对国策和行政的影响。其典型机构便是冈田启介内阁的内阁审议会,“在举国一致下聚集人才,作为政府的企划和咨询机关,在内阁更迭时保持国策一致”[3]13。二是展开“选举肃正”以疏通民意,强化对选举活动的管制,标榜公平选举,企图恢复民众对议会的信任。
但这两个方面却处于分离状态。正如新官僚田泽义铺称:“天皇通过众议院选举而明了社会公论,若有政治家的主张与大多数国民希望相一致,天皇就任命他组阁,这就是立宪政治之常道。”[4]131那么,由谁来确定政治家的主张是与大多数国民相一致呢?在政党政治时期,民意通过政党政策在议会中表达出来,然后由政党执政而得以实现;但在政党政治崩溃后,虽然民意仍可通过选举表达出来,却没有了承载和实现它的政治主体,因为制定国策的新官僚并不是由民众选举出来的,也就是说,内阁与议会之间出现了正当性的割裂。近代著名的哲学家户坂润认为:“举国一致下的国民并非实际的国民,而是假设虚拟的国民。”[5]115-124历任法制局长官、农林大臣、众议院议长的政友会议员嶋田俊雄亦严厉批判称:“哪个国家会无视民意,除去议会第一大党和众议院绝对多数党而实现举国一致内阁呢?”[6]2-3
此时,只有以充分的民意为政治基础组阁,政局方能安定,但举国一致内阁下的“政治革新”未能成功,并没有产生出承载和实现民意的政治主体。此时政界有一共识:若要获得民众支持,就必须“超越一切政党斗争,超越一切阶级斗争”,“只有国家主义大众党才能成为日本克服国际重压的中心势力”[1]341。例如,秋山定辅、久原房之助等展开一国一党运动,建川美次、小林顺一郎则企图成立右翼新党。尽管新党运动兴起,但政友会与民政党却在此过程中愈加弱化。
1936年11月,日德防共协定签订,日苏关系紧张,军部急需强化国防,寺内寿一陆相、永野修身海相也希望有新党支援。12月,陆军的林铣十郎大将、海军的安保清种大将、金融资本代表的结城奉太郎、民政党的永井柳太郎、昭和会的山崎达之辅、政友会的中岛知久平、前田米藏、新官僚的后藤文夫等,在荻窪的有马赖宁家中会谈新党事宜,即“荻窪会议”,欲推举近卫文麿(1891年10月12日-1945年12月16日)为总裁,但近卫认为,“新党运动若仍以原有团体为基础,则不能有效吸纳其他民众,也无新的纲领整合全体国民”[7]11,他所寻求的是整个体制的全方位转换。近卫还反省举国一致内阁的弊端,认为它缺乏民众基础:“连接统帅与国务的只有陆军大臣,因而陆军大臣掌内阁死穴,国务不过受统帅操纵而已,国民生活外交政策也与国民舆论相分离”,“各政党不能抑制军部,因此,应以国民为基础,成立与原有政党不同的国民组织,进而成立政府,抑制军部并解决战争”[8]24-26。
1940年7月,近卫在第二次组阁后发表政党观,认为:“之前政党有两个弊端,一是立党宗旨中的自由主义、民主主义、社会主义等世界观和人生观,与我国体不符;二是党派目的在于争夺政权,有碍议会翼赞大政之道”[9]134。随后,近卫内阁发表《基本国策要纲》:“基于国体本义,庶政一新,确立国防国家体制基础”,欲建议会翼赞体制和新的国民组织。8月28日,在新体制准备委员会上,近卫首相称:“高度国防国家的基础在于国内的强力体制”,“它非一个内阁、党派或个人的临时性需要,而是强力贯彻政策的经常性需要”,其关键就在于实现“下意上达、上意下达”;他批判过去的政党“代表个别、局部利益”,而“国民组织运动则超越自由主义下的多元性政党政治,其本质是举国性的、全体性的和公共性的”,是“包括政党、政派、经济团体、文化团体等,公益优先的超政党国民运动”,“不允许部分的、对抗的和竞争性的政党运动”,同时,新体制以有违一君万民之国体本义为由否定“一国一党”体制[10]23-27。新体制运动对之前的政党政治抱有强烈的批判和否定态度,其政治性十分明显。
所谓“高度国防国家”,其实就是“出于国防目的而一元化统合所有势力,它所保护的不是个人或特定集团利益,而是全体利益”[11]38,是国民基础与政治构成的根本性变化,其底层则是对自由主义政治原理的反动。因为,在自由主义政治观下,政党与选民间的关系是流动性的,但大政翼赞运动需要的是运动组织与国民间的恒久稳固,避免因选举而产生利益分歧和过度竞争。
二 大政翼赞会的违宪问题
1940年10月12日,大政翼赞会成立,近卫首相出任总裁。大会同时发布了《大政翼赞运动规约》,并确定机构组织。12月14日,《大政翼赞会实践要纲》发布,其中明确规定:“树立天皇归一、物心一如之国家体制”,本会“与政府乃表里一体之协力关系,上意下达、下情上通以实现高度国防国家体制”,内容则包括:挺身实践臣道,建设大东亚共荣圈,建设翼赞政治、经济体制,建设文化、生活新体制[12]96-97。
最初的大政翼赞会组织相当复杂,上设中央本部事务局,下有地方支部,中央本部事务局分为总务局、组织局、政策局、企划局、议会局等五局;同时,设置中央和地方协力会议,负责“下情上通、上意下达”。中央本部事务局的职务多由政府人员充任,其目的就在于实现综合统制,当时很多人都认为应通过翼赞会的高度政治性来完成“臣道实践”[13]13-14。
但是,在1941年1月召开的第76届议会(又称“翼赞议会”)上,大政翼赞会的政治性却成了重要议题,议员对大政翼赞会的人员构成、宪法地位及其性质等问题进行了讨论。如众议院议员川崎克基于《宪法义解》中的“大政施行必须出自内阁及其各部,立宪目的在于将主权使用在正确轨道上去,即通过公议机关与宰相辅弼”,认为在议会及国务大臣之外不能施行大政,若将大政翼赞会作为贯彻政府政策之机关,是“与宪法精神不符”;对此,法制局长官村濑直养回答:“统治的根本组织自然是公议机关及内阁国务大臣,但所谓大政翼赞,要比法律上的作用扩展一些,所谓天皇统治,指臣民奉天皇之命并向天皇归一,从而实现统一翼赞天皇,天皇乃国民及国土所有者,广义上说的大政翼赞,并非是法律之形式所定。”[14]36-38但川崎克仍持批判态度:“细究其机构,有模仿德意志纳粹和俄国苏维埃的痕迹,给人一种混血儿的感觉”,并强调其政治性,“不免有治外法权而与天皇对抗,或成为过激思想之温床”[14]81-82。
在2月8日的众议院预算总会上,近卫首相对大政翼赞会的宪法性质做统一答辩,承认翼赞会“与宪法上负有辅弼之责的国务大臣及行政各部是表里一体的关系,辅助协力,并无独立政见,不能确立政策,强制或支配国家机构”,只是用来贯彻政府政策和上通国民意思,并且翼赞会“不是政事结社,所以不适用《治安警察法》第五条,它是公事结社”,“不是政党政治时代的那种以争夺政权为目标的政治,亦非与之相伴随之政治,但在实现广泛行动目标以革新国内全体上来说,有其政治性和政治力,而与狭义的政治无关”[15]98-100。为什么强调其非政治性呢?因为《治安警察法》第五条对“政事结社”作出规定:“现役及召集中的预备役后备役陆海军人;警察;神官神职官僧侣及其他宗教师;官立公立私立学校教员及学生;女子;未成年者;剥夺或者停止公权力者”等七种人不得加入[16]502。如果大政翼赞会有政治性,从而作为“政事结社”的话,上述七种人就会被排除在外,它也就不可能是“全体国民翼赞之运动”,因此也就与之前的政党没有本质区别。
与此同时,大政翼赞会在社会舆论中也引起了宪法论争。京都大学法学教授佐佐木惣一发文批判翼赞会,其要点有两个:“第一,规约规定总理大臣出任总裁,而且其他国家机构也多数参与,大政翼赞会与政府表里一体,因此,它应是国家团体,属政事结社”;“第二,总理大臣出任总裁的话,他有可能与天皇对抗,这就有违宪法精神和国体”[17]255。因为,大政翼赞会总裁与总理大臣一致的话,就等于是大政翼赞会总裁直接负责国政;而且,若规定大政翼赞会总裁出任总理大臣的话,天皇的任命大权实际上就被否定了,这也与明治宪法明显矛盾。但是,京都大学教授黑田觉却明确提出了大政翼赞会的合宪性,他认为:“翼赞会不是由部分国民结成的政治团体,而是‘官民协同的国家事业、全体国民翼赞之运动中坚’”[11]34,“翼赞会并不是与国务大臣的辅弼及帝国议会的协赞相并列,独立进行有法律效果的翼赞”,“翼赞会只是在政府与议会之间内在联络,促成改善辅弼及协赞,防止因为偶然误解或意见缺乏疏通造成的政府与议会间的对立,但政府与议会并不受翼赞会的法律性约束”[11]35。学者山崎又次郎对黑田觉的合宪论提出严厉批判:“概念法学的宪法学者却对大政翼赞会表示满腔赞意,这种学者若非投机分子,便是学术自杀者”[18]371。
鉴于议会及社会舆论中的批判,近卫内阁不得不在1941年4月2日发布大政翼赞会机构改组,废止了政治性强的政策局、企划局以及议会局,避免违宪质疑,纯化大政翼赞会的“公事结社”性质。如此一来,大政翼赞运动便失去了承载民众意思的政治主体,大政翼赞会游离于宪法机关之外。而要将大政翼赞会合宪化,唯一的途径便是通过选举将大政翼赞会的意思输入到议会。
1941年10月16日,现役陆军大将东条英机(1884年12月30日-1948年12月23日)出任首相,同时兼任内务大臣与陆军大臣。随着对英美宣战,东条内阁强化统制,2月18日,内阁决定实施“大东亚战争,完成翼赞选举贯彻运动”,以阿部信行大将为首,贵众两院、大政翼赞会、财界、在乡军人、言论界等各界代表三十多人集会,结成翼赞政治体制协议会,并在地方建立支部,确立了“推荐选举制”。结果,翼赞政治体制协议会推荐的候选人有八成当选,在众议院的466名中占据381名,其中新人占到199名,军部出身者、产业报国人士、翼赞会相关者、大陆建设者等多有当选,如中野正刚、桥本欣五郎、赤尾敏等,翼赞会成员,“特别是一道府县壮年团长、庶务、组织部长等地方组织运动的实力派多有当选;二是道府县常务委员、协力会议议长、郡市支部长等地方代表人物”[19]238。选举结束后,翼赞政治体制协议会解散。5月20日,在大东亚会馆成立了翼赞政治会,参加者有阁僚、贵众议员(除皇族外)以及财界、言论界、大政翼赞会等代表一千余名。与此同时,所有政治结社解散,翼政会成为划时代的举国性政治团体。
在成立翼赞政治会的同时,东条内阁将产业报国、农业报国等运动组织以及刷新选举、奖励储蓄、健民运动等行政机关统统纳入大政翼赞会,并实施机构改组,以新方针、新人事、新机构来强化国民统制。东条内阁通过选举实现了大政翼赞会与议会的连结,将大政翼赞会意志转化为宪法机关上的意志,“臣道实践”正式进入宪法体制。
三 大政翼赞的本质:天皇制国体与明治宪法的融合
1935年,在右翼、在乡军人及部分政党的主导下,日本开展“国体明征运动”②,其终极目标是“从根本上改正机关说及其相关典章文物制度,使之与国体相一致,显扬日本精神,以彰显皇国日本之真姿”,使天皇与国民融为一体,国体与政体相一致,“天皇与臣民在命令服从、统制扶翼、指导奉教、慈民归衣、祈祷报恩等精神轨道上团结以进行政治活动,其中心便是天皇政治,从道的观念上说是皇道政治,从国体上说就是国体政治”[20]。然而,所谓的大政翼赞又为何会违宪呢?东条内阁成立的翼赞政治会又有何种意义呢?
(一)皇道扶翼——大政翼赞的正当性
国体明征运动后,文部省在1937年发布《国体之本义》称:“大日本帝国由万世一系之天皇奉皇祖神敕而永久统治,此乃我国万古不易之国体,基此大义,作为一大家族国家奉体亿兆一心之圣旨,尽忠克孝,发扬美德,此为我国体之精华,国家永久不变之大本”[21]9;用《教育敕语》精神来解释明治宪法第一条,“天皇不只是外国所谓的元首、君主、主权者、统治权者,而是现御神基于肇国之大义统治国家”[21]132-133;帝国宪法“不是权力关系的永固化与规范化,也不是民主主义、法治主义、立宪主义、共产主义、独裁主义等抽象理论或者实际要求之制度化,也不是移植模仿外国制度,而是彰显皇祖皇宗遗训之统治洪范”[21]128-129。政体也“不是委任统治,不是英国式的统而不治,不是君民共治、三权分立和法治主义,而是天皇亲政”;排除单纯的强制性统治权,将历史性和社会性的伦理道德融入天皇统治大权,“宪法第一条的重点在于万世一系,这是外国所没有的”,“它是阐明我国体世界无比,不单单是统治权的规定”[22]139-140。这就凸显了天皇制国体与欧美国家近代化政体的区别。
在当时人看来,天皇统治与纳粹主义本质不同。纳粹强行一国一党,偏重权威,不存在共同社会的家族国家,民族精神难以结合,“其政治受经济支配而毫无目的,是以个人主义强者为本意的征服、榨取、反抗、斗争的政治,是实现强者利益,美化征服、支配、榨取的欺瞒性手段”[23]173,所以,“因其历史传统与社会环境,现实中霸道色彩浓厚”[22]94-99。日本的天皇统治则被认为是历史事实,是家国一体的,所施行的政治是神道政治、皇道政治,是“臣民自由充分发挥能力并归于天皇的皇道扶翼政治”[24]48。
所谓“皇运扶翼”,也就是《大政翼赞会实践要纲》中的“实践臣道”,“它内在于我国国体,内在于国体精神、皇道主义超人格主义的国家本质之中,是皇民存在之核心”,它既是日本臣民对天皇自然而强有力的尊崇之情,也是臣民的生命法则和最高伦理规范,“臣道实践”与国民历史和生活融为一体[25]150-151。这样的话,日本国民不是消极地被统治,而是积极实践臣道以扶翼天皇统治,天皇是民族和国家的中心,与国民融为一体,天皇与臣民同心一体,天皇统治需臣民扶翼,臣民需以天皇为中心,二者不再是单纯统制与被统制的对立关系,而是“亲密无间”的。所以,必须清算阻隔天皇与臣民的政党政治和官僚政治,“国家的思想与经济实现一元化组织,彻底发挥国民总力”,“上有天皇亲政,下有国民扶翼,这样才会有强力的皇国政治”[24]73。
而所谓新体制,就是要实现民众参与天皇政治,是“万民翼赞实现亿兆一心之体制,不单是政治翼赞,而是所有职业领域上的翼赞”,国体中的伦理道德与宪法规范融合,“超越了既有的公法和私法观念,很难用偏重国家与个人意志的既有法学观念来说明”[26]386,伦理道德超越了一切规范。因此,大政翼赞不能受到欧美法思想中的政治性约束,它在国体上有其正当性和必要性,而现实中的大政翼赞运动就成了打破政党政治和官僚政治的必要实践。当翼赞会在近卫内阁受挫时,军国主义法学者中野登美雄就批判称:“政府不应采取回避态度,应以良心、勇气和睿智,基于国体与国防之义,公明正大地阐明立场。臣道实践、职域奉公是正当不可侵犯的,是扶翼天皇、聚合国民政治力的必要基础”[25]174,批判近卫内阁在贯彻翼赞体制上的不彻底性。
(二)议会职能——大政翼赞会是否违宪的关键
从明治宪法来讲,天皇亲政必须“依宪法而行”,而明治宪法要求权力分立,如若失去议会的协赞机能,将出现政府独裁或天皇专制,这与国体是相矛盾的,所以必须重视议会。
在明治宪法中,议会是“基于我国立宪政体的基本性格三权分立,日本臣民的代表者参与天皇的立法权和一定范围的行政权,以尽翼赞之城,监视督励政府翼赞之宪法机关”[27]539。而这里的“立宪”,与欧美国家的立宪是不同的。在国体主义者看来,欧美的立宪主义“不过是支配阶级政治的合理化”,不是真正的立宪主义,因为“它们没有君臣一如、万民一体之生命社会原理”;所以,他们进而指出日本的独自性:“日本若是彻底贯彻国体自觉,政体上充分实现国体意义,将会成为世界上空前之真正立宪主义”[28]251-252,从而排除欧美政治原理,树立天皇制国体下的“立宪政治”。
其实,在制定宪法时,伊藤博文(1841年10月16日-1909年10月26日)曾表明:“(宪法草案)不依据欧洲主权分割之精神,与欧洲数国之制度中的君民共治不同”[29]89,明确否定孟德斯鸠的三权分立,主张大权不可分割;但与此同时,伊藤又不得不承认,“既已实行宪法政治,君主权就不得不受到限制”[29]154,设置责任内阁与议会来分割天皇大权之运用,即职能性分权。其实,这也是穗积八束所说的“分业之分”[30]54。可以看出,帝国议会不是行使立法权,“只是在立法权的实施过程中,能够参与讨论而已”[29]263。但是,这却是日本式立宪政治的关键,即议会是以其职能性分权而独立于政府。
议会代表全体臣民表达意见,但“议员并非是受臣民的委任,臣民也不是议员的授权主体,帝国议会并不是经国民授权,不受其指挥命令,但议会意志行为被视为国民的意志行为,是国民的法定代表机关”[27]541。议员非臣民委任,不受选民的约束,不代表选民的利益,议员的委任主体是天皇,因此就排除了国民指挥和命令议会的正当性;议员只能扶翼天皇尽臣道,当然不能结成政党“侵入”国政。“我国民多年来忘记了日本国体的行动原理,直接模仿欧洲阶级国家的政治体制或政治原理,政党也以阶级利害为原理处理国政,以致造成弊害百出,侵害国家基础,才引起昭和维新的护国政治运动,以及大政翼赞运动的产生”[27]590。
议会是国民意志的法定代表机关,也在职能性分权下维护明治宪法的“立宪性”,所以,即便是大政翼赞运动,也必须重视议会地位。但近卫内阁没有重视甚至是回避议会,这就造成大政翼赞会与明治宪法的冲突;而东条内阁成立翼赞政治会,将翼赞会的政治性“回归”议会,从而解决了其违宪问题。从根本上说,天皇制国体与明治宪法融合之后,大政翼赞、议会代表民意、权力分立等便共存于国体之中;在发动大政翼赞的同时,也必须要重视议会,否则便会有违宪嫌疑。
四 结论
大政翼赞当然是日本强化战争体制的需要,但也是政党政治崩溃后重整政治结构的方式,是对自由主义政党政治的反动与否定。以国体明征运动为契机,“万世一系”的历史性与社会性伦理道德被融入天皇统治大权,强制性权力得以“淡化”,宪法规则变成狭义政治,而“臣道实践”、“万民翼赞”则成为广义政治,大政翼赞体制在国体上有了其必要性,与此同时,宪法上的权力分立及议会职能也在国体上有了正当性。
日本法西斯用广义政治上的大政翼赞运动来否定议会政治,同时通过议会来维持狭义政治上的“立宪面目”,使万民翼赞获取宪法上的正当性,而其途径便是“推荐选举制”,以此将大政翼赞会的意思输送至议会,并成立翼赞政治会来承担大政翼赞会的政治性,这在解除了大政翼赞会“违宪嫌疑”的同时,也实质性地抽空了议会的代表民意机能和职能性分权。伦理道德凌驾于宪法规则、国民生活泛政治化的结果,便是宪法上的规则失范,最终只能是贯彻国体精神实现“强制性一致”,议会则沦为将“强制性民意”正当化的渠道,天皇成为所有权威的源泉、所有权威的权威,宪政精神也就被消解了。
注释:
①国内代表性专著有:杨宁一《日本法西斯夺取政权之路:对日本法西斯主义的研究与批判》,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崔新京、李坚、张志坤《日本法西斯思想探源》,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蒋立峰、汤重南《日本军国主义论》上下,河北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等。代表性论文有:李玉《三十年代日本法西斯政权的形成及其特点》,《世界历史》1984年第6期;李玉《三十年代日本急进的法西斯主义运动与中间阶层》,《世界历史》1987年第3期;武寅《三十年代日本财阀与法西斯势力的关系》,《世界历史》1985年第11期;高洪《战争期间日本军国主义法西斯的精神专制》,《日本学刊》2005年第4期;张劲松《日本军事法西斯主义思想专制述论》,《日本研究》2000年第2期;王金林《日本天皇制法西斯主义的理论构成》,《日本研究》1995年第4期;徐平《战前日本军部法西斯体制确立原因新探》,《日本学刊》1991年第3期;朗维成《日本法西斯主义运动之探讨》,《外国问题研究》1986年第2期;张景全《二战前日本的现代化与法西斯化》,《日本问题研究》2012年第1期;胡月《论日本法西斯统治的“国民组织化”》,《沈阳大学学报》2010年第5期等。
②“国体明征运动”:1930年代日本的右翼势力抬头,极力排斥国家机关中的自由主义势力,宪法学者美浓部达吉便是其主要攻击对象。1935年2月18日,菊池武夫在贵族院攻击美浓部达吉的“天皇机关说”有违国体,从而掀起“机关说排击运动”,最后右翼团体、在乡军人、军部、政党、议会等各政治势力都被牵涉其中,发展成为全国性政治运动。当时的冈田启介内阁不得不在8月、10月先后两次发布“国体明征声明”,并迫使美浓部达吉辞去贵族院议员职务,以公权力抹杀了“天皇机关说”。所谓“天皇机关说”:是指美浓部达吉基于国家法人说而对明治宪法作出的立宪性解释,主张统治权属于法人国家,天皇是其最高机关而行使统治权。“天皇机关说”与穗积八束、上杉慎吉等人的“天皇主权说”相对立,为大正民主运动、政党内阁等提供了理论支持。
[1]永井柳太郎编纂会.永井柳太郎[M].东京:劲草书房,1959.
[2]铃木梅四郎.政界的根本净化[M].东京:实生活社出版部,1932.
[3]阿古岛俊治.何为内阁审议会:了解新设国策参谋本部的全貌[M].东京:今日问题社,1935.
[4]田泽义铺.政治教育小论[C]//后藤文夫.田泽义铺选集.东京:田泽义铺纪念会,1967.
[5]户坂润.现代日本的思想对立[M].东京:今日问题社,1936.
[6]嶋田俊雄.排击伪装的举国一致[M].东京:安久社,1936.
[7]上村文三.近卫在新党运动中的行动[M].东京:教材社,1938.
[8]朝日新闻社.失去的政治:近卫文麿公的手记[M].东京:朝日新闻社,1946.
[9]赤木须留喜.近卫新体制与大政翼赞会[M].东京:岩波书店,1984.
[10]大政翼赞会奈良县支部.翼赞纲要[M].奈良:大政翼赞会奈良县支部,1940.
[11]黑田觉.国防国家理论[M].东京:弘文堂,1941.
[12]神户市企划课.决战国策的展开[M].神户:神户市企划课,1944.
[13]伊藤操一.通过翼赞议会看现实政界的底部及翼赞会问题[M].东京:新东亚时情研究所,1941.
[14]川崎克.钦定宪法的真髓与大政翼赞会[M].东京:固本盛国社,1941.
[15]交友俱乐部.帝国议会概要:第76回[M].东京:交友俱乐部,1941.
[16]行政裁判所.有关行政裁判的法令(下)[M].东京:文光堂,1901.
[17]广濑健一.过渡期政治论[M].东京:昭和刊行会,1943.
[18]山崎又次郎.新体制的基础:帝国宪法论[M].东京:清水书店,1943.
[19]日本政治研究室.日本政治年报(昭和17年):第1辑[M].东京:昭和书房,1943.
[20]川口晓弘.宪法学与国体论:国体论者美浓部达吉[J].史学杂志,1999,(7).
[21]文部省.国体之本义[M].东京:文部省,1937.
[22]藤泽亲雄.近代政治思想与皇道[M].东京:青年教育普及会,1935.
[23]松井贤一.世界变局与日本[M].东京:东海出版社,1941.
[24]藤泽亲雄.日本思维的诸问题[M].东京:人文书院,1941.
[25]中野登美雄.日本翼赞体制[M].东京:新公论社,1941.
[26]大串兔代夫.现代国家学说[M].东京:文理书院,1941.
[27]里见岸雄.帝国宪法概论[M].东京:立命馆出版部,1942.
[28]里见岸雄.日本政治的国体构造[M].东京:日本评论社,1939.
[29]清水伸.帝国宪法制定会议[M].东京:岩波书店,1940.
[30]穗积八束.宪政大意[M].东京:日本评论社,194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