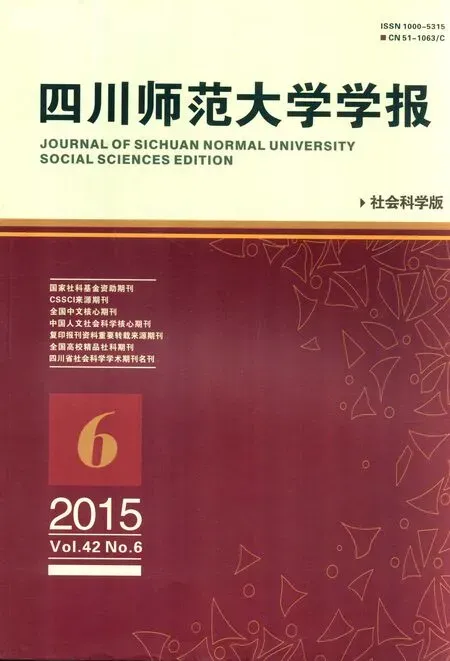“新都”抑或“旧城”:抗战时期重庆的城市形象
张 瑾
(重庆大学 新闻学院,重庆401331)
抗日战争赋予了重庆城市特殊的历史地位。作为中国的战时首都,从1937年11月20日国民政府发表移驻重庆宣言,至1946年4月30日发布还都南京宣言,重庆扮演着全国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和舆论中心的角色。伴随抗战内迁,重庆的城市化进入了“超常规”的发展期,城市规模空前扩大,都市人口急剧增长,城市经济及产业结构也因沿海工业的内迁而迅速膨胀。一方面,重庆因国民政府的内迁而被建构出一个前所未有的“新都”形象①。有人甚至认为,重庆并非一般“内地落伍的不堪想象的一个城市”,简直就是“大上海的缩影”②。另一方面,重庆城市政治地位的快速提升,似乎并未能改变“新都”的旧形象。在外地人看来,这个战时新首都与想象中的现代都市差距甚远。重庆市政所凸显的秩序混乱、交通拥堵、卫生环境恶劣以及城市公共设施落后等问题,更让“新都”的形象备受争议。直到抗战结束时,有关重庆城市形象的讨论仍在继续。
迄今为止的学术界相关成果中,以梁侃的论文最为集中地从国民政府迁都的政治意义和文化意义论及重庆的形象问题[1]255-275。本文拟运用重庆市档案馆、台湾“国史馆”以及美国哈佛大学、普林斯顿大学、耶鲁大学等馆藏档案,并辅以战时报刊以及回忆录、日记性质史料,对抗战时期重庆城市“新”与“旧”的面向进行系统梳理和深入分析。笔者聚焦日军大规模轰炸时期及其前后的重庆城市建设与规划、市政管理与民间都市意识等问题,从卫生、街道空间秩序、公共交通以及居民素质等方面展开讨论,不包括对城市形象③的经济贸易水平等层面的考量。本文希望通过对抗战首都重庆的城市现代性话题的建构过程的讨论,探究国民政府迁渝对重庆城市形象变迁的影响及其意义④。
一 国府迁渝:新重庆的首都形象
1937年11月16日,国防最高会议正式决定迁都重庆,国民政府各机关职员除其最高长官留南京主持工作外,其余均自当天起陆续离开南京转赴武汉集中。11月19日,蒋介石在南京主持召开国防最高会议,并作“国府迁渝与抗战前途”的讲话,阐明国府迁渝的重要意义。他指出,国民政府移驻重庆,乃是战略性的撤退,是以四川为持久抗战的大后方和民族复兴之根据地;他“希望政府和党部同人迁渝以后,秉承主席教导,对于一切职务,不但要照常努力,而且要积极整顿,格外振作,在艰苦之中,力求革新和精进,总要使有一番新气象,来安慰前方的将士,激励后方的军民”⑤。11月20日,林森率领国民政府直属的文官、主计、参军三处的部分人员抵达汉口。当天,林森以国民政府主席的名义向中外记者公开发表“国民政府移驻重庆宣言”,庄严宣称:“国民政府兹为适应战况,统筹全局,长期抗战起见,本日移驻重庆。此后将以最广大之规模,从事更持久之战斗。”⑥11月26日下午,林森一行抵达重庆,重庆军政当局及各界代表十余万人前往码头热烈欢迎,盛况空前。12月1日,国民政府正式宣布在简陋的重庆新址办公。
国府迁渝拉开了抗战内迁的大幕,从1938年至1939年间,“政府官员连同大批西迁难民像潮水般涌进了重庆”[2]89。举国大内迁,改变着战前重庆的城市生态。在有限的空间里,重庆接纳了国民政府政治中枢、经济命脉和文化精英,“城市即国家”的宏大画卷自此出现。这个内陆中国的“新都”开始处处呈现出“新气象”。这种“新”,首先体现在政治环境与氛围上[3]。此时,《时代》周刊对重庆城市的报道中,其称谓也由原先的“鸦片之都”更新为“政府的官方所在地”(officially the seat of the Gover n ment)、“中国的内陆首都”(China’s inland capital)、“官方首都”(t he official capital)和“国际化都市”等。
1939年初春,美国人白修德⑦抵达重庆,他观察到了国民政府移驻重庆后的政治氛围:“每天清晨,处处都可听见凄楚动人的国民党党歌:‘三民主义,吾党所宗,以建民国’,当我努力把这首每天把我们从梦中吵醒的歌翻译出来时,西方的来访者都不禁为这又滑稽又严肃的歌词捧腹。但是配曲却是既令人激动又令人感伤的,我一听到它就感到震动。黄昏,当国民党的十二罗经点星旗徐徐降落时,军号齐鸣,传遍了这个城市的每个角落,我也为之感动不已。”[4]71-72
在抗战的大环境下,“新都”重庆处处呈现出国家的景观,也散发出一种英雄主义的气质。白修德即写道:“这个逃难政府属下的几千名文职官员给予我的第一个印象就是他们的英勇气慨。他们中间的任何人本来可以像其他成千上万的人那样,留在被占领的沿海地区,奴颜婢膝地屈从于战胜的日本人的颐指气使。可是他们不愿意这样做。他们宁可忍受重庆的酷暑和高温,忍受在既潮湿而又无取暖设备的屋子里度过严冬;他们宁愿眼睁睁地看着孩子们生病,甚至因病夭折,但他们不肯屈服。”这种民族主义的气节,令白修德感动,他说:“去采访那些官员却令人感到鼓舞。那个时候,他们的孩子在政府办公楼台阶上嬉戏,他们的太太们把湿衣服晾到办公楼,而他们自己则在集体食堂吃饭,并且教他们的孩子如何对付春雾消散时必然会降临的空袭。几袋大米和一点菜油是公家每月的配给品。全家住在公家宿舍的一间屋子里,冬天生炭盆取暖。”[4]8-9
新迁来的国民政府,还有一个特别的“新”,即所谓“无处不在的美国方式”。白修德认为:“这种渗透由于蒋介石夫人的介入而达到高峰。她受过韦斯利学院的教育,是最高统帅的妻子,就是她劝说丈夫参加基督教卫理公会的。蒋介石的财政部长是孔祥熙,他读过美国的两个大学:奥柏林和耶鲁;蒋的外交部长是1904年的耶鲁毕业生;他的教育部长是匹兹堡大学毕业的;立法院长是孙科,拥有哥伦比亚和加利福尼亚两个大学的博士学位。新闻部长是密苏里新闻学院的毕业生。中国银行总裁是宋子文,后来做过中国的行政院长,是哈佛大学1915年的学生。中国政府中的美国毕业生名单是开列不完的——多得无法计算。从国家卫生署到盐业总局再到外贸委员会比比皆是。中国的驻外使节中,哈佛、哥伦比亚大学的学生也占压倒性优势;驻华盛顿的,是先后就读康奈尔大学毕业生;驻巴黎的惠灵顿·郭先生,不仅拿到了哥伦比亚大学的三个学位,还编辑过该校的校报。不仅如此,他眼下正为其儿子成为哈佛大学《克里姆森》——哈佛红杂志的职员而自鸣得意呢。我在哈佛的学位在这里比在波士顿吃香多了。后来,我组织了一个中国哈佛大学俱乐部,其中蒋介石重庆政府里的高官占的数量竟然比日后约翰·肯尼迪入主华盛顿时的哈佛俱乐部的人还要多!”[5]20美国园艺专家、重庆国民政府行政院农业顾问戴兹创(Theodore Dykstra),从另一个角度也谈到中央政府的“美国化”现象。从1942年至1943年,戴兹创在农林部中央农业实验所工作,他观察到迁到北碚的中央研究院的大部分专家均有美国留学背景⑧。
与此同时,重庆城市行政地位的升格提上日程。鉴于战时首都的特殊地位,国民参政会参政员胡景伊等21人向政府建议,改重庆市为“甲种市”,“直隶行政院”。该提案后经参政会议决,陈由国防最高会议令交行政院审议。1938年9月,在行政院第三八四次会议上,行政院院长孔祥熙提出改重庆为行政院直辖市的提案。提案指出,位于长江、嘉陵江交会处的重庆市,“当水陆交通总汇之冲,经济上原属西南之重要商埠,近更成为后方政治中心,人口剧增,事务繁庶,殊有充实其机构,以资应付特殊情形之必要”,“尤属切合现时需用”⑨。会议同意了孔祥熙的提案,并决定:“准援照直属市组织,定名为重庆市政府,乃隶属为四川省政府,但为增进行政效率起见,必要时得径函行政院秘书处转呈核示。”⑩此后,重庆市政府遵行行政院的要求,改组完善市政组织,增设社会局、财政局、工务局和卫生局。
1939年5月5日,行政院颁布改重庆市为行政院直属之甲种市的明令⑪。1940年9月6日,国民政府颁布明令,令重庆为陪都⑫。重庆再度迎来城市建设的新机遇。此后,国民政府在更大的范围内直接主导了大轰炸期间的重庆城市建设。为避免日军轰炸时投掷燃烧弹引发的城市大火,政府启动了“开辟火巷”工程,初步确立了主城区城市道路的主体框架;“中央机关迁建区”的划定,也在相当程度上改变了重庆主城的空间结构;而轰炸后的政府疏散政策,进一步推动了城市空间的有规划拓展,奠定了旧城区、新市区及郊区并存的“大重庆”格局。在陪都成立一周年之际,孔祥熙发表讲话称:陪都本身的建设,拟照一般的大都市的计划,从事于改善成为一个完美的现代都市,有便利的交通、完善而普遍的上下水道、安适的住宅、优美的环境⑬。陪都建设计划委员会以“务使重庆为适合战时之陪都、为民族永久复兴之根据”,并参照“现代都市事业”发展的惯例,推出了“都市设计”、“交通”、“建筑”、“污水与垃圾处置”、“公用事业”、“土地处置”等工作纲要和系列规划;在设计“行政区”时,还考虑“轰炸危险”的因素,按照“防空疏散建筑规则”,将行政区分散到其他 各 区⑭。
随着军政、文教、工矿企业的大量迁渝,重庆的城市人口迅猛增长。据统计,1939年初,重庆有限的空间即容纳了47万余人,人口的分布大致为:居住在重庆主城区(巴县、两江环抱的重庆主岛)的人口约占全市人口的55%,约有16%的人口居住在主城的郊区和两江之间的乡村地带,有14%的人居住江北城和长江北岸的乡村,长江南岸有15%的人口⑮。陪都重庆的“新”体现在内迁人群所带来的新素质。西方传教士高度赞誉抗战大内迁给重庆带来的变化,称:“这群从东部来的训练有素、现代而先进的群体在保守和欠发达的西部已经显示出惊人的影响力。过去的一年,因为这次从东部带来的大内迁,在保守的西部更多的变化正在发生,这些变化可能要比过去五十年的成绩都大。”⑯
中央机关迁建区的北碚,是内迁人士集中之地,处处体现出新的气象。全面抗战爆发后,距重庆市区仅数十公里的北碚,已成为迁渝人口的重要落脚点。至1938年7月,各地的事业机关、文化团体、学校以及内迁民众,纷纷汇集北碚,先后迁来的南京科学社、中山文化教育馆、中央党史编纂委员会、复旦大学、四川中学、中央工业实验所等单位,“约计在二十个团体以上”;而人口激增,也导致北碚出现“房荒”问题和环境卫生需求,“所有平时空余之房屋已告人满之患”[6]。《嘉陵江日报》上登载的新式洋房出售、出租的广告在增多,具有“近代设备”的新式旅馆也有了;而号称“北碚唯一旅社”的兼善公寓,醒目地打出了别样的广告词:这是一个“无臭虫”、凉爽、雅致、舒适、艺术、整洁的旅社[7],以适应外来者对环境卫生的高要求;雇家庭保姆的广告,也要求被雇者须“略具卫生常识”。在北碚,商店的“各牌香烟应有尽有”[8],还有供应冰淇淋、刨冰、鲜橘水、汽水、可可、咖啡、牛奶等各色冷热饮料的“峨嵋饮冰室”[9]。1938年3月17日,报纸刊登的“下江商店”广告,列举的经销商品种类繁多,从学校各类文具,如信笺、信封、墨水、抄本、日记本、书写纸、黑板、仪器等,到家庭工业社的各类产品,如化妆品、肥皂、蚊香、毛巾、味精、上海酱油、花露水、牙膏、牙粉、牙刷、糖果等,应有尽有;3月22日,报纸还以“为不再使尊夫人懊恨起见”为标题,推介“北碚唯一之百货店”销售的“上海酱油”[10]。
军阀统治时期的旧秩序和原有的都会生态都在发生变化,“新都”重庆似乎不再是本地人的天下。以1939年的重庆餐饮业为例,在17家有规模的“中餐馆”中,仅从店名看,至少有10家为外来店,包括排名前三位的“京沪驰名的老牌子”,就有“南京浣花餐馆”以及号称“本店各部茶房来自上海,素有训练”且拥有“大礼堂”餐厅的“都城饭店”;与战前以传统的“豆花便饭”为主的“小吃馆”不同,全市的26家“小食店”中,有一半以 上 为 外 省 迁 入 的 店[11]89[12]广告,82,139。 在 “新 都”,餐饮业之繁荣,“与上海相似”,“各省餐馆小食店都有”,“本地馆子亦非常发达”[13]106。仅北碚就有广东陶陶酒家、北平餐馆、河南豫菜等来自五湖四海的饭店,在北平有40年的历史、专做精美豫菜的厚德福饭庄也来北碚开分店了[14]。本地菜系还尝试革新,国泰饭店以“新型川菜,清洁可口,时代设备,明朗悦目”[12]2为广告,以适应外来人群的口味。据白修德观察:“到战争结束为止,我在重庆吃到的珍馐佳肴,除了偶尔能在巴黎和纽约吃到以外,是世界上其他城市所没有的。从福建、广州、上海、北京、湖北、湖南的大饭店逃难来到重庆的厨师,施展了他们各具地方特色的烹调绝技。”⑰[4]8-9
内迁重庆的高校和文化机关给这个原本封闭、落后的内陆城市带来了高素质的人群和浓厚的文化氛围,“新都”的阅读市场与印刷品的生产环境发生了重要变化。有人观察到:
在此比较满意的事,要算跑书店了。……自政府移来后,文化的活力也随之增长了。如从南京搬来的中央书店、拔提书店、正中书局、军用书局等;从上海分来的生活书店、上海杂志公司等;从汉口分来的新生书店、华中图书公司等。它们最近都先后在此开幕,生意热闹非常。这些新书店可说全部都以关于战时读物——书报、刊物、图画——作为主要的营业。它们搜罗的很丰富,而且十分完备,可说是集中了全国战时读物之大成。而且它们经营方法也很巧妙,如销路最广的是《抗战》、《群众》、《解放》、《全民周刊》、《世界知识》、《文摘旬刊》等,都是从汉口打好纸样,用航空寄来重庆印刷。同时,它们又有所谓“航空杂志”,销售的办法,就是将各处出版的主要杂志,全用航空寄递,只须加上相当邮费而已。这对于有阅尽天下新书杂志狂的人们,确是很合口味的。……现在,重庆的售珠市——重庆的书店街——是代表了上海的四马路了!在满足读者精神食粮一意来说,目前重庆的市民是比上海幸福得多了![15]
1943年10月9日,《基督教科学箴言报》也载文报道了重庆的阅读市场,称:“每条街道都可以发现一些小书店,那里可供阅读的有小说、严肃的读物,以及杂志和二手的外国图书——通常都是英语读物。众多的顾客中不仅有学生,还有各个年龄层的读者,他们希望通过阅读开拓视野,因为这些年的战争限制了他们的生活空间。阅览室以提供热饮吸引读者,可供借阅的图书馆和很多重庆书店都很受欢迎。”[16]旅居重庆的美国出版商 Willia m Sloane,在写给美国Doubleday Doran&Company的上司Malcol m Johnson的信中说:“书店里摆满了杂志。多数看起来都是看《国际事务季刊》的那种读者。……受教育是中国的知识阶层非常看重的事情。阅读是一件受重视的事情,能给人以知识的东西是好的阅读材料”,他指出,“我们的出版者应该认识到这里的图书需求市场,那就是几乎达到大学出版社水平的理性读物。”⑱
二 像与不像:“新都”的“旧”
董显光说“重庆不适宜做战时首都理由很多”,比如重庆的“气候”就使得这个城市不宜居,“在滨海都市习惯阳光中生活者深感沉闷。重庆一年中最少有九个月全城都笼罩在浓雾中,令人透不过气来。其他三个月阳光普照的月份,雾是没有了,可是热度飞升到像在蒸笼里”[2]89。白修德也批评重庆的气候,称:“新到的人也许会发现天气比人更为恶劣。重庆只有两个季节,而两季都坏。”[17]8然而,重庆让人诟病的远不止“气候”问题,这座充满各种非现代性要素的城市,实在是太不像国家的首都了。来自沿海现代化都市想象的批判者的批评话语,势必与军阀刘湘时代的重庆都会形象形成对立和冲突。
(一)秩序之混乱
1938年10月,国民党四川省党部主席陈公博在《中央日报》上发表连载文章《对重庆说些话》,指出:初到重庆的人们,大概没有几个人能够得到好的印象,尤其是一般“下江人”——其实不止于下江人,你若问他们对于重庆的印象怎样,他们很容易迭起几个指头,数说八九个重庆的缺点[18]。其中,缺点之一,便是秩序混乱。一位作家说他刚到重庆时,“那一种纷乱、杂吵、拥挤”的情形,几使其“脑袋要爆裂”[19]。在陈公博看来,重庆秩序混乱的主要原因很多,其中警察力量虚弱,尤其是警员质量低劣,是导致“新都”秩序不良的主要因素,他还举了若干例子来证明自己的判断[20]。
重庆的市政状况不良,乞丐与路毙在重庆街头似乎是常见的事情。据当时人记载:“渝市郊内外,乞丐很多,往往追随行人,甚至半里一里的跟着讨索,纠缠不休,而对于旅渝的外省人为尤甚。这种乞丐都是瘾民的变相,蓬首垢面,皮包骨现,令人目不忍睹。下江仕女见到了,颇肯激发恻隐之心,施以铜元。本地人物像见惯了,无动于衷,置之不理,所以最后的结果是路毙。这种路毙,在当地也没好行其德者出为收殓。下江人见到路毙,唯有报告警察,但警察也不甚关心,一似非其职权以内所应理者。”[21]126在重庆街上,“熙熙攘攘地走着穿着劣质棉布衣服的没有表情的人们。麻风病人很多。他们都是乞丐,情有可原地态度恶劣。你必须赶紧从你的钱包里找点钱给他们,如果动作慢了,他们就会过来戳你躲闪的皮肤”[22]17。
(二)交通之落后
秩序混乱是交通落后造成的。早在未修马路以前,重庆的城区街道就“人稠地狭,拥挤非常”;马路修成后,市面上“大小汽车、人力车轿同时并行,车水马龙,俨然一半新不旧之大都市”;抗战大内迁,带来人口激增,重庆的交通更是“拥挤不堪,秩序甚坏”;此外,重庆因位处山城,地势崎岖,马路“多倾斜之处”,“不易行驶马车”[12]73,故本地人“皆以轿代步”[23]23。据统计,全市“所有马路,除成渝公路及南岸公路不归本市管理外,综计仅20公里,其比例已甚小。而此短短20公里中,较好之柏油路仅8,448公尺,劣质之碎石路计12,237公尺,碎石路因修理不良,热则扬尘,雨则泥泞,行人不堪其苦,路质亦极低劣”[24]43。至于现代化的交通设施,重庆差距更远。据《重庆指南》介绍,截止1938年底,重庆市各种交通工具的统计数据如下:营业汽车54部,自用汽车457部,人力车2,091部,自用人力车208部,营业脚踏车193部,机器脚踏车15部,乘轿3,332乘,汽车无523人,人力车夫4000余人,轿夫4,000余人,此外,开办于1934年的市内公共汽车,至1938年底仅有10余部,且运营路线较长,以至于乘客“太形拥挤”[12]73;“除少数拥挤不堪之公共汽车及供不应求之人力车外,为现代都市交通大动脉之电车尚付缺如,以致街衢行人拥挤,往来耗费时间,甚且随时发生危险,既影响市民之生活,亦阻害市区之繁荣”[24]42,在“繁盛市区,道路纵横,每于交叉路处,行人拥挤,车辆阻塞堪虞”[24]42,“沿扬子、嘉陵两江,原有码头均极简陋,运输交通,胥感不便”[25]49。
1938年8月14日,国民政府行政院参事陈克文抵达重庆,他在日记里写道:“重庆是怎样的一个地方,现在还没清楚的概念。朋友谈话中知道第一是交通困难,从上清花园(行政院办公地址——引者注)到城里去,要一个小时左右的人力车或轿子。”11月20日,陈克文在搬家后体验到重庆交通之苦,他在日记中写道:“回院办公的交通太不方便了”,这段约半里的路程,“马路未通,房子建筑在山上,小径斜坡,天雨泥泞,简直一步都走不动”[26]270,319。
(三)景观之破旧
战时重庆的城市公共设施十分简陋,很难谈得上具备现代性的都市景观。“举凡现代都市应有之设备,重庆大多只具雏形,甚或付诸阙如,以是建设事业,百端待举”[24]42-43。一位在重庆的西方人说:“重庆是一个非常糟糕的居住地,每栋房子看起来都要倒塌的样子,而房子实际上的状况就是如此。房子外面泥灰因为轰炸而剥落得厉害。”⑲政府部门解释旧城改造的困难状况,重庆市工务局在市政报告中亦承认:“房屋本身之设计尤为简陋,环境卫生亦未顾及。”[25]49-50
这种状况当遭遇日军大轰炸时,更是雪上加霜。1939年“五三”、“五四”大轰炸后,原本破旧的都市景观,因轰炸几成一片废墟。吴稚晖指出,因为轰炸,“全重庆市的道路和建筑,毁者毁,新者新,几乎全改其面目”[27]吴序,27。马莎·吉尔红在回忆录中也描述了她对1941年重庆的印象:“重庆看起来就像是一大辽阔的灰棕色废墟瓦砾,……根本就不像是一个首都,唯一的优势就是日本人不能到达这里。我看到的就是一个灰色的,没有规划的,泥泞的,聚集着毫无生气的水泥建筑物,以及穷人的棚屋。”⑳[22]47
“新都”也几乎是一个没有娱乐生活的都市,晚上最多可以打打麻雀牌。陈克文日记称:“这两三个月除此之外,什么消遣都没有了。电影许久没有看:交通不便,进城困难,而且没有可以看的片子。公余饭后,四个人谈天也谈得无话可说,跳棋也下得生厌了,于是麻雀牌便自然而然的成为重新有了吸引力的朋友。”㉑
(四)公共卫生之差
战时重庆的公共卫生很糟糕。“由于战争时期大批人涌入,本来条件很差的重庆挤满了人,比以往更加使人感到不舒服,变得更加肮脏,供应也更加紧张。……职员和工人领不到全薪,许多人营养不良。”[28]370-371在这里,人们习惯“使用烟煤,全城笼罩在乌烟灰末之中。住在山下者空气不甚流通,住在山上者又为山下之炊烟所熏,所以重庆市民患肺病者百分比必定大得惊人”㉒。1938年11月6日,陈克文乘坐轿子经过城区小街巷,观察到重庆人的“病容”。他在日记中写道:“湫隘曲折,阴湿污秽,臭气熏天,老幼男女,瑟缩其间,毫无人色”,他感叹:“这些都是地道的重庆街道。这样的市民生活,真是和粪堆里的蛆无异。重庆市政,今后唯一急务,应该是改进公共卫生几个字。”[26]312
重庆不仅街道不整洁,且充满臭味,卫生环境恶劣,与战时首都形象极不相称。一位西方人描述重庆街道:“街道上到处是泥浆,而且臭气冲天。所有的粪便排污都是通过开放式的沟槽,或者是人工挑的粪桶来搬运去作为肥料。”㉓白修德也写道:“重庆总是雾气腾腾的,除非是在晴朗的仲夏……。这里街巷总是阴暗的,有些地方狭窄不堪,以至于过路人须用雨伞挡着两边屋檐的滴水方可通过。这一切,组成了一个香气臭气同时散发的气味交响乐。散发香气的是食品和调料,鲜花的芬芳,烧熟的饭栗,焚香炉,还有鸦片的烟雾;发臭气的是未收拾的垃圾和遍地的粪便。”“收粪人每天清早挨门挨户倒空各家的马桶,用竹扁担挑着晃晃悠悠的两桶大粪,赤脚快步沿石阶运送到江边被外国人幽默称为‘甜蜜船’的驳船上。他们把粪便倒进驳船里,便返回来。赤身裸体的船工们摇着橹,把这些污浊的驳船驶向臭气冲天的各收集点去。”㉔[4]5陈公博感叹:“重庆的马路、大街、小巷,无处不发见人家抛掷弃物,我在早晨和黄昏的街上散步时,无处不发见涕痰。有一次我和自己打赌,倘使我走完一条甚至短短一条街,而不发见涕痰,我发誓作一篇文章恭维重庆市。然而结果,我只有失望,没有方法发见这个奇迹。”[29]
重庆的卫生环境最糟糕的还是老鼠多得惊人。一位在重庆大学教书的外教描述了房间抽屉里的硕鼠,让人惊恐,甚于空袭警报㉕。陈克文也说:“重庆的老鼠比重庆的人口还要多得多”,灭鼠十分不易;他引述同事的话说:“要消灭重庆的老鼠不能用捕杀的方法,必须制一种消灭生殖能力的药,散给老鼠吃,再加以捕杀,才能生效。否则捕杀的速率,决追不过生殖的速率,不过这样,非二百万的经费不办云云。”[26]405
(五)四川人不好
“新都”重庆的负面形象中,还有这里的人不好。陈公博说,重庆的市民全无修养,不懂礼貌[20]。白修德在《中国的惊雷》一书中写道:“难民和流亡者几乎立刻认定重庆是一个可恶的地方,而他们认为最坏的东西之一,是重庆人。和政府一起到长江上游的下江人,把四川人当做特别种类的此等角色。”[17]8因大量内迁人口的涌入,重庆发生房荒,房租上涨,外地人因此发出了本地人“恶劣”、四川人靠不住的怨言。陈克文日记中对川人不好的印象,就集中在1938年下半年找房子时期;他对川人出租房屋时不讲信誉的诟病,又常常与其对四川军阀政治的批评联系起来㉖[26]274,288,293,304,308,311,318。
四川军阀政治的遗产,构成了战时首都的“旧”因素。所谓重庆的“旧”景观,不仅建立在与沿海现代化都市比照基础上的观察,且与四川军阀政治直接关联,这种外来者建构的重庆落后形象,又在相当程度上渲染和强化了“新都”旧的一面。陈克文就说:“重庆市一切公共的交通和卫生似乎一向没有管理,没有人注意,可是许多矗立路旁,巨墙围绕的私人大夏,里面则殊为浪费。这也可以反映过去的四川政治是怎样的实际情形 。”㉗[26]319
批评重庆的人群,主要来自原先居住在南京、上海、北平的人们,即通常所谓的“下江人”。初到重庆的“下江人”群体,人数不多,却带给战时首都一种“一切无不下江化”的氛围。梁侃的论文,归纳了民国文献中有关战时重庆“本地人”与“下江人”两种称呼的含义:大抵“本地人”都是“坏”、“蛮横”、“狡猾”、“敲竹杠”的,而“下江人”大都是“摩登”、“阔绰”且带有一些傻气的,这种地域成见使“下江人”对四川的一切都看不大贯;他指出,尽管他们并不觉得自己的城市有多“摩登”,一旦落户重庆,却能发现这个“新”首都的一大堆的问题,甚至还突生出一种沿海人的骄傲,而对这个内陆城市横竖看不顺眼[1]264-265。这种文化上的偏见,在国民政府迁渝初期表现得十分明显。当年就读于复旦大学新闻系的四川籍学生何鸿钧,亲身经历了复旦大学“下江”学生与本地同学因习俗差异引发的“沿海较高文明与内陆落后文化之间的冲突”㉘。不过,这两种都市想象的对立,在日军大轰炸开始后,发生了明显变化。据白修德的观察,自1939年5月之后,日本人的炸弹从文化上将本地人和下江人融合在了一起——中国人。他说:“两年后,就我的观察,这两个方面的人都同我相处得十分愉快。那时重庆没有太多的恐慌,新迁来的和本地人学会了和平共处。”[5]70,22-26
三 规范“新都”:脱胎换骨之举措
梁侃认为:“既然将重庆定位战时首都,就要把它作为一个首都来建设。改变重庆的城市形象,推行沿海地区十年建设时期的经验,便成为政府迁都重庆的文化意义。”㉙[1]263于是,国民政府便天然地承担起重塑“新都”形象的责任,随之而来的便是由官方主导的各项改造战时首都的新举措陆续出台。
(一)升国旗,唱国歌
国旗、国歌是民族国家认同的典型政治符号,升国旗、唱国歌则是国民政府培养国家民族意识的标志性举措。1938年最后一天,宋美龄出席重庆新运总会的新年“除夕聚餐会”并致辞,其中就谈及“一个国家国旗的尊严,和人民对国旗应当的崇敬”的问题,她还痛心地谈到五年前首次入川时在成都“曾亲见一个屠夫,把国旗当做围裙使用”的事情,她认为“在现时代的中国,这种不合理的行动,太令人痛心了”,她“敦嘱大家,自二十八年元旦起,大家应该领导民众,切实纠正,使我们的青天白日旗,不再沾染些微的污秽,同时,希望我们的国土,也洗涤已沾的污秽”[30]。
蒋介石对于升降国旗的仪式十分重视,他多次电示重庆市长吴国桢等规范升降国旗仪式,如“规定民家商店悬收国旗时间,并令警察切实执行”,令“重庆各处所悬国旗旗杆顶由市府统一式样改正”,令“重庆街道悬挂国旗应整齐划一”等㉚。1943年9月20日,蒋介石再次指示贺耀祖,令“重庆各团体悬挂国旗遵照规定升降时间”,要求市内各团体商号于纪念日悬挂国旗执行每日升降程序,否则属“不合体制”者,要求“以后对于国旗升降时间,应由市府加以规定,并通令全市遵照实行,一面并由警察局切实纠正。尚有未照规定升降者,则应由该区警察所长或巡官负责。希即规定升降时间,通令实施为要”㉛。此项举措执行效果似乎不错。据时人观察,重庆“各商号所悬挂国旗,色样大小,完全一律,悬挂地位,成一水平线”,认为仅就“国旗的整齐化一项”,重庆就可评定为“全国的模范”[31]217。
这种新的风尚对长期封闭自治的军阀独立王国而言,是破天荒的。后来,这种具有象征意义的政治符号也出现于重庆都市生活的其他方面。比如“剧院不仅是娱乐场所,也用来树立党国领袖的威望:各影院在未开始放正片之前,先映国旗一面,飘飘然临风招展的样子,继映最高当局暨党国伟人名、肖像,是时观众皆全体肃立,静聆播唱国歌毕,始就坐观映”[21]148。
(二)新首都,新生活
此时,移风易俗的新生活运动也在重庆大力推行,并覆盖城市生活的方方面面㉜。白修德说:“重庆过去是一个自我调节的地方性社会的省会;现在它突然被推进了一个新的世界。国民政府先遣人员一到,就发现以往那种懒散的生活方式缺乏纪律性,难以执行战争时期严肃的政治任务。鸦片在一九三八年冬立刻被查禁。在我到达前四个月,澡堂也被禁止。商人们过去聚集在那里宴欢作乐,席间还可以出入蒸汽弥漫的浴室,澡堂的女招待给他们搓背按摩,他们甚至在浴室里干一些荒淫无耻的勾当。严峻的纪律是战时改革的主题,因此,喝烈性酒立即遭禁,奢华的传统结婚典礼被列为非法。后来还打算用简单的火化仪式来代替铺张浪费的旧式丧葬。人力车和滑竿都编了号,发给执照。甚至还发动了一场禁止随地吐痰的运动。”[4]7-8
蒋介石手令严禁公务员跳舞冶游,也是一例。《中央日报》刊发“最高当局命令”,宣称:“兹为整饬纪纲,挽回风气起见,嗣后各级公务员,如有赌博、跳舞、冶游及其他不正当行为者,无论任何阶级,准由宪警立即拿解,从严惩办,勿稍徇纵。”[32]1939年3月,重庆市警察局发布公告,严厉取缔男女同浴的风俗,“以正风化,而维治安”[33]179-180。
外省人也观察到新生活运动对重庆形象的改变,称:“到了重庆,第一件事使人赞叹的,就是新生活运动了。”“市民的服装异常朴素。男女学生非但一律穿制服,就是走上街头,也着制服,整齐极了。普通商民虽无同样服装,但式样大都一律的。妇女服装,黑布最多,杂色很少,都是国货,尤多土产。商店之门以及街楼,均有‘购买舶来品是莫大的耻辱’等标语。至于鞋子,学生规定黑色鞋子,省府曾有这样规定:‘凡为妓女得穿高跟皮鞋’,以致一般高贵的妇女们,都不愿仿效了。”[31]217“新生活运动”的推行为重庆带来新气象,不仅都市餐饮卫生大为改进,比如饮食店中有专门查究卫生人员检查,鱼肉鲜货摊摆设有规定时间,且居民开始更为早起锻炼,“习早操”,“练国术”,并由重庆市党部国术训练处专任指导,不收学费;在城市秩序上,“在行的方面,市内街道,不及上海天津等广阔,城中区的中山路外,都是崎岖不平,但无论五六岁小学生,都能遵守靠左边走,狭窄道上,尽有千百行人,不会发生冲突,尤其是集会时候,成群的人,鱼贯而入,不见丝毫冲突,令人见而发生良好的印象”;其他“如禁烟运动,军人禁入电影院,升降国旗时,均须立正致敬”[31]217。
1939至1943年间,蒋介石频繁发布各种手令及手谕,内容涉及“新都”的市政建设、城市景观、公共卫生等诸多细节。为解决城市乱贴标语壁画等问题,蒋曾发布手谕,令“重庆所有标语与壁画十日内洗净重新张贴”,并令“重庆市各种标语一律正楷书写,违者取缔”,甚至还指示吴国桢“重庆市马车马匹瘦弱,马主应注意喂养,并检查取缔”㉝。
(三)改街名,修马路
战前,重庆街道名称的形成大致有五种途径:(1)以商业市场为起源的街名,如油市街、鱼市街、棉花街、老衣服街、杂粮市街、木货街等;(2)以历代官署名称命名的街巷,如上都邮街、下都邮街、守备街、中营街、左营街、二府衙、厘金局巷等;(3)以山城的地理特征和位置命名的,如上大梁子街、下大梁子街、小梁子街、小河顺城街、大河顺城街、水巷子、二十梯、十八梯、三门洞街等;(4)以大族姓氏命名的街巷,有柴家巷、江家巷、戴家巷、曹家巷、蔡家湾、韩府大巷等;(5)以寺庙包括西方宗教教堂及其机构命名的街道,有关庙街、长安寺街、罗汉寺庙、山王庙街、天主堂街、育婴堂街、仁爱堂街、清真寺巷、报恩堂巷、若瑟堂巷等[34]23-26。在 战时的“下江人”看来,重庆有不少非常不雅的街名,如猪行街、粪码头、鸡街、马屎堆、猪毛街等;重庆的街道系统紊乱且名称易混淆,如《重庆指南》就介绍:“本市街名不少含有封建意识者,而各区已修成之马路亦大多一街数名,市民不易寻见。”[12]135因此,改变重庆城市面貌,可以做的第一件事,或许就是更改街道的名称。
对此,重庆市地方政府采取了积极的态度。1938年12月11日,重庆市警察局长徐中齐呈报重庆市长蒋志澄,称:“查本市原有街道,编钉门牌,历时已久,脱坏甚多,且各处新建马路房屋,亦经次第落成,门牌一项,多付阙如,每于邮件往返,户口清查,诸多不便。爰拟将全市门牌重新编钉,并即趁此时机将从前街坊名称,名实欠当,及相互雷同者,酌予合并,或另拟名称,俾便识别。”该报告还提出计划,在全市推广实施,“以规划一”㉞。12月13日,《中央日报》刊发中央社消息称:警局负责人发表谈话,“此次警局订正街道名称,颇引起社会人士之注意”,“一二报纸,略有评论”,负责人进一步解释订正街道名称的缘由和意义,在于重庆现有的街道门牌之混乱,不仅使“邮电往返、户口清查,诸感不便”,且令“外来人士,寻觅一地至感困难”㉟。
1939年1月13日,重庆市警察局遵照重庆市政府令,函请有关机关举行商决更改街名会议,参加的相关单位有重庆市政府秘书处、市社会局、巴县地方法院、巴县江北县政府、财政、工务、电报、电话、邮政各局等,重庆绅耆曾子唯、温少鹤等16人一并出席,会议一致认为:“本市街道段落零碎,马路既成,街名允应早为确定。同时,街名雷同,与有不合现代提倡科学扫除迷信之精神者,亦应择优更改,以作一劳永逸之计,当将应改街名一致通过,并议决由警察局办理纪录在卷。”㊱
而街名要如何更改才好呢?改“街”为“路”似为现代化之举。30年代,大凡传统的城市街道名称,多为“某某街”。重庆大街小巷共400余条,除郊区新开辟的两三条路外,或称街,或称巷,或称湾,或称沟,其他称坎、洞、堆、坊、岩、坪等。偌大城区,没有一条叫做“路”的街道。只有“摩登”的城市,才有许多称之为“路”的街道。梁侃指出:“毫无疑问,对久居南京上海的下江人来说,‘路’显然要比‘街’更加摩登,更加进步。倘使我们以1930年的‘首都干路定名图’,对照1942年的‘重庆街道图’,可以发现南京成为重庆建设的样本;改主要街道之名称,南京有48条街道,重庆有20条左右。”[1]270重庆街道原无路牌,市政府决定将干路大街之牌,仿上海路牌办法,横立人行道侧,小牌则钉于墙头,门牌用蓝底白字,写明街名,并编号数[21]12。
梁侃认为,如果改街为路仅仅是一个抽象概念的转换,那么街道名称的更改却具有政治象征意义。于是,战时重庆更改的路名呈现出如下情形:(1)以国民党政治意识形态为标志的路名,有民权路(原都邮街、关庙街、鱼市街至较场口)、民族路(会仙街、小梁子街、龙王庙街、治平街)、民生路(杂粮街、售珠市、武库街、劝工街);(2)以国民党领袖人物命名的街道,有中山路、中正路、林森路、岳军路等;(3)其他含有政治意义的路名,有中华路、民国路、和平路、中兴路、新生路、凯旋路、五四路、邹容路等[1]270-271。
需要指出的是,更改街名也是应对日军轰炸、开辟火巷工程的实际需求。1939年11月16日,重庆市工务局局长吴华甫提出“本市街道名称自拆除火巷后多已失实如何整理请讨论案”。为此,重庆市政府决定“组织本市街名拟定委员会,由警察局召集派员参加”,第一次会议即商讨新开辟火巷的命名事宜,并当场决定原则三条:一、化零为整;二、凡新辟火巷之宽度为十五公尺者成为路,十公尺者为街;三、凡称路之命名以新颖及含有抗战建国之意义为准则,凡称街之命名可酌量运用旧有名称。依据上述原则,重庆市警察局拟具命名草案表,并于当年十二月七日提交各局代表会议修正,通过了“新命名火巷名称三十条”,此次命名仅有“自十八梯通上南区马路之新辟马路奉命暂缓命名”㊲。在大轰炸期间,火巷的开辟构建了重庆城区道路的雏形。
(四)打扫卫生,消灭老鼠
1938年11月,重庆市卫生局成立,由医学博士梅贻琳任局长,隶属重庆市政府,主管重庆市环境卫生、医疗防疫、医药管理、救护训练、检验保健、卫生教育等事项。下设三科九股一室,有工作人员39人。其中,第一科下分清洁、取缔、卫生工程3个股,专掌环境卫生。1943年1月,梅贻琳辞职,王祖祥接任局长,直至抗战结束[35]58。卫生局成立后,即明确公共卫生的目的为减低死亡率、患病率,治理环境卫生、改善医药防疫设施、促进一般健康、厉行健康教育等均属于公共卫生的重要工作㊳。
卫生局成立以后,颁布了一系列法规、规章等,其中包括《重庆市取缔垃圾清洁规则》、《重庆市卫生局清洁队组织规程》以及《重庆市卫生局粪便管理所临时售粪办法》等有关城市公共卫生的规章制度㊴。1939年8月1日,重庆市清洁总队成立,职工517人,在城区设4个区队[35]27。清洁总队主要负责清除街道、运除垃圾、捕捉野犬、挑运粪便等。1941年1月16日,卫生稽查队组织成立,设卫生稽查长1人,卫生稽查员16人,专责管理关于督导环境卫生及医药业、饮食店、公共场所等有关卫生之调查取缔事项㊵。至1943年,卫生局附属机关共有33个单位,属于环境卫生的有清洁总队及其附属九区队及一特务队,此外还有卫生稽查队及灭鼠工程队共13个单位㊶。
重庆市清洁总队打扫街道的职责,据重庆市档案馆藏重庆市卫生局档案记载,包括清扫道路、免费挨户收取垃圾、清除市内外旧垃圾堆、道路洒水、设置废物箱等。此外,市卫生局对餐饮业、公共娱乐场所、旅馆客栈、澡堂浴室、理发业等行业也制定若干管理规则,并派卫生稽查员随时检查取缔,指导改良。例如卫生局要求饮食商店一律按照规定办理登记注册,厉行取缔出售冷饮食物,如刨冰、酸梅汤、冷糖水等,以防时疫。各大小牛乳棚场一律由卫生局稽查员随时抽查,或是提取牛乳以比重方法检查及计算乳牛产乳量,以防止在牛乳中掺水或豆浆。
战时首都的公共卫生运动,重点之一是灭鼠。据重庆市卫生局工作报告,灭鼠工作“着重于堵塞鼠洞,药剂毒杀,器械捕捉三种。并一面奖励捕鼠,备价收买(原为每头一分现改为二分以资鼓励),一面宣传鼠害,劝导改良建筑、妥存食品及严密处置废弃食物并提倡养猫”㊷。内迁的武汉大学生物系,更满墙张贴醒目标语,收买老鼠,生者每头二分,死者每头一分[21]122。不过,从重庆市临时参议会议员的提案看,1940年3至8月间的重庆城市公共卫生状况依旧堪忧㊸。
四 余论:城市抑或国家?
抗战时期,重庆的“新”与“旧”问题多半是外地人建构起来的。在这一建构过程中,包含着两种都市想象的抗衡,即:沿海现代化都市的想象与四川军阀防区体制下的内陆旧有都会的生态。伴随国民政府移驻重庆,这两种都市想象的对立,在某种意义上又演成一种中央与地方、外来精英与当地人之间的冲突或摩擦。而改造重庆,改变军阀时代的旧城秩序之举措,在形式上与国民政府的“去四川化”关联起来。董显光说:“那时候,四川的部分地方势力虽经安抚仍保留着割据的局势,未减狭隘的地域观念,视外来人如闯入的不速之客。”[2]89围绕刘湘的去世以及张群入主川政而发生的激烈斗争,显示出内迁初期中央与地方的矛盾。媒体舆论先行,也宣告着国民政府对川人地方观念改造的意志㊹。1939年“五三”、“五四”大轰炸后,贺国光被任命为重庆市市长。同年年底,吴国桢出任重庆市市长。1942年12月8日,国民政府又任命贺耀祖为重庆市市长。“新都”的新,从市长的更换上体现出了新气象。
然而,这并不是一个能被彻底改造的旧都会。事实上,国民政府中央与四川地方势力的矛盾与冲突,在战争年代继续着,其复杂性远超张群主川的风波㊺。一方面,地方主义的存在,传统意识的顽固,中央政府似乎并没有彻底地拥有过这座城市。白修德说:“在这座逐渐被新来者搞得乌烟瘴气的古老城市里,除禁烟以外,其他任何法令都无法实施。在新的外部掩盖下,这座古城继续保持着它旧日的生活方式。”[4]8另一方面,关涉陪都形象的“面子工程”的市政建设诸多举措,其执行力并不好。就重庆市档案馆藏蒋介石有关重庆市政的手令/手谕的执行情况看,其中多属下令之初有效,过不久又“渐复故态”㊻。事实上,无论是更改地名,或是灭鼠卫生运动,还是新生活运动与战时市政管理,国民政府欲以南京、上海为榜样,改变旧重庆城市面貌的种种规范性举措的效果并不尽如人意㊼。
当日机大规模的轰炸结束之时,有关陪都的形象问题再度被提到公众面前。1942年底,《大公报》刊发社评文章《论重庆市政》,指出重庆存在的问题依旧是路政、卫生、交通和居住环境等基本建设缺乏实绩[36]。《时事新报》则批评说,重庆市民最感痛苦的两大问题,一为“住”,二为“行”[37]。1945年7月,《大公报》再发社评《市政感言》,指出:“重庆是一个周身伤疤的都市,而市政的设施,永远头疼医头,脚痛医脚……这样一个一百多万人口的都市,身为国际观瞻所系的战时首都,水不灵,灯不亮,路不平,终年闹着偷电抢水的风潮,公共汽车站行列常常拖到半里多长。下了几天雨,下水道的水会冲倒多少所房子,像中一路这样的市区心脏,竟让它污水长流,臭气冲天;而市区惟一的公园,四周都布满着垃圾堆,死老鼠,让细菌自由繁殖散播。这样的市政,怎样会不叫盟友窃笑!怎样会不使安身讬命的百万市民不寒而栗!”“重庆是一个千疮百孔的都市,它需要彻底的诊治,不要再头疼医头,更不要搽搽红药水就算完事。因此,我们才联想到这‘医生’的制度与职责等问题。”[38]这种对重庆市政的批评声音一直持续到抗战结束之后。1945年12月19日,《时事新报》社评文章指出:
重庆的市政,在战时因陋就简,现在理由甚多,人民还可曲以原谅。现在胜利已经四个多月,而目前市政仍未见改善,未免说不过去,战时人口永远在增加,市区不断在扩张,随时有各种因战事需要的紧急措施,物质逐渐缺乏,币值时时低落。现在则至少这几种原因及其威胁,已不复存在,则市政不应再坏下去。如果另有使市政坏下去的原因,恐怕只有一个,即政府各部分的大员已陆续东去,上级的监督逐渐松懈,然而这个应该成为原因吗?重庆的市民本不奢望像欧美那样现代化的市政,但是依旧因陋就简,在市民日常生活的必需条件方面切实改善,也并非不可能,因此,我们也只就日常生活的必要条件上说起。第一,市内及郊区交通,越来越不便了。……其次是电灯。重庆以前因战时军需生产和工厂用电力多,燃料又缺乏,所以常常停电。现在许多工厂已经停工或缩减,而市内南岸等区仍不少停电,……第三,重庆是个两江夹流的城市,而水是市民最大苦恼的原因之一。窃水之风,夏天曾闹得不可开交,有武装窃水,武装保护等戏剧性……最后是门牌。警察先生所谓牌照,也就是贫民最怕换的牌照,新旧不同,一条街名也时常不同。于是重庆市民出门,上坡下坡之不足,又常要在八阵图中上下左右来回找新旧牌照。除了大街以外,门牌的次序是莫名其妙的。挨着的两家可以差数十号,而中间号数又须上下摸索而后得。有的有许多小街共一名称,永不分别,譬如大田湾,上、下、左、右、东旋西转五六条胡同,门牌断断续续多至三四百号,而只有一个街名。市政当局宁可把许多约定俗成以大街的名称改来改去,仿佛只要把“中山”“青年”“复兴”等等名称用在街上,便算是实行了三民主义,而不肯把许多同一名称的小街标别数字或方向,以便利民。至于清除修理小街的垃圾,厕所,装置路灯这些“鄙事”,似乎更非京兆尹所屑为。[39]
12月20日,《时事新报》再发社评《谈重庆的市容》,对重庆的市容清洁和公共卫生提出批评。
值得注意的是,在众多批评声音中,有一种来自城市内部的声音,即康心如为议长的重庆市临时参议会的参议员们,他们对重庆市政建设等若干问题贡献的提案㊽,表现出地方精英对于现代城市的渴望。从参议员金融工商组成背景看,其有关重庆城市地位的呼吁与提案,凸显了地方精英的都市自治意识的成长,以及重庆“因商而兴”的城市商贸功能与都市形态的意义。在全民族抗战的大背景下,国民政府与外来精英成为重庆现代性话语建构的当然主导者,蒋介石以各种手谕直接介入重庆市政建设的细节,看似为蒋介石个性中的“事无巨细”的亲力亲为,实则是“自上而下”地重塑了抗战陪都的政治化“规范”。从这个意义言,战时重庆可谓“城市即国家”。而川人与“下江人”的矛盾,以及中央与地方关系问题的持续,地方绅士的呼声,从一个侧面表明战时重庆城市两种形态的冲突的现实。
无论是中央政府“自上而下”的规范,还是来自本地士绅“自下而上”的都市意识成长,都需要考虑长达五年半的日军轰炸重庆的事实。1939年“五三”、“五四”大轰炸是战时重庆遭遇日军持续的、恐怖性大轰炸的开端,残酷的轰炸致使重庆变为大后方的“前线”,这一灾难开启了战时重庆的城市景观在长时期内呈现残破不堪的形象特质。与此同时,重庆又因不屈服于日军轰炸的暴行,而展示出战时陪都在轰炸废墟上的“精神堡垒”形象㊾。发生在日军大规模轰炸之前后的重庆“新”与“旧”面向的讨论,在某种意义上还可看作战争对后方城市的民族国家建构的一个重要案例。
注释:
①1938年12月19日,宋美龄在对重庆妇女团体干部演说时指出:“我前四年到过重庆,现在是第二次了。重庆的面目,我已几乎不能认识。进步之速,实觉可惊。”(参见:《渝妇女界欢迎大会中蒋夫人训词原文——以六事勖妇女界努力抗战工作》,《中央日报》1938年12月19日第3版)宋美龄此话与其在1935年首次入川时的言论差异颇大。短短三年多,重庆为何进步如此之大?进步又表现在哪些方面?宋美龄并未展开说。从整篇讲话看,其出发点似为拉近与当地人的距离,为接下来的后方妇女动员奠定群众基础。不过,更有意味的是,宋的此番话语并非仅可理解为是外来精英的沿海现代化都市的一种想象,在国府内迁与战争环境下中国空间秩序重构的非常时期,建构战时重庆的政治地位更具象征意义。有关宋美龄首次入川时对重庆的表述分析,参见:张瑾《宋美龄视野中的重庆——以1935年著〈西南漫游〉为例》,《史学月刊》2014年第9期,第116-125页。
②沧一《重庆现状》,《宇宙风》1938年6月1日第69期,第152-153页。1939年2月22日,法国作家夏度纳也对记者谈了相同的观感:“重庆为余九年前旧游之地,其时犹类中古时代之城市,兹已一变为二十世纪之都会,交通便利,新式建筑,在在所见,与上海无异。”(见:《法作家夏度纳谈游渝观感,人心奋发建设进步》,《中央日报》1939年2月25日第2版)而重庆的夜景更让初到此的外地人“恍然身在上海、香港间”(见:刘显曾整理《刘节日记(1939-1977)》上册,郑州大象出版社2009年版,第23页)。有关战时重庆都市景观的记载,还可参见:Notes on a Trip to West China,by a For mer Resident of Nanking,March 1939,Albert and Celia Stewar d Papers,Group No.20,Box 8 Writings,Talks,8-179,Divinity School Library,Yale University;施康强编《四川的凸显》,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年版,第8-83页。
③从理论的角度上说,构成城市形象的要素是多元的,包括自然生态、地理环境、经贸水平、建筑景观、公共设施、制度文化、市民素质等,城市形象的诸要素不仅具有综合性与复杂性,且有关城市形象的感知又颇具主观性,其观察点往往聚焦于城市形象的外在呈现,如城市交通、城市卫生、城市建筑、城市居民素质、城市管理等方面。近年来,学界相关成果多从文学、人类学、艺术学、电影学以及建筑城规学等学科论及抗战时期的重庆城市形象问题(如:谢璇《1937-1949年重庆城市建设与规划研究》,广州:华南理工大学博士论文,2011年)。
④本文为2015年7月7-9日台北“国史馆”、“中央研究院近代史所”、“国立故宫博物院”主办“战争与历史记忆:抗战胜利七十周年学术研讨会”论文的修正稿。承蒙叶文心教授作为会议论文的评议人,何一民教授作为论文修正稿的匿名评审人,拙文在修改中多受到叶教授、何教授指正之启示,特此致谢。
⑤参见:《国防最高会议第五次会议记录(1937年11月16日)》、《国防最高会议密函(1937年11月17日)》中国国民党党史馆:档案号009/1、006/59。另参见:《王世杰日记(手稿本)》第一册(民国二十二年五月-民国二十七年十二月),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0年印,第140页;蒋介石《国府迁渝与抗战前途》,秦孝仪主编《先总统蒋公思想言论集》卷14演讲,台北: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1984年,第653-655页。
⑥周开庆《民国川事纪要》下册,台北:四川文献研究社1974年版,第31页。另参见:《国府移驻重庆 宣告中外继续抗战》,《中央日报》1937年11月21日第2版。
⑦Theodore H.White,中文名字白修德,1939年4月11日来到重庆,受雇于重庆国民政府中央新闻宣传部国际宣传处。6月9日,他开始作为“特约通讯员”为《时代》周刊撰写新闻稿,不久成为《时代》驻重庆的首席记者。白修德笔下的重庆,是一种极富政治意义的符号;他所建构出的战时首都,更多的是一种国家的形象。公开出版的白修德作品,集中描绘重庆图像的著作有两部,即《中国的惊雷》(1947年英文版)与《探索历史》(1978年英文版)。而哈佛大学档案馆特藏的白修德档案,所涉猎的重庆相关文献远远超出了上述两部公开出版物的内容。有关白修德档案中的重庆文献评介,参见:张瑾《探寻海外档案中的战时重庆图像——以哈佛大学白修德档案为例》,《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2期,第52-59页。
⑧参见:Diar y Entries,18,December 1942,p.42,pp.53-54;Papers of Dr.Theodore Dykstra,1942-1944,Harvar d-Yenching Librar y;Letter of Dr.Theodore Dykstra,January 12,1943;Letter of Dr.Theodore Dykstra,January 30,1943,Peipei,Szech wan.
⑨《行政院秘书长魏道明为重庆市准获照行政院直属市组织致重庆市政府公函(1938年10月13日)》,重庆市档案馆:重庆市政府全宗,典藏号0053-2-274。
⑩《国府年鉴资料:重庆市政府总论(1942年2月)》,重庆市档案馆:重庆市政府全宗,典藏号0053-11-78。
⑪《行政院为奉转重庆市为院辖市给重庆市政府的训令(1939年5月11日)》,重庆市档案馆:重庆市政府全宗,典藏号0053-2-274。
⑫《关于定重庆市为中华民国战时行都、战时陪都上行政院的呈(1940年5月18日)》,重庆市档案馆:重庆市政府全宗,典藏号0053-0004-00138。1940年9月27日,行政院为组织陪都建设计划委员会给重庆市政府训令,督饬主管机关“参酌西京之体制,妥筹久远之规模,藉慰舆情而彰懋典”。11月8日,国民政府令特派孔祥熙为陪都建设计划委员会主任委员,周钟岳、杨庶堪为副主任委员。11月27日,行政院训令派翁文灏、张嘉敖、魏道明、刘峙、张维翰、卢作孚、刘纪文、潘文华、陈访先、吴国桢、康心如为委员。次年4月24日,吴国桢在陪都建设计划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报告,称该机构为“一幕僚机关”,也是“决定建设陪都的通盘计划”之“唯一机关”,他指出,就都市设计而言,重庆“实可建设为我国的模范城市”。参见:重庆市档案馆、重庆师范大学合编《中华民国战时首都档案》第一卷《国府迁渝·明令陪都·胜利还都》,重庆出版社2008年版,第76-79页。
⑬《陪都奠立一周年纪念大会 孔主任委员演讲词》,第7页,重庆市档案馆:陪都建设计划委员会全宗,典藏号0075-1-16。
⑭《陪都分区办法建设提案(1941年)》,第60-63、88-90页,重庆市档案馆:陪都建设计划委员会全宗,典藏号0075-0001-0056。
⑮ J.E.Spencer.Changing Chungking:The Rebuilding of an Old Chinese City.Geogr aphical Review,Vol.29,No.1.(Jan.,1939):46-60.按:值得注意的是,1939年“五三”、“五四”大轰炸后,因政府的疏散政策导致人口一周之内骤减28万。此后,每当空袭结束、雾季来临之际,人口又快速回流到都市,类似的记载不少,如《关于检发二十九年春季重庆市人口疏散计划的公函、训令(1940年2月4日)》(重庆市档案馆:重庆市政府全宗,典藏号0053-0012-00065)。这种因日军轰炸导致的重庆人口季节性波动,一直持续到1941年末。1941年12月,重庆城市人口增至70万(参见:《关于改正重庆市人口增多及公司防空洞不足情形的代电、训令(1942年11月12日)》,重庆市档案馆:重庆市政府全宗,典藏号0053-0012-00149),1944年2月增至95万,到1945年4月重庆城市人口已达126万。有关战时重庆城市人口统计,参见:重庆市档案馆藏重庆市政府全宗、重庆市警察局全宗、重庆市社会局、北碚管理局等全宗;相关研究,可参见:内田之行《论抗战时期重庆市的人口变迁》,载靳明全、内田之行编《中日学者抗战文史研究文集》,重庆出版社2009年版。
⑯ Chungking,China’s New Capital,by George A.Fitch,February 12,1939,John Hersey Papers Group No.145,Box 4-1,Divinity School Library,Yale University.
⑰张恨水也注意到,重庆本地的川菜馆“极多”,可谓“五步一楼,十步一阁”,来自平、津、京、苏、广东的餐厅更“如春笋怒发,愈觉触目皆是。大概北味最盛行,粤味次之,京苏馆又居其次。且主持得人,营业皆不恶”(见:张恨水《重庆旅感录》,《旅行杂志》1939年1月号)。
⑱Willia m M.Sloane Paper,Box 2 Folder 1(9),CO 236,Manuscripts Division,Depart ment of Rare Books and Special Collections,Princeton University Library.
⑲㉓ Letter to Louise,January 5,1943,Whiting Willauer Papers,MC 142,Box 2,folder 4,Princeton Seeley G.Mudd Manuscript Library.
⑳《陈克文日记》对日机轰炸造成的城市废墟有相当细致的描述。此外,相关西文文献,可参见:美国哈佛大学白修德档案(Papers of T.H.White,HUM 1.10);美国卫斯理学院蒋宋美龄档案(Papers of May-ling Song Chiang,Box 2,MSS.1)和艾玛·米尔斯档案(Papers of Emma Delong Mills,MSS.2);耶鲁大学神学院特藏传教士档案(John Hersey Papers Group No.145,Divinity School Librar y,Yale University;China Record Project:Miscellaneous Personal Papers Collection,Group 8,China Missionar y Oral Historical Collection-4,Divinity School Library,Yale University)等案卷;口述史料,如:Stephen R.Mackinnon and Oris Friesen,China Reporting:an or al histor y of American j ournalism in the 1930s and 1940s,Ber keley:University of Calif or nia Press,1990;Peck,Graha m,Two kinds of ti me,Boston:Houghton Mifflin,1967.
㉑重庆缺乏娱乐活动,也与政府推行的“新生活运动”有关。陈克文说:“新生活运动虽然提倡高尚娱乐,可是高尚娱乐是什么,在什么地方?至今还没有给这些生活感觉枯燥的人们以若何的实际利益。娱乐是不应该漠视的,在这个战争的时候,提倡严肃的生活是违反人性的,并且事实上也做不到。我曾对之迈说,人类的历史是往娱乐和奢侈这条路走的,我们就算不能够提倡娱乐,提倡奢侈,至少我们不应该违反这趋势,抹杀这事实。个人在道德上尽可以从事刻苦的生活,提倡俭约,但是国家的政令设施是不能违反这个历史的倾向的。”见:《陈克文日记(1937-1952)》上册,第393-394页。
㉒胡庶华《理想中的重庆市文化区》,《重大校刊》1936年12月1日第4期。有关战时重庆市公共卫生状况的记载,还可参见重庆市档案馆藏重庆市政府、重庆市卫生局、重庆市警察局和重庆市社会局等全宗资料。
㉔据重庆市档案馆藏卫生局全宗(典藏号0066-0001-0003)记载,战时重庆城区的粪便运送有一套严格的程序,然而自1939年日军对重庆实施大轰炸,城区厕所多被炸毁,由于收运粪便的夫役疏散离城,致使运销脱节,粪便四溢。1940年3月16日,重庆市清洁总队奉命成立重庆市粪便管理所,统筹处理粪便事宜,城区设3个分所,挑粪夫役147人。由于缺少经费,粪便管理所于1941年1月1日撤销,归并清洁总队办理(见:《重庆市卫生志》,第28页)。
㉕ General Cortes.Circular letters,by ET M,Esther Tappert Mortensen Papers,Group No.21,Box 6-99,Divinity School Library,Yale University.
㉖战时重庆的“房荒”,引发了外地人对重庆形象的普遍的负面评价,如:徐咏平《满腹牢骚话新都——重庆》,《决胜周刊》第6期,第16页。另据重庆市档案馆馆藏文献看,所谓四川人不好,多表现在本地居民落后的素质和不文明的行为举止方面,如不讲信用、随街赤膊、随地吐痰、随街晾晒衣服、随街摆摊、大声讲话、乱贴广告等。
㉗吴济生在《新都见闻录》中对于战时重庆的批判话语,具有相当的代表性。这种批评或可视为战前陈衡哲所著《川行琐记》风波的延续。参见:叔永《四川问题的又一面》,《独立评论》第214号;《关于〈川行琐记〉的几句话》,《独立评论》第215号。有关20世纪二三十年代军阀刘湘时期的重庆旧有都会生态及城市化研究,参见:张瑾著《权力、冲突与变革——1926-1937年重庆城市现代化研究》,重庆出版社2003年版。
㉘何鸿钧口述资料,是1995年6月3日笔者在重庆出版社退休编审何鸿钧家中的采访记录。何鸿钧(1919-2007),重庆市秀山人,1937年考入重庆求精中学高中,1940年秋考入复旦大学新闻系,1944年秋毕业,1945年至1952年任重庆《新民报》记者、采访主任、编辑,后任重庆人民出版社编辑、重庆出版社政经编辑室副主任、主任,1987年评为编审,1989年退休。《嘉陵江日报》的文本也可印证何鸿钧的回忆,见:《“上江人”与“下江人”》,《嘉陵江日报》1939年10月19日第2版;苦口《四川人与“下江人”》,《嘉陵江日报》1939年7月9日第4版。有关“下江人”相关研究,可参见:张瑾《民国时期“下江人”的形成与认同刍议》,《西南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1年4期,第102-106页。
㉙梁侃的论文从政治意识形态和文化意义来讨论国民政府内迁后与四川地方的政治文化融合问题,颇有意义。然而,作者所建构的论题的史料来源单一,仅以“下江人”的主观文本并不能全面阐释战时重庆城市形象变迁的阶段性与特质。
㉚《蒋中正电示吴国桢规定民家商店悬收国旗时间并令警察切实执行(1 9 4 0年1 2月3 0日)》,“国史馆”:蒋中正“ 总 统 ”文物,典藏号002010300041057;《蒋中正手令及批示(二)(1941/01/23-1948/01/26)》,第45页,“国史馆”:国民政府档案,入藏登录号001000002111 A。
㉛《蒋中正手令及批示(三)》,第19、61-62页,“国史馆”:国民政府档案,入藏登录号001000002112 A。
㉜“新生活运动”的概念原本是1934年2月17日蒋介石在南昌剿共期间所思考形成。他认为,用军事力量收复中共占领的区域,尚不能完成使命,须继以社会的和经济的复兴工作才行;而欲谋物质的繁荣,尤须先行发扬民族道德,建立互助合作的精神,以纠正人民萎靡苟且的习尚。以中国固有的礼、义、廉、耻“四维”为基础创导的新生活运动由南昌试验,继而推广于全国。战前新生活运动的日常性工作,如“清洁规矩运动”、“季节性工作”、“劳动服务运动”、“三化方案推行”、“节约运动”、“改革习俗工作”等项,均以个人日常生活内容为主。全面抗战爆发后,新生活运动在工作内容上出现以战地服务为主的趋势。参见:吕芳上主编《中国抗日战争史新编:(一)合战抉择》,台北:“国史馆”,2015年7月印,第279-292页。在大后方重庆,新生活运动直接关涉到地方秩序和都市形象的建构问题。仅以重庆市档案馆藏档案为例,关涉都市形象的“整饬市容”与人们日常生活的衣食住行规范和卫生行为规范结合起来,如《新生活运动促进总会、重庆市夏令卫生运动委员会主办夏令卫生运动敬告“旅馆业”、“浴室业”、“茶社业”、“摊贩业”、“理发店”、“告市民书”、“住户书”等(1940年7月31日)》,重庆市档案馆:典藏号0066-0001-0041;《行都夏令卫生运动宣传大纲(1940年)》,重庆市档案馆:国民党重庆市执行委员会全宗,典藏号0051-0004-0028。
㉝《国民政府蒋中正手令及批示(二)(1941/01/23-1948/01/26)》,第42 页,“国史馆”:国民政府档案,入藏登录号001000002111 A。有关蒋介石在渝期间的手令,也可参见重庆市档案馆藏重庆市政府全宗相关文献。
㉞《重庆市警察局长徐中齐为拟更全市地名一览表事致重庆市市长蒋志澄的呈(1938年12月11日)》,第6页,重庆市档案馆:重庆市政府全宗,典藏号0053-0029-0110。
㉟《订正街道名称》,《中央日报》1938年12月13日第3版。《陈克文日记》也记录了因重庆地名的紊乱而找不到地址或跑冤枉路的情况。
㊱㊲《关于报送更改街名一览表的呈、指令及附表(1939年1月19日)》,第7-21页、31-32,重庆市档案馆:重庆市政府全宗,典藏号0053-29-110。
㊳《本局最近一周来之重要工作》,重庆市档案馆:重庆市卫生局全宗,典藏号0066-0002。
㊴重庆市档案馆:重庆市卫生局全宗,典藏号0066-卫-57-2;《取缔防害公共卫生案》,重庆市警察局全宗,典藏号0061-0016-5086(1);《处理违反卫生案件》,重庆市警察局全宗,典藏号0061-0016-5072;《取缔随地吐痰运动办法》,重庆市警察局全宗,典藏号0061-0016-5085。
㊵重庆市档案馆:重庆市卫生局全宗,典藏号0066-0001-0003。
㊶重庆市档案馆:重庆市政府全宗,典藏号0053-0003-0076。
㊷《重庆市卫生局工作报告(1940年3月至8月)》,第162页,重庆市档案馆:重庆市卫生局全宗,典藏号0066-0001-0003。另,有关灭鼠告示,参见:《新都的老鼠》,《浙江青年》第1卷第1期,第8页。
㊸《重庆市临时参议会参议员提案·参议会卫生组召集人连雅各布报告(1942年7月10日)》,第7-8页,重庆市档案馆:重庆市参议会全宗,典藏号0054-0001-00224。提案还指出:“公私厨房亟需改善”,大多是“烟尘臭气污秽满室”,“合乎卫生条件者百不一见”;“公私厕所亟应改善”,“查本市公私厕所多与阴沟相通,蝇鼠密集”,“臭气熏人”;“本市所售食物水果应实施检查”;城市空气因煤烟污染严重,“应设法改用无烟煤代替烟煤,使空气清洁”。另外,相关状况,还可参见参议员陈铭德在市政视察卫生组视察报告第101页中提到的问题。参见:重庆市档案馆:重庆市参议会全宗,典藏号0054-0001-00224。
㊹参见:《新民报》1939年9月21日《今后的四川》,10月17日代论《建设川康 川人应有的责任》,10月19日《刷新川政复兴中华,蒋委员长同四川同胞约法三章》;《时事新报》10月19日社论《四川——复兴根据地》。
㊺蒋介石对四川问题的关切,在唐纵日记中有所记载。如:1941年6月17日,唐纵记:“昨日委座在扩大纪念周声称,四川为中央之四川,非谁人之四川。满清三百年之天下,尚且可以推翻,尚有何可惧!如果再有地主土劣把持粮食,不遵中央命令,政府决不宽贷。”6月18日,他又记:“从委座近日对四川问题讲话之观点,似有解决川局之决心。”《在蒋介石身边八年——侍从室高级幕僚唐纵日记》,群众出版社1991年版,第275页。
㊻有关此次受命重庆市市长,吴国桢的回忆是:“在那时局紧张之际,四川人与下江人隔阂尚未厘清,派贺(国光)实比派吴为得也。”“贺(国光)本来在张(群)以前任行营主任,其绰号为贺婆婆,是一著名的好好先生,为四川军阀政客所熟知,此时派充重庆市长,自易为市民接受。”参见:吴国桢手稿《吴国桢传》下册,黄卓群口述,刘永昌整理,台北自由时报1995年初版,第308-309页。
㊼据重庆市档案馆藏档案,战时重庆市政建设有一套完整的官方行政流程。以蒋介石有关市政问题的手谕/手令为起点,国府与市府“自上而下”的工作秩序是:“蒋介石手谕/手令—市政府呈复—侍从室派员检查、签核意见—交办市府饬警察局、卫生局、工务局切实纠正—市长批示。”此外,关于工作执行的绩效考核也有一套细致的文案,再以蒋介石手谕/手令关于规范重庆市国旗悬挂仪式的执行情况为例,其考核点与程序为:悬挂国旗的方式、距离地面的高度、使用挂杆等、时间、使用设备等评价指标。为促效果,各项举措也出台相关“竞赛”项目。然而,有关市政举措的实际执行情况,可从媒体的批评文本中看出重庆城市改造之难。如:邹明初《再论战时行都的交通问题(社评)》,《新民报》1939年12月30日第2版;《社评:重庆市建设方案》,《新民报》1940年3月1日第2版;《社评:关于陪都建设》,《新民报》1940年10月25日第2版;《读者之声:“住”和“行”》,《新民报》1940年12月20日第5版;《社评:重庆住的问题》,《时事新报》1943年4月3日第2版。
㊽重庆市临时参议会成立于1939年8月,历时两届,1946年国民政府还都南京前正式成立参议会。前后三届参议会共计10年,集会23次。该会设有秘书处及民政、经济、建设、文教、法制、社会行政等专门工作委员会。主要职责是筹议研究重庆市政府重要建设方针,听取重庆市政府施政报告,向市政府提出建议案、询问案。该全宗档案共计802卷,藏于重庆市档案馆,其中有关市政建设等提案是研究战时重庆城市形象的第一手文献。
㊾有关重庆在轰炸中的形象,参见张瑾《重庆大轰炸期间的宋美龄》,《重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20卷第1期,第150-158页。
[1]梁侃.重庆作为战时首都的政治与文化意义[C]//纪念七七抗战六十周年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上册.台北:“国史馆”,1998.
[2]董显光.董显光自传:一个中国农夫的自述[M].曾虚白译.台北:台湾新生报社,1974.
[3]生气蓬勃的新都[J].家庭与妇女,1940,1(6):276-277.
[4]〔美〕白修德.探索历史——白修德笔下的中国抗日战争[M].马清槐,方生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7.
[5]Theodore H.White.In Search of Histor y:A Personal Adventure[M].Har per & Row Publishers,1978.
[6]抗战期中的北碚市历年户口的变迁[N].嘉陵江日报,1939-07-09(2).
[7]广告[N].嘉陵江日报,1938-08-05(2).
[8]广告[N].嘉陵江日报,1939-05-05(2).
[9]广告[N].嘉陵江日报,1939-07-10(3).
[10]为不再使尊夫人悔恨起见[N].嘉陵江日报,1938-03-22(2).
[11]唐幼峰.重庆旅行指南[M].重庆:重庆书店,1933.
[12]杨世才.重庆指南[M].第3版.重庆:北新书局,1939.
[13]杨世才.重庆指南[M].第4版.重庆:北新书局,1940.
[14]北平厚德福饭庄北碚分号启事[N].嘉陵江日报,1939-07-12(2).
[15]沧一.重庆现状[J].宇宙风,1938,(69):154.
[16]Randall Gould.Chungking Reading Public Intent on Wider Horizons[N].The Christian Science Monitor,1943-10-09(11).
[17]〔美〕白修德,贾安娜.中国的惊雷[M].端纳译.北京:新华出版社,1988.
[18]陈公博.对重庆说些话[N].中央日报,1938-10-02(4).
[19]端木露西.川居[N].中央日报,1938-09-25(星期增刊).
[20]陈公博.秩序似乎太乱了[N].中央日报,1938-10-09(4).
[21]吴济生.新都见闻录[M].上海:光明书局,1940.
[22]Martha Gellhorn.Tr avels with Mysel f and Another,A Me moir[M].New York:Jeremy P.Tarcher Putnam,1978.
[23]刘显曾(整理).刘节日记(1939-1977)[M].郑州:大象出版社,2009.
[24]重庆市建设方案[J].档案史料与研究,2002,54(3).
[25]重庆市抗战四年来之建设状况[J].档案史料与研究,2001,48(1).
[26]陈克文日记(1937-1952):上册[M].陈方正编辑校订.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12.
[27]杨世才.重庆指南[M].第5版.重庆:北新书局,1941.
[28]〔美〕巴巴拉·塔克曼.史迪威与美国在华经验[M].陆增平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4.
[29]陈公博.应对卫生注意些吧![N].中央日报,1938-10-05(4).
[30]捐助银杯义卖[N].中央日报,1939-01-01(3).
[31]瘦梅.新都的新生活[J].家庭与妇女,1939,1(5):217.
[32]严禁公务人员赌博跳舞冶游[N].中央日报,1938-12-22(3).
[33]陆思红.新重庆[M].上海:中华书局,1939.
[34]彭伯通.古城重庆[M].重庆:重庆出版社,1981.
[35]重庆市卫生志(1840-1985)[M].重庆:重庆市卫生志编委会办公室,1994.
[36]社评.论重庆市政[N].大公报,1942-12-14(2).
[37]社评.重庆市的“行”[N].时事新报,1943-04-06(2).
[38]社评.市政感言[N].大公报,1945-07-21(2).
[39]社论.复员后的市政[N].时事新报,1945-12-19(2).
——重庆市大足区老年大学校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