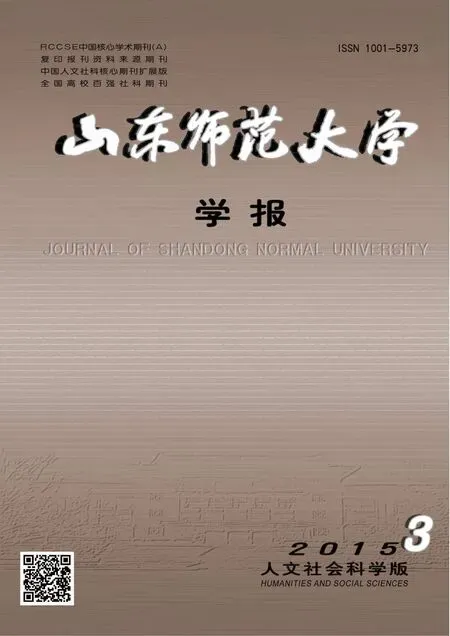透过《新青年》触摸五四文学革命真相*
朱德发
( 山东师范大学 文学院,山东 济南,250014 )
透过《新青年》触摸五四文学革命真相*
朱德发
( 山东师范大学 文学院,山东 济南,250014 )
《新青年》是五四文学革命的主媒体与主阵地,只要设身处地回到《新青年》这块历史现场,对胡适、陈独秀等文学革命先驱们的原创文本及其心态予以体察与感悟,便可透视出五四文学革命既未“彻底反传统”又未“全盘西化”,而是以科学的方法对传统文学进行“整理”。究竟是谁对五四文学革命作出“彻底反传统”的误判,从回望五四文学革命的研究史或接受史可寻找到答案。新中国成立至今60多年,大致是从由政治革命与文学革命关系、思想革命与文学革命关系乃至文学革命自足系统所构成的三大认知框架,来研究或接受五四文学革命的;而这三大认知框架从纵向上形成了对五四文学研究或接受的三个历史的或逻辑的层次,而正是从第二个逻辑层次的认知模式中,可以寻找出“彻底反传统”误判的源头。惟有回到文学革命自身系统,才能恢复其历史真相,以抵制新儒学派对五四新文学的无端指责与妄评。
《新青年》;五四文学;新儒学派;陈独秀;胡适;鲁迅
国际数字对象唯一标识符(DOI):10.16456/j.cnki.1001-5973.2015.03.001
《新青年》创刊百周年,它作为新文学与新文化生成的母体和传播媒体,被人们阅读或研究了近百年,难道五四文学革命的真相至今尚未摸清吗?其实这并不奇怪,它作为一个文化信息、文学信息皆丰盈充实的历史文本,由于阅读者或研究者深受历史条件和自身条件的限制,自然会导致每代人有每代人阅读的感受与体悟,甚至每个人有每个人研究的认知,见仁见智势所必然。因而,笔者此次研读《新青年》亦仅仅是重新触摸五四文学革命真相,难以做到完全还原其真相。
五四时期是个特定的历史范畴,它既不能定为“五月四日”这一天,又不能任性地将其界域扩大。笔者认同20世纪30年代茅盾对五四时期的界定,即从1917年至中共成立的1921年这五年。①茅盾说:“‘五四’这个时期并不能以北京学生火烧赵家楼那一天的‘五四’算起,也不能把它延长到‘五卅’运动发生时为止。这应该从火烧赵家楼的前二年或三年起算,到后二年或三年止。总共是五六年的时间。火烧赵家楼只能作为运动发展到实际政治问题,取了直接行动的斗争态度,然而也从此由顶点而趋于下降了。这样去理解‘五四’,方能够把握得‘五四’的真正的历史意义。”(见1931年8月《前哨·文学导报》第1卷第1期,署名丙申)这就是五四文学革命生成的特定历史范围。《新青年》创刊到停刊是1915年9月至1922年7月,笔者透过对它的解读来触摸文学革命真相,就限定在1917年至1921年这个历史空间。至于1921年7月共产党成立所标志的“后五四时期”,则非本文研究的范围。
一
《新青年》承载的文学革命信息与形态,能够较为辩证地对待中国古代文学,既没有对它绝对的肯定又没有绝对的否定;至少在文学变革的层面上没有形成如域外学者所说的“五四式全盘性反对传统权威的运动”②[美]林毓生:《论自由与权威的关系》,《五四:文化的阐释与评价》,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139页。,即“全盘性的反传统主义”,也没有像国内学者描述的那样:“如此激烈否定传统、追求全盘西化,在近现代世界史上也是极为少见的现象。”*李泽厚:《中国现代思想史论》,北京:东方出版社,1987年,第8页。从当年文学革命的实际情况来看,尽管对古代文学有所否定却没有完全否定,尽管对文学传统有所反对却没有彻底地全盘地反对,这就是《新青年》所显示的文学革命真相之一。
就以《新青年》传播的文学革命主张来说,学界大多认为胡适是彻底反对古代文学传统、追求全盘西化的代表,近半个世纪的五四文学研究几乎都是这样误解甚至诋毁他,甚至到了思想解放的20世纪80年代,一部所谓权威的“现代思想史论”竟能绕过胡适来谈论五四新文化运动与文学革命,这本身就是对历史真相的遮蔽。怎样才能对五四文学革命是否彻底反传统给出有理有据的历史判断?胡适是五四文学革命的总策划者、总设计师、首举义旗者,也是积极尝试新文学的带头者,这一历史地位是由历史发展确定好了的,是谁也不能取而代之的;然而,曾有一个历史阶段千百计地抹黑他、打倒他,以致使他在五四文学史上的真实面目长时期并不清晰。所以,要弄清五四文学革命的真相,无论如何不能疏离或绕开胡适在《新青年》这个舞台上的表演。
胡适于1917年10月发表在《新青年》上的《文学改良刍议》和1918年4月发表在《新青年》上的《建设的文学革命论》,既是他本人“闹”文学革命的系统主张,又是五四文化先驱们所认同的文学革命的重要宗旨。前者是从“破坏”入手论述文学改良,后者是从“建设”方面来设计文学革命蓝图,这是众所周知的常识。然而,有的学者在考察五四文学革命对古代文学或传统文学的态度和策略时,却或者忽视这两篇至关重要的原创理论文本,或者曲解它们。如果说在不正常的政治气候下这样做是可以理解的话,那么在思想解放的改革开放时期仍坚持这样的做法实在是不应该了。必须坦率地承认,胡适在这两篇文论中即使从“破坏”方面来探讨文学革命问题,尽管有的见解带有偏颇,然而总体上却也是坚持着科学与民主的求真务实的较为辩证的态度,把问题的讨论与解决始终纳入学术轨道。他所提出的有名的文学改良“八事”,既没有全盘否定“近世文学”,又没有全盘否定古代文学,对任何形态的文学都能坚持有破有立或者破中有立的思维方法,所破的是近世或古代文学的“大病”,而不是整个文学结构系统。因此,欲改良的不是所有的传统文学而是有“大病”的文学,根治了“大病”可以使文学的肌体更健全更完美,从而使那些没有弊病的文学作品或文学传统得到弘扬与承传,使那些有价值的文学越来越“益贵”且彪炳于千古文学史。这不是“彻底反传统”,而是医治文学的“大病”,以利于更好地光大传统。只要尊重史实的学人,都能清楚地看到胡适在指斥“近世文学之大病,在于言之无物”的同时,并没有只揭露南社所谓“第一流诗人”陈伯严的“涛园钞杜句,半岁秃千毫”的摹仿古人的“奴性心理”;而且亦褒扬了“今日之文学,其足与世界‘第一流’文学比较而无愧者,独有白话小说(我佛山人,南亭亭长,洪都百炼生三人而已)一项”,特别是称赞了文学史上“庄周之文,渊明老杜之诗,稼轩之词,施耐庵之小说,所以复绝千古也”。在胡适批判“今人犹有鄙夷白话小说为文学小道者”的同时,充分肯定了“施耐庵、曹雪芹、吴趼人皆文学正宗,而骈文律诗乃真小道耳”;当胡适指斥“吾国言文之背驰”而用死文言创造不出“活文学”的时候,他坚定认为“辽、金、元”三百年中国北部“发生一种通俗行远之文学”即白话文学,“文则有《水浒》《西游》《三国》之类,戏曲则尤不可胜计(关汉卿诸人,人各著剧数十种之多。吾国文人著作之富,未有过于此时者也)”,并断言“白话文学之为中国文学之正宗,又为将来文学必用之利器”*胡适:《文学改良刍议》,《新青年》1917年1月1日第2卷第5号。。这就是胡适首举文学革命义旗时对中国近世或古代文学“大病”诊断并“治之”所采取的方略,表现出其求真务实的科学分析态度;况且,“然此八事皆文学上的根本问题,一一有研究之价值”,作者并不想把“草成此论”强加于人,“伏惟国人同志有以匡纠是正之”。这并非如有人所批评的是表现了胡适在文学革命中的软弱性与妥协性,而是作为一个倡导者在中华民国国体里欲为“大中华造新文学”应具有的谨慎、严肃、谦虚的风范;否则,其文学革命主张不可能产生如此大的反响,并聚众结为《新青年》派而成就大业。
可见,在《文学改良刍议》中找不到胡适在文学艺术层面“彻底反传统”乃至“全盘西化”的充分根据;那么,在次年发表的《建设的文学革命论》所提出的“国语的文学,文学的国语”的建设新文学与标准国语的双向互动的宗旨中,就能察觉出胡适“彻底反传统”的用心吗?诚然,胡适确实认为“中国这二千年只有些死文学,只有些没有价值的死文学”;这些死文学“都是用已经死了的语言文字做的”,故“死文字决不能产出活文学”。但是,这个论断是有说服力的。不只因为它合乎“一个时代有一时代文学”的新陈代谢或革故更新的进化规律,也符合数千年中国文学演变的实际。试想,我国有文字记载以来有多少文学被淘汰?而淘汰了的文学在正常的政治生态与文化语境下则大多是或全部是死文字写的死文学;因之,无论在何时代都不能把淘汰死文学视为“反传统”,即使硬说成“反传统”也是清除了传统文学的“糟粕”,而保存下传统文学的“精华”。况且,胡适对中国二千年文学所给出的判断并不是全面否定的,即不是所有的文学都是“死文学”,只是说“有些死文学”;而其他的文学或中国的正宗文学则是:“自从《三百篇》到于今,中国的文学凡是有一些价值有一些儿生命的,都是白话的,或是近于白话的。”古代有《木兰辞》《孔雀东南飞》,陶渊明的诗,李后主的词,杜甫的《石壕吏》《兵车行》等;近世的《水浒传》《西游记》《儒林外史》《红楼梦》,皆可以称为“活文学”。这是肯定并颂扬中国优秀传统文学,哪里是“彻底反传统”?不仅如此,胡适曾多次强调我国传统的正宗白话文学是建设五四新文学所必须承传并借鉴的“模范的白话文学”*胡适:《建设的文学革命论》,《新青年》1918年4月15日第4卷第4号。,这表明,他是自觉地有意识地将我国优秀传统文学与创造五四新文学对接起来,并没有以否定或断裂传统文学为前提来建设新文学。1921年,胡适在给教育部第三届国语讲习所授课编写的《国语文学史》中,提出二千余年的中国文学形成了庙堂文学或贵族文学与国语文学或民间文学两大潮流:“从《楚词》变化出来的‘赋’,此后二千余年间,庙堂上都依着这个例演化许多贵族文学;所谓‘国语文学’者,其源头大都起自民间,大都是各时代从民间涌现出来的‘反庙堂’的文学潮流。”*《胡适全集》第11卷,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年,第9-10页。且不论这种区分是否准确,至少可以看出作为五四文学革命首倡者与谋划者的胡适对二千多年的中国文学进行过认真研究和系统梳理,他提出的文学改良“八事”或文学建设的“十字方针”都是有充分的学理根据和史实根据的,而所创造的新文学不是以“彻底反传统”为前提乃是以赓续传统文学为基石。至于“后五四时期”胡适对传统文学研究所取得的突破性的创新成就及其独著的《白话文学史》,更能显示出他对传统文化或传统文学的较为辩证的科学态度。
着眼于文学理论形态考察,作为五四文学革命的领袖之一的胡适,并没有把新文学运动引上“彻底反传统”直至“全盘西化”的道路,这就是《新青年》所记载的历史真相;那么,五四文学革命的另一位领袖陈独秀是否将新文学运动导入此路呢?
史实胜于雄辩。陈独秀于1915年9月创刊《新青年》(第1卷名“青年杂志”),并未提倡文学革命,既无主张又无尝试,仍以文言宣传新思想新文化,即使是年在该刊第3、4号上发表的《现代欧洲文艺史评》,指出“吾国文艺犹在古典主义理想主义时代,今后当趋向写实主义”,也仍然处在思想犹豫不决的矛盾中,即吾国文艺究竟提倡“古典主义”为宜还是“趋向写实主义”为宜?这种矛盾心态主要体现在陈独秀对“贵报三号登某君长律一首”的“按语”中。明明这首长律用典不当、文法不通,是属于“古典主义理想主义时代”的诗,而陈氏却把它“推为‘希世之音’”,又说它是“子云相如而后,仅见斯篇;虽工部亦只有此工力,无此佳丽”;由此可见“吾国人伟大精神,犹未丧失”。陈氏在自己主编的《新青年》发表这首“长律”且又给出如此拔高的推崇,这既表明其对我国古典主义文学的弊端视而不见且深深“迷恋”,又说明他没有认清惟有白话文学方是中国文学之正宗,也没有确立文学变革必须趋向“写实主义”的坚定信念。难怪胡适批评他:“适所以不能已于言者,正以足下论文学已知古典主义之当废,而独啧啧称誉此古典主义之诗,窃谓足下难免自相矛盾之诮矣。”*胡适:《寄陈独秀》,《新青年》1916年10月1日第2卷第2号。此时的陈独秀不是“反传统”文学而是维护了“传统文学”不该维护的“弊端”;然而,陈氏毕竟是位有气魄有胆识有才华的文化革命英雄和文学革命领袖,当1917年1月《新青年》发表了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之后,他旋即发表了《文学革命论》,不仅自觉地把“孔教问题,方喧呶于国中”的“伦理道德革命”即新文化运动与文学革命捆绑在一起,而且坦然无畏地声明:“文学革命之气运,酝酿已非一日,其首举义旗之急先锋,则为吾友胡适。余甘冒全国学究之敌,高张‘文学革命军’大旗,以为吾友之声援。”于是,他提出了“吾革命军三大主义:曰推倒雕琢的阿谀的贵族文学,建设平易的抒情的国民文学。曰推倒陈腐的铺张的古典文学,建设新鲜的立诚的写实文学。曰推倒迂晦的艰涩的山林文学,建设明了的通俗的社会文学”。有些学人就以“三大主义”的三个“推倒”为据,便断定陈独秀“反传统文学”的立场和态度比之胡适坚定而彻底;虽然不能说这种认知有误,但至少缺乏对《文学革命论》的细读精析而给出了草率的评判。陈氏欲“推倒”的仅是传统文学总体系统中的三种形态的文学,而不是对传统文学整体系统的颠覆,即使“推倒”的三类文学也是或染有“雕琢的阿谀的”病症的贵族文学而不是所有的贵族文学,或染上“陈腐的铺张的”病症的古典文学而不是所有的古典文学,或染上“迂晦的艰涩的”弊病的山林文学而不是所有的山林文学。尽管陈氏对传统文学这三种形态弊病的揭露没有胡适在文学改良“八事”中剖析得那么切实具体,然而这两位文学革命首领都能击中古代文学必须予以变革的要害,并相互声援携手共进,同心协力地撬动这场文学革命。既然要革古代文学的命,使用“推倒”这样的用语难免激烈一些,而“予愿拖四十二生的大炮,为之前驱”*陈独秀:《文学革命论》,《新青年》1917年2月第2卷第6号。的表述也显得“火药味”浓了些;不过陈氏主张文学革命的三个“推倒”只是欲“推倒”病态的古代或近世文学并非所有的传统文学,故而不是“彻底反传统”乃是清除传统文学的弊病,使我国传统文学焕发新的生机与活力。
有些学人往往以陈独秀的《本志罪案之答辩书》为根据,指斥五四文学革命是“彻底反传统”,并以此为口实来诋毁五四新文学。当时社会上“八面非难”《新青年》的“旧人物”甚至“青年学生”主要不是针对“文学革命”乃是思想文化运动,“把《新青年》看作一种邪说,怪物,离经叛道的异端,非圣无法的叛逆”,甚至非难《新青年》“破坏孔教,破坏礼法,破坏国粹,破坏贞节,破坏旧伦理(忠孝节),破坏旧艺术(中国戏),破坏旧宗教(鬼神),破坏旧文学,破坏旧政治(特权人治)”。对《新青年》杂志的这种非难或否定的口气,完全出自于一种极端偏激的社会心理与逻辑思维,至少没有系统认真地阅读与领会《新青年》所发表的一切文章,只是抓住一点不及其余或捕风捉影或道听途说地进行攻击与诽谤,妄图把《新青年》一棍子打死。且不说其他,就以文学革命为例,无论胡、陈的文学主张还是其他《新青年》同仁的文学见解,都不是完全破坏中国“旧文学”而主要是揭露其弊病,以进行改革而创造新文学。“那些旧人物”之所以痛心疾首地肆意诋毁《新青年》,追本溯源就是因为“本志同人”拥护“德先生”(民主)和“赛先生”(科学),而“要拥护德先生又要拥护赛先生,便不得不反对国粹和旧文学”*陈独秀:《本志罪案之答辩书》,《新青年》1919年1月15日第6卷第1号。,因为“国粹和旧文学”没有或缺乏现代民主精神和科学精神。陈独秀尽管在1915年《新青年》创刊号的《敬告青年》曾鼓吹“科学与人权并重”的思想,然而真正地把“德先生”与“赛先生”作为五四新文化运动两面大旗高高举起则是在《答辩书》中。这不仅表明为全人类所拥护所认同并带来莫大福祉的民主思潮与科学思潮已照进古老而幽暗的中国,而且也说明五四新文化新文学双向互动的运动是在这两大旗帜引导下兴起的,而运动本身亦体现了“民主”与“科学”精神。具体到文学革命,有了这两大精神,先驱们大都能自觉地以“民主”与“科学”的态度来分析或处理文学变革的问题,使新文学运动能沿着正常轨道运行,它怎能以彻底否定传统文学为前提而在空空荡荡的一片废墟上建设新文学呢?
既然文学革命两个首领并没有在《新青年》里鼓荡“彻底反传统”思潮,那么其他文学革命先驱或主将是否走上这条极端偏激的“彻底反传统,全盘西化”的道路?这里只能略加分析。钱玄同是五四文学的积极拥护者也是中国著名的音韵学专家,他在《寄陈独秀》信中既赞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陈义之精美,前已为公言之矣”,特别“胡君‘不用典’之论最精,实足祛千年腐臭文学之积弊”;又对文学改革“八事”或给以补充或提出异议,无不对古代文学作品作出具体分析,该赞的就赞,该斥的就斥,是给传统文学诊病治病而绝对不是否定传统文学;同时,他也认为苏曼殊的“思想高洁,所为小说,描写人生真处,足为新文学之始基乎”,亦称“梁任公实为创造新文学之一人”*钱玄同:《寄陈独秀》,《新青年》1917年3月第1号。。至于“社会上最反对的,是钱玄同先生废汉文的主张”,是否能以此为据给钱玄同戴上“彻底反传统”的帽子?这也应该作具体分析。因为钱氏乃中国著名的文字学家和音韵学家,他是依据人类语言文字自然进化规律提出的个人之见,并不代表文学革命先驱们都持此见,即使偏激也只限于语言文字领域并未涉及文学艺术领域,故而不能以此为理由说整个五四文学革命是“彻底反传统”的,对此陈独秀在《答辩书》中有更深切的回答。被鲁迅赞为《新青年》的“一个战士”的刘半农,“活泼,勇敢,很打了几次大仗”*鲁迅:《忆刘半农》,《鲁迅全集》第6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第71页。,即使这样一位战绩卓著的新文学英雄也没有在《我之文学改良观》中表现出“彻底反传统”的激进倾向,而是完全采取一种民主讨论与求真务实的态度来对待文学改良问题。首先他承认“文学改良之议,既由胡君适之提倡之于前,复由陈君独秀钱君玄同赞成之于后”,除了对“胡君所举八种改良,陈君所揭三大主义,及钱君所指旧文学种种弊端,绝端表示同意外”,并没有随声附会地完全盲从,而是就“文学之界说”、“文学与文字”之关系、“韵文之当改良者三”以及“形式上的事项”发表了独立之见。其中有些见解是对前三位文学革命主张的补充与细化,有些见解则是创新之见。例如,他认为“即吾辈主张之白话新文学,依进化之程序言之,亦决不能视为文学之止境,更不能断定将来之人不破坏此种文学而建造一更新之文学”*刘半农:《我之文学改良观》,《新青年》1917年5月1日第3卷第3号。,从而表现出他的远见性。即使以中外文学比较方法来分析中国古代与近世的文学弊端,刘半农也没有绝对的否定,更没有彻底否定整个传统文学,而是问题抓得准,理论析得透,令人诚服。被称为五四文学革命“双柱”的“周氏兄弟”,既是新文学理论的倡导者又是新文学实践的高手。鲁迅是听《新青年》“将令”创造了世界一流的短篇白话小说,并对中国传统文学尤其是小说作了系统研究,著成《中国小说史略》由北京大学新潮社于1923-1924年出版,其非反传统文学而是更好地继承了传统文学。其弟周作人连续发表两篇倡导文学革命的重要文论,一是《人的文学》*周作人:《人的文学》,《新青年》1918年12月15日第5卷第6号。,一是《平民文学》*周作人:《平民文学》,《每周评论》1919年1月19日第5号。,皆是从文学内容的改革上对国语文学主张给出的补充与深化。前者提倡以个人主义为世间本位主义的“人的文学”,反对中国“从儒教道教出来”的“非人的文学”,虽然在其罗列的十类“非人的文学”中,也有“《西游记》、《水浒》、《聊斋志异》”等,打击或否定面过宽,不免有“彻底反传统”之嫌,但他没有反对自古以来具有人道主义或人文关怀倾向的文学。后者《平民文学》应似《人的文学》的姊妹篇,如果说后文对古代的非人的文学否定太多,那么前文则对平民文学作了具体界说,充分肯定了“《红楼梦》要算最好”的小说,“因为他能写出中国家庭中的喜剧悲剧,到了现在,情形依旧不改,所以耐人研究”。可见,周作人亦没有“彻底反传统文学”,若是联系后来他把五四文学革命视为明末“公安派”、“竞陵派”文学变革的重演,更可以说明周作人对传统文学的态度了。
通过上述的简略考察,足以表明《新青年》兴起的这场文学革命,至少在文学艺术层面并没有“彻底反传统,全盘西化”;尽管有些个别观点偏激一点或者说得绝对一些,然而从总体或全部史实来看,却没有呈示出把新文学与传统文学绝对对立起来的问题。揭露旧文学的弊端决不是“彻底反传统”,借鉴西方的新思潮新方法以创造新文学更不是“全盘西化”。可以老实地说,文学革命通过较为切实的科学态度对传统文学弊病的揭露或对庙堂文学贵族文学的批判,真正复活了中国传统文学的生命力与活力,真正展示出中国文学具有不朽价值与超越意义的特质。试看,今天出版的中国古代文学史里那些当年五四文学革命所肯定与称颂的作家作品不亦是书写的主体对象吗?当今海内外风行流传的中国古代文学的经典名著不亦是当年五四文学革命所承认的“正宗白话文学”吗?当年文学革命先驱甚至视《水浒传》《西游记》《儒林外史》《红楼梦》等为白话文学“模范”,亦算远见卓识吧?由此可以说,五四文学革命至少在文学本体层面没有“彻底反传统”,而是以科学的方法“整理”了文学传统,即清除传统文学系统里的弊端或“国渣”,并梳理了传统文学系统里的“国粹”或“精华”,予以发扬光大。正如当时胡适所说:“整理就是从乱七八糟里面(指旧有的学术思想)寻出一个条理脉络来;从无头无脑里面寻出一个前因后果来;从胡说谬解里面寻出一个真意义来;从武断迷信里面寻出一个真价值来。为什么要整理呢?因为古代的学术思想向来没有条理,没有头绪,没有系统,故第一步是条理系统的整理。因为前人研究古书,很少有历史进化的眼光的,故从来不讲究一种学术的渊源,一种思想的前因后果,所以第二步是要寻出每种学术思想怎样发生,发生之后有什么影响效果。”“第三步是要用科学的方法,作精确的考证,把古人的意义弄得明白清楚。因为前人对于古代的学术思想,有种种武断的成见,有种种可笑的迷信”,“故第四步是综合前三步的研究,各家都还他一个本来真面目,各家都还他一个真价值”*胡适:《新思潮的意义》,《新青年》1919年12月1日第7卷第1号。。如果遵照这四个逻辑步骤来“整理”古代文学,那就将“传统文学”的研究纳入科学的学术轨道,真正可以辨清何为文学的“国粹”,何为文学的“国渣”。前者无疑是有价值的传统文学,后者当然就是无价值的传统文学。文学革命先驱们这样来对待古代文学,怎么能说是“彻底反传统”呢?这就是《新青年》昭示我们的历史真相。
二
既然历史真相昭示出五四文学革命在特定的历史范畴与文学层面没有“彻底反传统”,那么这个影响深远的历史误判究竟是如何形成的?为什么至今未得到“正本清源”?这是值得深长思之的。
并非所有的个体或群体的学人都能理直气壮地承认胡适、陈独秀是五四文学革命的领袖,或有些人只承认陈独秀不承认胡适,这种误解有深刻而沉重的政治原因。若政治对历史有意地遮蔽或歪曲,那是相当可怕的;当今,虽已拨开政治乌云而露出历史真相,但在乌云遮蔽时所形成的思维定势却难以打破。故而,作为新文学研究主体,只有彻底从既定的思维成见中解放出来,真正诚服《新青年》承载的铁的史实,方可认清胡、陈二位及其文学革命主张在五四新文学运动中的领袖面目与主导地位,以及钱玄同、刘半农、周氏兄弟等文学革命先驱们所发挥的独特作用。然而,这个《新青年》派在五四时期导演的文学革命这场历史活剧,所运用的思维方法却是进化论的新与旧认知模式,统统把传统文学即古代与近世的文学名之为旧文学或旧派文学,没有从政治上规定其性质,而将建设的国语文学或白话文学、人的文学或平民文学则统统名之为新文学,亦没有从政治上来定性。所以,“反对旧文学”不一定是否定一切有价值的古代文学或传统文学,“提倡新文学”或建设国语文学也不一定要完全肯定它们是有价值的文学。只要不从政治上判定新旧文学性质,它们在中华民国的国体或政体里,皆没有法理为根据将它们彻底打倒;新文学有生成的良性政治生态,而旧文学则有存在的权利,即使文学革命关于“文白之争”展开多次论战,白话处于绝对优势而文言也仍然照样通行,文言书写的传统文学照样出版发行。这不只因为五四文学生成政治背景的中华民国为众声喧哗、百花争妍提供了开放宽松的社会环境,也因为进化论引申出的“新与旧”认知模式,不论是“新”或者是“旧”都不是价值范畴。新文学虽“新”而价值不一定高,旧文学虽“旧”但价值不一定低。对此,文学先驱们皆有明确的界说。茅盾曾言:“最新的不就是最美的、最好的。凡是一个新,都是带着时代的色彩,适应于某时代的,在某时代便是新。”*茅盾:《小说新潮栏宣言》,《小说月报》1920年1月25日第11卷第1期。故而“新”缺乏价值内涵,仅仅是个时代的标志。周作人亦说过:“新旧这个名称,本来很不妥当。其实‘太阳底下何尝有新的东西?’思想道理,只有是非,并无新旧。要说是新,也单是新发见的新,不是新发明的新。”*周作人:《人的文学》,《新青年》1918年12月15日第5卷第6号。既然“新”非价值范畴,那么从进化论引申出的新与旧认知模式所命名的新文学或旧文学都不是美与丑、好与坏的价值标志。因此,文学先驱们“反对旧文学”并不意味着否定一切有价值的古代文学,更不是彻底否定一切有价值的传统文学。事实上,他们对“旧文学”的态度也是如此。
略考五四新文学的接受史或研究史可知,1935年赵家璧主编的《中国新文学大系》既是对五四时期文学革命取得的文论成果和创作成绩的总汇,又是对五四新文学从理论主张到各体作品的总评。从其为各个大系所撰写的“导论”来看,可以说真实地展示了五四时期文学革命的本来面貌,既没有给新旧文学进行阶级定性更没有把“反对旧文学”认定为“彻底反传统”,只是从史实或史料出发以进化论的“新与旧”认知思维对五四文学给出了“信史”的书写,它的历史真实性经过漫长的时间检验至今不可撼动。当1939年李何林编著《近二十年中国文艺思潮论》时,他力图运用阶级论框架,对五四文学革命进行阶级分析,给出阶级的政治的定性,说“德先生”所标示的“民主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政治形态;科学是资本主义的思想体系”,而“文言文”则是“封建文化的表现工具”,“反封建的思想”充满了“新文学运动的整个内容”。*李何林:《近二十年中国文艺思潮论》,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5-6页。然而,李何林对五四新文学所作的阶级分析并未达到应有的思想高度,尤其对中国新文学的性质及其领导思想作出了误判,在1949年解放前夕受到批判。他在“自评”中曾检讨说:“我对于五四前后一二年反古文、文言文的斗争和提倡白话文的运动,认为是资产阶级的文学运动”,并没有说“这是在无产阶级及其思想领导下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革命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反帝反封建反买办资产阶级(一九二七年以后的官僚资产阶级)的新民主义的文学运动”。*李何林:《五四以来中国新文学的性质和领导思想问题——〈近二十年中国文艺思潮论〉自评》,《光明日报》1950年5月4日。1951年新中国教育部主导拟订的《〈中国新文学史〉教学大纲》明确规定五四新文学“不是‘白话文学’、‘国语文学’、‘人的文学’、‘平民的文学’等等”,而是“无产阶级思想领导”的“新民主主义的文学”*《〈中国新文学史〉教学大纲(初稿)》,《新建设》1951年7月第4卷第4期。;据此,王瑶著的《中国新文学史稿》(1951)、刘绶松所撰的《中国新文学初稿》(1956)都把五四文学革命定性为无产阶级思想领导的反帝反封建的新民主主义文学,而1979年问世的唐弢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史》则是这样断定的:“在文学领域内高举彻底反帝反封建的革命大旗,这个任务不能不落到无产阶级领导的‘五四’以后革命文学的肩上。”*唐弢:《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第6页。这里强调的是“五四”以后而不是“五四时期”的反帝反封建的新民主主义文学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不管这种说法是一种策略还是有什么潜台词,亦不管把五四文学革命定性为无产阶级思想领导的反帝反封建的新民主主义文学是否正确,它们都没有认定五四文学革命是“彻底反传统的”。而从新民主主义文学的彻底反封建的特征中自然可引申出“反封建”就是“反对旧文学”,既然“旧文学”皆是封建主义性质的文学而且又是“彻底反之”,这不就是“彻底反传统”吗?然而上述三种具有代表性的纳入阶级论框架书写的中国新文学史却没有作出这样的判断,究竟何时何人将五四新文学运动误判为“彻底反传统”的?
对于五四文学革命的解读、研究、认知乃至书写,到20世纪80年代发生了重大而深刻的变化。随着改革开放新时期的来临和“实事求是,解放思想”的认识路线的深入人心,包括五四文学研究在内的整个学术界出现了阳光明媚的春天。这里,笔者不禁要回望新中国成立至今,对于五四新文学的接受或研究史。若粗略考析这段接受史或研究史,从阅读、接受的认知框架来看,大致经过了三个历史或逻辑的层次。
第一个层次是建国之初中国新文学史学科成立至“文革”结束,把对五四文学的解读与接受纳入了政治革命与文学革命之间关系所形成的认知框架,以阶级斗争的观点来分析和判断。为了夺取政权和巩固政权的需要,借助五四文学革命的解读或书写来印证无产阶级领导的彻底地不妥协地反帝反封建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是从“五四”开始的。这样一来,五四文学革命顺理成章地成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有机组成部分。因此,它的政治性质和领导思想亦是“无产阶级领导的彻底地不妥协地反帝反封”的。为了证明这一论断的无可辩驳的正确性,不顾史实地抬高早期共产主义者李大钊在新文学运动中的“领导”地位,以此取代五四文学革命真正领袖胡适与陈独秀的领导资格;同时,极力从鲁迅的《呐喊》与《彷徨》小说集中挖掘社会主义思想因素,说《狂人日记》的主导思想是无产阶级的阶级论所致,甚至到“五四”这个特定历史范畴以外去寻找证明史料。随着所谓的阶级斗争、路线斗争的激化,五四文学革命的真正倡导者或实验者胡适、陈独秀、周作人等以不同的“罪名”彻底被打倒,这就意味着以《新青年》为主阵地掀起的那场地地道道的“文学革命”被否定。尽管纳入政治革命视野来解读五四文学革命,将“旧文学”、复古派或旧派文人统统视为封建文学或封建势力,把非对抗性的矛盾变成对抗性矛盾,甚至成了新民主主义革命要推翻的“三座大山”之一,这显然使“旧文学”、复古势力成为新民主义文学的不可调和的敌对一方,属于“彻底地不妥协地反封建”的范围;然而,在这个政治革命的框架里认知和接受的五四文学革命,却罕见“彻底反传统”的表述。
第二个层次是20世纪80年代对“文革”展开大批判的“拨乱反正”、“正本清源”的新时期,将对五四文学革命的研究与接受纳入到思想革命与文学革命之间关系所构成的认知模式,以人道、人性、个性、自由、民主、科学等现代理性思维来解读和认知,并有“实事求是,解放思想”的思想路线为此认知模式的运行扫除路障和禁区。若从思想革命的视角考察五四文学革命,那就侧重于新文学内容的开掘与发现,无疑会判定五四文学革命实质上是一场思想启蒙运动与人的解放运动,它所运用的思想启蒙或人性解放武器无疑是包括个性主义、人道人义甚至社会主义因素在内的以“民主”与“科学”为旗帜的多元复杂的现代意识,它要批判的是整个封建主义制度及其意识形态;那就视“旧文学”是“封建意识形态”的载体进行剖析,从而把中国人特别是平民百姓从封建专制主义及其纲常伦理桎梏中解放出来。由于五四文学革命所参与的彻底反封建的思想革命与80年代兴起的新启蒙运动有诸多惊人的相似之处,为彻底批判“文化大革命”的封建法西斯专制或极左思潮的毒害,将中国人从灵与肉中再次解放出来,主流意识形态便借助五四文学革命的启蒙思想资源,来完成“拨乱反正”的历史使命。伴随着这场新的思想启蒙运动,五四文学革命的研究亦掀起热潮,胡适、陈独秀、周作人等五四时期的风云人物受到正面评价,鲁迅亦走下“神坛”。不过,在思想革命的框架中来解读五四文学革命,既把周作人的《人的文学》所蕴含的个性主义和人道主义当成文学主潮,又将鲁迅的《呐喊》《彷徨》作为中国反封建思想革命的一面镜子,充分发掘出鲁迅小说所达到的难以企及的思想深度和高度,故而严重遮蔽了五四文学革命激荡起的国语文学大潮。所谓“思想革命”就是在意识形态领域里的“革命”,具体到五四时期的意识形态领域的革命就是“提倡新道德,反对旧道德”的革命,亦即以现代新思想来革旧思想的命;而旧文学则是旧思想的载体,所以“反对旧文学”从思想革命的角度来说就是解构封建意识形态。不过,它要解构的不是局部的封建意识,也不是封建思想因素,乃是封建意识形态的整体思想结构。这样,五四文学革命与传统旧文学在意识形态领域就形成了非此即彼的异质对抗的态势。根据这种形而上的直线逻辑推理,很容易获取“五四文学革命是彻底反传统的”结论。在笔者的阅读视野中,记得20世纪80年代见到美籍华人学者林毓生所著的《中国意识之危机》(1979)将五四新文化运动定性为“全盘性的反传统主义”,这个论断是如此的绝对而武断。虽然它是从思想文化的角度研究五四新文化运动而作出的判断,但由于文学革命是新文化运动的重要一翼,无疑也具有“全盘性的反传统主义”的性质。林氏的观点在我国学术界影响深远,不少学人在五四文学研究的著述中引用它、发挥它,就连李泽厚所著的《中国现代思想史论》也认同林氏的“全盘性的反传统主义”的见解,并从思想文化革命的层面纵横捭阖地寻找史料或史实来论证五四新文化运动是彻底反传统的。李泽厚认为,以《新青年》为主媒掀起的“新文化运动的启蒙要求和主张的彻底性和全面性,为谭、严、梁阶段所不可比拟。它以彻底与传统决裂的新姿态和新方式,带来了新的性质”。而这新的性质就是:“主张彻底扔弃固有传统,全盘输入西方文化,便成为新文化运动基本特征之一。”*李泽厚:《中国现代思想史论》,北京:东方出版社,1987年,第11页。认定五四时期的“启蒙性的新文化运动开展不久,就碰上了救亡性的反帝政治运动,二者很快合流在一起了”*李泽厚:《中国现代思想史论》,北京:东方出版社,1987年,第13页。;于是,李泽厚便作出了五四运动是“启蒙与救亡的双重变奏”的影响颇大的结论。尽管林氏和李氏都着眼于思想文化层面对五四运动给出了判断,然而无不深深地影响了五四文学革命的研究或接受,使之大都坚信五四文学革命亦是“彻底反传统”的,并表现了彻底反封建以“启蒙”与彻底反帝以“救亡”两大并举的文学主题。其实,这都是在思想革命的框架里来解读五四文学革命所导致的误判。关于五四文学革命并没有“彻底反传统”,上述已论及;这里只说“启蒙”与“救亡”两大主题的相互变奏的论断是缺乏充足的历史根据的。在五四时期这个特定历史范畴的《新青年》所发表的新文学作品,似乎没有一篇是表现反帝救亡主题的,甚至轰轰烈烈的五四反帝爱国运动在《新青年》上也见不到强烈的反响。这怎能说新文学领域出现了“启蒙与救亡的双重变奏”的主题呢?况且,研究现代思想史撇开了胡适、周作人对于五四新文化运动与文学革命的独特贡献,明明知道一个是新文化与新文学的领袖一个是新文化运动与文学革命的健将却绕过他们而不顾,在“拨乱反正”后出版的李泽厚的《中国现代思想史论》(1987)怎能恢复五四新文化启蒙运动与文学革命的真相?显然只能获得偏颇的历史结论或者导致对五四文学史的重大遮蔽。找来找去,也许上述林、李两位学者就是对五四文学革命作出“彻底反传统”误判的始作俑者。
第三个层次是20世纪80年代中期至今,随着“回到文学本身来研究现代文学”口号的提出,对于五四文学研究或解读或接受亦回到文学革命本身,就是把五四文学革命视为一个独立自足的系统来研读。它虽与政治革命有联系,却不是政治的附庸而是葆有文学革命自身的本体性和规律性;它虽与思想革命的启蒙运动密切相关,但文学革命仍保持自身的独立性和本体性,并没有完全成为思想启蒙的工具。既然回到五四文学革命的本身来研究它,那就要设身处地回到鼓动文学革命的主媒《新青年》这块现场,从文学革命先驱们发表的原创文论或文学作品以及行为痕迹中,去触摸体察文学革命全过程、文学理论主张的性质及其在实践中所产生的影响与效果,从而弄清作为独立系统的文学革命与外在系统政治革命或思想革命的或疏或密、或远或近的关系,于新与旧的进化论的认知模式中发现,五四文学革命不仅没有“彻底反传统”而是运用科学的方法对古代的传统文学开始予以“整理”。
笔者之所以略考五四文学革命的接受史或研究史,不只是要说明五四文学革命即使有反传统之嫌却也没有“彻底反传统”,至于在政治革命或思想革命所构成的认知框架中来解读五四文学革命所作出的“彻底反传统”的论断并不科学,而是为了政治革命或思想革命的需要导致的误读;而且更重要的是为了不给新儒学派以“彻底反传统”的误判作为口实,甚至把方兴未艾的当下对我国数千年传统文化文学的再发现再评价的热潮与百年前的五四新文化新文学运动异质对立起来,借以抹黑或诋毁五四时期生成的新文化与新文学以及文学革命先驱们,并寻找契合点或结合部将古代文化传统与五四开始的现代文化传统衔接起来,以作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体系的源远流长的文化资源。在我看来,若说百年前的五四新文化运动与文学革命是借用了实验主义的科学方法来“整理”数千年的传统文化与文学,强调分清何为“国粹”何为“国渣”,取其前者弃其后者;那么新时期以来对传统文化与文学的再发现再评价则是坚持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史观及其方法论,可以更好地理清传统文化与文学的“精华”与“糟粕”,对前者应极力地发扬光大,切实做到“古为今用”;对后者务必除掉,否则便会“沉滓泛起”,损伤21世纪我国现代性文学的茁壮成长和健康发展。
Through the New Youth to Feel the Truth of the “May-Fourth” Literary Revolution
Zhu Defa
(School of Liberal Arts, Shandong Normal University, Jinan Shandong, 250014)
TheNewYouthis the main media and the main position of the “May 4th” literature revolution. We can perceive the “May-Fourth” literary revolution have neither “radically anti-traditional” nor “totally Westernized”, and get scientific approach to arrange the traditional literature if we just put ourselves in returning to the historic scene of the “new youth” and understand the original text and mentality of Hu Shi, Chen Duxiu and other literary revolution pioneers. Wed can look back to the historical research and acceptant history of the “May Fourth” literary revolution and find who made the misjudgment for the revolution. This article argues that more than 60 years since the founding of New China, there are roughly three cognitive frameworks includ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political revolution and literature revoluti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ideological revolution and the literary revolution and the literary revolution self system to study or accept the “May-Fourth” literary revolution. And the three cognitive frameworks formed the three historical or logical hierarchies in the studies and reception of the revolution on the longitudinal. The present paper aims at the discovery of the sources of the “radical anti-traditional” misjudgment from the second logic level cognitive model. We can recover historical truth only by looking back to its own literary revolutionary system to resist the groundless accusations and absurd comments from the new Confucianism faction.
the “New Youth”;the “May-fourth” literature; the new Confucianism faction; hen Duxiu; Hu Shi; Lu Xun
2015-04-15
朱德发(1935—),男,山东蓬莱人,山东师范大学国家重点学科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资深教授,博士生导师。
I209.6
A
1001-5973(2015)03-0001-11
责任编辑:李宗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