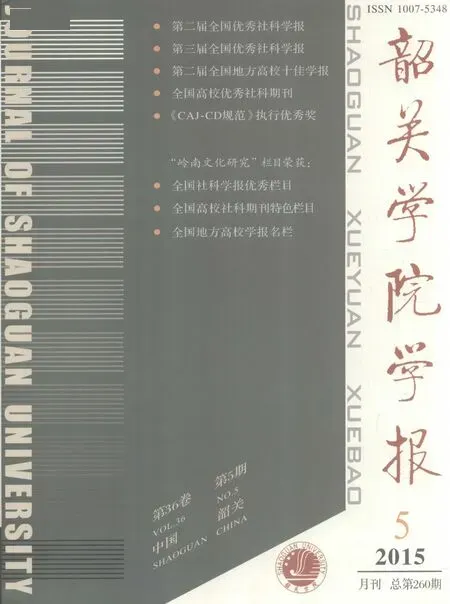论切斯特曼翻译伦理模式及其缺陷
——从“爱的伦理”到“翻译的爱”
任晓光,赵莹莹
(1.韶关学院英东农业科学与工程学院,广东韶关512005;2.驻马店高级中学英语组,河南驻马店463000)
论切斯特曼翻译伦理模式及其缺陷
——从“爱的伦理”到“翻译的爱”
任晓光1,赵莹莹2
(1.韶关学院英东农业科学与工程学院,广东韶关512005;2.驻马店高级中学英语组,河南驻马店463000)
切斯特曼翻译伦理模式极具有系统性,但是其瑕疵在于对平等伦理的违背、翻译主体间性的忽略及共同伦理基础的缺失。翻译的爱的伦理模式可以对切斯特曼的翻译伦理模式做出重要的补充和完善;而以爱的伦理作为基础伦理,既能体现主体的平等性,又能起到维系主体间友好协作的重要功能。
切斯特曼;翻译伦理;爱的伦理
无论东西方文化有何差异,从本质上说,它们都蕴含着一个共同的内核,那就是伦理关怀。伦理旨在寻求最基本的道德原则,以处理对与错、是与非、善与恶等社会问题,而翻译作为关乎译者选择的一种社会实践活动必定与伦理密不可分。翻译伦理立足于对译者的研究,进而探讨翻译过程中涉及的种种伦理问题。传统上,翻译伦理是通过“忠实”这一概念传达的,不管是关乎直译、意译的对等模式,还是以目的为依归的功能模式,争论的焦点其实都集中在伦理诉求上,只是表达方式略微含蓄。在所有翻译伦理模式中,切斯特曼的模式最具系统性,在我国影响也最为深远。切斯特曼为构建系统、科学的翻译伦理学作出了重要贡献,但是在对平等伦理的违背、对翻译主体间性的忽略和共同伦理基础的缺失上也存在瑕疵。本文以哲学的爱的伦理为理论基础,以翻译中的情感价值为依托,认为翻译的爱的伦理可以补充和完善切斯特曼的翻译伦理模式。以爱的伦理作为基础伦理,既能体现主体的平等性,又能起到维系主体间友好协作的重要功能。
一、切斯特曼的翻译伦理模式及其不足
在西方国家的影响下,我国翻译领域也掀起了对伦理问题的探讨,但主要是介绍和借鉴他国的研究成果。从翻译伦理的研究现状来看,翻译伦理尚无明确定义,且其框架有待进一步探讨和落实。在诸多翻译伦理模式中,切斯特曼对翻译伦理的研究比较客观(不为一家一派发言),具描写性,最有系统,在中国影响也最大[1]。他在翻译理论的基础上概括出五种翻译伦理模式,即再现的伦理,基于规范的伦理,交际的伦理,服务的伦理和承诺的伦理。其中,再现的伦理是指不加增减或改变地再现源语文本或作者意图;基于规范的伦理要求译文符合目的语文化的规范和读者的期待;交际的伦理强调将他者视为主体并与之交流,这里主要指跨语言或跨文化障碍的交流;服务的伦理将翻译视为一种商业服务,译者要按客户要求完成任务;承诺的伦理视承诺为美德,要求译者追求完美,力争优秀[2]。为使承诺的伦理更具体化,切斯特曼提出“圣哲罗姆誓言”(a Hieronymic Oath),规定了译者需信誓旦旦做出的种种承诺,目的是为了提倡真实伦理的职业行为,形成和巩固译者的国际声誉[2]。
诚然,切斯特曼的五种翻译伦理模式具有高度的概括性和普适性,几乎所有译者在翻译过程中都会受到一种或几种翻译伦理的影响。但若仔细审视这几种翻译伦理模式,不难发现一些显著的局限。首先,该伦理模式违背了平等的伦理,致使译者权利缺席,主观能动性受损。译者需要履行种种义务,而享有的权利却寥寥无几。在切斯特曼的理论框架内,似乎译者要对整个翻译活动负责,而其他参与者则是隐形的,无需履行任何义务,做出任何承诺。我们不禁要问,难道读者、客户和出版商真的没有必要对译者负责吗?切斯特曼的出发点是伦理诉求,但他本人却忽视了平等的伦理,而在任何文化中,道德和伦理的概念都是以公平和平等作为基本内涵的[3]。众所周知,权利和义务就像硬币的两个面,相辅相成,密不可分。译者在对作者、客户和读者履行义务的同时,也应该享有一定的权利,反过来说,作者、客户和读者也应该对译者负责,赋予其适当的权利。对译者权利的罢黜同时也是对其主观创造性或者说主体性的抹杀。其次,翻译的主体间性被忽视。翻译活动本身就是一种伦理活动,因为其主体间性特征涉及到诸多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如作者与译者、译者与读者、译者与翻译评论者以及译者与赞助人之间的关系等[4]。
根据许钧[5]的观点,翻译的主体包括狭隘的主体,即译者,也包括广义的主体,包括作者、译者与读者,作为实践的主体,他们的交往理性寓于互动性和关联性之间而绝非孤立分离,不是也不应该是译者一个人在唱独角戏。但切斯特曼过于强调译者单方面的义务和责任,忽视了对全局性和整体性的关注,因而割裂了主体间性的链条。再次,缺乏共同的伦理基础。服务的伦理和基于规范的伦理属契约伦理范畴,符合合同或读者期待的行为,即被视为伦理行为,而再现和交流的伦理属于功利主义伦理范畴,只要达到诸如再现原作或促成交流的预期结果,译者行为就被视为符合伦理要求,由于缺乏统一的伦理基础,我们无法找到统一的标准去判断译者的行为到底符不符合伦理规范。
总之,切斯特曼的伦理模式损害了译者的主观创造性,忽视了翻译的主体间性,并且缺乏统一的伦理基础。因此,我们认为有必要对它进行补充和完善,以推进翻译伦理研究的进一步发展。笔者认为,以哲学中“爱的伦理”为理论基石,结合翻译中译者的情感价值,得出“翻译的爱的伦理模式”,可用来弥补切斯特曼翻译伦理模式之不足。
二、费尔巴哈和舍勒的“爱的伦理”
“爱的伦理”是哲学史上一个永恒的话题。从人际关系上来分,爱包括亲情之爱,男女之爱,朋友之爱,同胞之爱以及博爱等等。众多思想家如尼采、马克斯·舍勒、弗洛姆、费尔巴哈、保罗·蒂里希、欧文·辛格等都曾对人类社会的爱的伦理进行过探讨,本文主要介绍费尔巴哈和舍勒的爱的伦理之观点,因为他们的理论侧重于人性的本质和人际关系,与翻译伦理有着更为密切的关系,而其他人的观点主要着眼于男女之间的情爱。
费尔巴哈和舍勒立足基督教博爱的伦理精神,探讨了爱的本质和爱在维系人与人之间关系中发挥的重要功用。费尔巴哈侧重于探讨人的社会本质,他反复强调爱意味着爱自己也爱别人,使自己幸福也让别人幸福,必须把爱做为最高的道德原则。同时他认为,爱是人与人之间的唯一关系和人们实践中最高最重要的原则,“如果人的本质就是人所认为的至高本质,那么在实践上,最高的和首要的基则,也必须是人对人的爱,”爱是协调个人利益和社会利益,利己与他者矛盾的唯一途径[6]。大体而言,费尔巴哈注重探讨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把爱的伦理视为维系人际交往的重要手段。舍勒则主要以个人为本位,其伦理侧重于人的情感价值。他提出了一种“爱感优先论”的伦理学爱之本体论,其基本命题是人作为爱之在优先于人作为认识之在和意愿之在。舍勒认为理想道德的建构就是爱的秩序(ordo amoris)的建构。人们只能认识自己所“爱”的对象,“爱始终是激发认识和意愿的催醒女,是精神和理性之母。”[7]47按照舍勒的观点,“被爱的东西带给我们快乐,被恨的东西带给我们反感”,对事物有兴趣和爱是“为一切行动奠基的最基本、最为首要的行动。”[7]69为此,舍勒专门区分了三点:首先,若对某物毫无兴趣,就根本不存在对此物的感觉和观念;其次,我们的观念和感知沿着我们的意趣行动;再次,某一对象的直观和意义实现的程度处在我们的意识之中,而这种程度的任何提高都有助于提升对该对象的意趣[8]800。
哲学中“爱的伦理”被视为外在的价值枢纽和内在的价值指涉,我们认为,翻译作为一项于外关乎主体间的交往,于内关乎译者情感价值取向的活动,必定彰显并实践“爱的伦理”。
三、“翻译的爱”的伦理
尽管费尔巴哈和舍勒所提出的爱的伦理主要是基于基督教的精神伦理,但我们仍可从中汲取理论精华。从费尔巴哈和舍勒关于爱的伦理的探讨不难看出,作为一种最基本的人类情感,爱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以及人际交往中发挥着重要功用。当我们谈到翻译这个关涉译者的情感、立场和选择,以及作者、译者、读者和赞助人之间关系的活动时,我们无法回避译者的主体性和翻译的主体间性问题,也就不可能避开爱的伦理这一哲学命题。爱的伦理可以体现在译者在选材上的好恶方面,也可体现在与其它主体间的关系上。
在西方翻译史上,许多译者如温特华斯·迪龙(Wentworhth Dillon),约翰·德莱顿(John Dryden)等都曾发表过对译者选材的看法。迪龙认为,译者与原作者之间必须建立起一种“友谊”,即译者在翻译之前,必须检查自己的情趣,热忱于哪方面的题材,然后寻找与自己情趣、热忱以及风格相符的诗人,像择友一样地选择原作者[9]119。德莱顿从亲身经历中体验到,他在翻译与自己性格类同的作者时,更能得心应手。例如,他很满意自己所译的奥维德:“这是不是老人对自己最小的孩子的偏爱,我说不上;但在我看来,这些译作是我所有的翻译作品中最出色的。也许,这位诗人比我尝试过的其他人更易于传译,另外也许他更符合我的特点。”[9]121在我国的翻译史上,傅雷、郁达夫、冰心等许多翻译家都曾公开表露过他们对某一作家或某种作品的偏爱。
译者所体现出的译有所好、译有所爱其实是一种深层次的伦理诉求。一方面,它表明了译者对自身的责任感,既然意趣是感知的导线,他们不愿违背自己的意趣和良知,接受厌恶或力所不能及的任务。另一方面,它体现了译者对翻译事业高度的责任感,他们追求卓越,向往完美,希冀留给读者的是一部充分彰显个人才情的杰出译作,而非一部差强人意的作品。由此可知,爱的伦理在激发译者主观能动性上发挥着重要作用。相对于翻译的主体间性而言,译者、作者、读者和客户之间也需要爱的伦理作为指导原则,因为,正如费尔巴哈所认为的,爱是协调个人利益和社会利益、利己与他者矛盾的唯一途径,是人与人之间的唯一关系和人们实践中最高最重要的原则,维系翻译各主体间的关系必须以爱的伦理为基石。客户以敬爱之心对待译者,尊重译者的爱好和选择,不仅有利于译者充分发挥主观创造性,实现自我价值,也能使原作由于出色的译文而为异域读者充分地了解和认识,于此同时,客户也会因为收获高质量的译作而获利不菲。如果译者以仁爱之心对待客户,他们会推己及人,想客户之所想,急客户之所急,尽最大努力在规定的时日交出保质保量的译品,而不是拖延时日,耽搁计划,或是盲目接受任务,在翻译时却力不从心,结果难保译作质量,让客户受到难以估量的损失。若是读者以友爱之心看待译者,就会把阅读译作视为与作者或译者的友好交流,赏识作者的才华,认可译者的价值和贡献。这样,爱的伦理成为连接翻译各主体的纽带,成为保证主体间性和谐统一的枢纽,为促进翻译事业持续、良好、稳步的发展提供不竭的动力。总之,爱的伦理在提高译者主体性,协同主体间交往方面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切斯特曼翻译伦理模式的不足正是在于损害了译者的主观创造性和忽视了翻译的主体间性,而爱的伦理可以成为该模式的一个行之有效的重要补充和完善。
哲学中“爱的伦理”主要提倡人内在的挚爱之德性以及人与人之间的博爱。翻译的爱的伦理主要是针对于翻译的主体而言。从狭隘的层面来说,爱的伦理主要是指译者在选材方面 (如对某一作家或某种题材的作品)的偏爱以及翻译活动的主体(如作者、译者、读者和客户等)相互之间所秉持的爱的思想,如尊敬、关怀、理解和包容等。就广义的层面来说,翻译的爱的伦理是指翻译参与者对整个翻译事业以及对有效传播和输入人类文明或文化的挚爱。
不难看出,我们所谓“爱的伦理”与切斯特曼模式中的各伦理之间有着重要的关联。比如,切斯特曼再现的伦理要求译者对作者负责,基于规范的伦理要求译者对读者负责,服务的伦理要求译者对客户负责,承诺的伦理要求译者对翻译事业负责,交流的伦理要求译者对跨文化交流负责,然而,不管是对作者、读者、客户的责任还是对翻译事业或是跨文化交流的责任,归根结底都是爱的伦理的具体体现,爱就意味着高度的责任心和强烈的使命感。可以说,爱的伦理是元伦理,为其他伦理之基石,其他伦理皆形成于爱的伦理,是爱的伦理的具体化,爱的伦理是指导或影响其他伦理的标竿,隐含地体现在翻译的整个过程中。当然,不同的伦理模式之间既有冲突又有合作。比如,原则上,译者受客户所托,需按客户要求行事。如果译者的喜好与客户要求里应外合,则作者、译者和客户之间会结成最佳组合,而合作的结果是取得最佳效果。反之,若分配给译者的任务是译者不喜欢或无法胜任的,则译者要么接受任务,但交出的往往是差强人意的作品,要么婉言拒绝,这表明爱的伦理和服务的伦理总体上虽协调统一,但有时也可能产生冲突。
四、结语
翻译伦理是构成翻译理论的“核心价值体系”[10]iii在研究过程中,我们要善于将对翻译伦理的理论建构和批判结合起来,既要认可现有理论的价值,又要认识到其局限和不足,既要以宽容的态度接受其存在,又不能固守僵化的伦理模式。正如张景华所指出的,我们应该主张翻译伦理的开放性和多元性,这对于丰富当前的翻译理论研究和开展理论争鸣极为重要[10]202。切斯特曼的翻译伦理模式为构建系统、科学的翻译伦理学做出了重要贡献,但对译者主观能动性的伤害和翻译主体间性的忽略也成为其理论的瑕疵之所在。应该说,切斯特曼的伦理模式还存在其他问题,如各伦理模式的应用范围有限,而伦理模式之间存在不兼容性等,本文所指出的只是其最明显最需完善之处。以上我们以哲学的爱的伦理,特别是费尔巴哈和舍勒的爱的伦理之观点,为理论基础,结合哈贝马斯的“交往行动”理论阐明了爱的伦理在维系主体间性中发挥的重要作用,提出以爱的伦理来完善切斯特曼翻译伦理模式的不足。需要指出的是,我们的出发点是为解决切斯特曼翻译伦理模式中明显的不完善之处,而翻译的爱的伦理模式并非万能,不能解决切斯特曼伦理模式所存在的全部问题。同时,引入爱的伦理又会导致与其它伦理模式之间的新的摩擦和冲突。然而,矛盾是无时不有,无处不在的,而科学研究的本质就是要发现矛盾,解决矛盾,它不会因为矛盾的存在而裹足不前,相反,正是有了矛盾的存在,才有更多新的视角和解决方案的提出,从而进一步推进研究。
[1]朱志瑜.翻译研究:规定、描写、伦理[J].中国翻译,2009(3):5-12,95.
[2]Chesterman,Andrew.Proposal for a hieronymic oath[J].The Translator:Studies in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20017(2):139-154.
[3]吕俊,侯向群.翻译学——一个建构主义视角[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5:275.
[4]骆贤凤.中西翻译伦理研究述评[J].中国翻译,2009(3):13-17,95.
[5]许钧.“创造性叛逆”和翻译主体性的确立[J].中国翻译2003(1):6-11.
[6]费尔巴哈.费尔巴哈哲学著作选集:下卷[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4:315-316.
[7]马克斯·舍勒.爱的秩序[M].林克,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5.
[8]舍勒,马克斯.舍勒选集:下卷[M].刘小枫,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9:800.
[9]谭载喜.西方翻译简史[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
[10]张景华.韦努蒂翻译思想研究[M].上海: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09.
On Chesterman’s Translation Ethics Models and Its Defection——From“Ethics of Love”to“Love of Translation”
REN Xiao-guang
(1.College of Agricultural Sciences and Engineering,Shaoguan University,Shaoguan 512005,Guangdong; 2.English Section,Zhumadian Senior High School,Zhumadian 463000,Henan,China)
Chesterman’s five models of translation ethics are very systematic,while they are of pitiful flaws for their violating the ethics of equality,neglecting the intersubjectivity of translation and lack of basic ethics. Ethics of love can be taken as an important complement of Chesterman’s models of translation ethics,for the ethics of love,as basic ethics,may not only reflect the equality of subjects,but maintain a friendly cooperation between subjects involved in translation.
Chesterman;translation ethics;the ethics of love
H315.9
A
1007-5348(2015)05-0123-04
2015-04-11
任晓光(1986-),女,河南濮阳人,韶关学院英东农业科学与工程学院助教,硕士;研究方向:翻译学。
(责任编辑:明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