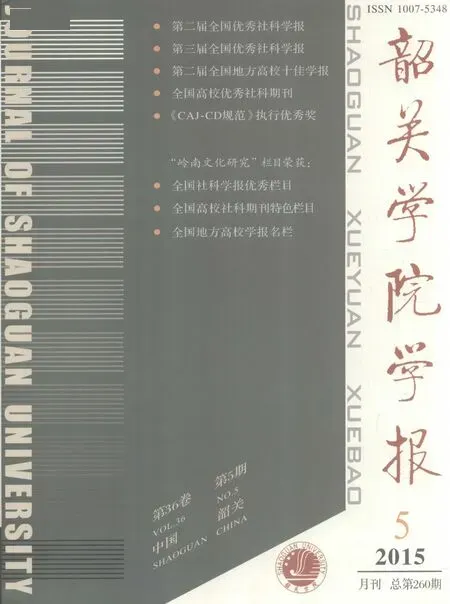先秦民间情歌记录情况概述
——以《诗经》为考察文本
王焰安(韶关学院 学报编辑部,广东韶关512005)
先秦民间情歌记录情况概述
——以《诗经》为考察文本
王焰安
(韶关学院 学报编辑部,广东韶关512005)
《诗经》记录了部分先秦民间情歌,形成了汉族民间情歌记录史上的第一个兴盛时代,而书写材料的改善、统治者采诗观政的需求、唱诗奏乐的需要,是其能被记录的动因。
先秦;民间情歌;记录;《诗经》
自从人类性爱活动进入到有意识的阶段,民间情歌便每时每刻都在产生、传唱,然而因无人记录整理,绝大多数的民间情歌就像风一样消逝得无影无踪,使我们丧失了一份珍贵的文化遗产。但是,通过仔细爬梳、寻绎,我们也会欣喜地在古籍中发现一些民间情歌,聊以勾勒出民间情歌记录的基本线索。本文试对先秦时期民间情歌的记录情况作一概述。
一
从考古发掘可知,我国有文字记载的历史是从甲骨文开始的。虽然从那时开始有了文字,但民间情歌却很少得到记录。据考察,目前所见最早的民间情歌只有“候人兮猗!”和“鸣鹤在阴,其子和之。我有好爵,吾与尔靡之。”两首。前一首见于《吕氏春秋·音初篇》:“禹行功①《文选·南都赋》、《吴都赋》注均作“行水”。,见涂山之女,禹来之遇,而巡省南土。涂山氏之女乃令其妾候禹于涂山之阳,女乃作歌曰:‘候人兮猗!’实始为南音。”后一首见于《易经·中孚》。“候人兮猗!”是否是南音之始,则未必,但说它是初期形态较完整的民间情歌则是可信的。因为民间情歌有一个由简单的音节到完整的语句再到富有诗意的辞句的发展演变过程。《易经·中孚》的形态比较完整,是民间情歌进一步演变发展并趋于成熟后的形态。除此,很难再在其他文本中寻觅到那一时代乃至之前的民间情歌的身影。直到春秋时代成书的《诗经》,这种状况才有所改变。
为什么《诗经》能够记录民间情歌呢?我们认为有主、客观的原因。第一,书写材料的改善,为记录民间情歌提供了可能。文化的传播必须依赖于一定的传播载体,最早的传播载体是口与耳,随后便发展到接绳、结草,再后来便发展为文字。但是什么是文字书写的合适载体呢?这可苦煞了先秦的人们,他们经过长期的实践与摸索,终于确认龟甲、兽骨和青铜器、石头是最好的书写载体。但这些载体坚固异常,难于刻写,所以当时的记录仅局限于巫史的纪实性内容,且文字短而精,抒情性的内容则很少涉及。而此时代浓厚的巫史风气,使得人们只重视巫史,而不可能去关注民歌、记录民歌。到了西周、春秋时代,文字的载体改为了竹简、布帛,大大方便了人们的记录。随着书写材料的改进,为丰富记录内容提供了极大的可能,既注重记录纪实性的内容,也注重记录抒情性的内容,这就把民间歌谣纳入了记录的范围,民间情歌也因此而有机会跻身其中。第二,采诗观政的需要,导致间接记录了民间情歌。周朝统治者为了观民风、考政绩,建立了采诗制度。民间采诗说最早见于《左传》,《左传·襄公十四年》引《夏书》曰:“遒人以木铎徇于路。官师相规,以执艺事以谏。”《左传·昭公二十一年》引泠州鸠曰:“天子省风以作乐。”《礼记·王制》载:“天子五年一巡狩,岁二月,东巡守,至于岱宗,柴而望祀山川,觐诸侯,问百年者就见之。命太师陈诗以观民风。”《毛诗·卷阿传》:“王使公卿献诗以陈其志。”《汉书·食货志》追记了春秋时期采风的情形:“男女有不得其所者,因相与歌咏,各言其伤。……孟春之月,群居者将散,行人振木铎徇于路,以采诗,献之太师。比其音律,以闻于天子。故曰:‘王者不窥牖户而知天下’。”虽然统治者采诗的目的,不是为了搜集民歌,更不是为了搜集民间情歌,而是为了维护其统治的长治久安,正如鲁迅先生在《且介亭杂文集·门外文谈》中所说:“王官们检出它可作行政上参考的记录下来。”但是,由于统治者对采诗工作的重视,在一定程度上推动和促进了民歌的搜集、记录工作的开展。民间情歌由于其内容与社会生活广泛地交织在一起,蕴涵着广泛的社会内容,既包含有社会风俗,又包含有政治因素,从而在搜集民间歌谣时,间接地搜集和记录了民间情歌。第三,唱诗奏乐的需要,导致直接记录民间情歌。因为西周时举行祭祀、典礼、宴会、酬酢,都必须唱诗奏乐,负责音乐之用的乐师,因为工作的需要,必须不断地丰富音乐的内容,为此,不得不走向民间,搜集民谣,为己所用。朱自清在《经典常谈》第四篇《诗经》中认为:“有了文字以后,才有人将那些歌谣记录下来,便是最初写的诗了。……他们大概是些乐工,乐工的职务是奏乐和唱歌;唱歌得有词儿,一面是口头传授,一面也就有了唱本儿。歌谣便是这么写下来的。我们知道春秋时的乐工就和后世阔人家的戏班子一样,老板叫作太师。那时各国都养着一班乐工,各国使臣来往、宴会时都得奏乐唱歌。太师们不但得搜集本国乐歌,还得搜集别国乐歌。不但搜集乐词,还得搜集乐谱。……”周锡馥在《诗经选·前言》中认为:“根据现有史料,我们可以基本肯定,歌谣的采集工作,以音乐家们的贡献最大。当时各国设有乐师,负责诵诗、奏乐的工作。他们除了自己创作之外,并搜集歌谣来丰富乐章。各国的乐章通过交流或进献,集中到周王庭,统一由太师(乐官之长)掌管。因此,《诗经》的最早的搜集、整理者是周王室的乐官。”所以《诗经》“三百五篇,皆弦歌之”,则都 “合 《韶》、《武》、《雅》、《颂》之音”[1]。由于乐官们搜集歌谣的目的是为了丰富乐章,民间情歌是天籁之声,音美曲美,因此,具有抒情性质的民间情歌便自然而然地成为他们记录、搜集的对象,从而在他们搜集、整理而成的《诗经》中留下了一席之地。
正是在这三种合力的相互作用下,自生自灭了很久历程的民间情歌,才第一次大规模地被记录、整理而保存下来,成为民间情歌记录史上的第一个里程碑。
二
由《诗》而《诗经》,随着其地位的逐步提高,民间歌谣的真性情便逐渐湮没了,作为表现人欲的民间情歌被曲解、附会、凿空了,使人莫明其所以然者。正如郑振铎先生在 《插图本中国文学史》中所言:“《诗经》却遇到了不可避免的厄运:一方面她的地位被抬高了,一方面她的真价与真相却为汉儒的曲解胡说所蒙蔽了。”[2]但是,只要认真研究诗教理论,结合当时具体的历史和社会情况,仔细分析《诗经》中的作品,即“用‘诗经’时代的眼光读《诗经》”[3]99,《诗经》中民间情歌的本来面目就会一一显现出来。
《诗经》收集了自西周初(公元前十一世纪)乃至之前到春秋中期(公元前六世纪)大约五百年间的三百零五篇诗歌,“经周王朝各代王官、乐师加工修订”后,不断流传,不断修改雅化,“流传既久,经手亦多”[4],诗的真面目逐渐消失模糊,诗的语言特色消失①“诗”经过了乐官和史官们的整理,从而无方言词、无韵部变化,只有统一的“雅言”,以致有人把其作为否定《诗经》中有民间歌谣的证据。,诗的本义无法确定②同一首诗,已经被人解读出多种题旨,有的多达十余种。,所以“我们今天所见到的《三百篇》,尤其是二南十三风,决不是原来的面目。”[5]但具体到对民间情歌的确认,则尤为如此。
《诗经》“明明是一部歌谣集”[3]214,由于人们没有“认真地把它当文艺看”[3]214,所以到目前为止,似乎还没有人明确提出《诗经》中的哪些诗篇是民间情歌。不过,前人虽不是为了“达诂”哪些是民间情歌,但是他们从文学视角的解读《诗经》,已经注意到了“民歌”、“情歌”的事实,只不过是以“淫奔诗”、“婚恋诗”、“情诗”等概念而代之了。
(一)淫奔诗
朱熹虽然认识到 “国风”部分多是民间歌谣,“所谓‘风’者,多出于里巷歌谣之作,所谓男女相与咏歌,各言其情者也。”[6]2但在分析《诗经》中的具体作品时,却没有采用民间歌谣的概念,而是以“淫奔诗”称之。
朱熹认为:“郑卫之乐,皆为淫声。然以《诗》考之,卫诗三十有九,而淫奔之诗才四之一。郑诗二十有一,而淫奔之诗已不翅七之五。”[6]481而因朱熹所说的只是《郑风》和《卫风》的大约数,后人便有了不同的确认数据,马端临、周予同认为是24篇[7,8],莫砺锋认为是30篇[9],檀作文认为是28篇[10],郝永认为是40篇,其中《郑风》中有《将仲子》、《叔于田》、《大叔于田》、《遵大路》、《有女同车》、《山有扶苏》、《萚兮》等17首;《齐风》中有《东方之日》等4首;《陈风》中有《东门之池》、《东门之杨》等6首;《邶风》中有《凯风》、《静女》等3首;《鄘风》中有《墙有茨》、《桑中》等5首;《卫风》中有《木瓜》、《氓》2首;《王风》中有《采葛》、《大车》、《丘中有麻》3首[11]。
由于朱熹只着眼于“淫奔”,因而其所列诗中有的是宫闱丑行的,如《墙有茨》,内容与情歌不符;有的是叙事诗,如《氓》,形式也与情歌不符。
(二)婚恋诗
婚恋诗的内涵较广,从绝大多数文章来看,一般将其归结为爱情诗、婚嫁诗、弃妇诗三个方面。由于内涵的不明确性,因而导致了婚恋诗数目的不确定性。有的认为是50余首[12]、有的认为是76首[13]、有的认为是77首[14],有的甚至认为是123首,其列“民间婚恋诗”为:《周南》中有《关雎》、《葛覃》、《卷耳》等7首;《召南》中有《鹊巢》、《草虫》、《行露》等8首;《邶风》中有《柏舟》、《绿衣》、《日月》等12首;《鄘风》中有《柏舟》、《墙有茨》等6首;《卫风》中有《淇奥》、《硕人》、《氓》等8首;《王风》中有 《君子于役》、《君子阳阳》、《扬之水》等8首;《郑风》中有《缁衣》、《将仲子》、《遵大路》、《女曰鸡鸣》、《有女同车》、《山有扶苏》、《萚兮》、《狡童》等17首;《齐风》中有《鸡鸣》、《著》等9首;《魏风》中有《汾沮洳》、《十亩之间》2首;《唐风》中有《扬之水》、《椒聊》、《绸缪》等8首;《秦风》中有《小戎》、《蒹葭》等4首;《陈风》中有《宛丘》、《东门之枌》、《衡门》等9首;《桧风》中有《羔裘》、《素冠》等4首;《曹风》中有《蜉蝣》、《候人》2首;《豳风》中有《素冠》、《东山》等3首;《小雅》中有《棠棣》、《杕杜》、《我行其野》、《谷风》等13首;《大雅》中有《大明》、《思齐》、《韩奕》3首[15]。
由于着眼于婚恋,因而所列诗中,有的只含有婚恋内容,如《大雅》中的《大明》、《思齐》;有的是有创作者的,如《旄丘》,为臣子作;《简兮》,为贤人作;《棠棣》,周公作。有的是贺婚诗,如《鹊巢》。有的是悼亡诗,如《绿衣》。有的是弃妇诗,如《蝃蝀》。因而,有的不是民间歌谣,有的不是情歌。
(三)情诗
情诗,可以视为情歌的别称。它是对《诗经》中“男女情思之辞”的准确体认,是从文学角度探求诗本义的结果。
有关情诗的内涵,一般没有大的出入,基本上都着眼于相识、相知、相约、相思、失恋等内容,但因解读角度不一,具体篇数时有变化,如王宗石认为52首;张西堂认为72首;段楚英认为71首;钟晓华认为60首左右[16]。
有关《国风》中的情诗,基本可以等同于民间情歌。鉴于此,我们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兹大致列出《诗经》中所记录的民间情歌目录。
《周南》中的民间情歌为:关雎、汉广、汝坟、卷耳
《召南》中的民间情歌为:草虫、行露、摽有梅、江有汜、野有死麕
《邶风》中的民间情歌为:终风、匏有苦叶、北风、静女
《鄘风》中的民间情歌为:柏舟、桑中
《卫风》中的民间情歌为:竹竿、有狐、木瓜
《王风》中的民间情歌为:君子阳阳、采葛、大车、丘中有麻
《郑风》中的民间情歌为:将仲子、遵大路、女曰鸡鸣、有女同车、山有扶苏、萚兮、狡童、褰裳、东门之墠、风雨、子衿、扬之水、出其东门、野有蔓草、溱洧
《齐风》中的民间情歌为:东方之日、甫田、卢令
《魏风》中的民间情歌为:汾沮洳
《唐风》中的民间情歌为:扬之水、椒聊、有杕之杜
《秦风》中的民间情歌为:蒹葭、终南、晨风
《陈风》中的民间情歌为:宛丘、东门之枌、东门之池、东门之杨、防有鹊巢、月出、泽陂
《桧风》中的民间情歌为:羔裘、隰有苌楚
三
这部分二千多年前记录下来的以黄河流域为主的民间情歌,尽管不足以代表当时民间情歌的全部,但却为我们留下了弥足珍贵的民间情歌史料,有利于我们对民间情歌的研究及当时社会风尚的认识。
[1]司马迁.史记·孔子世家[M].北京:中华书局,1962:1936.
[2]郑振铎.插图本中国文学史[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37.
[3]孙伯党,袁謇正.闻一多全集:诗经[M].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93.
[4]郭豫衡.中国古代文学史[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30.
[5]高有鹏.中国现代民间文学史论——中国现代作家的民间文学观[M].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2004:415.
[6]朱熹.诗集传[M].南京:凤凰出版社,2007.
[7]马端临.文献通考[M].北京:中华书局,1986:1540.
[8]周予同.周予同经学史论著选集[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159.
[9]莫砺锋.朱熹文学研究[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0:225.
[10]檀作文.朱熹诗经学研究[M].北京:学苑出版社,2003:97.
[11]郝永.朱熹《诗经》解释学“淫诗”说新论[J].河南教育学院学报,2014(1):106-111.
[12]褚斌杰.诗经与楚辞[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85.
[13]程俊英,蒋见云.诗经注析[M].北京:中华书局,1991:2-432.
[14]冷国俭.诗经婚恋诗研究——兼论奴隶社会婚姻文化[J].佳木斯师范专科学校学报,1993(1):13-16.
[15]黄伦峰.周代婚俗下的《诗经》婚恋诗研究[D].桂林:广西师范大学,2007.
[16]钟晓华.闻一多《诗经》研究对《诗经》中情诗读法的影响[J].云梦学刊,2009(2):112-116.
Record Summary of Folk Lover Song in Pre-Qing Dynasty——Based on Investigation Text of The Book of Odes
WANG Yan-an
(Editorial Department of Journal,Shaoguan 512005,Guangdong,China)
Part of Pre-Qing Dynasty love longs are recorded in The Book of Odes,and that time was the first thriving time of recording history of theHan nationality folk love songs,the improvement of writing material, the demands of the ruling class for songs,the demands of music for singing the songs are all the reasons for the songs being recorded.
Pre-Qing dynasty;folk love song;record;The Book of Odes
I207
A
1007-5348(2015)05-0010-04
2015-03-26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基金项目“汉族民间情歌史”(13YJA751049);广东省哲学社会科学“十二五”规划2012年学科共建项目“汉族民间情歌史研究”(GD12XZW14)
王焰安(1962-),男,安徽宿松人,韶关学院学报编辑部编审;研究方向:民间文学。
(责任编辑:廖铭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