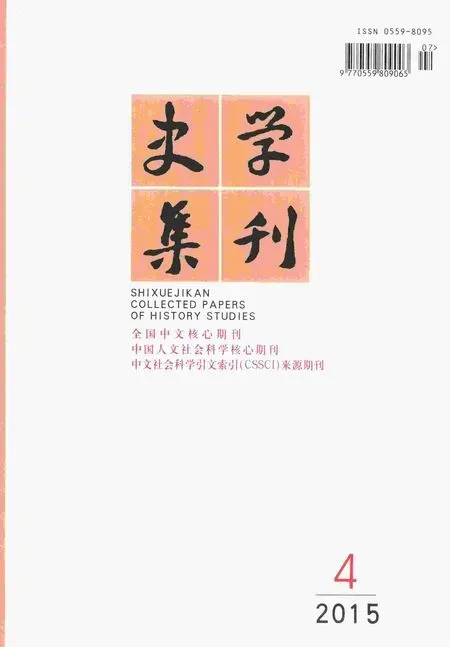《满洲历史地理》的学术特征及观点倾向
张文静
(东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吉林长春130024;北京语言大学外国语学院,北京100083)
日俄战争后,为了适应日本政府“经营满洲”的国策,日本历史学者展开了对中国东北、朝鲜、蒙古历史地理的研究。1908年,在满铁总裁后藤新平的授意下,满铁东京支社建立了“满鲜历史地理调查部”。该调查部的主持者是日本东洋学的奠基人之一、东京帝国大学的白鸟库吉。作为历史学家,白鸟库吉在服务于日本政府“经营满洲”的现实需要的同时,主张进行“纯学术”研究。于是,“满鲜历史地理调查部”成立之后,白鸟库吉就带领箭内亘、津田左右吉、池内宏、松井等、稻叶岩吉等学者在中国东北广泛搜集历史和地理资料,并以这些资料为中心对中国东北、朝鲜、蒙古的历史地理、交通、民族、文化展开系统性考察和研究。他们的研究成果在相当长的时期里对日本的东洋史研究产生了决定性影响,从而在学术上确立了日本东洋史学“东京文献学派”的地位。1914年,“满鲜历史地理调查部”被认为是“纯学术机构”,与满铁实际任务不符而遭废止,“满鲜历史地理调查部”的后续研究工作移至东京帝国大学文学部。在“满鲜历史地理调查部”存在的六年里,经过系统的梳理与考据,于1913年9月至12月相继出版《满洲历史地理》两卷、《朝鲜历史地理》两卷和《文禄庆长之役》正编第一卷。这三部著作从原始民族出现于“满洲”和朝鲜半岛开始,对不同历史时期的“满洲”和朝鲜少数民族政权的地理位置、领土构成、疆域进行了系统的考证与梳理,是“满鲜历史地理调查部”存在期间的系统性研究成果。
“满洲史”研究作为日本东洋史学“东京文献学派”的核心研究领域,随着东洋史学的学术传承,至今仍然是一个备受日本东洋史学界关注的研究课题。本文主要以“满鲜历史地理调查部”存在期间的核心研究成果《满洲历史地理》第一卷为主要研究对象,探讨其资料来源、研究目的、方法、视角,期望通过这样的工作,能够从治史风格上展现出《满洲历史地理》的学术特征,给予其恰当的学术定位,找寻白鸟库吉、稻叶岩吉等学者在“满铁”资金支持下展开的学术性研究中所流露出的政治倾向。
一、日本学者的批判与问题的缘起
“满鲜历史地理调查部”撤销后,东洋学派以东京帝国大学文学部为研究基地,由满铁继续提供研究资金,持续进行后续研究。其核心研究成果是1915年12月至1941年10月陆续出版的《满鲜地理历史研究报告》十六卷。《满鲜地理历史研究报告》在继续对“满洲”历史上主要民族进行考据性研究的基础上,展开对“满洲”历史上的民族盛衰、政治军事制度、思想文化等领域的专题研究。其学术视野与“满鲜历史地理调查部”存在期间的“满洲史”研究大体一致,即在重视历史地理考证的基础上,关注“满洲”历史上的民族存在状况及纷争,其核心研究立场亦是将乌桓、鲜卑、扶余、勿吉等民族的活动疆域排除在中国王朝的疆域之外,突出“满洲史”的“自主性”发展,这无疑支持了战前日本政治宣传中的“满韩一体”理念。
如果说《满鲜地理历史研究报告》是东洋学派在“满鲜历史地理调查部”被撤销后对“满鲜史”进行的后续学术性研究,那么,战前出版的大量“满洲史”、“东洋史”书籍则是东洋学派对其研究成果的推广和普及。如,池内宏的《满鲜史研究》①池内宏的《满鲜史研究》均为吉川弘文馆出版,由上世第一册、第二册,中世第一册、第二册、第三册构成。其中,中世第一册和中世第二册分别于1933年和1937年出版,上世第一册、上世第二册和中世第三册分别于1951、1960和1963年出版。、松井等的《東洋史講座第四期》②松井等:『東洋史講座第四期』(清初至现代)、国史講习会、1926年。、《东洋史讲座第八卷》 (满州民族盛衰时代)和《东洋史讲座第九卷》 (新支那时代)③松井等:『東洋史講座第八卷』(满州民族盛衰时代)、『東洋史講座第九卷』(新支那时代)、雄山阁、1930年。、《东洋史精粹》④松井等:『東洋史精粹』,共立社書店、1931年。等。这样,在战前的日本史学界,东洋学派以“满鲜历史地理调查部”期间搜集到的历史资料和初步研究成果为基础,基本构筑起了以“满洲史”为基础,进而拓展到朝鲜史、蒙古史、中国史乃至亚洲史的完整研究体系,奠定了日本“东洋学”的研究基础。
近年来,针对“满鲜历史地理调查部”期间的“满鲜史”研究,日本学界出现了批判性观点。泷泽规起认为,“满鲜史”研究试图向大众普及“满洲”和朝鲜这两个地域的“不可分割性”,并通过“朝鲜民族的发展”和“爱抚鲜人”的逻辑来达到使日本侵略大陆正当化的目的。⑤滝沢規起:「稲葉岩吉と 「満鮮史」」『中華世界と流動する民族』社会文化科学研究科研究プロジェクト報告書第37集、2003年3月。井上直树认为,“满鲜史”研究是为了对所谓“满韩一体”进行历史性说明而提出来的。⑥井上直樹:『日露戦争後の日本大陸政策と 「満鮮史」-高句麗史研究のための基礎的考察ー』、『洛北史学』第8号、2006年6月。这些观点指出了“满鲜史”研究与现实政治之间的关系。上述批判切中要害,但是,由于并没有对其具体的学术视角与观点、史料的搜集与整理的基本原则、分析史料的方法、对待民族纷争的基本理念等问题进行细致分析,导致上述批判仅仅局限在与现实政治和侵略战争的对照层面上。
在学术上对“满鲜历史地理调查部”期间的研究成果展开批判性研究的是东洋学派的第二代学者旗田巍。旗田巍在1964年发表的论文《“满鲜史”的虚像——日本的东洋史家的朝鲜观》中,将白鸟库吉、池内宏等人的“满鲜史”研究的基本视角概括为:“将朝鲜的历史与满洲的历史相融合,归纳成‘满鲜史’”。对于这种做法,旗田巍批评说:“一般情况下,在思考历史之时,首先思考的是民族问题,朝鲜史是作为朝鲜民族的历史才得以确立的,然而,将朝鲜与满洲总括的历史作为民族的历史是不能成立的。”⑦旗田巍:『「満鮮史」の虚像―日本の東洋史家の朝鮮観―』、鈴木俊教授還暦記念会1964年,第476頁。尽管旗田巍的上述批评隐含着战后初期东洋学派将现实的民族和国家视作历史研究固定前提的倾向,①井上直樹:『日露戦争後の日本大陸政策と 「満鮮史」-高句麗史研究のための基礎的考察ー』、『洛北史学』第8号、2006年6月、第77頁。但是,这种从民族起源的角度出发对“满鲜历史地理调查部”期间的“满鲜史”研究的批判,无疑是从学术性角度出发的。从总体上说,战后日本东洋学派的后续成员大多致力于拓宽东洋学的研究范围,加深对亚洲各国历史的研究,出色的成果层出不穷,却鲜有对“满鲜历史地理调查部”期间的“满鲜史”研究成果进行历史学的深入研究和评判。
综上可见,从基本的研究方法、史料构成和研究框架入手剖析《满洲历史地理》,将有助于对“满鲜历史地理调查部”期间的“满鲜史”研究的学术特征做出准确定位。
二、历史地理学的研究方法与《满洲历史地理》的史料构成
《满洲历史地理》秉承了东洋学派首创的历史地理学的研究理念。白鸟库吉在史学研究理念上推崇的是德国实证主义历史学派兰克学派的史学研究,《满洲历史地理》便是在实证主义研究理念的指导下进行的。如,对中国和朝鲜史籍中的记述着重进行史料辨伪、考证和批判;重视地理,注重对“满洲”的实地调查。日本东洋学派对东洋史的研究是以地理位置的考证为前提的,《满洲历史地理》全篇就以对历代“满洲”疆域的细致考证作为其核心研究目标,这种以地理位置和疆域范围的考证为前提的研究理念也是日本东洋学派的后继者们始终秉承的研究理念之一。《满洲历史地理》以中国的历史朝代作为基本框架,对不同历史时期中国东北的少数民族政权和中原王朝设置的行政机构的疆域做了细致考证,并梳理出基本的疆域演变脉络。《满洲历史地理》还附有多幅详细地图②其附图包括:《武帝始建之四郡》、《前汉时代满洲图》、《前汉时代朝鲜图 (昭帝以后)》、《后汉时代满洲图》、《三国时代满洲图》、《西晋时代满洲图》、《前燕时代满洲图》、《后燕时代满洲图》、《后魏时代满洲图》、《渤海时代满洲图》、《隋代及唐初满洲图》。,这些附图都是用当时最先进的军事地理标尺绘制的,其地理位置精确程度高、地理考证非常详细。
“满鲜历史地理调查部”设立期间,白鸟库吉率领诸弟子,在中国搜集大量古籍作为研究“满鲜史”的基本史料,其搜集到的史料在《满洲历史地理》第一卷的“引用书目解说”中做了细致解读。其中不仅包括《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资治通鉴》等官修正史,还包含《水经注》、《山海经》、《黑鞑事略》、《朝鲜纪事》、《东夷考略》等记述地理沿革的相关史籍,其列举的中国史籍总计138部。从其搜集到的史料来看,在对“满洲史”具体史实的考证中,中国史籍无疑构成其主要资料来源。可以判断,白鸟库吉在“引用书目解说”中罗列的史料是在考证疆域和地理变迁时用作参考的。也就是说,《满洲历史地理》将中国史籍中对东北历史和地理的记述当作需要“批判”和“辨伪”的历史资料。从这个角度也可以说,《满洲历史地理》是将大量中国史籍解构之后,重新以历史地理学的研究理念建构起来的系统性研究成果。
除了中国史籍之外,《满洲历史地理》还列出了21部朝鲜史籍。这些资料的获得,使得《满洲历史地理》的研究能够站在中朝双方各自的历史视野当中梳理历史发展脉络。然而,《满洲历史地理》在解构中国史籍的传统叙史结构时,表露出对中国史籍及中国传统史学思想的轻视之意。如,《满洲历史地理》第一卷在辨析十二地支动物的起源时说:“证支那之历史,可知汉人古来好于自国之内谋求他国之起源,又有将外国之人视为自国臣民之习癖,” “以此寄寓此国之民倾慕中国之意”。③白鳥庫吉監修,箭内亙、稲葉岩吉、松井等:『満州歴史地理』第一巻、南滿州鉄道株式会社1913年,第58-59頁。这也构成其解构中国史籍叙史结构的情意性因素。
三、《满洲历史地理》独特的叙史框架
《满洲历史地理》第一卷包含七篇,即,第一篇《汉代的朝鲜》、第二篇《汉代的满洲》、第三篇《三国时代的满洲》、第四篇《晋代的满洲》、第五篇《南北朝时代的满洲》、第六篇《隋唐二朝高句丽远征的地理》、第七篇《渤海国的疆域》。《满洲历史地理》第二卷包含九篇,即,第一篇《辽在满洲的疆域》、第二篇《许亢宗行程录中所见之辽金时代的满洲交通路》、第三篇《金在满洲的疆域》、第四篇《东真国的疆域》、第五篇《元在满洲的疆域》、第六篇《元明时代的满洲交通路》、第七篇《明代辽东的边墙》、第八篇《建州女真的原住地及迁住地》、第九篇《清初的疆域》。由于是系统梳理“满洲史”的著作,因此,《满洲历史地理》采用按年代叙史的成书方式。从其篇目来看,《满洲历史地理》的主要框架是按照中国王朝的更迭顺序叙述的。从结构上看,《汉代的朝鲜》尽管与全书的框架很不匹配,却被置于第一卷第一篇这个重要位置,俨然是开宗明义。《汉代的朝鲜》由两部分构成:考证汉武帝在朝鲜建立的四郡的疆域变迁,以及废真番、临屯二郡后,两汉时期乐浪、玄菟二郡的疆域变迁,在叙史时间上与《汉代的满洲》基本相同。《汉代的满洲》由三部分构成:“前汉在满洲的领土”①考证辽东郡及所属十八县、辽西郡及所属十四县、右北平郡及所属十六县的位置与疆域。、“后汉在满洲的领土”②考证辽东郡及所属八县、辽西郡及所属五县、右北平郡及所属四线、辽东属国及所属六县的位置与疆域。、“两汉领土以外之满洲”③考证乌桓、鲜卑、夫余、挹娄、高句丽的位置与疆域。。
值得注意的是《汉代的朝鲜》这个似乎应当放到同为《朝鲜历史地理》当中的篇目,为何会出现在《满洲历史地理》当中,对此鸟库吉并未做出解答。我们对照津田左右吉的《朝鲜历史地理》第一卷的框架便可获知答案。《朝鲜历史地理》第一卷共有14篇:第一篇《浿水考》、第二篇《三韩疆域考》、第三篇《百济慰礼城考》、第四篇《好太王征服地域考》、第五篇《长寿王征服地域考》、第六篇《真舆王征服地域考》、第七篇《任那疆域考》、第八篇《新罗征服地理考》、第九篇《罗济境界考》、第十篇《百济战役地理考》、第十一篇《高句丽战役新罗进军路线考》、第十二篇《唐罗交战地理考》、第十三篇《新罗北境考》、第十四篇《后百济疆域考》。关于第一篇《浿水考》的研究目标,津田左右吉在绪言中说:汉武帝元丰二年,汉灭卫氏朝鲜后,“收其故地,设乐浪郡。而朝鲜之北境自汉初定为浿水,及至设置乐浪郡,其属县之一便为浿水县。本书之第一篇浿水考,即研究浿水为哪条河川,浿水县位于何处,以期考订半岛之势力与大陆之接触线位于何处”。④白鳥庫吉監修,津田左右吉:『朝鮮歴史地理』第一巻、南満州鉄道株式会社1913年、第1-2頁,“绪言”。由此可见,两部著作在考证朝鲜半岛的地理上有明确分工:《满洲历史地理》中的《汉代的朝鲜》旨在考证自汉武帝至后汉时期,汉王朝在朝鲜半岛置郡的地理沿革;《朝鲜历史地理》旨在考证在汉王朝控制范围之外的朝鲜半岛上政权的疆域及变迁。这意味着,在白鸟库吉等东洋派学者看来,在《满洲历史地理》中出现的《汉代的朝鲜》特指在汉王朝政权控制范围内的朝鲜,因而在当时属于“满洲”。由于没有从古代史的角度对“朝鲜”这一既包含地域性,又包含民族性特征的地理名词进行解读,使他们不得不将朝鲜分割在两部著作中进行疆域的考证,而其使用的“朝鲜”一词很显然是刚刚被日本合并的朝鲜。这也导致在开始进行古代“满洲”和朝鲜的考证研究时,战前的日本东洋史学家就立足于将“满洲”与朝鲜的历史合并为“满鲜史”。
在《满洲历史地理》第一卷的框架当中还有一个现象值得关注。在叙述每个统一王朝的“满洲”的篇目下,其下一级目录都要分为中国中央王朝领土以内的“满洲”和中国中央王朝领土以外的“满洲”。除了第二篇《汉代的满洲》包含“两汉领土以外之满洲”在前文中已有提及之外,第三篇《三国时代的满洲》包含两个目录: “魏在满洲的领土”和“魏领土之外的满洲”;第四篇《晋代的满洲》的第一章叙述的是统一王朝—— “西晋时代”,其中包含两个目录:“西晋在满洲的领土”和“西晋领土以外的满洲”;第五篇《南北朝时代的满洲》包含两个目录:“北朝诸国在满洲的领土”和“北朝诸国领土以外的满洲”。在叙述篇幅和考证的详细程度上,两个目录的内容基本持平。这种研究框架渗透出一种试图厘清在统一的中央王朝控制时期,中原王朝政权辐射到中国东北地区的边缘线的研究初衷。然而,在《满洲历史地理》第二卷中,第一卷的这种框架并未出现,这自然是由于辽代以后,中原历代王朝相继在中国东北确立了完整的统治体系,中原领土“以外的满洲”已经找寻不到了。
白鸟库吉在《满洲历史地理》第一卷的绪言中,阐述了其“满洲史”的研究计划:“由于古代之事迹,史籍甚为贫乏,不便展开研究,故欲先阐明材料比较丰富之近代,后言及古代,此为适当之顺序。据此方针,关于满洲,第一期之研究事项定于辽代以后。由稻叶岩吉负责明清时代,箭内亘负责元明时代,松井等负责辽金时代,收录于本书第二卷。及至完成上述研究,进入第二期,由松井氏承担隋唐时代、箭内氏承担南北朝时代及汉魏时代之一部分、稻叶氏承担汉代之一部分,以此移至古代之研究,其成果收录于本书第一卷。”①白鳥庫吉監修,箭内亙、稲葉岩吉、松井等:『満州歴史地理』第一巻、第6頁,“绪言”。白鸟库吉等人的“满洲史”研究,是按照先近代再古代的顺序进行的,采取这种逆向顺序的主要原因在于史料掌握的不平衡性。这似乎也可以解释资料相对丰富的第二卷没有采用第一卷那种趋向于统一的框架,而是可以细致地考证“交通路”、“居住地”、“边墙”等。第二卷的研究不仅完成了第一卷的考证中原王朝政权辐射的边缘线及其动态变化的研究任务,更深入考证了中国东北地区各地的地理沿革和各民族往来交通。
四、“间空地”理论和“南北二元对抗”理论在《满洲历史地理》中的体现
白鸟库吉力求在《满洲历史地理》中进行所谓“纯学术”的考证性质的研究,也尽量在书中避免出现对中国古代东北历史的理论性解说。然而,在细读之后,仍然可以看到“间空地”理论和“南北二元对抗”理论的痕迹。
“间空地”理论是白鸟库吉在日俄战后就提出并开始诠释的理论。1905年,白鸟库吉发表《满洲的过去及将来》,首次提出了解决“满洲”问题的建议,1912年,白鸟库吉在《满洲问题和中国的将来》一文中,明确提出“满洲”处于“间空地状态”,认为在当时的形势下,日本政府应当采取“维持现状,保持和平”的态度。②白鳥庫吉:『白鳥庫吉全集』第十巻、岩波書店1971年、第154頁。在白鸟库吉看来,“间空地”是不属于任何国家的“无主之地”,在历史上,“间空地”一般处于三方势力的交汇之处,当三方势力均衡时,作为缓冲之地的“间空地”就会显现,当这种均衡状态被打破时,“间空地”就被势力相对强大的一方占据。白鸟库吉认为,在中国东北和朝鲜地区,在秦代、唐代、清代都出现过“间空地”,尽管三个时代的“间空地”在疆域范围上有所不同,但却拥有同样的性质——中国与朝鲜都不拥有该地。③白鳥庫吉:『白鳥庫吉全集』第十巻、第152-153頁。可见,“间空地”理论的实质是试图诠释中国东北和朝鲜地区是“无主之地”,在历史上不属于任何一个国家,因此,当时有能力占据这一地区的日本在该地区实行的殖民侵略行为便被解读为“历史的常态”。在《满洲历史地理》中,也可以看到“间空地”理论的相关阐释。在第一篇《汉代的朝鲜》中指出,鸭绿江与大同江之间的区域自秦灭亡后,在历史上的不同时期都处于三股势力互相角逐之下,“是实际上无所属的间空地”。不仅在“满洲”地区,在朝鲜半岛的汉江流域,也是汉、貊、韩三民族冲突之纷争地。④白鳥庫吉監修,箭内亙、稲葉岩吉、松井等:『満州歴史地理』第一巻、第44-45頁。在考证乐浪郡的位置时,也得出乐浪郡北部,即鸭绿江下游、大同江流域一直是户口稀薄,兵马相争之地,属于“无主之地”的结论。⑤白鳥庫吉監修,箭内亙、稲葉岩吉、松井等:『満州歴史地理』第一巻、第81頁。
“南北二元对抗”理论是白鸟库吉在1901发表的论文《戎狄对汉民族的影响》中提出的,在1904年发表的论文《关于我国强盛的历史原因》中,白鸟库吉进一步用“南北二元”理论解释亚洲衰败的原因。所谓“南北二元”,即把中国和亚洲的历史概括为以长城为界限的南方文化民族和北方游牧民族之间对抗的历史,在这种对抗导致的南北势力的消长过程中,历史被动性地向前推进着。“南北二元对抗论”是白鸟库吉东洋史学研究的重要理论之一,这一理论同样被应用于《满洲历史地理》当中。如,在考证汉代乌桓的位置与状态时,其主要观点为:汉兴盛之时,即武帝平定匈奴后,徙乌桓于塞外,为汉侦查匈奴动静,后霍光击乌桓,至后汉末期,乌桓各部“自立为王”,其兴盛长达40年。上述结论不仅无视汉“置护乌桓校尉监领之”的史实,反而将臣服于汉朝、并被置地居住的乌桓视为“蚕食汉地之外国”。在叙述两汉时期的鲜卑历史地理时,夸大其“疆域广大”、侵扰中原的“战功”的倾向也十分明显,而对两汉王朝对其授职、安置则只字未提。①白鳥庫吉監修,箭内亙、稲葉岩吉、松井等:「満州歴史地理」第一巻、第189-199頁。有意突出民族间“对抗”,无视汉民族与周边少数民族间政治交往和文化交流。《满洲历史地理》第一卷还将鲜卑、夫余等民族划归为“魏领土以外之满洲”,在叙述乌桓兴衰时写道:“西历180年,檀石槐死后,内讧起,领土分裂,势大衰,至3世纪初,乌桓濒临衰亡,其民皆没入鲜卑,今长城以北之地皆归鲜卑所有。由此可知,今之长城乃所谓中国之北境之事,始于汉魏之际也。”②白鳥庫吉監修,箭内亙、稲葉岩吉、松井等:「満州歴史地理」第一巻、第219-220頁。
五、研究结论的政治倾向
尽管白鸟库吉主张从事“纯学术”的考证性研究,但是我们从《满洲历史地理》的考证中仍然会发现如下特征。
首先,突出历史上汉民族与周边少数民族的对抗性关系。《满洲历史地理》基本上运用“掠夺”、“侵入”等词汇阐释朝鲜与秦、汉两王朝之间的关系。“朝鲜以蕞尔小国能够在亚细亚半岛的南端维持长期独立,未被相邻的大国支那吞并,其主要原因是支那将长城及辽东辽西之塞外地区经常性地存在着的强勇之戎狄视为敌国”。③白鳥庫吉監修,箭内亙、稲葉岩吉、松井等:「満州歴史地理」第一巻、第32頁。这种试图淡化古代中国东北的汉民族和少数民族乃至朝鲜半岛政权之间的政治联系、文化交流,而是强调敌对关系,进而将中原政权与少数民族政权定位为“敌国”的倾向是日本东洋学派在战前东洋史研究中的一个特征。
其次,研究重心聚焦于塞外少数民族政权。在《满洲历史地理》中,似乎是与中国史籍中重视中国王朝与塞外民族之间的政治性隶属关系的叙述原则相抗衡,将研究的重心聚焦于塞外少数民族政权,突出少数民族政权在势力强盛时期与中原王朝的军事较量,夸大少数民族政权的政治独立性。而对于历代中原王朝对少数民族政权的册封、授职等政治活动避而不谈。如,在叙述高句丽侵扰玄菟、辽东二郡时,《满洲历史地理》完全站在高句丽的立场上,不惜用“英迈勇武”这样的情意性词汇来褒奖高句丽的太祖大王。④白鳥庫吉監修,箭内亙、稲葉岩吉、松井等:「満州歴史地理」第一巻、第94-95頁。
第三,认为历史上中国王朝对中国东北地区的控制是暂时的,各民族争雄才是常态。对于中国中原王朝在东北边疆的经营水平,《满洲历史地理》第一卷认为,战国和秦汉时期中原王朝对东北边疆的经营是“上古支那种族的光辉历史,足以与此显著的发展相对比者,于后世之中仅见明初一时”。⑤白鳥庫吉監修,箭内亙、稲葉岩吉、松井等:「満州歴史地理」第一巻、第104頁。认定中原王朝对东北边疆的控制在历史上是暂时的,突出中原王朝的衰败和外部种族的繁衍、兴盛,特别重视少数民族政权对中原王朝领土的“蚕食”。其重要的研究理念—— “间空地”理论和“南北二元对抗论”也是为了证明中国东北地区在历史上就是民族争雄的“无主之地”这一政治性结论的核心理论。
综上所述,东洋学派能够搜罗到中国和朝鲜的丰富史料,很多朝鲜史料是此前从未被发掘的,从而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中国古代东北史研究。然而,《满洲历史地理》倾向于一个政治意欲十分明显的结论:“中国东北和朝鲜半岛在历史上不在中国中央王朝控制的范围之内。”虽然白鸟库吉提倡“纯学术”研究,但由于其观点不自觉地站在了为日本对中国东北的侵略寻找所谓“历史依据”的立场,因此,其研究结论仍然无法脱离为即将开始的侵略战争服务的政治性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