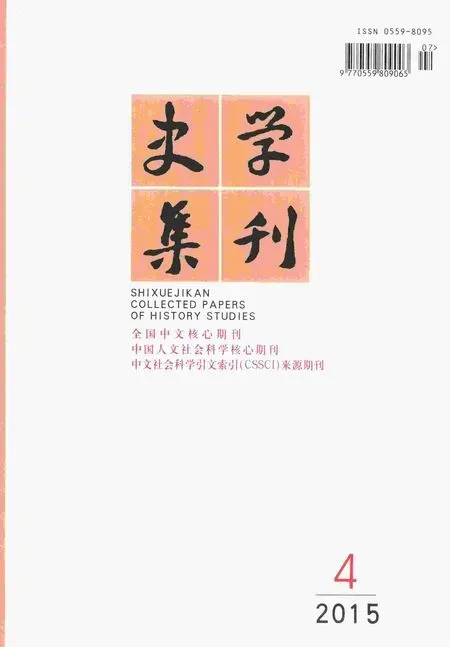从近世走向近代——宋元变革论述要
王瑞来
(四川大学,四川成都610065;日本学习院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
一、宋元变革论的形成经纬
2005年,受邀参加科举废除百年学术研讨会,由于我在日本参与编纂东亚共同历史教科书课题组中主动承担的是元代部分,因此对元代比较关注,在考虑提交论文时,我决定写元代的科举停废,为人们考察20世纪的最终科举废除提供一个历史的参照。在查找资料和撰写论文的过程中,接触到的史实与头脑中学术积淀,互相撞击,产生了思想火花,形成宋元变革论这一命题的雏形。
以此为契机,开始了我的学术方向转型,目光从上向下,从长期以研究皇权为主的中央政治研究转向对地方社会的研究。
以《科举取消的历史》①王瑞来:《科举停废的历史:立足于元代的考察》,刘海峰主编:《科举制的终结与科举学的兴起》,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55-166页。为起点,继续进行资料搜集与深入思考。当时,我在与东洋文库的同行们在完成中嶋敏先生领导的《宋史选举志译注》②中嶋敏编:《宋史选举志译注》(1-3),东京:东洋文库1992-2000年版。之后,进行内容相关的宋人笔记《朝野类要》③由我个人单独作业的点校本《朝野类要》,于2007年由中华书局出版。的译注作业。笔记中关于选人改官难的条目,让我对进士登第后的命运开始关注,并且与元代科举停废带来的士人职业取向贯穿起来,结合以往研究中积蓄的个案,写成一篇数万字的长文,①长文分批发表,现已刊出四篇:王瑞来:《金榜题名后:“破白”与“合尖”——宋元变革论实证研究举隅之一》,《国际社会科学》,2009年第3期;王瑞来:《“内举不避亲”——宋元变革论实证研究举隅之二》,《北京大学学报》,2012年第2期;王瑞来:《小官僚,大投射:罗大经仕履考析——宋元变革论实证研究举隅之三》,《文史哲》,2014年第1期;王瑞来:《士人流向与社会转型——宋元变革论实证研究举隅之四》,《上海师范大学学报》,2014年第2期。初步阐述了我主张的宋元变革论。
二、宋元变革论与唐宋变革论
宋元变革论,看上去是与唐宋变革论针锋相对的命题。其实,两者并非二元对立,都是从不同视角对中国历史走向的观察。根据一定的时代特征,把历史划分为若干时段观察,自然是一种具有逻辑意识的方式。除了唐宋变革论,还有美国学者的两宋之际变革论、宋元明变革论,还有由中唐至明变革论等。②以郝若贝 (Hartwell,Robert M.)、韩明士 (Hymes,Robert P.)、刘子键、史乐民 (Paul Jakov Smith)、万志英 (Richard von Glahn)等人的学说为代表。郝若贝:《750-1550年间中国的人口、政治及社会转型》(Demographic,Political and Social Transformations of China),《哈佛亚洲学报》(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第42卷,1982年第2期;韩明士:《官宦与绅士:两宋江西抚州的精英》(Statesmen and Gentlemen:The Elite of Fu-chou,Chiang-his in Northern and Southern Sung),剑桥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刘子键:《中国转向内在:两宋之际的文化内向》(China Turning Inward:Intellectual-Political Changes in the Early Twelfth Century),哈佛大学东亚研究委员会1988年版;史乐民、万志英:《中国历史上的宋元明变迁》(The Song-Yuan-Ming Transition in Chinese History),哈佛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
在诸多的命题中,20世纪初由日本内藤湖南首倡、宫崎市定等充实的唐宋变革论无疑影响最大。进入21世纪的重新关注,更使这一命题的影响达到前所未有的程度。③2005年南开大学历史学院与《历史研究》编辑部联合举办的“中国传统社会基本问题讨论”的争论热点之一就是唐宋变革论,2006年《河南师范大学学报》与《江汉论坛》又分别推出关于唐宋变革论的讨论专辑。个别专论之荦荦大者,则有如下:包弼德:《唐宋转型的历史反思——以思想的变化为主》(刘宁译,刘东编:《中国学术》第1卷第3期,商务印书馆2000年版)、张其凡:《关于“唐宋变革期”学说的介绍与思考》(《暨南学报》2001年第1期)、李华瑞:《20世纪中日“唐宋变革”观述评》(《史学理论研究》2003年第4期)、罗袆楠:《模式及变迁:史学视野中的唐宋变革问题》(《中国文化研究》2003年第2期)、李庆:《关于内藤湖南的“唐宋变革论”》(《学术月刊》2006年第10期)、张国刚:《“唐宋变革”与中国历史分期问题》(《史学集刊》2006年第1期)、柳立言《何谓“唐宋变革”?》(《中华文史论丛》2006年第1辑)、张广达:《内藤湖南的唐宋变革说及其影响》(《唐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57页)。李华瑞主编:《“唐宋变革”论的由来与发展》,天津古籍出版社2010年版。
唐宋变革是指中唐至北宋的变革,并非仅指唐宋之际,北宋作为这一变革期的终点,把唐代的因素发展到极致。因此说唐宋变革论作为古代以及古典主义终结的归纳,精辟而到位。至少从政治形态的变化看,我并不持有异议,在我的日文版《宋代的皇帝权力与士大夫政治》④王瑞来:《宋代的皇帝权力与士大夫政治》终篇第3节《关于唐宋变革论之我见》,东京:汲古书院2001年版,第501-504页。一书中专有一节阐述了我的认识。不过,唐宋变革论并不涉及宋代以后的中国历史演变。并且,在我看来,始初建立在部分推论基础之上的唐宋变革论,对两宋不加区分的捆绑论述具有一定的缺陷。最主要的是,唐宋变革论是追溯中国历史,向前看而得出的认识。
历史是流淌于时空之中一条连绵不断的长河。事物的变化大多如此,一个事物臻于完美,一个过程进行到后期,便开始酝酿下一个过程,便开始发生变异。这是持续的发展。唐宋变革论诉说的是中国历史从中古走向近世的变化。而我则是向后看,从南宋历元,跟明清、乃至近代的联系来观察得出的认识。观察的矢向不同。
靖康之变,北宋遽然灭亡。突然的巨变,政治场的位移,开启了下一个变革。靖康之变是一个促因,许多变革的因素已酝酿于北宋时期。这些因素伴随着时空的变革而发酵,偶然与必然汇合,从而造成宋元变革。这一变革,由南宋开始,贯穿有元一代。开启了中国历史走向近代的滥觞。探寻中国如何走向近代,宋元变革论会给出回答。
唐宋变革论与宋元变革论都不能摆脱宋代。宋代是两个变革的交集。不过,唐宋变革论至北宋而终,宋元变革论自南宋而始。同一帝系、同一制度下的两宋,既同又异。无论研究唐宋变革论,还是宋元变革论,皆不可将两宋捆绑在一起,笼统言之。在承认遗传的前提下,尤应留意变异。
叫宋元变革论,实在是一个容易引起误解的提法,让人误以为是指在宋元之际发生的变革。其实,与绵亘200多年的唐宋变革一样,我是指一个并不短暂的时段,也长达200多年,准确定义说应当是南宋至元变革论,变革期包括整个南宋和元代。出于简洁,就称作跟唐宋变革论相类的宋元变革论。
三、宋元变革论的学术背景
宋元变革论,并非我的首倡。前面提及,欧美学者有两宋之际变革论、宋元明变革论,还有由中唐至明变革论等。我必须承认是受到这些说法的启示。
那么,欧美学者的这些认识又从何而来呢?追溯学术史背景,大概还要回到首创唐宋变革论的日本。战后的相当长时期内,日本学者的中国史研究领先于世,并且出于冷战等原因,欧美的几代学人大多通过日本学者的论著来认识中国史。
关于这种学术背景,不仅仅是我个人的观察,并且还得到了欧美学者的亲口印证。1993年春,我在日本东洋文库巧遇英国学术院院士、牛津大学教授杜德桥,当时,我正在将近藤一成的《英国的中国学》长文翻译成中文,于是便围绕着有关英国的中国学问题,与杜德桥教授展开了讨论。他说,二战期间,西方国家对日作战,客观上形成了许多学者学习日语的局面。战后,这些学者又转向中国文化与历史的研究。可以说,这一代学者受日本中国学研究的影响较大。①王瑞来译:《英国的中国学 (下)》译者附记,台北:《汉学研究通讯》第12卷,1993年第4期,第244页。
后来,又看到我大学时代的老师张广达先生也有同样的认识:“在西方史学界,宋代一向是最受喜爱的中国朝代之一,一些西方学者把宋代呈现的种种新气象比拟为中国近世的文艺复兴,有的称之为‘新世界’这样的评价,非常可能就是受到了内藤史学的宋代近世说的直接、间接影响。”②张广达:《内藤湖南的唐宋变革说及其影响》,邓小南、荣新江主编:《唐研究》第11卷,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6页。
从这种特殊的学术背景上考虑,大量吸收日本学者的中国史研究成果,欧美学者对宋代以后的中国历史演变的观察,极有可能是来自日本学者的启发。不仅是欧美学者,汉语世界的学者也逐渐接受了近世这一历史分期的概念。例如近年在台湾举行的第四届国际汉学会议的论文集,便题名为《近世中国之变与不变》。③柳立言主编:《近世中国之变与不变》,台北:联经出版公司2013年版。其实,早在20世纪30年代,与日本学界有着共同视野的中国学者已经注意到、并使用了来自日本的“近世”概念,同时也加进了自己的解释。比如吴天墀先生就把北宋庆历时期视为中世和近世的分界线。④吴天墀:《中唐以下三百年之社会演变——庆历变革与近世社会之形成》(上),未刊稿,刘复生抄录整理。
从内藤湖南首倡到宫崎市定完成,日本学者不仅提出了为学界瞩目的唐宋变革论,还从世界史的视野出发,全面确立了不大为日本以外学者提及的近世社会的学说体系。⑤[日]宫崎市定著,砺波护编:《东洋的近世》,东京:中央公论新社1999年版。日本学者在中国史研究领域导入“近世”的概念,据考证,当始自京都大学教授内田银藏,其在1903年出版的《日本近世史》一书中所提出的“宋、元、明的文化是近世中国文化”的观点。详见[日]葭森健介:《唐宋变革论于日本成立的背景》,《史学月刊》,2005年第5期。同样是京都学派、较宫崎市定小十几岁的岛田虔次具体阐述了“近世说”导入的理由:“我的论证方法是这样的。首先把宋以后的中国与欧洲的近代Modern Age并行 (因为说的是从14、15世纪开始的时代过程,所以不是被19、20世纪的西欧文明所理念化了的‘近代本身’)。接下去因为自觉到都是人的社会,所以在宋以后的中国也肯定有与文艺复兴期以后的欧洲同样的现象。根据对这样的事之探究,中国史的普遍性与特殊性肯定也就明了起来了。”⑥[日]岛田虔次著,甘万萍译:《中国近代思维的挫折》后记,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329页。近藤一成评价道:“内藤湖南提倡,宫崎市定展开的唐宋变革论是日本的中国史研究可举出的最重要的成果之一,至今仍然是考察这一时代的坐标轴。”①[日]近藤一成:《宋代士大夫政治の特色》,新《岩波講座·世界歷史》9《中華の分裂と再生》,东京:岩波书店1999年版,第305页。近世这一时段是介于古代与近代之间的过渡阶段。无论叫作“近世”还是“前近代”,都是日本表示这一历史分期的通常用法。这样的中国历史分期,无疑比迄至鸦片战争的漫长数千年都视为古代的时代划分要精密得多。
对于近世的起讫,尽管在认识上有分歧,但推原首倡者宫崎市定等日本学者比较一致的认识,应当就是从宋代开始,并且主要就是指宋元时代。根据宫崎市定等日本学者的观察,宋元时代与西亚、南亚以及欧洲的近世社会有着共通的时代特征。世界史意义上的近世社会,东西方同时从这一时代开始平行展开。这一时代特征,佐竹靖彦从两个视点对中国的近世社会进行了扼要地归纳。一是从农村时代转向城市时代的社会结构变化,二是从宗教时代转向知识时代的变化。②[日]近藤一成主编:《宋元史学的基本问题》总论,中华书局2010年版,第4页。在我看来,前者反映的是社会生产力发展带来的商品经济的繁荣,后者则体现的是科举规模扩大带来的士人阶层的壮大。而这一切,都生长在北宋,开花在南宋,繁盛在元代。
唐宋变革论与宋元近世说是相互联系的两个时代观察。我主张宋元变革论,既有欧美学者的启示,更有日本学者潜移默化的影响。
不过,时代的推移呈渐进性,非如豹变。正像需要经历一段晨光熹微的黎明之后才会有旭日东升一样。在我看来,北宋处于消化唐宋变革成果、蓄积下一个变革因素的时期,而南宋才开始走向近世。斯波义信先生指出,北宋后期大规模水利工程的兴建,更使江南地域经济的开发达到高潮。不仅是经济,经济基础之上的文化也俨然重心倾斜于南方。仅举一个明显的事实,“唐宋八大家”中的宋代六家皆为南方士人。这些北宋蓄积的因素直接构成了政经合一的南宋发展基础。
然而,以王朝更替为视角的内藤湖南的近世历史分期,把近世的起点确定在北宋的创立。他认为:“唐和宋在文化的性质上有显著差异:唐代是中世的结束,而宋代则是近世的开始,其间包括了唐末至五代一段过渡期。”③内藤湖南:《概括的唐宋时代观》,《内藤湖南全集》第5卷,东京:筑摩书房1972年版,第309页。这样的历史分期尽管有其一定的道理,但从总的历史演进大势来看,还是有很大的咬合不上之处。没有摆脱王朝循环的框架,同唐宋变革论一样,宋代近世说不区分两宋,是其有欠详密的一面。其实,很多国内外中国史研究先贤,都先后从与近代历史的联系上,观察到了宋代与前代的巨大差异。其实他们笔下的宋主要指的是南宋。比如,曾与内藤湖南在天津见过面的严复就说过一段有名的话:“古人好读前四史,亦以其文字耳。若研究人心政俗之变,则赵宋一代历史最宜究心。中国所以成为今日现象者,为善为恶,姑不具论,而为宋人所造就,什八九可断言也。”④严复:《致熊纯如函》,《严复集》第三册,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668页。严复与内藤会面,参见内藤湖南:《燕山楚水》,中华书局2007年版。钱穆先生也说:“论中国古今社会之变,最要在宋代。宋以前,大体可称为古代中国,宋以后,乃为后代中国。秦前,乃封建贵族社会。东汉以下,士族门第兴起。魏晋南北朝定于隋唐,皆属门第社会,可称为是古代变相的贵族社会。宋以下,始是纯粹的平民社会。除蒙古满洲异族入主,为特权阶级外,其升入政治上层者,皆由白衣秀才平地拔起,更无古代封建贵族及门第传统的遗存。故就宋代而言之,政治经济、社会人生,较之前代莫不有变。”⑤钱穆:《理学与艺术》,宋史座谈会编:《宋史研究集》第七辑,台北:台湾书局1974年版。对于宋、元、明时代,钱穆先生讲道:“可说是中国的近代史”。⑥钱穆:《中国文化史导论》(修订本),商务印书馆1994年版,第175页。钱穆先生甚至直接说:“中国的近代史,自宋代即开始了。”⑦钱穆:《中国历史研究法》,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5页。以宋代为划期,将宋以后归为近世、近代,几乎是上一代学者的共识。张其昀就这样表述:“研究中国史学者,通常以宋代为近代史之开始。”①张其昀:《张其昀先生文集》第21册《新刊本宋史序》,台北:中国文化大学出版部1989年版。根据我的理解,如果从与后世的联系上看,先辈学者笔下的宋,主要就南宋而言。
历史的演进交织于遗传与变异之中。不截然分开而又区别观察,才是正确的研究姿态。北宋具有较多的唐代因素,而南宋又具有较多的北宋因素,都是必须加以留意的。余英时先生将南宋的高、孝、光、宁前四朝称之为“后王安石时代”,就是注意到了遗传因素,而他也观察到变异和断裂。②余英时:《朱熹的历史世界——宋代士大夫政治文化的研究》上册,三联书店2004年版,第8-9、15页。
由于同一帝系的两宋在制度设置和统治方式上的覆盖,纠结在一起的因素很多。应当从遗传的外衣之下,通过缜密的研究,揭示出时代的变异。从这个意义上说,两宋应当加以剥离区分。受到日本和欧美先学的启示,我明确提出的宋元变革论,不过是对既有学说的补充与实证。
四、从南朝到南宋:时空在江南重合
历史在时空中运行。以时间观之,根据时代变化的特征,必须把历来视为一体的北宋和南宋加以切割。以空间观之,也必须将地域进行切割,将南北分开。广袤的中国大陆,地域发展的不均衡性,使得研究者不可能将这一大陆板块的空间演化笼统地纳入统一的时间演进中进行观察,否则,研究结论的精确度便会大打折扣。在这方面,美国学者施坚雅 (G.William Skinner)的宏区划分理论范式为我们的考察提供了有益的启示。③[美]施坚雅撰,牛贯杰译:《中国历史的结构》,单国钺主编:《当代西方汉学研究集萃》(中古史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版,第1-32页。
为什么我将宋元变革的开启期确定在南宋?历史发展的偶然性让时空在江南重合,从而开启了中国历史的新一轮变革。地域发展既相对独立又互相联系,既不平衡又渐进趋平。一池湖水,尽管水深水温有不同,毕竟同为一池,交互影响。变革从南宋江南的时空发端,如水流从高就低,借由元明统一的时势,政治、经济、文化的推手便将变革向整个大陆各个地域辐射扩展。
我将视点聚焦在江南。让我们从明清向上回溯。以明清为主的近代以前江南研究,已经有了丰富的研究积累。台湾学者刘石吉认为,“明清以来,商品经济的发展和商业市镇的兴起,在江南更是普遍与突出的现象,经济结构在此起了大变化,初期的资本主义业已萌芽发展。19世纪中叶西方经济势力冲击到中国沿海、及近代通商口岸都市出现之前,江南地区的‘近代化’(不是‘西化’)的程度已经达到相当的水准。”④刘石吉:《明清江南市镇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1页。樊树志也指出:“江南地区经过长期的开发,到明代进入经济高度成长时期,最先显示出传统社会正在发生的变革,社会转型初露端倪。农家经营的商品化程度日益提高,以农民家庭手工业为基础的乡村工业化 (即学者们所说的早期工业化),在丝织业、棉织业达到了世界先进水平,工艺精湛的生丝、丝绸、棉布不仅畅销于全国各地,而且远销到海外各国,海外的白银货币源源不断地流入中国。严格意义上讲,江南市镇已经领先一步进入了‘外向型’经济的新阶段。”⑤樊树志:《江南市镇:传统的变革》,复旦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2页。
那么,明清江南高度的商品经济与早期工业化是从天而降的异军突起吗?我曾研究过给人以强烈的凭空崛起的蒙古开国史,从中找到了直接或间接接受汉文化影响的因素。⑥王瑞来:《中国史略》第8章《世界的中国》,东京:DTP出版社2006年版。同样的道理,经济高度发达的江南,最近最直接的基础是南宋和元代。圩田等江南广泛的土地开垦,农作物新品种的引进,技术的改良,促进了财富和人口的增长。据李华瑞先生转述,英国学者伊懋可的代表作《中国历史的模式》(The Pattern of the Chinese Past)详细研究了13世纪中国农业达到的水平,包括工具、肥料、农作物的品种及引进和改良、灌溉体系、农产品商品化程度等。伊懋可认为宋代中国已经发生了农业革命,南方成为全国的粮仓,大运河犹如一道商业通道,中国拥有当时世界上最高的农业生产率,并由此在交通运输、金融、信贷、城市化与市场系统各个领域都出现了革命性变革。①李华瑞主编:《“唐宋变革”论的由来与发展 (代绪论)》,第29页。
江南商业市镇发展的最初高潮出现在南宋,②陈国灿、奚建华:《浙江古代市镇》,安徽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174-175页。商业经济的兴起引发传统经济结构性产生变化,江南农村经济在宋代、特别在南宋已演变成为农业、手工业、商业、运输业和其他服务业在内的有机体系。③葛金芳:《农商社会:两宋江南社会经济的时代特征》,邓小南、杨果、罗家祥主编:《宋史研究论文集 (2010)》,湖北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121页。保守地说,宋代每年进入流通领域的商品总额大致在1亿贯左右。商业信用开始发达,北宋出现世界上最早的纸币交子仅仅在有限的区域流通,但受交子启发,南宋多次发行的会子或关子已成为社会主要支付手段,在“钱楮并用”的基础上贵金属称量货币白银也开始跻身于流通领域。④李埏:《从钱帛并行到钱楮并用》,邓广铭、程应镠主编:《宋史研究论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王文成:《宋代白银货币化研究》,云南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这些状况出现的背景因素,都是商品经济的繁荣。南宋在特殊的国际政治格局之下,依托江南发达的商品经济,历来的“头枕三河,面向西北”的立国态势,终于彻底转向为“头枕东南,面向海洋”,⑤葛金芳:《大陆帝国与海洋帝国》,《光明日报》,2004年12月28日。海外贸易成为南宋重要的财政收入来源。
元军统帅伯颜的《奉使收江南》中的诗句“精兵百万下江南,干戈不染生灵血”,⑥伯颜:《奉使收江南》,崔增亮主编:《古典文学》下册,人民教育出版社2008年版,第201页。尽管对他奉行忽必烈的“不杀”政策有些夸大,但蒙古人的江南征服,除了少量威慑性屠城之外,多数以不流血的形式完成。关于蒙古的基本不流血的江南征服,除了从《宋季三朝政要》等史书可以概见之外,个别学者的个案考察也可以印证这一事实。比如,申万里的《元代教育研究》就观察到,宋蒙战争对四明地区影响不大,元代庆元路的文教活动在原有的物质基础之上,仍然蓬勃发展。⑦申万里:《元代教育研究》第七章《元代庆元路的儒学教育考察》,武汉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561-594页。蒙古的不流血征服,对于江南来说,意义极为重要。这使自南宋以来的经济结构未遭重创,改朝换代并未中断经济发展的进程,反而更开阔了疆域的形成与多种贸易方式的导入,更为刺激了江南经济由内向转为外向。这就是宋元留给明清的铺垫。
其实,对于明清江南高度的商品经济,不少学者都有长时段的延伸观察。李伯重讲到,若就狭义江南及长江三角洲而言,从13世纪初到19世纪中叶,也就是南宋后期到清朝中叶这六个多世纪,确实是一个经济成长方式发生重大变化的时期,即从以前的“广泛型成长”转变为“斯密型成长”。⑧李伯重:《多视角看江南经济史 (1250-1850)》,三联书店2003年版,第8-9页。而斯波义信则有更为延伸和清晰的观察:“8-13世纪的中国取得了很大的经济增长,从而带来了社会和文化方面的变化。总之可用一句话概括为:与其说是纯农业文明,不如说是都市化文明含有更多的固有特征。这是延续到19世纪中国社会的最大特色。”⑨斯波义信撰,方健、何忠礼译:《宋代江南经济史研究》,江苏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65-66页。
明清的宋元因素不可忽视。日本学者杉山正明敏锐地观察到,宋元时代的中国“以华北为重心的状况开始向江南和南方移动”。他所说的宋代无疑主要是指南宋。因为他在后面接着讲道:“以南宋的成立和前后的华北人口的向南移动为开端,真正意义上的江南开发和汉化开始深化,江南各地域的人口、社会、经济、文化的比重增大。”杉山进一步由南宋俯视了元代:“这个南北逆转的现象被元代直接继承下来 (严格地说来到了元代才真正开始展开),与明代的状况直接相连。这可以说是和现在有关的中国史上的大现象。”[10]杉山正明:《蒙古时代研究的现状及课题》,[日]近藤一成主编:《宋元史学的基本问题》,第288页。杉山的这段话,可以佐证我主张的宋元变革完成于元代,并且也意识到了宋元变革之于近代中国的意义。
蒙元史专家的杉山以世界史的视野高度评价了江南在元代的地位:“为了能够彻底洞察明代中国,有必要主动进行南宋、元代的江南研究。从欧亚规模来看,蒙古经过吸收南宋的遗产,当时的江南是世界首屈一指的充满富有的‘生产社会’(当然是彻底和其他地域比较后),以陆海两种方式向世界开放。可以说蒙古时代与同时代的欧亚和非洲相比,江南社会的优势是明显的。”①杉山正明:《蒙古时代史研究的现状及课题》,[日]近藤一成主编:《宋元史学的基本问题》,第288页。显然,在杉山看来,从社会发展的角度观察,元代并不是一个黑暗的时代。据明史研究者的观察,元代江南的繁荣在明初由于政策因素而遭受损害,到了明中期以后,远离政治中心的江南才重现繁荣。②夏维中、韩文宁、丁骏:《关于江苏地域文化的几点思考》,范金民、胡阿祥主编:《江南地域文化的历史演进文集》,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3年版,第25页。
90年代到美国访学的杉山注意到了美国的学术动态:“在某种程度上已经显露出美国的宋代史研究者转向元代史研究,特别是江南研究方面的集中现象非常显著。”因此他在将近20年前就预测道:“把握江南北宋——南宋——元——明等大潮流,无疑会成为研究中国历史的一个要点。”③杉山正明:《蒙古时代史研究的现状及课题》附记,[日]近藤一成主编:《宋元史学的基本问题》,第305页。现今,江南这一地域对于近世中国研究的重要性,已经成为多数研究者的共识。
在南宋历元的积淀之上,政治中心再度北移的明代光大了江南。持续繁荣而富庶的江南,在清代成为全国歆羡而向往之地。江南,不仅一直保持经济重心的优势,而且成为文化重心。近世乃至近代,最具中国元素之地,舍江南而无他。钱穆先生就概观言之:“下经安史之乱,南部重要性日益增高,自五代十国迄宋代,南方的重要性竟已超过了北方。我们也可以说,唐以前中国文化主要代表在北方,唐以后中国文化的主要代表则转移到南方了。”④钱穆:《中国历史研究法》,第120页。钱穆先生所说的宋代南方重要性,自不待言,以南宋为突出。而我讲的江南,即是广义的南方。宋元变革的大剧,在江南的特定舞台上上演。
五、从侧面切入的尝试
(一)科举的盛世
论述中国历史如何走向近代,宋元变革论是一个相当宏大的命题。我个人其实无力全面驾驭,只是提出命题,并从一个侧面切入进行了初步阐述。
基于个人的研究经历,我决定从南宋科举及第后选人入官这一点切入,从而揭橥社会转型之渐。因为,在多数情形之下,知识人都是社会的主要引领者。
如所周知,从北宋太宗朝开始,伴随着宋朝统一事业的基本完成,亟须各级管理人才的现实状况、重文抑武的战略转变以及笼络士人的政治策略等多种因素,让宋朝政府全速启动了科举这架机器,开始了大规模的官僚再生产。
从此,两宋三百余年间,每科取士几乎都达数百人乃至上千人。两宋登科者,北宋约为61 000人,南宋约为51 000人。⑤两宋科举人数的统计,参见何忠礼:《两宋登科人数考索》(杭州大学历史系宋史研究室编:《宋史研究集刊》第2集,浙江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与张希清:《南宋贡举登科人数考》(《古籍整理与研究》第5期,中华书局1990年版)、《北宋贡举登科人数考》(北京大学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编:《国学研究》第2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这些数字的总和数倍于宋朝以前和以后的历朝科举登科人数,折射出科举制度和由此造就的士大夫政治的时代辉煌。
由于“本朝取人虽曰数路,然大要以进士为先”⑥周必大:《周文忠公集》卷一三六《论发解考校之弊》,《宋集珍本丛刊》影印本,线装书局2004年版,第52册第409页。的政治设计,在多种入官途径中,进士出身者升迁最快,金榜题名后,飞黄腾达者,史不绝书。“白衣举子”,风光无限。
(二)辉煌后的阴影:科举难、改官难
然而辉煌有阴影。科举造就了不少高官显宦,他们显现出耀眼的光芒。但同时科举也制造了无数的范进式的潦倒士人,却不大为人所瞩目。即使在科举盛行的宋代,以解试百人取一,①周必大:《论科举代笔》云:“大约州郡数十人方解一名,亦有至一二百人者。”参见周必大:《周文忠公集》卷一三六,第406页。省试十人取一约计,②徐松辑:《宋会要辑稿》选举五之三,中华书局1957年版。也只能有千分之一的幸运者可获得金榜题名的殊荣,而多数士人则与之无缘。③千人取一的科举倍率,北宋时来访的日本僧人成寻也注意到了。《参天台五台山记》卷二载:“予问司理官子秀才明州秀才来由,答云:明州、温州、台州秀才,并就台州比试取解,约五百来人已上取十七人,将来春就御试取三人作官。五百人秀才中只取三人作官,天下州军镇秀才廿万余人,春间御前比试只取三人给官,约千人取一也。”(东京:风间书房1978年版,第70页)就是说,五万人的金榜题名的光芒,遮蔽了五千万人次举子以及更多的支持着他们的家人的悲辛。
更为值得注目的是,这五、六万幸运儿在金榜题名后的命运,也并非个个都是风光无限。这是被迄今为止的研究漠视的一隅。北宋真宗朝开始确立选人改官制度,多数选人需要包括顶头上司在内的五名举主推荐,方能有资格升迁京朝官。制度性的规定,加上举主和胥吏人为因素,使得普通选人改官格外困难。这在北宋中后期已见端倪,降至南宋,员多阙少日渐严峻。尽管南宋政府保证了科举取士的正常进行,却不得不在选调的葫芦口死死卡住。在政界缺乏背景的普通及第者,尽管可以成为低级官僚的选人,由于制度上和人际关系上的因素,却几乎无法挣脱出通向成为中高级官僚的瓶颈。南宋贺允中就指出过:“寒士改官,视为再第。”④李心传撰,胡坤点校:《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一七八,绍兴二十七年十二月癸卯条,中华书局2013年版,第7册第3417页。事实表明,选人改官,难于科举登第。因为不仅靠成绩、政绩,还要靠人脉,个人无法掌控命运。只有走出选人七阶,进入京朝官序列,仕途方能充满光明。正如周必大具体讲到的那样,“知县、通判俱已得阙,自可弹冠以昌远业”。⑤周必大:《周文忠公集》卷一九八《与李季允埴》,第53册第121页。
大量通过千分之一高倍率的激烈竞争科举及第者,在此后的仕途上遭遇到更为激烈的新一轮升迁竞争。多数需要在七阶选人所构成的庞大“选海”中经历漫长的翻滚,只有少数幸运者由于各种因缘际会,得以顺利改官,升迁到中级以上的官僚地位。大多数选人摧眉折腰,被呵责役使,忍受地位低下、俸禄微薄,小心翼翼地熬过十几年,甚至耗尽毕生的心血,到死也难以脱出“选海”。
士大夫政治这个“如来佛”所创造的宋代科举、选调、改官的官僚体制,就像是一个立着的葫芦。这个葫芦的下部容量最大,容纳的是成千上万的举子和以其他方式企图走上仕途的人。千里拔一的科举考试和其他入官方式,就像是葫芦中间的狭窄部分。这是一个瓶颈,很难通过。然而通过之后,也还不能脱颖而出,只是向上进入了葫芦的另一个层次。刚开始进入到这个层次,会觉得有一种解除通过瓶颈时那种窒息的轻松,很快就会发觉这是一个比葫芦的下部还要狭小的空间。在这个狭小的空间里,挤满了想要冲出葫芦口的选人,而能够冲出比前一个瓶颈更为狭窄的葫芦口的选人寥寥无几,多数人就躺倒在葫芦的中间层了。
“入流太泛,入仕甚难。受命者至有十余年不成一任,贤愚并滞,殊无甄别”。⑥周必大:《周文忠公集》卷一三四《举官状》,第2册第398页。科举、荫补、摄官、进纳、军功、吏人补授等等,宽泛的入流,将官场这个葫芦的底层塞得满满的,宋王朝扩大统治基础的初衷走向了反面,选人入官的制度性的问题与实施中流弊,让“贤愚并滞”。尽管针对“贤愚并滞”的问题,朝廷做了一定的补救措施,让选人七阶中层级较高的文林郎以上者可以关升京官致仕,⑦周必大:《周文忠公集》卷一三四《论选人关升后致仕白札子》,第2册第400页。但这仅仅具有安慰之意,对已经走到仕途终点的士人来说,难掩影响一生命运的失意。
“金榜题名时”,在过去曾被形容为人生得意的几个境遇之一,但金榜题名后,却让多数金榜题名的时代宠儿得意不再,失望至极。文献中记载,南宋初年就有一个姓姚的士人“累举不登籍,遂束书归休,绝意荣路”。⑧洪迈:《夷坚志》支甲志卷七《姚迪功》,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764页。
科举难,改官难,严酷的现实最终让对仕途绝望的士人“绝意荣路”,与主流政治产生疏离,使多数士人潜沉下层,滞留乡里,导致士人流向多元化。胥吏、幕士、讼师、商贩、术士、乡先生都成为士人的谋生选择。社会流动由纵向更多地趋于横向。纵向的推移带来横向的变化。下层士人和官僚无法进入主流的结果,最终必然是漫溢的支流淹没了主流,社会发生转型。
(三)疏离主流,士人走向地方
美国学者郝若贝指出,从江南经济最发达的华南地区逐渐形成自在自存性的几类大族考察,南宋的社会文化精英的志向和心态显然与北宋的不同。北宋精英大多怀有报效朝廷、得君治国的抱负,因而不惜脱离故乡。到了南宋,地域精英虽然不排除仍有跻身庙堂之志,但是扎根地方开始成为他们的主要选项。对此,张广达先生高度评价道:“郝若贝注意考察两宋之间士大夫的差异,这是他的贡献。”①张广达:《内藤湖南的唐宋变革说及其影响》,邓小南、荣新江主编:《唐研究》第11卷,第52页。而包弼德先生解读唐宋变革论说,唐宋的社会转型只是政治精英和文化精英,亦即士大夫的身份的重新界定以及他们逐步演变为“地方精英”的过程,而不是内藤所描绘的贵族门阀制的终结和“平民”的崛起的社会画面。②包弼德撰,刘宁译:《唐宋转型的反思——以思想的变化为主》,刘宁译,刘东编:《中国学术》,第1卷第3期,第72-75页。我觉得包弼德先生的解读正可以用来解释我所说的宋元变革论。因为走向地方的趋势,明显出现在南宋。
在经济发达、地方势力强盛的背景下,不少士人以各种形式流入地方社会。士人的参入,在客观上提升了地方社会的知识层次,强化了地方社会的力量。才士不幸地方幸。拥有文化权力与社会资源的地方精英,构成庞大的网络,促进了地方社会的发展。由于商品经济与社会网络的力量使然,走向地方的士大夫精英与横向流动于地方各个角落的士人,不同于往昔的文人失意归隐,他们不可能隐于林泉,隐于市廛,自外于社会,而是以谋势或谋生的积极姿态参与地方事务之中。
士人流向地方,既有因科举难而形成的水往低处流的主动选择,也有被动接受。南宋愈加严酷的“员多阙少”的状况,让有出身的士人长时间待阙于乡里。据我考证,《鹤林玉露》作者罗大经就是进士登第八年后,才走后门得阙入官。③王瑞来:《小官僚,大投射:罗大经仕履考析——宋元变革论实证研究举隅之三》,《文史哲》,2014年第1期。由于僧多粥少,不少低中级官员在一期差遣任满之后,也要回乡待阙。甚至即使是获得了差遣任命,也还要等到那个差遣的位置空出来之后方能赴任。同样也要滞留乡里。士人、士大夫滞留乡里,也并非无所事事,这些有身份有地位的人物,为地方所倚重,被邀请或主动参与到地方事务之中。除了待阙,丁忧守丧的三年,也给了士大夫在一定时期回归乡里和参与地方活动的机会,在地方留下他们的印记。对此,我可以举出南宋文坛大家杨万里的例子。杨万里从选人改秩成为京官不久的隆兴二年 (1164)便丁父忧回乡守丧,乾道三年(1167)服除授知隆兴府奉新县,但一直在乡里待阙,又过了三年的乾道六年方得赴知奉新县任。这是杨万里担任低级官僚时的经历。升迁到了中级官僚的杨万里,同样还需要待阙。他淳熙二年(1175)夏改知常州,但家居待阙到淳熙四年夏始有空阙赴任。④杨万里的经历,参见辛更儒撰:《诚斋先生杨万里年谱》,(宋)杨万里撰,辛更儒笺校:《杨万里集笺校》第十册附录,中华书局2007年版。南宋的宰相史浩就说过“贤大夫从官者,居官之日少,退闲之日多”。⑤参见袁桷:《延祐四明志》卷一四《本路乡曲义田庄》转述,中华书局编辑部编:《宋元方志丛刊》第6册,中华书局影印本,1990年版,第6343页。因各种原因“被地方化”,在乡里的长期滞留,既让士大夫重新贴近乡里,也让乡里亲近了士大夫。
南宋的这种变化,与此后长期停废科举的元代社会变化紧密相关,也与明清时代乡绅势力的历史渊源割舍不断。
元朝的停废科举,基本堵塞了旧有的士人向上流动的通路。彻底绝望的士人只好一心一意谋求在地方的横向发展。在多元选择中,为吏大概是最多的选择。这不仅是士人利用知识优势的务实之举,还隐含了过去通过科举走向仕途之梦。这种选择也与元朝政府从胥吏中选拔官员的方向一致。
流向地方的士人的知识资源与发达的商品经济所形成的经济实力,两者合流,促进了地域势力的发展。而元代科举在几代人几十年间的停废以及儒户的建立,又将士人彻底推向了地方。除了利用知识优势为吏,从事教育也是士人的众多选择之一。传道授业,士人将政治理想倾注于社会。
将精力倾注于地方的士人,首先从齐家做起,经营一个家族,扩充一个家族的经济基础、政治地位和社会影响。齐家是同地方建设同步进行,密不可分的。近代中国社会的宗族,最可靠最直接的来源就是南宋,从南宋延续而来。从此,宗族势力一直在地方社会作为末端血缘集团发挥着重要作用。并且士大夫家族间以及富民与士人的联姻,都构成了广泛的人脉网络和一定的地方势力。
北宋的士大夫政治精英,在社会上开始形成新士族。由于没有了官僚贵族世袭制,恩荫这种世袭的余泽也只能停留在官僚金字塔的低层,因此为了家声不坠,科举出身的士大夫还是把希望寄托在科举之上。不仅士大夫官僚同僚之间广泛联姻,还吸纳有发展潜力的士人进入家族,为家族灌注新鲜血液。因而有“榜下择婿”的现象存在。所谓“婚姻不问阀阅”,①郑樵:《通志》卷二五《氏族略》,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313页。只是不问过去以地望郡望相称的旧阀阅,新的名门阀阅不仅要问,并且还是特别讲究。不仅“榜下择婿”,还寻求一切机会物色择婿,甚至掠夺择婿。胥偃择欧阳修为婿,②《宋史》卷二九四《胥偃传》,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9818页。晏殊择富弼为婿,③《宋史》卷三一三《富弼传》,第10249页。都是典型的事例。
北宋末期就发生过这样一个悲剧,一个叫曾安强的士人已经与温氏女子订婚,有一天在泰和快阁读书的曾安强,被路过的广东路转运使看中,要把女儿许配给这个有为的青年,业已订婚的曾安强居然答应了下来。消息传到未婚妻耳中,竟然导致自杀身死。④清《雍正江西通志》卷九九《列女》。这是一个没有展开的陈世美与秦香莲的悲剧故事。相信这在两宋并非特例。然而,对择婿者无可厚非,这反映了宋代士人和士大夫建设新士族家族的努力。治国平天下是士大夫政治背景下的士人宏大理想,但原点无疑是立足于齐家。简单地说,士族是士人最为根本的目标。美国学者韩明士对两宋的抚州地域进行考察。就士人的婚姻状况来说,北宋时期婚姻面向全国,南宋则倾向于本地。前者与士人力图走出地方入仕中央的目标是一致的,后者则与士人回归地方的倾向相吻合。⑤韩明士:《官宦语绅士:两宋江西抚州的精英》(Statesmen and Gentlemen:The Elite of Fu-chou,Chiang-his in Northern and Southern Sung),剑桥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210-212页。尽管韩明士在史料运用上存在一定问题,⑥对于韩明士的批评,参见包伟民:《精英们“地方化”了吗?——试论韩明士,〈政治家与绅士〉与“地方史”研究方法》,邓小南、荣新江主编:《唐研究》第11卷,第653-671页。但他所观察到的北宋和南宋士人流向差异倾向则无疑是应当予以承认的。
六、精英引领社会转型
作为精英治国的士大夫政治,在北宋开始形成,其意义不仅显示于政治领域,还影响到社会的各个层面。这是中国历史上出现的划时代变化。士大夫政治格局,让中国文化的发展也改变了既往的形态。春秋战国、魏晋南北朝,五代十国,中国思想文化都是在王朝失去深入控制社会能力之时,开出了绚烂之花。而北宋则在士大夫的主宰之下,中国文化走上自然发展的正常之路,伴随着经济繁荣而繁荣,政治之手不再成为文化发展的强力钳制。科举规模的扩大,带动了全社会的向学,印刷业也由此空前兴盛。士人作为一个阶层,像滚雪球似的前所未有地扩大。
靖康之变,中断的只是北宋王朝的进程,并未改变士大夫政治的基本格局。不死鸟在江南重生,包括士大夫政治在内的北宋因素,由于传统、惯性以及百年积淀都被南宋全面接受。并且在南宋的特殊背景下走向地方社会。如同随风潜入夜,士大夫政治浸透到社会的各个角落。任何时代的地域社会都存在着支配势力与领导层。在南宋,就是士大夫、士人引领着地方社会。
作为一个阶层,士人的身份逐渐明确并得到认同。并且,时空的变化,让士人与士大夫的面向也有了改变,由致君转向化俗,更为注重在地方的发展。在北宋,士人循蹈的还是得君行道的上行路线,从南宋开始,士人则逐渐面向地域,行走移风易俗的下行路线。
政治精英体现在入朝为官,是对地域的脱离,而士大夫家族的根却根植于地域。随着士大夫政治的壮大,根植于地域的新士族也同时在壮大,北宋的苏州范氏,南宋的四明史氏,都是宋代新士族兴起的一个缩影。北宋时代开始建设经营的新士族,到了南宋,在商品经济发达的江南,业已在各个地域盘根错节,相当强盛,既有经济实力,又有政治影响力,还拥有世代编制的无所不在的巨大人脉网络,成为不可忽视的地方社会的主导性势力。
这里还想举出一个具体个案。前面提及的曾安强,其曾孙求周必大为早已死去的曾祖父文集写序,后来另一房的孙子又来让周必大把那序文也给他们一份,于是周必大又誊抄给了他们。不能不写,不能不抄,为敬慕前人也好,为人情人脉也好,周必大都必须要做。而周必大并不是普通说求就可以求的刀笔吏,他曾经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宰相。因为曾氏在庐陵并非无名小户,也是有势力的世家旺族。周必大在一篇文章中,称求他写序的曾安强曾孙曾寅亮为“故人”,意即老朋友,并通过曾寅亮的介绍,他还为别人写了《太和县仰山二王行祠记》。除此之外,周必大还应担任衡州耒阳县令的曾安止侄孙曾之谨之请,写过《曾氏农器谱题辞》。据周必大庆元四年所撰《朝议大夫赐紫金鱼袋王君镇墓碣》①周必大:《周文忠公集》卷七七,第51册第718页。可知,曾之谨还是朝议大夫王镇的女婿。这些事实,都表明了曾氏家族在当地的影响力。退归乡里的周必大出于各种复杂的考虑,一定要维护彼此的关系,这是一种利益的联结。②参见王瑞来:《科举家族与地域网络——以曾安强与周必大为中心的个案解析》,《社会科学研究》,2015年第3期,第1-5页。
南宋的中央政治有一个引人注目的现象,这就是在不少时期权相当政。从秦桧、韩佗胄到史嵩之、史弥远,再到贾似道,宰相专权的时间几乎占据了南宋150年历史的一半以上。宰相专权尽管可以视为士大夫政治的极致发展,但毕竟是一种变质。长期的宰相专权,让中央政治的运营处于不正常的状态。而不正常的状态又使不少士大夫精英对中央政治产生了疏离。在史弥远去世后,岭南的崔与之被任命为右宰相,但他居然多次坚辞不就。对于崔与之坚辞的原因,有保持晚节说,有砥砺士风说,其实深层的原因就是对中央政治的疏离。③参见王瑞来:《“百世闻之尚激昂”:读菊坡诗》,朱君泽主编:《崔与之与岭南文化研究》,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414-415页。对中央政治疏离,崔与之是一个代表,像这样的士大夫精英为数绝不会少。与中央政治疏离,那么去向便是地方社会。
出官入绅,士大夫政治精英出于各种原因回到乡里之后,又变身为地方领袖,在长期经营的家族基盘之上,权势余威、富甲乡里、精神力量等综合因素,都足以使他们指麾一方。这些回到地方的士大夫精英,也成为仕途失意或对仕途望而却步的士人所依附的靠山。
自北宋以来士大夫政治的引导以及展示的辉煌,带动了全社会的向学和文化提升,从而使士大夫政治拥有了一个广泛基础,这就是为数众多且不断滋生的士人层。在北宋,这个士人层向士大夫政治的金字塔尖聚集。到了南宋,攀塔路难行,这个士人层在地方弥散。不过分布于地方的士人并非一盘散沙。
以诗词书画等文化和道学等学术为媒介,各个地域的士人形成庞大而广泛的社会网络。这种士人网络,既编织于本地域,又由于人际交流,横向扩展于其他地域,并且向上延伸于各级官府。入仕与否并不重要,共同的文化背景,构成了士人间彼此沟通的身份认同。
由于拥有文化知识,并且拥有广泛的人脉,又有各种社团组织依托,更有宗族的根基,士人属于地方上具有整合能力的阶层。动乱时代崇尚武力,军人活跃。和平时期则是士人的天下。“士农工商”,传统的职业划分,士居于首。爱字惜纸,普通庶民对拥有文化知识的歆羡,让士人在社会上一直受到尊重。对地方公益事业的积极参与,则更加扩大了士人的威望与影响力。修桥铺路,兴修水利,赈灾救荒,建学兴教,凡属公益事业,都能看到士人活跃的身影。
如果说北宋政治呈现出由精英士大夫主宰的状态,南宋社会则是由分布于地方的江湖士人群体所主导。江湖士人群体成为举足轻重的势力。南宋中后期在文学领域出现的江湖派,实际上是一个大多位居下层的中小作家群体。这些作家有些是虽入仕却滞留于选人的低级官员,有些甚至就是未曾入仕的布衣。这个活跃于南宋中后期的文学群体,拥有广泛的社会影响。知识人社会角色的转变,推动了精英文化向平民文化的转型。向通俗而世俗方向发展的社会文化,精英意识淡薄,疏离政治,贴近民众。元代杂剧的兴盛,明代市民文化的繁荣,似乎都可以从南宋中后期的文化形态中窥见形影。
然而,从另一方面观察,自南宋开始大量投身于地方的士人,与国家政权并未完全脱节,多数士人积极参与的社会建设,其实也是国家末端统治的一环。士人和士大夫,在乡为民,入仕为官,这种特殊的双重身份,使他们居中成为连接官与民的纽带。斯波义信先生观察到,从南宋开始,大量“公心好义之士”参与到他称之为“中间领域”的活动之中,即倡导或组织既不完全属于官也不完全属于民的义庄、义仓和义役等活动。①斯波义信:《南宋における “中間領域”社会の登場》,佐竹靖彦等编:《宋元時代史の基本問題》,东京:汲古书院1996年版,第185-203页。然中文版《宋元史学的基本问题》收入此文时将“中间领域”译作“中间阶层”,似未得其质,不知是否得到了斯波先生的首肯。这其实也是梁庚尧先生所指出的民间力量对国家公权力整合乡村秩序的参与。②梁庚尧:《南宋的农村经济》,台北:经联出版事业公司1984年版。国家公权力贯彻乡役制度,地方乡绅推行义役制度,两者之间既有紧张的纠结,又有主动的配合。利益指向尽管有不同,但在客观意义上都是对乡村秩序的整合与建设。
正如钱穆先生所言:“士之一流品,乃是结合政治社会使之成为上下一体之核心。”③钱穆:《中国历史研究法》,第44页。士人的积极参与和官府的主导相济互补,“齐家、治国”的道学指引,以及政治经历,让以士人和还乡的官僚士大夫为主体的乡绅与国家政权有着剪不断的联系。地方上的士大夫精英、大量普通士人,加之以献纳等方式买来出身夸耀乡里的富民,作为乡绅阶层,从事地方建设,调解地方纠纷,分派役职,动员民众,具有相当大的号召力,成为与国家权力既依附又抗衡的强大地方势力。
立足地方,胸怀天下,可以说是南宋以来乡绅的一个写照。南宋以降的政治生态环境,让更多的士人把对王朝的事业心转向地方建设的社会担当。
从南宋后期的士籍产生,到元代的儒户确立,不凭血缘,不靠门第,文化贵族的世袭,终于在元代得到了法律上的认可。不以拥有财富为标志,不以职业为区别,而以文化为身份,无恒产的士跻身于以职业划分的众多户种之中,成为编户齐民的一类,拥有不纳税,不服役的特权,从自贵到他贵,比较社会的其他阶层,儒户的确可以称得上客观存在的一个精神贵族群体。江南的这个群体,据估计拥有10万户之多。④[德]傅海波、[英]崔瑞德编,史卫民等译:《剑桥中国辽西夏金元史》第9章《蒙古统治下的中国社会》引述萧启庆先生的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727页。这为明清强势的乡绅社会奠定了深厚的基础。
原本作为士大夫政治的理论基础而形成的理学,在南宋特殊的背景下逐渐光大为道学,成为弱势国家所赖以支撑的精神支柱。失去了中原的王朝需要以“道”来申说正统,这是催生道学的一个客观的背景因素。而士大夫则以道统的承载者身份来充当了全社会的精神领袖。道学到了元代完成了南北精神统一,《大学》中“格物、致知,正心、诚意、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八条目的发掘阐释,成为连接个人、家族、地方、国家的精神纽带,从而达成地方社会主导的国家与地方的互补。于是,南宋光大的道学,经由元代,在明清一统天下。
道学弘扬的道统,不仅超越了王朝,还在汉字文化的覆盖下超越了族群。而道学通过教育、教化向民众的普及,又成为建设地方的士人层连接与领导民众的方式之一。南宋以降兴盛的书院所彰显的私学理想与实践,从某种意义上说,也是北宋以来士大夫政治唤醒和培植的独立意识在士人社会的广泛渗透。①参见王瑞来:《将错就错:宋代士大夫“原道”略说——以范仲淹的君臣关系论为中心的考察》,《学术月刊》,2009年第4期。不仅是书院,包括社仓、乡约、乡贤祠等机构与公约的设置,在国家与家庭之间形成一个互为作用的社会权威场,充分显示了士人在道学理想牵引下对地方的关怀与主导。道学在地方社会成为新兴士绅的道德标榜与精神指导。在弘扬道学的旗帜下,加上科举和为吏等“学而优则仕”的魅力驱动,商业活动等实用需要,教育从南宋开始获得了空前的普及。
人皆有出生地,带有独特的地方印记。但在南宋以前,这种地方印记,除了在建立同乡人际网络时被刻意强调之外,在力图走出乡里,向上发展的士大夫那里一直比较淡漠。而南宋以降,政治与社会环境的变化,让着意于谋求在地方发展的士人逐渐强化了地方意识。对于发掘和树立的乡贤或先贤的祭祀,便显示了士人精英强化地方认同的努力。不过,乡贤并不只是现成的存在,而是经过了士人根据自身价值理念标准的筛选。在南宋以降,这种理念标准就是道学意义,道学的理念一以贯之。乡贤是地方的先贤,但又是超越地方的楷模。道学覆盖地方,乡贤回归地方。这样的乡贤树立,灌注了士人的普世理想。而乡贤的祭祀,无疑也成士人掌控精神指导权,并由此间接显示领导地位的方式之一。
除了从事教育之外,没有了科举的时代,拥有文化知识的士人流向更为分散而多元,犹如水漫平川,渗透到社会的各个领域。多数士人或许并没有多么崇高的理想与道义担当,只是为了养家糊口而为稻粱之谋。我曾考察过由宋入元的黄公望的生平。②王瑞来:《写意黄公望——由宋入元:一个人折射的大时代》,《国际社会科学杂志》,2011年第4期。这个以画出《富春山居图》而闻名于后世的画家,曾经长期为吏,有个叫张句曲的人戏题《黄大痴小像》就说黄公望是“贫子骨头,吏员脏腑”。③陶宗仪:《南村辍耕录》卷二八《戏题小像》,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版,第317页。除了为吏,黄公望还教书、算卦、入教,从事过多种职业。作画只是晚年的一种兼职。南宋袁采讲道:“士大夫之子弟,苟无世禄可守,无常产可依,而欲为仰事俯育之资,莫如为儒。其才质之美,能习进士业者,上可以取科第、致富贵,次可以开门教授,以受束修之奉。其不能习进士业者,上可以事笔札、代笺简之役,次可以习点读,为童蒙之师。如不能为儒,则医卜、星相、农圃、商贾、伎术,凡可以养生而不至于辱先者,皆可为也。”④袁采:《袁氏世范》卷中《子弟当习儒业》,天津古籍出版社1995年版,第105页。袁采为士人指示的出路,不是出于他开明的臆想,而是南宋实况的反映。我在《士人流向与社会转型——宋元变革论实证研究举隅之四》一文中,从史料中爬梳出的士人经营田产例、士人剃发出家例、士人教书例、士人经商例、士人为吏例、士人投身反乱例,就是明证。
七、从近世走向近代
进入南宋后的“员多阙少”,使绝大多数科举登第后的士人停滞在低级官僚的层面,至死无法升迁至中级官僚。严酷的仕途现实让士人失望、绝望,逐渐与主流政治产生疏离,士人流向形成多元化。而元代长期废止科举,更为促进了这种趋势。大量士人参与到地方社会,提高了地方社会的知识层次,引领了社会转型。明清以来强势的地方乡绅社会,来源正是南宋历元的积淀。
俯观明清,虽然科举得到了完全的恢复和发展,但以乡绅为主流的多元而强势的地方社会业已形成,呈现出任何政治力量也无法改变的势态。究其始,溯其源,发端于南宋,壮大于蒙元。
地方社会的崛起是宋元时代变革的一个标尺。南宋士人在科举和改官时遭遇的境况,并且由此所形成的士人流向多元化,实在是催化宋元社会转型之一因。
南宋又仿佛回到了南朝,政治、经济中心再度合一,经济重心的作用发挥得尤为显著。元朝取代南宋,科举的停废,以吏为官,则加速了自南宋以来的社会变化。社会变化的基础是经济结构。而蒙古人对江南基本上实行的不流血征服,则保全了经济结构的完整。竭力彰显文治的蒙元统治,又与士人说服统治者以儒治国在主客观上达成合流。
从南宋开始盛行的以职业划分户种的做法,全面实行于元代,到明代依然被保留下来,文献中明代负担劳役的军户、灶户 (制盐)、乐户、果户、菜户、渔户、打捕户等,随处可见,大量手工业户种从农业分离出来,改变了社会结构,近代社会职业划分的基础渐次奠定。
宫崎市定在评论吉川幸次郎的《宋诗概说》时认同吉川的说法:“宋人们的生活环境,与过去中国的状况相比,具有划时代的变化,靠近了现代的我们。”①宫崎市定:《吉川幸次郎著〈宋诗概说〉》,《东洋史研究》,1963年第1期。这是相当敏锐的观察。
“靠近了现代的我们”的“具有划时代的变化”,酝酿于北宋,开始于南宋,完成于元代。“像一杯混沌的鸡尾酒,经过南宋至元转型的动荡,降至明清,中国社会又变得层次分明,无论是乡绅阶层还是地方社会,都大致定型,走向近代。”②王瑞来:《写意黄公望——由宋入元:一个人折射的大时代》,《国际社会科学杂志》,2011年第4期。
时 (南宋、元)、地 (江南)、人 (士人)三要素互动,造成宋元大变革,中国社会开始向近代转型。回望历史,尽管有不少迂回曲折,然而大河奔流已非任何力量所能阻挡。
——士大夫的精神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