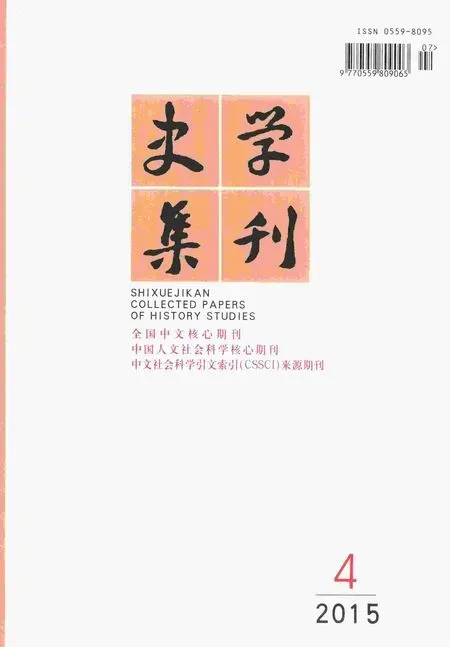试说乡村社会与中国佛教寺院和僧人的互相影响
严耀中
(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上海200433)
中国古代佛教寺院所处的环境主要可分乡村、名山、城市三个类型,这也构成了寺院存在的环境差异,从而影响了寺院佛教的发展,并构成寺院与社会关系的不同类型。这里仅就乡村社会的环境对寺院与僧人,也就是给佛教在乡村的存在与发展带来了新的形态和各种影响,构成中国佛教史的一个不能忽视的侧面。试说如下:
一
不同的社会环境之间的差异会不会对僧侣和寺院发生影响?答案是肯定的,因为僧侣是生活在寺院里的,寺院就是僧人的生存环境,而寺院又是其所在地之社会的一个组成单元,所以环境的变化应该会影响到寺院和僧侣。“佛教的传播实际上就是正规的僧团——寺院 (Vihãra)的传播”。①许理和:《汉代佛教与西域》,任继愈主编:《国际汉学》第二辑,大象出版社1998年版,第299页。而寺院功能的发挥和它们所处的位置环境大有关系,环境有自然与人文之分,对宗教来说,更重要的是人文环境。这是因为社会中的宗教是以人为基础,并是处于人际关系结构中的宗教,而影响社会形态和人际关系的两个最基本要素,便是人口数量和人口素质,后者包括对佛教的信仰程度,因为信众是寺院香火的基础。他们在地域分布上是非常不均匀的,于是在这两点上构成了社会中乡村和城市之间的主要背景差异。因此,当寺院处于社会结构中的不同环境位置时,它们必然会产生不同的外在和内在社会适应性。
由于至少到东晋十六国起,中国的寺院才接收了大量出家的汉人,②因为佛教在两汉间传入中土,此后诸朝虽不禁止信佛,也允许佛教建寺立像,但不允许汉人剃度出家,直至西晋犹“时禁晋人在沙门”(《法苑珠林》卷五四《惰慢篇·引证部》)。正如任继愈先生所说,汉魏时的佛教“一般广大群众只是被作为特权贵族施舍的对象才接触到它”,参见任继愈:《中国佛教史·序》,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9页。因此只有在永嘉之乱以后,原先禁令失效,大量汉人方能出家进佛寺。寺院数量也大大增加,广泛分布在乡村、名山和城市。“天下名山僧占多”,自东晋起,庐山、虎丘山等就有高僧前后相继筑寺修行,至南北朝摄山、天台山等更是成为一宗之名山。这些佛教名山由此成了寺院和僧侣的集中地,而与城市和乡村寺院不大一样。①不过五代以前的“名山”主要是有着一宗之“祖庭”而扬名天下,如国清寺之于天台山。唐以后如九华、普陀等山皆以围绕某一菩萨或佛的崇拜,在这些名山上分属诸宗的寺院几乎都有。在这些佛教名山上,寺院之间彼此相邻,有数十乃至上百。如此密集的寺院和僧众群,既是互衬和互补,也起着相互监督和制约的作用,而且包括僧官在内的官府对名山诸寺的管理一般也比较严密,有时候还受到朝廷的特别关注。另一方面,由于仰慕名山,流动前来挂单的僧众多,四方蜂拥而来的拜佛香客则更多,还有随之而来的不少小商小贩。因此少数名山上寺院的社会环境反而与城市里的差不多,不同的只是自然环境,从而和一般的乡村寺院有所区别,应该另当别论。
至于城市寺院,由于中国古代城市相对山区乡村有着两个主要特色。第一,城市是政治 (有时包括军事)中心,除京师外,绝大多数为州、郡、县各级地方长官的驻地,军政吏员及其家族和依附者构成了城市人口中很重要的部分,甚至是居住者中的多数。第二,城市中包括服务业在内的商业手工业远要比农村集中发达,至于山区林地更是远离商业,至少是因为城市的交通比较发达从而为商业流通提供了有利条件。工商业发展还带动产生出相当的市民阶层,尤其在唐、宋以后,市民阶层成了城市佛教徒中间不容忽视的一部分,这使得城市与名山这两类寺院的周围信众在社会阶层的构成中有着很大的不同。
存在于广大农村里佛教寺庙之环境,包括自然条件和信众社会,都与前两类寺院有很大区别。
二
存在于乡村中的寺院由于和本地社会俗众打成一片,相互的影响程度比城市和名山中的寺院大得多,给乡村寺院及其僧侣所造成的利弊也就更为显目。归纳起来,大致有以下各点:
第一,乡村地域环境之限制对寺院僧众和信众关系构成的影响。中国古代的寺院虽然有着十方寺、子孙寺等差别,但因为出于官府对控制僧侣流动的需要和地理交通条件的限制,寺院里的僧人有着很强的区域性。于是产生了对僧人来源的影响。此外,众多寺院的集中有利于僧人的寺间流动和佛学上的交流,于是产生了僧人的素质问题。②如张弓先生对《高僧传》中高僧所在的隋代寺院统计:“见于隋僧行止的佛寺262所”,大部分是在城市里,仅京兆郡(长安)就有64所。(参见张弓:《汉唐佛寺文化史》上册“寻兰篇”,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93页)“高僧”应是僧众里得到僧众和社会公认的精英,却主要在城市,甚至是在都市里,至少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城市僧众素质要高于乡村里的僧众。因为僧众的素质决定着寺院的作用,而寺院的环境等等客观条件又影响着僧众的素质,两者是互联的。并且由此关联出寺院的功能和形象,以及这两者合起来的社会作用。在农村寺院出家的僧众,一般都来自附近的地域,不若城市和名山的寺众往往来自四方各地。他们之间,以及他们与附近信众之间有着相近的生活习惯,操着相同的方言,容易形成较为紧密的关系。如苏州一带流传的夏至谚语中有“六九五十四,乘凉入佛寺”③参见《吴下田家志》等,转引自杜文澜辑:《古谣谚》卷四八“夏至冬至谚”条,中华书局1958年版,第618页。等。这些俚语民谚至少表明佛教与民众日常生活关系密切所留下来的印记。至于在一些特定的地域,如在3—9世纪的高昌,几乎一大半寺院都以族姓或家族代表冠名,如麹寺、粟末义寺、都郎中等,甚至起着与家庙族庙类似的作用。④严耀中:《麴氏高昌王国寺院研究》,《文史》第34辑,中华书局1992年版。而城里的寺院或名山大刹则多为十方寺,挂单的僧众多来自四面八方,信众也多为外地朝拜进香而来,有很大流动性。
第二,乡村寺院以地方经济为依托,互相荣衰与共。由于寺院在农村地区成了难得的公共场所,也因此往往成了乡村集市的所在地,更不用说每逢佛教节日所举行的大规模庙会了。这些集市或庙会对乡村经济和佛教双方都起着促进的作用,其实佛寺的修造和存在本身也是对地区经济的一个促动,因为修造需工匠材料,有寺就有香客和香烛消费等等,都会或多或少带动商品经济发展。不过乡村寺院的经济状况一般要远比城里的寺院差,僧众的生活条件当然也会差得多。如果地方上遇到一些天灾人祸,收成欠佳,经济萧条时,情况就更糟糕了。在如此经济的生存压力之下,一种结果是僧人亡失,“满山残雪满山风,野寺无门院院空”①元稹:《雪后宿同轨店上法护寺钟楼望月》,《元稹集》卷一七,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191页。成了常见的景象。即使僧众不流失,在这样物质条件很差的寺院,香火不会很旺,寺院为主的集市或庙会就难成规模甚至难以举行。而且由于乡村的经济实力有限,人口密集度不高,所以乡村寺院规模一般并不很大。此外一个副作用是,如果没有高僧前来,缺乏物质条件的寺庙对外地的僧人和信众缺乏吸引力,由本地乡民出身的僧人和信众无论是宗教素质和文化素质的平均水平都会低于城里寺院,宗教的社会影响就会减弱,这也是乡村缺少名寺的一个原因。
第三,乡村寺院与信众之联系有别于城市和名山上的寺院。因为在中国寺院不仅仅是僧人苦修之地,而且还是一般在家信徒朝拜的场所,它周围总有着多寡不一的信徒群。他们是寺院的存在基础,寺院同他们的关系就是寺院的主要社会关系,并在这样的关系中凸显寺院的社会性。因此乡村寺院的信众群就相对固定。这些地域性很强的信众群体在给寺院带来稳定的香火同时也给寺僧带来特有的约束。这是因为中国古代的农村由于多以家族聚居的形态生活,乡约族规和人情习俗是社会的主要纽带。由于在封建体制内,维持秩序的“伦理刑法扩展到民事领域并将不重要的民事关系的调整委之于风俗习惯和家法族规”。②任喜荣:《伦理刑法及其终结》第四章,吉林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129页。身处其中的寺院及僧侣也不得不受其强烈的制约。这些制约和戒律结合起来往往成为乡村寺院明文或俗成的僧制寺规,尤其在地方大族头面人物成为寺院主要施主的情况下。因为当施主交给寺院的财富数量较大时,内律允许其对“施舍出去的财物是还有很大的说话权的”。③何兹全:《佛教经律关于寺院财产的规定》,《中国史研究》,1982年第1期。这种说话权其实也就是关于财物使用的某种附加条件,于是这种条件也就成了加在僧团或僧侣身上的一些特殊约束。如宋太宗淳化年间莆田郑氏舍田于崇圣庵诸刹,“付与寺僧充柴薪之用,递年计该产钱二百三十四贯。入庵而后,子孙不许侵渔,寺僧亦不许盗献豪门”。④参见《广化寺檀越郑氏舍田碑记》,丁荷生、郑振满编:《福建宗教碑铭汇编》兴化府分册,福建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7页。这后面一句话就是对寺僧行为的一种约束。其实这种情况早已有之,如吐鲁番出土的《宁朔将军麹斌造寺碑》中,麹氏对“寺主不良,费用非理”规定了处置办法,⑤参见《麹斌造寺碑》,摹本载黄文弼:《吐鲁番考古记》,中国科学院出版1954年版,第52页。此类不得有违施主意愿的约束在南北朝至隋唐期间不少寺院都有。⑥参见何兹全:《佛教经律关于寺院财产的规定》,《中国史研究》,1982年第1期。由于这些施主乃至一般村民与寺院僧人朝夕相处,因此当地民众对僧侣的约束要比其他地方来得更为贴近和严格。如清代广东顺德县《文海林氏家谱·家规》云:“凡僧尼道士三姑六婆,毋许入门,不惟远嫌疑,亦以端风化也。”浙江山阴《项里钱氏宗谱·族规》中也禁止僧道尼姑等“穿门入户”,要“杜其往来,以免后悔,此是齐家最要紧事”。这些家规族戒虽然是直接针对本族族人,但对位于这些宗族居住地区的寺院僧侣当然会感受到压力而迫使他们更加小心谨慎。因此历史上乡村寺僧不良行为记载很少,换言之农村地区寺院的戒律维护要好过城市,社会环境也是一大因素。另外,筑造乡村寺庙的工匠由于建筑视野和技术水平的限制,总是会将寺院的布局和房屋风格向本地传统式样靠拢,促成了寺院外观的进一步地方化,寺内所塑佛像的造型及附加装饰也更与本乡本镇的观念和环境接近。⑦太史文 (Stephen Teiser)先生在对一些西部石窟中所塑生死轮图像研究后指出,“石窟的创始人也被雕刻在生死轮的中央,这些都是地方特征的表现”。参见太史文:《地方式和经典式:甘肃和四川生死轮回圈》,胡素馨主编:《佛教物质文化,寺院财富与世俗供养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上海书画出版社2003年版,第237页。
第四,乡村佛教与地方民间信仰有更多的结合,在很大程度上导致了佛教的民间化。一方面是因为乡村往往迎合民众的信仰需求,重视做法事等宗教服务功能,偏于宗教的形式而轻义理,于是对和其他地方崇拜的区分就不大讲究。另一方面,由于佛教有着作为全国性宗教的优势,一般会把具有地方特色的崇拜变为佛教信仰或染上佛教色彩。如唐初,“研精律藏二十余年”的“襄部法门寺沙门惠普”在当地移风易俗,即“楚俗信巫杀为淫祀。普因孚化,比屋崇仁。又修明因道场三十所”。①郭子林点校:道宣《续高僧传》卷二一《唐荆州神山寺释玄爽传》,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785页。又如敦煌文书中有名“四分戒” (P.3135)者,系敦煌佛弟子索清儿在病中为求治愈抄录《四分戒》所写之序,其云:“乙卯年四月十五日,弟子索清儿为己身忽染热疾,非常困重,遂发愿写此《四分戒》一卷。上为一切诸佛、诸大菩萨、摩诃萨及太山府君、平等大王、五道大神、天曹地府、司命司录、土府水官、行病鬼王、疫使知文籍官、院长押门官、专使可官、并一切幽冥官典等,伏愿慈悲救护”等等。其中“太山府君、平等大王、五道大神、天曹地府、司命司录、土府水官”等其实都是中土的民间神祇,现在都列入了佛教的神灵中了。还如在浙江遂昌县,“本地称所有神的塑像,画像等为‘老佛’”,②参见吴真:《遂昌庙祀神考析》,上海民间文艺家协会、上海民俗学会编:《中国民间文化——地方神信仰》,学林出版社1995年版,第9-15页。即成佛门中的了。再如流传在民间的《土地宝卷》说土地神被佛祖制服后,被佛祖遣使遍游天下。③参见车锡伦:《中国宝卷概论》,《中国民间文化》,1995年第2期,第335页。甚至也把关羽列为伽蓝神之一,此说首先始于荆南玉泉寺,董侹《重修玉泉关庙记》云关羽在该寺显灵,被自天台赶来的智者大师所济度,遂成为佛教神祇。④董诰等编:《全唐文》卷六八四,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第3102页。除此之外,佛教还将自身原有的一些神祇具备民间信仰的功能,以此来作为渗入中土民间崇拜的一个方面。这中间也可分为两类,一是将佛经中的一些神祇形象化、本土化,在民间成为新的崇拜对象,如“树神”、“狮子大王”、“五通神”,⑤参见严耀中:《汉传密教》第十八、十九、二十诸章,学林出版社1999年版,第270-316页。及所谓“肉身菩萨”⑥参见严耀中:《中国佛教世俗化的一个标识——关于唐宋文献中“肉身菩萨”的若干分析》,北京大学东方研究院华林编辑部编:《华林》第二卷,中华书局2002年版。等。二是一些有民间影响的高僧死后演化为地方崇拜对象。如在江浙一带有宝志、杯度、济公,后来还有“修炼成佛,俗名罗佛”⑦杨守仁修:《万历严州府志》卷六“分水县罗佛庵”条。的罗佛真人等,在福建则有真济三公、行端和尚、佛姑娘、三平祖师、定光古佛、清水祖师等等。⑧福建的佛教俗神情况,可参见林国平、彭文宇:《福建民间信仰》第六章,福建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63-322页。这些新的来自佛教的民间崇拜分流了民间的信徒,在佛教与原地方信仰的影响消长中,起着可观的作用。在这个过程中由地方僧人管理民间崇拜的场所往往起着重要作用,如明代“僧人李师、王如千、杨满湖”参与了阳城县汤王庙的重建,他们至少是管理该庙的人员之一,到了清康熙二十八年,该庙则明确有“住持僧本源”。⑨分见冯俊杰编:《山西戏曲碑刻辑考》卷六《重修汤王庙记》、卷八《成汤庙化源里增修什物碑记》,中华书局2002年版,第299、388页。这种结合的结果使得我们在叙述中国佛教时多了一个名词:“民间佛教”。乡村寺院是表现民间佛教的重要场所,也是“三教合一”最坚实的社会基础。因为三教合流是佛教最早表现出来,也是历来最主动的,这种倾向同样反映在民间佛教里。
三
当然乡村佛教寺院既然与当地社会保持密切的关系,在受到地方上影响的同时,也一定会有反向的影响。这些影响除了佛教对社会一般的影响外,还发挥了一些独特的社会作用。如侯旭东先生通过对北朝并州乐平郡艾县安鹿交村“合村邑子”所造之佛像碑进行分析后指出:“通过造像,特别是题记位置的设计与内容吸引过往行人,尤其是皇帝、官吏的注意不无联系”,并表现为一种国家认同。[10]侯旭东:《北朝村民的生活世界——朝廷、州县与村里》,商务印书馆2005年版,第264页。其实造像碑往往就是乡村寺院的一个组成部分,造像碑对帝王官吏的吸引,也就是乡村寺院政治作用的一个侧面。
除了上文说及的佛教与地方民间信仰之间的互相融合外,佛教对地方上其他文化也作用颇大。这是因为乡村寺院与所在地的关系更为紧密,使佛教在地方上所起社会作用也往往更为显目。与城市相比较,乡村是文化教育相对落后的地方,这使得村寺或所谓“野寺”成了其中文化上的闪亮点。因为寺庙里总会有僧人能识字读经的。如果有高僧在此的话,那寺院绝对是这个区域里的文化制高点。这个制高点的作用非常广泛,有戒律和因果报应等道德说教作用,有修桥铺路等示范义举,有医药赈灾等慈善功德,有推动文化教育的影响,有保护寺院四周林木山水之功劳等等,等于成了一个个地域的文化和慈善中心。于此记载论述的文字已有非常之多,这里就不再一一列举。①如其中一些例子可参见全汉昇:《中古佛教寺院的慈善事业》(《食货》,第四期第一卷,1935年)等论著。当然城里的寺院也有这些功能,但城市里寺院多,各种与文化有关的如学校、医生等教外影响更多,还有官府在直接笼罩着,其寺院文化对该佛寺周围居民社会的辐射作用反而没有乡村孤寺来得重要。此外乡村的寺院往往带有戏台,且从唐宋以降的诗词中我们可以看到,有相当大的一部分诗词是文人墨客在住或游地方上寺庙时即兴所做。这其实也是佛寺在乡村的文化作用之一。
佛寺对乡村的丧葬影响很大。由于中国人的坟墓主要修筑在乡村,即使是城市居民死后也会回原籍下葬,至少是要葬在郊外,乡村佛寺一般都要参与丧事,更不用说专门的“坟寺”了,所以对民间丧葬风俗产生各种影响。首先,佛教对丧葬仪式影响之一在于随葬品中。陪葬物里有着佛教内容的端倪已见诸魏晋南北朝。三国两晋时江南已有不少装饰有佛教内容的所谓“魂瓶”被考古工作者陆续发现。又如南齐时张融在其遗嘱中关照他死后下葬时要“左手执《孝经》、《老子》,右手执小品《法华经》”。②《南史》卷三二《张邵传附张融传》,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837页。再如在浙江温州的一座有“永和八年 (352)九月十□余□氏”铭文砖的东晋墓陪葬品里,还有一个石质藏经盒,其盒盖正中阴刻楷书“无垢净光陀罗尼经函”③参见吴明哲:《浙江温州市瓯海区出土东晋铭文砖》,《文物》,1998年第11期。九个字,可见此佛经也是随葬品之一。在唐代的墓葬中以天王像来避邪驱魔十分流行。如洛阳龙门及花园村、润西谷水、关林,西安狄寨、羊头镇、灞桥、韩森寨,礼县兴隆、新寨,凤翔南郊和南关村东等地唐墓都有天王俑出土,且与文官俑等“组合已成定制”。④参见洛阳文物工作队:《洛阳龙门唐安菩夫妇墓》,《中原文物》,1982年第3期;洛阳文物工作队:《唐睿宗贵妃豆卢氏墓发掘简报》,《文物》,1995年第8期;洛阳文物工作队:《河南洛阳润西谷水唐墓清理简报》,《考古》,1983年第5期;洛阳博物馆:《洛阳关林59号唐墓》,《考古》,1972年第3期;马咏钟:《西安狄寨出土唐三彩》,《文博》,1994年第1期;陕西文管会:《西安羊头镇唐李爽墓的发掘》,《文物》,1959年第3期;西安市文管会:《西安唐金乡县主墓清理简报》,《文物》,1997年第1期;张正岭:《西安韩森寨唐墓清理记》,《考古通讯》,1957年第5期;昭陵文管所:《唐越王李贞墓发掘简报》、《唐临川公主墓出土的墓志与诏书》,《文物》,1977年第10期;赵丛苍:《凤翔出土一批唐三彩和陶俑》,《文博》,1989年第3期等。1983年河南临汝发掘的一座唐代小墓中也有天王俑一件;⑤参见临汝县博物馆:《河南临汝县发现一座唐墓》,《考古》,1988年第2期。另外,甘肃秦安杨家沟、敦煌老爷庙一号、长安郭家滩十二号等唐墓中足踏鬼怪的所谓“武士俑”,其实也都是天王俑。⑥参见甘肃省博物馆:《甘肃秦安县唐墓清理简报》,《文物》,1975年第4期;夏鼐:《敦煌考古漫记—— (二)老爷庙唐代墓葬的清理》、考古所陕西考古队《宝鸡和西安附近考古发掘简报》,《考古通讯》,1955年第2期。这些在隋唐墓葬的发掘清理报告里几乎不胜枚举,说明佛教随葬品自魏晋起已成为广大农村墓葬中的一个重要内容。
为死者祈祷而举行法事,愈来愈成为寺院的一项重要活动。如当今所谓梁皇忏 (即慈悲道场忏),用以超度亡灵,企求冥福。不过其中也有与恶鬼受戒相连的成分,如宗磐述供天忏仪时云:“此番恶贼,盖是鬼子母未受戒时,食王城男女,居人怨之,故作此目”。⑦释道法校注:志磐《佛祖统纪》卷三四《法门光显志·供天》,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版,第754页。如此法会忏仪在中国民间社会中有着极为广泛的势力,不过性质上乃属于大乘佛教。此外,葬法是又一大影响。火葬,佛教中称荼毗,或作阇维、阇毗、阇鼻多等,本为僧侣之葬法,“火焚水沉,西戎之俗”,⑧《南史》卷七五《隐逸顾欢传》所载《夷夏论》,第1876页。而在中国“自释氏火葬之说起,于是死而焚尸者,所在皆然”。⑨永亨:《搜采异闻录》卷三,《笔记小说大观》第九册,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1984年版,第365页。此在江南民间尤成时尚,据宋人周煇言:“浙右水乡风俗,人死,虽富有力者,不办蕞尔之土以安厝,亦致焚如”,骨灰也葬于寺院的池塘内。①参见周煇:《清波杂志》卷一二,戴建国编:《全宋笔记》第五编第九册,大众出版社2012年版,第127页。当时一些寺院专设有“化人亭”,以火化尸体。如南宋吴县城外通济寺“久为焚人空亭,约十间,以罔利。合城愚民,悉为所诱,亲死即举而付之烈焰”。②顾炎武:《日知录》卷一五“火葬”条,上海商务印书馆1933年版,第19、20页。再如四川凉山地区出土的一个唐末宋初间的火葬罐,“上面书写有红色的梵文文字和贴有小块的金箔”,随葬品还有密宗法事所用的“铜金刚杵一件”。③四川凉山博物馆:《四川发现古代火葬墓》,《考古》,1984年第9期。说明了地区性火葬与佛教间的关系。此外如唐代太原一度“俗为浮屠法者,死不葬,以尸弃郊饲鸟兽,号其地曰‘黄阬’。有狗数百头,习食胔,颇为人患,吏不敢禁”。④《新唐书》卷七八《宗室李暠传》,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3531页。这些城市里少见的丧葬现象当然是佛教寺院在乡村存在的结果,说明佛教面临不同地区也是入乡随俗而使其本身发展呈现多样化。如此变化在城市和名山的寺院中就不大容易见到。
以上种种表明,虽然大多数著名的佛教寺院不是在名山就是在城市,但寺院的多数却是在广大乡村,它们通过在与乡村社会的相互融合,联系着超过90%的中国民众,成为佛教在中国最重要的生存基础。除了宗族的祠堂之外,寺庙可以说是乡村最重要的公共建筑了。而且祠堂只为一姓一族所有,而寺庙却对当地所有百姓开放,⑤一些大族的家庙、坟寺除外。但这些寺庙毕竟是少数,有的也向一般信众开放。因此寺庙往往成为乡村居民最大的公共场所。正因为有着这样的因素,寺庙殿塔也成了地方上的标志性建筑。我们在一些碑文上可以看到地方上一些寺庙虽然迭经兵火之灾,却能毁了重修,再毁再修,绵延数百年而长存不衰。所以上述乡村佛寺与其周边社会的那种互动关系,也是中国佛教史里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由于佛教寺庙在乡村起着如此的社会文化中心的作用,实际上它也替代朝廷在农村基层的一些社会功能。如宋辽时燕山云居寺所在乡民“同德经营,协力唱和,结一千人之社,合一千人之心。春不妨耕,秋不废获。立其信,导其教,无贫富后先,无贵贱老少,施有定例,纳有常期,贮于库司,补兹寺缺”。⑥王正:《重修范阳白带山云居寺碑》,陈述辑校:《全辽文》卷四,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81页。又如唐代白鹿乡佛教邑社组织的宗旨说得很明确,“此邑耆宿长幼士女等知身觉悟,共发齐心。且好人恶煞,蠲弊崇善,所以贤达君子多爱法焉,于是矻矻勤心,孜孜不怠”。⑦董诰等编:《全唐文》卷七五七石文素《白鹿乡井谷村佛堂碑铭》,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第3485页。因此可以说乡村的佛教寺院通过和民众结社互动,往往在广大的农村社会中起着稳定和凝聚力的作用。所以长期以来在中国古代,朝廷任命的行政官员能够只下延到县一级,把社会管理让地方自行解决,从而节约了不少行政成本,寺庙在其中所发挥的那些功能也功不可没。不过从另一方面说,乡村佛教寺院的这种社会政治功能之获得,也是其官方化的一个侧面。而在这个过程中,宗教的神圣性也渐渐地减去它的光辉。而作为这种演化的另一方面,则是其一成不变地受到包括僧官衙门在内的官府控制。因此自唐宋以降,只要是体制内的佛教寺院,无论其是否在乡村,对朝廷至地方各级政治之影响是微不足道的。
总之,鉴于在古代中国,农村人口占着全国人口中的绝大多数,乡村民众的信仰成了宗教在社会存在的基础,所以乡村寺院对佛教的社会作用至关重要。而乡村寺院与当地社会民众之间的互相影响是全方位的,或多或少牵涉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乡村地区的这些寺庙在时间和空间上的广泛分布也足以说明佛教寺院和中国古代农村社会的紧密结合。文献中如此的例子是大量的,不过由于篇幅关系,本文不能一一枚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