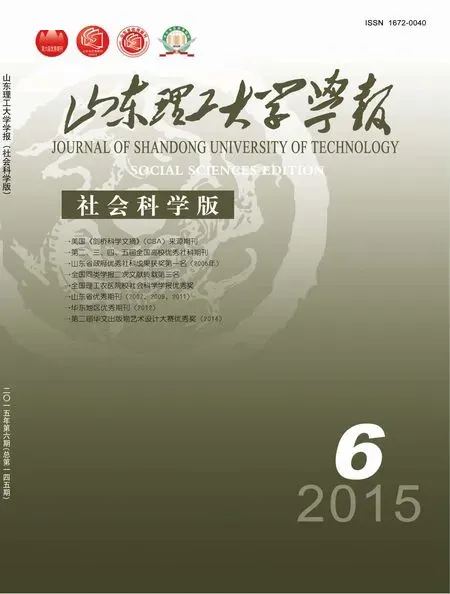魏晋士人人格特质论
岳庆云
(山东理工大学 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山东 淄博 255049)
魏晋士人人格特质论
岳庆云
(山东理工大学 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山东 淄博 255049)
魏晋时代不仅是“文的自觉”的时代,也是“人的觉醒”的时代。作为魏晋文化的开拓者和领导者,魏晋士人深感社会制度的腐朽与政治统治的黑暗,继而转向玄学,醉心于诗酒、放诞其言行、崇尚个性与自由,最终形成了为后世称颂的“名士风流”。魏晋士人的人格意识中,潇洒飘逸的姿容气度、自然率真的情感追求、浓郁悲凉的生命意识以及自由逍遥的人生理想等四个方面的特质构成了当时士人人格的主要内容。魏晋士人的人格魅力超越了时代并及于后世,如曹植、阮籍、陶渊明等对中国后世文人人格产生了深远影响。
魏晋士人;文的自觉;人的自觉;人格理想
鲁迅先生认为,魏晋时代是“文的自觉的时代”,并把曹丕的《典论·论文》视为“文的自觉”的发端。[1]189李泽厚先生则认为,魏晋时代实现了“人的觉醒”。他说:“《古诗十九首》……无论从形式到内容,都开一代先声。……它实质上标志着一种人的觉醒。”[2]91“文的自觉”,意味着魏晋文学脱离了汉代经学的桎梏,走向了审美的文学。而“人的觉醒”,则意味着魏晋士人摆脱了伦理道德的束缚,发现了审美的人生。可以说,魏晋时代不仅是“文的自觉”的时代,也是“人的觉醒”的时代,二者都是与魏晋士人人格特质的形成相伴而生的。
作为魏晋文化的开拓者和领导者,魏晋士人深感社会制度的腐朽与政治统治的黑暗,继而转向玄学,醉心于诗酒、放诞其言行、崇尚个性与自由,后人称之为“魏晋名士”。对于“魏晋名士”,后世多以“风流”一词来加以描述。如《世说新语·品藻篇》曾记载,有人问袁侍中:殷仲堪相比韩康伯怎么样呢?对方回答说:在玄理的收获方面,二人的高下还难以分辨。然而韩康伯门庭清净,显然具有“名士风流”,可见殷仲堪不如韩康伯①注:本文中引用《世说新语》内容,参考刘义庆著.陈书良译注.世说新语[M].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2015年。。此处的“名士风流”,即“魏晋时期士人追求的一种具有魅力和影响力的人格”,[3]31也是本文要探讨的魏晋士人的人格特质。
一、潇洒飘逸的姿容气度
魏晋士人非常看重服饰。在《抱朴子·饥惑》中,葛洪曾这样描述魏晋士人的服饰特点:“日月改易,无复一定……所饰无常,以同为快。”这说明,魏晋士人非常注重着装,且款式多变。《世说新语·容止篇》记载:士人庾子嵩身高不满七尺,“腰带十围”。“十围”亦作“十韦”,形容粗大。可见衣服宽大是魏晋士人服饰的基本特点。鲁迅先生曾认为这种宽大的服饰跟服药有关,因为当时士人流行服用“五石散”,服药之后,皮肉会发热、发红,为防皮肤被衣服擦伤,所以要宽衣博带。[1]190这种着装风格,使得魏晋士人有一种潇洒飘逸之感。陶渊明曾有“舟遥遥以轻扬,风飘飘而吹衣”之句,对魏晋士人的服饰之美作出了形象的描述。而魏晋士人清谈时所持之物——麈尾,更衬托出魏晋士人清新脱俗的气质。
魏晋士人非常看重容貌。《世说新语·惑溺篇》曾记载:“妇人才智不足论,自宜以色为主。”认为评判一个女性的首要标准是外在的容貌,才智是不值一提的。《世说新语·容止篇》记载:“潘岳妙有姿容……少时挟弹出洛阳道,妇人遇者,莫不连手共萦之。”这说明魏晋时期不仅看重女性的容貌,也非常看重男子的容貌。《世说新语·容止篇》又载:“左太冲绝丑,亦复效岳游遨,于是群妪齐共乱唾之,委顿而返。”左太冲的“东施效颦”一方面说明当时对容貌的重视已蔚然成风,另一方面说明魏晋士人已把这种外在的美貌内化为气质,是模仿不出来的。
魏晋士人还非常看重风神气度之美。《世说新语·容止篇》曾记载:嵇康风姿特秀,时人赞之“萧萧肃肃,爽朗清举”;士人夏侯玄“朗朗如日月之入怀”;而李安国则“颓唐如玉山之将崩”;裴令公容貌俊秀如“玉人”;王右军“飘如游云,矫如惊龙;”王恭“濯濯如春月柳”。这些描述皆以“物”喻“人”,将人的风神气度比作松风、日月、美玉、游云、惊龙、春柳等自然事物,这种语言方式看似模糊,实则效果更加逼真传神。由此可见,魏晋士人不仅注重服饰、容貌之美,还将其进一步内化为一种清新俊朗的风神气度之美。
总之,魏晋士人通过对服饰、容貌以及风神气度的关注所呈现出的潇洒飘逸之美,是其内在审美理想的外在显现,也是其人格特质的重要内容。这说明魏晋士人已把审美的目光转向了人自身,向内发现了审美的自我,发现了审美的人生。
二、自然率真的情感追求
人性,顾名思义,是指只有人才具备的特性,该特性为人所独有,可以区别于人与其他事物,包括动物、植物。人格的形成是以人性为基础,人格是特殊的人性,可以看作人与人之间最显著的精神区别。魏晋以前,士人人格意识的确立囿于伦理道德的范围之内,自晋人起,士人把目光转向了伦理道德之外,逐渐展开对自然的生命状态和率真情感的追求,呈现出一种前所未有的自然率真的人性之美。
“竹林七贤”中的阮籍颇具代表性。关于阮籍,《晋书·阮籍传》曾这样概括:“其外坦荡而内淳至”,此处的“坦荡”指的是其外在行为的放诞。“淳至”指的是其内心的自然率真。《世说新语·任诞篇》详细记录了他的“坦荡”行为,如居丧饮酒、青白眼的故事、哭邻家处子、醉卧美人侧等。这些放诞的行为背后,其实隐藏着阮籍对扼杀人性的礼教的痛恨、对生命的惋惜以及内心的自然率真。
嵇康自幼博览群书,诗风高雅脱俗,既是一位天才式的人物,也是“竹林七贤”的精神领袖,文学、玄学、音乐等无不博通,故在当时文坛上有着很高的声誉和地位,是当权者最想拉拢的对象。刘勰的《文心雕龙》曾这样评价嵇康的为人:“惟嵇志清峻。”在“竹林七贤”中,嵇康是一性情耿介之人,“刚肠疾恶,轻肆直言,遇事便发”(《与山巨源绝交书》)。他既不会如阮籍那般徘徊于入世与出世之间,苟全性命于乱世;更不会如山涛、向秀、王戎等那样晚节不保、走向仕途。面对当权者司马氏的诟陷,嵇康以宁折不弯、宁死不屈的态度对抗,最终慷慨赴死。鲁迅曾评价说,嵇康之耿介断送了他的性命。有些人和事,看不惯就要说出来,不管当权者高不高兴;说出来了,也绝无悔意,大不了以死抵之。嵇康之耿介是造成他人生悲剧的根本原因,但同时也彰显了他自然率真的人格魅力。
学者李泽厚曾高度评价阮籍和陶渊明,认为他们二人分别创造了两种迥然不同的艺术境界:阮籍忧愤无端、慷慨任气;陶渊明则是超然事外,平和冲淡。罗宗强曾评价说,与“竹林七贤”相比,陶渊明“心中纠结着一个未能免俗的情结”。[4]348恰恰因为这个情结,陶渊明的心态才更趋平和。以“竹林七贤”为代表的魏晋玄学家理想的人生是过一种庄子式的“逍遥”生活,他们从一开始就把自己摆在世俗生活的对立面,因而只能停留在理想阶段,难以实践。而陶渊明却能在俗世中找到他人格独立和精神自由的栖息之地,以远离朝堂、回归田园的方式求得自我与群体的两安状态。陶渊明也曾有过孤独,但他的孤独主要是为俗世所困而引起的失群感,一但弃官场而归田园,这种心情便会大大地改变。因而,陶渊明形成了一种冲淡自然的人格特质。
总之,魏晋士人各具特色的人格魅力是魏晋“人的觉醒”最有力的证明。阮籍的坦荡与淳至、嵇康的耿介与坚定、陶渊明的平和与冲淡等品性,充分展示了魏晋士人自然率真的人性之美。
三、浓郁悲凉的生命意识
自古以来,生与死的矛盾一直是人类所要面对的首要问题。孔子曾发出这样的感慨:“未知生,焉知死”;“朝闻道,夕死可矣”;“善死守道”。在孔子看来,社会的道德仁义比个体生命更重要,现世生活远比死亡更重要,因而对于“死”是存而不论的态度。相比之下,庄子对死亡更为重视,他曾说:“死生亦大矣”;“生死存亡之一体”;“死亡,命也”。他认为自然天命是生死的本体,主张让个体的人在自然状态中听从天命,这样就取消了生死差别。可见,先秦时期的先人们对待生死的认识尚且处于混沌的初级阶段。
东汉末年,士人所依附的政权和道德规范走向崩溃,个体的“生与死”问题引起了士人的普遍关注。这种转变始自《古诗十九首》。“人生忽如寄,寿无金石固”;“人生寄一世,奄乎若飘尘”;“生年不满百,常怀千岁忧”;“人生非金石,岂能长寿考”。这些诗句表现了人生的无常以及生命的短暂,借此传达出一种对生的眷恋及对死的恐惧之情,是《古诗十九首》浓郁悲凉的生命意识的充分体现。
魏晋士人对生命的思考,主要体现在诗歌作品中。对于生命短促的感叹,是贯穿于魏晋诗歌的一大主题。孔融曾给曹操写信举荐人才,一开篇即感叹时光飞逝:“岁月不居,时节如流,五十之年,忽焉已至。”“月明星稀,乌鹊南飞,绕树三匝,何枝可依”。这首《短歌行》真实地表现了曹操对时光一去不返的茫然与悲凉之感。曹丕也曾感叹“年寿有时而尽,荣乐止乎其身”。与荣华富贵一样,时间是非常有限的,当意识到这个问题的时候,以“生与死”为核心的生命意识就产生了。
在《咏怀诗》中,阮籍这样总结自己的生命状态:“终身履薄冰,谁知我心焦。”在当时黑暗的政治斗争中,阮籍不愿向当权者妥协,去做一颗任人摆布的棋子,因而每天都活得战战兢兢;另一方面,他又要于茫然中追求那虚无飘渺的人格理想,世人的眼光和耻笑不足为惧,但是自己的安身之处又在哪里?这一切都化作了焦虑、孤独与茫然融入了阮籍的诗歌。当人被一种巨大的孤独包围时,可能会对自己甚至周围所有的一切产生质疑,个性率真的阮籍甚至流露出对友情和亲情的不信任。阮籍通过诗歌所表露的情绪与他在《大人先生传》中的自由心境相比,真有天壤之别。这种鲜明的对比更加衬托出阮籍的孤独与焦虑。阮籍这种对自己内心世界的坦露,既是一种自我关怀意识,同时也是一种生命意识的体现。
魏晋士人的生命意识是以个体的生命为本体,包含对时间逝去的不舍、生命短促的感叹、对死亡的恐惧以及对生的焦虑,这一切都是建立在魏晋时期“人的觉醒”的基础上。这种浓郁悲凉的生命意识既是魏晋士人人格理想与生存困境的矛盾显现,又是对儒家、道家生死观的超越与深化。
四、自由逍遥的人生理想
在人生理想方面,魏晋人士同样有自己独到的见解。曹植塑造的理想人格是“玄灵先生”。曹植在《释愁文》中说“辞赋小道,固未足以揄扬大义”。在曹植看来,排在他人生第一位的是建功立业;又说“若吾志不果,吾道不行,则将……成一家之言”。如果仕途不畅,再去从事创作、著书立说,将“立言”置于“立功”之后。不幸的是,曹植在建功立业的道路上屡屡受挫,于是作《释愁文》,借“玄灵先生”之口,为诗人开出释愁良方,借以宣扬道家的“无为”和“淡薄”思想。“玄灵先生”,其实只是诗人虚构出来的人物,却寄托了曹植向往自由的人生理想。
在《达庄论》和《大人先生传》两篇文章中,阮籍塑造了他“至人”“大人先生”式的理想人格。这种理想人格是阮籍所崇尚的自由的人格,其实质是超越个人、社会与时空等一切要素,从而达到一种绝对自由。然而,这种理想人格是很难在现实中存活的。在中国古代文化中,文人的人生选择主要有两种,一是“入世”,一是“出世”。阮籍在《大人先生传》中所塑造的“士君子”和“隐士”的形象分别代表了这两种人生选择。“士君子”认为自己最重要的品质是拥有“古今不易之美行”,这种“美行”是指道德修养,其存在的价值主要依附于礼法名教,是大部分人都会做的一种选择。按照家庭出身和自身所受的教育,阮籍也应该做一个“士君子”。但自我意识的觉醒,使得阮籍认识到士君子所尊崇的礼法名教束缚其实扼杀了人性之美,在旧有的秩序下追求自由是不可能实现的。因而,阮籍首先否定的是这种“士君子”的人格。而所谓的“隐士”看似远离朝堂、超凡脱俗,但仍“恶彼而好我,自是而非人”,难以超越个人的是非与功利,阮籍也否定了这一人格。在《大人先生传》中,还有一种“薪者”的“圣人无怀”思想。所谓的“圣人无怀”主张人要在精神上超越物质层面的束缚,包括生死、富贵贫贱、个人名利等,只有做到了这一点,才能达到超越个人和社会的状态,即一种“无怀”的自由状态。但阮籍认为这种“圣人无怀”思想还有不足,他的最终的理想人格是“大人先生”式人格。所谓“大人先生”式人格不仅要做到“圣人无怀”,还要做到“虑周流于无外”,即超越时空的限制。很显然,这种崇尚绝对自由的理想人格仅是一种不切实际的空想。但在一定程度上,阮籍的这种空想拓宽了自己的精神空间,开启了一种审美的人生。
在魏晋时代,玄学家于现实世界中受挫,转而向彼岸世界追寻自由,最终沉溺于空想。于现实与理想之间,魏晋士人痛苦忍受双重的失落。东晋的陶渊明却在“士君子”与“隐士”之外,塑造了理想的“五柳先生”,找到了一种充满自由与快乐的“田园”生活。在《五柳先生传》中,陶渊明这样描述他的田园生活:“闲静少言,不慕荣利。好读书,不求甚解。”“造饮辄尽,期在必醉”。读书、作诗、饮酒成为其生活中的主要娱乐方式。“环诸萧然,不蔽风日”,虽然日子苦了点,但精神的舒畅和愉悦是庙堂之上所不曾拥有的。可见,陶渊明在清苦的田园生活之中找到了栖身之所。陶渊明虽然也在诗歌中表达了顺应自然的道家思想,但他却未停留在精神世界逍遥上。正如李泽厚所说,陶渊明“无论人生感叹或政治忧伤,都在对自然和对农民生活质朴的爱恋中得到了安息”。[2]108
不论是曹植的“玄灵先生”、阮籍的“至人”或“大人先生”,还是陶渊明的“五柳先生”,这些都是魏晋士人对自己理想人格的一种设想。在《论〈世说新语〉和晋人的美》一文中,宗白华认为“晋人之美,美在神韵”。[5]217这种自由逍遥的人生理想,充分体现了魏晋士人的神韵之美。
五、结语
综上所述,魏晋士人的人格意识中,潇洒飘逸的姿容气度、率真自然的情感追求、浓郁悲凉的生命意识以及自由逍遥的人生理想等特质成为士人人格塑造的主要内容。以上人格特质可谓“名士风流”由外到内最好的呈现。不仅如此,魏晋士人的人格特质对后世文人人格的建构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比如曹植。作为一个诗人,曹植以一种高度的热情执着追求人生价值的实现。他的诗歌中充满了对生命意识的探索,有人性的觉醒、心灵的感悟,也有作为前驱者巨大的孤独和焦虑。作为一个士族后裔,深受传统文化和家世背景的影响,曹植有着强烈的社会参与意识,希望将自己人生价值的实现与国家的命运融合在一起,对社会变革和政治体制也有自己独到的见解。闻一多先生说过,“陈子昂的宇宙意识来自正始,社会意识来自建安”。曹植以自己的人格魅力为后世的知识分子遗留了勇于担当、努力实现自我价值等优良品质。
比如阮籍。“竹林七贤”中的士族文人因为相同的志趣爱好而相互吸引,但面对政治强权,最终做出了不同的选择。向秀、山涛和王戎,最终向当权者妥协,出来做官以求得安身立命之所;嵇康则宁死不屈,拒绝与当权者合作,最终被司马氏所害;阮籍所采取的态度是既不向政权靠拢,也不公开抗争,而是以游离的方式徘徊于官场与世俗之间。阮籍的这种自觉远离政治、寻求精神解脱的处世态度,徘徊于入世与出世之间、审时度势、伺机而动的生存法则为后人所继承和实践。中国知识分子双重人格的典型当属阮籍,对后世影响极大。
再如陶渊明。陶渊明留给后人的除了诗歌,还有他“不为五斗米折腰”的高洁品格。早期也有济世之志的陶渊明,因厌倦官场的黑暗与虚伪,愤而辞官,归隐田园。在腐败的官场与难以实践的人格理想之间,陶渊明的田园生活将后世文人的人格理想落到了实处。后代知识分子大多采用实用的态度、根据自己的生存需要来学习陶渊明。建功立业仍是知识分子实现人生价值的首选途径,一旦陷入困境,往往会产生一种怀才不遇的失落感。退而求其次的田园生活会成为文人偏安一隅的精神家园。因而,知识分子一方面会保持一颗赤子之心,嫉恶如仇,但也不可能成为制度和罪恶的终结者,其人生选择的局限性早在形成的初期就已经显露端倪。
[1]鲁迅.魏晋风度及其他[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
[2]李泽厚.美的历程·美学三书[M].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1999.
[3]袁行霈.陶渊明研究[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
[4]罗宗强.玄学与魏晋士人心态[M].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1.
[5]宗白华.美学散步[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
B83
A
1672-0040(2015)06-0045-04
2015-01-10
岳庆云,女,山东高密人,山东理工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讲师,文学硕士。
(责任编辑 杨 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