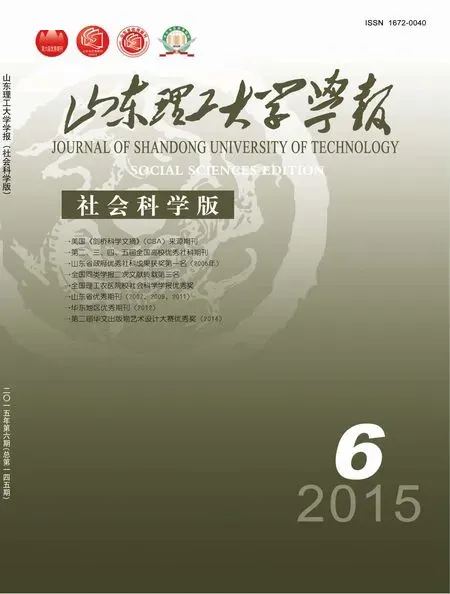顾炎武学术道德思想与实践——兼论对研究生学术道德教育的启示
杨 虎
(北京大学 继续教育学院,北京 100080)
顾炎武学术道德思想与实践
——兼论对研究生学术道德教育的启示
杨 虎
(北京大学 继续教育学院,北京 100080)
顾炎武是中国传统学者的优秀代表,其以“博学为文,行己有耻”为治学宗旨,身体力行了做学问及学术道德思想的四个理念:明道救世,勇担社会责任;采铜于山,撰写传世名著;独立磊落,保持耿介之气;自主创新,坚持实事求是。其理念对当今教育,尤其是研究生学术道德教育的启示包含三个方面:管理部门扩充学术道德教育资源,借鉴前人优良治学传统;导师言传身教,重视学术道德,承担“律人”的作用;研究生养成阅读优秀著作或学术传记的良好习惯。
顾炎武;学术道德;研究生教育
顾炎武(1613-1682),学术界尊称为亭林先生,是我国明末清初著名思想家、史学家、语言学家,他是一位百科全书式的著名学者,被后人誉为“清代开国儒宗”和“一代儒林之冠”。作为中国学术史上承先启后、继往开来的伟大宗师,[1]他对学术道德问题有高度的自觉意识,不仅从理论上系统地论述了学术道德规范问题,并且以自身的治学经历践行了学术道德规范,其严谨的治学风格,为后人树立了楷模。对学者如何治学与为人,有积极的借鉴和警醒作用。高校的研究生学术道德教育,也应充分研究和利用其学术道德规范及思想,为我们高校的教育和治学水平的提高提供借鉴。
一、顾炎武学术道德思想内涵
(一)博学于文,行己有耻
顾炎武毕生信奉并坚持的圣人之道和治学宗旨,可概括为八个字“博学于文、行己有耻”。“博学于文”,是对学者学问方面的要求,即通过读万卷书、行万里路,达到一个博通众家、守正出新的大家气象,最终实现“通经致用”的目标。这里所说的“文”,既有书本知识,也有实践内容,包含甚广,即“自一身以至于天下国家,皆学之事”,[2]41要想精通,殊非易事。因此,在顾炎武看来,治学之路,永无止境:“盖天下之理无穷,而君子之志于道也,不成章不达。故昔日之得,不足以为矜;后日之成,不容以自限。”[2]27具体到他的著述活动,终其一生,都是处在“正在进行”的状态中,而从未有“彻底完成”时,真正做到了“君子之学,死而后已”。[2]92“行己有耻”,是在学者道德品行方面的要求,“自子臣弟友以至出入、往来、辞受、取与之间,皆有耻之事”,[2]41这就要求学者做一个心存耻辱之戒,都能守住道德底线的“有耻之人”。顾炎武认为,古人所强调的“礼义廉耻”中,“耻”是最重要的标准,因为“人之不廉而至于悖礼犯义,其原皆生于无耻也”。而作为“四民之首”的文人士大夫,更应该在这一方面起到良好的表率作用,所谓“士大夫之无耻,是谓国耻”。[3]772“士而不先言耻,则为无本之人”。[2]41
在顾炎武的治学实践中,“博学为文”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明道救世,勇担社会责任;采铜于山,撰写传世名著。“行己有耻”突出反映在两方面:独立磊落,保持耿介之气;自主创新,坚持实事求是。对于今天的学者而言,“博学为文”和“行己有耻”这两方面的要求也是密不可分的。如果没有基本的道德底线,只是把学问作为追名逐利的“敲门砖”,就可能无所不用其极,而不可能静下身心,坐冷板凳,去从事“博学于文”的苦差事。正如梁启超所言,学者“人格不立,便讲一切学问都成废话”。[4]70所以“博学于文”的前提,一定是“行己有耻”。同时,只有博览诗书,知行合一,以经典著述涵养气质修为,以圣贤之训砥砺德行,才能不断增强“行己有耻”的自觉性和自律性。今天学界的很多失德失范行为,究其根源,就在于违者缺乏“行己有耻”的自律意识和习惯。要净化学术环境,提倡学术道德,都可落实到学者的“行己有耻”上。
(二)明道救世,勇担社会责任
情关社稷苍生,勇担社会责任,是中国知识分子的优良传统,也是学者践行学术道德的第一要义,顾炎武就是这方面的杰出代表。顾炎武身处明清易代之时,目睹了世道衰败、朝代更替的变局,从年轻时即“感四国之多虞,耻经生之寡术”,[2]131断然弃绝科举事业,专心研讨经世之学。明清易代之际,他积极投身抗清运动。明亡之后,顾炎武怀抱故国之思,以反清复明作为人生使命,平生的学术研究活动,都是围绕这一主题展开的。即使反清复明的政治理想无法实现,仍坚信“立言不为一时”,寄意著述,以待后来“意在拨乱涤污,法古用夏,启多闻于来学,待一治于后王”。[2]139所以他的治学经历与政治活动密不可分,与当时很多学者钻研用心于内的“性命之学”不同,他的著述中体现着强烈的现实关怀和经世致用之意,力图通过“用心于外”的“博学于文”,承担起学者“明道”与“救世”的社会责任。
在顾炎武看来,“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3]757更何况历来以“修齐治平”为使命的文人士大夫?对于孟子提出并为历代读书人奉为处世圭臬的原则“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他提出了不同见解:作为读书人,无论何时何地,不问穷达与否,都要承担起“救民于水火”的社会责任。达而在位时,固然要兼善天下;穷而在野时,也不应消极地独善其身。他说:“今日之民,吾与达而在上者之所共也。救民以事,此达而在上位者之责也。救民以言,此亦穷而在下位者之责也。”[3]1084虽然一生未能进入仕途,是典型的“穷而在下位者”,但顾炎武一直以豪杰自命,以天下为己任:“天生豪杰,必有所任……今日者拯斯人于涂炭,为万世开太平,此吾辈之任也。仁以为己任,死而后已。”[2]48
在此理念下,顾炎武治学首先反对只求名利的学术研究。针对当时学者把著述视为“成名求利”捷径的做法,顾炎武批评说:“凡今之所以为学者,为利而已,科举是也。其进于此,而为文辞著述一切可传之事者,为名而已,有明三百年之文人是也。”[2]166成名求利,当然是愈快捷愈好,学术成果只是获取名利的手段和途径而已,其质量和价值之低可想而知。与此同时,顾炎武还反对空疏清谈,鄙视脱离实际的玄虚研究。针对明末学界普遍存在的“以明心见性之空言,代修己治人之实学”等弊病,他明确提出:“君子之为学也,非利己而已也,有明道淑人之心,有拨乱反正之事,知天下之势何以流极而至于此,则思起而有以救之。”[2]166他评判著述、文章价值的基本标准是:“文须有益于天下”,“文之不可绝于天地者,曰明道也,纪政事也,察民隐也,乐道人之善也。若此者,有益于天下,有益于将来。”[3]1079
在著述实践中,顾炎武以孔子“删述六经”为楷模,提出自己的写作标准:“凡文之不关于六经之指、当世之务者,一切不为。”[2]91比如,他曾言撰写《日知录》三十余卷,分为经术、治道、博闻三大部分,其用意在于期待“有王者起,将以见诸行事,以跻斯世于治古之隆”。[2]98即便是今天看来无关世务的古音学研究,仍然寄寓着他的良苦用心。他认为“读九经自考文始,考文自知音始”,便通过正文字,审音声,明训诂来研究经史,撰写《音学五书》,意在“续三百篇以来久绝之传”,最终实现“通经致用”的宏伟目标。整体来看,其著述多属国家典制,郡邑掌故,天文地理、河漕兵农、风俗世道这些直面现实的“实学”,“所言皆天下大计,卓然名论”。诚如张舜徽所言:“亭林志在经世,于历代典章因革,政教利弊,了如指掌。凡所考证,皆引古以筹今,留意民瘼,不忘当代。”[5]3这与当时知识分子读时文、写八股、闭门格物、袖手谈心性的旨趣和做法,形成了鲜明对比。
(三)采铜于山,撰写传世名著
要通过学术研究实现明道救世的人生目标,就必须要有强烈的精品观念和传世意识,严肃对待著述事业,绝不能率尔操觚,轻言著述。顾炎武心目中的优秀著作,是那些“古人之所未及就,后世之所不可无”的作品,也就是要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开拓新领域,研究新问题,做出对当代和后世均有价值和意义的研究成果。在他心目中,只有司马光、马端临倾注一生精力专心著述《资治通鉴》《文献通考》的做法才值得效法,而今人求多求速以求名求利的著书方式则不值一哂。他甚至认为,一味追求著述数量的做法,必然会导致著作质量的下降:“多必不能工,即工亦不皆有用于世,其不传也宜。”[3]1080
顾炎武在著述实践中,绝不做“一年磨十剑”的“急就章”,而一贯追求“十年磨一剑”的“精品力作”,提出并坚持了“采铜于山”的著述方法:“今人纂辑之书,正如今人之铸钱。古人采铜于山,今人则买旧钱,名之曰废铜,以充铸而已。所铸之钱既已粗恶,而又将古人传世之宝,舂剉碎散,不存于后,岂不两失之乎?”[2]93所谓“铜”是指资料,“采铜于山”是广泛搜集和利用原始的一手资料,进行原创性的研究,提出新知新解。“旧钱”或“废铜”则是指别人用过的二手资料,使用这样的资料,其结果是不知资料的本源,所得结果像废铜铸出的钱那样,质量很差,还会将原始资料曲解散碎,为害甚大。为了做到“采铜于山”,顾炎武在其著述活动中,采取了以下基本方法。
1.“著书不如抄书”的文献资料工作。据潘耒记述,顾炎武“精力绝人,无他嗜好,自少至老,未尝一日废书。出必载书数簏以随,旅店少休,披寻搜讨,常无倦色”。[3]1终生与书为伴,以著述为业,是一名纯粹的“读书种子”。他从小即遵从嗣祖顾绍芾“著书不如抄书”的教诲,养成了抄书不辍的良好习惯。他说自己:“游四方十有八年,未尝干人,有贤主人以书相示者则留,或手钞,或募人钞之。”[2]30抄书,看似笨拙,但其重要作用有二:一是读书学习,便于抄写者记忆,所得学问,更为扎实;二是积累资料,长年累月的抄录,为其著书工作积累大量的文献资料。像《天下郡国利病书》《肈域志》等书,便由长期大量抄辑正史、实录、方志、历代名公文集而成初稿,这显然已经成为一种比较高级的抄书形式。顾炎武的著作均以淹博著称,与其可贵的抄书习惯分不开。
2.“九州历其七,五岳登其四”的实地考察工作。顾炎武特别重视“行万里路”的考察工作。终其一生,不辞艰辛,风雨无阻,足迹伴天下。而且这种实地考查,并非泛泛的游山玩水,走马观花,而是走一路,学一路,问一路,写一路。他说自己:“比二十年间,周游天下,所至名山、巨镇、祠庙、伽蓝之迹,无不寻求,登危峰,探窈壑,扪落石,履荒榛,伐颓垣,畚朽壤,其可读者,必手自抄录,得一文为前人所未见者,辄喜而不寐。”[2]29全祖望记述他出游考察的常态是:“凡先生之游,以二马二骡,载书自随。所至厄塞,即呼老兵退卒,询其曲折;或与平日所闻不合,则即坊肆中发书而对勘之。”[6]146可见出游考察、积累资料、书本与实践比照勘对、挥毫著书已经融为一体,不可分离,这是纯学术性的考察,也是成就大学者,写出优秀著作的坚实保障。《山东考古录》《京东考古录》《营平二州地名记》《昌平山水记》诸书,都是顾炎武通过认真的实地考察,将调查所得资料与书本记载相结合,进行分析研究后而写成的作品。
3.“知我者当为攻瑕指失”的谦虚态度。顾炎武深信“独学而无友,则孤陋而难成”。终其一生,交游甚广,梁启超先生曾列《亭林学友表》收录36位优秀学者,[4]80-84均与顾炎武有论学交游之谊,可谓真正的“以文会友,以友辅仁”。对于知交学友,顾炎武往往看到的是其长处和优点,并努力见贤思齐,没有丝毫的狂妄自大、文人相轻的习气。他每成一书,都会自视欿然,多方求教,虚心听取并采纳别人的批评建议,而不愿听一些夸奖吹捧之辞。他对朋友诚恳地说:“知我者当为攻瑕指失,俾得刊改以遗诸后人,而不当但为称誉之辞也。”[2]190《日知录》被阎若璩驳正若干条,他一见便欣然采纳。《音学五书》也经张弨改正一二百处,对此书的完善帮助很大。
4.“如切如磋,如琢如磨”的精细打磨。顾炎武清楚地认识到任何一本著作都是与今人相处之日短,与后人相处之日长,一旦落笔为文,就应“立千秋以上之人于前,而与之对谈;立千载以下之人于旁,而防其纠摘”。[7]12他针对当代学者“速于成书,躁于求名”的做法,指出“著述之家,最不利乎以未定之书传之后人”,[2]77并在著述活动中,力戒此弊。他每撰一书,绝不急于求成,而是以异常严谨甚至苛刻的态度,反复修改,力争以完美的状态示人。他说自己“自三十以后,读经史,辄有所笔记。岁月既久,渐成卷帙,而不敢录以示人”。语曰:“良工不示人以璞。虑以未成之作,误天下学者。”[3]1853他撰《音学五书》,历时三十余年,“所过山川亭鄣,无日不以自随”,期间五易其稿,手抄三遍。在书版已经刻好即将刷印出版前,还在书版上修改了四次。连他自己也感叹“其著述之难而成之,之不易如此”。[2]26撰写《日知录》时,有朋友问他“又成几卷”,他回答说,这样提问,是“期之以废铜,而某自别来一载,早夜诵读,反复寻究,仅得十余条,然庶几采山之铜也”,[2]93足见其态度之精审。后来,潘耒要求刊刻《日知录》时,他回信拒绝,并说“《日知录》再待十年,如不及年,则以临终绝笔为定,彼时自有受之者,而非可预期也。诗云:‘如切如磋,如琢如磨’,此之谓也。”[2]77真可谓是一息尚存,便打磨不休。如此著书,焉能不成传世名著?
(四)独立磊落,保持耿介之气
顾炎武以“行己有耻”为要求,从伦理学的角度对中国传统知识分子阶层的负面国民性进行了深刻的反思和批判。在他看来,当代知识分子最大的问题就是普遍存在着根深蒂固的“夸毗之性”。所谓“夸毗”,就是巧言令色,善为进退,无骨气,无操守的奴才之性、乡愿之性。夸毗之人,只以名利富贵为念,长袖善舞,明哲保身,毫无原则和气节可言。这样的人如果在位任职,则“常足以遗民忧而召天祸”,[3]162如果从事学术研究,必定会曲学阿世、枉道从人。顾炎武对这一劣根性深恶痛疾,并大力提倡“耿介之性”来予以救治。所谓的耿介之性,就是以不同流俗、特立独行的姿态,努力保持文人士大夫的独立人格和思想。如何保持学者的耿介之性,而不沦为夸毗之人,顾炎武提出应该从三方面着手去做。
1.不趋附权贵。无论何时,总会有些读书人唯以功名利禄为念,甘做权贵的附庸和奴才,“望尘而拜贵人,希旨以投时好”。[3]430在顾炎武看来,这是一种典型的无耻行为,有志之士绝不肯为。他的嗣母在明亡之后,绝食而亡,临终对顾炎武有“无仕异代”之嘱。入清后,顾炎武一直以明末遗民自居,终其一生,从未屈服于清廷的威逼利诱,当有人鉴于他的声望和学问,推荐他出仕清廷,参与《明史》的修纂工作时,他断然拒绝,说“人人可出而炎武必不可出”,“七十老翁何所求?正欠一死!若必相逼,则以身殉之矣”。[2]53保持了读书人出处去就的“大节”,赢得了人们的尊仰。
2.不阉然媚俗。就是绝不作为获取名利而从众之好,自降身份,“自贬其学”的媚俗之举。“‘大匠不为拙工改废绳墨,羿不为拙射变其彀率’,若徇众人之好,而自贬其学,以来天下之人,而广其名誉,则是枉道以从人,而我亦将有所不暇。”[2]47同时不将编辑出版自己的著述作为求名于世的手段,他因此而讽刺有人“欲自刻其文集以求名于世,此如人之失足而坠井也”。[2]96
3.不依傍古人。在顾炎武看来,在治学中一味模仿古人,邯郸学步,不敢或不能“自出己意”,提出自己的见解,形成自己的风格,也是一种缺乏独立思想和人格的表现。学术贵在创新,著作如无新意,只讲依门傍户,就没有存在的价值,他批评说:“近代文章之病,全在摹仿,即使逼肖古人,已非极诣,况遗其神理而得其皮毛者乎……进此而窥著述之林,益难矣。”[3]1097他还直言不讳地批评自己的一位朋友:“君诗之病在于有杜,君文之病在于有韩、欧,有此蹊径于胸中,便终身不脱依傍二字,断不能登峰造极。”[2]95-96
顾炎武提倡并坚持耿介之气,使他成为“风雨如晦”时代的特立独行者,在学术史上留下了伟岸刚健的身影。这一气概也与近代学人大力表彰的“独立精神,自由思想”等观念有异曲同工之处。如无任何独立和自由思想,则学者将无以言学。顾炎武曾对朋友说过:“某虽学问浅陋,而胸中磊磊,绝无阉然媚世之习。”[2]94可谓精确的夫子之道,应该成为今日学人努力遵循的忠言谠论。
(五)自主创新,坚持实事求是
顾炎武认为,《礼记·曲礼》中的“毋剿说,毋雷同”之训,即“取人之说,以为己说”,乃古人立言之本,应该成为今人遵循的基本著述法则。因此他特别强调学术研究原创性,提倡实事求是,征引有据的朴实学风,宁可劳而无获,不可不劳而获,尤其反对剽窃、“乱改古书”和“以文辞欺人”等无耻之举。在他看来,古往今来的剽窃行为可概括为四种。[8]
1.“以他人之书而窃为己作”。这是最严重的剽窃行为,以郭象剽窃向秀的《庄子注》,何法盛剽窃郗绍《晋中兴书》最为著名。而到了明代,这种完全隐去他人姓名,径直剽窃他人成果的情况却非常普遍,顾炎武指出:“若有明一代之人,其所著书,无非窃盗而已。”可悲的是,当代剽窃之人,只有郭象之“薄行”,而无其“俊才”,“不能通作者之义,其盗窃所成之书,必不如元本。”因此,顾炎武将这类剽窃者直斥为“钝贼”。[3]1073
2.“以前人之书改窜而为自作”。这种情况虽有加工改编,但仍有抄袭的成分,以班固据《史记》作《汉书》,宋祁据《旧唐书》修《新唐书》,朱熹据《资治通鉴》成《通鉴纲目》为代表。顾炎武引其嗣祖顾绍芾的话说:“凡作书者,莫病乎其以前人之书改窜而为自作也。班孟坚之改《史记》,必不如《史记》也;宋景文之改《旧唐书》,必不如《旧唐书》也;朱子之改《通鉴》,必不如《通鉴》也。”[2]30
3.“隐没古人名字,将为己说”。以明代弘治以后的经解之书为代表。虽然不是整本或大篇幅地抄袭,但在引用他人的观点时,却往往隐去其姓名,据为己说。针对这种问题,顾炎武提出无论引用何人之言,都应注明其姓名,即便没有具体姓名,也要注明观点的出处何在:“凡述古人之言,必当引其立言之人。古人又述古人之言,则两引之,不可袭以为己说也。诗曰:‘自古在昔,先民有作。’程正叔传《易·未济》‘三阳皆失位’,而曰:‘斯义也,闻之成都隐者。’是则时人之言,而亦不敢没其人,君子之谦也,然后可与进于学。”[3]1162
4.“仅取已成之书抄誊一过而成新书”。在修撰新书时,只是抄录先前之书,拼凑而成,虽然注明出处,但由于是大量抄录,全无裁剪加工创造,类似于今日的“攒书”行为,因而也是一种剽窃行为,其代表是永乐年间官修的《四书五经大全》。顾炎武说:“当日儒臣奉旨修《四书五经大全》,颁餐钱,给笔札,书成之日,赐金迁秩,所费于国家者不知凡几。将谓此书既成,可以章一代教学之功,启百世儒林之绪,而仅取已成之书抄誊一过,上欺朝廷,下诳士子……上下相蒙,以饕禄利,而莫之问也?”由于是官方行为,所以其为害更大,“经学之废,实自此始”。[3]1043官方著述尚且如此,遑论一般学者?所以历来学者言明代学问空疏,实在是渊源有自。
顾炎武发现除剽窃外,在学术研究中还存在着“乱改古书”和“以文辞欺人”的不端行为。所谓乱改古书,是在注解和出版古书时,缺乏“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的谨慎态度,在理应存疑之处,凭主观臆断乱改原文。明代从万历年间以后,此风渐盛。“不知其人,不论其世,而辄改其文”,[3]1077导致“文益晦,义益舛,而传之后日虽有善读者,亦茫然无可寻求矣”,[3]1075谬种流传,贻误后学。所谓以文辞欺人,就是违反“修辞立其诚”的原则,在著述中不能真实客观地陈述事实、表达观点,而是以非为是,以丑为美,混淆是非,以虚言欺世。“末世人情弥巧,文而不惭。固有朝赋《采薇》之篇,而夕赴伪廷之举者。苟以其言取之,则车载鲁连,斗量王蠋矣”。[3]1095等而下之,还有一部分文人主动为奸臣权佞缘饰其奸,助纣为虐。这实际上都是典型的学术造假行为,顾炎武将此类人斥之为“巧言令色”之徒。如汉代梁翼、唐代李林甫、明代魏忠贤这些奸臣,原本都是不学无术之徒,之所以能够为患天下,与一二文人为其摇旗呐喊,文奸饰非,有极大的关系,“是故乱之所由生也,犯上者为之魁,巧言者为之辅”。[3]1092
二、对研究生学术道德教育的启示
顾炎武的优秀学术道德思想和理念是他成为一流学者的重要原因。其对今天学者思考如何治学与为人,有借鉴和警示作用。他指出的学者不讲学术道德规范的问题,直到今天仍未销声匿迹,个别还有愈演愈烈之势。郭清香指出:“百年前之字字句句,尤似针对今日之事事物物。人心之浮躁,‘学者’之无耻,‘时文’之盛行,窃书之猖狂,竟与顾炎武所言丝丝入扣,令人汗颜,叫人警醒。”[9]当然,时过境迁,顾炎武的有些观点和做法在今天的高校治学中未必能够完全适宜,但这并不意味着可以放松学术道德方面的要求。对个人而言,正确的态度应该是,取法乎上,心向往并力行之。对高校的研究生学术道德教育而言,有以下三方面的启示。
第一,对学校教育管理部门而言,应进一步扩充研究生学术道德的教育资源。在开设课程、教材编写时,努力挖掘和充分利用传统教育中的优质资源,在教育理念、内容和方法方面,进行必要的补充和调整。笔者在研究这一问题,从中国知网上查找相关文献时,尚未发现从传统文化和传统学术的角度来探讨研究生学术道德问题的文章。实际上这是对理论研究和实践工作均有参考利用价值的宝山良田。伟大的学者,必须以高尚的道德修养作为支撑。做人、做事、做学问是高度统一的,学术道德失范,归根结底还是人的道德自律出现了问题。中国传统学术所提倡的和强调的正是学者的高度自觉意识和严谨的自律习惯。尤其是像顾炎武等优秀学者,他们“以天下为己任”“知行合一”“重义轻利”“尊德性与道问学并重”,倾注一生心血撰写名著的治学理念和做法尤应值得提倡和发扬光大。如果能够采用适当的方式加以利用,必定对研究生的教育感染力大大增强。梁启超就认为,顾炎武不仅是经师,而且是人师,“他的感染力所以能历久常新者,不徒在其学术之渊粹,而尤在其人格之崇峻”。[4]79-80要在高校中大力弘扬我国优秀传统文化,让师生一起继承中国传统学者的优良治学传统,十分必要,同时也可避免在谈论这一问题时,“言必称希腊”而“不知有魏晋”。
第二,是对于研究生导师而言,首先是通过言传身教,重视和不断加强学术道德理念,在做好自律的基础上,切实承担起“律人”的作用。大学的学科特点、导师风格、研究生个性的差异等,决定了导师育人的方式是多样的。但无论如何,最基本的“以身作则、言传身教”不能忽视。孔子云:“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这一论断,用在导师培养研究生方面十分贴切。在顾炎武的诗文集中,可以看到大量与师友论学明道、相互砥砺的篇章,对其门生弟子甚至后世学者起到了很好的教育作用。今日读来,仍能想见其为人。其次是在教学方式上,除了日常的课堂讲授外,还要特别重视在课堂外的“耳提面命”与“旁敲侧击”,真正让学生感到“从夫子游”的教育感染力。顾炎武论学的很多文章,都是和门生学友的往来书信,篇幅、内容、格式均无一定之规,但其言之谆谆,作为学者的殷切期许,溢于言表。现在的高校,师生之间课堂之外的交流途径更为多样和便捷,可以作到随时沟通教导。行动与否,用心与否,结果却有较大的差异。
第三,对于研究生尤其是人文社科领域的研究生而言,在学习知识技能的同时,应养成阅读本学科领域传统大师的论学著作或学术传记的良好习惯。这不仅能学到治学门径和成功经验,而且能够感受到学者们的高尚品行,激励他们树立严谨的治学态度,立志脱于流俗,把提高学术道德修养作为研究生阶段的一项重要内容,这对他们的长远发展有很大益处。梁启超曾谈自己阅读顾炎武著作的感受说:“他的说话,虽没有什么精微玄妙,但那种独来独往的精神,能令几百年后后生小子如我辈者,尚且‘顽夫廉,懦夫有立志’。”[4]72钱穆也评顾炎武:“其志意之切挚,风格之严峻,使三百年后学者读之,如承面命,何其感人之深耶!”[10]139两位国学大师相近的阅读感悟,对于有志做大学问的人而言,应该是“心有戚戚焉”。
[1]陈祖武.高尚之人格,不朽之学术——纪念顾炎武亭林先生四百年冥诞[J].文史哲,2014,(2).
[2]顾炎武.顾亭林诗文集[M].北京:中华书局,2008.
[3]顾炎武.日知录集释(全校本)[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
[4]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M].北京:东方出版社,1996.
[5]张舜徽.清人笔记条辨[M].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
[6]全祖望.鲒埼亭集(第二册)·亭林先生神道表[M].上海:商务印书馆,1936.
[7]顾炎武.顾炎武全集(第20册)[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
[8]许苏民.“行己有耻”的道德底线与中国伦理学的近代转型——论顾炎武道德伦理思想中的近代性因素[J].吉首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4).
[9]郭清香.博学有耻,求实创新——论顾炎武的学术道德思想[J].求是学刊,2003,(2).
[10]钱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
B249.1
A
1672-0040(2015)06-0080-06
2015-07-10
杨虎,男,陕西大荔人,北京大学研究生院奖助办公室主任,继续教育学院副院长、副书记,助理研究员,文学博士。
(责任编辑 石学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