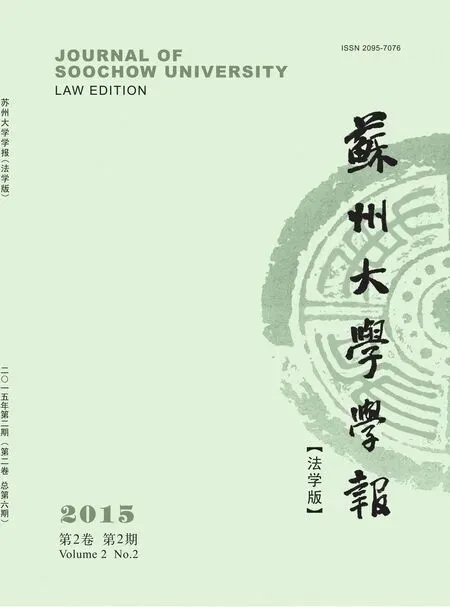罗马法中的“权利”抑或“应得”:拉丁语词 Ius 之含义与汉译问题的文本、逻辑及语言学分析
*上海海事大学法学院教授,法学博士。
内容摘要:以罗马法中的Ius之含义为争议核心的罗马法中是否存在权利概念的问题,肯定说将Ius理解为“权利”,但这一论断无法经受语言学上的反训理论和逻辑学上的类比推理的双重考验。经考证,Ius应为“应得”概念,后世“权利”、“义务”概念均由其下位义发展而来。并且,对原始文献的文本分析和伦理学上的研究亦表明,“应得”概念契合于罗马人的正义理念和务实精神。考虑到我国目前将Ius汉译为“权利”的主流做法有其历史成因,且所谓罗马法中的“权利”之表述已成习惯,就Ius之汉译不妨采取一种介于理想与现实之间的方案,将其在不同语境中所表现出来的含义分别译为“应得”、“权利”和“义务”,同时强调对后两种译法在理解上应当保持清醒的历史意识。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7076(2015)02-0065-20
引 言
长期以来,罗马法中就已存在权利概念的观点,几乎成为我国学界的通说,这不仅体现在普遍使用“权利”来表述罗马法中的各种制度的罗马法教材和论及这些问题的相关论文与著作中,亦不乏学者尝试对于这一观点进行论证。 ①然而,随着人们对权利问题研究的深入,学界针对这一传统观点,也不时地发出了不同的声音。 ②尤其是近年来关于权利概念之形成过程问题的最新研究成果的出现,使罗马法中究竟是否存在权利概念的问题不无疑问。因为学者的研究赫然向我们展示着权利概念正式出现于欧洲中古时代末期的14世纪, ③这自然同时向已经习惯于不假思索地以权利概念描述罗马法的我们发出了一声质问——罗马法中难道真的存在权利概念吗?早在权利概念正式出现之前,罗马法中长期以来被我们称作“权利”的那个东西究为何物?显然,兹事体大,它已然是一个引起了极大争议的问题,也必然是西方法学史研究中的一个难点。然而,这些都不能作为我们对其避而远之的借口。因此,笔者将在本文中基于对学界论争的观察和评价,从一个较“前人之述”来说相对独特而在笔者看来又是极值仰赖的视角,即综合运用文本分析、逻辑分析和语言学分析等方法,来就此论争及其相关问题,向学界提供另外一种思考的路径。
在正式展开对这一问题的讨论之前,笔者拟先将本文的研究范围加以界定:关于罗马法中是否存在权利概念的问题,本文将以对罗马法原始文献中的拉丁语词Ius的分析为中心,并认为这一限定不至于影响论证的周延性。这是因为:第一,现有的西方法史学研究已经充分表明,近现代法中的权利概念直接来自于罗马法中的Ius,申言之,权利是对Ius的主观方面意义的概念表述。迄今为止,关于罗马法中是否存在权利概念所进行的论争,无疑是以Ius作为“主战场”,甚至是唯一的真正意义上的“战场”。 ①第二,罗马法中除了Ius之外,固然还存在其他不少语词也被我们理解为某种“权利”,例如Servitutibus(“地役权”)、Usu fructu(“用益权”)、Usu(“使用权”)、Habitatione(“居住权”)、Actio(“诉权”)等,但是它们都是Ius的种概念,罗马法原始文献多在对它们的描述中以Ius一词加以指称, ②或者直接以Ius作为属概念结合它们各自的种差来进行界定。 ③因此,它们是不是权利,与Ius是不是权利本质上是一个问题,通过对后者的分析即可获得相同的结论。第三,罗马法中除了Ius及其各种种概念之外,固然还有不少语词被我们称作“某某权”者,但是“权”这一汉字,原本也还可以作为“权利”之外的其他语词的简写,如“权力”、“权能”、“权限”等,并且,我国学界亦尚未见较有力度地论证它们与“权利”含义上等同或者它们系“权利”的种概念者。本文既以研究罗马法中是否存在权利概念问题为己任,故对于它们暂且不予涉及。因此,本文旨在通过对拉丁语词Ius的分析来考察罗马法中是否存在权利概念问题。
另外,除了尚有争议的表示“权利”这一含义之外,Ius还有很多其他含义,例如罗斯科·庞德(Roscoe Pound)指出它具有十种含义,其中四种比较接近于我们现代人所理解的“权利”。 ④《牛津拉丁语词典》中所列明的义项更达十三种之多。 ⑤但是,为使笔墨尽可能地集中于本文的研究目的,若非因论证之所需,则对于其中与此议题关系不大或明显与权利概念不相接近的义项,笔者也不将之纳入本文的讨论范围。
一、争议未了:罗马法中是否存在权利概念之论争述评
乍看起来,就罗马法中是否存在权利概念的问题,肯定说和否定说之间似乎难以展开真正的较量。其中的原因,一方面在于前者已然在我国罗马法研究的话语体系中占尽了优势地位,深入人心,另一方面在于就论争的命题本身而言,二者以其各自的攻守之势,其论证逻辑上胜出对方的条件在难易程度上也极不对等,因为从逻辑上说,论证某事物的存在比论证其不存在要简单得多。这似乎是一个大力士和一个幼童之间的竞技,而胜负规则是幼童身中一个白点即输,而大力士则只要未成浑体均白即赢。然而,正如笔者将要展示的,问题并非如人们所想象的那么简单。无论如何,既然论题已经被挑了起来,那么暂且先让我们作壁上观,看看肯定说和否定说各自的招数吧。
(一)肯定说的依据
尽管只需一个例证即可使肯定说“取胜”,我们在此还是试举三例,通过对三个典型的罗马法原始文献片断的分析,充分展示肯定说的论证依据之所在:
(1)然而,为了使遗嘱全面有效,遵守朕上面说明的规则是不够的。而一个有处于权力下的儿
子的人必须注意,要或指定他为继承人、或指名地剥夺其继承权。否则,如果以沉默遗漏他,遗嘱是无效订立的。到这样的程度,即使该儿子在家父生存时死亡,任何人也不能根据该遗嘱成为继承人,因为不消说,遗嘱自始便不成立。但对女儿或其他父系男女卑亲属,古时并不遵守这一规则。如果他们既未被指定为继承人、又未被剥夺其继承权,遗嘱确实并不无效,但他们被授予增加权(ius adcrescendi),直到他们获得一个确定的份额。对这些人,尊亲也不必指名地剥夺其继承权,但他们可用“其他的人”一语集体地剥夺他们的继承权。 ①
(2)用益权(ususfructus)乃在保持物的本质情况下对他人之物使用和收益的权利(ius)。 ②
(3)我们发出警告,或因我们享有某种禁止权(ius prohibendi),比如为了从公开地或秘密地从事某一施工的人那里获得潜在损害担保;或因某一施工被进行将违反为调整建筑而颁布的法律、皇帝的敕令;或因某一施工将在圣地、安魂之地、公共场所或河岸上被进行。在后一种情况下还可以发布令状。 ③
在前引出自优士丁尼(Iustinianus)《法学阶梯》的第一个片断中,作者主要论述了遗嘱中对于两类不同的继承人的沉默遗漏将分别导致的不同法律后果。其中,如果沉默遗漏对象是“处于权力下的儿子”,那么该遗漏将导致“遗嘱自始便不成立”的法律后果;如果沉默遗漏对象是“女儿或其他父系男女卑亲属”,则遗嘱“并不无效”,而是给“他们授予增加权(Ius Adcrescendi)”。在这里,我们的重点不在于关注沉默遗漏两类继承人各自导致的法律后果之差异,而在于分析其中提到的“Ius Adcrescendi”实为何物。其实,优士丁尼紧接着便对之作了解释,即“直到他们获得一个确定的份额”。根据注释,这个“确定的份额”是四分之一,是类推法尔其丢斯法的法定应继份的规定。到优士丁尼时代,这个份额被增加到三分之一。获得这个确定的份额之后,该“Ius Adcrescendi”归于消灭,显然,这非常符合为我们所耳熟能详的权利理论,因为权利包括了以获得某物为其内容的情形,其内容的实现也正是权利消灭的原因之一。再者,所针对的客体是遗产,也不与权利客体理论相违背。可以说,用权利概念来理解这里的Ius,似乎看不出丝毫破绽。
在前引出自保罗(Paulus)的《论维特利(Vitellius)》第3卷的第二个片断中,作者通过使用“Ius”作为属概念,给“Ususfructus”下了一个经典定义。这一定义为优士丁尼《法学阶梯》所全盘接受。 ④在《民法大全》的其他片断中,大量存在着关于“Ususfructus”的规定,包括:针对有体物——有体物消灭,它本身也必然被消灭; ⑤它是从“所有权(Proprietate)”中分离出来的; ⑥其享有者不可使“所有权”的状况恶化,但却可以将其改善, ⑦“所有权”人不得妨碍其行使, ⑧也不得在未经同意的情况下在用益物上设立“役权”,以致影响其行使; ⑨其存在仅限于一定时间之内; ⑩等等。面对这些规定,稍微有些现代民法学基础的人都会联想到一个概念——用益物权。应当说,即便我们不能肯定罗马法中的“Ususfructus”就是现代民法上的用益物权,但是用权利理论来理解它,似乎也是没有问题的。如果此说果真成立,那么它的属概念“Ius”,自然也就应该对应于权利概念了。
在前引出自乌尔比安(Domitius Ulpianus)的《告示评注》第52卷的第三个片断中,作者论述了通过发出警告来禁止一项新施工之进行的各种法律依据,其中提到的第一项依据是享有某种“Ius Prohibendi”。基于这一“Ius Prohibendi”,人们可以做的是:向新施工者发出警告,对方只有在提供了担保之后,才可以进行建筑。 ①而其目的则在于前引片断中提到的防止损害的发生。由此可见,无论是从设立这一制度的目的还是内容及其效力等来考察,“Ius Prohibendi”似乎也都符合作为一项权利的条件,如此一来,这里的“Ius”乃是表示一个权利概念也就毋庸置疑了。
可以说,诸如前引三个片断在权利的意义上使用“Ius”的情形,在《国法大全》中俯拾皆是。由此而形成了罗马法上存在权利概念的观点,且该观点能风行学界,自然不足为奇。那么,另外一些学者又何至于冒着巨大的学术风险来提出这一简直冒学界之大不韪的否定说呢?
(二)否定说的依据
否定说的依据主要在于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从权利概念的形成历史来反推罗马法中不存在权利概念。笔者认为,我们讨论罗马法中是否存在权利概念,亦即讨论罗马法中是否存在一个与近现代法学话语体系中的“权利”内涵一致的概念,即便近现代法学中对“权利”的内涵认识并未获得完全的共识。作为双方进行讨论的平台,这一点是不言自明的,否则任何人都可以以自己对权利概念的独特理解,来涵摄罗马法中的Ius,并得出一个或许是其所希望得到的答案。现在,既然法史学的研究已经证实,近现代法学中的权利概念由于基督教内部对“使徒贫困”问题的讨论而正式出现于14世纪,而且恰恰是在对肯定说所主张是为“权利”的“Ius”改造分离而得的, ②以及直到16世纪方才在雨果·多诺那里“占据私法概念金字塔的顶点”, ③那么,我们便可以毫无障碍地反推出,改造之后所得的“权利”,与改造之前的“Ius”,有着不同的内涵,二者并非同一概念。另外,设若罗马法中既已存在权利概念,通过使用一系列堪成其体系之经络的诸如所谓“所有权(Dominium)”、“地役权(Servitutibus)”、“用益权(Usu fructu)”、“使用权(Usu)”、“居住权(Habitatione)”、“债权(Obligatio)”、“诉权(Actio)”等概念,权利概念赫然早已在盖尤斯和优士丁尼的《法学阶梯》中发挥了体系建构的作用,又何至于还轮得到雨果·多诺来荣膺这顶“以‘权利’建构私法概念金字塔之第一人”加注的桂冠呢?从这一点来看,肯定说的主张将面临有力的挑战。
第二,从法典体系逻辑的视角来反推罗马法中不存在权利概念。“众所周知的私法之人、物、讼三分法似乎由盖尤斯(Gaius)在公元2世纪中叶在他的《法学阶梯》 ④中得到介绍”, ⑤并且在优士丁尼《法学阶梯》之中得到官方采用。而三分法的建立,很大程度上是仰赖于无体物与有体物的划分,换言之,无体物概念起到了体系建构的作用。随着后世权利概念的形成,既已采用权利而又尚未放弃无体物概念来建构体系的《法国民法典》和《奥地利民法典》由于采用双重标准而无可避免地陷入逻辑上的混乱,唯待《德国民法典》摈弃无体物概念而独采权利概念来建构体系,方才避免这一问题的出现。 ⑥而在罗马私法的三分法中,类似于《法国民法典》和《奥地利民法典》的逻辑混乱问题是不存在的,由此可知,其中不存在同时使用无体物和权利概念来建构体系的问题。既然无体物概念存在于罗马法中为学界毫无疑义地承认,那么不存在的就该是权利概念了。
第三,基于对罗马法原始文献的文本分析,可以认为“Ius”并非权利概念。与我国法学界在这一方面甚少作为不同的是,不少西方学者进行了这一工作,我们先来对他们的典型观点加以介绍和评论。
法国学者米歇尔·维莱(Michel Villey)就乌尔比安关于正义的著名定义作了分析:
正义是分给每个人以其ius的稳定而永恒的意志。 ①
对此,维莱指出,罗马法中上述分配给个人的Ius因各人的地位而别,实际上包括了对其有利和不利的Ius,例如“Ius Parricidium(弑亲)”的结果是被塞进一个有蝰蛇的袋子里,然后扔进台伯河,而这里的Ius就不能被理解为是一种权利。 ②
意大利学者皮朗杰罗·卡塔兰诺(Pierangelo Catalano)则围绕罗马法学家马尔西安(Marcianus)的《法学阶梯》中的一个片断展开分析:
有时候我们用ius这个词表示亲属关系,比如说我和某人或他人有血亲关系(ius cognationis)或姻亲关系(ius adfinitatis)。 ③
关于这一片断,卡塔兰诺认为,这里的Ius明显指的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不仅可能包括权利,同时也可能包括对其不利的义务,而肯定说则很可能使人无法理解Ius与处于不利的人之间的关系。 ④
苏州大学王健法学院方新军教授则指出,保罗在其作品《萨宾评注》中关于Ius的含义的另外一个片断,更加直接地体现了罗马人是在客观意义上理解Ius,亦即并非作为一个权利概念来使用它:
Ius有多种说法。一种是人们把任何时候都公正和善良的事物称为ius,比如人们说自然法;另一种说法是指对某个城邦的所有人或多数人有利的事物,如人们讲的市民法。在我们的城邦中,“荣誉法”也不无理由地被称为ius。裁判官是在执掌ius,即使当他做不公正的裁判时人们也这样说。当然这里指的是裁判官应该如何裁决,而不是他已经如何裁决。从另一个意义上讲,ius这个词指执法的地点,其依据来自于人们在执法地所做的事。我们可以用此说法确定这个地点:无论裁判官决定在什么地方执法,只要他们保持自己的权力的尊严并遵守祖先的习俗,这个地点都有理由被称为ius。 ⑤
与前述学者们从一般意义上来分析Ius的含义不同,牛津大学法学院教授约翰·菲尼斯(John Finnis)更侧重于在具体语境中来对Ius作为权利概念提出质疑。他所分析的是盖尤斯《法学阶梯》中论及城市不动产役权的一个片断中的内容:
城市里的不动产的iura就是诸如修一座更高的建筑物的ius,以及阻碍邻居建筑的光线的ius,以及不能修筑建筑物的ius,以免阻挡邻居建筑的光线……。 ⑥
菲尼斯指出,我们显然不能将这里的Ius替换为Right(权利),因为说一项“为免阻挡邻居建筑物的光线而不能修建筑物的权利(right)”是没有意义的。诸如此类表述,还可以见之于D. 8. 2. 2中使用同一个Ius去涵盖“建筑物加高(altius tollendi)”和“限制建筑物加高(non altius tollendi)”等。据此,他进一步发挥,认为在罗马法律思想中,Ius通常是指当事人之间根据法律对正义的分配;以及在那样的分配中某个当事人的角色可能是一种负担,而非利益——更谈不上选择的权力或自由。 ①
在笔者的阅读范围之内,否定罗马法中存在权利概念的西方学者还有阿拉斯代尔·麦金太尔(Alasdair Macintyre)、 ②雅克·盖斯旦(Jacque,Ghestin)与吉勒·古博(Gilles Goubeaux)、 ③阿弗尔特(Affolter)、 ④梅兹格(E Metzger) ⑤、艾伦·沃森(Alan Watson) ⑥等。彼得·斯坦(Peter Stein)显然也意识到了这个问题的存在,尽管他只是表明了一种并非决然明确的态度。 ⑦
(三)对迄今为止的论争之评述
一个巴掌拍不响,既然肯定说长期以来占据着主导地位,对论争的评述得从否定说对肯定说的攻击开始。
笔者认为,基于攻击的角度不同,现有的否定说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不直接针对肯定说以罗马法原始文献中比比皆是适宜于理解为“权利”的Ius作为立论的主要依据,而是从法史学的角度进行迂回攻击,例如方新军教授对权利概念形成的历史的考察;另一类是直接针对罗马法原始文献中的Ius展开分析,从其中大量存在不能被理解为权利概念的Ius的角度进行直接攻击,如维莱、卡塔兰诺、菲尼斯等对罗马法文本的分析。下面笔者对这两类攻击角度略加评述。
首先,基于法史学研究的迂回攻击的确在很大程度上动摇着肯定说,只是由于它在论证方法上以立代破,而不是正面解释罗马法文本中被肯定说理解为“权利”的那些Ius何以不是权利,因此可能被认为不够一针见血,在说服力上会被打上一些折扣。这好似一出“真假美猴王”,双方均使出看家本领力证自己就是真猴王,却谁也未见抛出如来佛祖手中那个能将对方罩出原形的紫金钵盂来。从这个意义上说,肯定说和否定说算是“打了个平手”。
其次,基于罗马法文本分析的直接攻击虽然试图接近对手之锋芒而正面出招,但是实际上还是没有触及其实质,并且由于在论证逻辑上处于绝对劣势,其论证力反而远逊于迂回攻击。比如卡塔兰诺、菲尼斯等,无不致力于论证Ius具有“权利”之外的其他含义,即在很多情形下不能将Ius理解为“权利”。然而,想必肯定说也没有绝对主张Ius只能表示“权利”的意思,例如,似乎从来没有人主张“Corpus Iuris Civilis”应当理解为“国权大全”而不是“国法大全”。因此,这种所谓的直接攻击始终只是表面上的,攻击者只能算是耍了个花枪,偷换了论题。而对于其中的真实论题,即如何解释权利概念在其他众多情形下对Ius含义的“恰当”表达,他们根本没有触及。
总之,笔者通过上述观察与分析发现,在迄今为止关于罗马法中是否存在权利概念的论争中,方新军教授从法史学研究出发所作的迂回论证相当有力地撼动了肯定说的结论,然而囿于这一选定的研究方法的限制,这种论证并非对肯定说的核心论据发起正面攻击,因此使肯定说得以牢牢依靠罗马法原始文献这一“杀手锏”来突出重围,从而最终仍能在整个论争中与否定说维持对峙状态。无疑,这仍然是一个未了的争议。笔者认为,要真正弄清楚罗马法中是否存在权利概念这一问题,就必须直面肯定说的核心论据,以此作为讨论中的焦点问题。因此,笔者接下来所作的讨论,将会基于一种在方法上科学且于双方都“公允”的考虑,把罗马法原始文献中被我们习以为常地称作“权利”的那些Ius也纳入我们的分析视域之中。
二、破肯定说:Ius作为“权利”之困境
既然如前所述,无论是肯定说还是否定说,都没有对罗马法学家保罗所论及的罗马法中的Ius一词具有多种含义的论断提出疑义,那么我们的讨论就不妨从这一共识基础上开始。并且我们在本文伊始就通过对拉丁语词Ius的分析来讨论罗马法中是否存在权利问题的周延性作了肯定性论证,为了避免在论证过程之中主题被偷换,我们可以将之转而表达为:“权利”能否作为具有多种含义的拉丁语词Ius的一个义项?只要“权利”可以作为Ius的义项之一,那么即可说明罗马法中存在权利概念;否则,则意味着罗马法中不存在权利概念。至于Ius在此之外尚且还有其他什么含义,可以在所不问。
(一)语言学分析的导入
涉及对一个语词的义项的考察,这显然已经不是一个单纯的法学论题了。适时地藉助于语言学知识来对它进行分析,或许会让我们对问题的探寻迈入柳暗花明的又一村。既然这里涉及作为一个多义词的Ius的义项问题,我们不妨就从这里入手。
不过,严格说来,“Ius”作为拉丁语中可以同时表示多种含义的语言符号,其各种含义之间的关系状态并非仅有一词多义,而是有两种可能:第一种可能是其中至少有一种含义与其他含义之间不存在任何意义上的关系;第二种可能是其所有含义之间均或多或少地存在意义上的关系。而这种各个含义之间在意义上的关系之存在与否的区别,在语言学上具有重要的科学研究意义。前者被称为“异实同名”,后者才是“一词多义”。 ①例如笔者的姓名是“宋旭明”,但是在另一个地方有人在与笔者姓名不发生任何联系的前提下也取名为“宋旭明”,那么“宋旭明”这个语言符号实际上各有完全不同且互无关联的指代意义,属于异实同名的两个概念。
我们首先就来看看Ius是否存在异实同名现象。确然,在《牛津拉丁语词典》中,Ius以三个词目出现,其中在列入了“权利(Right)”义项的那个词目之外,其他两个Ius分别表示一种汤汁和一个岛屿的名称。 ②根据这两个词义,我们看不出它们之间及它们与列入了“权利”义项的Ius词目之间有何意义上的关联,词典编纂者将它们作为三个不同的词目,正反映了他们也是这么认为的。因此,作为三个独立的词目的Ius之间,乃是异实同名的关系。后两者既然没有显示出在词义上与我们讨论的“权利”有关,自然不在考察之列。那么,“权利”是不是有可能原本应当作为一个与其他含义异实同名的语词单列词目,却被错误地纳入了作为多义词的Ius的一个义项呢?也绝不可能。在此,我们姑且假设Ius真的包含有“权利”义项,那么,从保罗对Ius含义的列举中即可看出,并非只有一个含义与“权利”有关,例如裁判官执掌的Ius常被理解为“权利”,而其执掌Ius的地点,也可因此被称为Ius,这就意味着这两个义项之间存在意义上的联系,故而在关系上不符合异实同名的特征。因此,对于所谓的作为权利概念的Ius与表示其他词义的Ius之间以异实同名的关系存在的可能性是可以排除的。
因此,对于Ius具有多种含义,我们便只能归结为一种一词多义现象。自从“语言学上的哥白尼”索绪尔(Ferdinand de Saussure)在其奠定现代语言学之根基的著名学说中提出了对语言现象的历时语言学研究和共时语言学研究相结合并以后者为重点 ①之后,对于一词多义现象,语言学的研究也是从这两个方面进行的。就对Ius之含义的考察而言,历时语言学研究给我们的第一个启发便是,我们应当考虑这样一种可能,即Ius是在罗马法由其远古时期迈向后古典时期的的历时过程中生成了“权利”的含义。不过,对于这一点,整个法学界尚未见有人提出,人们在讨论Ius的含义时,也都是径直将从远古时期到后古典时期的罗马法中的Ius整体上作为一个讨论对象。既然肯定说和否定说在这一点上获得共识,那么就为我们对罗马法原始文献中的Ius的义项仅作一个共时语言学分析而在论证的周延性上提供了保障。
在这里,我们先提出一条对作为多义词的Ius是否包含“权利”义项的问题作共时语言学分析的整体思路来:如果Ius包含“权利”义项,那么将“权利”作为一个义项来对Ius进行分析时,Ius仍然应当具备其作为多义词的一些特定属性。而一旦我们在罗马法原始文献中发现如果Ius包含“权利”义项将不具备作为多义词的一些特定属性,便可断定Ius不应当包含“权利”义项。因为Ius是否包含“权利”义项在共时语言学上是一个一般性问题,其结论普遍适用于Ius其时在整个拉丁语语言体系中的含义,不存在在罗马法原始文献中之此处是而彼处否的情形。因此,否定说只要能找到一个包含有被肯定说理解为“权利”的Ius的片断,证明该种理解将破坏Ius作为一个多义词的某些属性,那么就能达到证明Ius不能包含“权利”义项的目的。在这里,我们可以发现,通过语言学分析方法的运用,肯定说与否定说双方的“攻守之势异也”,论证逻辑上胜出对方的条件在难易优劣程度上发生了倒向否定说一边的有趣转变。
按照我们设计的分析路径,现在首先假设肯定说举例说明的那些情形下,Ius的确是表示“权利”的含义。我们已经说过,肯定说和否定说是共同基于对现代法中的权利的理解来讨论Ius是否包含“权利”义项这一问题的,现在我们既已假定Ius在某些情形下是作为权利概念,这就意味着这里的Ius的含义必须符合权利概念的判断标准,换言之,我们实际上同时也就假设了这样一个运用三段论原理将双方所理解的权利概念去涵摄这些情形下的Ius的过程为正确。既然如此,否定说自然也可以用现代法中的义务概念去涵摄其他某些情形下的Ius,如果这些情形下的Ius也能符合一个三段论的推理,那么该Ius也应当承认为是义务概念。对于这一点,前文已经提及,西方学者已经作了很多论证,例如“不能修筑一座建筑物的ius”,又如弑亲的Ius。但让笔者觉得可惜的是,他们“刚刚开了头却又煞了尾”。此前,肯定说和否定说都未对对方主张的这种观点提出正面反驳,那么我们就姑且假设它们全都成立,在这个双方都没有异议的基础上将对问题的讨论往前推进。换言之,就是对这种假设做语言学分析,看看上述假设在语言学分析之下是否还能经得起逻辑推理的考验而成为一个得到论证的结论。
(二)语言学分析下的逻辑推理之考验
既然我们已经假设Ius在不同情形下既可能表示“权利”又可能表示“义务”,这就意味着在共时平面上,“权利”和“义务”可以同时作为Ius的两个义项。另外,我们都知道,“权利”和“义务”又是法学中的一对对反概念,无论我们将前者理解为一种选择的自由或者一种利益等,后者都表现为与之相反的一种不能选择的不自由或者一种不利益等,它们在语言学上应当归为一对反义词。现在,它们又同时作为了Ius的义项,这就意味着Ius在共时平面上兼具两个含义相反的义项。这是一词多义中的一种相当特殊的语言现象,属于现代语义学中所称的“反义同词(Enantiosemy)”, ②也属于我国传统训诂学中的“反训”的研究范围。
在西方学界,对反义同词的研究被认为首先出现于阿拉伯语言学家的专论中。卡尔·阿贝尔(Karl Abel)在关于埃及古语的研究中涉及了这一问题,在希伯来,迄今为止仅一些单独的此类词汇在希伯来语文献及其现代注释和期刊中得到了附带性的注意和评论。 ①在希伯来全面而系统地讨论这一有趣问题的,是兰岛博士的《新旧希伯来语中的反义同词》一书。 ②奥地利心理学大师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还从心理学角度对这种语言现象进行研究,著有《原始词汇中的对反意义》一书。 ③在意大利,有莱普希(G Lepschy)的“意大利词汇中的反义同词与反语”成果。 ④在俄语世界,反义同词现象也受到了较为热烈的关注。 ⑤
就我国传统训诂学中的“反训”而言,自东晋郭璞在给《尔雅》作注时提出这一问题以来,有过不少争论,甚至有人认为它子虚乌有。近二十多年来,我国语言学界掀起了一股研究反训问题的热潮,在一些问题上取得了可喜的进展,获得了大致的共识,这或被认为部分是因为引进了“建立在科学研究方法基础之上”的西方语言学理论。其中的一个典型,是北京大学蒋绍愚教授在将历代被纳入反训问题研究范围的各种语义现象梳理为七类,再根据英国语言学家莱昂斯(John Lyons)的语义学所提供的标准,即在共时平面上一词兼具两种相反的含义,将“反训”确定为包含三种类型,这被我国语言学界认为是本阶段反训研究的一个重要的实质性突破。 ⑥笔者下文拟运用蒋绍愚教授的研究成果对此问题进行分析,不仅仅是因为该研究的方法和结论在学界获得相当程度上的肯认,还因为藉此可以避免可能招致的两个批评:第一,笔者不直接采纳否认反训现象存在的观点,以免于被批评为“为了达到证明Ius不可能兼具‘权利’、‘义务’二义这一观点之目的而通过选择语言学界关于反训的立场而避实就虚,从而将问题简单而不负责任地抛给语言学界”;第二,笔者不直接采纳纯粹的我国传统训诂学中对反训问题的各种研究结论而采用蒋绍愚教授运用西方语言学方法得出的结论,以免于被批评为“以原本就属于西方语言的拉丁语词Ius之含义为研究对象,却懵然罔顾乃至蓄意回避西方语言学中足以藉之以解决这一问题的方法和结论”。下面我们结合蒋绍愚教授经研究整理排查之后归纳的三类“确是‘反训’”的语言现象, ⑦对照我们基于前文的假设所推理出来的Ius兼具“权利”、“义务”二义的阶段性结论进行分析。
第一类反训是修辞上的反用。例如“冤家”原指仇人,但也可以指自己的情人。如黄庭坚《昼夜乐》:“其奈冤家无定据,约云朝又还雨暮。”又如“可憎”原指可恨,但也可以表示可爱。如王实甫《西厢记》:“早是那脸儿上扑堆着可憎,那堪那心儿里埋没着聪明。”然而,这些都是作为一种修辞手段的临时反用,限于在某种语境中使用,且义域较窄。而我们讨论的Ius一词是罗马法中的学术概念,其表现出兼具相反的二义,决不可能是一种修辞手段的运用;同时,它被长期广泛地使用于整个罗马法中,也不存在临时反用或义域较窄的问题。显然,Ius不符合这一类反训的情形。
第二类反训是一个词原本就有两种“反向”的意思。例如先秦汉语中的“受”兼有“接受”和“授予”之义。前者如《诗经·大雅·下武》:“于斯万年,受天之佑。”后者如《韩非子·外储说左上》:“因能而受官。”又如“内(纳)”,本为“收入”,又为“交纳”。现代汉语中的“借”,也有“借出”、“借入”二义。在这里,蒋绍愚教授全部围绕着动词举例分析,并且说明它们兼具相反二义的原因有两种。第一种是正如清代文字训诂学家段玉裁所解释的,某些动词在造词之始就是为了整体地表达“甲将某物暂时给乙”的意思,只是当甲乙两方分别从自己的角度来看,由于各自的动作方向不同,该词的词义便发生了分化。“受”、“借”均属此类。第二种是某些动词由使动用法而形成新的反向词义,如“内(纳)”则属此类,很明显,它仍然是从整体角度来描述由两个方面合成的一个动作,只是在二义形成的方式上与第一种不同。笔者认为,如果蒋绍愚教授有意于将该类反训词限于动词,那么作为名词的Ius就明显地可以被排除在外了。即使我们就是否“限于动词”不敢臆断作者原意,我们也可以看出Ius在罗马法原始文献中被分别用来表示“权利”和“义务”时,不具有兼顾双方的整体性。固然,现代法学中总是将“权利”和“义务”相提并论,认为它们是对应共存于双方当事人之间的整体意义上的法律关系之中,但是罗马法原始文献中的“权利”和“义务”并非在这种基于权利义务对应共存的整体意义上使用。例如前文提到的“修筑一座更高建筑物的权利”和“不能修筑一座建筑物的义务”就不是这种关系,它们都是基于一方当事人的立场来各自表达具有“权利”或“义务”的情形。否则,与“修筑一座更高建筑物的权利”对应的“义务”就不是它在该片断中出现的那样,而应当是“不得妨碍对方修筑一座更高建筑物的义务”了。由此可见,Ius也不符合这一类反训的情形。
第三类反训是经由词义的引申而形成反义的情形。前已述及,当代西方认知语义学就经由引申而形成多义词的现象形成了丰富的理论,而就其中经由反义引申形成反义的情形,则在我国反训领域内多有研究。例如“释”兼有“弃去”和“放置”之义。前者如《礼记·礼器》:“释回增美质。”注:“释犹去也。回,邪僻也。”后者如《礼记·文王世子》:“春,官释奠于先师。”注:“释奠,设荐馔酌奠而已。”又如,“扰”兼有“乱”和“驯”之义。前者如《左传·襄公四年》:“德用不扰。”注:“德不乱。”后者如《周礼·太宰》:“以扰万民。”注:“扰,驯也。”至于陶渊明《桃花源记》中的“落英缤纷”由于“落”兼具“落下”和“落成”二义而究竟所指哪端,则更已成为人们常常论及的一个趣谜。训诂学研究表明,这些词兼具相反二义,都是词义引申的结果。对于所例举的这些词的词义引申的过程,蒋绍愚教授对它们进行分析之后划分为三种类型。第一种是两种词义虽然相反却又仍有相同的地方。例如现代汉语中的“放”,既有“放弃”之义,又有“放置”之义,而它们同的地方却在于都有“去放”这个动作。第二种是一个词的本义与其作为“治”的对象之义共用该词。例如段玉裁在《说文》中对“乱”的注解:“烦曰乱,治其烦亦曰乱也。”与此类似的还有“扰”、“衅”等词的正反二义。第三种是一词通过“辽远”而向两个相反的方向延伸出二义。例如“淼”和“渺”写法不同但实同一词,“淼”义为“大水”者,如屈原《哀郢》:“淼南渡之焉如?”“渺”义为“微小”者,如苏轼《赤壁赋》:“渺沧海之一粟。”当然,这些类举不是封闭性的,但是蒋绍愚教授从中得出一个规律,即引申而来的反义与本义之间必须存在一个“中间环节”。以此来判断Ius的两个义项“权利”和“义务”,无论我们假设是由“权利”引申出了“义务”,还是由“义务”引申出了“权利”,它们之间的中间环节何在呢?我们找不到任何可以支撑这一推断的语义学依据,甚至我们找不到任何蛛丝马迹来显示Ius的所谓“权利”和“义务”两个词义不是同时形成而是先后形成的。
这样看来,Ius在词义上就不具有任何一种类型的反训所应当具有的属性了。既然如此,我们就可以断定事先的假设即“权利”和“义务”同为Ius的两个义项是不能成立的。
(三)两点补充性驳证
更有甚者,我们再从以下两个方面进行观察,将会更加确信Ius兼具“权利”和“义务”两个相反的义项这一阶段性结论不能成立。
第一,若以为拉丁语词Ius包含“权利”和“义务”两个义项,恐怕是对罗马法的锻造者罗马法学家们语言能力的低估。“反训”何物?共时平面上一词兼具相反二义,即便依赖语境,也常常会造成意义含混,对于语言交际功能是有消极作用的,“落英缤纷”便是一例。因此,反训一般是不能长久存在的,在语言中总要用种种手段把它们区分开来,例如现代汉语中发展出“借给”一词,以试图替代“借”的一个词义。 ①反训词在文学描写、生活交际之中尚且获此等评价和命运,那么Ius作为一个罗马法中被广泛使用的法学概念,其严谨性不曾亦不容为肯定说或否定说一方所肆意否定,若果真为“反训”,又何至于未因在使用中造成混乱而招致指责呢?更何况,前文例举的多种反训现象都还只是基于语言学上的共时存在,并不一定刻意要求存在于同一本书中,这就已然为它们基于各自的语境使词义得到确定提供了条件,而Ius的所谓“权利”、“义务”二义,不但出现在同一本书中,甚至出现在同一个片断、同一个句子中,如菲尼斯分析过的Gai. 2. 14,这就使人们通过语境来区分词义更加受到限制。试想,长期浸淫于古希腊以语言修辞学为重要内容的优秀哲学思想,并在此基础之上经由西塞罗的“搬运”和“罗马化”而最终拥有了成熟的罗马法技术, ②加之手中还握着以“词义清晰、语法严谨”著称的拉丁语,即便Ius作为一个普通词汇真的兼有正反二义,罗马法学家们会将它们原封不动地直接搬入以“法理精深、内容丰富、措辞确切、严谨、简明和结论清晰、语言精辟”而著称的罗马法之中吗?
第二,如果Ius兼有“权利”、“义务”二义,且不管这种特殊性何以容易引起人们的注意,单论二者在罗马法中得到高频率地使用,却不被罗马法学家保罗在前引对Ius的诸种含义的解释中提到,就足以构成怪事一桩。诚然,在保罗没有宣称其列举具有周延性的前提下,我们不能求全责备地认为他已经穷尽了Ius的所有义项,但是在其他罗马法学家们对Ius含义加以描述的为数有限的片断中,例如在前文所引马尔西安在其《法学阶梯》中论及这一问题的片断中,“权利”和“义务”仍然付诸阙如。或许有人要说,保罗谈到的“裁判官执掌的ius”就是指“权利”,那么我们要问,裁判官执掌的只有“权利”吗?“弑亲的ius”、“不能修筑建筑物的ius”何尝不是由裁判官执掌呢?手心手背都是肉,如果这里的Ius真的是指“权利”,保罗有什么理由对于“权利”和“义务”如此“厚此薄彼”呢?
就罗马法中是否存在权利概念之争而言,笔者认为,否定说论及至此,原本可以算是完成了论证。但是人们或许要说:破论容易立论难,Ius既然不是“权利”,那它究竟是什么?还有什么概念能比“权利”让我们更好地理解罗马法中Ius在该种语境之中的含义呢?看来即便仅仅是为了对自己所持否定说加以巩固,笔者也有必要考虑如何面对这一追问,因此下文将转入对笔者观点的进一步阐述,来正面说说Ius究竟为何物。
三、立应得说:Ius作为“应得”之证成
其实,在前文的分析过程中,我们应该已经可以感觉到Ius的庐山真面目在隐约之间有迹可循了。至少有一点应当肯定,它长期以来被理解为权利概念,必然还是因为与“权利”有几分形似。另外我们也应当承认,它与义务之间其实也存在着类似于和权利之间的“形似”关系,因为正如前文述及的众多西方法学家所指出的那样,它在很多情形下所表达的内容正类似于我们今天的义务概念之所指。只是这样出现的频率远较权利概念为少,因此倒还不至于被人们拉去做一回假猴王。这就给我们提供了一条破解的思路——权利与义务这一对对反概念的差别在人们看来如此之大,一个什么样的概念才可能会同时与它们都有这种“形似”的关系呢?我们就从这里入手,顺藤摸瓜,来对Ius之真面目一探究竟。
(一)Ius与“权利”、“义务”构成非严格意义上的“属种关系”
很明显,Ius与“权利”和“义务”都具有“形似”关系,必然是一个兼具权利、义务两个概念之共同属性的概念。而当我们想要寻找两个概念之间的共同属性时,办法无非就是各自朝着自己上位概念的方向去寻找二者共同的属概念,这有点类似于两个人寻找他们共同的尊亲属。既然Ius又兼具二者的共同属性,那么答案已经很明显了,逻辑学告诉我们,它就是权利和义务的属概念。当然,这里必须说明的是,所谓的属种关系,原本用来描述的是两个在共时平面上共存的概念之间的关系。前文我们既然已经证明了罗马法中不存在权利概念,那么严格说来这一“属种关系”在罗马法中是不存在的,只是为了行文方便,暂时借用这一表达来加以描述。
这种存在于历时平面的“属种关系”,与反训现象之间具有很大的相似性,这也是人们将Ius误解为包含“权利”义项的重要原因。蒋绍愚教授对于它们与反训之间的区别作了分析,对其加以了解,将于我们理解Ius不应当属于反训而是属于“属种关系”极有助益。
蒋绍愚教授以“臭”为例来说明这种现象。先秦时期,“臭”为一切气味的统称,它包括香气、臭气等下位义。在不同的语境中,“臭”或是统指气味,或是以它的下位义出现。一个词在不同语境中显示出下位义是很正常的,例如现代汉语中说到“养鸡”,包括公鸡和母鸡。但是“半夜鸡叫”中的“鸡”就只能是公鸡,而“鸡下蛋”中的“鸡”就只能是母鸡。但是我们决不能说“鸡”有“公鸡”和“母鸡”两个词义。“臭”与此同。 ①由此可见,语言学是将词义和下位义作了区分的,一个词在特殊语境中显示出来的下位义与其本身具有的词义是两回事。笔者认为,表示的意义越抽象的词,其所适用的语境就越多,而可能显示出的下位义就越多,例如“为”、“做”、“干”等简直可以称作“万用动词”,它们在不同语境中显现出来的下位义几乎是不可胜数的,但是我们决不可能说它的词义多得不可胜数。
不过,与“鸡”、“为”等不同的是,“臭”的词义在历时平面上发生了变化,即由上古的统指气味发展到后来的仅指臭气,换言之,原来是“臭”在特定语境中显示出来的下位义“臭气”,到后来成了“臭”的固定词义。当人们习惯了这一点以后,再回过头去看上古“其臭如兰”这样的例子,就会认为这里所表示的“香气”的意思和当时人们习惯的“臭气”的意义恰恰相反,于是就说是反训了。 ②
关于罗马法中存在权利概念的肯定说主张Ius具有“权利”之义,与对“臭”的误解何其相似!Ius在罗马法中原本是用于统指可以同时涵盖今天我们认为“权利”和“义务”之所指在内的一个概念,它在特定的语境中显示出来的下位义,有时所指的类似于今天我们说的“权利”,有时所指的类似于今天我们说的“义务”。而真正今天我们所用的权利概念,前已论及,基于法史学研究结论,要到14世纪才正式出现。而其出现的方式也与“臭”相当类似,即Ius一词在特定语境中的下位义“权利”被独立出来,成为Ius的一个固定词义。随着拉丁语在中古时代从古代的形式逐渐变成我们今天看到的诸如法语、意大利语、西班牙语等罗曼语形式, ③Ius也被译成近代欧陆语言中的各种形式,如意大利语将之译为“Diritto”, ④意为“权利”,同时也不再在具体语境中形成“义务”的下位义。当人们习惯了用“权利”来理解“Diritto”等词时,再回过头去误认为Ius也具有“权利”的词义,或者误认为Ius兼具有“权利”和“义务”一对相反的词义,也就不足为奇了。
(二)Ius的含义应当是“应得”
Ius与后世的“权利”、“义务”之关系得到明确之后,我们便能免于受到后者干扰地分析其真实含义了。与“臭”类似,Ius在具体语境中不仅可能以其下位义出现,还有可能以其统指义出现。后者无疑就是我们要找的Ius的真实含义了。
最直接而严谨的方法,仍然是到对Ius之含义进行阐述的罗马法原始文献中去寻找,如前所述,直接论及这一问题的主要是保罗和马尔西安的片断。当然,由于Ius本身是个多义词,我们在寻找这一统指意义上,必须首先排除明显并非我们所指的其他词义,例如关于“法”、“执法地点”、“亲属关系”的表述。剩下的那一处表述,可能正是我们前文述及可以统指“权利”和“义务”两个下位义的Ius——“裁判官是在执掌ius,即使当他做不公正的裁判时人们也这么说。”当然,对于这一处表述,黄风教授认为Ius应当理解为“法”,其原因在于裁判官的司法活动是由“法(ius)”所派生的,并且构成其渊源。在拉丁文中,司法被称为Iurisdictio,字面含义是“说法”,因此这里应当指的是裁判官通过其裁判来说法。 ①然而,笔者认为这里的Ius不应当是指“法”。首先,裁判官虽然也有造法能力,但是一旦我们肯定法必须具有普遍适用性,而不是指导某个个案判决的临时规范,那么裁判官造法就并非是直接通过裁判,而是通过裁判官告示。实际上,裁判官的主要职责恰恰不在于造法,而是在于司法。司法自然不在于“说法”,用我们现在的术语来说,它在于说出案件之中的当事人的“权利义务”,而这就是保罗所说的“执掌ius”。其次,保罗明示,即使在裁判官做不公正的裁判时,他仍然被认为是在执掌Ius。这就说明了这种行为不具有普遍适用性,因为对于一个不公正的Ius执掌行为,罗马人是不会让它获得法的普遍效力的,至少不会作出这种明确的表示,这缘于罗马人对法的正义性的追求,对此笔者后文还将论及。再次,片断原文中的“reddere”被译为“执掌”,这可能显得有点抽象,不是很好理解。实际上,该词还有“返还、恢复”的意思,我们也可以理解为裁判官是在恢复类似于当事人的“权利”、“义务”的Ius,然而我们很难理解他是在恢复“法”。
如此一来,基于裁判官的司法职能,我们可以来对Ius在这一语境下的含义作一个推断:裁判官的司法职能与我们现代的法官如此接近,那么他所“执掌”或曰“恢复”的这个Ius,就与我们现代法中的“权利”和“义务”也相当接近了,因为我们所理解的法官的司法职能,就在于基于法律的正当程序,明晰双方当事人之间的实体权利义务关系,而最终使双方当事人各得其所应当得到的东西。而这个其所应当得到的东西,对其中某一方当事人来说表现形式是多样的:它或者可能是一项对其有利的补偿如一项“权利”,或者可能是一项对其不利的惩罚如一项“义务”。而在罗马法中尚不存在权利概念的背景之下,就裁判官“执掌”或曰“恢复”的对象,则并没有作是权利还是义务的区分,而是仅用了一个语词Ius表示,但是其所指代的,无疑也是类似于我们现代法中的“权利”和“义务”的东西,并且既然用一个Ius表示,证明了它的确兼具二者之共性。因此可以断定,该处的Ius,正是我们要讨论的兼具“权利”和“义务”之共性的Ius。从笔者对现代法官司法职能的描述来看,如果我们要对这里的Ius概念的描述中剔除罗马法中所不存在的“权利”,不妨使用“当事人所应当得到的东西”,或者将其简称为“应得”。因为它是对所谓“权利”和“义务”的一个概括表述,而在这里,裁判官所“执掌”的对象也正是仅用一个Ius来表示的。因此可以说,用“应得”来理解这里的Ius,无论是在内容上还是形式上,都是与原文相契合的,可谓“神形兼似”。
带着这一结论,回过头去看罗马法原始文献中对Ius的描述,我们就会有豁然开朗的感觉,伴随着这种感觉而来的,自然是对于笔者这种理解的进一步确信。比如乌尔比安在其《法学阶梯》第一卷中所述:
对于打算学习罗马法的人来说,必须首先了解“ius”的称谓从何而来。它来自于“正义(iustitia)”。实际上(正如杰尔苏所巧妙定义的那样),ius是善良和公正的艺术。 ②
在这里,Ius一般被翻译为法,笔者认为这就使得原文的含义被缩减了。第一,学习罗马法,并非只是指学习“法”本身,还包括学习“法”的适用,也就是在个案中如何去“执掌”或者“恢复”某人的“应得”。第二,无论是“法”,还是“应得”,它在罗马人那里都应当来自于正义。第三,不论是“法”还是“应得”,它们都是“善良和公正的艺术”,可以说,其中一个方面的缺失,都谈不上是真正的“善良和公正的艺术”。在这里,将Ius同时理解为“法”和“应得”,是完全契合原文的。而认为其只能被理解为“法”,则未免显得片面。同时,从这个片断中,我们对于“应得”本身的认识在此也能获得进一步的深化——这里的“应”所体现的应然性依据,应当就在于Ius的词源“正义(Iustitia)”。
在前引乌尔比安对正义的著名定义中,Ius表示“应得”的含义以及它与正义的关系,同时得到了精练的表达。首先,我们利用这一定义中同时出现了“正义”和“Ius”,掉过头来通过正义来理解Ius,那么原话可以转而表述为:“Ius是基于正义这种不懈的、永恒的意志而分给每个人的东西。”既然是“基于正义”,自然理所“应当”;既然是每个人经由“分给”而来的东西,自然是一种“所得”。因此,将Ius理解为“应得”,在这里是恰如其分的。与前一个片断不同的是,这里的Ius显然不能解释为“法”,因为它要和“分给每个人”搭配成句,是具体层面上的,而不是一般层面上的。因此,通过这个片断,我们可以非常确切地肯定,Ius在罗马法中具有“应得”的含义。
实际上,将Ius理解为“应得”而不是“权利”,在我国学界早已有之。例如我国学者张企泰先生在其翻译的《法学总论》中,就将前述乌尔比安对正义的定义译为:“正义是给予每个人他应得的部分的这种坚定而恒久的愿望。” ①在西方法学界,则有前文引述过的菲尼斯的“Ius通常是指当事人之间根据法律对正义的分配”的表达作为佐证。
然而,在我们现代人的观念中,除了抽象的“正义”和具体的“权利”、“义务”,似乎并不存在一个介于二者之间的“应得”概念。那么,对于这个陌生的概念,我们应当如何理解它呢?笔者认为,我们必须要结合罗马人所推崇的正义理念和他们所秉持的务实精神来加以理解。
(三)“应得”彰显着正义理念和务实精神之结合
前已述及,Ius作为“应得”,可以从“应”和“得”两个方面理解,其“应”在于它基于正义,其“得”在于它以一种具体而实在的利益分配为表现形式。
《国法大全》中直接或者间接论及正义与Ius之间的关系的片断很多,前者更是被置于各个部分之首用以开宗明义。这反映了“正义”观念在罗马人心中的崇高地位。我们再去读一读“被誉为罗马法灵魂的三部作品” ②之一的《论法律》,看看西塞罗在其中以那样庞大的篇幅所论述的Iustitia(正义)与Ius的关系, ③便会对于罗马法的这种安排的自然法思想基础有更加深入的理解。不过,笔者不想在这个法学界老生常谈却又浅尝辄止的这一点上花费更多的笔墨。实际上,长期以来法学界限于将Ius理解为所谓的“客观法”和“主观权利”,并且在这两个概念的遮蔽之下将Iustitia与Ius的关系仅仅理解为“正义”与“法”或者与“权利”之间的关系,错过了从“应得”的视角来理解这一关系,也就看不到罗马人是如何通过“应得”这一概念,水乳交融地将源自希腊的抽象的正义理念溶入到他们的细密的法律规定之中去的。甚至由于我们常常不无生硬地拿自己已经用得“顺手”了的权利概念去对Ius削足适履,因而还产生了许多对罗马法从理念到制度的似是而非的观点。而在伦理学界,由于不存在仅将Ius理解为“客观法”和“主观权利”的前见,或者他们根本不曾如法学界这样考虑到了“客观法”和“主观权利”而来研究Ius,基于其特有的学科视角,他们从Iustitia的视角来研究Ius,或者说将对Iustitia和Ius的研究紧密结合,取得了不可忽视的成果,可藉以弥补法学界研究的不足。我们要全面地理解Ius,就必须打开视野,去看看伦理学界对罗马法中的Ius是怎么理解的。
实际上,对于现代法学来说如此陌生的“应得”概念,若要溯及其源头,应当越过古罗马,追到古希腊。廖申白教授认为,希腊神话和史诗是“应得”思想的源泉, ①但正如笔者前文所指出,“应得”乃是“应”与“得”的结合,通过希腊神话和史诗,主要是表现了人们在“应”的层面上的追求与向往,与在实际生活中如何安排各人之“得”,则尚有一定的差距。因此,笔者认为希腊神话和史诗所承载着的更多是“正义”而非“应得”思想。首先将“应”与“得”结合起来,从而将正义概念引入对利益的分配的,是梭伦的改革。公元前6世纪初的雅典人将富人与穷人之间矛盾激烈的雅典委托给首席执政官梭伦。梭伦认为,要做到正义就要在双方之间不偏不倚。在富人这边,他认为贪婪是城邦社会纷争的根源,所以要求富人压制他们的欲望,并采取系列措施促进平民在人身方面的自由和为遭遇不正义而伸冤的机会。但是,他同时拒绝了平民要求析分城邦财产的要求,认为财产属于其所有者,不可以不正义地侵夺,而要靠努力挣得。梭伦说,他要手持坚盾,挺身遮护两方,不让其中任何一方不正义地取胜。并且他还写了很长的诗篇,对他的思想做了很充分的说明。 ②梭伦将正义理念引入对利益的分配,从而形成了“应得”概念,来表示给一个人所应当得到的东西。 ③
然而,柏拉图对“应得”提出了质疑,认为这一概念将使正义不得不同恶联系起来,因为正义的含义中包含了用恶来惩罚一部分人,这就与当时的古希腊人普遍将正义看成一种必定是善的德性相冲突了。柏拉图在其《理想国》第一卷中对这一问题进行了论述。 ④
亚里斯多德则通过引入“守法”和“违法”的概念,来在梭伦的“应得”概念与柏拉图的批评之间进行中和。他指出,在总体上,正义意味着守法,违法便是不正义。梭伦的正义观在于应得的思想表达着正义的积极意义,这种意义应当在同守法这种总体的正义相区别的具体的正义层次上理解。具体的正义在消极方面意味着不要去不义地多得,否则就是伤害他人的利益。当一方的利益违反其意愿而受到了损害时,将不义地多得的人多得的部分归还受损一方这个行为,只是使双方的利益关系恢复到发生前的状态,而不是施加惩罚或以一恶报一恶。因为,这只是将前者不应得的部分收回,这个部分既然是前者不应得的,收回它对那个不义的夺得就算不上伤害或惩罚。 ⑤
斯多亚学派则围绕着它所提出的核心概念“自然”来建构思想体系,而统治宇宙的便是“自然法”,它是理性法。理性作为一种遍及宇宙的万能的力量,是正义的基础。 ⑥斯多亚学派致力于一种世界大同主义的倡导,认为理性要求我们把公共福利、共同的善置于个人利益之上, ⑦这与着眼于个体的“应得”思想明显不同。但是,斯多亚学派的自然法思想被西塞罗吸收了过去,并与“应得”思想结合在了一起。
西塞罗认为自然理性是宇宙的主宰力量,并提出智者的理性是衡量正义与非正义的标准。 ⑧有理性的人的特征是按照理性给予每个人以应得的东西,而这就是正义。 ⑨这样,西塞罗将正义归结为一种形而上的客观力量,并且以此作为标准来确定每个人的“应得”,这就将斯多亚学派和亚里斯多德的主张有机地结合在了一起。西塞罗的“应得”思想为罗马法学家所全盘接受,并且藉由他们所发展出来的足以让他们在此方面“作为希腊人的老师”的罗马法中发挥得淋漓尽致。
四、区别对待:介于理想与现实之间的Ius之汉译问题
对于Ius是“权利”还是“应得”的理解,还必然影响到该词的翻译问题。由于主张罗马法中存在权利概念的肯定说长期以来在我国学界占据着主导地位,对Ius的翻译也深受这一观点的影响,文首提到的现象便说明了这一现实。不过,这一现实的形成并非完全是因为误将“应得”理解为“权利”,其中还另有原因。将这些原因纳入到考察的视野之中,对于我们客观地评价我国学界目前对Ius的翻译现状和合理地提出相应的方案,是很有必要的。
(一)Ius之汉译现状的历史成因
关于Ius的翻译,前文已就其被译为“客观法”和“主观权利”的原因略有涉及。现在我们对此作进一步的深入探讨。笔者认为,我国的法律继受的历史是一个重要原因,对此我们应当给予相当的注意。具体而言,Ius一词目前被汉译为“权利”,首先缘于我国近代以来并非直接以罗马法而是以西方近代民法作为法律继受的对象。
罗马法与近代民法固然一脉相承,但是其间社会发展所导致的差异也是不可抹煞的。拉丁语词Ius,在中古时代以来形成的各罗曼语言和日耳曼语言之中,分别被译为意大利文的Diritto、法文的Droit、德文的Recht等。如果仅仅是这样一个简单的替代也就罢了,问题是在此期间,欧洲的法律概念体系发生了巨变,而这个巨变之所以产生,就在于权利概念的出现。自从有了从主观意志方面得到理解的权利概念,Ius就被解释为兼具客观Ius和主观Ius双重含义。伴随着中古时代以来各罗曼语和日耳曼语对Ius的翻译的展开,Ius兼具的客观和主观双重含义便同时被赋予给了Diritto、Droit、Recht等词。为了在语境不足以对该词的这两种含义进行区分的情况下实现区分,西方学界采用了为该词添加“客观的”、“主观的”等定语的方法。对于其中在客观方面的含义,中古时代以来的西方学界是如同我国学界一样将其理解为“法”,还是如同罗马法学家一样将其理解为“应得”,暂且难以判断,但从笔者接触到的西方学者对于这一问题的表述来看,前者不在少数。比如在已经不像欧陆各国那样使用同一个单词来翻译Ius的双重含义的英语中,我们非常频繁地看到Ius被译为表示“法”的“Law”,却几乎看不到它被译为表示“应得”的“Due”或者“Desert”。看来,我国学界将其汉译为“客观法”,很大程度上也是受传染自近代以来的西方学界。另外,就主观方面的含义而言,将14世纪以后的一些拉丁文献中的Ius以及各种西方法学法律文献中的Diritto、Droit和Recht等本身理解为“权利”这是没有问题的,因为其时权利概念既已产生。但是因此而藉由后面形成的这些罗曼语词和日耳曼语词对罗马法中的Ius的翻译作用而反推后者也就是“权利”,则是对Ius的误解了,对于这一点,前文已经进行了论证,不再赘述。尽管也有西方学者意识到了这一问题,如艾伦·沃森承认将Ius与“权利”作简单的对应是不正确的,但是更多的学者还是直接用“权利”来理解罗马法中的Ius的。 ①由此可见,早在近代西方学者那里,对罗马法中的Ius的理解就开始出现了两个偏差:第一,将Ius在某些情形下表示的含义“应得”理解为“法”;第二,将近代以来形成的“权利”概念等同于罗马法中的Ius在部分情形下的含义。不过,有一点还是值得肯定的,即所谓的双重含义,西方学者是从整体层面上来说的,也就是从共时平面上的词义的角度来说的。至于在具体的语境中,Ius还是要么被理解为“法”,要么被理解为“权利”。
然而,在对Ius的理解问题上,我国学界不仅沿袭了近代以来西方学者的老毛病,而且还因“水土不服”产生了新毛病,它们大都表现在有关的翻译问题上,并通过翻译使得这些新旧毛病交叉感染,越拖越重。
众所周知,近代中国的法律继受,并没有一开始就溯及罗马法,而是直接取材于近代欧陆民法,“法律移植”一词更加形象地描述了这一已遭学者诟病的过程。放在Ius的含义分化史中来看,我国在此法律移植的过程中在将所谓的双重含义加以区分方面走得更远。与欧陆的Diritto、Droit及Recht等词均具有双重含义,且此双重含义常常需要通过加定语方能准确地表示其中之一不同,英语世界为此双重含义各赋予了一个词语加以表示,从而便有了我们常见的Law和Right的明确区分。这一做法为“权利”这一语词作为我们今天所使用的意义上的法学概念在我国的出现奠定了基础,因为它正是在美国传教士丁韪良(William,Aleexander,Parsons,Martiin)于1860年代所从事的维顿(Wheaton)的《万国律例》汉译本中诞生的。 ①因此,欧陆语言中的Diritto、Droit及Recht等在主观方面的含义,就这样通过英语中的“Right”转而被汉译为“权利”;而同时基于对前文提到的西方学者的第一个误解的接受,它们在客观方面的含义,则通过英语中的“Law”,转而被汉译为“法”。无论如何,这一译法使得二者的区分在我们的语言之中更为清晰,也无需再像欧陆语言中那样需要根据语境或者通过加形容词来区分含义了。 ②本来,一个单独的“权利”语词为我们避免将之等同于罗马法中Ius的一种含义创造了机会,但是,由于该词的使用者们如此熟悉它与各欧陆中的Diritto、Droit及Recht等词的源流关系并如此深刻地受到西方学者观点的影响,同时我国学界长期以来又如此满足于采注释法学方法继受近代民法,而在罗马法研究方面相较而言长期落后,因此虽然也有对罗马法中的Ius加以翻译的需要,但是都因没有深究罗马法中的Ius与近代民法中的Diritto、Droit及Recht等词在实质上存在的区别,便最终紧随着近代以来西方学者的步伐,亦步亦趋地将“权利”一词追加给了罗马法中的Ius。这就造就了我国学界对前文提到的西方学者的第二个误解的接受。
至于因“水土不服”产生的新毛病,笔者指的是“法权”一词的译法的产生。我国在1950年代初的马克思主义经典文献的汉译工作中,曾将德文单词Recht译作“法权”。这一译法的原委在于,当时主事的中共中央翻译局对于Recht一词在特定语境下是表示“法”还是表示“权利”吃不准,就生造出看起来兼顾两种词义但实际上词义不明的“法权”一词来加以应付。由于“法权”的这一产生背景,它从来就不具备确定的内涵和外延,不具备作为一个概念所需要的最基本的条件。后来主事者认识到这一译法的错误,于1971年12月12日在《人民日报》上以《“资产阶级法权”应译为“资产阶级权利”》的文告加以更正。 ③然而,近些年来,又有学者重新提出了这个问题。郑永流教授在其“为‘什么’而斗争——《为权利而斗争》译后记”中认为,耶林在《为权利而斗争》一文中明确说明了自己也有意同时在两个意义上使用Recht一词, ④因此他认为在这种语境之中翻译为“法权”是可以的。不过,似乎迄今为止,尚未见有人以“法权”来翻译Ius,否则他至少需要提供类似于郑永流教授所提供的直接证据来证实作者同时在两个意义上对之加以使用的意图,方可免于被批评为“武断”。因为,同时在两个意义上使用一词,往往也是基于一种修辞手法,名曰“双关”。而在一般情况下,多义词亦常常呈现出“单义化”倾向。当然,这只是其一。其二,我们不能将Ius译为“法权”,还因为所谓的“法权”一词仍然是从“法”和“权利”相区分的角度形成的,只是将二者又简单地合并在一起,这就不能正确地体现出罗马法中的Ius当时还并没有独立出在主观方面的含义的事实。当然,这里无疑还涉及一个需要专门讨论的问题,即Ius作为先于权利的概念,虽则不能用“权利”来理解它,但是理解和翻译毕竟不完全是一回事,那么我们究竟能否用“权利”来翻译它呢?笔者将在下文对Ius汉译方案的比较分析中涉及这一问题。
(二)Ius之汉译的各种可能方案及其选择
Ius作为罗马法中的一个专业术语,其翻译无疑也应当遵循一定的术语翻译科学的规则和方法。通常认为,术语翻译的方法包括音译、形译、意译、音意兼译和借用五种,其中的形译明显不适合Ius的翻译问题,而音意、兼译则提出了对于法学研究来说显得比较苛刻的翻译美学上的要求,故而笔者均不作讨论。
我们首先来看借用。所谓借用即直接地部分或全部借用原语来进行翻译。例如将“X- ray”汉译为“X-射线”,将原意为“脱氧核糖核酸”的“DNA”汉译为“DNA”。 ①Ius明显无法采用第一个例子的那种部分借用。至于全部借用,是有条件的,一般用于全部意译相当复杂、至少就专业词汇而言,将其借用原语反而比全部意译更加容易在学界所接受。这一点对于Ius来说是不具备的。尤其在Ius一词兼有多义的现实条件下,基于避免其各种含义之间发生混淆的考虑,笔者更加不赞成采用借用的方案。 ②
在译语中不存在对应词的情况下,对于原语术语也可以采用音译的方法。 ③例如,罗马法中的“mancipatio”被汉译为“曼兮帕蓄”,即采此法。这就向我们提出了一个问题:笔者在文中屡屡用到的“应得”,是否可以算作Ius的对应词。其中的“对应”,笔者当然已经论证过了,现在的问题是,它是已经存在于汉语中的一个“词”吗?固然,“应得”达到了作为“词”的条件,即作为“语言结构中的基本单位,能独立运用,具有声音、意义和语法功能”, ④并且也已经有伦理学界在使用它,但是对于法学界来说,可以说是比较陌生的,更还没有被接受为一个入典术语。正因为如此,可能被用于翻译Ius的这个“应得”,目前处于一个岔道口上:学界接受,它便可以登堂入室,正式成为Ius的对应词而存在;学界不接受,它便会逐渐被淡忘从而不能作为其对应词而存在。在这种情况下,笔者认为不应当光凭有无对应词这一点考虑而断然否定将Ius音译为诸如“优斯”的做法。但是,我们同时也应当看到,纯粹的音译常常失去其意义上的表征,如果原语作品中没有采取一种汉译之后能让人们理解的方式对该被音译词加以解释的话,要使译成的作品能为人们所理解,译者又必然要面临着一个解释的问题。而Ius正是一个这样的概念,保罗和马尔西安在解释Ius的各种用法时,对于其用于指称“应得”含义的Ius,偏偏没有从正面作出解释,而只是说“裁判官是在执掌ius”。因此,音译者必然逃避不了对其进行解释。而在这里音译者要解释的对象,偏偏又是法学界争论极大的问题,在人们普遍已成思维定势地使用“权利”来理解它的现状之下,这种解释也就面临着巨大的阻力,一旦人们的视线从这一解释上移走,毫无表意作用的音译便无法使人们有效地摆脱其思维定势,很可能再次回到用“权利”来理解该音译的状态。另外,音译还有一个不符合学界的使用习惯的问题,尽管这一问题不是对Ius进行音译的方案所独有的。由于存在上述种种弊端,笔者认为对Ius进行音译不能说是一个理想的选择方案。
我们来看意译。它是根据原语词语所反映的概念译成译语的词语。对术语进行意译,是根本大法,因为意译术语概念明确,易懂易记,只要可能,应当尽量采用。不过在命名上,它显然远较借用和音译要难。以义定名时,译名最好考虑命名理据,做到名副其实,名实越切越好,因此一定要弄清原术语的内涵,尤其是当其含有一定的历史文化内涵时。 ①
如果纯粹根据上述意译标准来考虑,基于前文对于“应得”一词分别在“应”和“得”两个方面名实相符的肯定,笔者认为翻译成“应得”是最合适的。同时,它还可以避免上述借用方案和音译方案中存在的所有弊端。然而,毋庸讳言,它也要面临缘于语言使用习惯方面的巨大阻力。这种习惯的阻力包括两方面,一是对新术语的不习惯,二是对旧术语的习惯。前已述及,对于我国法学界来说,“应得”应当算是一个相当陌生的概念,相反,“权利”作为一个概念早已在现代社会深入人心,成了我们文化内涵的一部分,这无疑又从外部增加了“应得”概念被广为接受的阻力。要知道,习惯的力量是大得可怕的,它曾使数部民法典在判例法的强势背景下归于流产,也正使我国学者的诸如改“善意取得”为“诚信取得”、 ②改“法律行为”为“法律交易” ③的呼吁极难奏效!现在,笔者在此对Ius的汉译问题的主张即使得到人们的认同,也无疑同样要面临着与此相似的阻力。译事维艰,诚哉斯言!在这种理想与现实的两难之间,笔者倾向于采取一种相对折衷的办法,即将Ius的理解问题与其翻译问题作一个相对的区分,在Ius表示的是接近于“权利”的含义时,仍然照顾到人们的习惯做法,将其译作“权利”。很明显,这是一个将比音译方案招致更大思维定势风险的做法,是面对着理想与现实之间的差距,不得已而为之的一个选择。因此我们无疑应当对这一做法时刻保持清醒的头脑,始终不要忘记英国罗马法学家弗里茨·舒尔茨(Fritz Schulz)所反复强调过的历史意识, ④绝不可以以我们的权利概念去与Ius等同。如果译者也能如艾伦·沃森那样,在翻译伊始便对Ius被译作“权利”做一个二者不能等同的说明,甚至比他说明得更加明确详细一些,那么对于排除读者的误解,也是大有裨益的。
同时,我们不能忽视了目前还存在着这样一种情形,即Ius在某一语境中的含义明显并不与“权利”接近,但是仍然被译作“权利”。笔者认为,对于这种情形,我们便完全没有理由去照顾人们的使用习惯了,因为此种情形下的习惯所表现出来的远不止是一种理解上的偏离,它甚至会让译文在表意上前后矛盾,甚至可能导致文法不通。例如前述“不能修筑建筑物的权利”就是一个矛盾的表达。因此,笔者主张,在Ius表示的是接近于今天我们所说的“义务”的情形下,我们将它翻译为“义务”,如将该例表达为“不能修筑建筑物的义务”;而在Ius表示的是“权利”和“义务”的“属概念”时,我们还是应当将其译为“应得”,例如将乌尔比安对“正义”的定义译作“正义是分给每个人以其所应得的稳定的、永恒的意志”。
余 论
虽然我们认为罗马法中不存在权利概念,但是不等于我们主张罗马人不存在权利观念和权利意识,尽管他们并不知道这种观念或意识被后人称作“权利”并在法学中被赋予如此崇高的地位。我们知道,概念是反映对象特有属性的思维形式,它的形成,标志着人的认识已经从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认识。 ⑤“权利”尤其是要作为一个法学概念被规定在长期以来被誉为“永恒的理性”的罗马法中,这种理性认识的层次明显还要超过一般生活概念的高度。而所谓的“观念”和“意识”则只要求是一种“思维活动的结果”,只要它是一种“看法” ①或者一种“觉察” ②。可见,观念和意识源于一种比较低级的思维活动,它不像概念一样需要得到明确的界定。在一些具体情形下,罗马人萌生一些在一定程度上类似于后世权利概念之所指的观念或者意识,是完全有可能的。因此,当我们要下一个罗马法中存在权利概念的结论时,我们理所当然地要求该权利概念要经得起作为一个概念应当经得起的逻辑推理的考验。但是,当我们证实了罗马法中并不存在权利概念时,我们却不能想当然地将罗马人当时可能存在的权利观念和权利意识也一同否定了。因为或许就是罗马人思维中的那么一点点权利观念和权利意识的火星,经由基督教作为火种保存和蓄养起来,才在中世纪末期生成了权利概念的火炬,借着文艺复兴运动刮起的个人主义之东风,点燃了近现代民法中权利思想的熊熊圣火,并最终伴随着民法典在世界范围内的传播而燎遍全球。
“Right”or“Due”in Roman Law
——An Analysis on the Text,Logic and Linguistics to the Meanings and Translations of Latin Word“Ius”
Song Xu-ming
Abstract:With regard to the problem of whether there existed the concept “Right” in roman law or not,which makes Ius’s meanings as its focus,the theory of affirmation understands “Ius” as “Right”. While this conclusion can not be verified by either the theory of enantiosemy in linguistics or the analogism in logic. According to these reviews,Ius should has been the concept “Due”,from whose hypogynous meanings having developed the concepts “Right” and “Duty”. Moreover,the text analysis to the source materials and the research of ethnics indicate that the concept “Due” correspond to the Roman belief of justice and spirit of practicality. Considering the historical causes of formation for the mainstream of translating “Ius” into “Right” in our country,and the so- called “Right” in Roman law has been used to using,we can adopt a intervenient translating mode,a mode between the ideal one and practical one. Namely,“Ius” can be respectively translated into “Due”,“Right”and “Duty” according to its lingual circumstance. At the same time,the consciousness of history should be emphasised about the understanding to the translations “Right” and “Duty”.
Keywords:Roman law;right;due;ius
(责任编辑:娄爱华)
参见夏勇:《人权概念起源——权利的历史哲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36- 40页;丛日云:《西方政治文化传统》,大连出版社1996年版,第317- 319页;汪太贤:《西方法治主义的源与流》,法律出版社2001年版,第93- 95页。
参见王涌:《私权的分析与建构》,中国政法大学法学博士论文,1996年;方新军:《盖尤斯无体物概念的建构与分解》,载《法学研究》2006年第4期;李中原:《ius与right的词义变迁——谈两大法系权利概念的历史演进》,载《中外法学》2008年第4期。
参见方新军:《权利概念的历史》,载《法学研究》2007年第4期。
I. 2. 13pr.[古罗马]优士丁尼:《法学阶梯》,徐国栋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89页。
D. 18. 6. 8. 2. 参见[古罗马]优士丁尼:《民法大全·学说汇纂·用益权》,米健译,法律出版社1999年版,第1页。
D. 39. 1. 1. 17.[意]桑德罗·斯奇巴尼选编:《物与物权》,范怀俊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84页。
I. 2. 4pr. 参见[古罗马]优士丁尼:《法学阶梯》,徐国栋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41页。
I. 2. 4pr. 参见[古罗马]优士丁尼:《法学阶梯》,徐国栋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41页。
I. 2. 4. 1. 参见[古罗马]优士丁尼:《法学阶梯》,徐国栋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41页。
D. 7. 1. 13. 4. 参见[古罗马]优士丁尼:《民法大全·学说汇纂·用益权》,米健译,法律出版社1999年版,第15页。
D. 7. 1. 15. 6. 参见[古罗马]优士丁尼:《民法大全·学说汇纂·用益权》,米健译,法律出版社1999年版,第20页。
D. 7. 1. 15. 7.[古罗马]优士丁尼:《民法大全·学说汇纂·用益权》,米健译,法律出版社1999年版,第20页。
D. 7. 1. 3. 2. 参见[古罗马]优士丁尼:《民法大全·学说汇纂·用益权》,米健译,法律出版社1999年版,第2页。
D. 39. 1. 8. 2. 参见[意]桑德罗·斯奇巴尼:《物与物权》,范怀俊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87页。
参见方新军:《权利概念的历史》,载《法学研究》2007年第4期。
Orestano. Azione,Diritti Soggettivi,Persone Giuridiche[M]. Bologna,1978. 119. Cfr. LUIGI,ORSI. Pretesa[A]. Enciclopedia del Diritto(X X XⅤ)[Z]. Prerogative- Procedimento,Milano,Giuffrè,1962,p.364.
Gai. 1. 8. 参见[古罗马]盖尤斯:《法学阶梯》,黄风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4页。
See Peter Stein. The Character and Influence of the Roman Civil Law[M]. London and Ronceverte:the Hambledon Press,74. 在这里,彼得·斯坦使用了“似乎(seems)”一词,但是这并非针对三分法,而是针对盖尤斯何时提出三分法保持怀疑。他接下来马上谈道:“对于这个方案,正如我在其他地方曾经论证过的那样,盖尤斯已经重叠(superimposed)在一个更早的安排之中。”I. 1. 2. 12. 参见[古罗马]优士丁尼:《法学阶梯》,徐国栋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1页。
参见方新军:《盖尤斯无体物概念的建构与分解》,载《法学研究》2006年第4期。
D. 1. 1. 10pr.[意]桑德罗·斯奇巴尼选编:《正义和法》,黄风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39页。
Villey Michel. Suum Ius cuique Tribunes[A]. in Studi in Onore di Pietro de Francisci(Ⅵ)[C]. Giuffrè,Milano,1956,p.364.
D. 1. 1. 12.[意]桑德罗·斯奇巴尼:《正义和法》,黄风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40页。
Pierangelo Catalano. Diritto,Soggetti,Oggetti:un Contributo alla Pulizia Concettuale Sulla Base di D. 1. 1. 12[A]. Ivris Vincvla. Studi in Onore di MARIO,TALAMANCA(Ⅱ)[C]. Jovene,Napoli,2001,p.102.
D. 1. 1. 11.[意]桑德罗·斯奇巴尼:《正义和法》,黄风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40页。
Gai. 2. 14. GAIUS. The Institutes[M]. Translated by S,P,SCOTT,Cincinnati:The Central Trust Company,1932. 120.在黄风教授的汉译本中,这一部分内容在该片断中残缺。参见[古罗马]盖尤斯:《法学阶梯》,黄风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82页。
[美]约翰·菲尼斯:《自然法与自然权利》,董娇娇、杨奕、梁晓晖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09页。
See Alasdair Macintyre. After Virtue:A Study in Moral Theory[M]. London,1981. 67.转引自[英]A·J·M·米尔恩:《人的权利与人的多样性——人权哲学》,夏勇、张志铭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5年版,第5页。
参见[法]雅克·盖斯旦、吉勒·古博:《法国民法总论》,陈鹏等译,法律出版社2004年版,第122页。
Vgl. Affolter. Die celsinische Actio und der Anspruch des Buergerlichen Gesetzbuchs[J]. ZZP,1901,(31):p.456- 457.
See E Metzger. A Companion to Justinian's Institutes[M]. London:Gerald Duckworth and Co.,Ltd,and New York: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7,p.209.
See Theodor Mommsen & Paul. The Digest of Justinian(Ⅳ)[M]. Translated by Alan Watson. Philadelphia,Pennsylvania,1985.艾伦·沃森在其从事的《学说汇纂》英译本中大量使用“Right(权利)”来翻译“ius”,但是在该译本的第一个片断D. 1. 1. 1pr中,他便以译者注的方式明确承认:“我们不能将Ius从拉丁文精确地译成英文。”既然如此,英文语词Right与拉丁语词Ius就不是真正的一回事。因此,笔者认为严格说来,艾伦·沃森已经通过间接方式表明了对于罗马法中存在权利概念的问题持否定态度。
See Peter Stein,Legal Institutions:The Development of Dispute Settlement[M]. London,1984,p.128- 129. 彼得·斯坦在此论及罗马法中的诉讼时说道:“然而,我们将诉讼等同于权利,是因为将诉讼代之以一个我们很容易便意识到了的权利概念,而罗马人则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才逐渐意识到这一点的。”但是对于“时间的推移”的具体信息,作者却语焉不详。
参见贾宝书:《词典编纂中的“异实同名”与一词多义》,载《辞书研究》2002年第1期;徐青:《论词义与释义的几个问题》,载辞书研究编辑部编:《词典和词典编纂的学问》,上海辞书出版社1985年版。
See Oxford Latin Dictionary[Z]. Oxford:Clarendon Press,1968,p.984- 986.
参见[瑞士]费尔迪南·德·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高名凯译,商务印书馆2005年版,第143页。
See G Lepschy. Freud,Abel e gli opposti[A]. Mutamenti di Prospettiva nella Linguistica[C]. Bologna,Il Mulino,1981,pp. 173- 198;Jenntfer Stonre. Italian Freud:Gramsci,Giulia Schucht,and Wild Analysis[A]. Discipleship:A Special Issue on Psychoanalysis(Spring,1984),Vol. 28,p. 122,Note 48;I,M,CASANOWICZ. Die Gegensinnigen Wörter im Alt- und Neuhebräischen[J]. The American Journal of Semitic Languages and Literatures,Vol. 13,No. 3(Apr.,1897),p.231.
See I M Casanowtcz. Die Gegensinnigen Wörter im Alt- und Neuhebräischen[J]. The American Journal of Semitic Languages and Literatures,Vol. 13,No. 3(Apr.,1897),p.231.
Vgl. E,Landau. Die Gegensinnigen Wörter im Alt- und Neuhebräischen[M]. Berlin:S. Calavary,1896.
See SigmundI,Freud. The Antithetical Meaning of Primal Words[M]. in The Standard Edition of the Complete Psychological Works of Sigmund Freud,vol.Ⅺ,Trans.James Strachey,London:Hogarth,1957.
G,Lepschy. Enantiosemy and Irony in Italian Lexis[J]. The Italianist,1981,(1):pp.82- 88.
See Alexei Shmelev. Cognitive Mechanisms of Enantiosemy(with Special Reference to Russian)[A]. Published on The Fifth Annual Conference of the Slavic Cognitive Linguistics Association,The University of Kansas,22-23 October 2005;IRINA,MATVEEVA. Enantiosemy as a Phenomenon of Semantic Change[Z]. http://fccl.ksu.ru/conf2003/cogmod/index.htm,2007- 06- 15.
刘志生、黄建宁:《近二十余年以来‘反训’研究综述》,载《长沙电力学院学报》2003年第2期。
参见蒋绍愚:《古汉语词汇纲要》,商务印书馆2005年版,第137- 152页。
参见蒋绍愚:《古汉语词汇纲要》,商务印书馆2005年版,第155页。
参见徐国栋:《共和晚期希腊哲学对罗马法之技术和内容的影响》,载《中国社会科学》2003年第5期。
参见蒋绍愚:《古汉语词汇纲要》,商务印书馆2005年版,第145页。
参见蒋绍愚:《古汉语词汇纲要》,商务印书馆2005年版,第145页。
[美]布龙菲尔德:《语言论》,袁家骅、赵世开、甘世福译,商务印书馆2004年版,第5页。
[意]维柯:《论意大利最古老的智慧——从拉丁语源发掘而来》,张小勇译,上海三联书店2006年版,第29页,注释53。
参见黄风:《罗马私法导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20页。
D. 1. 1. 1pr.[意]桑德罗·斯奇巴尼:《正义和法》,黄风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34页。
[古罗马]查士丁尼:《法学总论》,张企泰译,商务印书馆1990年版,第5页。
[古罗马]西塞罗:《论义务》,王焕生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代序。
[古罗马]西塞罗:《论法律》,王焕生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31- 81页。
参见廖申白:《论西方主流正义概念发展中的嬗变与综合》,载《伦理学研究》2002年第2期。
参见[古希腊]亚里斯多德:《雅典政制(第12章)》,商务印书馆1959年版。转引自廖申白:《论西方主流正义概念发展中的嬗变与综合》,载《伦理学研究》2002年第2期。
参见廖申白:《论西方主流正义概念发展中的嬗变与综合》,载《伦理学研究》2002年第2期。
参见[古希腊]柏拉图:《理想国》,郭斌和、张竹明译,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6- 15页。
?
⑤参见[古希腊]亚里斯多德:《尼各马可伦理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转引自廖申白:《论西方主流正义概念发展中的嬗变与综合》,载《伦理学研究》2002年第2期。
参见冰子剑:《古希腊罗马的政治观念转换》,http://www.siwen.org/ltxxlr.asp?id=2236,2015- 04- 16.
[美]梯利:《西方哲学史》,葛力译,商务印书馆1995年版,第122页。
[古罗马]西塞罗:《论法律》,王焕生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35- 39页。
参见冰子剑:《古希腊罗马的政治观念转换》,http://www.siwen.org/ltxxlr.asp?id=2236,2015- 04- 16.
笔者曾就被罗马法学家杰尔苏(Celsus)使用Ius作为属概念进行界定的拉丁语词Actio的含义问题向德国特立尔大学的法史学教授利弗内尔(Rufner)请教,其中涉及到对Ius的含义的理解问题。利弗内尔教授即直接运用权利理论来对之加以分析,并且对此等方法的合理性未加说明。这留给笔者一个这样的印象,即利弗内尔教授根本没有意识到这种方法可能存在问题。从笔者接触到的西方学者对于这一问题的表述来看,利弗内尔教授的做法显然很具有代表性。
Hungdah Chiu. The Development of Chinese International Law Terms and the Problem of Their Translation into English[A]. Jerome Alan Cohen. Contemporary Chinese Law:Research,Problems and Perspectives[C]. 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70;夏勇:《人权概念起源——权利的历史哲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86页;李贵连:《话说“权利”》,载《北大法律评论》第1卷第1辑,北京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
基于这一点,笔者不主张将在主观方面意义上得到使用的Ius、Diritto、Droit、Recht等译作“主观权利”,无论它们是否有一个定语“主观的”加以修饰。这是因为,这些词加上定语表示主观方面的含义,是该词二义情形下的无奈之举。如今,既然“权利”一词在汉语中被专门用以表示被译词的主观方面的含义,再在此汉译词汇之前修饰以“主观的”,则无疑是画蛇添足之举,并且很容易导致人们误以为其与“客观权利”相对应。
参见陈忠诚:《“法权”还是“权利”之争》,载《法学》1997年第6期。
参见[德]鲁道夫·冯·耶林:《为权利而斗争》,郑永流译,法律出版社2007年版,第86页。
参见黄忠廉、李亚舒:《科学翻译学》,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2004年版,第108页。
当然,应当说明的是,与纯粹的对罗马法原始文献的翻译不同,在专门对Ius的含义问题进行研究的语境下,例如本文,为了避免因在行文中对其采用某一种译法而可能造成在论证逻辑上“倒果为因”的客观结果,或者给人以“以结论为前提”的主观印象,直接用原语Ius来表示,是可以的而且是必要的。这种情形其实不属于借用,而属于与翻译无关的引用。
参见黄忠廉、李亚舒:《科学翻译学》,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2004年版,第103页。
《辞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99年版,第1115页。
参见黄忠廉、李亚舒:《科学翻译学》,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2004年版,第104- 105页。
参见徐国栋:《客观诚信与主观诚信的对立统一问题——以罗马法为中心》,载《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第6期。
参见米健:《法律交易论》,载《中国法学》2004年第2期。
Cfr. Fritz Schulz. I Principii del Dititto Romano. Firenze,Casa Editrice le Lettere ,1995,p.1- 4.
《辞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99年版,第3745页。
《辞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99年版,第1423页。
《辞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99年版,第576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