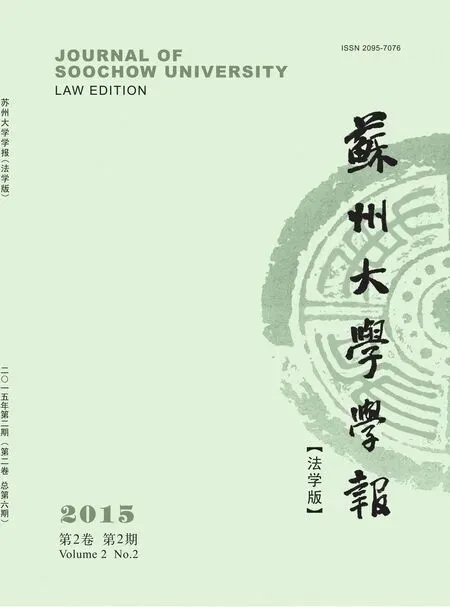论香港基本法解释方法的冲突与协调
秦前红 *付 婧 **
*武汉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武汉大学法学院宪法学与行政法学专业2013级博士研究生。
本论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香港基本法框架下立法权与行政权互动关系研究”(项目编号:13AFX004)和2011年度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一般项目“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解释问题研究”(项目编号:11YJA820057)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内容摘要:香港基本法的解释权属于全国人大常委会,同时全国人大常委会授权香港法院解释基本法。《基本法》的解释充满了解释主体、解释体制、解释技术和方法各方面的矛盾和冲突。全国人大常委会按原意方法解释基本法,特区法院按照其普通法传统解释基本法,从而导致解释结果的差异性,全国人大常委会和特区法院解释方法的不同与其所处的体制并非简单对应关系,两者从技术层面仍有较大空间化解因释法方法的差异性引发的冲突。现阶段基本法解释的冲突协调依赖于基本法解释的基础制度构造,主要体现为特区法院自身的司法建设和全国人大常委会解释基本法程序规则的完善。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7076(2015)02-0052-
港英时期,香港案件的司法终审权为英国枢密院司法委员会所拥有,当时香港谈不上具有违宪审查意义上的司法审查权。与美国马伯里诉麦迪逊案的“伟大篡权”不同,香港法院获得具有违宪审查意义上的司法审查权始于1991年《英皇制诰》第7条修订和《人权法案条例》通过之时。1997年,中国政府恢复对香港行使主权后,将司法终审权授予香港,而未将对《基本法》的最终解释权授予香港,由此出现了香港终审法院终审权和《基本法》最终解释权分离的问题。根据基本法第158条的规定,全国人大常委会享有《基本法》的解释权,但法官在审理案件过程中又不可避免要解释《基本法》。所以如何理解《基本法》解释权的权力配置,如何协调《基本法》解释导致的法制冲突,如何保证全国人大常委会的解释权不影响香港特区的司法独立,都是极其重要的问题。
一、基本法解释权的配置:对《基本法》第158条的分析
根据《基本法》第158条,《基本法》解释权属于全国人大常委会,同时人大常委会授权特区法院在审理案件时对《基本法》关于特区自治范围内的条款进行解释,并授权特区法院可以有条件地解释《基本法》其他条款。从法条字面含义看,全国人大常委会的解释权是固有的,而香港法院的解释权是中央通过《基本法》授予的。 ①
(一)《基本法》第158条下的基本法解释权配置框架
《基本法》第158条对《基本法》解释权的归属和行使做了明确规定,《基本法》第158条第(1)款规定《基本法》的解释权属于全国人大常委会,这符合单一制国家的立法集中和法制统一原则,也保证了《基本法》在全国的统一理解和实施。 ②《基本法》第158条第(2)款规定全国人大常委会授权特区法院在审理案件时自行解释《基本法》有关特区自治范围内的条款,所以香港法院对有关自治范围内的《基本法》条款可以自行解释而没有必要提请人大常委会释法,这体现了对香港高度自治和保留原有法律制度的尊重,但对哪些条款属于“自治条款”,案件当事人、特区法院、特区政府和全国人大常委会可能均有不同的理解。《基本法》第158条第(3)款规定特区法院对除“自治条款”外的“其他条款”也可进行解释,但对此款的条件限制在于:特区法院需要对《基本法》中关于中央人民政府管理的事务或中央与香港特别行政区关系的条款进行解释(类别条件),而该条款的解释又影响到案件的判决(需要条件),在对案件作出不可上诉的终局判决前,应由香港特别行政区终审法院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作出解释(前置程序)。许崇德教授认为此项限制的目的在于,香港法院享有司法终审权,对《基本法》作出的解释会伴随判决的生效而具有法律约束力,为了避免特区法院在对涉及中央利益的条款的解释与全国人大常委会不一致而需对终审法院施加限制。 ③可见,人大常委会的《基本法》解释权是全面和无限的,香港法院的解释则必须受到一定的限制,事实上有香港学者(比如Yash Ghasi教授)也接受了人大常委会解释权“覆盖《基本法》全部条款,因而是全面的;这一权力在无具体案件下也可使用”的看法。 ④香港终审法院在刘港榕案中亦承认全国人大常委会对《基本法》的解释权并不限于在诉讼中提请解释的情况。 ⑤总之,全国人大常委会对于特区自治范围内条款是否有权进行解释,但一般而言,人大常委会会进行自我约制,不对《基本法》中纯粹涉及特别行政区内部事务的条款作解释。
(二)《基本法》第158条的制度性漏洞
《基本法》第158条第(3)款规定特区法院有条件地全面解释《基本法》,终审法院在吴嘉玲案中给出了判断前述条件是否满足的方法: ⑥(1)在审理案件时,唯独终审法院才可决定某条款是否符合该条件;(2)终审法院先判断某条款是否符合“类别条件”,只有符合“类别条件”后,终审法院才进入对“有需要条件”的判断,两项条件都符合后,终审法院再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提出释法请求。因而有学者认为在终审法院的实践中,吴嘉玲案的做法更多地不是审查涉案的《基本法》条文是否有必要提交全国人大常委会解释,相反,更像为拒绝提交提供理由。 ⑦当然为了避免前述“嫌疑”,吴嘉玲案中终审法院花费了大量笔墨来论证所谓的“主要条款标准”,即当案件涉及两个条款需要解释时,X条款为自治范围内的条款,而Y条款为自治范围外的条款,X条款与Y条款之间存在关联时,首先要判断X条款与Y条款谁为主要条款:如果X条款为主要条款,则不需要提请,自行解释即可;如果Y条款为主要条款,则需要提请解释。 ⑧正如陈弘毅教授所评论的,终审法院这一空穴来风的做法在《基本法》第158条第(3)款的规定中找不到任何依据,此举无疑违反了《基本法》第158条的字面含义和规范目的。 ①
在庄丰源案和外佣居港权案中,终审法院都借助上述判断方法,认为案件涉及的相关条款并不符合“类别条件”,因而无须提交全国人大常委会解释。因此,直到 2011年,终审法院才在刚果金案中第一次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释法,这也是迄今为止唯一一次由终审法院发动的人大释法。在终审法院决定提请人大释法的判决书中,多数意见在吴嘉玲案的基础上,除重申吴嘉玲案提出的两项条件——“类别条件”和“有需要条件”外,还需判断争议条款是否符合“可争辩性条件”。 ②可以想象的是,在“类别条件”、“有需要条件”和“可争辩性条件”的严格限定下,绝大多数涉及《基本法》解释的案件均可由终审法院自行定夺是否提请人大常委会解释。从终审法院的判决表述来看,“唯有香港终审法院有权决定是否应当提请解释”,有学者将此权力概括为“提请解释判断权” ③,尤其是当人大常委会认为应当提请,而香港法院则认为不应当提请时,就会出现香港法院取代人大常委会扩大其解释权的结果。这一矛盾出现后,究竟如何解决和补救,《基本法》均未作规定。此外,并非每一起案件的终局判决都由终审法院作出,下级法院在作出终局判决前是否应将需要解释的问题提交终审法院,再由终审法院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进行解释呢?对这一问题,《基本法》也未作出任何实体上或程序上的规定。 ④
(三)“司法扩权”背景下香港法院基本法解释权扩张
在纵向分权方面,《基本法》并未对非自治范畴内的争议处理机制作出清晰界定,当纠纷发生时,如何确定该事项是否属于上述范畴?以何种标准及由谁来确定?从《基本法》目前的规定中难以求得明确的答案。全国人大常委会认为香港应就不明之处请示中央,而香港司法机构则可能倾向于自己做出判断。把香港法院和全国人大常委会对于《基本法》的解释权限划分为对自治范围内事务条款的解释和对涉及中央和特区关系事务条款的解释,也仅是一种不得不为之的理论上的“简化”,因为香港法院在具体的案件审理过程中职司法律解释,必须一并研究与争议条文相关的其他《基本法》条款,方可得出正确的结论。具体案件可能既会涉及自治条款同时又涉及中央管理事务,《基本法》条文本身也难以区分到底哪些属于自治范围内条款或是属于中央与特区关系条款。就代议制机关与法院的关系而言,早前香港的行政主导体制导致代议制机构的发展受到严重限制,使得香港立法会无法对终审法院形成强有力的制衡。近年来越来越多涉及立法权与行政权权限争议、立法会内部事项争议的案件诉诸法院, ⑤法院利用审理此类案件强化自身的《基本法》解释权的趋势不容小觑。而行政对司法的制衡主要体现在人事方面,行政长官通过行使法官任命权实现对司法权的影响,但这种任命权受由当地法官和法律界及其他方面知名人士组成的独立委员会制约。香港回归后,司法权独树一帜,正是由于其他重要权力分支尚不能对香港司法机关构成强有力制衡带来的结果。
二、香港法院解释《基本法》的方法与原则探析
在《基本法》第一案马维昆案中,高等法院首席法官陈兆恺指出了《基本法》规范的错综复杂性:《基本法》既作为全国性的法律,又是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宪法。 ①但针对《基本法》这一特殊的宪制性文件,由于条款的概括性,很多具体规范的含义并非仅从文义的角度就能作出正确的判断,故法院不应僵化地固守普通法中的文义解释,此时目的解释就成为一项重要的释法方法,这也是普通法理论中宪法性文件解释的常用方法之一。然而,“目的解释”是否能够适用于《基本法》的所有条款在马维昆案中尚未得到解答。陈兆恺法官并没有专门阐述《基本法》的解释方法,只是认为应根据《基本法》的性质与地位来解释基本法; ②另一位法官黎守律也表达了“普通法的解释规则和技术是否为解释《基本法》”恰当方法的疑虑。在论及临时立法会立法的效力这一问题时,他认为完全从普通法规范来判断这一问题是存有缺陷的。 ③可见,此时法院尚未将普通法传统与《基本法》的解释方法联系起来。在后来的吴嘉玲案中,终审法院虽然没有直接讨论是否应当运用普通法的解释方法来解释《基本法》,但终审法院认定《基本法》的目的在于保障特区的高度自治和基本人权,因而主张采取宽松的目的解释方法。
(一)系列“居留权”案:从目的解释转向文义解释
1.目的解释
吴嘉玲案中对是否应当就有关条款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提请解释的问题,采用了目的解释的方法,终审判决开篇即声明,在中国主权下建立一个“高度自治”的香港特别行政区,是《基本法》作为法律文本整体所具有的目的。而《基本法》第158条第(3)款有关终审法院在审理案件时就中央政府管辖事项或中央与特区关系的条款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解释的这一程序,旨在强调全国人大常委会对特区法院进行授权,即只要不是“非自治”类条款,香港法院均可“自行”解释。 ④然而《基本法》既保障国家主权,也保障特区的高度自治;既保障特区的繁荣稳定,也保障特区的人权,从前述判词不难看出,特区法院在吴嘉玲案中并未对《基本法》的目的作出全面的理解而将其简化为“保障特区的高度自治”。而在马维昆案中,上诉法庭认为《基本法》的目的在于维持香港原有制度的“延续性”,而没有考虑《基本法》的其他目的,如高度自治和人权保障等。 ⑤所以有学者批评指出法院在运用目的解释时拥有广泛的裁量权,法院可自行决定立法的目的到底是什么,可以选择性使用一系列依据来得出想要的结论而忽视法官们自认为不满意的材料和证据,若没有可信赖的立法背景资料,法院对立法目的的探究可能变得毫无节制,甚至可能扭曲立法的通常含义。 ⑥
针对吴嘉玲案中上诉人的居留权,终审法院基于人权保障的目的,认为《基本法》第24条第(2)款对于香港永久性居民类别的列举是对于居留权充分、自足的保障。如果居留权享有受制于《基本法》第22条第(4)的规定,则将会把权利置于“危险境地”——香港居留权会处于大陆政府裁量性的掌控之下,而身在大陆有资格获得香港居留权的香港永久性居民,将由此遭遇到身处其他地区的同类申请人不会遭遇的歧视对待, ⑦此处彰显了终审法院对于《基本法》人权条款积极保护的态度。在探讨《基本法》中人权条款的解释方法时,终审法院首席法官李国能主张一种宽松的、目的性的解释方法,“法庭应当对第三章那些规定了宪法权利的条款给予宽松解释,以保证香港居民能够充分享有《基本法》所确认的权利与自由”。而对于采取目的解释的原因,终审法院解释,“《基本法》这样的宪制性文件必然会出现法律空隙和模棱两可之处,而在填补这些空隙或澄清模糊语句的时候,法庭有责任从文本和其他相关材料中发现并确证其立法原则与目的,并且通过法律解释将其明示出来”,而特定条款的立法目的可以根据有关外部材料(如《中英联合声明》)来加以判断。 ①从这里可以看出,吴嘉玲案中法院在确立《基本法》规范的立法目的或原意时,并没有否定合理的外来资料的价值,但对于“文义的、技术性的、狭隘的或僵化的解释”则采取明确反对的态度。 ②
2.文义解释
在普通法解释理论中,文义解释并非要排除立法目的,并且常以立法目的来佐证文义解释的合理性。立法目的与文义解释之间的关系在庄丰源案中得到了最直接的体现,终审法院首先强调,尽管全国人大常委会的解释在香港具有普遍约束力,但法院在解决具体诉讼争议的时候,仍然应当适用普通法的一系列原则和方法。根据普通法的原则,法庭在解释《基本法》时的具体任务就是理解《基本法》文本所使用的文字,从而获知寓于该文字中的立法意图。法庭承认,“不能孤立地理解争议所涉条款的文字,而是应如吴嘉玲案那样,将文字置于其语境与目的中来考虑……尽管法院应该避免文义的、技术性的、狭隘的或僵化的解释,但是决不能对文字强加某种无法承受的意义” ③。庄丰源案中,终审法院除明确以普通法中的文义方法来解释《基本法》外,同时也强调立法目的以及外来资料对于确定条款文义的重要作用,凡是有助于了解《基本法》背景或目的的外来资料,一般均可用来协助解释《基本法》。这些可供考虑的外来资料包括《中英联合声明》,以及《基本法》通过前不久提交全国人大审议的《关于基本法(草稿)的解释》(1990年3月28日)等等辅助资料。 ④但与吴嘉玲案对待目的解释的态度不同,庄丰源案中法院的判词表述为“文字的含义必须置于其语境与目的当中来理解”,即语境与目的都是服务于文义解释的辅助方法而已。在庄丰源案中,终审法院更多地是在论证普通法传统中如何平衡立法目的与法律文本之间的关联以及如何接纳并评估与立法过程相关的证明材料。
(二)《基本法》解释的普通法传统及其影响
吴嘉玲案的重要意义在于,确定了香港特区法院将沿用普通法方法与原则来解释《基本法》。庄丰源案中,终审法院又花费了很大篇幅来说明法律解释方法的问题,包括普通法传统中如何平衡立法目的与法律文本语句的关系、如何接纳并评估与立法过程相关的证明材料等方面的原则和技术。引人注目的是,终审法院在庄丰源案中以一种典型的普通法“区分规则”来处理全国人大常委会对《基本法》第22条第(4)款和24条第2款第(3)项的解释,并且以普通法中的分权原则来论证法院对法律的“独占解释权”,即便是面对人大释法这样的权威性法律文件,香港法院仍遵循普通法的方法、原则来理解和处理。庄丰源案表明,香港法院不会主动放弃普通法传统赋予法官的、在个案审判中运用普通法的规则、技术以及裁量权进行解释的权力。然而,实践层面,终审法院的这种做法导致人大释法中的“有关陈述”部分失去了对香港特区法院的拘束力。在庄丰源案中,入境事务处处长曾主张应就《基本法》第24条第2款第(1)项提请人大释法,否则将导致大量在香港出生的中国公民有资格成为香港永久性居民,但终审法院指出即使处长败诉也不会导致大批内地人士立即涌入香港。 ⑤然而此案后的十余年里,大量大陆孕妇赴港生子给香港社会带来巨大的人口压力,这不能不说是庄丰源案的后遗症。正因如此,庄丰源案遭到了来自内地学者的批评,有学者指出判决区分技术虽然根植于普通法传统,但区分的不确定性以及人大常委会的宪法地位、解释法律的运作机制、解释法律的效力等因素决定了香港特别行政区法院不能以这一规则对人大常委会作出的法律解释进行“再解释”。 ①更有学者严厉指出,普通法必须适应《基本法》所确立的新宪制秩序的变化,融入到《基本法》所构建的制定法体制中,任何以普通法传统改造、适用、解释和评判《基本法》的行为,都是本末倒置的行为。 ②
继庄丰源案后,始于2008年的刚果金案再次见证了香港原有普通法规则与《基本法》之间的冲突,刚果金案中与“一国两制”法治实践具有相关性且法律上尚不明确的是“国家行为”这一术语。《基本法》中的“国家行为”是普通法意义上的,还是国内法意义上的,这种区分直接关系到法律程序、司法管辖权和相关规则的适用。有学者认为从《基本法》第19条看,国家行为问题应当适用普通法规则,香港法院应扮演“判断是否属于国家行为”的重要角色。 ③终审法院判决多数意见认为:(1)国家豁免是《基本法》第19条下的国家行为;(2)根据法律和宪法,香港必须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绝对豁免原则保持一致;(3)终审法院有必要将《基本法》第13、19条提交全国人大常委会解释。 ④终审法院的多数判决在认定《基本法》与普通法的关系时指出,香港原有的有关国家豁免的普通法,如果这些法律与中央人民政府根据第13条第(1)款所决定的国家豁免规则或政策有抵触,则这些普通法须按照《基本法》第8条、第160条以及1997年《关于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第一百六十条处理香港原有法律的决定》,在适用时作出必要的变更、适应、限制或例外,以确保关于这方面的普通法符合中央人民政府所决定的国家豁免规则或政策。 ⑤根据终审法院的判决,刚果金案并没有拓展香港法院普通法适用因为空间,反而潜在地减少了未来法院在处理包括国家豁免在内的一切外交事务时的司法空间,中央未来的任何决定均可能构成不受挑战的国家行为。不过未来法院仍很有可能采取如庄丰源案中的做法来减少全国人大常委会对刚果金案解释的影响。
《基本法》实施后,特区普通法如何在一个新的宪制框架下生存发展,特区法院是否应当及时调整法律解释方法以顺应这一变化呢?2013年的外佣居港权案也是针对《入境条例》对《基本法》条文适用范围的限缩所提起的司法审查。法院认为普通法当中“通常居住”的含义并不清晰,在此情形下立法机关有权对这个尚不清晰的宪法概念进行细化或限定,裁定外佣的“居住特质”已远离传统上被认为的“通常居住”的范围,不得被视为《入境条例》所规定的“通常居住于”香港,因而不能成为香港永久性居民。 ⑥简而言之,终审法院赞同立法机关对宪制性法律文件中的法律概念进行填充(限缩),巧妙化解了外佣居港权案可能对香港社会带来的人口风险。在该案中,上诉法庭张举能法官认为,“只要有可能,普通法概念的含义应当作出调适以符合制定法的文本表达” ①。终审法院前首席法官李国能也指出:“普通法在全球各个普通法适用地区有不同的方向发展,正是其长处而非其弱点。普通法的特异之处,是法庭应用有关法律时,有空间凭籍经验因时制宜和因地制宜。” ②
(三)香港法院运用国际法、比较法资源解释基本法
尽管香港已是一个相对独立性的法域,但终审法院仍大量引用海外判例(overseas jurisprudence)来进行司法审查,有学者将之归因于香港缺乏根深蒂固的保护人权的宪政传统,所以大量的外部资源,国际人权法便成为香港司法发展“宪法”的重要来源。 ③但国际法、比较法资源在充当司法审查的依据时,并不具有直接的规范效力,其作用是通过辅助解释《基本法》或《香港人权法案条例》的形式实现的。《基本法》第39条通常被解释为“《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人权法案条例》与《基本法》一样具有宪法性地位”,香港法院则将国际公约作为《基本法》与国际标准之间的桥梁。国际公约被《基本法》通过第39条并入香港本地法律因而成为《基本法》保障人权最强有力的工具。1997年回归后的香港法院以更加开放、能动的姿态在人权法领域使用国际法和比较法,诸如平等机会委员会诉教育署署长案中,《基本法》第25条、《人权法案条例》第22条、《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26条、《性别歧视条例》以及《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得到适用;同性恋平权案中,当事人认为现行刑法中相关条款违反基本法,构成了以性取向为基础的歧视,损害了公民的平等权,《基本法》第25条,《人权法案条例》第14条、第22条,《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2条、第3条、第17条、第26条得到适用等等。此外,国际条约监督机构的评论,香港政府提交给条约监督机构的年度报告,先进普通法国家如加拿大、英国、美国、澳大利亚、新西兰的判例,先进宪法法院如南非宪法法院判例,先进的国际裁决机构如国际法院的判例等,也是香港法院解释和适用《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和《人权法案条例》援引最多的资源。但终审法院对国际法、比较法资源的援用并不僵化,而是按照普通法的精髓不断发展这些案例。如在2012年的变性人结婚案中,终审法院明确拒绝英国法院在Corbett案中的判决,英国法院裁定繁殖性交是普通法下的婚姻构成之基础,因此只有生理因素才能成为评定某人性别的标准。但终审法院认为,随着时代变迁,此种婚姻构成论已不适合多元文化融合的香港,除了繁殖这一要素,在考虑和评定性别身份时,还应将生理、心理和有否进行过“变性手术”等因素纳入考量。 ④
三、全国人大常委会解释《基本法》的方法与原则探析
全国人大常委会在1999年释法中采用的原意解释是针对终审法院在吴嘉玲案中的错误判决而采取的纠偏行动,而2004年及2005年释法为了化解特区社会对《基本法》相关条款的争论,也采用原意解释方法。但未来《基本法》实施过程中将会出现更多需要全国人大常委会释法的情形,而个案差异又会很大,因此在这些案件中,全国人大常委会有必要根据个案的具体情况选择有利于《基本法》实施的方法来解释《基本法》。
(一)全国人大常委会的释法方法——原意解释、结构解释
全国人大常委会在吴嘉玲案中反对香港终审法院的解释,认为终审法院在判决中对《基本法》条款所作出的解释,不符合立法原意。全国人大常委会采用原意解释的方法解释《基本法》相关规定:《基本法》第24条第2款第(3)项这一规定的立法原意体现了“防止内地人口大量涌入香港,维护香港的长期繁荣稳定”的目的。《基本法》第22条第4款的立法原意正是肯定内地与香港之间长期以来实行的出入境管理制度这一立法原意,完全是为了保证内地居民有序赴港,符合香港的整体利益。 ①对于如何寻找立法原意,全国人大常委会借助于法律文本之外的辅助资料来加以确立。全国人大常委会在首次释法时就引用了相关立法资料。其提出本解释所阐明的立法原意以及《基本法》第24条第2款其他各项的立法原意,已经体现在1999年8月10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香港特别行政区筹备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通过的《关于实施〈基本法〉第24条第2款的意见》中。另外,2011年的第四次释法也体现了这一方法,本次解释的核心问题是国家豁免政策是否属于《基本法》第13条所称的“对外事务”和第19条所称的“外交事务”。全国人大常委会在解释中除了援引了宪法有关国务院权力的规定外,还引用了原《基本法》起草委员会主任委员姬鹏飞的相关论述,以表明国家豁免政策属于《基本法》第19条所指的特区法院无权管辖的“外交”事项,从而证明特区法院对国务院决定国家豁免政策的行为无管辖权。
2005年3月10日,香港特区行政长官董建华向中央人民政府提出辞呈,12日中央政府批准董建华辞去行政长官职务。《基本法》规定行政长官任期五年,而董建华的任期从2002年开始,于三年后的2005年辞职。那么,新当选的行政长官任期究竟是完整一届的五年任期,还是完成两年的剩余任期呢?遂引发所谓的“二五之争”。根据朴素的文义解释,这一条款并未区分补选行政长官还是初选行政长官,法律上规定任期都是五年。而人大常委会于2005年作出解释,确定补选行政长官的任期是前任剩余的任期。从基本法委员会负责人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所作的释法说明中可以看出,全国人大常委会针对法律文本采取了结构解释的方法,即综合考虑了《基本法》第 45条、第46条、第53条、附件一等多项条款之间的逻辑关系来进行解释。在全国人大常委会结构解释的推理过程中,为了进一步强化人大释法的合理性,这次人大释法过程中仍然通过外部权威资料的辅助,如根据《基本法》第53条起草过程中的立法资料推断出补选行政长官的任期应依据《基本法》第45条确定,最后又根据2004年 4月《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香港特别行政区2007年行政长官和2008年立法会产生办法有关问题的决定》来对其结构解释得出的结论进行反证,因而有学者认为本次人大释法的基本宗旨仍是寻求立法原意,采用的是原意解释方法。 ②不过,也有学者认为虽然人大释法注重立法原意,但在对补选行政长官任期的人大释法中,原意解释的方法仅仅是补充性的而非主导性的,假如没有这些体现立法者原意的权威资料,仅依赖结构解释的方法,人大释法也是完整且成立的。 ③
(二)全国人大常委会原意解释的合理性反思
特区社会质疑全国人大常委会原意解释主要体现在对其还原立法原意过程的方法方面。如有香港学者针对全国人大常委会运用1996年筹委会的意见作为解释的论据提出质疑,人大常委会为什么不用《基本法》制定时的资料来证明1999年的解释就是《基本法》通过当时(1990年)的“原意”呢? ④吴嘉玲案中终审法院也承认,外来资料对《基本法》的解释有一定的帮助作用,但在陈锦雅案中,特区政府提交了中英联合小组的有关协议作为证明《基本法》第24条第3款的立法原意,高等法院虽承认这一证据的真实性,但拒绝采信。 ⑤而庄丰源案中,法院选取解释方法的具体顺序表现为“文本—目的导向”的解释方法优于原意解释,但并没有完全排斥原意解释。终审法院还在庄丰源案中决定排除1999年“居港权解释”作为“对本案有拘束力之解释”的地位,令筹委会意见退而成为某种“参考性材料”,仅供法庭综合考量之用,有学者将终审法院这一做法命名为“庄丰源案规则”,即1999年人大释法案仅仅针对基本法第22条第4款与第24条第2款第3项构成有效解释,解释文中援引其他法律文件的文字仅构成论理文字(说理文字),不具有拘束力。 ①有学者注意到,在对全国人大常委会1999年“居港权解释”释法方法的接受上,在2009年的一起涉及功能界别选举的政治性案件(即陈裕南及另一人诉律政司司长案)中,香港特区高等法院倾向于以全国人大常委会在“居港权解释”中表达的法律解释规则来适当调整普通法的法律解释规则, ②原讼法庭指出:“一般而言,《基本法》制定以后发生的任何事件均不能影响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在制定《基本法》之时的实际立法原意……但全国人大常委会有权解释与澄清《基本法》条款的含义……且根本不可能忽视人大常委会对筹备委员会工作(包括该办法)毫无保留的批准,这一点清晰表明了《基本法》整体背后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真实原意”;“即使在普通法原则下,当一部后来的法律与一部先前的法律存在实质关联的情况下,后来的法律可用来协助解释先前的法律。其背后的观念是,立法取向在这些法律与共同术语中存在连续性”。 ③但在刚果金案中,终审法院仍然坚持庄丰源案所确立的解释规则——只有《基本法》公布前的有关法律资料,才可被接纳为辅助解释《基本法》的外部资料。 ④而在外佣居港权案中,关于“居港权解释”的特别陈述是否构成对《基本法》第24条第2款第4项有拘束力的解释,庄丰源案判决能否成为外佣居港权案高等法院上诉法庭适用的先例,上诉法庭对此未予置评,故对于上诉法庭而言,“庄丰源案规则”的适用仍然是开放的。 ⑤而终审法院在对该案的判决中决定不提请释法,也未对下级法院的做法作出回应,刻意回避了对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律解释规则的可接受性作出判断。
因此有学者建议全国人大常委会应建立一套完整的探寻《基本法》立法原意的程序规则,其中包括对还原立法原意的资料选择也要形成规则,以此完善原意解释的论证过程。 ⑥也有学者指出,筹委会的“意见”等其实是对《基本法》文字未能完整表达立法者意图的补救措施,尽管这种补救措施难以通过原意解释所要求的程序性审查,不能成为证明立法原意的有效资料,但在实质意义上完全可以推定为立法者的本来意图。 ⑦终审法院曾在庄丰源案中援引内地学者廉希圣教授就立法解释性质的阐述,指出立法解释除了对法律文字、法律用语作出阐释外,还可以进一步对法律“明确界限”和“补充规定”。 ⑧正是出于对中央政府可能利用释法的方式实质性地修改《基本法》,从而损害特区高度自治的担忧,特区法院更愿意牢固遵守《基本法》文本的意涵,反对通过法律解释赋予超出《基本法》文本所覆盖的内容。随着香港《基本法》的实施,立法原意也可能因立法者理性有限或故意模糊处理而呈现缺失状态,以留待日后时机成熟再主动立法或者修法,这些情形都要求释法者在原意之外寻求解决方案,当出现了《立法法》所规定的“新情况”时,全国人大常委会完全有权对《基本法》作出补充性解释,过分强调原意则是不必要的自我束缚。
四、基本法解释冲突的制度归因及协调
从方法和技术上看《基本法》的解释,很难找到一种稳固而现成的“基本法解释方法”,正如学者Michael C. Davis所言,《基本法》是以大陆法技术为主要特征的中国法律与普通法的“杂交”(hybrid), ①注定了对《基本法》的解释充满了解释主体、解释体制、解释技术和方法各方面的矛盾和冲突。对“一国两制”法治实践而言,全国人大常委会和香港法院运用不同的释法方法解释同一部法律,也可能会继续出现。与此同时,另一个已然出现的客观事实也颇值得注意,即对香港法院所坚持的普通法解释方法,全国人大常委会至今并未提出过任何权威性的否定或异议,而特区法院在遵从和适用人大常委会的解释时,也未提出过任何异议或说明,此种双方默示的“认同”表明香港法院的释法和全国人大常委会的释法业已达成了一定程度的平衡,即互相尊重各自对《基本法》的解释,而当解释发生冲突时,以全国人大常委会的解释为准,但香港特区法院在司法审查中仍会以普通法方法来适用全国人大常委会的解释。
(一)基本法解释冲突的制度归因
1.基本法解释权配置的制度性缺失
《基本法》第158条规定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和香港法院的释法权,条款内容的不周延性是引发释法权争议的制度根源,尤其是对于是否属于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的条款的判断权归属。在释法前的吴嘉玲案中,香港终审法院认为其是提请判断的唯一主体,但全国人大常委会四次释法行为表明,特区法院的提请并非是全国人大常委会释法权行使的唯一起动程序,全国人大常委会也可以应国务院或委员长会议的提请进行释法。 ②从实践层面而言,香港法院必然是处理基本法解释问题的前沿实务机关,是否需要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提出释法请求也由终审法院自行判断,但终审法院极有可能将提请释法机制虚置化,从而限缩全国人大常委会的释法权。这样,尽管全国人大常委会有权主动释法,但“一国两制”政策绝不希望终审法院的判决一再被中央推翻,因此除了依赖全国人大常委会自身的审慎与克制外,与终审法院就提请释法的标准达成共识则是《基本法》第158条制度建设的关键所在。
虽然《基本法》第158条规定了香港特区终审法院是提请人大常委会解释的主体,但法律并没有明确规定而实施中可能面临的其他主体还包括:一是特区其他审级法院是否能够成为提请主体;二是行政长官是否能够成为提请主体。终审法院在吴嘉玲案中作出了权威性裁决,即只有终审法院有权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释法,因为只有终审法院的判决才是《基本法》第158条规定的“不可上诉的终局判决”,但如果下级法院审理案件时发现需要解释的条款涉及“中央人民政府管理的事务或特区与中央的关系”,下级法院是自行解释,还是中止程序,申请终审法院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解释?若特区各级法院均可自行解释《基本法》中“关于中央管理的事务和中央与特区关系的条款”,不管案件是否事实上上诉至终审法院,都存在特区法院处理“中央管理的事务”的权力僭越的法律困境,这也说明了需要通过立法解释或终审法院选择适当的案件整合解释机制,《基本法》第158条第2款也并未禁止特区内部自行制定约束特区法院的提请释法的规则和程序。从《基本法》第48条、第43条的规定来看,法律条文并未明确授权行政长官提请释法,行政长官的两次提请也招致了学界和社会的广泛争议, ①香港终审法院对于行政长官的提请行为,也一直未做评论。但从事实来看,人大常委会接受行政长官通过中央人民政府提请解释并作出了有效解释,已然构成对行政长官提请权限的确认。
2.处理普通法与《基本法》关系的制度性失灵
《基本法》中有相关制度涉及《基本法》司法适用中《基本法》与普通法的关系,但这些制度尚未付诸实践,如《基本法》第160条规定香港原有普通法要成为香港特区法律必须根据《基本法》进行适应化,适应化程序包括事先审查和事后审查两种。在1997年2月23日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通过的《关于根据〈基本法〉第一百六十条处理香港原有法律的决定》中没有对普通法进行逐项审查,只是规定了包括普通法在内的香港原有法律适应化的原则。事后审查则要求在特区成立之后,如果发现普通法与《基本法》相抵触的,按照《基本法》规定的程序进行修改或者废除,但这一程序迄今并没有真正启动过,香港法院反而是不断强调普通法是香港的法律传统,坚持以普通法的方式适用和解释《基本法》,使得《基本法》要通过香港法官的解释进行一种转换后才能成为法律规则加以适用。普通法推行的法官造法和遵循先例原则使特区法院在审理案件的同时又可以创造新的法律规则,并且终审法院认为在合适的时候,还可推翻自己的先例,由此引领相关法律的发展,因此人大释法很难决定《基本法》的发展方向。基于对香港特区终审权的尊重,全国人大常委会不能对香港法院的判决进行审查,但是一旦香港法院判决中蕴涵的法律规则或原则成为香港判例法时,这些新判例规则就构成了香港特区法律的组成部分,理论上,这些判例也不能与《基本法》相抵触并应接受全国人大常委会的事后审查,但事实证明《基本法》规定的审查机制对香港普通法的冲击十分有限。
(二)基本法解释冲突的制度性协调
有学者提出中央与特区就基本法解释冲突的协调应采取完全诉讼化的方式,如释法过程应包含普通法诉讼程序中的陈词、法律代表、辩论等几乎全部程序,并将所有程序向社会公开, ②这一观点至少在目前我国宪制架构内缺乏法制基础,还可能涉及《基本法》的修改。尽管香港有论者对人大常委会释法的批评主要集中在“立法解释”容易给人修改《基本法》而不是“释法”的模糊印象,但亦有学者观察到人大常委会在《基本法》实施中的角色明显有别于其在国内的传统宪法地位,全国人大常委会在解释基本法时展现了某种司法属性,运用了一定的司法技术,作出了具有判决式特征的“解释”, ③这种观察也恰好印证了《基本法》的包容性,使人大释法与香港普通法传统并行不悖。鉴于此,基本法解释冲突的制度性协调必须充分考虑到香港的普通法法治状况,具体争议个案的差别,解释案被法院所适用的可能方式,对现有法律规则及后续法律问题的影响等因素。
1.解释方法方面
全国人大常委会和特区法院所使用的释法方法与各自体制之间并非简单的对应关系,在某些解释方法的运用上甚至具有相通之处,如都强调立法目的在解释中的重要性,重视《基本法》的立法背景以及《基本法》的特殊性质在解释中的参考价值等。历史上普通法也并非完全排斥“立法历史材料(Legislative history materials)”的运用,如在著名的Pepper v. Hart案中,英国法官便发展出一套严格使用立法历史材料的规则,当立法含义模糊不清时,法院可以参考议会对于“立法历史材料所反映出的立法的精神与目的”的阐述。 ①而在确定立法原意或条款的字面意义时,双方都主张在某些情况下可以借助于与《基本法》相关的内部和外部资料。当社会现实发生重大变化后,法官不应再僵化地固守法律条文,而应通过探求文本背后的立法意图来解释文本,如终审法院就强调,虽然《基本法》于1997年7月1日才实施,但由于《基本法》的背景及目的是在1990年制定《基本法》时就确立的,所以与解释《基本法》相关的外部资料应是《基本法》制定之前或同期存在的资料,而不应是制定之后的资料。在资料的择取和运用方面,特区法院的做法无疑值得全国人大常委会借鉴。对全国人大常委会而言,加强解释文本和相关法律文书的论证性、专业性和逻辑性,适当扩展和充实解释文书的阐述、论证成份,包括终审法院的说明和意见,案件当事人、社会和学界的意见和理论观点,基本法委员会的讨论过程和意见,都应当在说明文书中向人大常委会全体会议做详细交待并公布,这对提高解释的权威性和公信力显然是十分必要的。对特区法院而言,加强对国家宪法及法律解释制度的认识也是非常必要的,要认识到全国人大常委会的释法依据在于我国宪法,人大释法是对《基本法》的有效补充,解释案作出之后,与基本法一样必然要在特区普通法的环境中完整适用。
2.解释程序方面
整合和改善基本法解释的程序,可以考虑在以下方面建立相应的程序规范:就特区法院而言,应订立香港终审法院提请解释的程序规则或指引,终审法院在提请解释的法律文书中,应包括释法问题的提起、所涉《基本法》条文对案件的影响、案件当事人的意见、各级法院的解释理据和解释方法、普通法在同类问题上的适用、可依据的历史权威参考判例等;就人大常委会而言,应强化基本法委员会的咨询职能,充分尊重基本法委员会的意见,订立基本法委员会的议事规则,赋予基本法委员针对基本法解释的问题召集专家证人的权力,以增强其专业权威性和公信力。就目前而言,基本法委员会缺乏公开、规范化的议事规则,公众无从了解基本法委员会内部的工作情况和法律意见,也未见公开的基本法委员会咨询报告,这些因素都影响了人大释法的公信力,因此未来应当着力改进。
综上所述,全国人大常委会和特区法院基本法解释方法上的差异性,并非人们想象的那样严重,伴随基本法的深入实施,双方均有空间调整自己的法律解释理论和技术,从而最大限度化解因释法方法差异引发的冲突。但针对基本法解释更深层次的问题在于,我国宪法和香港基本法对于全国人大常委会、终审法院如何行使基本法解释权仅提供了较为粗浅的规定,而香港回归以来的人大释法实践尚未积累起足够的经验,因此在与香港地区普通法传统之间的互动方面产生冲突也在所难免。现阶段基本法解释冲突的协调应重点依赖于香港特区的司法克制和全国人大常委会解释基本法的程序完善两个方面。同时,作为中央机关的全国人大常委会的释法最终必须以最大程度促进香港特区对国家主权的认同为目标。近年来,香港法院利用审理政治性案件强化自身的基本法解释及宪法审查权能的趋势不容小觑,香港政治案件涌入法院的根本原因在于政治过程的失败,尤其是政治民主的缺乏。当没有其他有效渠道来处理政治争议时,法院就可能被用来当做一个追求政治改革的工具,广泛的救济渠道固然可以使相关权利人有机会得到宪法上的救济,但也可能被政党、团体、个人所利用,有些议员甚至将提起司法复核视为挑战特区政府的一种方式。因此香港司法机构有必要采取审慎的态度行使其司法审查权,避免过度介入涉及中央与香港关系的政治性议题,从而引发不必要的“宪法性危机”。
The Conflict and Coordination of the Legal Interpretation
on the Hong Kong Basic Law
Qin Qian-hong Fu Jing
Abstract:The power of interpretation of Hong Kong Basic Law belongs to the Standing Committee of the Nation People’s Congress(NPCSC),and the NPCSC will authorise the HK courts to interpret Hong Kong Basic Law,according to the Article 158 of the Hong Kong Basic Law. While,when the Basic Law needs to be interpreted,lots of conflict have been coming,because the NPCSC prefers originalism interpretation method,and HK courts prefer the common law tradition method. However,from technical perspective,there is still much space for them to resolve conflicts caused by different interpreting methods. Coordination of conflicts in the interpretation of Basic Law depends on the basic system construction of Basic Law interpretation,mainly for judicial construction of HK courts and improvement of proceeding rules of the NPCSC interpreting Basic Law.
Keywords:Hong Kong Basic Law interpretation;Originalism interpretation;textualism interpretation;Commom Law
(责任编辑:程雪阳)
有学者批评指出香港基本法的解释机制不宜概括为双轨制或二元制,因为《基本法》的解释权属于全国人大常委会,而香港法院获得的解释权只能是来自全国人大的常委会的授权。参见邹平学:《香港基本法解释机制基本特征刍议》,载《法学》2009年第5期。
许崇德主编:《港澳基本法教程》,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67页。
许崇德主编:《港澳基本法教程》,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69页。
Yash Ghai,Hong Kong’s New Constitutional Order:The Resumption of Chinese Sovereignty and the Basic Law,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2nd ed,1999,p.198.
LAU KONG YUNG AND OTHERS v. THE DIRECTOR OF IMMIGRATION,FACV10/1999 paras.57- 63.
NG KA LING AND ANOTHER v. THE DIRECTOR OF IMMIGRATION,FACV14/1998 paras.89- 90.
祝捷:《香港特别行政区终审法院法规审查技术实践及其效果》,载《政治与法律》2014年第4期。
NG KA LING AND ANOTHER v. THE DIRECTOR OF IMMIGRATION,FACV14/1998 paras.102,103.
陈弘毅:《终审法院对“无证儿童”案的判决:对适用〈基本法〉第158条的质疑》,载佳日思、陈文敏、傅华伶主编:《居港权引发的宪法争论》,香港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27页。
DEMOCRATIC REPUBLIC OF THE CONGO AND OTHERS v. FG HEMISPHERE ASSOCIATES LLC,FACV5/2010 para.398.
曹旭东:《香港基本法解释制度的漏洞及填补——居港权案的再思考与刚果金案的新启示》,载《云南大学学报》2012年第1期。
有学者认为对这一问题的缺乏规范并非当时的立法意图缺失,而是立法者不想直接界定香港其他法院的司法管辖权。参见朱国斌:《香港基本法第158条与立法解释》,载《法学研究》2008年第2期。
如2005年梁国雄诉行政长官案,涉及香港政府行政命令与立法会立法权限的冲突;2006年梁国雄诉立法会主席案,涉及修正案动议权、立法会议事规则是否违宪;2008年郑家纯、梁志坚诉立法会案,涉及立法会调查权;2009年陈裕南及罗堪诉律政司司长案,涉及《立法会条例》第25条及26条有关立法会选举团体投票是否违宪等。
HKSAR v. MA WAI KWAN DAVID AND OTHERS,CAQL1/1997 para.13.
Ibid.,para.14.
Ibid.,para.148.
NG KA LING AND ANOTHER v. THE DIRECTOR OF IMMIGRATION,FACV14/1998 paras.12,81,82.
HKSAR v. MA WAI KWAN DAVID AND OTHERS,CAQL1/1997 para.13.
佳日思:《〈基本法〉诉讼:管辖、解释和程序》,载佳日思、陈文敏、傅华伶主编:《居港权引发的宪法争论》,香港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23页。
NG KA LING AND ANOTHER v. THE DIRECTOR OF IMMIGRATION,FACV14/1998 paras.107- 111.
NG KA LING AND ANOTHER v. THE DIRECTOR OF IMMIGRATION,FACV14/1998 paras.74- 77. 香港学者佳日思指出,在马维昆案的上诉法庭判决尤其是马天敏法官的判词中,目的方法通常是与“宽宏方法”对等的。作为先例,Diplock勋爵在Jobe案(Attorney-General of Gambia v Jobe [1984] AC689 at 700)的陈述以及Wilberforce勋爵在Fisher案(Minister of Home Affairs v Fisher [1980] AC 319 at 328)中的陈述被经常援引。从上诉法庭的判决中,并不清楚这两种方法是如何联系在一起的,并且使用“宽宏方法”的例证并不多。与目的方法不同,宽宏方法似乎较少依赖立法机关的意图而是更多考虑作为法院的宪法责任的保护权利的需要。参见佳日思:《〈基本法〉诉讼:管辖、解释和程序》,陈文敏、傅华伶主编:《居港权引发的宪法争论》,香港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28页。
NG KA LING AND ANOTHER v. THE DIRECTOR OF IMMIGRATION,FACV14/1998 para.76.
THE DIRECTOR OF IMMIGRATION v. CHONG FUNG YUEN,FACV26/2000 para.6.1,6.3.
THE DIRECTOR OF IMMIGRATION v. CHONG FUNG YUEN,FACV26/2000 para.6.3.
THE DIRECTOR OF IMMIGRATION v. CHONG FUNG YUEN,FACV26/2000 para.7.
姚国建:《1999年〈人大解释〉对香港法院的拘束力——以“入境事务处处长诉庄丰源案”为例的考察》,载《法商研究》2013年第4期。
张淑钿:《香港基本法司法适用中的争议——从基本法与普通法的关系角度》,载《太平洋学报》2010年第7期。
Peter Wesley- Smith,Constitutional and Administrative law in Hong Kong,Hong Kong:Longman Asia Limited,1994,p.106.香港终审法院在“马维昆案”判决中极力表述终审法院为“授权性地方司法机关”的属性,认为香港法院作为中国的地方性区域法院,无权审理中华人民共和国在香港行使主权的行为,特区法院不能质疑人大决定或决议后成立筹委会的理由是否合理,因为这些决定或决议属于主权行为,其有效性是不受特区法院挑战的。不过法院仍表示法院有权查证主权者行为是否事实上存在,否则法院就没有履行自己的职责。HKSAR v. MA WAI KWAN DAVID AND OTHERS,CAQL1/1997 para.60,61.
DEMOCRATIC REPUBLIC OF THE CONGO AND OTHERS v. FG HEMISPHERE ASSOCIATES LLC,FACV Nos 5,6 & 7 of 2010 paras. 183,226,410- 411.
DEMOCRATIC REPUBLIC OF THE CONGO AND OTHERS v. FG HEMISPHERE ASSOCIATES LLC,FACV Nos 5,6 & 7 of 2010 para.407.
VALLEJOS EVANGELINE BANAO,also known as VALLEJOS EVANGELINE B v. COMMISSIONER OF REGISTRATION AND ANOTHER,CACV204/2011 paras.116- 117.
VALLEJOS EVANGELINE BANAO,also known as VALLEJOS EVANGELINE B v. COMMISSIONER OF REGISTRATION AND ANOTHER,CACV204/2011 paras.39,40.
李国能:《2009年4月6日在第十六届联邦法律会议(香港)开幕典礼辞》,载香港政府新闻网:http://sc.isd.gov.hk/gb/www.info. gov.hk/gia/general/200904/06/P200904060129.htm,访问时间:2014年3月25日。
陈弘毅:《公法与国际人权法的互动:香港特别行政区的个案》,载《中外法学》2011年第1期。
W v. THE REGISTRAR OF MARRIAGES,FACV 4/2012 para.90.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第22条第4款和第24条第2款第(3)项的解释》,1999年6月24日。
姚国建:《论普通法对香港基本法实施的影响——以陆港两地法律解释方法的差异性为视角》,载《政法论坛》2011年第4期。
强世功:《文本、结构与立法原意——“人大释法”的法律技艺》,载《中国社会科学》2007年第5期。
Lin Feng and P.Y.Lo,One Term,Two Interpretations:The Justifications and the Future of Basic Law Interpretation,Hualing Fu,Lison Harris and Simon NM Yong,ed.,Interpreting Hong Kong’s Basic Law,Palgrave Macmillan,2007,p.151.
CHAN KAM NGA AND OTHERS v. THE DIRECTOR OF IMMIGRATION,CACV40/1998 para.9.
黄明涛:《论全国人大常委会在与香港普通法传统互动中的释法模式——以香港特区“庄丰源案规则”为对象》,载《政治与法律》2014年第12期。
李纬华:《关于香港特别行政区终审法院适用提请释法规则状况的检讨》,载《政治与法律》2014年第4期。
CHAN YU NAM v. SECRETARY FOR JUSTICE,HCAL32/2009 paras.98- 100.
DEMOCRATIC REPUBLIC OF THE CONGO AND OTHERS v. FG HEMISPHERE ASSOCIATES LLC,FACV Nos 5,6 & 7 of 2010 para.310.
VALLEJOS EVANGELINE BANAO,also known as VALLEJOS EVANGELINE B v. COMMISSIONER OF REGISTRATION AND ANOTHER,CACV204/2011 paras.125- 131.
?
姚国建、王勇:《论陆港两地基本法解释方法的冲突与调试》,载《法学评论》2013年第5期。
强世功:《文本、结构与立法原意——“人大释法”的法律技艺》,载《中国社会科学》2007年第5期。
THE DIRECTOR OF IMMIGRATION v. CHONG FUNG YUEN,FACV26/2000 para.6.1
Davis,Michael C,“Human Rights and the Founding of the Hong Kong Special Administrative Region:A Framework for Analysis”,Colum.j.transnatl L 34.2(1996):pp.315- 316.
全国人大常委会1999年6月24日的首次释法《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第二十二条第四款和第二十四条第二款第(三)项的解释》以及全国人大常委会 2005年4月27日的第三次释法《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第五十三条第二款的解释》都是应国务院的提请进行的。全国人大常委会2004年4月6日的第二次释法《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附件一第七条和附件二第三条的解释》是应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委员长会议的提请进行的。
有学者认为,特区政府享有在“基本法之外”通过中央人民政府请求释法的自由裁量权,但特区政府在行使这一自由裁量权时,应充分考虑基本法的宪法性安排和作为香港重要基石的普通法。虽然特区政府行使这一自由裁量权的行为是合法的,但却可能使得法院的司法审查变得不那么重要,进一步限制了终审法院的管辖权。因为,一旦中央人民政府应特区政府的请求提请释法,那么终审法院就不再有能力请求释法或自行解释基本法了。参见 Marsden Simon,“Regional Autonomy,Judicial Criticism and the 2005 Interpretation:Judicial Independence in Hong Kong Compromised Again”HKLJ,Vol 36,2006,pp.119- 121.也有学者认为《基本法》的大体安排是,律政司向行政长官提供实施《基本法》和其他法律的建议,如果一项依据该建议作出的政府行为或立法的合法性受到质疑,应由法院来决定这一问题。行政长官借助全国人大常委会释法的行为意味着以一种不符合《基本法》的一般安排,尤其是不符合第158条规定的方式,绕过香港的司法机构,或者说是把全国人大常委会确立为香港的终审法院。参见佳日思:《人大常委会的解释及其影响》,载佳日思,陈文敏、傅华伶主编:《居港权引发的宪法争论》,香港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207- 208页。
佳日思:《〈基本法〉诉讼:管辖、解释和程序》,载陈文敏、傅华伶主编:《居港权引发的宪法争论》,香港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52页。
黄明涛:《论全国人大常委会在与香港普通法传统互动中的释法模式——以香港特区“庄丰源案规则”为对象》,载《政治与法律》2014年第12期。作者指出,基本法解释有如下几个特点:其一,基于具体案件或争议而启动释法,不论是依提请而解释或是主动解释,其目的都在于解决具体争议,而不是面向未来创设普遍性规则。其二,采用了一定的说理文字来佐证其欲宣示的法条之“含义”或解决方案。其三,释法所作出的“实质决定”的涵盖面是狭窄的,不超过解决当前争议之必要范围,正是基于前述特点,人大常委会的基本法解释具有了“司法化”的特征。
Simon N.M Young,Legislative History,Original Intent,and the Interpretation of the Basic Law,Hualing Fu,Lison Harris and Simon NM Yong,ed.,Interpreting Hong Kong’s Basic Law,Palgrave Macmillan,2007,pp.19- 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