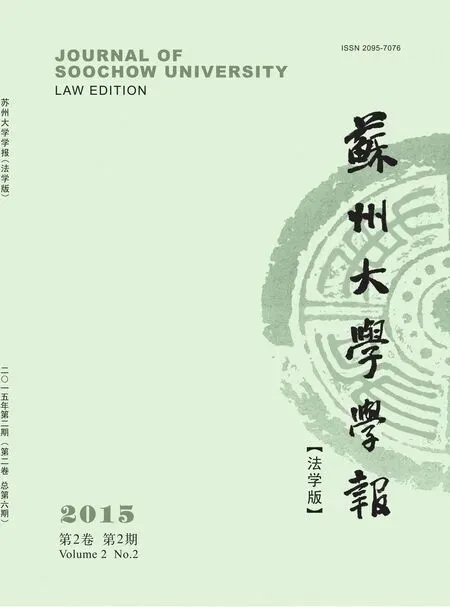有组织犯罪的研究导向:超越具体类型的一种“规划”
*扬州大学法学院教授,法学博士。**扬州大学法学院教授,法学博士。
内容摘要:如若将有组织犯罪视为上位概念,有组织犯罪研究就不应被降格为其下位概念所对应的诸如犯罪集团犯罪研究和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研究等。而要想在“规范建设”和“政策建设”上作出贡献,则有组织犯罪研究在犯罪学中的起点定位便显得尤为重要。为了使得有组织犯罪研究显见成效,社会学、心理学和经济学等学科交叉方法的深入运用就显得尤为必要,而这些学科方法完全可以是“多分支”的并用或交错运用,并且应关注这些学科的最新发展及其理论成果。对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的领会,将使得有组织犯罪研究获得强劲的“精神指引”和“目标召唤”。有组织犯罪法的出台或许将是有组织犯罪研究成果的最高体现。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7076(2015)02-0094-0
中国的法学研究包括刑事法学研究,特别是刑法学研究一直惯于“风起云涌”。在“风起云涌”之中,相关研究便难免显得“热情有余而理性不足”,甚至有“跟风”或“凑热闹”之嫌,由此导致相关研究在“自说自话”之中呈现出“无的放矢”或“漫无目的”的“表面繁荣”局面。正因如此,对于慢慢升温的有组织犯罪研究,我们应该保持着一种警醒,而有组织犯罪研究导向问题便在相当意义或相当程度上能够发挥此种警醒作用。
一、有组织犯罪研究的问题导向
何谓有组织犯罪?到目前为止,具代表性的观点便已林林总总:(1)共同犯罪说,即有组织犯罪,是指两个以上的人为了某种(某个、某些)具体的犯罪目的而组织起来共同实施的犯罪活动,并且有组织犯罪与法律意义上的共同犯罪基本相同。(2)集团犯罪说,即有组织犯罪,是指故意犯罪者操纵、控制或直接指挥和参与,组织结构严密、等级森严或组织成员相对稳定,有特定行为规范和有逃避法律制裁的防护体系的犯罪组织和犯罪联合体,为获取巨大经济利益和其他利益而使用暴力恐吓、腐蚀及其他非法手段所进行的集团性犯罪活动。(3)黑社会犯罪说,即有组织犯罪,是指黑社会犯罪组织实施的犯罪活动,因为在国际社会包括联合国预防与控制犯罪机构的官方文件中,均视有组织犯罪为黑社会犯罪。(4)有经济目的犯罪集团说,即有组织犯罪,是指二人或二人以上,按照组织和等级永久性集合在一起,为最大限度地获取经济利益,采取恫吓、暴力和贿赂腐蚀的方法而实施的行为;(5)多种含义的有组织犯罪说,即有组织犯罪有广义、狭义、最狭义三个概念:广义的有组织犯罪,是指二人以上故意实施的一切有组织的共同犯罪或者集团犯罪活动;狭义的有组织犯罪,是指二人以上的有一定组织形式,主要犯罪成员基本固定,社会危害大,反侦查能力强的集团性犯罪组织所实施的犯罪活动;最狭义的有组织犯罪,是指二人以上有一定组织结构和组织关系,内部结构紧密、等级森严、犯罪能量大、自我防护能力强的超集团性犯罪组织所实施的犯罪活动,通常指那些最具有典型意义的黑社会组织所实施的犯罪。(6)二元论说,即有组织犯罪的概念包括犯罪学意义上的有组织犯罪概念和刑法学意义上的有组织犯罪概念。从犯罪学的角度,有组织犯罪应界定为三人以上故意实施的一切有组织形式的犯罪活动。在外延上它包含一般性犯罪集团实施的犯罪、带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和典型黑社会犯罪,但不包含没有组织形式而是临时纠集起来存在简单分工的一般结伙犯罪;从刑法学的角度,有组织犯罪,仅指一般性犯罪集团实施的犯罪和带黑社会性质组织实施的犯罪,不包含典型的黑社会犯罪,因为后者在实践中尚未出现,在刑事规范上也没有体现。 ①
从前文对有组织犯罪的定义或界定之中,我们可以看出中国大陆刑法学界到目前为止对有组织犯罪的把握,存在如下较为明显的问题:一是将有组织犯罪“降格”或“限缩”为另一个概念如“共同犯罪”或“犯罪集团”等。至于在“共同犯罪”或“犯罪集团”前面加定语的那些定义或界定,如“有组织的共同犯罪说”和“有经济目的犯罪集团说”,则将有组织犯罪“降格”更低或“限缩”更小;二是将有组织犯罪变成一个“莫衷一是”的概念,至少在一定程度上是如此,如“多种含义的有组织犯罪说”和“二元论说”。前述所指出的问题说明:以往中国大陆刑法学界对有组织犯罪的研究,还没有形成一个明确的、集中的从而是“坚定”的问题意识,以致于有组织犯罪概念所对应的问题被消解或转移。而这种研究状况,说得难听一点便是“顾左右而言他”甚或“挂羊头卖狗肉”,因为作为消解或转移问题的那些定义或界定绝大多数是表述在以“有组织犯罪”为名的著述包括论文和著作中。实际上,从共同犯罪、团伙犯罪、集团犯罪、黑社会性质的组织犯罪、黑社会组织犯罪到有组织犯罪,前述概念的先后提出表明人们对犯罪现象认识的不断深化,而此认识的不断深化是与犯罪现象本身的不断发展演化相对应的。如此说来,有组织犯罪这一概念应是犯罪现象的一种“高级”发展形态,如有学者指出,有组织犯罪是当今国际社会公认的一种最高形态的犯罪。 ②因此,作为犯罪现象的一种“高级”发展形态的有组织犯罪便包含着或“沉淀”着较之低一级的犯罪形态甚至包括与一般共同犯罪相对应的复杂共同犯罪,但它绝不至于等于乃至小于较之低一级的犯罪形态包括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那就是说,有组织犯罪在犯罪现象的“层级”中应被予以“适得其所”的安排,而这种安排最终是为了明确、固定或“锁定”有组织犯罪这一概念的问题指向,从而确保我们所研究的将是一个确定的新问题或新课题。于是,这里要着重强调的是,尽管在某种意义上我们可将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视为有组织犯罪的“最高形态”,但也不能将有组织犯罪研究完全等同于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研究,因为有组织犯罪显然是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的上位概念,故两者所指称的问题位阶有别。易言之,我们不能把有组织犯罪本身与有组织犯罪的某种形态相等同。至于学者们一致强调典型的黑社会组织在当下中国大陆还没有出现,而刑法尚未规制黑社会组织犯罪的问题,这或许恰恰预示着将有组织犯罪研究落定在高于从共同犯罪到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的理论层次,当然也是其本应对应的理论层次上,则或许具有一种“前瞻”意义。
在将有组织犯罪这一概念所指向的问题,即将有组织犯罪研究的问题对象予以明确、集中乃至“坚定”前提下,有组织犯罪研究仍然存在着另一个问题,即“由点到面”的问题。有组织犯罪研究可因“组织”的性质划分而被具体为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研究如“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的新型生成及其治理”、恐怖组织犯罪研究如“恐怖组织犯罪的新型生成及其治理”、邪教组织犯罪研究如“邪教组织犯罪的新型生成及其治理”和其他类型的有组织犯罪研究。我们并不否认前述具体类型的有组织犯罪研究的意义或价值所在,但这些具体类型的有组织犯罪研究仍面临着由特别到一般的归纳总结与概括提升,从而形成有组织犯罪的一般命题,以最终使得有组织犯罪研究能够在“一览众山小”之中显示其研究意义与研究价值,并同样避免有组织犯罪研究局限于“低层次”的“目光短浅”与“气量狭小”。
二、有组织犯罪研究的学科导向
有组织犯罪研究在问题的逻辑上包含着有组织犯罪的犯罪学研究和有组织犯罪的刑法学研究,而这意味着有组织犯罪研究可以在不同的学科中予以展开。但是,两者的研究不应在相互“盲视”中进行,而是应该相互关照乃至相互“眷顾”。因为有组织犯罪的犯罪学研究是一种事实学研究,而其刑法学研究则是一种规范学研究,又因为我们对有组织犯罪的预防与治理至少具有刑事规范性,故有组织犯罪的犯罪学研究应把有组织犯罪的刑法学研究所欲解决的问题和所要达到的目标作为自己研究的必要方面乃至“方向”,从而使得这种研究不是“盲目”的,更非“自娱自乐”。可以这么说,在犯罪问题上,如果作为事实学的犯罪学研究不具有“规范建设性”或“政策建设性”,则其将变得几乎没有意义甚或毫无意义。
但是,在有组织犯罪的犯罪学研究与刑法学研究这两者之间,刑法学研究更应主动地关照乃至“眷顾”犯罪学研究,因为有组织犯罪的刑法学研究的“规范性建设”需要“营养源供给”,而此“营养源供给”正是有组织犯罪的犯罪学研究所提供的各种客观性命题以及相关实证性结论。否则,有组织犯罪的刑法学研究将变成“无病呻吟”,或将变成“墙上芦苇”,轻者“腹中空空”,重者“东倒西歪”。这里或许牵扯出有组织犯罪研究中的一种“学科姿态”问题。而心照不宣的是,在中国大陆,纯粹犯罪学的研究任务是由刑法学界为主体担当,而绝大多数刑法学者既无纯粹犯罪学的学术背景,也无纯粹犯罪学的学术兴趣。因此,若真想在有组织犯罪研究中形成或收获最终的“建树”,则参与其中的刑法学者们恐怕要“修正”一下“唯刑法学是瞻”的学术背景,并“浓厚”一下犯罪学的学术兴趣。换句话说,在有组织犯罪研究中,参与其中的刑法学者们应着力上好犯罪学的“第二课堂”。笔者在研究罪刑关系时曾获得一种难得的认识,即在犯罪概念的构造中,人身危险性的受关注最终得归功于实证犯罪学。正如我们所知,刑事古典学派注重的是犯罪的概念研究,如实证主义犯罪学的代表人物菲利所批评的那样,刑事古典学派把犯罪看成是纯粹的法律问题,把注意力集中于犯罪的法律名称和法律定义而将犯罪人的背景人格抛置一边。 ①这样,刑事古典学派在考察犯罪问题时便抓住了共同性而丢弃了个体性,抓住了客观性而丢弃了主观性,抓住了回顾性而丢弃了前瞻性。在此基础上,菲利提出,在研究和理解犯罪之前必须首先了解犯罪人。 ②菲利所说的了解犯罪人包括了解犯罪人将来再犯的事实根据和将来再犯的可能性大小。事实上,实证犯罪学的兴起作出了未为人们充分注意的刑事法学方法论上的重大贡献,因为其将犯罪学方法带到刑法学中来,即将事实学方法与规范学方法糅和到一起。国内已经形成的“已然之罪”与“未然之罪”理论 ③和“罪行之罪”与“罪人之罪”理论 ④,都可以说是实证犯罪学的方法论成果。这些理论都因觅见了人身危险性而使学术眼光由单纯回顾而拓宽为既回顾又前瞻。可以说,没有实证犯罪学,便没有人身危险性理论;而没有人身危险性理论,也就没有新旧两派刑法理论之融合即没有综合主义刑法理论的形成。由此,犯罪学对于刑法学的推动作用应始终值得我们高度重视。 ①将前述认识移转到有组织犯罪研究问题上来,我们或许应该更加重视有组织犯罪的犯罪学研究,因为我们或许会更加清楚地看到:我们的刑法学到目前为止总体上还是停留于纯粹规范学的方法论思维。由于规范终究是社会事实的反映,规范学也需要事实学提供事实基础,故包括犯罪学在内的事实学的渗透无疑将是刑法学再图发展的根本途径所在。那么,有组织犯罪的刑法学研究至少不能在对有组织犯罪的犯罪学研究的“无动于衷”之中而陷入“波澜不惊”,最终变得死水一潭。
总之,我们应该重视对有组织犯罪的犯罪学研究。马克思曾言:“立法者应该把自己看成一个自然科学家,他不是在制造法律,不是在发明法律,而仅仅是在表述法律,他把精神关系的内在规律表现在有意识的现行法律之中。如果一个立法者用自己的臆想来代替事物的本质,那么我们就应该责备他的极端任性。” ②对此,刑事法学者们应把通过犯罪学研究而得出的有关有组织犯罪的客观结论提供给立法者作相应的立法参考,以防止他们“制造”或“发明”法律,而这便意味着或要求着刑事法学者们应先在犯罪学上客观如实地“表述”有组织犯罪本身的所有问题。
三、有组织犯罪研究的方法导向
社会学、心理学与经济学等学科交叉法应是有组织犯罪研究予以重视的研究方法,这是由有组织犯罪自身的特性即其复杂性所决定的。
就社会学研究方法而言,发生在社会中的犯罪本来就有社会因素,故社会学研究方法的采用自不待言。而这里要强调应将社会学方法用深用透,因为有组织犯罪毕竟是“有组织”的犯罪,而非简简单单的单个人犯罪。如有学者指出,犯罪好比社会有机体的疾病,疾病是健康的大敌,但它又是保留有机体健康必不可少的条件,一个永不生病的有机体必是一个新陈代谢停滞的没有生命活力的肌体。那么,当社会有机体内部矛盾最激烈时,社会的新陈代谢也最旺盛,社会的生命力也最旺盛,作为新陈代谢的犯罪也最活跃。同时,犯罪又是社会能量的一种极端释放方式,而当异质的社会能量的累积因社会的强制性高压而导致社会自身的“脆裂”’和“分崩”,则犯罪便具有了像弗洛伊德所说的“能量宣泄”功能,且其“宣泄”在给社会带来灾难的同时,也给社会的异质能量带来了一定程度的消解,从而避免更大的导致从根基上动摇并危及社会的恶害。因此,犯罪也是社会客观存在的“排气孔”和“安全阀”。 ③前述论断启发我们:在社会学方法中,我们可用一种称之为“社会有机体论”的方法来考察有组织犯罪问题。其实,有组织犯罪的“组织”在某种意义上也是一种“有机体”甚至“社会有机体”,只不过是社会这一“有机体”的“毒素”没有得到及时排泄而淤积起来的一个“病体”而已。既然犯罪能够通过能量“宣泄”而使得社会这一“有机体”在必要的“新陈代谢”中维持必要的健康状态,那么,社会也可以通过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健康发展而令有组织犯罪的“组织”即犯罪组织本身或难以得到“孕育”,或在已经形成“癌变”之后得到有效“放疗”或“化疗”。这是就有组织犯罪的单纯预防来看问题,但在有组织犯罪的刑法司法中还涉及有组织犯罪的刑事责任认定如共犯角色到底如何恰当划分的难题。有学者指出,与普通的共同犯罪不同,有组织犯罪的具体犯罪行为未必是由组织的领导者直接参与的具体犯罪行为,即使背后的指使,也未必由犯罪组织的领导者直接进行,甚至领导者处在行为之背后,都不见得直接进行了具体行为的策划,而就具体的犯罪行为来说,甚至找不到犯罪组织领导者在行为中起到的作用。在此情况下,共同犯罪的归责原则适用便会存在一定的难度,因为一般共同犯罪的主要作用者或者组织领导者容易认定,但在有组织犯罪中,组织者并不直接进入犯罪现场,而在大型的、组织严密的犯罪组织中,组织领导者一般还具有被人们认可的正面形象包括相应的正常且较高的社会地位,以至于形式上褪去了“黑色”而刻意染成了“白色”甚至“红色”。但是,那些“看不见”的领导者与“看得见”的走卒者之间的关系正像决胜千里之外的将军与前线杀敌的士兵之关系一样。于是,在有组织犯罪中,案件的总体事实脉络与每个个体之间的关系,便构成了网状的事实关系网和价值关系网,从而使得有组织犯罪的价值判断基于事实的复杂性而相应地变得复杂,这便引起主从犯判断的复杂。 ①
就心理学研究方法而言,有组织犯罪的组织成员之所以能够“结合”而非仅仅是“组合”成一个组织并且是冒险的组织,往往有某种心理因素在起一种纽带作用,而此心理因素可以是信念或价值观上的“苟同”或畸形认同,故心理学方法在有组织犯罪研究中也大有“用武之地”。在存在心理因素的纽带作用下,有组织犯罪中的“组织心理”还往往进一步体现为一部分成员对另一部分成员的追随乃至崇拜甚或“膜拜”,而这种心理又可能反向“招纳”或“凝聚”更多成员。那么,这里或许将使心理学得到一种特别的运用。在心理学上,“从众”是一种心理现象。有学者指出,“从众”是“由一个人或一个团体的真实的或是臆想的压力所引起的人的行为或观点的变化” ②。另有学者指出,“从众”是指“个体在群体中常常会不知不觉地受到群体的压力,而在知觉、判断、信仰以及行为上表现出与群体中多数人一致的现象,这就是从众现象” ③。其实,“从众心理”未必是在一个人或一个群体的“压力”下才形成的,有时或常常是在一种“感染力”下所形成,或曰“熏陶”而成,而在规模越大的有组织犯罪或犯罪组织中,情况越是如此。显然,“从众心理”是一种归属心理。在我们看来,在一个松散的群体中,人们保持着粗疏的联结关系,这样的群体往往缺乏足够的向心力,而人们对于群体的依赖心理就比较微弱,从而降低了从众现象发生的机率。而在一个不缺乏行为榜样的群体中,如果人们之间形成相对稳定的较强的凝聚力,群体能为成员们提供道德观念的参照系,那么,这样的群体就很容易出现“从众”现象。可见,从众现象的产生及其强弱还与群体的规模有关,即群体规模越大,则越容易产生“从众”现象且“从众心理”较强。这个道理能够用来有力地说明有组织犯罪中的心理因素。与“从众心理”相对的是“众从心理”,是指“团体中由于多数人受到少数人意见的影响而改变原来的态度、立场和信念,转而采取与少数人一致的行为” ④。“众从心理”实际上也是一种归属心理,即“本能地在精力旺盛、信仰坚定的人中间寻找自己的主子,他们永远需要这种人物” ⑤。在我们看来,不是靠着“压力”而是靠着“感染力”所促成的“从众心理”和“众从心理”,在某种意义上又都可描绘为“魅力复制型心理”,而这种心理所导致的便将很可能是对某种邪恶的“坚定不移”甚或“视死如归”。在有组织犯罪中,“从众心理”和“众从心理”往往同时存在,而当心理迷茫的时候,“从众心理”和“众从心理”便容易获得活动机会,从而形成一种“召唤”或“凝聚”,而此“召唤”或“凝聚”既可形成在一个既有的犯罪组织内部,也可形成在一个既有的犯罪组织的内外之间,使得一个既有的犯罪组织具有对外开放性与吸纳性。可以想象,“从众心理”和“众从心理”在有组织犯罪或犯罪组织对社会构成的危害或威胁中的作用和分量,因为“观念通过不同的方式,终于深入到群体的头脑之中并且产生了一系列效果时,和它对抗是徒劳的。……让观念在群体的头脑里扎根需要很长时间,而根除它们所需要的时间也短不了多少” ⑥。研究有组织犯罪中的“从众心理”和“众从心理”,有助于我们考察犯罪组织的形成和有组织犯罪的实施,从而有助于我们在有组织犯罪中从主观方面来把握有组织犯罪或犯罪组织中的成员的地位及其作用,从而便于在对照刑事政策和刑法规范中公平合理地落实刑事责任。
就经济学研究方法而言,无论是有组织犯罪的成员,还是有组织犯罪的犯罪组织本身,都有一个利益得失的权衡问题,当然在利益权衡的过程中也会受到其他“非利益因素”的影响,如所谓纯粹的道德观念乃至“利他动机”,故经济学的方法在有组织犯罪研究中也能发挥其应有的和特别的作用,即一种“解释力”的作用。那么,对有组织犯罪能发挥更好“解释力”的经济学是一种什么样的经济学呢?答案是:行为经济学。标准经济学即新古典经济学假定人的行为是理性的、不动感情的、自私的、追求自身效用最大化的,即将在精于“计算”中创造性地实现利益最大化视为一切经济分析的基础,从而认为所有非理性的行为皆不存在。而行为经济学却认为人的行为所追求的远不止于此,人们还关注公平、互惠和社会地位等许多其它方面,即认为经济行为的产生既有经济因素,也有非经济因素。标准经济学所提出的人的无限理性、无限控制力和无限自利性,在行为经济学这里受到拒斥,从而导致行为经济学促成经济学的传统力学研究范式向以生命为中心的非线性复杂范式的转换,即在现实中关注个体的“个性”追求。 ①行为经济学不是区别于新古典经济学的边缘学派或颠覆性理论,而是以新古典理论为基础的西方主流经济学的最新前沿理论。行为经济学突破了新古典经济学对经济人的“外在假设强加”即“经济理性强加”,而把目光转向经济人的个体动机,并用心理学包括行为心理学和认知心理学予以说明。
在行为经济学的视野下,即便是在纯粹以经济目的而存在的有组织犯罪中,其组织成员甚至包括被我们称之为“领导者”、“策划者”的那些成员也并非“完全理性人”,亦即他们身上会多多少少存在着“非理性因素”包括具有异质性的个体动机,而此个体动机甚至包含着“利他因素”。当包括具有异质性的个体动机的“非理性因素”能够说明犯罪成员在实施有组织犯罪时的主观恶性大小或人身危险性的轻重,则其便能够影响个案中行为人非难可能性的大小和应受刑罚惩罚性的轻重,即影响到刑事责任的个案认定以及个别预防的斟酌,从而影响着刑法规范乃至刑事政策的个案落实。如在某个有组织犯罪中,某组织成员是出于对“欠债不还”的心中不平而参与实施非法拘禁债务人的行为,或出于对“贪污贿赂”的心中不满而参与实施对作为公务员的被害人的敲诈勒索等。相反的例子,如在某个有组织犯罪中,某组织成员是出于对行使民主权利的控告人、申诉人、批评人、举报人的心中不满而参与实施非法拘禁或敲诈勒索等犯罪行为。在有组织犯罪的组织成员身上的“非理性因素”相对于“理性因素”而言,两者的关系似乎类似于政治经济学中的价格与价值的关系,而价格围绕价值上下波动似乎可以用来类比“非理性因素”所对应说明的主观恶性与人身危险性对刑责基准以及刑罚基准的影响以致于调整。
多学科交叉法使得有组织犯罪研究便是犯罪社会学、犯罪心理学和犯罪经济学等浑然一体的综合性研究。需要强调的是,在有组织犯罪研究过程中,并非只能运用社会学或心理学或经济学的某一分支理论,而是存在着多个分支理论并用或交错运用的可能,并且我们同时应关注相关学科的最新发展及其理论成果。当然,对有组织犯罪研究所采用的方法还可包括政治学等方法,甚至自然科学的成果也在研究方法的考虑之内。
四、有组织犯罪研究的意义导向
对某项研究的意义不甚明了,或虽有认识但“目光短浅”,这不仅将直接决定该项研究的价值高低,也将直接决定该项研究的“品味”与“境界”,所谓“取乎其上得乎其中,取乎其中得乎其下”是也。对有组织犯罪研究意义的把握,道理依然如此。
有组织犯罪研究必须注重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的重要意义,这是检验有组织犯罪研究是否取得进展乃至实现创新的一个极其重要的指标,也是有组织犯罪研究取得进展乃至实现创新的最为直接的证明。有组织犯罪研究的理论意义至少应该体现在犯罪学和刑法学两个层面,且以给犯罪学和刑法学以崭新的命题为实质性的“交代”,并且是在有组织犯罪所对应的层面上给出这种“交代”。因为正如现有的有组织犯罪研究的“成果”所整体表明的那样,有组织犯罪被作出了宽窄不同的各种界定而导致有组织犯罪在名称转换之中变成了“其他犯罪”,从而有组织犯罪被作了“偷换论题式”的对待,以致于最终在实质上导致“煞有其事”的有组织犯罪研究在相当程度上变成了一种“空谈”,即有组织犯罪研究变成了“其他犯罪研究”。实际上,如果只是对共同犯罪或团伙犯罪或集团犯罪甚或黑社会犯罪作出某种或某些哪怕就是“有新意”的突破或展开,也体现不了有组织犯罪研究的理论意义所在。也就是说,在有组织犯罪研究中,我们应避免将有组织犯罪研究在“自言自语”中降格为共同犯罪研究或团伙犯罪研究或集团犯罪研究或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研究。易言之,无论是在犯罪学中,还是在刑法学中,有组织犯罪研究应力求做到“有名有实”,即具有一种“实在的”,从而“完整的”和“独立的”理论品格,或曰构成一种能够自成一块的刑事法“理论实体”。
与理论意义相对应,有组织犯罪研究应给予刑事立法和刑事政策以直接的或有力的影响,这是有组织犯罪研究的实践意义所在。有组织犯罪研究对刑事立法的影响包括对刑事实体法即刑法的影响和对刑事诉讼法的影响。“凡事皆有可能”,当刑法分则对有组织犯罪的定罪量刑作出了“特别规定”,或者是在“连动”着黑社会性质组织的犯罪中被作出了定罪量刑的规定,则我们有理由为有组织犯罪研究的“实践成就”而“沾沾自喜”。又当刑法总则对有组织犯罪的定罪量刑作出了“特别规定”,或者是在“连动”着共同犯罪乃至单位犯罪中被作出了定罪量刑的规定,则我们便有理由为有组织犯罪研究的“实践成就”而“喜不自禁”。而当刑事诉讼法对有组织犯罪作出了就强制措施和审理程序的“特别规定”,当然是有利于更好地治理有组织犯罪的“特别规定”,正如司法实践部门早就发出的关于贪污贿赂犯罪的诉讼程序的“特别规定”的呼声,则我们便更有理由为有组织犯罪研究的“实践成就”而“喜出望外”。特别是,当我们的刑事政策终于将有组织犯罪作为一种“特色内容”,则我们便有理由为有组织犯罪研究的“实践成就”而“孤芳自赏”了。“首恶者必办,胁从者不问”,曾经是我们的一项刑事政策。但有组织犯罪的深入研究告诉我们,在有组织犯罪中,在“首恶者”与“胁从者”之间还有诸如“大恶者”和“一般恶者”等“中间类型”的人物或角色,则“首恶者必办,胁从者不问”的刑事政策就应作相应的调整,并体现出刑事法治的应有谦抑性,如“胁从者不问,恶者宽办,大恶者必办,首恶者重办”。最后,当有组织犯罪研究能够对刑法、刑事诉讼法乃至刑事政策都能给出一些有理有据且切实可行的“建设性”完善建议,即拿出具有“规范建设性”和“政策建设性”的研究成果,则一部独立的单行法即《有组织犯罪法》的出台也并非没有可能。
以上对有组织犯罪研究意义的展望,虽显“飘渺”但非“渺茫”,因为此展望将为有组织犯罪研究“指示”一种目标或方向,而此目标或方向又能够转化为有组织犯罪的强大理论动力或“理论动机”。将有组织犯罪研究仅仅作为一种小小的“战斗”对待和作为一种颇具规模的甚或气势恢宏的“战役”对待,其斩获有天壤之别。而对有组织犯罪研究在理论和实践两个层面上更高更远的意义把握,将使我们走出对有组织犯罪研究的一种“小家子气”。试想,从问题导向到学科导向到方法导向再到意义导向,我们既讲“战术”,也讲“战略”,则有组织犯罪研究不是在真正着手之前便已进入一种有着特殊意义的“有组织”了吗?而此种有着特殊意义的“有组织”或许将使得有组织犯罪研究已经“事半功倍”并且“高瞻远瞩”了。由此而论,我们不要忽视有组织犯罪研究的意义导向问题,因为在此意义导向问题里面潜藏着有组织犯罪研究的目标和方向、品味和境界、动力和斩获。
五、结语
本文所提出的有组织犯罪研究的四个导向并非杂乱堆砌或机械排列,而是有着一定的内在关联,并呈现出一种层层递进的关系。具言之,问题导向指明的是有组织犯罪研究的“逻辑起点”,学科导向指明的是有组织犯罪研究的“方位落定”,方法导向指明的是有组织犯罪研究的“铺陈技术”,而意义导向所指明的则是有组织犯罪研究的“精神指引”或“目标召唤”。于是,有组织犯罪研究的四个导向便交代了从哪里开始研究,如何展开研究,奔向何处研究。可见,本文虽非有组织犯罪研究的盘盘盏盏皆“干货”的“本体论”,但或许对有组织犯罪研究能够起到一点“总体规划”的作用。于是,我们期待着有组织犯罪研究在理论和实践两个层面都能呈现出较为完整的而非“支离破碎”的新气象!
The Research on the Organised Crime:
a Kind of Project Overstepping Concrete Styles
Wan Guo-hai Ma Rong-chun
Abstract:If we believed the organised crime as a general concept,the research on the organised crime should not be lowered to the research on the crimes that exist as subordinate concepts,such as group crimes,underworld organisation crimes. If the attempts are made to make progress on norm construction and policy construction,starting research location of the research on organised crime in criminology is of great importance. In order to gain obvious research efficiency in organised crime,it is rather necessary for us to use crossdiscipline method of integrating sociology,psychology and economics,which can be used simultaneously and at staggered times. Meanwhile,we should pay attention to their newest development. The mastery of the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significance will give s obviously strong spiritual guidance and goal- orientation to organisationcrime research The best symbol of the results of the research on organised crime would be the Enactment of Organised Crime Law.
Keywords:the Organised crime;Criminology;Criminal Integration;Criminal Policy
(责任编辑:钱叶六)
李洁:《打击有组织犯罪法律适用中的难点及其消解途径》,载《国家检察官学院学报》2009年第6期。
李洁:《打击有组织犯罪法律适用中的难点及其消解途径》,载《国家检察官学院学报》2009年第6期。
[意]菲利:《实证派犯罪学》,郭建安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24页。
[意]菲利:《实证派犯罪学》,郭建安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6页。
陈兴良:《刑法哲学》(修订版),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100- 128页。
白建军:《罪刑均衡实证研究》,法律出版社2004年版,第67- 72页。
马荣春:《罪刑关系论》,中国检察出版社2006年版,第27- 29页。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183页。
蔡道通:《刑事法治的基本立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72- 74页。
李洁:《打击有组织犯罪法律适用中的难点及其消解途径》,载《国家检察官学院学报》2009年第6期。
[美]阿伦森:《社会心理学入门》,郑曰昌等译,群众出版社1985年版,第22页。
孙时进:《社会心理学》,复旦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201页。
时蓉华:《新编社会心理学概论》,东方出版社1998年版,第340页。
[法]古斯塔夫·勒庞:《乌合之众——大众心理研究》,冯克利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5年版,第166页。
[法]古斯塔夫·勒庞:《乌合之众——大众心理研究》,冯克利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5年版,第46页。
黄祖辉、胡豹:《经济学的新分支:行为经济学研究综述》,载《浙江社会科学》2003年第2期。
——许春金先生
——张荆先生
——张荆先生
——张黎群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