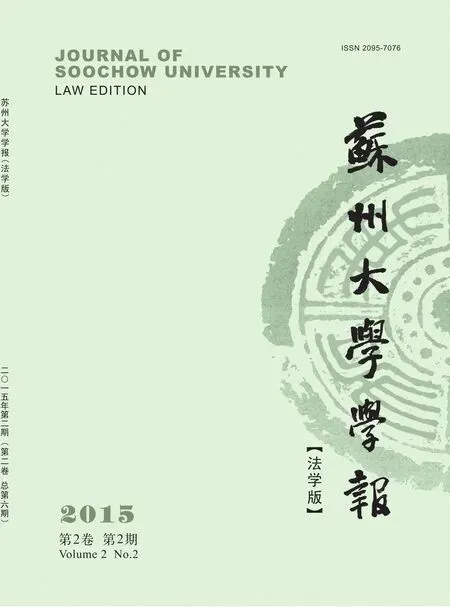网络开放平台侵犯著作权问题辨析:以“腾讯协议”为样本
*上海交通大学凯原法学院博士后,中央民族大学法学院副教授。
本文系作者主持的“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面上资助”(项目编号:2013M531159)、“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特别资助”(项目编号:2014T70412)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内容摘要:开放平台是云计算环境下为满足网络用户个性化需求而产生的一种全新技术手段和商业模式,为此带来的知识产权问题值得关注与应对。平台服务提供者为第三方应用开发商及用户提供信息传播的技术支持和便利条件,其并没有跳出现有法律规范对网络服务提供者的主体范围界定。区分直接侵权与间接侵权的关键并非过错与否,而是导致损害结果的原因力大小或因果关系。平台服务提供者承担何种间接侵权责任,应依照引诱侵权、替代侵权及帮助侵权的构成要件作具体分析,我国现行规则在此方面的不足和缺陷是导致司法裁判不统一的主要原因,可参考国外相应做法修改完善。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7076(2015)02-0102-09
在互联网飞速发展的今天,为满足用户不断变化的需求,一种新的技术手段和营销策略——开放平台(Open Platform)应运而生。所谓开放平台,指一种以云计算为技术基础的网络服务模式,即所谓的“平台即服务”。 ①面对网络中数以百万计的形形色色的个性化需求,单凭一家公司自身的力量显然力不从心,开放平台则把网站的服务封装成一系列计算机易识别的应用程序编程接口(API)或函数开放出去,供第三方应用开发者使用,由此增加系统的功能。在开放平台中,平台服务提供者提供硬件、软件、操作系统、软件升级、安全及应用程序托管等服务,第三方应用开发者则可以运用和组装平台接口,不断开发出新的应用,并在平台上运营。 ②简言之,开放平台凝聚了众人的智慧,大大降低了信息传递成本,提高了创新效率,满足了用户个性化需求,代表了互联网发展的新趋势。然而,开放平台甫一推出,就面临诸多法律困扰,如信息利用、用户权益保护、产权归属等,而知识产权无疑是其中一大难题。在开放平台中,第三方应用开发者可能复制、使用未经知识产权人许可的作品、技术方案、商标或外观设计,网络用户也可能借助平台传播、分享涉嫌侵权材料。此时,平台服务提供者将承担什么样的法律责任,就值得深入研究。笔者谨以《腾讯开放平台开发者协议》 ①(以下简称《腾讯协议》)为例证,以平台服务提供者涉及的最典型侵犯知识产权类型——著作权为切入点,结合我国和国外相关法律规定和近期司法实践,对开放平台中可能涉及的知识产权问题展开探索性的思考,以求抛砖引玉。
一、平台服务提供者的法律地位
开放平台是一个互联网及IT技术领域的新名词,但这并不影响通过分析和归纳相关主体的行为性质来确立其法律上的地位。如前文所述,开放平台涉及平台服务提供者、第三方应用开发者、网络用户及著作权人等四方主体,其中最关键的便是如何界定平台服务提供者的内涵,为此就有必要探讨现有的法律概念——网络服务提供者(Internet Service Providers,ISP)能否涵盖平台服务提供者这一问题。
(一)网络服务提供者的界定
首先,应明确ISP的含义及范围。ISP与网络内容提供者(Internet Content Providers,ICP)有着显著差异。ICP指信息内容由自己复制、选择、编辑,并通过网络向他人提供、传播,因此可能构成所谓的直接侵权;而ISP不直接提供信息内容,其系统中的信息内容是由其用户产生和提供的(usergenerated),ISP仅仅为这些信息内容的存储、接入、搜索、链接、传播和分享等提供技术支持与便利条件。如果ISP就其用户利用此便利而产生的直接侵权行为存在主观过错(明知或应知),则可能承担所谓的间接侵权责任。可见一方面,ISP的范围足够宽泛,可以容纳提供网络设施服务、提供接入服务、提供主机服务、提供社交通信服务、提供搜索链接服务等各类信息技术和商业模式,但这些类型又共有一个实质性内涵,即仅提供服务,不提供内容!
我国无论是2006年颁行的《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条例》(以下简称《条例》)、还是经两次修改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计算机网络著作权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解释一》)抑或2010年颁行的《侵权责任法》都没有给出ISP的确切定义。《条例》只是列举了“提供信息存储空间”、“提供搜索、链接服务”、“提供自动接入服务”、“提供自动传输服务”和“提供自动缓存服务”等几类ISP,并规定“未选择或未改变服务对象所提供的作品、表演、录音录像制品的,不承担赔偿责任” ②。《解释一》甚至将提供内容服务也作为ISP的一种类型。 ③但“提供内容服务”是个令人困惑的概念。正如前文所言,提供“内容”与提供“服务”是相对应的,ISP显然不提供内容,而仅仅为用户所选定的内容提供传输、存储或搜索等便利服务。遗憾的是,于2013年1月1日开始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侵害信息网络传播权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以下简称《解释二》)第3条仍然坚持了ISP可以包括“通过信息网络提供权利人享有信息网络传播权的作品、表演、录音录像制品”这一类型,概念混淆带来的负面效果可能在所难免。
(二)平台服务提供者属于ISP
作为一个抽象的法律概念,ISP涵盖了多种不同技术类型的主体。《条例》将ISP分为四类——即自动接入网络服务提供者、自动缓存网络服务提供者、信息存储网络服务提供者和搜索链接网络服务提供者,并分别规定了免于承担赔偿责任的不同情形。基于开放平台的技术特点和商业模式,有学者结合国际国内比较典型的开放平台(如亚马逊、微软、腾讯、百度)在实践中扮演的角色得出,平台服务提供者并没有突破目前著作权法特别是信息网络传播权制度的规则体系,仍然扮演着单纯的提供网络技术服务的角色: ①即(1)提供信息存储服务;(2)提供搜索链接服务;(3)提供数据传输服务。
可见,平台服务提供者本质上仍然属于ISP,即通过提供信息网络服务,使得用户可以向互联网提供信息或者从互联网获取信息,其仅为这些信息内容的存储、接入、搜索、链接、传播和分享等提供技术支持与便利条件。
二、平台服务提供者是否构成直接侵权
应该说,“直接侵权/间接侵权”这一对用语并不是我国法律规范中的现有概念,而是由美国司法判例创造并成文化,进而通过学说继受引入到我国相关研究之中。有学者认为,在著作权领域,是否以过错为要件以及行为本身是否应受权利人控制是区分直接侵权与间接侵权的界线。 ②笔者对此不敢苟同。在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索尼案 ③中,美国联邦最高法院认为,被告免遭直接侵权之诉乃是因为其对信息内容的自动复制属于非自愿(non- volitional)行为。在后来的CoStar案 ④中,联邦第四巡回上诉法院以索尼案为引证,强调“意愿(volition)”是判定直接侵权的重要要件。尽管著作权法并不要求侵权人知道他正在实施侵权或蓄意破坏著作权人的利益,但却要求侵权行为必须是以某种有意义的方式作出的(it nonetheless requires conduct by a person who causes in some meaningful way an infringement)。 ⑤依照《布莱克法律词典》(2004年第8版)的界定,volition指能够做出某一选择或决定的能力。可见,虽然美国著作权法没有明确把主观过错作为承担损害赔偿责任的要件,却通过在客观行为中掺入“意愿”要件间接承认了行为人的自主选择是其承担责任的必要前提。不仅如此,有学者还对美国现行著作权法中所谓的严格责任提出了质疑,认为这不符合著作权法的历史。 ⑥而我国的著作权法及相关民事立法并没有将“无过错”作为侵犯著作权的归责原则,而《侵权责任法》更明确规定,无过错原则仅适用于法律明文规定的情形,如产品责任、环境污染、高度危险等。
既然过错与否不是划定直接侵权与间接侵权的界线,那又该如何区分两者呢?我们还是要回到创造了这对概念的美国判例上来。在著名的Netcom案 ⑦中,上诉法院认为:“虽然著作权法规定了严格责任,但在本案中,被告的系统只是被第三方用于制作复制件,(为认定承担责任所需的)意愿要件和因果关系要件并未得到满足。” ⑧可见,既然“过错”(判例将其表述为“意愿”)不是区分直接侵权与间接侵权的要件,那剩下的就只有“因果关系”要件了。实际上,传统民法理论同样给出了共同侵权人承担连带责任的根源——原因力或相当因果关系,如史尚宽先生指出,帮助侵权之所以构成共同侵权,是因为“各自之违法行为关联共同为损害之原因或条件” ⑨。也就是说,在“帮助型”共同侵权中,被帮助者实施了最终的侵权行为,是导致损害发生的直接原因,而帮助者则仅仅为其实施侵权提供工具、手段或其他便利,在原因力或因果关系上是间接的,但又是不可忽略、不可原谅的。因此,辨别直接侵权与间接侵权的界线只有一个——原因力之大小。
《解释二》对区分直接侵权与间接侵权做了最好注解,其第4条规定:“有证据证明网络服务提供者与他人以分工合作等方式共同提供作品、表演、录音录像制品,构成共同侵权行为的,人民法院应当判令其承担连带责任。网络服务提供者能够证明其仅提供自动接入、自动传输、信息存储空间、搜索、链接、文件分享技术等网络服务,主张其不构成共同侵权行为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可见,最高人民法院将“共同侵权行为”做了最狭义上的界定——即“共同提供作品、表演、录音录像制品”的行为,而仅为上述信息内容的传播提供媒介、空间或其他便利的不属于“共同侵权行为”。所谓“提供信息内容行为”就成了具有分水岭意义的关键词,对此,《解释二》第3条第2款加以了明确:“通过上传到网络服务器、设置共享文件或者利用文件分享软件等方式,将作品、表演、录音录像制品置于信息网络中,使公众能够在个人选定的时间和地点以下载、浏览或者其他方式获得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其实施了前款规定的提供行为。”由此可见,《解释二》与美国DMCA的做法是一致的,即判断“提供信息内容行为”的关键在于确定此信息内容是由谁主动、自愿地将其置于网络系统之中。
正如前文所述,由于平台服务提供者属于ISP的一种类型,其涉嫌侵权材料是由第三方应用开发者或网络用户主动上传、复制、使用或传播,平台服务提供者仅仅是为侵权材料的传播提供了媒介、空间或其他便利,且没有对其收到或发送的材料之内容加以改动,在原因力上是间接的,故不可能承担直接侵权责任。这种业务模式从根本上说是为了被“广泛应用于合法的、不受争议的用途”,是一种中立性的技术服务。恰如 《世界版权公约》第 8条的议定声明中所指出的:“不言而喻,仅仅为促成或进行传播提供实物设施不致构成本条约或《伯尔尼公约》意义下的传播。”
三、平台服务提供者的间接侵权责任
一般而言,间接侵权包括三种情形,即引诱侵权、替代侵权和帮助侵权。笔者分别就这三种情形的构成要件,分析平台服务提供者可能面临的侵权风险。
(一)引诱侵权
引诱侵权是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在著名的Grokster案 ①中创立的概念,其有两个构成要件:第一,行为人主观上有希望或纵容他人实施侵权的故意;第二,行为人客观上有积极诱导、鼓励他人实施侵权的行为。就平台服务提供者而言,很难从常态中推出其满足这两个要件。相反,《腾讯协议》中腾讯强调自己是“中立的平台服务提供者”,“因用户使用应用产生的任何问题、责任等,由开发者单独向用户负责并承担一切责任,与腾讯无关”; ②开发者的应用程序,或者由用户使用应用服务产生的内容,如果违反法律法规,损害他人权益“引起的纠纷、赔偿责任等一概由开发者自行承担”。 ③除此之外,为防范法律风险,腾讯还设立了“通知—删除程序”。 ④
但腾讯开放平台是否真正“中立”呢?笔者注意到《腾讯协议》直接将推广规定为开放平台服务的组成部分。腾讯提供有所谓的“广点通服务”,通过“QQ 空间”、“朋友”(pengyou.com)等推广资源平台,向其用户推荐第三方开发之应用。 ⑤不过,这种推广并不能被视为是积极诱导、鼓励第三方实施侵权,因为并非所有应用都包含侵权内容,创造开放平台的初衷也只是为了促进信息的获取与传递、降低搜索与交易的成本,故具有“实质非侵权用途”。 ⑥因此,很难就此得出腾讯具有引诱侵权的主观意图和客观行为。
(二)替代侵权
著作权法中的替代侵权源自一般侵权法中的监管者责任,如在Dreamland案中,法院认为舞厅老板对他人在其舞厅进行涉嫌侵权的表演负有责任。 ①后来,美国法院通过一系列判例延续了这一概念。 ②故此,替代侵权具有两个构成要件:其一,对侵权行为有监督和控制的权利和能力;其二,从侵权行为中获得直接经济利益。笔者注意到《腾讯协议》约定:开发者在应用发布前,需要向腾讯提交能够证明自己对应用享有版权或同等权利的证明材料和经营资质证明。 ③而且,在发布应用、相关信息、内容及对其进行编辑、修改和更新之前,开发者都必须经过腾讯的“确认”。 ④如果发现违法行为或侵权行为,腾讯可以根据自己的判断,随时单方面地删除任何有关信息和内容,甚至于终止提供平台服务,并可以惩处第三方开发者。 ⑤
从这些约定能否推出腾讯具有监控的能力和权利呢?笔者认为这值得思考。首先,这些约定是腾讯为了避免遭受侵权指控的事先防御措施,对第三方开发者起到一种警示和威慑作用,很难说现实中腾讯能够对第三方开发者发布的所有信息内容进行没有遗漏地审查。其次,即使腾讯能够做到没有遗漏的审查,那也是因为开放平台是一个新鲜事物,打算或能够在开放平台上发布应用的开发者目前为数不多,腾讯因此能够做出事先及同步监控。这就好比上述“舞厅案”一样,舞厅的容量毕竟有限,舞厅老板能够做到随时监控。但开放平台毕竟不是舞厅,一旦技术成熟,且获得广泛认知后,网络的扩散效应是无法比拟的。此时,腾讯便很难做到事先及同步监控。最后,替代侵权中的“监督和控制的能力和权利”是立法者的认定,而非当事人的约定,这里面有价值考量的因素。也就是说,当一种新技术出现时,立法者是应该将其扼杀在摇篮里还是让其有一定的发展空间,然后再评判其对权利人的损害程度,这需要深入思考。著作权法的历史告诉我们,无论是立法还是司法,对传播技术的革新都保持了一种谦抑态度,从而大大推动了社会的进步。在对待ISP侵犯著作权问题上,世界各国的立法共识是:ISP不承担事先的监管和审查义务。如美国DMCA规定,“除非是为了符合标准技术措施的要求,任何避风港都不得解释为要求ISP对其服务进行监督,或者主动搜寻侵权活动的线索” ⑥。欧盟指令则规定,成员国不得要求ISP承担审查传输存储信息以及主动搜寻侵权活动的一般义务。 ⑦因此,笔者认为不应当匆忙认定腾讯具有事先监控的能力和权利。
至于第二个构成要件——从侵权行为中获得直接经济利益,从《腾讯协议》和腾讯目前的实际操作来看,腾讯的确从应用开发者那里获得了直接的经济利益。如作为开放平台推广服务的回报,第三方开发者需要向腾讯支付平台服务费。 ⑧但我们很难就此认定腾讯的这些收入是直接来自应用开发者的侵权所得。如果腾讯真正做到了协议中提及的事先及同步审查、监管的话,就更明确否定了这一推论。退一步讲,即使著作权人有充分的证据证明腾讯确实从应用开发者的侵权所得中获得了直接的经济利益,且腾讯目前也有能力和权利监控实施该侵权行为的应用开发者,符合美国法中的替代侵权构成要件,却很难在中国法中找到裁判依据。因为不论是我国《著作权法》还是《民法通则》,都找不到“替代责任”这一用语,即使《侵权责任法》的第32条(监护人责任)、第34条(用人单位责任)及第35条(接受劳务者责任)在一些学者看来属于“替代责任”而非“自己责任”,但法律显然没有将ISP间接侵犯著作权归入“替代责任”。
《条例》首次引入“替代责任”,其第22条列举了提供信息存储空间的ISP不承担损害赔偿责任的五项条件,其中包括“未从服务对象提供作品、表演、录音录像制品中直接获得经济利益”。《条例》如此规定不但有越权造法的嫌疑,更可能因欠缺“有权利和能力控制侵权行为”这一前提的限制,而导致“直接获利”概念被司法实践任意解释乃至滥用,陷ISP于不公之境地。据笔者了解,目前不少法院的态度是,只要ISP从其用户处获取了直接的经济利益,而不论是否“有权利和能力监控侵权行为”,都必须承担损害赔偿责任。如在不久前审理的“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有限公司诉苹果电子产品商贸(北京)有限公司和苹果公司侵犯著作权纠纷”一案 ①中,法院认定苹果公司从第三方开发商收取的费用有两个来源:一是提供开发工具、测试环境等的技术服务费;二是第三方开发商所获收益的分成,并认为这两者均构成《条例》中所列的“直接获利”要件,故应承担共同侵害之责任。笔者对此观点不敢苟同。首先,平台服务提供者为第三方开发商提供一定的软件开发工具和测试环境,只是为了保证开放平台的安全性、稳定性和高效性,而无法推定平台方直接参与了涉嫌侵权软件的开发和运行。毕竟技术服务是一般性的、中立性的,世界各国的立法也都没有把“收取技术服务费”作为“从侵权中直接获利”的方式。其次,从应用开发商的收益中分成也不能据此推定平台服务提供者知晓并参与了侵权行为。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开放平台以营利为目的才得以存在。作为提供“信息存储空间”服务的ISP,苹果公司显然可以与第三方应用开发商通过协议约定技术上的支持和利益上的分配,从中无法解读出苹果公司明知或应知第三方应用开发商意欲或正在实施侵权,更无法解读出其“有权利和能力控制”第三方的侵权行为。虽然苹果公司可能基于协议事先了解到第三方应用的部分内容,但很难说现实中苹果公司能够对第三方发布的所有信息内容进行事先的一一审查。据笔者了解,中国目前绝大多数平台服务提供者对于第三方应用开发者只能做到主体资格审查、权利登记证书等形式审查,很难做到权利归属、侵权与否的实质审查。在此问题上,DMCA第512条(m)款明确排除了法院对第512条的任何款项作如下解释:ISP应履行积极义务来监管其服务以发现侵权活动,才能获得“避风港”的保护。 ②可见,在“通知—删除”制度架构下,DMCA将识别侵权者的责任分配给了著作权人。 ③这一规定无疑为美国传播技术的革新和网络产业的发展提供了必要的法律环境。
在法律移植和学说继受的影响下,我国不久前出台的《解释二》第8条第2款也委婉地指明,ISP“未对网络用户侵害信息网络传播权的行为主动进行审查的,人民法院不应据此认定其具有过错”,也便不构成侵权。第11条进一步规定,ISP从网络用户侵权行为中直接获利的,仅仅是“负有较高的注意义务”,而不能当然推定其事先已经知悉并有能力控制用户的侵权行为。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这里的“有权利和能力控制”不能理解为ISP在收到著作权人的通知后,能及时发现涉嫌侵权者并移除涉嫌侵权材料,而只能理解为有“事先”监控的权利和能力,因为ISP之所以能够引入避风港免责,就是因其在通常情况下无法事先知晓和控制其系统或网络上由他人提供的海量信息,如果仅仅因为ISP从他人侵权行为中获取了直接的经济利益这一单一因素而要求其承担损害赔偿责任,而不考虑其是否有权利和能力事先控制此侵权行为,是否有对侵权行为“坐视不管”等其他因素,则避风港将演变为不折不扣的“风暴角”,与立法宗旨背道而驰。在2012年美国著名的Viacom v. YouTube案 ①中,联邦第二巡回上诉法院强调,“有权利和能力控制指ISP能够移除或阻止其网络中的侵权材料之外的其它东西(something more)。” ②这里的“其它东西”究竟意指何物,法院并未言明,但又引证了Perfect 10 v. Cybernet Ventures案的裁判意见。在该案中,美国加州中区地方法院认为:如果ISP对网络用户上传至其系统中的材料进行了事先的预审,以评估这些材料是否满足其特定的布局、外观和内容等要求,即可以判定ISP有权利和能力控制。 ③联邦第二巡回上诉法院借此提示说,如果ISP明知其网络用户的具体侵权行为,且对此行为施加了不必要乃至频繁的实质性影响,则可以判定ISP有权利和能力控制。 ④相比而言,中国上述“大百科全书案”中法院对苹果公司是否“通过事先的审查和监督,已知或应知第三方应用开发商正着手实施侵权”这一重要事实缺乏充分的表述与论证,而直接基于其在分销中获利这一片面因素而认定其应承担责任,难以令人信服。
(三)帮助侵权
帮助侵权也有两个构成要件:其一,知道或理应知道他人正在或着手实施侵权行为;其二,为他人侵权提供了必要的设备、工具或其他便利。 ⑤应该说,帮助侵权最难分析的便是第一个构成要件,特别是何谓“理应知道”,这是判断平台服务提供者有无过错,进而可否援用“避风港”免责的关键。对此,欧盟的态度是,虽然ISP不承担事先主动审查和搜寻侵权活动义务,但又规定,成员国可以根据自己的国内法,要求ISP为了监督和防止某种特定的非法活动承担合理注意义务。 ⑥至于“合理”的标准,则是留待欧盟各成员国通过各自的立法与司法来加以解释和发展的。而美国的DMCA则规定,ISP“没有明知侵权信息或侵权活动在网络系统中的存在,也不知道任何可以明显体现出侵权信息或侵权活动存在的事实情况” ⑦下,不属于对注意义务的违反。可见,如果相关信息仅仅达到了“可能侵权”程度,但没有达到“显而易见”或“一目了然”的程度,ISP仍可获得避风港的庇护。
就我国的法律规定而言,《侵权责任法》第36条第3款规定:“网络服务提供者知道网络用户利用其网络服务侵害他人民事权益,未采取必要措施的,与该网络用户承担连带责任。”这里的“知道”指“已然明知”还是“不知但理应知道”,确实较为模糊。而《条例》第22条第3款规定ISP为服务对象提供信息存储空间的免责条件之一是“不知道也没有合理的理由应当知道”服务对象提供的作品、表演、录音录像制品侵权的,第23条但书条款则明确规定:ISP为服务对象提供搜索或者链接服务时“明知或者应知”所链接的作品、表演、录音录像制品侵权的,应当承担共同侵权责任。所谓“明知”即实际知道,它包含两层含义:第一,直接且清楚地知悉某种事实或状况;第二,指知晓某种信息或情况,而该信息或情况会引起一般理性人对事实作进一步的探究或查询。 ⑧所谓“应知”,指推定知道,即对于某人基于合理的注意就能了解的事实,法律推定其应该且已经了解该事实,而不论其事实上是否知情。 ⑨不仅如此,推定知道也即赋予了被告相应的提供证据责任,以抗辩自己不知道,恰如研究者所言,“应当知道”属于推定故意,它是相对于现实故意而言的。现实故意是指有证据证明的故意,而推定故意是指没有证据能够直接证明,但根据一定的事实可以推定行为人具有某种故意,行为人如果否认自己具有此种故意,必须提出反证。 ①笔者认为,第22条的“知道”等同于第23条的“明知”;第22条的“有合理的理由应当知道”等同于第23条的“应知”。
《侵权责任法》与《条例》的表述不一导致了司法裁判的不统一,降低了法律的稳定性和可预期性。相比来说,对ISP主观状态的要求,《条例》比《侵权责任法》规定得更为科学合理,但即使是适用《条例》第23条的“应知”,然何谓“合理的注意义务”,法院的解释并不一致。如在“网络互联(北京)科技公司诉上海全土豆网络科技公司侵犯著作财产权案”中,有用户将原告享有著作权的作品上传至被告的网站,被告未能及时发现。一审法院认为被告“作为专门从事影视、娱乐等的视频分享网站,对用户上传至其网站上的影视作品应有更高的审查注意义务” ②。而二审法院则认为ISP在主观上是“未尽到一般注意义务的过失,而并非是未尽什么特别的更重的注意义务” ③。从法经济学的角度观之,所谓“合理”指“对以下两个方面给予同等的对待:一是他自己承担的加强预防的成本;二是其他人享受的,因预防措施的加强而使事故的发生率和严重性降低所带来的利益。如果他所承担的成本大于预防措施给别人带来的利益,那么他的行为就是不合理的” ④。因此笔者认为,一审法院判词中的“更高的审查注意义务”与前述“事先的审查义务”并无二致,必然抬高ISP 的监控成本,而这是与国际通行做法相违背的。
司法实践中,常见的一种情形是ISP对用户上传的信息内容进行了整理、分类或编辑,但是否能就此推定ISP已知或应知侵权行为呢?对此,不同法院的看法也不一致。在“广东中凯文化发展有限公司诉广东省深圳市腾讯计算机系统有限公司案”中,一审法院认为腾讯公司作为信息存储空间的ISP,每天面对存储空间的海量上传信息,要求其对每一个上传视频内容进行事先的版权审查,无论是技术上还是商业上都是不可行的,这将导致信息存储空间这项互联网新业务无法正常开展。腾讯公司在接到起诉状后已删除了相关内容,据此认定腾讯公司明知或应知用户上传的作品侵权,事实和法律依据不足。而二审法院却认为:
腾讯公司在其视频分享网站上设置了创造、娱乐、音乐、影视、游戏等栏目,此设置不仅便于注册用户分类上传内容,也便于腾讯公司审核注册用户上传的内容。腾讯公司作为专门从事影视、娱乐等视频分享网站的服务商,应当对用户上传的影视作品负更高的注意义务,但腾讯公司未尽其应有的审查注意义务,在主观上存在应知的过错。 ⑤
笔者认为,不能从ISP对其服务对象上传的信息内容进行了分类、整理而当然推定其已知或应知侵权活动的存在。正如前文所言,通过技术手段对海量信息进行自动化、格式化的分类、整理,仅仅是出于为用户上传、存储或检索相关信息提供便利,从而提升网络效能之目的,而并不一定是为了鼓励、引诱或帮助侵权活动。借由美国“索尼案”创造的“非实质侵权用途”标准来看,这些技术或商业模式具有一般性、中立性,即使通过了整理分类,这些信息也仍然可能是纷繁多样且时刻处在变动之中。因此,不能就此断然推定ISP已经知晓或理应知道其网络系统中存在涉嫌侵权内容。美国DMCA中的“红旗标准”指明,当有关他人实施侵权行为的事实和情况已经像一面色彩鲜艳的红旗在ISP面前公然飘扬,以至于处于相同情况下的理性人都能发现时,如果ISP采取鸵鸟政策,装作看不见侵权事实,则可以认定ISP至少应当知道侵权行为的存在。 ⑥换句话说,判定ISP“已知或应知”与否,并不在于从一般的、盖然的状态下推测出什么,而在于通过特定的、具体的、明显的事实足以断定ISP已然知晓侵权活动的存在。恰如学者所言:“权利人对于自己产品更了解,其更具有比较优势来识别所存在的侵权行为和产品。如果让网络服务提供者承担概括知道的侵权责任,其唯一的选择就是限制产品的出售,这无疑会损害消费者的选择。如果仅仅因概括知道侵权行为的存在就需要承担侵权责任,那么服务提供者将处于动辄得咎的境地,以至会抑制大量的合法交易,损害消费者利益。” ①可见,苛以ISP过高的注意义务,必将抑制其技术革新和开发新的商业模式,其结果可能是整个社会福利的下降。
结 语
开放平台虽然属于云计算环境下一种新的技术手段和商业模式,但其引发的侵犯著作权问题并没有超越现有法律规则的适用范围。通过对平台服务提供者为第三方应用开发者及网络用户提供信息内容传播的技术支持和便利条件这一行为属性的分析与归纳,不难看出其仍然属于ISP的某一类型,在涉嫌共同侵权的原因力上是间接的,也便不太可能承担所谓的“直接侵权”责任。当然,如果其满足引诱侵权、替代侵权或帮助侵权的具体构成要件,则应当承担“间接侵权”责任。在我国现有著作权立法文本中,ISP与ICP的概念混淆、“间接侵权是否属于共同侵权及是否承担连带责任”的不确定性、替代责任中欠缺“有监督和控制侵权的权利和能力”要件、帮助侵权中的“应当知道”的判定标准不一等诸多不足是导致困扰司法实践、威胁法制公平、效率、稳定和权威性的主要问题,理应及时加以澄清与修正,从而为中国互联网产业的健康有序发展铺平道路。
On the Copyright Infringement in Network Open Platform
——Take “Tencent Agreement” for Example
Xiong Wen-cong
Abstract:Open Platform is a new technology and business model to meet user’s personalized needs in the cloud computing environment. The problem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raised from open platform should be noticed and replied. By providing technical support and facilitated condition of information transmission for the third- party application developers and internet users,platform providers don’t go beyond the scope of ISP’s definition. The distinction between direct infringement and indirect infringement is not the subjective intention,but the causality. Platform providers’ tort liability should be based on the specific analyzation of inducement infringement elements,vicarious infringement elements,and contributory infringement elements. The weakness and deficiency of our country’s rules is the main reason causing the disunity of judicial judgment,and we should amend and improve that rules referring to the foreign approaches and provisions.
Keywords:open platform;copyright;ISP;indirect infringement
(责任编辑:李 杨)
根据美国国家标准和技术研究院(National Institute of Standards and Technology,NIST)权威研究,所谓“平台即服务”(Platform as a Service,PaaS)是指用户可以利用云服务提供者提供的平台,使用云服务提供者支持的语言和工具,开发应用程序,并将其部署到云服务提供者的云基础设施之上。用户不管理或控制此应用软件的底层基础设施,包括网络、服务器、操作系统或者存储,但是,用户可以控制所部署的软件以及软件运行的配置。
参见《2012中国互联网开放平台白皮书》第12 页,载http://open.qq.com/,2015年4月20日最后访问。
载腾讯开放平台:http://open.qq.com/,2015年4月20日最后访问。
参见《条例》第20条、第21条和第22条。
参见《解释一》第4条、第5条。
张钦坤:《云计算、开放平台与服务商版权责任》,载《电子知识产权》2012年第12期。
王迁:《〈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条例〉中“避风港”规则的效力》,载《法学》2010年第6期。
Sony Corp. of America v. Universal City Studios,Inc. 464 U.S. 417(1984).
CoStar Group,Inc. v. LoopNet,Inc.,373 F.3d 544(4th Cir. 2004).
Id,at 549.
Dane S. Ciolino,Erin A. Donelon,Questioning Strict Liability in Copyright,54 Rutgers L. Rev. 351(2012).
Religious Tech. Ctr. v. Netcom On- Line Commc’n. Servs.,907 F. Supp. 1361,(N.D. Cal. 1995).
Id,at 1368- 1370.
史尚宽:《债法总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73页。
Metro- Goldwyn- Mayer Studios,Inc. v. Grokster,Ltd.,545 U.S. 913(2005).
《腾讯协议》第2.6条。
《腾讯协议》第2.7.2条和第2.7.3条。
《腾讯协议》之附属规则6:腾讯开放平台侵权投诉反通知指引。
《腾讯协议》第4条。
美国索尼案创造的“技术中立”标准。
Dreamland Ball Room,Inc. v. Shapiro,Bernstein & Co.,36 F.2d 354,355(7th Cir. 1929).
Gershwin Publishing Corp. v. Columbia Artists Management,Inc. ,443 F. 2d 1159,at 1162(2d Cir. 1971);Polygram Intern. Pub.,Inc. v. Nevada /TIG,Inc.,855 F. Supp. 1314(D. Mass. 1984).
《腾讯协议》第5.2条。
《腾讯协议》第2.7.1条。
《腾讯协议》第2.7.2条。
See 17 U. S.C.§512(m).
See EU Directive on Electronic Commerce,Article 15.
新华网:《腾讯正式宣布提高开放平台分成,超十万开发者获益》,载http://news.xinhuanet.com/tech/2012- 01/06/c_121836167. htm,2015年4月20日最后访问。
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1)二中民初字第10500号。
17 U.S.C.A.§512(m).
See Perfect 10,Inc. v. CCBill,LLC,488 F. 3d 1102,1113(9th Cir.2007)(判决认为DMCA通知程序将监控侵权——识别潜在侵权材料和大量文件侵权——的责任分配给了著作权人,我们不愿将这一重要责任从著作权人转移给ISP)。
Viacom Int'l v. YouTube,Inc.,676 F.3d 19,(2d Cir. 2012).
Id. at 38.
213 F. Supp. 2d 1146,1173(C.D. Cal. 2002).
YouTube,676 F.3d at 38.
Gershwin Publishing Corp. v. Columbia Artists Management,Inc.,443 F. 2d 159(2d Cir. 1971).
See EU Directive on Electronic Commerce,Recital47 & 48.
See 17 U. S.C.§512(c)&(d).
参见薛波主编:《元照英美法词典》,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第26页。
参见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2008)朝民初字第21731号民事判决书。
陈兴良:《“应当知道”的刑法界说》,载《法学》2005年第7期。
参见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2008)浦民三(知)初字第440奶号民事判决书。
参见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2009)沪一中民五(知)终宇第19号民事判决书。
[美]罗伯特·考特、托马斯·尤伦:《法和经济学》,张军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495页。
叶若思、祝建军:《视频分享网站帮助侵犯著作权的认定》,载《科技与法律》2010年第2期。
See Melvile Nimmer & David Nimmer,Nimmer on Copyright,Mattew Bender & Company,Inc.,12B.04[A][1](2003).
曹阳:《知识产权间接侵权责任的主观要件分析》,载《知识产权》2012年第1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