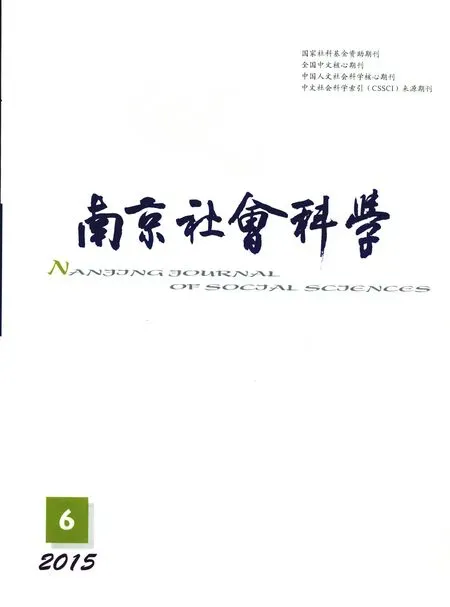“天人之辨”与先秦儒家生态审美思想研究*
吴承笃
“天人之辨”与先秦儒家生态审美思想研究*
吴承笃
“究天人之际”是中国传统哲学的基本问题,先秦儒家的代表人物从不同的角度针对“天人关系”展开了探讨。从孔子、孟子到荀子,在天人之间构筑了一条从“知天命”到“制天命”的发展路径,而生态审美观念则从追求个体与自然在精神上的共鸣,走向了通过社会化的仪式表达人与天和的审美情怀。
天人之辨;生态审美;孔子;孟子;荀子
“究天人之际”是中国传统哲学的基本问题,也是中国传统生态智慧重要的理论生发点。在对“天人关系”的体认中,中国古人以“天人和谐”为价值旨归,以“天人合一”为基本理念,形成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态观念。先秦儒家的代表人物从不同的角度针对“天人关系”展开了探讨,在天人之间构筑了一条从“知天命”到“制天命”的发展路径,展现出先秦时期儒家生态观念的内在发展理路。同时,在以“天人之辨”为基础形成的生态智慧背后,是先秦儒家的生态审美观,二者互为表里,是一体之两面。正如杜维明所言:“在儒家所塑造的学术传统中,美学、伦理学和讲天人相遇的超越的神学、形而上学,是一气贯穿的。”①从孔子、子思、孟子到荀子,“天人之辨”的哲学观念与生态审美思想始终相生相伴,厘清其内在关联与发展脉络,不仅有助于统观先秦儒家的生态审美思想,而且可以管窥儒家思想中一以贯之的生态观念。
一、“践仁知天”与孔子的生态审美观
先秦时期人们对于“天”的认识与态度不断地发生着变化。从巫觋、祭祀与礼乐的共同特征来看,夏商周三代均属于原始宗教时代,天人之间,或者说神界与人界是完全隔绝且截然不同的。神与人的沟通成为当时宗教观念中的关键性问题。在殷商时期,“帝”、“上帝”是流行的至上神的称谓,而这一观念又是从祖先神的观念中发展而来的。当时卜辞中虽有“天”字,但一般作“大”来理解。“在卜辞中,对于上天的称呼,只称‘帝'或‘上帝’,尚未发现称天的。‘天'字虽有,但‘天'字是作‘大'字用,不是指上天。”②到了西周时期,“帝”的观念逐渐被“天”所取代,这里的“天”依然是与人世间隔绝的至上神,是有位格性的意志神,但是与殷人的“上帝”观不同的是出现了“天命靡常”与“以德配天”的思想。“殷人‘宾帝’,所以先王在帝左右。……周王为天之子,故为配天。”③此时,人们对于天命开始产生了动摇与怀疑,相应地出现了对人自身的力量的觉悟和肯定。“天”虽然依旧保持着不可动摇的神圣性和神秘性,但是天人之间已不再是单向的和对立的。由于“天命靡常”,人与“天”的交往充满了变数,人可以而且必须介入到万物的生命流转之中,同时人又必须通过发挥自身的德行才能够“顺天”、“知天”,才能够保民而王,即“以德配天”。在这里包含着一个重要的问题,即“德”本身不是一个自足的概念,而是在配天的过程中出现的,具有感怀上天与顺从天命之义。在天人之辨中,何以“配天”成为人的德行确立的标准。这一思想对于儒家的影响至深,儒家所倡导的内圣与外王等核心思想都是从“配天”的过程中生发出来的,而这也是先秦儒家生态思想的根源。
孔子传承了周人的观念,在多处表达了对周人思想的尊重。在天人之辨中,孔子对于“天”的理解有继承的一面。如他认为“天”是有位格性的意志神,“获罪于天,无所祷也。”(《论语·八佾》)又如“天生德与予,桓魑其如予何?”(《论语·述而》),这里传达出的是“以德配天”的思想。而像“死生有命,富贵在天。”(论语·颜渊)等言论,则是对“天命靡常”思想的发展。对于“天”的态度则是敬畏。“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论语·季氏》)另一方面,孔子对于天人关系的理解又超越了周人的思想,体现出他作为儒家创始人的独创性和时代性。在对“天”的认知中,在原来的至上神之外又蕴含着或神秘或自然的客观力量的内涵。孔子融汇了春秋时期的自然天道观,强调突出宇宙自然的法则与规律。“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论语·阳货》)“天”具有了自然的意义,但却不仅仅是物质层面的自然,而是“形而上者”与“形而下者”的统一,是无形的天命与有形的自然界的统一,也隐含着人与自然统一的生态思想。对于天人的关系,孔子提出人要顺天敬天而行,这种敬畏是与人的主观能动性和理性精神合而为一的。他通过“仁”的观念将“天道”与“人道”相沟通,在体认天命的过程中突出了人自身的道德力量,认为人应该努力培育内在的道德精神以“立人极”而“赞天地之化育”。牟宗三指出,孔子“立仁教以辟精神领域,将‘疾敬德'以‘祈天永命'之王者受命之政规转而为‘践仁以知天'之个人进德之道范。”④在此,天的意义和价值发生了转移。周人的“以德配天”是由外而内的“降命”与“受命”,天尚在身外,而德是一种被动的体认和功利性的计算。孔子强调“与命与仁”(《论语·子罕》),将外在之天融入人的内心而成为“仁”的源泉,“仁”就是内在之天,“仁”的标准就在于人对天命领悟的能力与程度。孔子“仁”的观念张扬了人的主体性,但却没有走向主体的虚妄,而是强调人应主动应合天命的召唤。人与天的对立和紧张被化解了,人不必向外追求,“反身内求”就可以参悟天命,“天人合一”在人的内心得以实现。因此,“仁”对于“天”没有太多的功利诉求和现实的紧迫感,而是在“天”的指引下人必须承担的生命体验。
在孔子的思想中,人对于天命的追求和领悟,构建起了天人之间积极、亲和的关系,明确了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和合共生的生存态度,这正是生态精神的积极呈现。由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发展为人与自然的审美关系,这在孔子美学是一个必然的结论。“生态思想强调人与自然的和谐,倡导天地万物的共生共荣。”⑤天人相和的生态观念渗透在孔子的美学思想中,形成了以“敬天”、“法天”为基本理念,以“和”为最高境界的生态审美思想。
孔子通过“大”的范畴传达出对于“天”的敬畏与景仰之情。“大哉尧之为君也!巍巍乎,唯天为大,唯尧则之。”(《论语·泰伯》)孔子所说的“大”是融合了道德与审美的情感,是指主体对于对象产生的一种敬畏之情,并且伴随着一定程度的神秘感。虽然在这里孔子更多的是对尧时礼仪制度的赞美,但是这种赞美却是通过对“天”的效法而得出的,“则天”思想反映了孔子对于天道自然的崇敬,体现出敬畏自然的生态审美观。在《左传》中也有以“大”形容天地自然的记载,季札观乐时评论说:“德至矣哉,大矣!如天之无不帱也,如地之无不载也。”(《左传·襄公二十九年》)这里对“大”的理解与孔子是一致的,都反映出天地自然可敬可畏的道德属性与审美属性。对于具体的自然对象的欣赏,孔子通过“比德”的理论指出了人对自然的审美活动中积极主动的道德生成的特点,更加明确地表达出“法天”、“配天”的生态审美诉求。在“比德”中,主体作出了双重判断:对于自我是道德判断,对于自然对象是审美判断,相应地生成了道德感与美感,这两种情感在主体内心虽然性质不同但却是统一的。“智者乐水,仁者乐山;知者动,仁者静;知者乐,仁者寿。”(《论语·雍也》)这段话不仅说明了人的精神品质不同,对自然山水的喜爱也不同,而且通过“乐”字揭示了道德属性与具体的自然对象存在的内在沟通。自然山水是人的内在德行的源泉,人对于自然山水的欣赏可以转化为人自身精神品质的提升,审美的结果不是感官上的愉悦和满足,而是精神上的共鸣、思想上的升华。孔子多次表达过相同的观点。如“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论语·为政》)“岁寒而后知松柏之后凋也。”(《论语·子罕》)等言论,同样是把自然现象内化为人的精神品质,在自然审美中得到精神的愉悦。
“知天”、“法天”的最高境界是自然与人文的融合无间,也是孔子追求的生命境界。孔子借曾点之口描述了这种天人相和的境界。“暮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夫子喟然叹曰,吾与点也。”(《论语·先进》)朱熹评注说:“曾点之学,盖有以见夫人欲尽处,天理流行,随处充满,无稍欠缺。故其动静之际,从容如此。而言其志,则又不过即其所居之位,乐其日用之常,初无舍己无为人之意。而其胸次悠然,直与天地万物,上下同流,各得其所之妙,隐然自见于言外。”⑥朱熹以与天地万物同一来解释这段话,的确切中了孔子所追求的天人相和的审美境界,但是以人欲和天理的对立来解释却并非孔子对于天人关系的理解。朱熹将天地万物都划归天理之中,以永恒的形而上之“理”来决定个别事物是其所是的本性,这是典型的宋明理学的思想。在孔子的思想中,“仁”不是形而上的存在,甚至没有明确的概念界定。天人相和是求“仁”的必由之路,对于“仁”的体认,需要人在实践中主动地顺从天命,在“践仁知天”的过程中不断地自我超越。因此,孔子倡导的“和”,弥合了感性与理性的鸿沟,它既是人文的理想境界,也是自然的生命境界,既是纯净自然的审美体验,也是道德的最高追求。这种“和”的境界,已经超越了以人与自然二分为前提的天人交往模式,天人和谐的生存理想内化到人的具体生存的各个方面,是人上下求索的、不断超越的动力与源泉。这一点对于当前的生态美学建设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二、“立命”“存性”与孟子的生态审美思想
据韩非记载,孔子而后,儒分为八,曾子为其一。子思、孟子发展了曾子的思想,把“仁、义、礼、智、圣”作为人的先天本性和施政理论,充实与发挥了性命之学,并且提出了“性善说”和“良知论”,成为孔门仁学的正统。
孟子继承了孔子的“天命”思想,对于“天”的认识也与孔子接近。《孟子》一书,提及“天”字共有81处。据杨伯峻分析,“天”在孟子那里共有三种含义:其一为“自然之天”,如“天油然作云”;其二为具有“主宰”(意志)之义的“天”,如“无敌于天下者,天吏也”;其三是“命运之天”,如“若夫成功,则天也。”⑦但是从具体的使用语境来看,孟子“天”的内涵中人学色彩逐渐增强而神性意识在不断地减弱,“天”更多的呈现为以按照客观规律周行不殆,且行不言之教的外在力量。按冯友兰的观点,孟子的“天”更多表现为“义理之天”⑧。“天与之者,谆谆然命之乎?曰:否,天不言,以行与事示之而已矣。”(《孟子·万章上》)“天”是人性的来源,孟子非常看重“天”的“行”与“示”,因为这是作为有限存在的人追求无限的人性的路标。“天”是“莫之为而为者”,“命”是“莫之至而至者”(《孟子·万章上》)。“天命”在身表现为人与生俱来的使命感,孟子毫不掩饰对于一切皆命的感慨,“莫非命也,顺受其正。是故知命者不立于崖墙之下。尽其道而死者,正命也。桎梏死者,非正命也。”(《孟子·尽心上》)“命”分“正命”与“非命”,人虽有“命”在“天”,但能否“顺受正命”却在于自己。正如孟子提出人性本善但仅具“善端”一样,“正命”仅仅是人能够知天尽性的可能性,还需要主体发挥自身的主动性才能立己身之命。“求则得之,舍则失之,是求有益于得也,求在我者也。”(《孟子·告子上》)人应该以自身的行动积极“顺天”以回应人之“正命”。在此,孟子把“性”与“命”统一了起来,“顺受正命”的道德律令被贯彻在人心秩序的构建中,把天所赋予人的正命为人之本性,即存性。“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存其心,养其性,所以事天也。夭寿不贰,修身以俟之,所以立命也。”(《孟子·尽心上》)仁义礼智圣即是天所赋予的“正命”,是属于“求则得之,求之在内”的东西。这样,孟子一方面肯定了人天生就是天命在身者,明确了天命的决定意义;另一方面以返身内求的姿态,强化了人的主体性和道德伦理的自觉性。“存其心,养其性,所以事天也。”(《孟子·尽心上》)因此人之性来自于天命,人必须通过后天的努力,将天所赋予人的“正命”确定为人性。
孟子将“存心”“养性”作为人格修养的目标,已经显露出道德形而上学的端倪,但是无论是“心”还是“性”还都不是先验的存在,需要在追求天所赋予的“正命”的过程中去体认。孟子以“养气”说阐述了人主动地追求天命以尽性的观念。孟子之前较为流行的说法是“气”代表了贯穿万物的生命力,落实于人身上指“血气”。如晏子曾说:“让,德之主也。让之谓懿德。凡有血气,皆有争心,故利不可强,思义为愈。”⑨但在孟子这里更多的是指凝聚了理性的感性力量,是集自然属性与道德属性于一体的客观存在。《孟子》一书中这样表述:“‘敢问夫子恶乎长?’曰:‘我知言,我善养吾浩然之气。’‘敢问何谓浩然之气?’曰:‘难言也。其为气也,至大至刚,以直养而无害,则塞于天地之间。其为气也,配义与道;无是,馁也。是集义所生者,非义袭而取之也。行有不慊于心,则馁也。’”(《孟子·公孙丑上》)人凭借这种“集义而生”的“气”而与宇宙天地相交通。通过养浩然之气的方式来完善人格,从而达到一种人格审美的新境界,这一点在学界已得到广泛的认同。但是“养气”又不仅是个体人格的培养,它的最高境界已经上升到了与天地合一的宇宙层面,是把个人内心的仁义扩张到与天地万物同德的地步。冯友兰认为,孟子的“浩然之气”是天人合一的“天地境界”,是就“人与宇宙底关系说”。处于天地境界的人,“他已知天,所以他知人不但是社会的全的一部分,并且是宇宙的全的一部分。不但对于社会,人应有贡献;即对于宇宙,人亦应有贡献。人的行为,……不仅与社会有干系,而且与宇宙有干系。”⑩在由养“浩然之气”而抵达的“天地境界”本身就是生态美学思想的典型表述,“‘天地境界'实际上是一种‘天人相和'的生态美学思想。”⑪孟子曾以“恻隐之心”等作为人异于“禽兽”、“野人”的特殊本性,似乎突出了仁道与自然的区分。但是这种区分并不主张人与自然的二分,更不会走向人与自然的对立,而是强调在天人合一的基础上实现自我意识的觉醒,通过自身不断的努力去“涵盖乾坤”而达到至高的“天地境界”。因此“天地境界”已不仅仅是天人相和的生存理想的静态描述,而且蕴含着人向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生态审美境界不断努力的理想与追求。成人成己与顺天而为高度统一,人的主动性与天地的生生之道和谐一致,从而呈现出更加积极的生态姿态。
在孟子的思想中,与“养气”直接相关的审美思想是“充实之谓美”。孟子说:“可欲之谓善,有诸己之谓信,充实之谓美,充实而有光辉之谓大,大而化之之谓圣,生而不可知之谓神。”(《孟子·尽心下》)在这里孟子受到了子思的影响,子思认为宇宙的本体为“诚”,即一种生生不息的生命力,天下万物都是它的呈现与结果,而且都凭借这种生命的力量渐进不息,最终达到其完满实现。孟子提出美就是天地万物生命特征完满实现时的存在形态,“充实”是对这种状态的描述。生命最初就潜含了美的因素,但并不一定最终成为美,只有当生命达到充实的状态,且其外在形态充分显示其内在本性时,潜在的美才能够成为现实的美。“五谷者,种之美者也;苟为不熟,不如荑稗。夫仁亦在乎熟之而已矣。”(《孟子·告子上》)“五谷”只有在成熟时,即在存在形态上与“荑稗”有着明显区别时,才是真正的“种之美者”。这是事物之存在特性达到“充实”时的具体表现。对天地万物而言,美不是静止的和现成的,也不是先天存在的必然结果,而是生命体发展的阶段性呈现。对于人而言,追求“美”如同追求“正命”一样,是“求则得之”的努力目标,需要养“浩然之气”才能得之。焦循对“充实之谓美”的解释是:“扩而充之使全备满盈,是为充实。充满其所有,以茂好于外。……美指其容也”。⑫朱熹的解释是:“力行其善,至于充满而积实,则美在其中而无待于外矣。”(《孟子集注》卷十四)他们都指出了人应该积极有为,通过“力行其善”,并“扩而充之”才能实现美。因此,在孟子这里,美是生命顺乎其天性发展的结果,但其过程并不像道家所提倡的“自然无为”,而是需要人遵循自然万物内在生命的尺度,需要人充分的发挥自身的自觉与努力。生态和谐是天地万物和谐相处、互生互荣的结果,生态美是一切生命勃勃生机的鲜活展现,人在生态世界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孟子的“充实之谓美”不仅揭示出美的生命性根源,而且明确了人作为天地之间有意志、有责任的存在着所必须承担的生态责任。
孟子在对“牛山之美”的论述中间接谈到了生态美的问题,也道出了生态的美丑与人心善恶的相似性。“牛山之木尝美矣,以其郊于大国也,斧斤伐之,可以为美乎?是其日夜之所息,雨露之所润,非无萌蘖之生焉,牛羊又从而牧之,是以若彼濯濯也。人见其濯濯也,以为未尝有材焉,此岂山之性也哉?虽存乎人者,岂无仁义之心哉?其所以放其良心者,亦犹斧斤之于木也,旦旦而伐之,可以为美乎?……”(《孟子·告子上》)孟子明确了草木葱茏的自然山水是美的,那是自然生命欣欣向荣的表现。但是经过人们长期的滥砍滥伐,加之过度放牧牛羊,森林和植被被破坏,牛山沦为濯濯童山。由于失去了绿色和生机,也就失去了往昔的生态美景。这里所包含的生态美的思想是与“充实”美论相一致的。孟子最后的落脚点是以牛山之美比喻人的本性,同时也指出了无论生态美还是人性之善端,都需要人努力去争取和呵护。对于生态环境和生态美,人应该有所作为,不仅应使之避免“旦旦而伐之”、“牛羊又从而牧之”的厄运,还要积极地维护生态平衡,保持自然的生机和生态美。“不违农时,谷不可胜食也;数罟不入池,鱼鳖不可胜食也;斧斤以时入山林,材木不可胜用也。谷与鱼鳖不可胜食,材木不可胜用,是使民养生丧死无憾也。”(《孟子·梁惠王》)在孟子看来,对于自然取之有道、取之有度是让百姓生活富足、安居乐业的王道,也是保持山水常青的生态美的重要手段。
三、“明于天人之分”与荀子的生态审美思想
荀子在中国思想史上颇具争议,他既传承了孔孟正统的基本思想,又吸收了先秦诸子的观念,在他身上“很明显的可以看得出百家的影响”⑬,因此宋儒和现代新儒家多视之为“不醇之儒”。可是正如荀子自述,“彼其人者,生乎今之世而志乎古之道”(《荀子·君道》),他虽对前代儒家,特别是对思孟学派多有突破,其基本的治学志向和精神品格与孔孟却是一脉相承的。在对天人关系的理解上,荀子提倡“明于天人之分”,主张“制天命而用之”(《荀子·天论》),继承和超越了前辈儒家的思想,在“天人相分”与“天人合一”的辩证统一中透露出独特的生态审美观念。
在荀子这里,“天”已不再是“主宰之天”或“义理之天”,而是表现为四时运行和阴阳变化的“自然之天”。荀子指出了自然规律的客观性,“列星随旋,日月递炤,四时代御,阴阳大化,风雨博施,万物各得其和以生,各得其养以成,不见其事而见其功,夫是之谓神。皆知其所以成,莫知其无形,夫是之谓天。”(《荀子·天论》)自然界是没有意志、没有目的的,它凭借有序和谐的运行生养万物,不以人的意志和愿望为转移。“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荀子·天论》)自然界的一切现象是依其客观规律而产生的,既不包含道德价值的判断,也不会预示社会活动的发展变化。“星队,木鸣,国人皆恐。曰:是何也?曰:无何也,是天地之变,阴阳之化,物之罕至者也。怪之,可也;而畏之,非也。”(《荀子·天论》)这种对于天的认识决定了荀子“天人相分”的天人观念。他认为,应该在了解并充分认识“天有其时,地有其财,人有其治,夫是之谓能参”的基础上“明于天人之分”(《荀子·天论》),把天人区分开来。天道在于生养,仁道在于修养。“天”的职分是“生”,即通过阴阳变化、四时交替生养万物,“夫天地之生万物也”(《荀子·富国》)。人的职责则在于不断提升自身的道德修养以更好地治理天地万物,“君子理天地。君子者,天地之参也。”(《荀子·解蔽》)荀子认为,“天道”与“人道”有区别但无尊卑,“天”虽生养了人,但是人却并非一味地受命于“天”,人能够总和万物,治理天地,使社会秩序合理,使天地万物和谐。他反对过于重视“天道”而忽视了“人道”的主张。庄子提出:“有天道,有人道。无为而尊者,天道也;有为而累者,人道也。主者,天道也;臣者,人道也。”(《庄子·天道》)荀子认为庄子的这种观点“蔽于天而不知人”(《荀子·解蔽》)。因此,对于人而言,“君子敬其在己者,而不慕其在天者”(《荀子·天论》),人不能完全依赖于“天”而消极“待命”,应该“制天命而用之”(《荀子·天论》),发挥自己的主观能动性,主动地承担起对于社会与自然的职责,在尊重、顺应自然的前提下有所作为。
荀子把天人相分却没有将天人对立,其思想中天人相和的思想底色是与孔孟相一致的。荀子在天人关系中构建了“天人相分”、“天人相参”为途径,寻求“天人合一”的天人之学。荀子认为,人是天所生养,不仅取之于自然,而且应该以人的职责还之于自然,因此,人要“备其天养,顺其天政,养其天情,以全其天功”。(《荀子·天论》)所谓“全其天功”,就是指依照自然的规律,秉持万物生成的天性而尽人事,不能违背和破坏。人与自然相处的过程中,应当协调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荀子把能“群”作为君子治世的根本,提出“人之生不能无群”(《荀子·富国》),这里的“群”不仅指向人类社会,而且应该扩展到自然万物。“君者,善群也。群道当,则万物皆得其宜,六畜皆得其长,群生皆得其命。”(《荀子·王制》)让天地间的一切都和谐相处,使之各安其位、各得其所,生生而不相害,这是荀子思想中作为君王的天职,也是生态理论所倡导的理想境界。更进一步,为了让天人和谐相处,人需要明确当为与不当为。“虽深,其人不加虑焉;虽大,不加能焉;虽精,不加察焉。夫是之谓不与天争职。”(《荀子·天论》)“不争职”包含着“顺天”的思想,即顺应自然规律,使自然养育充分完备。人应当凭借其“治道”合理地利用天时地利,“天有其时,地有其财,人有其治,夫是之谓能参。舍其所以参而愿其所参,则惑矣。”(《荀子·天论》)荀子认为,构建人与自然的和谐不应该仅凭借内在的道德修养,而应该加强社会秩序的规范和道德法令的建设,因此“治道”成为天人和谐的保证。实现了“治道”才能与天地相“参”,才能“参赞”天地之化育,这是社会发展和人生修养的最高境界。在这里,荀子把生态环境建设与社会治理统一了起来,把天地生养与人生修养统一了起来。通过以上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荀子与孔孟在“天人合一”思想上的不同,孔孟倾向于从仁学的文化心理和个体人格价值入手探讨人与天和的问题,从天人一体的角度谈到天人的和谐,而荀子则把目光放到了人类社会的群体组织上,强调“人为”与“治道”,从天人二分的角度思考天人合一的问题。正如李泽厚指出的,荀子“强调发挥了治国平天下的群体只须规范的方面”,“强调阐释‘礼'作为准绳尺度的方面,它由外而内。”⑭而这一点也正是荀子思想中的生态观念独特性之所在。
“礼”是荀学的核心观念。荀子把“礼”看作是“人道之极”,是维系社会等级秩序和统治法规的核心。他说:“故绳者,直之至;衡者,平之至;规矩者,方圆之至;礼者,人道之极也”(《荀子·礼论》),同时指出,“礼者,法之大分类之纲纪也。故学至乎礼而止矣。夫是之谓道德之极。”(《荀子·劝学》)“礼”的核心是保证社会群体“群而有分”,是君王治理的依据,是人与人相处的尺度。“礼”虽为“人道”的规范,但是“礼”之本在于“天”。“礼有三本:天地者,生之本也;先祖者,类之本也;君师者,治之本也”,即“上事天,下事地,尊先祖而隆君师”。(《荀子·礼论》)因此,外在的“礼”与内在的“德”是一致的,人尊“礼”而行实际上就是师法自然规律处理人事。荀子依“天”立“礼”,以“礼”修“德”,“天”“人”通过“礼”的媒介结合与沟通,实现了“天人合一”。
“礼”不仅决定了人的道德品格,而且也影响和规范了人的审美情感。荀子特别强调人的情感应该合乎礼仪。“故说豫娩泽,忧戚萃恶,是吉凶优愉之情发于颜色者也。歌谣傲笑,哭泣谛号,是吉凶优愉之情发于声音者也。……两情者,人生固有端焉。若夫断之继之,博之浅之,益之损之,类之尽之,盛之美之,使本末终始莫不顺比,足以为万世则,则是礼也。”(《荀子·礼论》)在“礼”的教化过程中,人性情感被放置于一定的形式之中,即具体的“礼”的仪式,仪式都不过是审美式的“文饰”,人的情感应该在仪式中得以表达和释放。荀子提出人应该以“礼”来约束和改造自然性情,“故圣人化性而起伪,伪起而生礼义,礼义生而制法度。”(《荀子·礼论》)这里所提的“伪”,就是符合“礼”的人为活动。只有“化性而起伪”,人才能成就君子之“美”,人的情感才是审美的。“性者,本使才朴也;伪者,文理隆盛也。无性则伪制无所加;无伪则性不能自美。”(《荀子·劝学》)经过“礼”的“伪饰”而形成的审美情感从根本上是符合天道的,它不仅满足了人类社会内部的“群而有分”的需求,而且实现了身与心的协调,自然与社会的和谐。“故人莫贵乎生,莫乐乎安。所以养生安乐者,莫大乎礼义。”《荀子·强国》“礼”克服了人的内在冲突,通过“养生安乐”,实现了人的自然生命和文化生命的和谐统一,体现了生态审美观念的价值诉求。
通过以上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到,随着人的自身力量的不断壮大,以及人类社会组织形式的不断成熟,从孔子到荀子,先秦儒家在天人关系中越来越具主动性,从对具有人格意志的主宰力量的敬畏,转向了师法天道以提高自身的修养和维系社会秩序的稳定。相应地,生态审美观念也从追求个体与自然在精神上的共鸣,走向了通过社会化的仪式表达人与天和的审美情怀。但是在总体上,先秦儒家的生态审美观念是一致的,都是在法天、敬天的前提下去探索“天人合一”的审美境界。总之,在孔子、孟子、荀子等先秦儒家的天人观念中,包含着各具特色的生态智慧和生态审美思想,值得我们在当前的生态研究中参考与借鉴。
注:
①杜维明:《一阳来复》,上海文艺出版社1997年版,第39页。
②杨荣国:《中国古代思想史》,人民出版社1976版,第4页。
③陈梦家:《殷墟卜辞综述》,中华书局1988版,第581页。
④牟宗三:《心体与性体》,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版,第190页。
⑤吴承笃:《栖居与生态——“诗意地栖居”的生态意蕴解读》,《山东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6期。
⑥朱熹:《四书章句集注》,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版,第140页。
⑦杨伯峻:《孟子译注》,中华书局1960版,第249页。
⑧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上册),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版,第35页。
⑨杨伯峻:《春秋左传注》,中华书局1990版,第56页。
⑩冯友兰:《冯友兰学术论著自选集》,北京师范学院出版社1992版,第227页。
〔责任编辑:青 末〕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Heaven and Human”and the Research of Pre-Qin Confucian Eco-aesthetics Thoughts
Wu Chengduo
“Correlation between the heaven and human”is the basic problem of Chinese traditional philosophy of Pre-Qin Confucianism.Representatives of Pre-Qin Confucian have launched the discussion of“relationship betweenman and nature”from different angles.From Confucius,Mencius to Xunzi,they have builta path of development between the heaven and human from“know destiny”to“master the laws of heaven”,and the ecological aesthetic ideas from the pursuit of the spiritual resonance between individual and nature,to the social ritual expression of the hamony aesthetic feelings between human and heave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heaven and human;Eco-aesthetics;Confucius;Mencius;Xunzi
Ⅰ206.2
A
1001-8263(2015)06-0137-06
吴承笃,山东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博士 济南250014
* 本文是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生态语言学与生态文学、文化理论研究”(12BZW007)的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