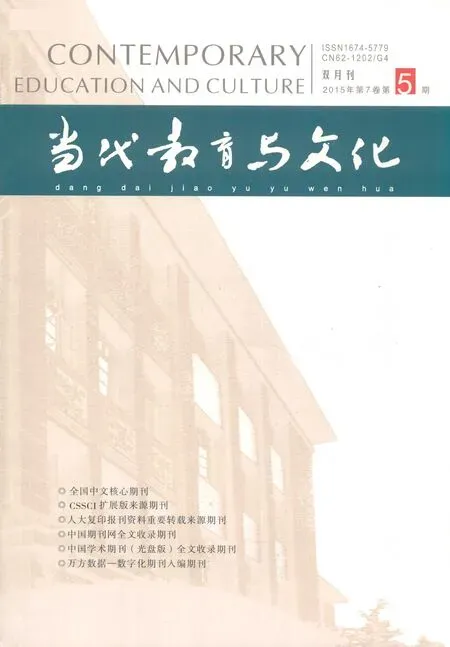“以友辅仁”:孔子教学的另一重要侧面——孔门弟子 “同学圈”现象考察
李如密
(南京师范大学 课程与教学研究所,江苏 南京 210097)
古语曰:“友者,师之半。”我国古代儒家教育就是以重视交友在人的发展中的作用为其特色的。[1]教育史专家高时良先生研究指出:“强调在教师教育下朋友之间切磋琢磨,相互帮助,这也是我国古典教育学的特点。西方教育学所揭示的教与学,通常只局限于教师与学生之间的关系。在我国,儒家从孔子开始,一脉相承,都把朋友的辅助看成教育和教学过程的重要环节。”[2]孔子曾教育其弟子:“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论语·述而》)这是因为交友对于个人进德修业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所谓“君子以文会友,以友辅仁。”(《论语·颜渊》)在孔子交友思想影响下,他的众多弟子都非常重视与同门的切磋琢磨、“相观而善”。孔门弟子之间组成的一个一个真实、具体、生动的 “同学圈”,让我们看到了孔子教学的另一精彩的重要侧面。
一、孔门弟子 “同学圈”现象是客观存在的事实
孔门弟子整体上就是一个大的 “同学圈”,每个弟子又拥有自己的小的 “同学圈”。大 “同学圈”由许多小 “同学圈”组成,小 “同学圈”之间又有部分的交叉。因为人是交往的动物,而进德修业又是在交往中进行的,每个人在 “同学圈”中既是受影响者,又是影响源。既是以自己为中心的 “同学圈”的核心,又同时成为别人为中心的 “同学圈”的重要他人。
我们如果深入考察,就会发现孔门弟子的 “同学圈”是有若干中心的,每个同学圈中又由多名弟子组成。如:
以颜回为中心的 “同学圈”中,就有子路、子贡、曾参,及其他同门。
以子贡为中心的 “同学圈”中,就有颜回、子路、子夏、子张、冉有、曾参、宰予、原宪等。
以子游为中心的 “同学圈”中,就有子夏、曾参、有若、澹台灭明等。
以子夏为中心的 “同学圈”中,就有司马牛、子张、子游、曾参、樊须等。
以子张为中心的 “同学圈”中,就有曾参、子游、子夏、宰予、子贡等。
以曾参为中心的 “同学圈”中,就有颜回、子贡、子夏、子游、子张、有若等。
以冉有为中心的 “同学圈”中,就有子路、子贡、公西华、曾皙、樊须等。
以宰予为中心的 “同学圈 “中,就有子贡、澹台灭明、冉有、子张、子路等。
……
在这些 “同学圈”中,子贡的 “同学圈”是较大的,并且他被许多同门视作各自 “同学圈”的重要他人。这与他性格较活泼、交友广泛不无关系。他所交往的同学,既有 “德行”能力突出的颜渊、曾参、原宪,也有 “言语”能力突出的宰予,既有“政事”能力突出的子路、冉有,也有 “文学”能力突出的子夏等。从文献记载来看,冉有的 “同学圈”就是另外一种不同的情形。他所交往的同门弟子就有 “政事科”的子路和 “言语科”的子贡,但是与同门中的 “德行”科和 “文学”科弟子却是没有交集的,其具体原因不得而知,最大的可能应该是他们与冉有在 “礼乐”方面缺乏共同语言。从冉有的实际表现看,他对于 “礼乐”的学习兴趣也不大。所以,孔门弟子 “同学圈”的存在,让我们看到了教育中较为复杂的深层问题,对此做一些考辩,可以补充孔门私学研究的空白。
二、孔门弟子 “同学圈”的影响因素及日常情景
孔门弟子众多,同门之间的关系也较为复杂。以重要弟子为中心形成的 “同学圈”,可以反映孔门私学内部的教育亚文化现象。对于孔门私学的研究,像过去那样只关注孔门的师生关系是不够的,还应该进一步认识到孔门弟子 “同学圈”的应有价值。前者是教育的一种垂直影响,而后者是教育的一种平行影响。一般说来,完整的教育应该是这两种影响相辅相成,融为一体,形成一种精神合力。那么,影响孔门弟子 “同学圈”形成的因素有哪些?其日常的情景又是怎样的呢?
(一)影响孔门弟子 “同学圈”形成的因素
有一些因素对于孔门弟子同学圈的形成起着自然微妙的作用。一是年龄因素。如子游的同学圈中的几位同门弟子,大多属于孔子晚年的弟子,比较年轻且年龄仿佛,据 《史记·仲尼弟子列传》载,有若少孔子四十三岁、子夏少孔子四十四岁、子游少孔子四十五岁、曾参少孔子四十六岁。他们几个基本上属于同龄人,又在一起随孔子进德修学,所以很自然地形成同学圈。二是学习阶段。有些弟子年龄相差很大,如颜渊和子路,一个少孔子三十岁,一个少孔子九岁,二人之间年龄相差二十多岁,但因为同是孔子早期弟子,那时孔子的弟子尚少,二人随侍孔子的机会多,便自然有许多的交集。颜渊虽然年纪较轻,但却少年老成;子路虽然年龄较长,但却充满活力。二人相处能够相互敬重,结下了深厚的同门情谊。三是共同活动。如孔子周游列国时,有些弟子追随左右,朝夕相处,共同经历了艰难岁月,对师生关系和同门关系都是一种考验。四是能力志趣。如颜渊的同学圈中的诸同门,都对颜渊的好学精神和高尚品德敬佩有加,经常在一起谈论志向、交流心得,很自然地将颜渊推到了同学圈的中心。
(二)孔门弟子 “同学圈”的日常情景
孔门弟子同学圈中的原生态生活情景是怎样的呢?借助有限而宝贵的历史文献资料,我们大致可还原其中的主要部分。但即便如此粗简的勾勒,已可让我们窥见孔门弟子同学圈中纷呈的精彩了。
同门之间的相互关心。(1)同门有忧,送上劝慰。《论语·颜渊》载:司马牛忧曰:“人皆有兄弟,我独亡。”子夏曰: “商闻之矣: ‘生死有命,富贵在天。’君子敬而无失,与人恭而有礼。四海之内,皆兄弟也。君子何患乎无兄弟也?”其实,司马牛并非真的没有兄弟,他实际上是兄弟四人,只不过他们在宋国的作乱行为,让司马牛不愿与之为伍,所以他实际感慨的是没有 “好”兄弟罢了。可见司马牛所 “忧”的尚限于个人血缘意义上的兄弟,而子夏劝慰他时则故意将之推及道德修养意义上的 “兄弟”。子夏对司马牛在患难时的这一道义上的精神抚慰,令孤独失望的司马牛感受到了同门的温暖。(2)同门分别,互留赠言。同门弟子平时生活在一起,一旦分别便免不了情之所至,难以割舍。如颜回与子路在平时常与孔子一起讨论问题,气氛相当融洽,二人年龄相差很大却情深谊厚。《礼记·檀弓下》载:子路去鲁,谓颜渊曰:“何以赠我?”曰:“吾闻之也,去国则哭于墓而后行,反其国不哭,展墓而入。”谓子路曰: “何以处我?”子路曰:“吾闻之也,过墓则式,过祀则下。”子路离开鲁国时,颜回提醒他注意相关礼仪;子路也特别关照颜回,平时在鲁国应该遵循的礼仪细节。后世朋友分别互留赠言之风,或许就是滥觞于此吧。
同门之间的相互辩难。(1)辨明本末,知所先后。孔门弟子虽然同时受教于孔子,但因每个人的理解不同,致使所领悟到的也就旨趣各异。如 《论语·子张》载:子游曰:“子夏之门人小子,当洒扫应对进退,则可矣,抑末也。本之则无,如之何?”子夏闻之,曰:“噫,言游过矣!君子之道,孰先传焉?孰后倦焉?譬诸草木,区以别矣。君子之道,焉可诬也?有始有卒者,其惟圣人乎?”从文中可见,孔子弟子子夏已经做了老师,都有 “门人”了,但他的同门子游显然不认可其教学方法。子游和子夏两个人虽然同列孔门 “文学”科榜单,但二者在思想观点上却存在着较为严重的分歧:子游认为自己是从仁义大处着眼,继承的是儒学之“本”;而子夏教授弟子不过拘泥于烦琐的礼仪小节,并未掌握儒家学术之根本,因而只能算是逐儒学之 “末”。言语之间明显流露出对子夏的不满。但是子夏对子游的批评并不接受,而是直接反驳说“言游过矣”,并且申明了自己的见解。《礼记·大学》有言:“物有本末,事有始终,知所先后,则近道矣。”子游、子夏之争看似尖锐对立、水火不相容,其实若能冷静地全面观之或正可互补相长、殊途同归。(2)贫而非病,秉德而行。《史记·仲尼弟子列传》记载:孔子卒,原宪遂亡于草泽中。子贡相卫,而结驷连骑,排藜藿,入穷阎,过谢原宪。宪摄敝衣冠见子贡。子贡耻之,曰:“夫子岂病乎?”原宪曰:“吾闻之无财者谓之贫,学道而不能行者谓之病。若宪,贫也,非病也。”子贡惭,不怿而去,终生耻其言之过也。也就是说,子贡与原宪本属同门,但实际处境却相差悬殊,一个 “结驷连骑”,是何等的风光;另一个 “摄敝衣冠”,是如此的寒酸。二人相见,尴尬难免。但是结果却发生了戏剧般的反转,一个擅长辞令与外交,在政界与商场上左右逢源的子贡,却在同门原宪面前不慎“失言”了。子贡一开始 “耻”之,此 “耻”是为同门的寒酸生活而 “耻”,并且以 “病”相怜。当原宪不卑不亢地辨析 “贫”与 “病”的不同,并声明自己是 “贫也,非病也”之后,子贡再一次感到了 “耻”,但此 “耻”已不再是 “耻”原宪,而是“耻”自己 “言之过也”。很显然,在特定意义上,正是同门原宪让子贡道德觉醒了。
三、孔门弟子 “同学圈”的主要功能
同学圈的存在及其活动,在孔门弟子的学习、修养和生活诸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产生了微妙而深刻的影响。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同门互助
孔门弟子有了问题,多数会直接向孔子求助,但也会有一些是在同门间互助解决。如 《论语·颜渊》载:樊迟问仁。子曰:“爱人。”问知。子曰:“知人。”樊迟未达。子曰:“举直错诸枉,能使枉者直。”樊迟退,见子夏曰:“乡也吾见于夫子而问知,子曰:‘举直错诸枉,能使枉者直。’何谓也?”子夏曰:“富哉言乎!舜有天下,选于众,举皋陶,不仁者远矣;汤有天下,选于众,举伊尹,不仁者远矣。”意思是说樊迟向孔子接连问了两个问题—— “仁”和 “知”,但对孔子所给与的两次回答的意思没弄明白,孔子见樊迟 “未达”,便又作了进一步的阐释,结果樊迟还是不明白,不过却没好意思再追问。樊迟从老师那儿退出来后,就去见同门子夏,向这位同门中的佼佼者再求教。子夏也就当仁不让地做了一回 “小先生”,用举历史人物作例子的方法对樊迟进行了相应的辅导,有了这些实例的帮助,樊迟终于透彻理解了老师讲的道理。类似的情况在孔门弟子同学圈中时有发生。如 《论语?里仁》载:子曰:“参乎!吾道一以贯之。”曾子曰:“唯。”子出,门人问曰: “何谓也?”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大意是:孔子说:“曾参啊,我的道是可以用 ‘一’贯穿起来的。”曾参说:“是。”孔子出去后,其他弟子问曾参:“是什么意思啊?”曾参说: “老师的道,只是忠恕而已。”在这里,其他门人显然不能理解孔子和曾参关于 “一贯之道”的问对,但孔子说完就走了,他们无法直接向老师再请教,所以就只好问曾参,由曾参进一步阐明孔子的意思,帮助解决他们的学习困惑。
(二)同门共决
孔门弟子同学圈常常自行决定有些事情具体怎么办。如 《论语·先进》载:颜渊死,门人欲厚葬之。子曰:“不可。”门人厚葬之。子曰:“回也视予犹父也,予不得视犹子也。非我也,夫二三子也。”颜渊死后,其同学想要 “厚葬”他,就先请示孔子,没料到孔子对此明确表达意见为 “不可”。若在平常,老师的意见可能就是定论,弟子们会照此办理,但同学们这一次竟一反常情,不顾老师的反对,仍然坚持 “厚葬”了颜回。这从中可以看出一方面颜回与同门之间的深厚情谊,另一方面孔门弟子同学圈是可以自行决定一些事情的,甚至老师的意见也可放到一边。再如 《孟子·滕文公上》载:孔子没,……子夏、子张、子游以有若似圣人,欲以所事孔子事之;强曾子,曾子曰:“不可!江汉以灌之,秋阳以暴之,皓皓乎不可尚矣。”也就是说,在孔子死了以后,其弟子子夏、子张、子游认为有若跟孔子相貌近似,便想用过去敬事孔子的礼节来敬事他,还勉强另一重要弟子曾参同意。曾参表态 “不行!”并阐明了自己的理由,认为孔子的形象无人可以代替。 《史记·仲尼弟子列传》亦载有此事,是这样记述的:孔子既没,弟子思慕,有若状似孔子,弟子相与共立为师,师之如夫子时也……有若默然无以应,弟子起曰:“有子避之,此非子之座也!”看来因为多数弟子的意见倾向于拥戴有若,所以即便有曾参一个人的反对,也得少数服从多数,最终还是将有若推上老师的座位,所谓 “共立为师”。后来只是因为有若表现不佳,其他弟子起哄,有若不得不下台,事情才算了结。
(三)同门共尊
因为孔子的道德学问深得众弟子的尊重和敬爱,同学圈的相互影响也起了重要的作用。如颜回就是被孔子有意树立的学习榜样,在同学圈中享有很高的威望。颜回不仅以其自身的修养得到了其他同门应有的尊重,而且也进而影响了同门中的许多人,使得孔门弟子因此团结得更加紧密,所以孔子才说 “自吾有回,门人益亲”(《史记·仲尼弟子列传》)。孔子去世后,弟子子贡的表现更加突出地表明师生感情非同一般。《史记·孔子世家》载:“孔子葬鲁城北泗上,弟子皆服三年。……唯子贡庐于冢上,凡六年,然后去。”在中国自古就有 “师生如父子”、“一日为师终生为父”的说法,这一传统就是由孔子师徒确立的。虽然 《仪礼·丧服》并无弟子为老师服丧的规定,但孔门弟子仍然按照孝子为父母所服的丧制为孔子服三年之丧,而子贡服六年之丧,更将师生之情置于父子之上。这在当时的中外教育史上都堪称佳话。对于那些社会上恶意中伤孔子形象的言行,作为孔门弟子的子贡均进行了坚决回击。如 “叔孙武叔毁仲尼。”子贡便说:“无以为也。仲尼不可毁也。他人之贤者,丘陵也,犹可逾也。仲尼,日月也,无得而逾焉。人虽欲自绝,其何伤于日月乎?多见其不知量也。”(《论语·子张》)司马迁就曾肯定说:“夫使孔子名布扬于天下者,子贡先后之也。”许多史实表明,在孔子形象的维护和儒学思想的传播方面,孔门弟子及其同学圈发挥了独特的不可忽视的重要作用。
(四)同门自正
孔门弟子的同学圈中整体是和谐的,但有时也会有些 “不谐音”。一旦发生这种情况,同学圈就会发挥其 “自正”功能。 《古微书》载: “邑名朝歌,颜渊不舍,七十子掩目,宰予独顾,由蹶堕车。”也就是说,当年孔门弟子路过朝歌,颜渊不肯留宿,七十弟子都捂上了眼睛,唯独宰予忍不住回头去看,被子路发现并一脚踹下车子。文中的“朝歌”就是殷商旧都,乃纣王失国之处。据 《史记·乐书》载:“纣为朝歌之音,朝歌者,歌不时也。”对于注重德行修养、讲求非礼勿视的孔门弟子来说,看到朝歌这样的地方而做出像颜渊等人的举动就是非常自然的。宰予因为自己表现另类而被大师兄子路踹下车子,就是收到来自同学圈的一种惩罚。孔门弟子同学圈的这种功能,就连老师孔子都看得清楚,有时还要借助一下呢。《论语·先进》就记载:“季氏富于周公,而求也为之聚敛而附益之。”孔子非常生气,对众弟子说:“非吾徒也。小子鸣鼓而攻之,可也。”也就是说,在孔子看来,若是弟子们的同学圈在他的同意下共同施压于冉有,对于冉有就是一种颇具震撼力的教育影响。
四、孔子对弟子 “同学圈”的关注与指导
孔门教学无法回避弟子的 “同学圈”。孔子有集体教学,就是在大的 “同学圈”中进行,如讲学于杏坛之上,习礼于大树之下,都是公开的,是面向所有弟子的。也有小组教学,是在小的 “同学圈”中进行,如孔子从教早期常与弟子颜渊、子路、子贡 “三人行”,就直接和弟子的同学圈交叉或重合。更多的是个别教学,孔子直接面对弟子进行 “答问”,通过影响同学圈的核心人物或关键人物,进而通过 “涟漪效应”影响弟子们的同学圈。所以孔子对于弟子的 “同学圈”非常关注,并给与及时的有益的指导。
(一)组织弟子们的活动
孔子教学有时采用侍坐形式,这就使得其弟子可以几人同时受教,相互了解,一起讨论共同关心的问题。如 《论语》就记载子路、冉有、公西华、曾皙侍坐,孔子与他们一起谈论个人的志向,使每一个 “圈中人”都有机会发言,既表达了自己,又了解了别人,还得到了老师的评点和教诲。孔子周游列国途中随机而教,时间较长,弟子们随侍左右,共同经历了许多事情。《史记》就记载有的弟子驾车了,有的弟子饿晕了,有的弟子掉队了,有的弟子质疑了,有的弟子怒目了。这一段共同度过的特殊经历,对于许多弟子来说,都会刻骨铭心、终生难忘,实在是一份不可多得的珍贵的教育与学习资源。孔子在鲁期间也常带弟子登东山、游沂水,在轻松和谐的氛围中触景生情,进行教育和教学。有时带领在学弟子到已仕弟子那儿去实地考察,加强不同 “同学圈”的联系。如 《论语·阳货》载:子之武城,闻弦歌之声。夫子莞尔而笑,曰:“割鸡焉用牛刀?”子游对曰:“昔者偃也闻诸夫子曰:‘君子学道则爱人,小人学道则易使也。’”子曰:“二三子!偃之言是也。前言戏之耳。”无疑地,孔子与子游的这番对话一定会在随行的 “二三子”中产生深刻而微妙的教育影响。
(二)指导弟子们的交友
在孔门私学中,孔子一直密切关注其弟子们的交友情况,因为在他看来 “不知其人视其友”,主张为人应慎重交友。但弟子们各从自己的实际出发,进行交友,孔子就冷眼旁观,从他们交友所形成 “同学圈”的情况,对他们的发展作出预测,以此提醒他们通过交友形成和发展各自的 “同学圈”时多加注意。如 《说苑·杂言》记载孔子的话:“丘死之后,商也日益,赐也日损。商也好与贤己者处,赐也好说不如己者。”对于子贡来说,他一方面个性活泼热情,有出众的言语才能,喜欢与人交往,另一方面也需要为他所擅长的经商和外交积聚人脉,不得不同各种各样的人包括 “不如己者”打交道。而子夏则不同,他性格勇敢孤傲、心胸狭隘,专注于 “文学”的修养,交友严格坚持 “与贤己者”相处。这样一来,子贡和子夏就形成了各自不同的 “同学圈”,子贡的多而泛,子夏的少而精,所以长时间分处不同的 “同学圈”,其进德修学就必然产生一个 “日损”一个 “日益”的结果。孔子深谙人的交友之道,从对于子贡和子夏日后可能会因 “同学圈”的不同带来发展的差异所作的深刻分析,即可见一斑。
(三)评点弟子们的言行
弟子们说了什么,做了什么,得在哪儿,失在哪儿,孔子作为他们的老师的评点,无论是对他们本人,还是所在的 “同学圈”,都是十分重要的。《吕氏春秋·察微》载:鲁国之法,鲁人为臣妾于诸侯,有能赎之者,取金于府。子贡赎鲁人于诸侯而让其金。孔子曰: “赐失之矣!夫圣人之举事,可以移风易俗,而教导可施于百姓,非独适己之行也。今鲁国富者寡而贫者多,取其金则无损于行,不取其金,则不复赎人矣。子路拯溺者,其人拜之以牛,子路受之。孔子曰:“鲁人必拯溺者矣。”子贡 “赎人而让金”,按照法律本该得到的而未取,这好像是品格很高;而子路 “拯溺而受牛”,似乎接受得心安理得,这显得品格有点鄙俗。当时或许也有不少的人会这样评论,但是孔子从这两件事的社会影响和示范效应的高度来评点,认为子贡 “失之矣!”因为他的做法有可能会导致 “不复赎人矣”;而子路的做法则可能产生后续模仿效应,致使 “鲁人必拯溺者矣”。两相比较,差别不言自明。孔子对这两件事的评点既精准又精辟,对于其弟子及 “同学圈”当然是一种及时雨一样的教育引导。可见,孔子确实无愧于一位善于引导的教育艺术家!
[1] 李如密.儒家教育理论及其现代价值 [M].北京:中华书局,2011:171.
[2] 高时良.学记研究 [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6:14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