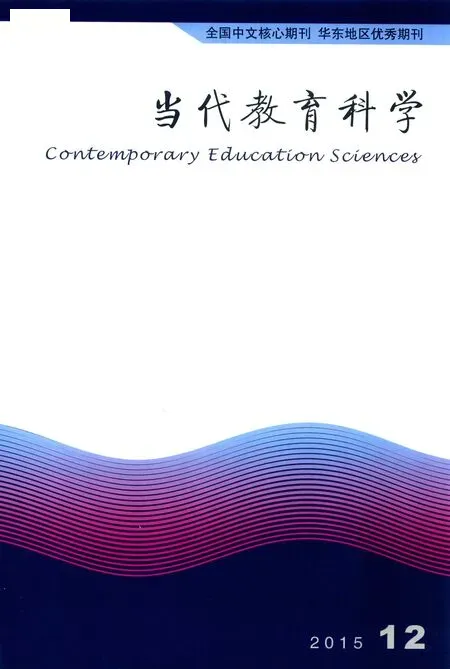何以关联:教师与算度
●宗锦莲
何以关联:教师与算度
●宗锦莲
教师与算度必然关联,其相互捆绑的决定性要素在于:一,教师被安放于学校场域,必须接受制度性逼迫、计划性安排及科层化管理;二,教师受困于算度网络,既要服从国家、教育行政部门及学校管理者的算度、内部系统中的自我算度,又要承受来自社会空间里的全景算度;三,教师链接着算度传递系统,作为一种一致化的工具,通过反复重申的灌输将算度逻辑传递给学生,在这一过程中,算度逐渐成为统治教师整个性情系统的行动惯习。
教师;算度;关联
“人人都在算度之中”是现代工业社会中作用于人的现实性后果及人所身处的惯常性状态。在算度整体性的运作机制里,教师扮演着极为复杂的角色,是算度的承受者、发起者、更是算度得以实现的中介人。教师被算度所要挟,不断地勾勒出算度料想中的形象,同时算度又依赖于教师力量,配合确凿的社会筛选机制与社会秩序的需要。我们可以推断,教师与算度必然关联,而关键在于在现实意义上教师与算度相互捆绑的决定性要素是什么?
一、安放于学校场域
学校是一个特殊的场域,它不仅是提供给师生活动的场所,更是由一系列的制度、计划、组织及师生间的互动构筑起来的关系。学校作为一种必要环境将教师与算度扣接在一起以至于无法辨清究竟是算度操控着教师,还是教师驾驭着算度。
(一)制度性逼迫
制度的出现是以人的不自律、不自觉为前提假设,是以消灭五花八门的欲望、斩除自由散慢的倾向为手段,它致力于人与人之间的互相妥协与彼此谅解,最终志在构建一个稳定的社会秩序。制度是无可辩驳的霸权形式,与强人所难、不随人所愿相关,也与逼迫对象执行相关。在制度的威逼利诱下,教师将自觉地变成另一种形式的制度,继而成为另一种强有力的规训力量。教师究竟为何在制度中甘愿受迫并自觉转换呢?
1.刻意等级划分的顶层设计。制度的顶层设计是指制度所偏好的动机、所秉持的理念、所追寻的目标。学校制度倾向于刻意地给教师划分等级。好比为教师架设一副可供攀爬的梯子,梯子自上而下分为若干等级。
值得注意的是,制度给予教师的梯子是一副而不是多副,这意味着对教师的等级划分标准是单一的、专制的,是抹煞教师多样性的一致性规定。既然应当保证使学校工作一致化和正统化的制度性条件,教育系统就试图使负责灌输的人受到一致的培养并拥有一致化了的和有一致化作用的工具。[1]例如中小学教师职称评定制度,不仅等级和名称统一,评价标准也大同小异。这种评定制度无视学科特征、年级差别、更无视教师本身的个性与优势,将现实性的特殊统统纳入到一套理想化的系统中,使其接受单向度的考量。学校制度的动机是将教师区分开来,理念是越简便越好,目标则是让教师各得其所、又不安其命——依附于外在强加,并迫切地寻求机会实现向上流动。
2.以算度为依托的操作手段。学校制度的基本手段是算度,即以精确化、精细化的分数或符号来定义教师。教师的工作成绩被分解为若干个考核要点,通过各要点分值的累计,换算出最终得分。每个教师都必须进入其中,接受一个个环节的检验,如同流水线上的产品般。因为制度就是这样规定的,对每个人都一样。
3.必须承担的违反性后果。制度的强大不仅仅在于告知人们哪些能做、哪些不能做,更在于完备地规定了“做或不做”的后果。当违反制度规定的代价大于收益、或超出行动者可承受范围的话,“惟命是从”将成为教师最优先的策略选择。更何况,除了违反性后果外,制度中必不可少的一块内容,便是对“温顺者”的奖赏。罚与奖双管其下,逼着教师只能就范。
4.自上而下的制度影响。制度是按权威分等级的一套角色。[2]学校制度并非是狭义上纯校本化的要求,而是在更高权威制约下的综合性存在。从国家教育制度的意志强加,到地方教育制度的约束规定,都是学校必须遵守的制度内容,学校制度中加工改造的部分都必须在国家及地方教育制度的框架内进行。教师在学校制度中所受的影响,自上而下、自成系统,是弥散在整个社会空间里无处不在的约束力。这其中,国家的在场无疑是最有效的,因为国家与其主体的关系是不对称的,[3]只要是国家的压力施加,教师都无法对抗,在国家的名义下,暴力色彩被张扬更为突出。
(二)计划性安排
除了由制度撑腰外,学校的一切教育教学活动全部都是由计划所决定,并按照计划层层推进。在学校层面的计划安排中,教师没有自主权,惟有参照计划表做该做的事。
学校的计划性安排究竟包含了哪些内容?教师怎样受限于这些内容呢?第一是招生计划,学校每年招多少人,招哪些人全部不由教师决定,甚至当学生进入学校,如何分班、各班由哪些教师带,也都与教师无关。教师被告知接收某某班,不管该班基础是优是劣,今后都将与教师捆绑在一起。第二是课程计划,国家课程计划是法定的,教师没有发言权。根据课程计划编排学校课程表由校长说了算。教师只需将课程表中与己相关的勾画出来,完成工作量即可。至于该门课程是否适合上午教授等都不会成为鉴定教师水平的因素。第三是教师招聘计划。为了完成学校工作,该团体的专门人才是按照制度控制和制订的程序,在指定的时间和地点,利用标准化和经过检查的工具来录用、培养和任命的。[4]专门人才循着怎样的偏好去挑选新教师,应聘者不得而知,老教师的意见也不会纳入考量的范围。第四是教师培养计划。每年学校有多少个骨干教师指标,通过何种途径进行骨干教师筛选全都已经事先被规定好了。不管有多少教师已经达到了骨干教师标准,被认定的骨干教师只有计划里有限的那几个。教师的现实价值被每年的指标数界分成若干等级,教师顺应着等级被分割成若干类别。第五是日常作息计划。何时上课、每节课多长时间、何时放学……被规定得分外细致。教师的日常生活被搭建成了一张时间表,时间成为隐性的规范指挥着教师的行动。限制教师自由的计划甚至有些还涉及了教师正常的生育安排。①
计划一经订立便固定下来,尤其是学校的教育教学计划,是国家强制性规定与学校经验累积的结果,长年为学校循环使用。久而久之,这些计划便会转化为常规,一种即便不去查阅计划表也可以正确行动的准则。各种学校文化有必要一致化和程序化,即被学校工作的常规和为了这些常规而“常规化”,也就是被一些重复和重建的练习和为了这些练习而“常规化”。这些练习必须相当刻板,以使那些尽可能不是不能被代替的辅导教师不停地让人们去重复。[5]重复使法定程序不断固化,逐渐演化为教育主体内在的秩序。
教育计划的确定性特征制造了威信,也为算度提供了丰富的操作内容。人们以是否按计划行事算度教师,教师根据学生落实计划的表现算度学生。算度是计划有效达成的重要手段,计划为算度权威性及说服力的增强贡献了力量,后者的功用丝毫不逊色于前者。
(三)科层化管理
科层制是人类社会创造出的一种接近完备的、用以协调专业化知识分工的理想机制。通过科层制内在的可计算性、可重复性、效率和秩序的苛求、劳动分工与专业化知识的深化,极大地推动了生产效率的提高和物质财富的积累。[6]经济生产组织为了追寻效益最大化对科层制青睐有加无可厚非,而学校组织对科层制的盲目崇拜令人痛心。学校科层化管理至少体现在:
1.层级架构。在学校组织中,全部职位按照管理权限和责任的不同,由低到高排列在不同的层级上,呈现一种顶端窄、底部宽的金字塔形。顶端由学校领导层构成,中部由学校中层干部即相互平行的各科室主任构成,第三层由学校业务干部构成,底部则由普通教师及学生②构成。权力从底层向顶端不断地集中,上下级之间的职权关系按等级严格划分,上级握有对下级进行命令及合法控制的权力,下级则需履行听从上级要求的义务。职位的高低给占据该职位的人不同限度的权威,这种权威却与教师专业性无关。并非专业知识、经验越多的教师越有权威,也不是上级必定比下级具有更强的专业素养。教师接受的是一套权威体系的控制,所关注的是教师对制度、计划及纪律等外在约束的遵从程度,而非作为教师内在价值的专业水准。
2.专门化分工。学校系统内的分工从大的方面来看,可以分为小学、中学、大学,每个学校内部又分为各种科目的科教室、各种性质的管理职能部门以及不同层次的学生班级。[7]分工促使每个人及每个部门履行职务、协调配合,分工同时也将学校教育教学的整体切割成若干孤立的碎片。为了配合各个专门化部门的管理,教师的工作被拆解得四分五裂。例如,教务处只关注教师课上得好不好、教科室只关注教师、有无论文发表。至于教师的课题研究是否有助于课堂教学质量的提升等究竟由哪个部门负责却难以分清。若一方关注过多,又会惹上越权的嫌疑,引发不必要的矛盾。于是,学校的一切事务只能简单化处理,不能复杂化思考;只能极尽明朗,不能想象式关联。算度精细化的操作及确切化的分类在泾渭分明的专门化管理板块中找到了根据。
3.数字统治。科层组织所采用的一切手段都是为了指向实现效率的最大化。最直接、最有效的方式便是对于数字的使用。教育行政部门评价一所学校的办学效益是关于各种“率”的统计指标,升学率、重点率紧紧掐住学校的命脉。学校为了获得漂亮的数字,将对各种“率”的考察下移到教师与学生身上,将教师与学生的行为及表现都纳入到可计算的范畴中。
学校变成了由数字操控的组织。科层架构以量化思维为运作精髓,上级通过数字来管理下级,下级通过赢得高分来取悦上级。管理者与教师、管理者与学生、教师与学生统统都陷入到这一泥潭中,价值与情感被层层覆盖,只露出装满分数的脑袋。以形式理性为信仰,以数字为图腾的学校将人异化为可测量的物与可换算的符号,并津津乐道于量化所带来的便捷与有效。
二、受困于算度网络
教师所处的社会情境是一个纵横交错的网络,这张网并非是简单意义上的社会关系图景,而是充满着权力争斗与利益博弈的紧张结构。教师作为网中的一个结点,占据着核心的位置,在与其他主体的关联中,通过一系列资本交换展开行动,从而指向可能的社会流动。究竟是什么在维系着网络的运转,在操纵着主体的行动,又决定着教师的处境呢?归根结底,还是算度。通过算度,教师被规定在特定的位置上;因为算度,教师必须与其他人密不可分;围绕算度,教师不断地调整着自己的行动。
(一)教育网络中的双重算度
以科层制为主要形式的教育系统形成了一个不间断的网络,教师在整个层级架构中处于中间位置,教师遭遇双重算度的命运,承担“被算度”与“算度人”的双重职责。
被算度是指教师成为算度的对象,算度者以特定的规则、标准为依据对教师进行精细化地考量。在教育网络中,算度者由多元主体构成。这些主体按照权力的多寡、作用力的大小及直接程度可以大致作以下区分:
1.作为立法者的国家。在国家与教师的统治关系中,国家扮演着立法者的角色,通过订立算度教师的相关法律法规,提出教师资格的合法化条件,明确教师在政治共同体中的身份,赋予其应有的权利和义务。国家在其有限的领土之内,通过立法垄断了对教师的处置权与制裁权,要求教师臣服于国家意志,成为国家意志的传播者与代言人。
国家宏观算度的局限在于,笼统地针对普遍意义上的教师,落实到具体教师身上的精细化程度与直接性略逊一筹,国家意志要想真正地发挥效力还需要经过层级的转换。国家作为最高的权威形式,其所确立的教师算度规定都将成为一切算度行动的绝对准则,凌驾于其他算度主体之上。
2.作为阐释者与实施者的教育行政部门。教育行政部门既是阐释者,分解与转化国家意志;又是实施者,落实各项管理与监督任务。较之国家,教育行政部门对教师的算度更为直接,它直接面向教师开展一系列名正言顺的算度活动,如教师招聘、职称评定,通过齐常化的标准设定,数量化的等级划分,将一部分教师筛选出来,又将一部分教师挡在门外。在教师眼中,教育行政部门是不可对抗的权力聚合体,既有国家权威的黄袍加身,又精道于算度技术。
3.作为执行者的学校管理者。学校管理者将国家意志与教育行政部门政策细化成详尽的条条指标,囊括了教师行为链条中的各个环节,关涉到教师行动指向的方方面面。学校管理者对教师的算度是极端精细化与专门化的块状管理。学校各个部门根据其性质及统辖范围,将教师行为拆解成与之相匹配的若干板块进行分类算度,各板块相对独立,但总和却涵概了教师的一切相关,有的甚至还溢出了教师的职责本身。为了更多地瓜分算度权力,学校管理者不断地发明各种新奇招术,如教案必须手写等,令教师们苦不堪言。
算度与教师的关系并非仅限于此,教师角色中还有另一个面向,那就是——算度者。在教师与学生的这对范畴中,控制与被控制的关系显而易见,教师无论从体制认可、知识占有还是经验水平上都要优越于学生。教师是绝对的权威,他们可以掌控学生的一言一行,并总能收获绝对的服从。算度是教师管理学生最有力的武器,通过日常行为规范考核评断学生品行,通过频繁的考试给学生排名。教师孜孜不倦于算度技术的开发,将算度的“唯分数”演绎得合理合法。
长期处于压迫下的教师,本应能够深刻体悟被算度的滋味,推己及人地体谅同样处于被算度中学生的痛苦,但教师的算度行为不仅没有收敛,反倒变本加厉。是教师无法对学生作出共情式的迁移,还是算度技术实在是太方便了——便于管理、便于控制、便于抵抗意外?在效率至上的普遍逻辑下,算度的高回报能够让人放弃以人为目的的终极价值,即便自身也是受害者。
(二)内部系统里的自我算度
自我算度是一种由自身发出、又指向自身的审度方式。教师在算度网络中的位置建立在他人的期望与自我的认识中,这来自于教师多大程度地追随于外力的趋使,又多大程度地听从于内心的坚持。自我算度则是达成自我认识的核心机制。
自我算度的形成发生在与他人算度的互动中:一是自我算度一致于他人算度,二是自我算度不一致于他人算度。前者是指教师通过自我算度确证的自己恰恰就是他人按照外在标准计算出来的那个人,教师分不清自己究竟是自我成就的,还是外物塑造的。教师在极端一致的算度结论中走向了行为的自觉,教师内在的自我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统一。这种情况并非不可能发生。
教师是从适龄青年中挑选出来,历经机械化的切割、塑型及包装,再经由标准化的检验、审核,输出到体制内继续进行打磨的合格产品。教师的炼成不是绝对自我意识的作用,而是被逐步偷换为依附于各种外在参照的假冒的自我意识的胜利。教师崇拜并信仰外在于自己的精细化定义,将之视作真实的自己。自我算度不仅紧随着他人算度的结论,随意更改着自我赋值,还将算度的一套技术奉为自我改善的法宝。教师会计算达至自己预期目标的差距,如果课题研究能为自己赢得5分的话,他们便会毫不犹豫地选择去做。至于研究什么、研究是否发自内心地喜欢都不重要,重要的是——那值5分,“5分”便是意义。这是一种扭曲的自我异化,手段与目的相互颠倒,手段成为了目的本身。
自我算度不一致于他人算度又可分为:一是自我算度超越于他人算度。教师为自己立法,成为自己的定义者、审判者与导引者。教师能成为超越者吗?能够挣脱体制的束缚成为萨义德眼中的“流亡者和边缘人(exile and marginal),业余者,对权势说真话的人”吗?对此,不敢枉下定论。只是必须看到,自始至终所受到的算度意识的培养,始终优先的算度逻辑的根植,根深蒂固的算度影响的包围,无处不在的算度权力的压迫,已将教师可能超越的空间填充得所剩无几,试图在体制内的流亡几乎等于自掘坟墓。
第二种不一致来自于“他人算度压倒自我算度”。他人算度的胜利不是教师甘愿共谋的结果,而是委曲求全的退让与暂时的妥协。其积极意义在于,教师至少还有对自我珍视价值的坚守。其无奈在于,教师终究还是要在屋檐下低头,服从他人算度的摆布。这也是一种异化:如果个体在他人面前维持一种连他自己也不相信的表演,他就会体验到一种特殊的自我异化,对他人产生某种特殊的戒心。[8]但这种特殊的自我异化还有希望,希望在于“不相信”。
(三)社会空间内的全景算度
教育是社会的子系统,教育网络寓于社会网络之中。教师置于社会网络中,算度的触角已延伸到社会空间里所有活跃的、或潜在的关系主体之中,交织成一个全景式的画面。
教师首先要接受“无差别的家长”的算度,不管他们是什么职业,处于何种阶层,只要家里有学生,就注定要将教师当作观看的对象。家长是强大的算度者,但与体制内的三元主体又有所不同。
家长算度是自发的,而非制度性的授予。家长在算度教师这件事情上,全凭自愿与自主,无须借助于外力。家长的算度可以是去规则、去逻辑、去合理性的,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根据利益的赢损程度进行主观化的判断。这种没有章法的算度方式常常令教师们心力交瘁。
是散点式的,而非着眼于普遍。家长所关心的是教师对特定学生的关爱程度,包括精力投入、教育方式及成果产出等。至于教师是否公平地对待每一个孩子都不是家长算度范围中的条款,甚至教师可以不公平地对待其他学生,只要对自己的孩子尽职尽责,便是好老师。
是暧昧不清的。在匿名的满意度调查中,家长可以毫不手软地评价教师。当与教师面对面时,几乎所有的家长都笑容满面。家长的暧昧掺杂了担忧与急切的双重情绪,既害怕大刀阔斧令教师恼羞成怒,又迫切地想要通过间接的不留情面给教师以警醒。在家长前、后台两套算度系统的交互中,教师的备受煎熬可想而知。
其次,要接受“专家系统”的算度。专家的实质就是假定如果要把事情做好就需要有一定的知识,而这种知识是分配不均的,有些人比其他人拥有得更多,那些人就应该管理这些事情,那些正在管理的人就要肩负起事情如何进行下去的责任。[9]在高度现代性的社会里,自认为拥有更多知识的专家对教师的干涉达到了白热化的程度。他们武断地定义教师,建构出一套所谓的专业化的体系来算度教师,无视教师已有的接受与理解能力。许多专家更以不速之客的身份介入教师的生活,对教师指手划脚,仿佛教师非得顺着他们的思路改变不可。
在专家算度的过程中,教师自始至终都是沉默者。在“专家系统”这一社会最赖以信任的权威体系面前,教师的弱势地位显而易见。似乎,没有专家系统的支撑,教师一发言便是浅薄,一思考便是荒谬,一行动便是盲目。
最后,要接受“社会舆论”的算度。教师常常处于社会舆论的风口浪尖,社会舆论即便不关涉具体的教师,但仍指向普遍教师的集体;即便不必然导致一定的后果承担,但仍能逼得教师如坐针毡。义务教育阶段绩效工资的实施引发舆论热议,诸如“教师凭什么拿这么多钱”的质问不绝于耳。“有差别的社会成员”将教师的价值与金钱划上了等号,当价值不匹配于一定量的金钱时,心理便开始失衡,并企图通过社会舆论的制造,重建价值秩序。这种形式的算度无孔不入,它直抵教师内部,对教师施加连续不断的影响。
三、链接于传递系统
教师在社会文明及教育文化传递过程中扮演着极为重要的角色,一方面习得社会的知识、技能、价值观、惯例与习俗,另一方面将这些习得物转化为教育的内容复制给学生。这些学生中必定又有一部分人成为了教师,继续投身于循环往复的教育传递中。
(一)工具:被一致化的教师
一致化的基础教育生产出了一致化的学生,一致化的师范教育又使部分一致化的学生成长为了一致化的教师,一致化的教育管理不断巩固这种一致化,最终将教师异化为不断发挥一致化作用的工具。教师的一致化体现在方方面面,但从根本上决定教师行为本质机制的还得归咎于两种偏好:一是对等级标准的迷恋;二是对持续分类的冲动。通过等级标准被层层筛选出来的教师,将等级标准作为自身行动的根本参照。作为在体制内竞争的优胜者,他们的成功得益于等级标准的存在以及达至标准所付出的努力。当教师站上三尺讲台开始影响学生的人生时,这种作成功者的经验被传播开来,成为学生必须要认可的真理。
教师审视学生的出发点源自于等级标准,学生超出或不满于标准的部分都将变成批判与改造的对象,例如学生课堂上随意插嘴,课间追逐打闹。参照标准,这些行为确实不可姑息。但在这些不达标的行为表象下,是否蕴藏着另一种潜在价值呢?——例如随意插嘴的学生思维敏捷,敢于表达;追逐打闹的学生体力充沛,活泼开朗。这些也许并不必然,但终究是各种丰富的可能性,教育的本质不就在于挖掘这些可能吗?但教师并没有耐心去培育这些可能性,只要不合标准的行为稍一露头便会被果断扼杀,因为标准是唯一的,也是最优的,其他的所谓可能都非正道。
由于自己便是分类的受益者,教师丝毫也不掩饰自己对学生的分类冲动。在教师眼中,学生不再是一个个鲜活的个体,而是被挤干了的一层层抽象等级。考试排名是最常见的分类方式,根据分数高低将学生从第一名排到最后一名,从而区分出“优生”与“差生”。③教师陶醉在这种次序争夺游戏中不能自拔,甚至对排名的疯狂已到了“班级比完年级比,年级比完再与其他学校比”的境地。学生就这样在教师热情高涨的分类行为中找到了自己的位置。
(二)手段:反复重申的灌输
教师向学生传递知识、文化与规则的方法并不多,最为受用还是灌输,尤其对学生的规训与教化。这与学校教育的特征有关,也与服务于灌输的各种有利条件有关。
学校教育是一个周而复始的事业,除了新学生有所差异外,教育内容、教育方法等都大致相当,教师一旦形成某种固定化的框架便很难改变。教师只会按部就班地重复既有惯例,告知学生规则,并监督执行。
教师对学生教育影响的施加通常有两条途径,即言传与身教,而言传远多于身教。教师总有一套教育话语辞令库,使用频率最高的无非是那么几句:“现在不努力,以后要吃苦头的”、“自己不对自己负责,没人对你们负责”……这种翻来覆去的重复,一方面是因为教育中发生的问题如此相似,导致教师不自觉地做出类似“刺激-反应”式的自动化关联;另一方面在于反复的灌输本身能够起到再生产的作用,正如鲍曼所说,所有的话语都界定了它们的主题,都要守护其界定的独特性以保证话语的完整,并通过对自己的反复重申再生产它们自身。[10]
学校仪式的作用也不可小觑。仪式首先是社会群体定期重新巩固自身的手段。[11]学校仪式通过“周期性地”举行,不断重申着教育的信仰,即所制定的规范与所珍视的价值,将大家快要失去的记忆重新唤醒,在大家快要松懈的时候将他们再重新灌输一遍。
学校物质环境则是一种无声的灌输,它们安静地待在那里,默默地散布着各种讯息。墙壁上醒目的校风校训、写满的规章制度、在公告栏中陈列的奖杯奖状、优等生风采展示,无不彰示着对规范与纪律的严苛,无不宣扬着对精英与优秀的崇拜。这是一种无声无息却又强大无比的力量,学生慢慢地修正其价值观念以迎合教育者的口味,以能在光荣榜中出现为成功的标识。学校物质环境,这种反复重申的灌输形式已经无法用确定的次数来计算了,因为它的发生无时无刻,并且无处不在。④
教师习惯性的重申,伙同仪式及物质环境的全力辅助,实现了教育自身灌输功能的最大化。传递在灌输这种直白且机械的方式里找到了自信,并在传递体系持续的有机运作中对其委以了重任。
(三)旨归:性情倾向系统的复制
人之内心秩序的建立是社会内部秩序得以维持的深层需要,人之内心秩序建立的过程也就是人屈尊于社会的权威之下不断调整、更新、重构与再造的过程。生成人之内心秩序最根本的机制是惯习,它是一个开放的性情倾向系统,不断地随经验而变,从而在这些经验的影响下不断地强化,或是调整自己的结构。[12]人的惯习始终寓于教育的传递系统中,发生在教师向学生施加教育影响的这对关系中。
教师所传递的不仅是单方面的知识、技能、规范或是习俗,更多的是“全面算度”的行动逻辑与“效率至上”的优先策略。这种传递至少可以被拆解为三项程序——习得、内化与复制。
习得是教育传递的前提。教师首先必须以已知者、先知者与多知者的角色进入到作为未知者、后知者与少知者的学生群体中。“知者”作为教师成其为教师的条件性要素要求教师事先习得以及之后持续不断地习得。教师的习得在多种层面、多种场景、多种情境中进行,或重叠交叉,或相互分离;教师的习得在多重意图、多重指向、多重追寻中展开,或直抵要害,或迂回盘旋。作为“曾经的学生”,教师学习意识形态与社会规则,努力成为合格的社会公民;作为“潜在的教师”,教师修炼师德修养与职业规范,努力成为合格的人民教师;作为“现实的教师”,教师屈从于规章制度与标准体系,努力成为不逾矩的职业人。不管是“曾经的学生”、“潜在的教师”还是“现实的教师”,其所习得的内容都构成了作为“知者”的重要经验。
内化是教育传递的关键。教师必须不同程度地认同社会主流价值体系,根据社会权威的偏好采取行动。要想做到这一点,仅仅依靠制度的规约是不够的,只有源自于教师内心自发的约束力,才能实现教师群体心甘情愿地对传递使命的担当。这要求教师将习得的准则——算度——整合到自身内部系统中去,将之转换为内心的自觉。事实证明,大多数教师都是温顺者,要么在法定权威的框架内谨言慎行,要么在规则允许的范围内争夺利益。标准的边界始终横亘在教师的内心深处,在合矩的奖赏与越轨的惩戒中,社会规约下的权威偏好系统逐渐占领教师性情倾向系统,当二者浑为一体、难以区分时,内化便已悄然发生了。
复制是教育传递的目标。个体自身成为生活世界中的社会性的再生产单位。[13]当教师内化社会的准则为支撑自身惯习的依据,并深信不疑时,便点燃了教师将之复制到学生身上的欲望。教师将自己习得并内化了的一套行动逻辑与优先策略视作抵达成功彼岸的不二良方,他们以“过来人”的角度循循善诱,不由分说地向学生灌输一种生存专断,即分数的差距便是人与人之间的差距等,从而再生产出如他们般顺从的未来公民。在以“算度”为主旨的惯习向学生输入与复制的过程中,教育场域与社会领域、儿童世界与成人社会的不适应感与不平衡感逐渐被消除,学生持续地体悟教师向他们传递的惯习的优越感,当学生也深信不疑时,复制便成功了。
不难发现,教师与算度的关联比任何他群都更为紧密、更为深刻,探清教师与算度关系本质的过程,就是帮助人们认识教师生存状态、理解教师行动逻辑的过程,也是催促人们看到无比真实的现实世界,并面对扼要概括的社会结构以及其中暗流涌动的林林总总的过程。
注释:
①如同骨干教师计划一样,每年给2-3个名额,只有领到许可才可以准备生子,而其他有意愿的人只能按序排队,耐心等待。
②学生群体也有相应的层级分类,有大队长、副大队长、班长、副班长、班委、组长、课代表等,但这种分类并没有严苛的权力等级,尚不能纳入科层制的范畴,在此不作关联。
③现在许多对“差生”的称谓已调整为“后进生”,但仍改变不了教师分类学生的实质。
④需要说明的是,学校仪式及学校物质环境的反复灌输并非仅以学生为对象,教师同样也是被灌输者,但考虑到本节主要强调教师的“传递者”身份,在此故意弱化,不作阐述,以免出现不必要的混淆。
[1][4][5][法]P.布尔迪约,[法]帕斯隆.再生产:一种教育系统理论的要点[M].邢克超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2:68,76,69.
[2][美]C·赖特·米尔斯.社会学的想像力[M].陈强,张永强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29.
[3][英]齐尔格特·鲍曼.通过社会学去思考[M].高华,吕东等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172.
[6]安云凤,田国秀.当代学校组织的科层特征分析[J].当代教育科学,2010,(22).
[7]张新平.对学校科层制的批判与反思[J].教育探索,2003,(8).
[8][美]欧文·戈夫曼.日常生活中的自我呈现[M].冯钢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200.
[9][10][英]齐格蒙·鲍曼.现代性与大屠杀[M].杨渝东,史建华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2:256,272.
[11][法]爱弥尔·涂尔干.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M].渠东,汲喆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507.
[12][法]皮埃尔·布迪厄,[美]华康德.实践与反思——反思社会学导引[M].李猛,李康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4:178.
[13][德]乌尔里希·贝克.风险社会[M].何博闻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4:109.
(责任编辑:曾庆伟)
宗锦莲/江苏省教育科学研究院基础教育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博士,研究方向为教育学原理、教育社会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