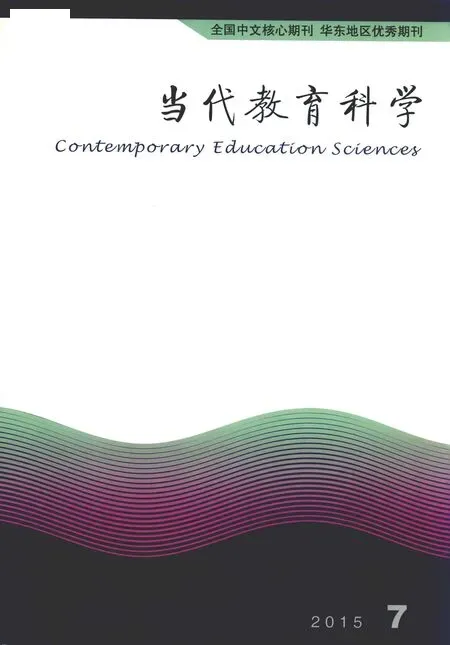施瓦布的科学课程研究及其启示*
●高 嵩
施瓦布的科学课程研究及其启示*
●高 嵩
通识教育是施瓦布进行科学教育探索的起点,更是其一生的教育生涯的研究基础,但是他的理论都是基于他当时的历史背景下遇到的问题提出的,因此当后人仅关注于其理论的只言片语时就会忽视了其适切性而造成实践中的偏差。站在历史的背景下对施瓦布关于通识教育和科学课程的探索历程进行分析,对其教育思想的形成进行整体的、历史的解读,可以为我国当下的课程改革提供借鉴。
施瓦布;科学探究;教育方法;课程设置
自上世纪至今,施瓦布都是世界教育领域影响最大的教育家之一,他的科学探究理论、学科结构理论、教育实践理论等在今天看来仍有着巨大的生命力。纵观施瓦布50多年教育探索的主题和动力,可以说都源自他大学毕业后便全身心投入的通识教育课程,都是他进行通识教育研究的后续发展。通识教育开启了施瓦布对科学教育的探索之旅,也奠定了他思考教育问题的基础和风格。他对教育的研究是全方位的,如科学教育、课程设置、课程评价等各方面均有深入的研究。同时,施瓦布是位教育实践家,在对教育现实问题的解答中不断探索并调整自己的理论,在脱离其研究背景的情况下仅仅对其文字进行理解很容易导致对其思想和理论的误读。因此,本文在历史的语境下,还原施瓦布进行通识教育课程研究的轨迹,探索对施瓦布教育理论的合理解读,从而有利于对施瓦布教育教学理论更好地继承和借鉴,以促进当下科学课程改革的更好发展。
一、施瓦布科学课程研究的背景
20世纪初期,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美国教育领域以实证和科学为特色的进步主义得以迅猛发展,从而降低了对西方传统人文主义的继承,这引发了传统教育的不满,招致了以恢复西方悠久的人文主义传统为宗旨的永恒主义者的批评。尤其是美国在1929年陷入空前的席卷全球的经济危机之时,各阶层的矛盾激化。这场危机进一步导致了对进步主义教育理念及方式的怀疑和反省,一时间,进步主义、要素主义、永恒主义等各主义间的争论此起彼伏。1930年,永恒主义的核心人物赫钦斯(Robert Maynard Hutchins)出任芝加哥大学校长,此时的他刚过30岁,风华正茂,有着强大的号召力与行动能力。赫钦斯及其拥趸者认为:教育的根本目的在于发展人性,从而使人可以表现出和谐、自制和文明,成为高尚的人,因此“自然主义、实用主义和科学哲学是不适当的,学校需要另外的指导价值和标准”,[1]而这些价值和标准存在于西方的传统之中,并且与不因时代而改变的传统的自由艺术有着密切的联系,教育的任务则是要使青年人理解并掌握它们。永恒主义者认为,阅读西方名著是获得这些传统的有效途径,[2]赫钦斯在《高等教育》一书中指出,“永恒学科首先是那些经历了许多世纪而达到的古典著作水平的书籍”。[3]他身体力行,在芝加哥大学推行他的名著阅读计划,力求让学生在名著的阅读中发展灵魂和理性,获得关于人的价值、人的命运的永恒真理,从而掌握通向美好生活的手段。
赫钦斯在芝加哥大学出任校长的头几年,也正是施瓦布在这里攻读学士和硕士学位的时期,他有机会接触到赫钦斯的教育思想,并深受其影响。在1937年施瓦布拿到生物学硕士学位并留校任教之后,便积极投身于赫钦斯引领的课程改革和开发的事业中去,并成为西方名著编辑委员会的委员。[4]
作为赫钦斯的拥趸,同时又有着物理学和生物学背景,施瓦布首先要考虑的是将科学课程与名著阅读课程体系承接起来。因此,在理论上论证科学课程在通识教育中的地位和作用是他要解决的第一个问题。
二、施瓦布对科学课程的规划及实施
(一)科学课程的地位和功能
在永恒主义的课程体系中,哲学、文学、历史属于理智训练的内容,数学、科学和艺术则属于理智训练的方法,而读、写、算则作为训练得以顺利实施的工具和技巧。[5]在刚刚加入赫钦斯团队的时候,施瓦布对于通识教育的思想还不成熟,但是他相信名著的重要性,同时他也认识到近代兴起的自然科学对人的成长也应该有着重要的意义,但是科学课程与传统课程之间应该形成怎样的关系,施瓦布并不十分清楚,同时他认为科学课程与哲学、宗教等传统课程不能矛盾,而且在功能上这些课程应该相互补充。
随着名著阅读课程的开展,施瓦布不断总结实施过程中的经验和问题,并在与他人的合作中形成了自己对名著阅读课程、科学教育、人的成长等方面的看法,尤其是与麦基翁①的合作,使他对各个问题有了更加深刻的反思,在教育理念上似乎更接近杜威的观点。此时,施瓦布开始突破了赫钦斯关于传统课程的描述,认识到了科学发展的多样性和科学实践的多样性,[6]他力图使科学课程既能与文化连在一起,又能保持科学的特色。于是施瓦布进一步提出“科学课程应把艺术分析的部分留给人文和哲学等学科”,在“不贬低传记知识和神话知识的情况下”,科学课程能够“赋予人们关于世界的知识”,为人们提供一种“批判性地理解人类知识的指导性的基础”,通过进行科学课程的学习,学生们可以“把握学科与领域、方法与内容、事实与观点之间的联系与区别”,通过“进行适合于科学学科的那些能力和判断力的实践”,通过自我教育,提升自身完成任务的能力。[7]
可见,在施瓦布看来,科学教育在整个教育体系中应该与其他学科互补,在不同的领域对人的成长起着虽然不同但都重要的作用。人文、哲学和艺术等知识的学习,可以发展人的理性、道德和精神,而科学教育则可以提升人的智慧、技术和能力,而这些对于社会及个人的发展都是重要的。在他及其同事的努力下,名著系列中也有了自然科学的书籍,如牛顿、麦克斯韦等人的著作,并且实验也成为了学习的重要方式。
(二)科学课程的设置
教学的目的决定着教学内容的设定和教学方法的选择。从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在永恒主义者那里,知识并不是第一位的,他们意图将课程与教材统一于西方的经典名著,并在名著的阅读中获取理智,发展灵魂。在为学生列出的一百多部名著中,基本囿于人文领域,并且三分之二发表于1700年之前,自然科学方面的则多为古希腊和古罗马时期的,近代的只有牛顿的《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和麦克斯韦的《电磁学》。[8]施瓦布自己也阅读了大量的原始文献,也正是在研读名著的过程中,他接触到了亚里士多德、杜威等人的作品,并逐渐形成了自己对科学课程在通识教育中的地位以及价值的理解,他认为科学课程的根本是让学生掌握研究和探索自然界未知事物的方法,而最好的学习方法就是尽可能地让学生投入到探究当中。[9]
在40年代末,施瓦布提出了三年通识教育课程规划,其中自然科学课程主要包括物理学和生物学,各占一年半的时间,而化学、心理学等相关学科则融于其中。此课程体系并不是严格地按照物理学或生物学的学科结构来组织,而是围绕着“数量相对较少的主题”来展开。以物理学的第三个单元为例,这个单元学习的主题是“原子结构理论”,教学进程并不按照由已知的与原子理论相关的知识入手,而是通过介绍放射性物质的发现和解释的历程,让学生意识到人们在探索原子结构问题的过程中所经历的事件、观察到的现象、产生的问题,在展示人们寻求解释的过程中,玻尔的原子理论、电荷与电磁场间的关系等也随之向学生展示,让学生体会到科学“理论在各种明显不同的现象实体中的统一作用”。[10]在教学中向学生提供科学课本,但更重要的是一系列经过选择和编辑的论文,[11]二者相互补充。论文向学生展示了科学家在研究中遇到的问题以及他将现象与结论结合的方式,而教科书则与论文进行关联,为理解论文提供了理论资料和知识背景,由此学生们既能够关注问题的探究,也关注了知识本身。
(三)科学课程的实施
虽然施瓦布最初积极参与到了永恒主义的课程建设中,但是随着教育实践的深入,尤其是在深刻思考了科学本质及科学教育的价值之后,施瓦布的教育理论最终偏离了赫钦斯的教育思想,施瓦布始终恪守的原则是“如何促进学生发展”,这样,非常系统和严格的知识并不是他主要关注的问题。
他认为“科学课程赋予人们知识”,并“提供批判性地理解人类知识的指导性的基础”,但这两部分不是孤立的,而是统一于科学实践的过程之中。他力图让学生重新经历科学家的探索历程,在现有条件下的有效方式就是阅读名著和论文。在施瓦布的理想中,学生可以与作者进行跨越时空的交流,通过关注作品的细节,还原作者形成问题域的过程,以寻求对原著的适切的解释。他要求学生不仅要明白论文的结论是什么,而且需要确定科学家选择证据的种类和原因,从而体会科学家产生结论的方式,并形成对所用方法有效性的判断。在此,学术论文便是“科学探究的例子、结论的容器和智力活动的核心”,学生进行的是“适合于科学学科的那些能力和判断力的实践”。[12]
施瓦布的科学教育围绕着对论文的理解和解释展开。学生需要“仔细阅读和讨论”论文:每周要经历三小时的讨论,为更好地理解论文,每周还安排了两小时的实验。教师的职责是帮助学生认识论文所涉及的现象,理解其中蕴含的问题,具体说来包括:作者要解决什么问题;他要达到怎样的结论;现有的条件怎样;为证明结论,他需要搜集怎样的信息,并且在实际操作过程中遇到了什么困难以及他是如何克服的;他利用怎样的方法处理信息;他是怎样限定他的问题域的;研究结果有效性和意义怎样。在后续的系列论文中,学生需要进一步比较相关论文,分析研究相同现象的不同作者分析的观点、形式及意义、差异性来源的变化。通过这样一系列的学习,施瓦布希望学生在寻找答案的过程中,不断发展“理解科学中的重要问题、理解解决问题的方法”及科学发展的多样性的问题,进而形成阅读、理解和研究的习惯,形成自己的问题,在“数据、相互联系、深度和详细程度等方面”,显示出主动的特征。
(四)施瓦布科学课程失败的原因分析
虽然在实施伊始人们对通识教育寄予了极大的期望,施瓦布更是投入了极大的热情并为之付出了十多年的努力,但包括科学课程在内的通识教育课程未取得满意的效果,终于在50年代后期难以为继,其原因主要来自三个方面。
首先是该课程的主导者,如赫钦斯、阿德勒(Adler)、麦基翁和克兰(Clarenee Faust)等人,他们自身对课程的构想存在着极大的不同。克兰、麦基翁等人认为“后代从罗马时代继承下来的讨论人文科学的方式绝不是唯一的必然的方式”,人类文明既是课程的目的,又是课程的手段,教育应解答文化与社会如何统一于个人的经历问题。这与赫钦斯的永恒主义思想相差甚远。随着课程改革的进行,施瓦布的思想逐渐靠近麦基翁,而其他教师所持意见更加繁杂,在课程实施过程中,这些不同观点之间的差异被放大,必然引发课程实施过程中的混乱。
第二,课程对教师要求太高。课程要求教师自己必须要对所列清单上的科学论文或名著具有深刻的见解,能够理解作者在研究过程中文化、个人和群体间的关系,对问题和过程的影响及在研究过程中的统一,并且具有对论文的研究引向深入的能力。然而对大多数教师来说,是难以领悟这些教育思想的实质的。
第三,鉴于通识教育产生的时代背景,在课程实施方法上,存在着强调文化要素和解释方法的肤浅的古典主义思想。科学研究是件非常复杂的社会活动,既与个人的知识储备、行动能力、研究方法有关,也与社会支持、外部环境等因素有关,[13]因此,科学活动在一定程度上是随机的,不可复制的。而学生则面临着与论文作者迥然不同的新的问题,这样,寄希望通过阅读文献名著提升学生的探究能力便有点缘木求鱼了。因此在实施过程中,学生普遍感到这门课程过于困难。
为改善这种情况,施瓦布及其同事在1943年对通识课程进行了调整,但并未有较大的起色,在投入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之后,施瓦布发现学生仍旧不能“灵活地掌握论文所提供的科学世界的模型”。在50年代后期,施瓦布在大学的地位已逐渐边缘化,通识教育实践也走到了尽头。但是对施瓦布来说,他对通识教育的探索一方面奠定了他以后研究教育问题的基本方法;另一方面,他的教育理论在科学教育领域产生了重大影响,在科学教育领域也有了自己的拥趸;第三,施瓦布对通识教育的尝试,也为其后来参与到60年代轰轰烈烈的基础教育科学课程改革中奠定了基础。
三、施瓦布科学课程思想及研究历程对我国科学教育的启示
虽然施瓦布的课程改革最终并未取得理想的效果,但是他对课程、尤其是科学课程的设置、实施所做的探索,为我们后人留下了宝贵的资料,并引发我们对当今教育的深刻思考。
(一)科学教育目标应该多元
在对教育目标的选择上,施瓦布“既关心作为知识的科学和课程,也关心代表技能和技术主体的科学和课程”,但是他一直致力的还是“探究习惯”的科学。然而这种习惯或能力是内隐的,难以显性地引导学生通往“康庄大道”,因此越来越多的人脱离了他的团队。他遇到的困境我们今天还在面临着,通过接受教育而改善生存条件依然是学生求学的动力之源,而面对多样的学生,教育时空的有限性与社会对学生要求及学生自身发展的多样性之间的矛盾仍旧不可调和。学校不是为学生所有的未来准备好一切,而是为其日后的发展打下基础。在科学技术日益深入人们生活的各个层面的今天,科学教育的目标也趋于多元化,正如美国《国家科学教育标准》提出的科学课程的目标是经过学习,学生能够“由于对自然界有所了解和认识而产生充实感和兴奋感;在进行个人决策之时恰当地运用科学的方法和原理;理智地参与那些围绕与科学技术有关的各种问题举行的公众对话和辩论;在自己的本职工作中运用一个具有良好科学素养的人所应有的知识、认识和各种技能,因而能提高自己的经济生产效率。”[14]我们也应与施瓦布一样,超越以知识或以技术为本位的课程观念,我们教育的核心任务是培养“积极思考的大脑”。
(二)科学探究是学生不断选择与建构的过程
在教学手段的构想中,无论是施瓦布当年,还是课程改革的当下,科学探究都是核心的教学方法,然而科学探究如何实施,不同的人有着不同的见解。施瓦布希望通过通识课程让学生理解名著的合理性,并移植其研究的方法,从而成为具有探究能力和习惯、积极思考并付诸行动的人。我们今天的课程改革也提升了科学探究的地位和要求,并希望学生在科学探究的过程中,建构知识、领悟方法和升华情感。但是对于科学探究如何操作仍旧见仁见智,[15]以致许多教师在实施中迷茫。而说到本质上,科学探究是一个不断选择和建构的过程,[16]学生在学习过程中,会将什么置于其研究的范围,会提出什么样的问题,或发现什么规律性,什么会引发他的兴趣,他将采取怎样的行动,在他与事物相互作用的过程中,他继续的路径,以及新的现象、实施的行动,对其原有的知识具有怎样的改变和更新等等,这一切,对于学习者而言,既使从整个人类发展的阶段来看,其正在经历的外部世界和内在的心理活动也是独一无二的,因此皮亚杰认为,学习即是创造,即是发明。因此施瓦布的那种“基于探究的探究”仅仅提升了学生的“阅读能力”也就不奇怪了。我们要提升学生的科学探究的能力,提升其科学素养,必须使其置身于对科学问题的思考和解决的情景中,探究的能力,只有在探究真正的科学问题的过程中才能提升。
施瓦布不仅对于科学教育与通识课程有着深入的研究,他对课程的评价、课程的情感,课程的设置等诸多方面都有着深刻的见解,并且施瓦布一生都执教不辍,至80岁仍奋斗在教学一线,他关于课程、教学的理论,在半个多世纪之后,仍有着强大的生命力。对当今课程与教学中遇到的问题,他睿智的思考仍旧可以给我们启迪。他的著作,对于我们今天的课程改革仍有着重要的借鉴和指导作用。当然我们也应该清楚,我们今天面对的问题已经大大不同于施瓦布所处的时代,我们也应该如施瓦布对待杜威、亚里士多德等先贤的著作一样,要在明确自身所面临问题的基础上有针对性的吸收,也要看到其失败和不足,形成对当下教育问题的借鉴,从而形成符合当下面临的教育状况的研究领域和研究思路。这才是对其理论的弘扬和发展。
注释:
①里查德·麦基翁(Richard Mckeon)(1900-1985),杜威的学生和同事,美国哲学家,曾任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文艺复兴和中世纪哲学首席教授、芝加哥大学教授,主张通过名著课程计划来实施通识教育。
[1]罗伯特.梅逊著.陆有铨译.西方当代教育理论[M].北京:文化教育出版社,1984,27.
[2][5][8]陆有铨.现代西方教育哲学[M].郑州:河南教育出版社,1993,160、90、90.
[3]华东师范大学教育系、杭州大学教育系编译.现代西方资产阶级教育思想流派论著选[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80,208.
[4]金传宝.施瓦布、巴格莱和杜威论课程理论与实践[J].山东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4,(1).
[6]韦冬余.论施瓦布探究型课程思想[J].全球教育展望,2012,(11).
[7][11][12]Ian Westbury,Neil J.Wilk主编.郭元祥,乔翠兰译.科学、课程与通识教育[M].北京:中国轻工业出版社,2008,12-13、40、45.
[9]张亮.“探究”教学的历史嬗变[J].当代教育科学,2008,(12).
[10]J.J.Schwab.The natural science:the three curriculum,the idea and practice of General Education:an account of the college of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M].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50,149-198.
[13][法]布鲁诺.拉图尓.[英]史蒂夫.伍尓加著.张伯霖,刁小英译.实验室生活:科学事实的建构过程[M].北京:东方出版社.2004,133-228.
[14]National Committee on Science Education Standards and Assessment, National Research Council,National Science Education Standards[M].Washington,DC:National Academy Press,1996,13.
[15]姜涛,廖伯琴.方法与建模:两种竞争的探究教学模式评析[J].课程·教材·教法,2012,(10).
[16]高嵩,王其超,洪正平.科学探究中的科学解释[J].山东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9,(6).
(责任编辑:孙宽宁)
重庆市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点项目“普通高中科学类模块课程教学实施调查及国际比较研究”(项目编号:10SKB15)。
高 嵩/西南大学科学教育研究中心博士后,山东师范大学物理与电子科学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为课程教学论,科学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