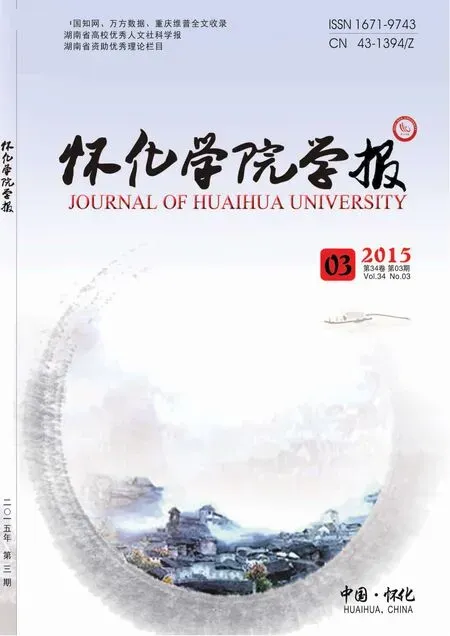1958:“再批判”的战略
于宁志
(徐州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人文社科系,江苏 徐州221004)
一、“再批判”的发动
《文艺报》1958年第2 期刊登了“再批判”专栏,一共六篇文章,分别是:《王实味的〈野百合花〉》、《种瓜得瓜,种豆得豆——重读〈三八节有感〉》、《莎菲女士在延安——谈丁玲的小说〈在医院中〉》、《斥〈论同志之‘爱’与‘耐’〉》、《罗峰的“短剑”指向哪里?——重读〈还是杂文的时代〉》、《驳艾青的〈了解作家,尊重作家〉》。《文艺报》“再批判”专栏刊出后,各地报刊纷纷响应,《北京文艺》第2 期、《文艺月报》第3 期都组织了“再批判”专栏,《光明日报》、《解放日报》、《羊城晚报》等也发表了批判文章。
《文艺报》第2 期经过毛泽东修改的《再批判·编者按语》写道:
王实味、丁玲、萧军的文章,当时曾被国民党特务机关当作反共宣传的材料,在白区大量印发。萧军、罗峰等人,当时和丁玲、陈企霞勾结在一起,从事反党活动。丁玲、陈企霞等在此后的若干年中进行了一系列的反党活动,成为屡教不改的反党分子。
……
上述文章在延安发表以后,立即引起普遍的义愤。延安的文化界和文艺界,针对这些反动言论展开了严正的批判。15年前的那一场斗争,当时在延安的人,想必是记忆犹新的。去年半年,文艺界展开了对丁玲、陈企霞反党集团的斗争和批判。许多同志在文章和发言里,重提起了他们15年前发表出来的这一批毒草。
1957年,《人民日报》重新发表了丁玲的《三八节有感》。其他文章没有重载。“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许多人想读这一批“奇文”。我们把这些东西搜集起来全部重读一遍,果然有些奇处。奇就奇在以革命者的姿态写反革命的文章。鼻子灵的一眼就能识破,其他的人往往受骗。外国知道丁玲、艾青名字的人也许想要了解这件事的究竟。因此我们重新全部发表了这一批文章[1]。
1942年,王实味的短文贴在延安最高学府中央研究院的整风壁报《矢与的》上,引起轰动,看的人很多,像赶庙会一样。王实味简直成了“革命圣地”的明星。这引起了毛泽东的高度重视,他深夜提着马灯去,要弄清王实味到底说了些什么,为什么有那么大的影响力。三年后,毛泽东还说:“四二年,王实味在延安挂帅,他的墙报,引得南门外各地的人都去看。他是‘总司令’,我们打了败仗。”[2]《野百合花》发表于1942年3月13日和23日《解放日报》文艺副刊,在延安引起震动,但引起国民党的注意却是在半年以后。1942年6月9日《解放日报》发表范文澜的《论王实味同志的思想意识》,指出“《野百合花》已被反共分子利用,广为宣传,当作反共工具”。范文澜的文章在《解放日报》发表后,又刊发于重庆出版的《群众》杂志第七卷第15 期,同期还有周文的批判文章《从鲁迅的杂文谈到王实味》(原载《解放日报》1942年6月16日)。国民党中央图书杂志审查委员会从《群众》杂志上看到这两篇文章,将报告送到高层,建议由中统进一步调查,中统获得《野百合花》一文,又从《解放日报》上找到类似的文章,包括丁玲的《三八节有感》,编写了一本小册子,书名为《关于〈野百合花〉及其它——延安新文字狱真相》,加上引言和按语,印刷出版了,时间是1942年9月。这离范文澜说《野百合花》已被反共分子利用已经过去了三个月。“范文澜在《野百合花》被敌特利用的事实尚未出台之时,就预支了这一‘证据’,就是要制造一个被敌人拥护的前提,这不能不让人感慨其良苦用心了;而历史的迷惑还在于:正是范文澜提前预支证据的大批判文章,才引起敌特的注意,终于使虚构的证据成了事实。”[3]“再批判”的批判者说国民党特务机关“翻印”了王实味等人的文章,其实,中统只是以《野百合花》等文提供的素材,进行加工再创作,并不是翻印。因为重读原文,《野百合花》等文提供的只是自我批判的精神,翻印达不到反共宣传的目的。延安整风运动中,对王实味的《野百合花》与丁玲的《三八节有感》等一批杂文,在性质上曾做过“敌我矛盾”与“人民内部矛盾”的区分,王实味被定为“托派分子”,其他人并没有予以追究。他们的文章也只有王实味和丁玲的杂文在报纸上被公开批判过,其他的“毒草”没有被正式批判。因为,那时批判的中心是王实味。到了“再批判”,批判的对象却增加了萧军、丁玲、艾青等人。
萧军1948年被批判,随后被扣上“反苏、反共、反人民”的罪名。丁玲在1955年被作为“丁、陈反党小集团”批判,后来结论又被推翻,但1957年“反右”运动时重遭批判,周扬在1957年9月作协党组扩大会议上认为丁玲1942年发表《三八节有感》,“和王实味、萧军等人共同反党”。为了配合周扬的讲话和对丁玲的批判,中国作协党组印发了一份名为《“三八节有感”、“野百合花”及其它》的材料。这份材料除翻印丁玲、王实味等人当年的文章,还翻印了中统的《关于〈野百合花〉及其它》一书。据有关人员回忆,这份材料引起了毛泽东的高度注意,批示重新批判当年延安的这批“毒草”。《文艺报》得知毛泽东的批示后,组织了一些批判文章,加上编者按语,以《对〈野百合花〉、〈三八节有感〉、〈在医院中〉及其它反党文章的再批判》为总标题,报送毛泽东。1958年1月中旬,毛泽东收到报告,把总标题改为“再批判”,而且认真修改了编者按语,强调了这些“毒草”的“反党”、“反革命”的性质和对其批判的重要意义[4]。
二、“以革命者的姿态写反革命的文章”
《文艺报》专栏“再批判”的“毒草”主要指王实味的《野百合花》、丁玲的《三八节有感》、萧军的《论同志之“爱”与“耐”》、罗峰的《还是杂文的时代》和艾青的《了解作家,尊重作家》。
王实味的《野百合花》是一组文章,原载于1942年3月13日和23日延安《解放日报》文艺副刊。王实味说这组文章以野百合花为总标题,是因为野百合花“不似一般百合花那样香甜可口,却有更大的药用价值”,其用意是对革命阵营内部的不良现象予以批评。延安整风运动时,发表了大量的批判《野百合花》和王实味的文章,许多文章先入为主,故意曲解,无限上纲,甚至辱骂攻击。1958年对王实味的“再批判”依然如此。
在《野百合花》的《前记》里,王实味追忆了女革命者李芬从容就义的情景,然后说:“在这歌转玉堂春、舞金莲步的升平气象中,提到这样的故事,似乎不太和谐,但当前的现实——请闭上眼睛想一想吧,每一分钟都有我们亲爱的同志在血泊中倒下——似乎与这气象也不太和谐!”批判者认为王实味“装模作样地”“追念李芬”,“把自己装扮成对敌人有着‘狂烈’的‘毒恨’和对同志有着‘狂烈’的‘热爱’的革命战士”,“借用死者的血染红了自己的面孔之后”,便开始了“巧妙的攻击”,“把生活中正当的健康的文化生活夸大、污蔑成歌舞升平的气象”。当全国人民把“民族生存、解放的线索系在延安的红旗杆上”时,王实味却“咬牙切齿地诅咒延安、辱骂延安,把延安描绘成昏天黑地的、没有‘爱’、没有‘温暖’、‘到处乌鸦一般黑’的世界”。“王实味在‘野百合花’里的污蔑、捏造、诽谤,还有许多”,《野百合花》“形象地表现了他对延安的‘狂烈的毒恨’”,因此王实味是“暗藏的敌人”[5]。
《野百合花》要求“爱”和“温暖”,批判者认为“王实味玩弄的是超阶级的‘爱’和‘温暖’的字眼,他歌颂的‘青年’也是一种虚幻的超阶级的‘人’的存在。实质上是一种资产阶级人性论的腔调。”[6]“王实味所爱的是那些具有反党思想反党情绪的人们,而对于忠实于党的同志和领导者,则咬牙切齿地恨之入骨。”[7]
王实味希望人们重视青年人的“牢骚”和“不满”,以此发现问题,消除不合理现象。但批评者认为,青年人思想上不能克服小资产阶级意识,对革命纪律、党的领导、民主集中制有些不习惯甚至有些抵触情绪,以至犯了错误,挨些批评,自己不认真改造,却牢骚满腹。王实味鼓励青年“发牢骚”、“大胆地揭破”,实质是引导青年“大胆地攻击党和人民”[6]。
针对《野百合花》批评的“衣分三色、食分五等”现象,批判文章说:“为了照顾某些负责同志和一些老同志的身体,他们的生活比一般同志稍微好一点点,这完全是必要的,合理的”。王实味要求的“绝对平均主义”,是“农民小资产者的一种反动性的幻想”[7]。还有的批判者说,王实味“抓住了延安某些知识青年的平均主义倾向”,“把革命者生活待遇上的些微必要的差别,夸张为‘衣分三色、食分五等’的‘等级制度’,笔锋一转,就把青年和党的领导者尖锐地划为对立的地位,把党的领导者扮为‘异类’”,王实味“煽动青年”“对准革命的领导者进攻”,“拿出全副‘生命底新锐的力’去反党、攻击党对革命事业的领导”[6]。
批评者总结说,王实味是“混进党内来的托洛斯基分子”、“混进革命阵营中来的反革命分子和阶级异己分子”,“冒充着革命阵营内部的‘自我批评’的姿态来对革命进行袭击”,他所做的一切都是“枪口对内”,“攻击革命根据地”。他把“革命圣地”“描写成漆黑一团,简直是一个黑暗的封建王国”,甚至“咒骂延安的天‘必然要塌下来’”。“他捏造事实或有意扩大我们的错误和缺点,目的是破坏我们的党,削弱党的领导者的威信,瓦解革命的队伍和政权”[7]。
丁玲的《三八节有感》发表于1942年3月9日延安《解放日报》文艺副刊。4月初的一次高级干部学习会上,《三八节有感》受到严厉批评。4月6日,《解放日报》发表克勉来信《“轻骑队”及其他》,在对“轻骑队”提出批评后,也批评了丁玲的文章。之后,丁玲做了检讨并转而积极批判王实味。
1958年对《三八节有感》的批判文章有王子野的《种瓜得瓜,种豆得豆——重读〈三八节有感〉》、王慧敏的《丁玲揭起的一面反党黑旗》和罗洪的《读“三八节有感”的感想》等。
丁玲在《三八节有感》中针对延安存在的严重的女性歧视,作了直率的批评:“延安的女同志”“不管在什么场合都最能作为有兴趣的问题被谈起。而且各种各样的女同志都可以得到她应得的诽议”[8]。1958年的批评者却否认丁玲指出的事实的存在,他们认为,丁玲“对党中央所在地的延安,嗅不到革命大家庭的温暖、看不到妇女翻身的事实、看不到革命斗争的远景。她所看到的,只是女同志被诽谤,结了婚不好,不结婚也有罪等等”[9]。有的批评文章说:“在丁玲的笔下,延安的妇女……都是男人诽谤、嘲弄、造谣的对象,也就是被压迫的对象。在丁玲的眼中,延安的妇女处境之惨比之在旧社会有过之无不及。延安到处是‘无声的压迫’。……丁玲的最后结论就是:延安是女人的地狱。”在此基础上文章断定丁玲“是在妇女问题上向党向人民射出了毒箭”,“指向解放区的婚姻法,指向新的社会制度”,并且认为《三八节有感》“同王实味的《野百合花》是异曲同工的反党的纲领”[10]。还有批判文章认为“丁玲以妇女问题为题,对当时延安的现实,对党的政策,对新社会制度,进行了极其恶毒的污蔑、诽谤与攻击”,《三八节有感》“可以说是丁玲明目张胆揭起的一面反党黑旗”[11]。
丁玲向女青年提出四点必须注意的事项:爱护自己的生命,做有意义的工作,独立思考,不随波逐流,坚持自己做人的原则等等。但批评文章却从这四点“企望”中引申出完全不同的涵义:丁玲号召“自己做人的原则”违背了“党的原则”和“革命的原则”,“她是劝延安的女同志不要随革命之‘波’,逐革命之‘流’”[10],《三八节有感》传播了“腐朽透顶的‘人不为己,天诛地灭’的反动的人生哲学,为某些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提出了拒绝改造的方法”[11]。
萧军的《论同志之“爱”与“耐”》发表在1942年4月8日延安《解放日报》第4 版。文章以《八月的乡村》中的两个细节阐述了“同志之爱”。唐老疙瘩宁愿被枪毙也不丢下受伤的李七嫂,铁鹰队长提起了手枪,却不忍心处决自己的同志。队员们都看不起因恋爱而消沉的萧明,只有铁鹰队长照常给予萧明“一种真诚的温暖”。1958年的批评文章认为“那个唐老疙瘩何尝是个什么‘革命的队员’,他无非是萧军的顽强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真情流露”[12]。唐老疙瘩在“革命环境异常艰苦时”,提出“不干‘革命’了”,这种“动摇分子”的结局必然“是可耻的掉队或死亡”。“对于唐老疙瘩的这种选择,我们除了感到可耻之外,还感到可憎!”[13]还有的批判者认为萧军“把革命纪律写得如此残酷,唐老疙瘩的爱情,萧明的爱情,一一被它夺去”,因此《八月的乡村》歪曲了革命的队伍和革命的纪律[12]。批判者正告萧军:“我们的子弹一旦发射出去,敢说命中的只有敌人!而萧军此处所谓‘同志的子弹打进同志的胸膛’,不过是他在玩弄阴毒的伎俩,企图对革命队伍又一次恶狠的诽谤和污蔑而已!”[13]
萧军认为“同志之耐”包含两个方面:一是干一番事业的能耐,革命者的任务就是“要随时随地和丑恶与不义战斗”;二是同志与同志之间要有说服、教育和理解,特别希望一些领导放下架子,给年轻人同情和尊重。批判者认为萧军所写的“耐”“一层用意”是“向党进行斗争要顽强”,“不能‘有一分退败的想头’,要像唐僧取经那样,经得起‘九妖十八洞’的‘捣乱’”;“又一层用意是:先在党的领导者身上抹上白点,把他丑化,然后迫着党向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思想缴械投降”[12]。
艾青的《了解作家,尊重作家》发表在1942年3月11日延安《解放日报》文艺副刊。该文一方面强调作家的独特作用,一方面要求作家独立批判和自由写作的权利。文中说:“作家并不是百灵鸟,也不是专门唱歌娱乐人的歌妓。……希望作家能把癣疥写成花朵,把脓包写成蓓蕾的人,是最没有出息的人——因为他连看见自己丑陋的勇气都没有,更何况要他改呢?愈是身上脏的人,愈喜欢人家给他搔痒。而作家却并不是喜欢给人搔痒的人。等人搔痒的还是洗一个澡吧。有盲肠炎就用刀割吧。有砂眼的就用硫酸铜刮吧。生了要开刀的病而怕开刀是不行的。患伤寒症而又贪吃是不行的。鼻子被霉菌吃空了而要人赞美是不行的。”1958年的批判文章却认为“党和毛主席”对“文艺和作家”已经是“非常关心和爱护”了,而艾青仍然坚持“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世界观和情感”“反党反人民”。“他不赞成作家歌颂延安,歌颂党和人民的伟大功绩。他认为歌颂延安的光明面就是‘把癣疥写成花朵,把脓包写成蓓蕾’,他说,‘鼻子被霉菌吃空了而要人赞美是不行的。’这里所谓的‘癣疥’、‘脓包’和‘霉菌’到底指的是什么?这样狠毒的咒骂不能说明旁的,只说明艾青对革命圣地的延安仇恨到怎样地步,他是怎样地完全现出自己的原形,站在革命的敌人方面去了。”况且作家本不应该“高人一等”,不应该被“当作超人供奉起来”,“写作自由”和“艺术创作的独立精神”不过是“资产阶级的滥调,听起来是使人发呕的”。至于“不能为人民服务只贪图个人利益、对革命发生腐蚀作用的作家”和“他们的反党作品”,“延安是不能给予,也不应当给予”“了解”和“尊重”的特权的[14]。
罗峰的《还是杂文的时代》发表在1942年3月12日延安《解放日报》文艺副刊。该文主张在“光明的边区”也需要杂文和“短剑”,因为“尽管你的思想如太阳之光,经年阴湿的角落还是容易找到,而且从那里发现些垃圾之类的宝物,也并不是什么难事。”1958年的批判文章质问罗峰的“短剑”指向哪里?“是谁规定的杂文一定要以讽刺为其特征呢?”“为什么讽刺一定要不考虑立场问题和效果问题,要不问对象,不区分敌友呢?某些站在反人民立场上的作家要挑人民的岔子,主张用制造黑暗的方法来‘反映黑暗’,诽谤人民,因而人民针锋相对地提出要多反映光明,歌颂人民,难道这是不可以的么?”[15]罗峰“还是杂文时代,还要鲁迅笔法”的“谬论”早就被“毛主席”批驳过了。1957年,“右派分子”“又在那里叫嚷什么‘干预生活’,鼓励用特写和杂文的形式‘揭露生活中的阴暗面’”,这和“还是杂文的时代”,“在提法上有所不同,但确实有‘异曲同工’之妙”。“延安是光明的”,“延安革命者的光明磊落,历史是最好的佐证”,对这样的革命队伍,“不去歌颂她,而去号召作家拿起讽刺的杂文,揭露所谓‘可怕的黑暗’,其用意是恶毒的”;“在我们国家里,人民不仅过着优裕的生活,而且可以自由的行使他们一切应有的权利。鲁迅生活的那个时代已经结束了,罗峰和徐懋庸还叫嚣什么,要用鲁迅对付敌人的办法来对付人民。这是极其卑劣的伎俩”[16]。
在批判者看来,杂文不一定要以讽刺为特征,讽刺一定要考虑立场和效果问题,如果批判和讽刺不问对象,不分立场和方法,一定会犯错误。但因为“敌人”经常“用制造黑暗的方法”“诽谤人民”,“人民针锋相对地提出要多反映光明,歌颂人民”,“人民内部的自我批评”也就不那么重要了,甚至应该废除。事实上,“再批判”者也是这么做的。《野百合花》、《三八节有感》、《在医院中》等都是因为涉及到了“人民内部的自我批评”,才被判成站在敌人的立场污蔑人民、攻击革命根据地的“毒草”。不管文学是站在什么立场上的讽刺,只要出现批判和讽刺,一定是对人民不利的,一定是对敌人有利的,如果批判和讽刺被敌人利用,那更可以据此判定为“毒草”,因为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都要反对。为了拒绝敌人对我们的攻击,为了拒绝讽刺被敌人利用,最好的办法就是取消对我们的讽刺。这是当时批判者惯用的批判模式和做法。1958年2月6日,《人民日报》发表题为《关于小品文问题的讨论》的文章,对1957年4月《人民日报》副刊开展的关于小品文问题的讨论进行了总结,重新强调了文学的阶级性和党性的问题。文章说,在去年的讨论中有的作者“片面地强调揭露现实生活阴暗面,说这是当前文艺界的‘新的创作要求’,而且认为作者这样做的时候,所需要的唯一条件是‘大胆’,而完全忽略了立场态度问题。有的作者坚持要用‘烈性而有副作用的药’,完全不提对敌人的批评和对人民的批评的根本区别。还有人说,对小品文必须废除一切‘清规戒律’,似乎社会主义文艺方针,文艺的人民性、阶级性和党性也都应该作为‘清规戒律’而加以废除了。”[17]按照该文的逻辑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为了拒绝“片面地强调揭露现实生活阴暗面”,为了拒绝“烈性而有副作用的药”,为了不在“立场态度问题”上犯错误,最好的办法是取消文学“对人民的批评”,仅保留“对敌人的批评”。
三、“再批判”的“战斗意义”
毛泽东大概始终没有忘记1942年的“文艺新潮”,当时碍于社会影响,投鼠忌器,采取了抓典型、惩一儆百的方式,暂时赦免了丁玲、萧军等人,只抓住了王实味的“托派问题”大力批判。1958年,“拿枪的阶级敌人”已打倒,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已溃散,但当年参与其事的多数作家都还在,他们在文坛还有一些影响,他们的自由思想也没有彻底改造,更重要的是“阶级斗争”依然存在,因此,现在终于到了彻底清算旧账的时候。
当时的一些批判文章说出了再批判的“现实意义”:虽然王实味等反党分子被埋葬在“垃圾堆”里,但他的《野百合花》“余毒未尽”。一些“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在一九五七年春天,“从垃圾堆里挖出了王实味的包含毒汁的‘野百合花’,当作标本,仿造出新的‘野百合花’来,向人们‘散布细菌,传染疾病’。为了使毒草、垃圾起充分的肥料作用,文艺报对王实味的以及丁玲、萧军、艾青、罗峰等人反动文章的再批判,是有其现实的战斗意义的”[5]。
不论是《野百合花》、《三八节有感》等杂文,还是《在医院中》、《我在霞村的时候》、《五月的矿山》等小说,都因为作家的独立思考和文学的批判精神而触及了“暴露”与“讽刺”的敏感问题,所以,这些作品都被打成“毒草”,到了1958年,要再次批判。
在毛泽东的文艺思想中,政治立场是一个根本的问题,它决定了对于具体事物的态度。什么东西是应当歌颂的,什么东西是不应当歌颂的,什么东西是应当反对的,什么东西是不能反对的;写哪个阶级的生活内容以及如何写(题材问题),以什么样的人物作为文学作品的正面人物以及如何塑造(人物问题),这些问题都取决于创作主体的政治立场。毛泽东说:“你是资产阶级文艺家,你就不歌颂无产阶级而歌颂资产阶级;你是无产阶级文艺家,你就不歌颂资产阶级而歌颂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二者必居其一。歌颂资产阶级光明者其作品未必伟大,刻画资产阶级黑暗者其作品未必渺小,歌颂无产阶级光明者其作品未必不伟大,刻画无产阶级所谓‘黑暗’者其作品必定渺小,难道这不是文艺史上的事实吗?对于人民,这个人类世界历史的创造者,为什么不应该歌颂呢?无产阶级,共产党,新民主主义,社会主义,为什么不应该歌颂呢?”[18]
于是,在1949年以后,中国可以暴露的对象越来越少,颂歌响彻于各个角落。新的规范已经使文坛形成了新的面貌。但是,1956年之后,“双百方针”引发的“文学突围”又使文坛出现了“暴露阴暗面”和“干预生活”的潮流。这种潮流必须给予严厉的批判和打击。所以,1958年再次强调立场问题,重新厘定暴露和歌颂的界限。什么可以批判,什么不可以批判,什么应当歌颂,什么又不能歌颂,都须给文学作明确的规定。它告诉人们:这就是文学的“禁律”,所有人都不能碰,一碰就会犯错误。《讲话》中对“歌颂与暴露”问题设定的“禁律”是必须遵守的。
“再批判”的功能是重申《讲话》“禁律”,把文学重新拉回到1942年和1949年之后已经确立的道路上来。奥威尔说:“谁掌握历史,谁就掌握未来;谁掌握现在,谁就掌握历史。”[19]1958年的“再批判”者拥有“现在”,也就拥有了解释历史的权力,解释历史也是为了掌握现在和将来。对“历史问题”的再次批判,能够正本清源,警示后人,维护“禁律”的稳固地位,确保文学发展的方向。只要现实中存在着违反“禁律”的现象,就需要批判这些“错误”的思想和行为,所以“再批判”不会只有这一次,它会不断地出现。
[1]再批判·编者按语[J].文艺报,1958 (2):2.
[2]封培定.“赔我一个王实味”[J].文史天地,2010 (1):26-27.
[3]黄昌勇.砖瓦的碎影[M].上海:同济大学出版社,2008:261.
[4]毛泽东.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七册[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21.
[5]吴强.蚂蝗与毒草——王实味和他的“野百合花”的再批判[J].文艺月报,1958 (3):85-87.
[6]王素稔.王实味煽惑青年的伎俩[J].北京文艺,1958 (2):4-5.
[7]林默涵.王实味的《野百合花》[J].文艺报,1958 (2):3-5.
[8]丁玲.三八节有感[J].文艺报,1958 (2):8.
[9]罗洪.读“三八节有感”的感想[J].文艺月报,1958,(3):5.
[10]王子野.种瓜得瓜,种豆得豆——重读《三八节有感》[J].文艺报,1958 (2):7-8.
[11]王慧敏.丁玲揭起的一面反党黑旗——读丁玲的“三八节有感”[J].北京文艺,1958 (2):7-9.
[12]马铁丁.斥《论同志之‘爱’与‘耐’》[J].文艺报,1958(2):18-19.
[13]李岳南.论萧军之毒与害[J].北京文艺,1958 (2):16-18.
[14]冯至.驳艾青的《了解作家,尊重作家》[J].文艺报,1958(2):23-24.
[15]严文井.罗峰的“短剑”指向哪里?——重读《还是杂文的时代》[J].文艺报,1958 (2):20-25.
[16]邢秋平.是谬论,也是恶毒的诽谤!——读“还是杂文时代”有感[J].北京文艺,1958 (2):19-20.
[17]山柏.关于小品文问题的讨论[N].人民日报,1958-02-06.
[18]毛泽东.毛泽东论文艺[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2:61-62.
[19][英国]乔治·奥威尔.一九八四[M].孙仲旭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0:3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