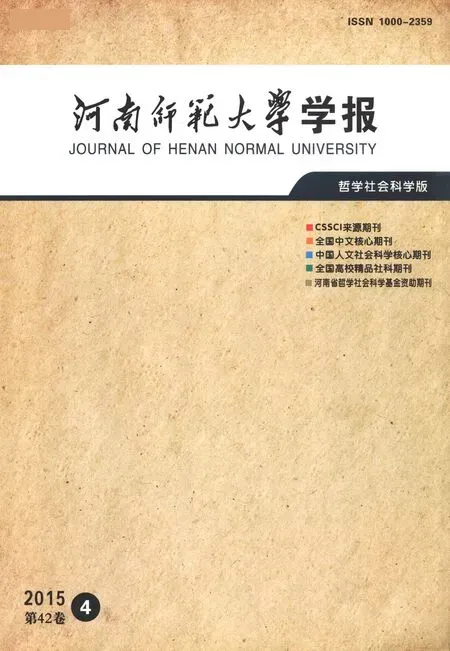艺术真实的价值诉求及其学科维度
贾怀鹏
(河南师范大学 文学院,河南 新乡453007)
一
艺术真实论萌芽于古希腊时期的模仿论。德谟克利特认为艺术源于人们对于动物行为的模仿,人类从蜘蛛那里学会了织布和缝补,从燕子那里学会了造房子,从天鹅和黄莺等歌唱的鸟那里学会了唱歌[1]。模仿论在古希腊时期是一个为众多哲人所认同的艺术理论,这其中便包括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但是,同样是模仿论,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和德谟克利特他们之间的观点有着深刻的差别。而正是在这些差别中,透露出艺术真实概念某些隐秘的气息。在文学理论中,人们对于艺术真实的相关命题中最耳熟能详的大概是:艺术来源于生活,却高于生活;艺术真实高于生活真实。在德谟克利特那朴素的模仿论中,只是指出了艺术来源于对生活的模仿,但是并没有断言这种模仿的结果却高于生活本身。
虽然同样坚持艺术是对现实的模仿,柏拉图却认为,艺术真实不但不高于生活真实,反而是低于生活真实的。柏拉图在《理想国》中提出了著名的三张床理论。柏拉图认为世界上存在着三张床。第一张是“理式”的床,关于床的最高真理。第二张床是木匠按照“理式的床”做出来的现实的床。这张床是对理式的摹仿,和真的实体的床已经隔着两层。第三张床是画家摹仿木匠的床创造的艺术的床。这是一种摹仿的摹仿,它和真实的床隔着三层。正因为这个理由,柏拉图主张将艺术家从理想国中驱逐出去[2]。在这里,现实的床就相当于生活真实,艺术的床相当于艺术真实。生活真实已然不是很真实,更何况是对生活模仿的艺术真实呢?柏拉图的深刻在于他在两千年前就开始怀疑人类感官的可靠性:眼见未必为实,耳听未必为真。他认识到,通过我们感官感知的生活世界只是一个现象世界,具有相对性和变异性,缺乏普遍性和恒定性,它不是本体世界,不具有绝对的真实性、永恒性和普遍性。所以,他才会企图借助于灵魂去抵达那个理念的世界。柏拉图著名的洞穴比喻也指出了“生活真实”的虚假性。在他看来,人类所以为真实的生活现象世界实则只是本体世界的一个投影或回声而已。何况是对于生活现象的模仿的艺术呢?
亚里士多德在《诗学》中指出,历史模仿的是实然的事情,而诗人的职责不在于描述已发生的事,而在于描写可能发生的事,即按照可然律或必然律可能发生的事。在亚里士多德看来,历史记录的是在生活中实际已经或正在发生的事情,是零碎的、繁杂的、偶然性的,缺乏规律性的。而以诗为代表的艺术则不同,它是按照必然律和可然律来描述可能发生的事情的,模仿或表现的是具有规律性的东西。因此,诗比历史更具有哲学性,意义更重大,因为诗所陈述的事具有普遍性,而历史则陈述特殊的事[3]。这里亚里士多德明确指出艺术真实是一种规律性真实,而不是现象真实。这就是后人通常所称的透过现象看本质的观点。
如此一来,亚里士多德巧妙地颠覆了柏拉图的观点。在柏拉图看来,艺术由于模仿的是生活,所以缺乏真实性。而亚里士多德却认为艺术模仿的不是生活现象,而是生活现象背后的本质规律,因此比生活现象界更加具有普遍性和真实性,从而也比历史更具有价值。在这里,实际上艺术从某种程度上反而成为了达致柏拉图的理想国的途径,即通过艺术找到本质王国、规律王国、真理王国。不过,与柏拉图不同,在亚里士多德看来,本质和现象是一体的,不可分的。这里有必要提及亚里士多德的形式理论。亚里斯多德认为实在界乃是由各种本身的形式和质料和谐一致的事物所组成。“质料”是事物组成的材料,“形式”是每一个事物的个别特征。某类的“形式”乃是某类都共有的特征。它存在于事物中,即特征。而这种“形式”,其实有点类似于规律、本质之类的具有普遍性东西,甚至是具有规定性的、概念性的,很接近柏拉图的理式了。比如:一个正方体的形式是“棱长都相等的六面体”,质料则可以各式各样,甚至大小也可以各不相同,但是只要符合这个形式上的规定,都是正方体。这比柏拉图的分有理论要高明多了。这种形式既存在于每一个特殊的具体的对象中,又具有普遍性和规定性,是完美的个别与一般的统一。这里其实也已经隐含着与现实主义文学密切相关的典型理论问题了。
二
表面看来,亚里士多德似乎很好地解决了艺术与真实的关系问题,也为包括文学在内的艺术的存在和发展赢得了理论根据。但是,这一切都是建立在概念的含混上的。历史上关于艺术真实问题的众说纷纭,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在于对于“何谓真”的问题的理解上的混乱。各个不同学科之间的隔阂也很深,导致不同学科的真实观自行其是。艺术真实问题,绝不仅仅是艺术领域里的问题,需要从跨学科的视角来重新审视艺术真实问题,才能对此有一个开阔的视野和较为清晰的认知。
真理理论主要可以分为以下几种:符合论、融贯论、实用主义理论、语义学理论、冗余理论等。其中符合论是传统上最有力量的真理理论。所谓符合,用康德的观点来讲就是知识与对象符合即谓之真,而罗素与维特根斯坦则将真理定义为命题与事实的符合。但是符合论的困境在于:作为认知对象的客体事实很难得到验证。也即是说,符合论的困难在于验证问题。怎样才能证明某一命题符合某一事实,这是困难的。尤其是历史事实,很难还原,也很难证实。再加上在事实与认知之间又加上了一个表述问题,使得符合论更加举步维艰。正是这种困难导致符合论在当代颇受争议,其他的真理理论的应运而生,亦与此有关。融贯论的长处在于其容易验证,但是问题在于:融贯论不能将真理与一个具有融贯性的童话区别开来。其他的真理理论其实都或多或少具有类似的缺陷。如果放弃符合论,放弃对于客观事实的追寻和靠拢,所谓的真理就失去了终极目标,很容易陷入自成系统的语言游戏。
后现代语境中的怀疑主义倾向虽然深刻,但是过于极端,并且混淆了一些基本概念。后现代主义反对主客二分,不承认独立于主体的客体对象的存在(实质上就取消了符合论的存在基础)。然而,主客二分只是一种认知上的权宜,就如一种方便操作的设定,这与我们给一类事物下定义一样,只是为了方便,概念与概念之间很难有截然的区分。至于客体对象能否独立于主体存在,答案显然是肯定的。只能说关于客体对象的认知不能独立于主体的存在,并不能说客体对象本身不能独立于主体的存在而存在。这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
柏拉图对于感官的怀疑是深刻的,但是问题在于我们的认知除了依靠感官之外,很难再依靠其他东西。他所依赖的灵魂或理性,显然并不能达致本体世界。康德以公理的存在为现实依据提出只有理性才能达到现象界的彼岸——物自体。他认为通过感性和知性所掌握的知识只是自然界的知识,不属于物自体,是相对的,不具有绝对的普遍性,也即缺乏绝对的真实性。康德从而陷入了不可知论,也即最真实的物自体,我们人类是无法认知的。这点实际上与柏拉图的洞穴比喻相当契合。真理从此永远沦陷于遥不可及的黑暗之乡了。所以罗素认为,尽管感官不完全可靠,但是感官所获得经验信息是我们唯一可信赖的。感官经验是知识的基础。哲学思考和逻辑分析,只是为了消除无用和错误的知识,本身并不能生产知识。先哲们的悲观论述给了后现代怀疑论者很大的启发。在现代性语境中,传说与历史之间的区别就是虚构与事实之间的差别,而在后现代语境中,虚构与事实之间的边界也是一种“虚构”。这表现在人类学领域里,就是所谓的表述危机。事实是事实,表述是表述,在怀疑论者看来,书写永远无法完全契合事实,而我们认识的或研究的都是书写,而非事实,因此我们只能追求融贯的真理或修辞的真理抑或主体间性的真理。福柯甚至不承认真实的存在,而只承认语言的存在。但是,语言毕竟只是一种工具,而不可能是真正的本体,语言只是社会的一部分,而不是全部。是以,正如伊格尔斯所说,并无多少人认同福柯的“真实并不存在,存在只是语言”的极端说法,多数人还是同意说,“语言的差异构成了社会,同时社会的差异也构成了语言”[4]。尽管如此,我们依然面临着追寻真实性的双重障碍:第一,主体如何能够借助于自身能力认知或把握客体对象;第二,主体对客体的认知需要通过表述来传递信息,如何能够保证主体的表述符合主体对客体的认知。甚至还可能有第三重障碍:其他主体如何能够准确地领会某主体关于客体知识的表述。
一切看上去似乎相当令人悲观。但是,这里可能存在某些微妙的错位。这种错位正是来自于人们对于真实性这一个概念的自觉不自觉的细微偏移。这种偏移实际上早在柏拉图那里就开始了,后来的亚里士多德、康德、福柯等人无不如此。这种偏移表现在:将不普遍当成不真实,将不规律当成不真实,不深刻当成不真实,将不本质当成不真实,将不准确当成不真实,将不恒定当成不真实。很多时候,人们混淆了“不准确”和“不真实”。我们看一只蚊子,看不太清楚,但是不等于我们看不到对象的存在,不等于我们无法粗略地描述对象的样子。我们无法准确的记录事实(fact),并不意味着我们意识不到事实的存在,并不意味着我们无法粗略的描述事实。当我们真诚地努力地用语言去描绘对象事实的时候,总是在努力接近事实真相,即使我们永远都无法看清楚事实的所有细节,但是我们至少可以努力让事实显得清晰、确实起来。如果不承认事实的存在,不承认我们能够“粗略”地认识和描绘事实,那么我们会走向虚无主义或所谓的主体间性。事实上,事实就在那里存在,我们也能够“粗略”地认知事实并描绘它。而这就足够了。当我们迎着事实而上的时候,我们总是在接近事实。同理,我们不能得到最具有普遍性的规律性知识,并不意味我们得到的相对性的知识就是假的或不真实的。就如牛顿经典力学,是一个相对真理,但是很真实,也很有用。柏拉图为什么认为感官感性不能获得真实?无非是因为感官得到的东西不够具有普遍性、规律性、永恒性、本质性、规定性。亚里士多德关于诗表现必然和可然的论述,实际上也是将艺术真实抬升为规律性真实、本质性真实,使得艺术真实成为一种具有普遍性的真实。
不管人们有没有意识到,这正是我们教科书上宣称的“艺术真实高于生活真实”的根底所在。倘若没有这些潜在的细微的偏移,我们如何能够理解“艺术真实竟然能够高于生活真实”?为什么贾宝玉这样一个虚构人物会比现实生活中的一个活生生的人更加真实呢?一个虚构的人物,不管它如何地具有必然性,又如何能够比实然存在的东西更加真实呢?诗的真实如何能够高于历史的真实呢?艺术真实如何能够高于生活真实呢?还有比生活真实更真实的吗?但是这些明显违背常识的结论,为什么几千年来我们竟然都没有反思,并欣然接受呢?这是历史最吊诡之处。造成这种诡异的偏差的根本原因在于历史上人们对于真实性的追求从来不是那么纯粹的——背后隐藏着各种各样的价值诉求。
艺术真实高于生活真实,并非是艺术真实在“真实度”上要高于生活真实,而是在“有用性”上即“价值”上要高于生活真实。就“真实度”而言,相对论和牛顿经典力学,不但不比一张实在的床更加真实,甚至还要弱一些(爱因斯坦还等着他的相对论被证伪),可是相对论和牛顿经典力学确实比一张现实的床有用多了。是以,各种所谓的本质、规律、普遍、一般等等说法背后,实则就是指向某种价值性诉求,而与真实本身无关。这也为后来的现实主义文学名声的败坏埋下了深达两千多年的陷阱。尽管现实主义文学号称是要客观地再现生活,要做历史的书记员,但是这从来只是一种表象。我们不要忘了,最著名的现实主义浪潮在历史上被称为批判现实主义。批判,谁批判,批判谁,批判什么,为什么批判,怎么批判?这里涉及到一系列价值判断和可操作的空间。所谓的本质真实和规律真实,是谁规定的本质,是谁掌控的规律,是谁需要的本质规律,这些所谓的规律符合谁的利益?与之相呼应的典型理论,究竟是什么样的典型才算典型?何种典型才是好的典型?批判现实主义的名声比其他现实主义要好得多。一个重要的原因是,虽然都是隐含着价值判断,但是前者的人道主义价值观更加具有先进性和普世性。建国后时兴的创作方法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这种创作方法强调真实,认为作品应当从现实的革命发展中真实地、历史地和具体地去描写现实。写出真实就是反映生活中最本质、最典型、最根本的东西,反映我们现实中最先进、日益成长、壮大的东西。何谓“最本质、最典型、最根本的东西”,何谓“最先进、日益成长、壮大的东西”?显然不可能是客观的,而只能是符合某些人的利益的东西。而现实主义文学中通常强调的人民性一词,其实同样如此。人民指的是谁?这个问题绝不仅仅是一个认识论问题,而是一个话语权问题。至此,现实主义文学开始彻底地沦陷了,而这个坑其实早在柏拉图时代就已经挖好了。现实主义文学从此臭名昭著,中国当代作家曾经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对它避而远之。人们宁可躲起来搞先锋文学的文字游戏,也不愿意面对“现实主义”。而莫言的现实主义创作也要冠上“魔幻”二字作为掩饰。
但是,价值诉求,对于真实性追求是不是一种完全的负面因素呢?也未必。价值诉求很多时候还是一种正面的力量,因为它提供了强大的动力。它能够促使作家以更大的热情投入于其中,从而可能获得惊人的效益。同时,价值诉求还提供了一种视角,可能给人带来全新的视野,从而为文学创作提供巨大价值。只是价值诉求的弊端也很明显:立场所导致的偏见和偏执,不能客观中立地看问题,甚至为了满足价值诉求而肆意篡改事实以致于主观性地违背了真实性要求。想要避免价值诉求所带来的对于真实性追求的伤害,有两个办法:一是舆论自由,让各种价值诉求的声音都得到展现,在众声喧哗中不断对比、矫正,这样能够避免一种价值观独大而导致的话语专制;二是作为作家自身不要过于偏执于某一种价值观,而要学会努力地多角度地设身处地去体会客体对象。
三
大概正是因为文学领域的感性诉求掩盖了其逻辑分析能力,导致文学的真实性走向了真实性的反面。这种极具反讽性的荒诞局面使得现实主义文学丧失了名誉。同时也使得科学与文学的对立更加壁垒森严。这种对立表现在科学主义和人文主义的尖锐对立上。在自然科学迅猛前进的步伐中,人文科学在反抗中不断萎缩,甚至丧失了科学的头衔,沦为人文学科。这归根结底在于在真实性的追求上,后者完全不是前者的对手。以致于国外的很多文论家干脆不承认文学与外在世界的对应关系,将文学描述成一个自成系统的独立存在,不接受任何外界事物的真实性检验。他们相信,文学话语是一种虚构话语,根本不可能通过外在的参照来证实或证伪。文学是一种不能够接受真实性检验的言语,它既不真实也不虚假,因而提出这样的问题是毫无意义的。这样的主义颇有些“躲进小楼成一统”的意味,虽然使得文学免遭真实性的逼问和追讨,但是终究不是真正的解决之道。至少,对于现实主义文学而言,真实性问题是无论如何都绕不过去的。托多罗夫们的观点用于其他文学样式也许还差强人意,但是面对现实主义文学,就不免显得有些心虚。并且如此立场,等于是自觉放弃了文学与科学在真实性方面的较量,实质上是一种装点门面的逃跑仪式。
那么,文学在真实性方面的努力是否真的一无是处呢?是否真的要完全放弃对于真实性的追求呢?我认为,情况并没有糟糕到这样的地步。文学或艺术,在真实性方面,还可以有自己的贡献。也即是说,艺术真实,依然还具有历史合法性,也具有切实的现实意义,并不能简单地抛弃。科学对于真实性的追求,恰恰是深受古希腊文化影响的,也即是说,科学真实指向的是规律性真实,是抽象的、普遍性的、恒定性的真实。化学元素周期表、物理定律、数学公理等等,在本质上都是抽象的真实。它们对于具体的、细节的真实并不是非常有兴趣。即便是社会科学,其关注的重心也是在群体结构、社会规则等规律性强的领域,对于具体个体的特殊性不甚关心,甚至还要有意当成意外因素排除掉。此外,无论自然科学还是社会科学对于真实性的实证性要求,使得其研究结论必须经得起反复实验验证,这大大限制了其研究范围。譬如中国古代汉语对于上古音的研究一般不多,原因在于上古音研究由于缺乏材料又不可能获得十足的可证实性,使得语言研究者不敢涉足这一领域。可是在人文社科领域,大部分事实都缺乏足够的材料和可验证性,譬如人类学家考察某个原始部落,可能只有他一个人见过这个原始部落并写了民族志,历史无法复原,也无法验证,社会科学的科学性要求使得其对之不感冒,这也是人类学为什么长期以来在社会科学中处于尴尬的边缘位置的原因。而这些都为人文学科留下了运作的空间。正如前面指出,并不是只有规律性的真实才是真实,具体的特殊的个体的真实也是真实。历史就是要记录这些看似杂乱的个别性真实。
我们不妨问几个问题:文学是否必须表现规律性真实?实然的事情其价值就一定低于必然的事情吗?科学或知识追求不是纯粹的吗,还要考虑价值高低吗?显然,如果知识真的是纯粹的,不考虑价值问题,那么一切问题都不是问题了。可是,事实上,知识很少有纯粹的,就如真实性一样,背后都是有价值考量的。那么,我们要思考的是:理论真实的价值就一定高于材料真实吗?我觉得理论的价值未必就高于史料的价值。作为规律总结的理论,其价值在于提供一种思考问题的角度和方式,而理论的风险在于它可能提供了一种错误的角度,也即这个理论可能是错误的。作为实然之事的记录的史料,其缺陷在于缺乏规律性,而其价值在于可以反复利用和阐发,永不过时,并且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愈发弥足珍贵,它可以作为理论的坚实基础,也可以作为人类寄托情思的处所,还可以作为满足人类求知欲的资料。也许短期来讲,理论真实的吸引力更大一些,但是长期来讲,材料真实的魅力一点不亚于理论真实。诸多名家在历史上曾经提出轰动一时的理论,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而逐渐淡去,只有少数经得起事实检验的理论存留了下来。相反,曾经寂寂无名的史料,甚至很多当时人们根本看不上眼的事实记录,比如日记、笔记、乃至账本,到后来都成了弥足珍贵的史料。我们很难说黑格尔有关美是理念的感性显现的理论论述的价值就高于库克船长的航海日志。历史上产生了太多的假大空的理论,虽然风靡一时,终究是昨日黄花。
我觉得,现实主义文学完全可以做到像历史书记员一样做到对事实的一丝不苟的记录,这正是现实主义文学的独特之处。它放弃了虚构性所带来的各种便利,但是获得了历史真实性的价值和增值空间,何况对于历史真实的欣赏所带来的快感就未必弱于幻想所带来的快感,正如我们对于历史剧的喜爱未必就弱于对玄幻小说的喜爱。如此一来,似乎有将历史学家与文学家混为一谈之嫌。事实上,现实主义文学家就应该具备史学家的气质和追求,正如优秀的史学家也多少有点文学家的气质。《史记》被鲁迅誉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即为明证。作为社会学和历史学的边缘学科的人类学就积极主动地向文学学习,创造了文化并置等研究方法,同时人类学家也常常自己创作文学文本,来传达某些微妙的事实。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人类学开始了其文学化道路,将文学的方法应用于人类学研究。有一些真实,是很难用逻辑化的语言清楚表达出来的,比如个体的复杂微妙的心理感受。中国的古人早就认识到这一点,所以提出“圣人立象以尽意”的观点,也开启了中国文学的意象理论进程。文学的优势在于文学家珍视个体的情感世界,并力图呈现它,而且也只有文学家才有能力通过巧妙的文学手段呈现这些奇妙的心理体验。同时这种呈现还必须充分考虑到文化情境,还需要阅读者的体验和领悟,才能达到对此类真实的感知。科学显然缺乏表现和记录复杂情感的能力。情感真实显然也是真实的一种。而这正是文学的擅胜之地。
文学还有一个重要的功能是科学所不具备的:即召唤情感体验。我们大抵有过类似的体验:一段惊心动魄的情感经历曾经给人留下弥漫不去的绕梁不绝的心理体验,如失恋,但是随着时间长了,尽管我们想要努力地回忆起那种感觉,但是那种感觉无论如何都回不来了,我们甚至还可以用理性的语言清晰地描述当时的痛苦表现,但是就是体会不到那种痛苦的感觉,我们为此感到有些失落。显然,理性和科学无法让我们重新体验那份浓烈的哀伤和美丽,唯有文学和艺术,才有可能唤醒我们沉睡的情感体验。这正是文学独特的价值,是科学很难替代得了的。如果那些情感体验也算是一种真实的话,那么,显然这种独特的真实只有文学能够抵达和唤醒。人们常常指责文学的虚构和想象损害了真实性的追求。但是实际上,科学也是需要想象的。我认为合理的想象不但不损害真实性,反而是接近真实的一种必要的方式。就如科学家对于原子的想象,物理老师还拿出原子模型来具象化抽象的东西,都是逼近和表现那些看不见的“真实”的最好方式。史料的稀缺必然要求所有的历史研究都需要极大的想象力去弥补史料之间的空隙。文学也是如此,一个人所能见到的东西是有限的,很多东西是见不到的,如别人的心理活动,这就需要合理想象。历史剧讨论中,人们埋怨对于真实性的追求导致了文学缺乏想象的空间,这是弱者的抱怨。能够在钢丝上跳舞才能显示出更高的艺术水准。何况历史剧可以想象的空间如此之大,何必还要去篡改真实的历史呢?
[1]蒋孔阳,朱立元.西方美学通史:第1卷[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9:34.
[2]柏拉图.理想国[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388-393.
[3]亚里士多德.诗学[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81.
[4]G.G.Iggers.Historiography in Twentieth Century:From Scientific Objectivity to the Postmodern Challenge[M].Wesleyan University Press,1997:13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