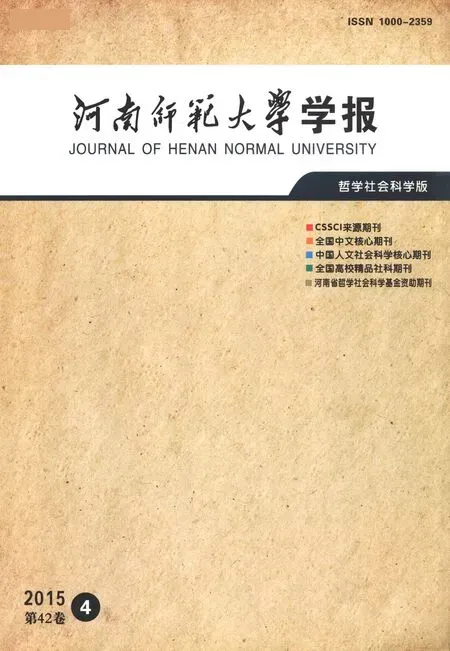二程语录与禅宗语录关系述论
赵 振
(河南师范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河南 新乡453007)
语录体是中国古代典籍中一种特有的文体形式,始源于春秋战国时期的教学和思想传播活动。当时由于诸子百家聚徒施教,私人讲学的风气比较盛行,老师与弟子之间经常就某些问题展开讨论,甚至是相互辩难,有人把这些内容记录下来,就成为语录体著作。《论语》就是其中的代表,清人李颙指出:“《论语》一书,夫子之语录也。”[1]它以记录人物言论为主,以师、弟子之间的问答为主要形式,采用口语,不避俚俗。唐宋时期,佛教中的禅宗一派为适应中国化及吸引更多信徒的要求,开始采用一种由师弟子共同参与的口传心授方式传道,而门生弟子将其蕴含种种机锋的问答、诘难、辩论等内容记录下来,就形成了众多的禅宗语录。到了宋代,由于书院教育发达,私人讲学风气浓厚,以程颢、程颐兄弟为代表的理学家,为了更好地传播儒家学说和建构新的思想体系,也纷纷借鉴禅宗的传道方式,采用语录的形式阐发儒学义理,探讨儒家圣人之道,从而推动了儒家语录的再次复兴和进一步发展。
一、禅宗语录的流行与宋代儒家语录的复兴
唐宋时期,佛教中的禅宗一派发展迅速,由于它的早期信徒多为下层贫民,文化水平不高,传统的依靠诵经修行的方式显然不适合他们。在这种情况下,禅宗提出了“以心传心,不立文字”的传教方式。因为在禅宗看来,语言文字具有明确的规定性,其表达能力有一定的局限性,因而无法表达禅悟的终极境界,有时甚至还会成为传达禅意的障碍。禅宗二祖慧可的再传弟子法冲指出:“义者,道理也。言说已粗,况舒在纸,粗中之粗矣。”[2]因此禅宗强调人的内在的心理体验,认为人的内在的心理体验是无限定的,人们依靠内在的心理体验就可以直达佛理。正如六祖慧能所说:“本性自有般若之智,自用智惠观 照,不假文字。”[3]54但人的根性不同,有智有愚,上根之人可以不假文字而顿悟自性,而下根之人就必须假借外在的帮助,也就是那些得道的高僧的指点,才能顿悟。所以慧能又说:“若不能自悟者,须觅大善知识示道见性。何名大善知识?解最上乘法,直示正路,是大善知识。”[3]59因此,受先秦儒家聚徒传学方式的启示,禅师们也根据因材施教的原则,或当头棒喝,或旁敲侧击,或逆向思维,或危言耸听等,对信徒进行随机接引,诱导他们自悟佛性。如《祖堂集》卷二载:
(僧璨)大集群品,普雨正法。会中有一沙弥,年始十四,名道信,来礼师。而问师曰:“如何是佛心?”师答曰:“汝今是什么心?”对曰:“我今无心。”师曰:“汝既无心,佛岂有心耶?”又问:“唯愿和尚教某甲解脱法门。”师曰:“谁人缚汝?”对曰:“无人缚。”师云:“既无人缚汝,汝即是解脱,何须更求解脱?”道信言下大悟。
针对道信和尚心中的疑问,僧璨禅师用了一连串的反问来引导其开悟。再如《景德传灯录》卷五云:
开元中有沙门道一住传法院,常日坐禅。(怀让)师知是法器,往问曰:“大德坐禅图什么?”一曰:“图作佛。”师乃取一砖,于彼庵前石上磨。一曰:“师作什么?”师曰:“磨作镜。”一曰:“磨砖岂得成镜邪?”“坐禅岂得作佛邪?”……一闻示诲,如饮醍醐。
怀让禅师以磨砖为镜设喻,使马祖道一明白了坐禅不能成佛的道理,从而顿悟。后来弟子们把这些包含了无尽机锋的对话记录下来,就成了禅宗语录。
禅宗语录形成于唐,盛行于宋,唐中期出现的六祖惠能的《坛经》当是最早的禅宗语录。但其真正大规模地编撰和传播却是在宋代。南宋郑樵在《通志·艺文略》“释家类”专设“语录”一类,著录禅宗语录56部,计91卷。当然这并非禅宗语录的全部,周裕锴认为两宋时期传世的禅宗语录当有百多家,数百卷,并且由两宋文人所作语录序跋来看,失传的禅宗语录数量则更为惊人[4]。不仅如此,继五代时释静、释筠编的《祖堂集》之后,宋人还把禅宗语录集的编纂推向了一座高峰,编刊了《景德传灯录》30卷、《天圣广灯录》30卷、《建中靖国续灯录》30卷、《联灯会要》30卷、《嘉泰普灯录》30卷等五部卷帙浩繁的综合性语录体集,号称“五灯”。而禅宗语录的大量出现,也使禅宗的发展由最初的“不立文字”走向了“不离文字”,正如宋人陈振孙所说:“本初自谓直指人心,不立文字。今‘四灯’(指《景德传灯录》《天圣广灯录》《建中靖国续灯录》和《嘉泰普灯录》)总一百二十卷,数千万言,乃正不离文字耳。”[5]这种情况的出现,一方面说明禅宗信徒的构成已经由当初以下层贫民为主变成了后来的以文人和士大夫为主,而语录的大量出现,也正是为了适合这一部分人的需要,另一方面也说明了当初禅宗所提倡的“不立文字”也并不是不要文字,而是不要执著于文字,即不要使文字成为直悟佛理的障碍。正如葛兆光所言:“不立文字并非不要文字、不信文字、不用文字。‘立’者树立之义,树立者何?树立权威。不立文字乃指不以文字之义为权威,不以语言之旨为指归,换佛家话说,即不执迷于文字语言。”[6]
禅宗语录通过对禅师话语的记录和整理,形成了一种师徒之间直接对话交流的传道风格,从而使传统的疏解经文的传道方式受到挑战,佛典也受到冷落。正如钱大昕所言:“佛书初入中国,曰经、曰律、曰论,无所谓语录也。达摩西来,自称教外别传,直指心印。数传以后,其徒日众,而语录兴焉。支离鄙俚之言,奉为鸿宝;并佛所说之经典,亦束之高阁矣。”[7]这种传道方式也给当时正在困惑中摸索的宋代理学家以很大的启发,因为汉唐以来的章句训诂之学严重桎梏了儒学的生命力,正如程颐所说:“经所以载道也,诵其言辞,解其训诂,而不及道,乃无用之糟粕耳。”[8]671因此,为了使儒学研究从汉唐经学的繁琐训诂考据中解放出来,并重建儒家思想理论体系,理学家们也纷纷采用口义的形式释经。它通过人物对话的方式,采用通俗的口头语言对儒家经典进行诠释。这就促使源于先秦《论语》的儒家语录体著述再次复兴起来。再加之宋代书院教育发达,私人讲学风气浓厚,也为儒家语录体著述的复兴提供了契机。如当时的学者胡瑗、孙复、王安石、张载、邵雍、程颢、程颐等诸辈大儒都纷纷设帐授徒,程颐曾描述其盛况说:“如胡太常瑗、张著作载、邵推官雍之辈,所居之乡,学者不远千里而至,愿一识其面,一闻其言,以为模楷。”[8]564-565在这种讲学的过程中,老师往往用新鲜活泼的口语向弟子们阐述经典大义,传授儒家圣人之道,即“讲论者为使听者易于领会,故多方设喻,语不求深,如话家常,娓娓而谈,唯以明白显豁为务”,而“诸生随堂听讲,唯恐失真,故片言只语不敢遗漏,口吻声态详加记载”[9]。这样就形成了各种各样的语录。以至于南宋学者赵希弁在《郡斋读书志·附志》中专设“语录”一类来著录其盛况。这里既有个人的语录单行本,如《河南程氏遗书》(以下简称《遗书》)、《河南程氏外书》(以下简称《外书》)、《横渠先生语录》、《元城先生语录》、《龟山先生语录》、《上蔡先生语录》、《晦庵先生语录》等;也有数家语录的汇编本,如《近思录》十四卷是“晦庵先生、东莱先生集周、张、二程之说也”[10]1210。《传道精语》三十卷、《后集》二十六卷是“李方子编濂溪、康节、横渠、明道、伊川、晦庵、南轩、东莱之说,类而集之”等[10]1213。
但有关宋代儒家语录的起源,后人却有不同的意见。顾炎武认为:“今之言学者必求诸语录,语录之书,始于二程,前此未有也。”[11]顾氏之说有误,因为非但语录之书不始于二程,就是宋儒语录亦不始于二程。陈植锷先生认为宋儒语录始于刘敞的《公是先生弟子录》,他说:“宋学家自刘敞门人所录《公是先生弟子录》开始,也多以语录的形式传道。”[12]此说亦不妥。陈氏提到的《公是先生弟子录》当指刘敞所著《公是先生弟子记》,“录”疑为“记”之误。赵希弁《郡斋读书志·附志》著录有刘敞《公是先生弟子记》一卷,并附解题云:“刘敞原父之说也。”[10]1145《四库全书总目》则著录为四卷,并认为“是编题曰弟子记者,盖托言弟子所记,而文格古雅,与敞所注《春秋》词气如出一手,似非其弟子所能,故晁公武《读书志》以为敞自记”[13]778。也就是说,此书同汉代扬雄的《法言》一样,乃托名老师与弟子之间的对话,实际上是作者自行设问,自问自答之辞。如《公是先生弟子记》卷二载:
或问曰:“太公治齐,尊贤而尚能,周公曰:‘后世必有篡夺之臣。’周公治鲁,尊尊而亲亲,太公曰:‘后世寖弱矣。’若是乎,圣贤之无益于治乱之数也?”曰:“否,此非圣贤之语也。致功兼并者文其过之言尔。齐不用太公之法,故齐夺;鲁不用周公之政,故鲁弱。尊贤尚能,非所以启篡也;尊尊亲亲,非所以致弱也。齐桓公修太公之法而霸天下,鲁僖公修周公之政,诗人颂之,以比三王,恶在其无益于治乱也。”
这段对话用语文雅,不类语录所用口语,因而其并非真正意义上的语录,所以《郡斋读书志·附志》没有将其列入“语录类”,而是归入了“杂家类”。
以笔者所见,宋儒语录当始自胡瑗。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卷一著录胡瑗《周易口义》十三卷,晁公武《郡斋读书志》卷一著录《胡先生易传》十卷,并附题解云:“此解甚详,盖门人倪天隐所纂,非其自著,故序首称‘先生曰’。”[10]29《宋史·艺文志》则著录胡援《易解》十二卷、《口义》十卷、《系辞》《说卦》三卷。朱彝尊《经义考》引李振裕语云:“《宋艺文志》既列胡援《易解》,复列《口义》十卷、《系辞》《说卦》三卷,而《扬州志》亦仍其目,误也。盖安定讲授之余,欲著述而未逮,倪天隐述之,以其非师之亲笔,故不敢称‘传’,而名之曰‘口义’。传诸后世,或称‘传’,或称‘口义’,各从其所见,无二书也。”[14]也就是说,上述各家书目所著录胡瑗《周易口义》《易传》《易解》等实际上为同一书,只是卷数分合稍有差异,《宋志》失察而误分为二书。而所谓口义,也就是老师平时讲课内容的记录。如《周易口义》卷一解释《乾卦》上九爻“亢龙有悔”云:
(口)义曰:此一爻居卦之终,亢极之地也。若圣人当衰耗之年,不可更专己任,必得圣贤之人以代己之聪明也。故尧之耄期倦于勤则授之舜,舜耄期倦于勤则授之禹,禹耄期则授之启,是圣人与时消息,知进退存亡,而不至亢极,故无悔耳。然圣人之德固无亢也,盖其年有亢耳,圣人之道固无悔也,盖其身有盛有长有耄耳。今上九是年齿衰耗,精神倦怠之时,若居此时不能自反而求代己任,则必有悔矣。
上述引文虽然省却了师生间的问答,但用口语对《周易》进行义理阐释的特征是很明显的,因此应当属于语录体著述。该书实际上就是胡瑗在太学讲《易》时的记录,后由弟子倪天隐整理而成。《四库全书总目》指出:“(《周易口义》)宋倪天隐述其师胡瑗之说。……王得臣《麈史》曰:‘安定胡翼之,皇祐、至和间国子直讲,朝廷命主太学。时千余士,日讲《易》。’是书殆即是时所说。”[13]5此外,《郡斋读书志》卷一还著录胡瑗《洪范解》一卷,并附题解云:“皆其门人所录,无诠次首尾。”意思是此书亦当属语录体著作。但四库馆臣却有不同有意见,《四库全书总目》著录胡瑗《洪范口义》二卷,并认为:“《周易口义》出倪天隐之手,旧有明文。晁公武《读书志》谓此书亦瑗门人编录,故无诠次首尾。盖二书同名‘口义’,故以例推。其为瑗所自著与否,故无显证。至其说之存于经文各句下者,皆先后贯彻,条理整齐,非杂记、语录之比,与公武所说不符,岂原书本无次第,修《永乐大典》者为散附经文之下,转排比顺序欤?抑或公武所见又别一本也?”[13]90也就是说,《洪范口义》是否为弟子记录的语录体作品还值得怀疑,原因是该书原本已佚,今本是从《永乐大典》中辑佚出来的,不能判定是否与晁公武看到的为同一书。此外,《直斋书录解题》卷三、《文献通考·经籍考》和《宋史·艺文志》又著录有胡瑗《春秋口义》五卷,今已不传,因此其是否为语录体著述更是无从考证。但不管怎样,宋代儒家语录源于胡瑗则明矣。
不过,无论是从内容还是影响来说,胡瑗《周易口义》都无法与后来的二程语录相比。因为二程语录不但详细记录了二程对诸多经典的解释、讨论与思考,更重要的是他们通过对儒家经典的重新诠释而建立起一套具有抽象性和思辨性的理学思想体系。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把二程语录作为宋儒语录的开端亦未尝不可。而《郡斋读书志》“语录”类把《河南程氏遗书》二十五卷附录一卷、《外书》十二卷放在首位,亦当是出于这方面的考虑。
二、二程语录与禅宗语录的关系
关于宋代儒家语录与禅宗语录之间的关系,明人杨巍《嘲儒》诗云:“尼父不言静,后儒何怪哉,纷纷诸语录,皆自‘五灯’来。”[15]近人梁启超则说:“自禅宗语录兴,宋儒效焉,实为中国文学界一大革命。”[16]在他们看来,宋儒语录的出现完全是儒家学者学习和效法禅宗语录的结果。但事实是否如此呢?我们试以二程语录为列,作一番具体的分析和探讨。
笔者认为,宋儒语录受到禅宗语录的影响是毫无疑问的,因为生活在那样一个佛教与禅悦之风盛行的时代,学者们不可能不受其影响。正如二程所言:
如杨、墨之害,在今世则已无之。如道家之说,其害终小。惟佛学,今则人人谈之,弥漫滔天,其害无涯。[8]3
昨日之会,大率谈禅,使人情思不乐,归而怅恨者久之。此说天下已成风,其何能救!古亦有释氏,盛时尚只是崇设像教,其害至小。今日之风,便先言性命道德,先驱了知者,才愈高明,则陷溺愈深。[8]23
由此可见,当时佛教对学者的影响是很大的,就连二程兄弟也不例外。如程颢“泛滥诸家,出入于老、释者几十年”[8]638,程颐“少时多与禅客语,欲观其所学浅深”[8]63。因此他们受到禅宗的影响亦在情理之中。一方面是在心性论上吸收了禅宗的心性学说。如禅宗认为:“一切万法,尽在自心(“心”原作“身”,依郭朋校语及上下文意思改。笔者注),何不从自心顿现真如本性?《菩萨戒经》云:‘我本元自性清净’,识心见性,自成佛道。”[3]58而二程则认为:“一人之心即天地之心,一物之理即万物之理。”[8]13也就是说,每个人的心灵都是与天地相通的,因而都具有洞悟真理的能力。正如程颐所说:
只心便是天,尽之便知性,知性便知天,当处便认取,更不可外求。[8]15
心即性也。在天为命,在人为性,论其所主为心,其实只是一个道。……天下更无性外之物。[8]204
在二程看来,心与性是一体的,这显然是对禅宗心性论的吸收与改造。但两者之间还是有本质区别的,因为在禅宗那里,心性只有认识功能,而二程则把它上升到宇宙本体的高度。程颐指出:“在天为命,在义为理,在人为性,主于身为心,其实一也。”[8]204又说:“自理言之谓之天,自禀受言之谓之性,自存诸人言之谓之心。”[8]296-297并批评禅宗只讲“识心见性”,而不知道“存心养性”。正如程颢所言:“孟子曰:‘尽其心者,知其性也。’彼所谓‘识心见性’是也。若‘存心养性’一段事则无矣。彼固曰出家独善,便于道体自不足。”[8]139也就是说,禅宗的“识心见性”虽与先秦儒家的“尽心知性”相当,但儒家讲“存心养性”,而禅宗则不讲存养。
另一方面,就是在表现形式上充分借鉴了禅宗的口传心授和面对面机锋对辨的形式。
其一,大量使用当时新鲜活泼的口语来阐释经典义理,以利于听众接受。如《遗书》卷三云:
“鸢飞戾天,鱼跃于渊,言其上下察也。”此一段子思吃紧为人处,与“必有事焉而勿正心”之意同,活泼泼地。会得时,活泼泼地;不会得时,只是弄精神。
程颢在语录中连续运用了的“吃紧”、“活泼泼地”、“弄精神”等宋代流行的俗语,以利于于听众对讲话内容的理解。并且其中的“弄精神”实际上是套用了禅语,《朱子语类》卷六十三指出:
曰:“程子又谓‘会不得时只,是弄精神’,何也?”曰:“言实未会得,而扬眉瞬目,自以为会也。‘弄精神’,亦本是禅语。”
不仅如此,二程有时还干脆直接引用禅语来启发弟子。如《遗书》卷一载:
侯世与云:“某年十五六时,明道先生与某讲《孟子》,至‘勿正心,勿忘勿助长’处,云:‘二哥以必有事焉而勿正为一句,心勿忘勿助长为一句,亦得。’因举禅语为况云:‘事则不无,拟心则差。’某当时言下有省。”
所谓拟心就是指用智。程颢借用禅语“事则不无,拟心则差”,说明人们要坚持不懈地追求和培养浩然之气的精神境界,既不能心中忘记它,但也不能拔苗助长,就像禅宗所说的既不能不应付事物,但也不可有拟心。因此冯友兰先生认为:“这一条泄露了道学和禅宗的继承关系。”[17]
其二,主张学习圣人之道不要泥于文字,要用心体悟。二程认为执著于文字会妨碍对道的领悟,所以当有弟子问:“作文害道否?”程颐回答说:“害也。凡为文,不专意则不工,若专意则志局于此,又安能与天地同其大也?”[8]239并指出:“解义理,若一向靠书册,何由得居之安,资之深?不惟自失,兼亦误人。”[8]169这与禅宗不执著文字的主张是一致的。所以程颢对程门高祖谢良佐专以记诵博识为能事十分不满,并对此提出了严厉批评。《外书》卷十二引《上蔡语录》云:
昔录《五经》语作一册,伯淳见,谓曰:“玩物丧志。”
明道见谢子记问甚博,曰:“贤却记得许多。”谢子不觉身汗面赤。先生曰:“只此便是恻隐之心。”
程颢之所以批评谢良佐“玩物丧志”,就是担心其沉溺于书册文字而影响了对“道”的体悟。程颢的话对谢良佐的影响可谓至深,以至于他在二程门下学习多年,连老师的讲话都不敢记录。《上蔡语录》卷三云:“昔从明道、伊川学者,多有语录,唯某不曾录,常存著他这意思,写在册子上失了他这意思。”所以今本《二程遗书》中只收录了一卷谢良佐事后追记二程讲学的文字。
其三,引导弟子从日常生活和眼前事物中洞彻圣人之道。《外书》卷十一云:
尹子(指尹焞)曰:“冯理自号东皋居士,曰:‘二十年闻先生(指程颐)教诲,今有一奇特事。’先生曰‘何如?’理曰:‘夜间宴坐,室中有光。’先生曰:‘颐亦有奇特事。’理请问之,先生曰:‘每食必饱。’”
很显然,程颐对冯理故弄玄虚的做法表示不满,就引导他从日常生活中去体悟圣人之道。因为在二程看来,所谓圣人之道并不是虚无缥缈的,它就存在于我们的日常生活中,是可感可知的。正如《外书》卷十二所载:
先生(指尹焞)尝问于伊川:“如何是道?”伊川曰:“行处是。”
有人问明道先生:“如何是道?”明道先生曰:“于君臣父子兄弟朋友夫妇上求。”
上述两条语录明显是借鉴了禅宗语录,与禅门中流行的“问:‘如何是道?’师曰:‘白云覆青嶂,蜂鸟步庭花’”[18]67、“问:‘如何是佛法大意?’师曰:‘蒲花柳絮,竹针麻线’”[18]146等问答,如出一辙。
其四,运用反语、反问、设喻等来诱导弟子。如《外书》卷十二云:
问有鬼神否?明道先生曰:“待向你道无来,你怎生信得及?待向你道有来,你且去寻讨看。”
面对弟子有关鬼神的询问,程颢没有直接回答,而是用反问来表明自己的态度。再如《外书》卷十二载:
或问明道先生,如何斯可谓之恕?先生曰:“充扩得去则为恕。”“心如何是充扩得去底气象?”曰:“天地变化草木蕃。”“充扩不去时如何?”曰:“天地闭,贤人隐。”
针对弟子“心如何是充扩得去底气象”、“充扩不去时如何”的疑问,程颢也没有直接正面回答,而是用了“天地变化草木蕃”与“天地闭,贤人隐”两个比喻,让弟子用心去思考揣摩。
其五,教导弟子心中不可执著于事。如:
伯淳在澶州日修桥,少一长梁,曾博求之民间。后因出入,见林木之佳者,必起计度之心,因语以戒学者,“心不可有一事。”[8]65
伊川先生在经筵,每进讲,必博引广喻以晓悟人主。讲退,范尧夫曰:“先生怎生记得许多?”先生曰:“只为不记,故有许多。若还记,却无许多也。”[8]430
目畏尖物,此事不得放过,便与克下。室中率置尖物,须以理胜佗,尖必不刺人也,何畏之有![8]51
上述所引语录中都隐含有佛教的“不执著”“性空”等思想。并且由此出发,程颐还对弟子认为“颜子(颜回)乐道”的观点提出了批评。《外书》卷七云:
(鲜)于侁问伊川曰:“颜子何以能不改其乐?”正叔曰:“颜子所乐者何事?”侁对曰:“乐道而已。”伊川曰:“使颜子而乐道,不为颜子矣。”
程颐认为颜回所乐非道,原因是圣贤心中是不会执著于事的,正如程颢所言:“颜子箪瓢,非乐也,忘也。”[8]88也就是说,颜回之所以能处陋巷而不改其乐,是因为他忘记了自己所处的艰苦环境。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出,二程语录受禅宗语录的影响是十分明显的,虽然他们表面上批禅学批得很厉害,但暗地里却学习和借鉴禅宗的东西。正如清代学者江藩所言:“禅门有语录,宋儒亦有语录,禅门语录用委巷语,宋儒语录亦用委巷语。夫既辟之而又效之,何也?盖宋儒言心性,禅门亦言心性,其言相似,易于浑同,儒者亦不自知而流入彼法矣。”[19]但尽管如此,我们也不能把包括二程语录在内的理学家语录的出现完全归诸禅宗语录影响的结果。正如美国汉学家贾德纳所言:“学者们倾向于认为,在编纂‘语录’的过程中,新儒学的思想家们是受到了禅宗大师‘语录’体的影响,毕竟,这两派的‘语录’有着极大的相似性,尤其在他们的表达风格和对口语化语言的创造性运用上。大多数新儒学大师,事实上,几乎所有被作为‘语录’对象的人,都曾经研究过禅宗佛教,因而毫无疑问熟悉佛学的‘语录’体。但是,最近的研究表明,一方面,禅宗佛教徒们确实可能早新儒家(似乎是比理学家更恰当的说法)大约一百年就已采用‘语录’形式,但另一方面,这种体例直到11世纪、12世纪,也就是说,直到它在新儒家之间流行开来时,才开始在禅师自身圈子内发达起来。如此说来,一种学派对另一种学派的影响是不那么易于假定的。”[20]也就是说,理学家语录在某些方面受到禅宗语录的影响是毫无疑问的,但不能过于夸大这种影响。因为理学家语录的出现既是当时社会儒、释、道三教并行,各种宗教派别和思想之间相互交融、相互影响的结果,实际上也是儒家学派自身发展的结果,它的出现是对汉唐经学的一种反动,是理学家们为进一步推动儒家学说的发展所作的一种新的尝试。相对于汉唐以来形成的以章句训诂为主的经解形式来说,以口义为主的语录不但有利于经书义理的阐发,还有利于理学家从中发挥自己的思想,并在与参与者的对话中不断碰撞产生出新的思想火花,从而创造出一种全新的思想体系——理学。因此,那种把理学家语录的产生完全归结于受禅宗语录的影响的观点是有失偏颇的。总而言之,二程语录与禅宗语录之间有本质的不同,禅宗语录是为了打破佛教经典的束缚,以一种更简便直接的方式接引听众,所以其中有许多令人匪夷所思的语言和动作,甚至有时不惜呵佛骂祖。而二程语录则是为了更好地维护和传承儒家学说,进一步发展和完善儒家思想理论体系,所以它虽然借鉴了禅宗语录的某些形式,但核心的内容却是在对儒家经典提出的问题,不断结合时代的特点而作出新的回应。所以我们不能把二者混同起来。
[1]李颙.二曲集[M].北京:中华书局,1996:426.
[2]释道宣.续高僧传·法冲传[M].大正藏:卷五十.
[3]郭朋.坛经校释[M].北京:中华书局,1983.
[4]周裕锴.禅宗语言[M].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9:108.
[5]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358.
[6]葛兆光.门外谈禅[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122.
[7]钱大昕.十驾斋养新录[M].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2000:382.
[8]程颢,程颐.二程集[M].北京:中华书局,2004.
[9]杨玉华.语录体与中国古代白话学术[J].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9(3).
[10]晁公武.郡斋读书志[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
[11]顾炎武.顾亭林诗文集[M].北京:中华书局,1983:131.
[12]陈植锷.北宋文化史述论[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367.
[13]永瑢等.四库全书总目[M].北京:中华书局,1965.
[14]朱彝尊.经义考[M].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卷十七.
[15]杨巍.存家诗稿[M].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卷六.
[16]梁启超.佛学研究十八篇[M].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16.
[17]冯友兰.三松堂全集:第十三卷[M].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2001:288.
[18]释普济.五灯会元:第一册[M].北京:中华书局,1984.
[19]江藩.国朝汉学师承记(附国朝宋学渊源记)[M].北京:中华书局,1983:190.
[20]田浩,等.宋代思想史论[C].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39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