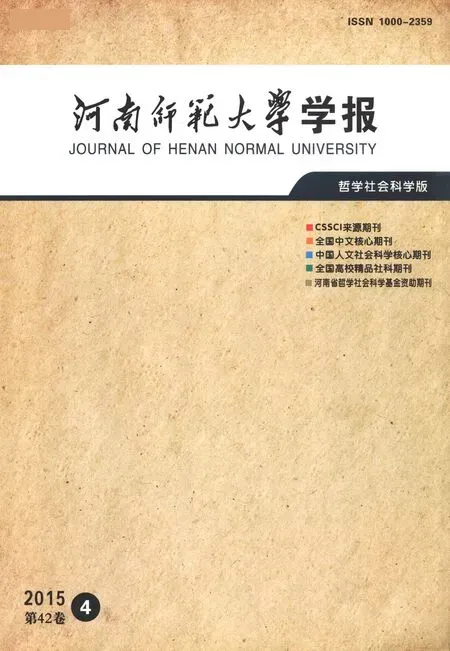马克思身体哲学的当代解读
张 璟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哲学院,湖北 武汉430060)
马克思的身体哲学以人的感性活动为基点,全面颠覆了意识哲学的形而上学传统。就理论形态而言,马克思的身体哲学在肯定人的感性活动的基础上,把人与自然、人的自然存在与社会存在、个体存在与社会存在、感性存在与理性存在有机统一起来,从而在致思向度上实现了从理性存在向感性存在、从感性存在向感性活动、从抽象思维向具象思维的哲学革命。马克思的身体哲学的重大意义在于,把抽象“解释世界”的意识哲学推向实际“改变世界”的身体哲学,把人的存在本质确定为自由自觉的“感性的人的活动”,从而宣告了形而上学传统的终结。当前,重新解读和推进马克思的身体哲学,反思和矫正现代化过程中的异化现象,走出身体存在与生命活动的困境,彰显身体存在与生命活动的价值意义,成为哲学研究的重大使命。
一、马克思的“自然之维”与身体的生成
如何看待自然,如何看待自然界对于人类社会的基础地位和决定意义,这是所有哲学都难以回避的重大问题。围绕着对这个问题的不同回答,划分出彼此不同的哲学派别:唯心主义派别认为,人类与自然界都是神造的,天意或某种神秘的精神力量主宰着自然界和人类的命运;直观唯物主义认为,外在于人类社会的自然界历来如此,永恒存在,它不受人的影响,反而外在地决定人类的命运;马克思的身体哲学把自然界的人的本质和人的自然的本质有机统一起来,从而揭示了人的本质力量及其源头活水。
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曾指出:“工业是自然界对人,因而也是自然科学对人的现实的历史关系。”[1]89应当说,人与自然的关系是人类历史过程中永恒的基础和主题,自然界的命运与人类的命运在这里紧密相连、同步生成。对此,理论界似乎早已部分地达成共识。然而,人自身的自然与人化的自然是如何相互作用、相互过渡的,如何才能较全面地把握其中实际发生作用的现实中介,至今还存在一些盲点或误解,有待进一步加以探讨。
按照马克思的自然观,可以把自然分为人化自然和人自身的自然两大类。马克思作出如下阐释:“劳动生产率是同自然条件相联系的。这些自然条件都可以归结为人本身的自然(如人种等等)和人的周围的自然。外界自然条件在经济上可以分为两大类:生活资料的自然富源,例如土壤的肥力,鱼产丰富的水域等等;劳动资料的自然富源,如奔腾的瀑布、可以航行的河流、森林、金属、煤炭等等。在文化初期,第一类自然富源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在较高的发展阶段,第二类自然富源具有决定性的意义。”[2]219可以看到,人们对自然的直接依赖程度,即主要靠自然界直接提供生活资料,还是主要通过物质生产活动从自然界获取生活资料,标志着人类文明的进化发展程度。马克思指出:“人直接地是自然存在物。人作为自然存在物,而且作为有生命的自然存在物,一方面具有自然力、生命力,是能动的自然存在物;这些力量作为天赋和才能、作为欲望存在于人身上;另一方面,人作为自然的、肉体的、感性的、对象性的存在物,同动植物一样,是受动的、受制约的和受限制的存在物,就是说,他的欲望的对象是作为不依赖于他的对象而存在于他之外的;但是,这些对象是他的需要的对象;是表现和确证他的本质力量所不可缺少的、重要的对象。说人是肉体的、有自然力的、有生命的、现实的、感性的、对象性的存在物,这就等于说,人有现实的、感性的对象作为自己本质的即自己生命表现的对象;或者说,人只有凭借现实的、感性的对象才能表现自己的生命。”[1]105人类同自然界关系的历史演进,人的表现自己生命的对象的不断变化,把不同文明程度的人类历史划分为几个彼此不同的历史分期,如渔猎文明、农耕文明、工业文明、后工业文明等。不论人类处于哪个文明史的阶段,都具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人不能脱离自然界,不能企图在自然界以外生存,不能脱离自然条件和不受自然条件的制约去从事任何生产活动;没有自然界,人类就根本不能生产,不能生活,不能创造自己、展示自己、实现自己,不能存活和持续发展,更谈不上享受什么幸福生活了。
实践活动是人的身体生成的现实中介。马克思提出:“在实践上,人的普遍性正是表现为这样的普遍性,他把整个自然界——首先作为人的直接的生活资料,其次作为人的生命活动的对象(材料)和工具——变成人的无机的身体。自然界,就它自身不是人的身体而言,是人的无机的身体。人靠自然界生活。这就是说,自然界是人为了不致死亡而必须与之处于持续不断的交互作用过程的、人的身体。所谓人的肉体生活和精神生活同自然界相联系,不外是说自然界同自身相联系,因为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1]56-57这里马克思所表达的精义在于,人身外的自然界和人自身的自然,不断地在人的对象性活动中相互作用,相互转化,在人能动地同自然界打交道的过程中,外在自然与人自身的自然相互影响、相互生成,于是,也就创生了人的生活、人的生命存在;通过人的能动选择,即通过人与自然相互作用的纽带,形成了人与自然有机统一的内在关系、整体关系,在这种关系中,人虽然是自然界的一部分,但却不是自然界中普普通通的一部分,而是有意识、有智慧、有灵性、会思想的特殊的一部分,因为人的活动是能动的、自觉自为的、有目的的活动。如果不承认这一点,把人等同于或混同于动物或一般的自然存在物,那就会把马克思的身体哲学混同于或等同于费尔巴哈的直观唯物主义。可见,身体的现实生成,靠人自己的选择、自己的活动、自己的劳作、自己的实践,而不能期盼上天或神灵的赐予,不能幻想有什么“天上掉馅饼”的奇迹。
为了阐明人与自然之间相互作用的现实中介,马克思又指出:“人自身作为一种自然力与自然物质相对立。为了在对自身有用的形式上占有自然物质,人就使他身上的自然力——臂和腿、头和手运动起来。当他通过这种运动作用于他身外的自然并改变自然时,也就同时改变他自身的自然。”[2]177可以看到,人自身的自然,虽有别于人身外的自然,却与外在自然密切相通。人的生命形式不同于自然界的动植物,更不同于无生命的自然物质形式,因为人不仅有其生理需求,有其求生欲望,而且还具有其他生物难以比拟的生存智慧、思想意识、精神追求和实践能力,是自然界中最具能动性和创造力的生命存在物。
身体的生成与人化自然的生成是彼此同步的。有了人的能动活动,自在的自然资源、自然对象才有可能被人自觉选择、加工、改造、制作成用以满足人的需要的生活资料或社会财富。随着社会生产力的不断提高,人类日益摆脱直接依赖于自然界、直接从自然界获取现成生活资料的存在状态和生存方式,逐步改变和提升自身的主体素质和生活境况。人与自然不可分离,人依靠自然界开展自己的生活资料的生产。人与自然之间水乳交融,“我们连同我们的肉、血和头脑都是属于自然界和存在于自然界之中的”[3]384。
人同自然的一体性,还体现为人的身体的生成必定要与其周围的环境同步生成、同命相连。马克思的身体哲学基于关注和尊重人的存在、人的活动的需要,总是把尊重人和尊重人的生存环境、尊重人自身的自然与尊重人身外的自然有机地联系在一起。在马克思看来,在人与自然相统一的过程中,始终贯穿着一个“交相利”的原则,否则,假如在人与自然之间出现了“交相害”的关系,那就必然导致人与自然的双重异化——人加害于自然,自然就会“惩罚”人;到头来必然是人自己戕害自己。这里存在着人与自然之间的“一荣俱荣”或“一损俱损”的同呼吸、共命运的关系,体现着“人创造环境,同样,环境也创造人”[3]92的双向互动关系。如果把人的身体的生成与周围环境的变化彼此割裂开来,对立起来,甚至执意地去通过“征服自然”“掠夺自然”“破坏自然”来发展经济,那就必然导致环境的蜕变与人的身体的异化,因为人不能在被严重污染、破坏的环境中得到幸福。
通过以上有关马克思“自然之维”的分析,我们可以得出以下启示:(1)身体的生成植根于自然界。人与自然界的界限是相对的,二者之间相互过渡,相互转化。马克思提出:“没有自然界,没有感性的外部世界,工人什么也不能创造。它是工人的劳动得以实现、工人的劳动在其中活动、工人的劳动从中生产出和借以生产出自己的产品的材料。”[1]53自然是身体现实生成的坚实根基,任何时候人们都没有理由把身体的健康和生命安全弃诸脑后。(2)身体的生成与人化自然的生成彼此同步。这里的人,是指现实的、有生命的个体的存在;这里的自然,是指与人相互规定的人化自然。马克思不满意费尔巴哈的观点,认为费尔巴哈“没有看到,他周围的感性世界决不是某种开天辟地以来就直接存在的、始终如一的东西,而是工业和社会状况的产物,是历史的产物,是世世代代活动的结果”[3]76。这说明,人与周围环境密不可分,人与自然没有谁先谁后、谁决定谁的单向关系。(3)现实的身体与其生存环境紧密相连。自然环境是人化自然的重要形式,它是人的本质力量的透射与确证。自然环境的质量如何,直接标志着人的素质和能力的实际状况。现代工业文明产生以来,发展经济的利益驱动,导致生态环境与人的身体同步地发生异化。破解人与自然绝对对立的恶性循环,不单纯是一个认识问题,而是一个生活方式和价值选择的人生立足点问题,是提升人的自觉自省和综合素质的问题;只要人们不能节制自己追求金钱和财富的狂热欲望,破解这个恶性循环的死结也就永远是无望的。
二、从“感性存在”到“感性活动”
马克思指出:“全部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无疑是有生命的个体的存在。”[3]67这里所说的个体特征在于“有生命”,而有生命的存在就意味着“活动”,是“动”的过程而不是“静”的在场。缘于此,马克思又指出:“首先应当确定一切人类生存的第一个前提,也就是一切历史的第一个前提,这个前提是:人们为了能够‘创造历史’,必须能够生活。但是为了生活,首先就需要吃喝住穿以及其他一些东西。因此第一个历史活动就是生产满足这些需要的资料,即生产物质生活本身。”[3]78-79这样一来,马克思的历史观与费尔巴哈的历史观就在“能动的活动”与“消极的定在”之间划清了界线。马克思认为,费尔巴哈虽然也强调“感性存在”,并力图以此来代替他不满意的黑格尔式的“绝对精神”,但他实际上“没有看到,他周围的感性世界决不是某种开天辟地以来就直接存在的、始终如一的东西,而是工业和社会状况的产物,是历史的产物,是世世代代活动的结果”[3]76。马克思看到,历史领域中没有“活动”的“存在”,什么也不是,没有“活动”什么也不再能存在。近现代以来,工业和商业的发展,人们对感性活动的认知,才使人们达到了自己的目的,由此获得自己所需要的生活资料。
“劳动的身体”是人类历史的前提。身体是历史的能动主体,是生产生活、生产人化自然、生产身体自身的能动力量。在马克思的唯物史观那里有其独特的理解视角,它把人类的历史看作是“劳动的身体”的展开史、经验史、实现史、更新史,尤其高度关注现代人的生存境遇,并在自觉反思中扬弃身体的异化和自然的异化,推进身体的解放和全面发展。即是说,在唯物史观的理论视域下,身体的发展程度是人类历史的标尺或轴心,但这并非放纵和迁就“人类中心主义”。身体的内涵十分丰富,它不仅在时间维度上包含“曾经的身体”“当下的身体”和“未来的身体”,而且在空间维度上包含“内在的身体”和“外在的身体”;可以说,唯物史观的身体视角,同时并包了“人身的自然”和“身外的自然”、身体的自身和身体的环境。对于马克思来说,人作为自然的存在物,“一方面具有自然力、生命力,是能动的自然存在物;这些力量作为天赋和才能、作为欲望存在于人身上;另一方面,人作为自然的、肉体的、感性的、对象性的存在物,同动植物一样,是受动的、受制约的和受限制的存在物……人只有凭借现实的、感性的对象才能表现自己的生命”[1]105-106。在异化劳动的历史背景中,人的对象性活动的对象和结果遭到了普遍的剥夺,这样一来也就无异于剥夺了人的身体、剥夺了人的生命;而任何对于身体的践踏、摧残和折磨,都是“釜底抽薪”式地阻挠、扭曲和中断人类历史的野蛮行径。
马克思的唯物史观对历史和现实世界的诠释,都是以身体为轴心、为基点的。作为马克思哲学基石的实践观、劳动观,不仅要求从关注“身体”的意向性、关注“身体”的实际境遇、尊重“身体”的感官体验和主观感受出发,而且高度关注实践和劳动的效果是否真正有利于身体的自由、解放和发展。判断一个社会历史阶段的性质或文明程度如何,不是依据它的承诺和宣言,而是要看现实中一个个身体的实际境遇如何,看实际进行的实践和劳动是不是身体的自主选择,看身体对于自己的对象性活动的结果是否拥有自主、自由的占有权、支配权、享用权。这就是说,要通过考察身体是不是自己命运的主人,身体是否能够真正成为自己活动的行为主体、自己价值取向的选择主体,即依据身体的精神和行为的自由度、身体的生活质量,来反观和判定特定社会历史阶段所实际达到的文明程度。当信息的获取与传递达到一定的发展阶段,如果一个社会的信息发布机构所传达的信息,总是与实际生活中一个个现实身体的实际处境严重不对称,即现实身体的实际生活状况被故意遮蔽起来,剥夺了现实身体的知情权、话语权、参与权、劳动权、享受权,那么,这个社会就无疑是一个严重扭曲的、文明匮乏的社会,这样的社会的劳动就无疑是异化劳动。
“对象性活动”是身体的本质规定。人的生命活动不只是简单的、类似于动物的本能活动。人们一边从事实际活动,一边为这种活动建构自己的意识、理论、计划、目标等等,即建构用于指导自己活动的实践观念,从而使得这种活动成为有目的的、自觉自为的活动。即是说,人能够从当下的存在预见未来的存在,为自己的行为预设方向和目标,并通过意志的努力朝着既定的目标前进。正是在这一点上,人与动物的界限就是确定的、不可逾越的。离开了有意识的理性支配,人就既不可能有属于自己的真正的精神生活,也不可能有真正人的物质生活,当然也就没有真正的、完整意义上的人的身体的存在。
要赋予身体的存在以真正人的意义,就必须把身体的存在视为能动的、有意识、有选择的自觉自为的活动,而不能仅仅以“感性存在”、以“我在活着”来诠释身体的本质。这是因为,对于“感性存在”既可以从“客体的”“直观的”形式去理解,也可以从“主体的”“能动的”方面去理解。前者是直观唯物主义的存在观,后者才是马克思主义的存在观。
今天,我们重新解读马克思的身体哲学,需要坚守身体的感性的“对象性活动”的基地,而不能满足于、停留于一般地谈论“存在”的意义,不能把人的“感性活动”降低为或者直观为人的“感性存在”,不能停留在费尔巴哈的类似于动物式的自然人本主义的立场上。因为身体的感性的“对象性活动”除了可供直观或外观地把握的特征以外,还同时具有非直观、非外观的丰厚的思想意识和精神文化内涵,比如身体的心理意向、兴趣爱好、理想信念、道德情感、审美情趣……所有这些内涵于人的感性的“对象性活动”中的身体特质,仅凭外在直观是根本无法理解和把握的。应当从实际存在的“自然压迫”和“社会压迫”下切实有效地推进身体的解放,自觉扬弃人的异化和自然的异化。这种对于异化的扬弃,不能局限于口头上,而必须付诸行动,付诸自由自觉的感性活动,这种活动正如马克思所强调的那样:“通过实践创造对象世界,改造无机界,人证明自己是有意识的类存在物,就是说是这样一种存在物,它把类看作自己的本质,或者说把自身看作类存在物。……动物只是按照它所属的那个种的尺度和需要来建造,而人懂得按照任何一个种的尺度来进行生产,并且懂得处处都把内在的尺度运用于对象;因此,人也按照美的规律来构造。”[3]46-47运用感性活动来创造身体,并且逐步地用全面的身体取代和超越片面的身体,这就是我们今天之所以重新强调马克思的身体哲学所实现的把“感性存在”推进到“感性活动”的理由,并借以领悟马克思身体哲学在哲学史上所作出的杰出的理论贡献,以及它所实现的哲学革命的深远意义。
三、从抽象思维到具象思维
马克思身体哲学的致思向度,在哲学史上实现了一场深刻的理论变革,它挣脱了传统哲学的话语范式,完成了哲学思维的身体转向:它摆脱严格的逻辑限定,摒弃意识哲学文本的约束,放弃建构严整理论体系的追求,以坦荡务实的姿态为人的感性活动和自由生活做辩护,这里有生动的对象性活动,有丰富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有身体的理想追求和发展蓝图,逐步地趋向于“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的高度文明社会的理想目标。
马克思确立新的哲学主题,把视野从意识和物质的二元对立转向活动与生活的主体——身体;摒弃以严整体系为特征的形而上学构想,确立以人的对象性活动为基地的身体哲学思维;放弃创构“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理论目标,勇敢地为现实的身体和人的生活做辩护。马克思指出:“意识在任何时候都只能是被意识到了的存在,而人们的存在就是他们的现实生活过程。”[3]72这里,可以换一种说法,即人的现实生活过程,蕴含着人的理性、意识,只是这种“理性”“意识”不是虚幻的、不可感知的,而是感性的、具体的,在人的现实生活中与感性的生活过程交融一体的。将来的高度文明的人类社会,将是“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的社会,是每个现实人的生命个体“无拘无束”的充分自由的社会,“事实上,自由王国只是在必要性和外在目的规定要做的劳动终止的地方才开始。因而按照事物的本性来说,它存在于真正物质生产领域的彼岸”[4]。可以想象,那将是身体无限自由、人生无限全面的美好境界。
在马克思的身体哲学视域内,没有空泛的概念,没有理论的训诫,没有宏大的昭告天下的标语口号,它始终从人的对象性活动和现实生活出发,高度关注人的自由解放,时刻关注身体的命运,在以下几个视点上向世人发出谆谆警示。
1.身体要推翻意识的压制。长期以来,人们习惯于把自身割裂为“意识”与“身体”两个部分,并且总是将意识归为人之高尚的决定性因素,身体通常被贬低为令意识产生诸多烦恼和障碍的根源。在《斐多篇》中,柏拉图记载了苏格拉底赴死时的无所惧怕、从容不迫、谈笑风生的场景,对苏格拉底而言,死亡的只是身体本身,是“灵魂和肉体的分离;处于死的状态就是肉体离开了灵魂而独自存在,灵魂离开了肉体而独自存在”[5]。在苏格拉底看来,消灭肉体是为了解脱灵魂的束缚,他的赴死是为了实现他的灵魂自由。马克思拒斥灵肉分离的身体观,他明确宣示,意识、理性本属于身体的一部分,是内在于身体的有机内涵,它只能服从于身体,服务于身体,为身体做谋划,为身体的生理需求、心理需求、精神需求做辩护,而不能用意识、理性去扼杀身体的欲望,用意识、理性去编制束缚身体的羁绊。
2.身体要谨防社会的改造。马克思把感性世界“理解为构成这一世界的个人的全部活生生的感性活动”[3]78,认为“生命的生产,无论是通过劳动而达到的自己生命的生产,或是通过生育而达到的他人生命的生产,就立即表现为双重关系:一方面是自然关系,另一方面是社会关系;社会关系的含义在这里是指许多个人的共同活动”[3]80。这里明确传达出这样的信息:个人以及个人的感性对象性活动,是全部社会的基础和支点,因此,社会就应该尊重个人,关爱个人,保护个人。然而,令人遗憾的是,历来存在等级、阶级、阶层对立的社会,无不对个人进行“改造”“训诫”“规制”甚至“蹂躏”,让个人做这样做那样,俯首听命,逆来顺受。福柯曾指出,社会中的各种实践内容、组织形式、权力技术以及各式历史悲喜剧,都是围绕着身体展开的角逐,并且对身体进行了精心的规划和锻造;于是,身体成了各种权力追逐的目标和统治的对象。社会惩罚,“最终涉及的总是身体,即身体及其力量、它们的可利用性和可驯服性、对它们的安排和征服”。在现实社会生活中,身体总是难免卷入政治领域,“权力关系总是直接控制它,干预它,给它打上标记,训练它,折磨它,强迫它完成某些任务、表现某些仪式和发出某些信号”[6]。在社会的“改造”“塑造”和“蹂躏”下,身体不再与人的神圣权利有任何关联,它不再是喜气洋洋的身体,而是悲观、被动、呆滞的身体,从而沦为社会的附属物、工具和奴役对象。
3.身体要警惕权力的蹂躏。权力,尤其是政治权力,如果不是清正澄明的社会治理手段,那它就一定是个人的异在、身体的异在。福柯指出,自18世纪始,身体被权利与政治包围,由此进入了“知识控制与权力干预的领域”。这里的身体是被动的身体,它被权力锻造和揉捏。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一个身体如果沦为一个牺牲者,就会被排除在国家的政治法律秩序之外,他和权利的联系因此被斩断。杀死这个身体,则无需承担责罚。历史的记忆提醒人们,身体和身体的权利是高尚的,值得人们从人性的和法律的角度予以尊重和保护,不能再让任何邪恶在身体面前施展淫威。
4.身体要祛除自我伤害。对于身体的伤害因素,有的是来自外在的力量,有些则是来自内在的力量,都具有自我伤害的性质。来自自我的伤害程度,在不同历史条件下存在差别,不见得社会越文明,自我伤害的程度就越低,甚至与文明程度的提高成正比例地加剧。比如,生活的奢侈对于身体的伤害、不同阶级或集团的政治谋划对于异己身体的伤害、由于科学技术的发展而破坏环境对于身体的伤害等等,在人类文明的初期由于条件所限就很少存在。细数起来,日常生活中的食物匮乏和暴饮暴食、厌恶劳动和过度劳动、过度纵欲和自寻烦恼等等,都是健康身体的大敌。
在马克思的身体哲学的思维向度内,没有空洞的标语口号,没有严谨的逻辑体系,没有固定的条条框框,没有神圣的清规戒律,这里只有活生生的人的对象性活动,只有一个个有尊严的身体,只有和感性世界融为一体的无比珍贵的生命;生命高于一切,导致生命和环境异化的财物、金钱、权力、地位等等,都是身外之物。这就是当今重新解读和发展马克思身体哲学的真谛所在。
[1]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
[2]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3]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4]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928.
[5]柏拉图.斐多[M].杨 绛译.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2000:13.
[6]米歇尔·福柯.规训与惩罚[M].刘北成,等,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9: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