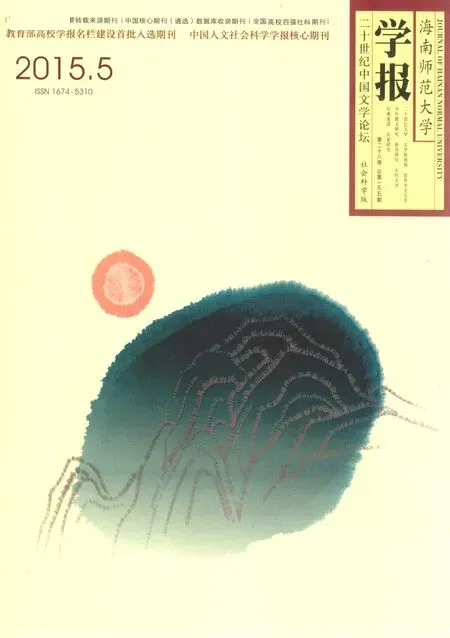理论资源与文学理论体系建构的深层危机
廖述务
(海南师范大学 文学院,海南 海口571158)
经多年积累,文艺学学科建设进入到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其显在的表征在于部分文学理论家在体系建构方面更趋自觉。有学者就认为,在反本质主义的视域中,新世纪有三种理论体系尤为值得关注:陶东风围绕《文学理论基本问题》形成的“整合主义”、南帆围绕《文学理论(新读本)》形成的“关系主义”、王一川围绕《文学理论》形成的“本土主义”。[1]当然,这是就“反本质主义”论域而言的。其实,理论体系的建构者并不止这些,童庆炳、杨春时等人的建构努力一样引人注目。文学理论体系的建构者大多是较有影响的文艺理论家。值得注意的是,理论教材的编写成为理论家建构理论体系的中介。这有如下几方面原因:教材的编写是理论家介入理论史、凸显自身学术特性与价值的重要方式;是确立理论话语权威的符号象征行为;教材本身的体系性也为理论体系建构提供了先天条件。当然,文学理论体系的建构不仅依赖教材本身,也与理论家自身的理论建树密切相关。体系建构是理论家学术研究的自然升华。
不过,诸多文学理论教材在处理中西文学理论资源时均存在一定局限。这反映了文学理论体系建构的深层危机。
一
在文学理论教材编写中如何取舍中西文论资源,显然不是一个单纯的技术问题。历史语境是最厚重的决定性因素。晚清的溃败与现代性进程的开启几乎同步,同时也隐约映衬出中西文明传统的高低优劣。五四时期,现代的先行者们过于贴近历史大幕,实难对这一进程做出超脱语境的理性判断。在对待中国文化传统这一问题上,他们中的大多数近乎一致地采取了激进的批判立场。这一文化态度对中国文学理论的早期形态产生了深刻影响。与其他学科一样,草创阶段的文学理论也是以译介为主。鲁迅先生所译厨川白村的《苦闷的象征》与章锡琛所译本间久雄的《新文学概论》,成为中国人最初接触文学理论的入门读物。日本的这两本著作都是西学东渐的产物。后来田汉所著《文学概论》则基本是本间久雄《新文学概论》的缩写本。由此可以看出,草创期的文学理论尚缺最起码的理论自主性,当然更谈不上理论体系之建构。它主要扮演了一个引入文论“火种”、传播基础知识的角色。因完全以西方为样板,传统文论自然不可能进入理论视野。
建国后的理论教材体现了一定程度的理论自觉。以群主编的《文学的基本原理》与蔡仪主编的《文学概论》是百年文学理论体系建构的发端。两位学者在与主流意识形态保持切近关系的同时,也有限度地持守着自身的理论立场。两部教材在体例上打破了苏氏教材三大板块(“本质论”、“作品论”、“发展论”)式的固定结构,发展出影响至今的五大板块式结构(在三大板块基础上增加“创作论”、“批评、鉴赏论”)。在对待中西理论资源这一问题上,以群主编的教材有巨大突破,本土文论资源开始出现,而且占据的比例不低。有论者统计指出,以群《文学的基本原理》(1964年版)引用了128个中国古代文论与文学注释,占全书注释总量的15.8%。全书引用最多的是现当代左翼理论家与文学家的观点,以鲁迅为最。[2]尽管如此,教材的框架与基本范畴依旧无法脱离苏联模式的巨大影响。如“形象”、“浪漫主义”、“现实主义”等范畴,其实都源自西方话语体系。也就是说,它在体系建构方面以借鉴为主,并没有高度的自觉性与自主性。相比而言,蔡仪主编的教材在理论资源的择取方面要逊色不少,它过多地依赖于意识形态领域的权威理论话语。
那么,以群主编的教材是怎样具体地征用本土理论资源的呢?在谈到“形象思维”时,它在引用别林斯基、黑格尔的观点的同时,也谈到中国现当代的鲁迅、赵树理等。它还引人注目地征引了大量中国传统文论思想,如刘勰、朱熹、孔颖达、皎然、钟嵘等人的论述。在谈“典型”、“现实主义”等概念时,也基本采取了类似的论述策略。应该说,以群主编的教材开创的理论模式影响深远。童庆炳主编的《文学理论教程》作为新时期最为重要的理论教材,就较多地借鉴与继承了以群教材的书写模式。在理论资源的处理方式上,这种借鉴与继承尤为明显。
以群主编的理论教材是文论体系建构的发端,是中国文艺学脱离苏联模式影响、走上理论自主的第一步。它所征引的理论资源以本土为主,而且与创作保持了灵活、多元的互动关系。这些甚至是新世纪新锐理论教材都难以企及的。童庆炳主编的《文学理论教程》在继承以群教材优点的基础上在多个方面又有了新突破。比如,它引入了文学活动论这一体系思想,将五大板块整合成一个有机整体;它还在叙事、话语理论等章节中引入了大量西方前沿思想,展现出与国外理论对话的诸多可能。尽管如此,它们组构的理论体系近年还是受到一些批评。
二
陶东风主编的教材《文学理论基本问题》在“导论”中批评指出,传统理论教材在处理中西理论资源时很容易下滑为一种拼凑行为。因为,中西理论传统的差异巨大,两者“具有极为不同的价值取向、基本范畴、理论框架以及表述形态”。比如一些理论教材在谈到“想象”这一西方概念时,就以中国的“神思”对举,这就完全没有考虑到中西文化哲学间的深刻差异(西方为主体性文化哲学,中国为天人合一文化哲学)。[3]18
应该说,这一批评具有很大合理性,一针见血地指出了传统理论教材在理论资源处理问题上的巨大缺陷。针对中西拼凑型的教材编写方式,《文学理论基本问题》提出了自身的编写准则,即“以当代西方的知识社会学为基本武器,重建文学理论知识的社会历史语境,有条件地部分吸收包括‘后学’在内的西方反本质主义的某些合理因素,以发挥其建设性的解构功能”。[3]20从西方知识社会学视野出发,《文学理论基本问题》力图摆脱非历史化、非语境化的知识生产模式,强调文化生产与知识生产的历史性、地方性、实践性与语境性。正是在反本质主义的知识视野中,该教材在理论建构上特别倚重福柯的“事件化”概念。这一概念与福柯的尼采主义谱系学思想密切相关。由此可见,陶东风主编的教材具有鲜明的后现代色彩,“后学”为其编写提供了理念基础。作为西方后学型教材的代表,《文学理论基本问题》在处理中西理论资源时又有何具体体现呢?因对中西拼凑式写法的反感,该教材采取了一种分而述之的方式来处理中西理论资源。比如第二章“文学的思维方式”中专辟两节来谈中西文学思维:第二节为“中国古代文论体系中的文学思维论”,第三节为“西方诗学体系中的文学思维论”。第六章“文学的传统与创新”也专辟两节分谈中西的传统与创新:第一节为“文学的通与变”,主讲中国古代文论中有关传统与创新的思想;第二节“古今之争”,则侧重于讲西方文艺复兴到浪漫主义时期有关传统与创新的思想。这种分而述之的后学式编写方式,其目的在于规避中西拼凑的尴尬。但实际上,这一危机并未消除。整部教材有点像把中国传统文论与西方文论进行一种简单并置与叠加,最终并没有解决如何将中西文论有机结合的问题。而且,因编写理念完全仰赖西方后现代哲学,其重心还是落在了西方文论资源上。
王一川的《文学理论》也与拼凑型理论教材有很大不同。他立足中国文论传统,意图构建一种带有中国特色的文论体系,他将其称作“感性修辞诗学”。他说:“置身在今天这个全球化或中西对话时代,需要从中国自己的文论传统中提取属于这个传统而又能存活于现代并且富于阐释活力的合适的概念或观念,参酌进行中的中外现代文论,加以必要的转换和改造,构建一种既属于中国传统而又富于个性特色的现代文论框架。”[4]这部教材极大程度地借助于中国传统文论的概念系统与精神内涵,当中感性、兴辞、意兴、衍兴、兴象等概念都与古代文论有着密切的关联。同时,在阐释文本层面、文学品质、文学创作与阅读等问题时,对西方的理论资源也有所借鉴。正因此,方克强认为,王一川的教材大致上可归结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建构思路。这种路向是对西方中心主义及其普世价值观在文学理论领域中表现的一种回应,也是重塑文学理论的中国角色和寻求中西文论平等对话方式的一次努力。其理论建构意识在新世纪新锐教材中是最强也是最显露的。[1]显然,依照这一建构思路,以群为代表的传统教材与陶东风主编的新锐教材在理论资源的处理上都过于依赖西方话语体系,没有确立起本土文论的主体性。
三
“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型的理论建构与“失语论”者之倡导甚是合拍。在后者看来,所谓“失语”,“并非指现当代文论没有一套话语规则,而是指她没有一套自己的而非别人的话语规则。当文坛上到处泛滥着现实主义、浪漫主义、表现主义、唯美主义、象征、颓废、感伤等等西方文论话语时,中国现当代文论就已经失落了自我。她并没有一套属于自己的独特话语系统,而仅仅是承袭了西方文论的话语系统”。“失语论”者还认为,要重建属于自己的话语系统,首先要接上传统文化的血脉,对“五四”以来的文化激进主义进行反思与批判。[5]
不过,在南帆看来,不论是中西拼凑型还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型,在对待传统文论时都带有观念主义的理想化色彩与民族主义的情感化倾向。他认为,某种成功的理论诞生之后,作者的确可能为自己的民族国家赢得荣誉,但人们不能仅仅因为作者的族裔而信奉他的理论。一种病毒的确认,一条物理定律,一段史料的考证,接受与否的理由是严格审定的学术价值,而不是作者的民族出身。显然,在南帆这里,功能主义代替了情感主义成为判断理论资源有效性的全新标准。面对现代性的全新语境,中国传统的文论命题,如文以气为主、盛唐气象、感兴、兴会等,都难以应对与阐释现代文学发展中出现的诸多问题。至少在目前,西方文学理论拥有更为强大的阐释能力。[6]因此,在南帆主编的教材中,传统文论开始大面积消失。该教材无疑是南帆“关系主义”理论体系建构的一个中介。它高度关注形式文论与现代语言学的意义与价值,因此文学性依旧是该教材关注的中心,但它同时强调后结构主义与话语理论对于敞开封闭的文本空间所具有的理论意义。这就为文化研究预留了足够空间。总之,在形式与意识形态之间如何寻求到一种动态平衡,成为“关系主义”关注的核心问题。从理论资源看,南帆建构的体系属于典型的“后学”型。
总体而言,南帆对待理论资源的功能主义态度较切实际,给“失语论”者莫大挑战。那么,这是否意味着“失语论”者的一些说法毫无理据呢?当然并非如此。传统文化在今天依旧是一种鲜活而有生命的存在。即便在文学领域,古典诗词曲赋依旧不乏写作者与爱好者。近年还兴起了“读经热”、“国学热”。精神层面,传统的意义更加巨大,它是不少文化人安顿灵魂的存在之家。不过,即便如此,它依旧难以应对现代性施予的压力。《白鹿原》的文化悖论与此类似。对此,我曾做过分析:“《白鹿原》意图营造一个儒家的‘文化神话’,它负责解释与规划白鹿原上的任何事件。但这一行为有着严格的疆界与封闭性,它只针对白鹿原这一所谓的儒家教化之地。当现代性的政治事件遽然进入到这个场域的时候,它采取了本能性的抵制与漠视的态度。这种态度源于这一文化视域的历史局限性。现代意义上的国家、政党、阶级斗争、经济体制以及思想文化观念等,都构成了一整套与儒家文化完全不同的运作体系。当现代性的诸种影响及后果呈现出来时,儒家文化无从应对,其阐释与实践能力轰然瓦解。于是,这些儒家的现代信徒必须收缩实践范围,以至于祠堂成为白嘉轩‘修齐治平’的唯一据点。”[7]显然,中西理论资源的分立归根结底源自两种文明形态的分殊。我们没有必要将两种资源强行扭结、拼凑在一起。南帆教材中传统文论的消隐不过是一种理性的书写策略,而与文化情感无关。
体系建构上的功能主义态度隐含了理论的自主性与话语权问题。对此,陶东风认为,勇敢直面中国现实、自由言说中国现实是解决问题的关键。[8]显然,仅此是远远不够的。全球化是全方位的,理论资源也不例外。福柯、詹姆逊、伊格尔顿、萨义德、哈贝马斯等理论家,不只流行于西方,而是全球性的理论焦点。而反观国内,我们的理论输出就要逊色得多。当下最切实的路径,就是加强理论研究的创造性与自主性。现有的理论体系建构大多以教材为中心,且以理论资源征引的地域、流派等来界定自身属性,这本身就是尚未完全达到成熟、自主阶段的体现。可以说,国内出现福柯式思想家之日,也就是理论自主性真正获具之时。到那时,所谓“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失语论”也就都成为陈年往事了。
[1]方克强.文艺学:反本质主义之后[J].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3).
[2]张法,等.世界语境中的中国文学理论[M].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10:98-105.
[3]陶东风.文学理论基本问题[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
[4]王一川.特色文论与兴辞诗学[J].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3).
[5]曹顺庆.文论失语症与文化病态[J].文艺争鸣,1996(2).
[6]南帆.理论的历史命运[J].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2003(5).
[7]廖述务.现代性与乡村祛魅——评张浩文的长篇新作《绝秦书》[J].小说评论,2014(1).
[8]陶东风.什么是学术研究的“中国话语”[J].民主与科学,2014(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