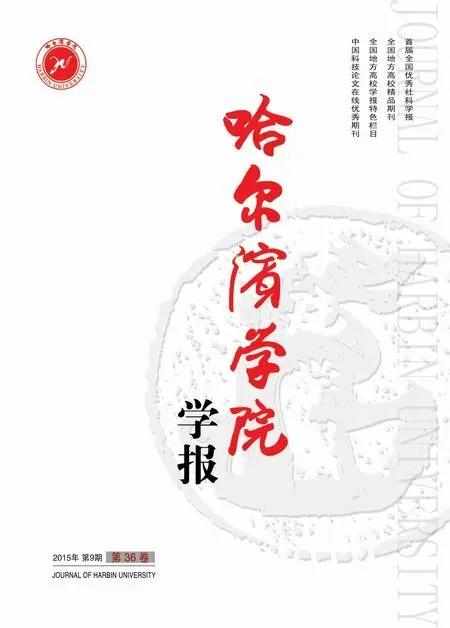严辨释教——陆九渊判别佛教考
韩兴波
(重庆师范大学 文学院,重庆 401331)
严辨释教——陆九渊判别佛教考
韩兴波
(重庆师范大学 文学院,重庆401331)
[摘要]陆九渊以“理”辨析异端,不认为“异端”就是佛教的专称;提出“天下之正理”,认为佛教道偏;以“公私义利”判别儒释,指责佛教在世俗社会问题上的谬误;针对门下弟子“溺佛”之事保持客观的态度,并未强加批判,同时又希望他们能够回归儒学。
[关键词]陆九渊;佛教;心学
陆九渊作为象山心学学派的领袖人物,以往思想研究比较偏重心学与佛禅的比较研究,在哲学思维、概念和范畴上认为心学是对佛禅思想的吸收。本文从陆九渊针对佛禅思想及其与儒家传统异同的辨析中,得到其自身对待佛教的态度,并进一步探讨两者关系。
一、力辩“异端”非特指佛教
自东汉初佛教传入中土,一直向社会各领域渗透。作为外来宗教,其本土化过程也是多方因素共同推动的结果,在此过程中,佛教渐趋性地对民族心理施以宗教影响。历三国、两晋、南北朝,行诸乱世,其宗教观念更加使世俗服膺。凡是外来思想的输入,总伴随着与本土传统观念的交锋。佛教传入后,儒士针对其是非同样存在不同的接受态度,这种是非评骘伴随佛教渐入、渐变的全过程。
《正诬论》列佛教十一条“诬”,强调佛儒两家的异处;郗超《奉法要》强调佛教与儒家的相同之处;慧远著有《出家》《沙门不敬王者论》等多篇文章,多角度肯定佛儒之同;唐代,三教鼎立,彼此消长,王通主张三教融合;傅奕、韩愈主张消灭佛教;柳宗元要求统合儒释。宋季,儒士多是排佛为主。综合考虑,“统合儒释和续传道统的双重要求,使儒教伦理拯救运动表现出相当复杂的文化情态和极其矛盾的学术心理:一方面,究心三教典籍,出入释老二氏,主动汲取其中的精神营养,是唐宋以来文人学者共同的为学方式,无一人能够例外;另一方面,辟斥二氏空虚,揭露释老祸患,标榜自己为道统嫡传正宗,讥讽他人已落入空门禅宗,又是宋明时期思想家们通行的论战手法,多数人不能超脱。”[1]陆九渊的观念自然是从先贤儒士的议论中而来,因而带有儒家传统的学术背景,又因为其独特的见解辨析而不同于前人。
陆九渊首先针对“异端”出现的时代和当时所指,申明“异端”的来源及具体内涵,“异端之说出于孔子,今人卤莽,专指佛老为异端,不知孔子时固未见佛老,虽有老子,其说亦未甚彰著夫子之恶乡愿,《论语》《孟子》中皆见之,独未见排其老氏,则所谓异端者非指佛老明矣”。[2](卷十三,P177)他认为后世为排斥其他学说,迫切地指责非正统学术,并没有对所用概念进行切实的考辩,也没有对佛教所出现的时代背景有所认识。“孔子之时,中国不闻有佛,虽有老氏,其说未炽”。[2](卷十五,P194)陆九渊认为孔子时代并未出现佛教,老学即使出现,也没有达到炽热的地步,孔子时代所指责的是“乡愿”,是对习俗性情的批评,而非排斥其他学说。“乡愿”与佛教作为不同性质的事物,不能在同一层面上进行概念的替换。“至孟子始辟杨墨,辟许行,辟告子。后人指杨墨等为异端,孟子之书亦不目以异端。不知夫子所谓异端者果何等耶?”[2](卷二十四,P288)孟子时代有排斥杨墨、许行、告子的言论,但孟子在观念中也没有将他们作为“异端”对待。陆氏针于此提出自己的疑问,但他旗帜鲜明地提出“异端”非特指佛教。
经过对“异端”所出现时代背景的思考,陆九渊进一步阐明他的辨解,对一种学说的排斥应当充分理解自家学说,进而才能分析何为“异端”。时人辟佛老容易“卤莽”,陆氏先从圣人所提出“异端”及其所排斥的行为入手,继而再从词意层面进行分析,“异字与同字为对,有同而后有异”,[2](卷十三,P177)“异与同对,虽同师尧舜,而所学之端绪与尧舜不同,即是异端,何止佛老哉?”[2](卷三十四,P402)“异端”是相对于有同端而言的。在这个逻辑思路下,只有同师于尧舜的学说才能有同异的分歧。佛教作为外来学说,不具备同的端绪,自然不能被指为异端。
在陆九渊的论著中有把老氏列为“异端”的论断。《智者术之原论》道:“孟子者,圣学之所由传也。故其言,发明圣人之智,而指当时所谓智者为凿。老氏者,得其一,不得其二,而圣学之异端也。”[2](卷三十,P350)此处陆氏又将老子学说作为“异端”,然而此处并不是违背之前所论述的“异端”的指向,他将孟子和老子的学术加以比对,此处孟子和老子都在圣学的同一框架下,陆氏认为老子端绪不与圣学同,故而才将其列为异端。
在被问及何为“异端”时,陆九渊直截了当地回答道:“子先理会得同底一端,则凡异此同的端绪,才能把不同于尧舜端绪的学说归为异端,陆氏对儒士排佛的盲目有所批评,那么他所认为的“理会”又是以何种“理”来领会呢?
二、以“理”辨析“异端”
陆氏在判别学说分歧时,采取审慎的态度,缜密的逻辑推理,在这个辨析过程中他始终遵循一个恒定的标准,即是“理”。那么象山所谓的“理”具体的内涵又是什么呢?
陆九渊思想的来源,自称是继承于孟子,因此他所提倡的理自然也是儒家思想中所认定的理的定义。“故曰,口之于味也,有同嗜焉;耳之于声也,有同听焉;目之于色也,有同美焉。至于心,独无所同然乎?心之所同然者何也?谓理也,义也。圣人先得我心之所同然耳。”[3]孟子此处将人类所共有的“口耳目心”作为感知外物的工具,以此领会“味声色理”,因此圣人与普通人的所得是一致的,原因就在于这个“理”,并将“理”上升到“义”,由外在感官的同引出内在“心”的同。象山心学核心的概念即是“本心”,它来源于《孟子》中,包含着“恻隐”“羞恶”“辞让”“是非”,是“仁义礼智”的四端,因此陆九渊此处的“理”便是传统儒家道德观。陆九渊就此处孟子的论说作为切入点,认为“此理所在,岂容不同。不同此理,则异端矣。”[2](卷十三,P177)对其他学说的批驳也一定应该在“理”的约束下。因此他提出:
“天下正理不容有二。若明此理,天地不能异此,鬼神不能异此,古圣贤不能异此。若不明此理,私有端绪,便是异端,何止佛老哉?世言穷理者亦不到佛老地位,若借佛老为说,亦是妄说。其言辟佛老者亦是妄说。今世却有一种天资忠厚、行事谨慤者,虽不谈学问,却可为朋友。惟是谈学而无师承,与师承之不正者,最为害道。”[2](卷十五,P194)
作为理学家的陆九渊,把万物是非的评定上升到哲学层面上,他认为“天下正理”是判别一切事物的至上标准,明晓此理便可以分辨一切学说的是非,值得一提的是,象山心学的这个“理”是绝对化的,不容有二的,因此“异端”问题走出门户之见,被放置在是否合乎道德观念之下。他批评穷理者不具备佛老学说水平,却借佛老学说妄自言说,就连排斥佛老的言论也是妄谈。另一方面,“理”正与否关系到道的益害,师承关系或学术源流是判断为学者的基本方向。
探寻“理”的具体所指,便只有回归到陆氏的心学主张,同异的争论对学说本身追寻的价值不大,只有以“理”相对比,才能探求这种差异。正所谓“尚同一说,最为浅陋。天下之理但当论是非,岂当论同异。”[2](卷十三,P177)这就自然产生“正理”与“邪说”的对立。有宋时代,儒学的回归,在对以往学术观点进行清理思考的同时,将儒家的正统地位又加以强化,理学家群体都有“辟佛”的言论,“长期以来,我们往往根据道学家‘辟佛’言论的表层涵义,断定道学(或理学)驳倒了佛教,中国思想的方向从此由出世转变为入世。这个看法似是而非,与历史事实不合”。[4](P75)道学家的立足点都是儒教,为争取学术正统自然排斥其他学说,因此陆氏的“理”带有鲜明儒家伦理道德的色彩。陆九渊虽然认为“异端”非特指佛老,但在“理”的框架下,他把佛老学说归为不正,“故某尝谓儒为大中,释为大偏。以释与其他百家论,则百家为不及,释为过之”。[2](卷二,P20)陆氏用诸子百家学说和释氏学说作比较,其立足点是儒家中庸思想,儒的“大中”,佛的“大偏”,是陆氏认识两家学术的基本观点。在对佛儒问题的追问中,他多次在辩解之后提出用“理”来考订两家学说的是非。陆氏的学说辨析中,潜藏着对佛教学术地位的承认,同时也反映出“理”的偏向。
三、佛教作为学术之一家
自佛教传入中土,其学说不断被继承改造,士大夫或从或否,争论不断,但对其学术地位的认同,却是其中考察的重点。对待一种学说的认识程度,反映出其人所立足的学术背景,从而能够解析其思想形成过程中思想观点的取舍。
宋代佛教的变化,与当时的人事制度有关。日籍学者高雄义坚于《宋代佛教史の研究》一书中《宋代寺院の主持制》讨论了十方主持制和甲乙徒弟制的应用情况[5]。十方制作为普遍决策机制,由官府决定正式继承者,使得士大夫阶层对佛教人事有相当大的影响力,因此佛教僧众自然产生向士大夫靠拢的趋势。“当宋室全盛及南,君相皆崇尚三宝,其时尊宿,多奉敕开堂,故有祝颂之祠,帝王之道,祖师之法,交相隆重。”[6]寺院的日常秩序与政治关系的结合,使得佛教学说内部产生新动向,吸引一大批士大夫走向佛教的阵营。
佛入中国,在扬子之后。其事与其书入中国始于汉,其道之行乎中国始于梁,至唐而盛。韩愈辟之甚力,而不能胜。王通则又浑三家之学,而无所讥贬。浮屠老氏之教,遂与儒学鼎列于天下。天下奔走而乡之者,尽在彼而不在此也。愚民以祸福归乡之者,则佛老等,以其道而收罗天下之英杰者,则又不在于老而在于佛。[2](卷二十四,P288)
陆氏阐述了佛教的大体发展脉络,佛儒相互争持,韩愈极力“辟佛”,但未能胜利,王通浑融三家,但是无所批判,使得佛教与儒学鼎列相争。佛教用祸福理念吸引一大批民众,不足论,然而“天下英杰”也被佛教拉拢过去。“至于士大夫之好佛者,虽其好佛,亦只为名而已!”[2](卷二,P19)士大夫阶层为了名声,趋向佛教学说,不是真正的向佛,但加重了佛儒学术间的争持。“北宋儒家实已无佛可辟,但佛教儒学化和沙门士大夫化毕竟也让禅宗的‘道德性命’普遍进入了儒家士大夫的识田之中,这才是道学家‘辟佛’的直接对象,然而已在儒门之内了。”[4](P105)对佛教的深入接受,使士大夫阶层的禅风日趋严重,这是理学家所批判的。针对学术的消长,陆氏有此论述:
“孟氏没,吾道不得其传。而老氏之学始于周末,盛于汉,追晋而哀矣。老氏衰而佛氏之学出焉。佛氏始于梁达磨,盛于唐,至今而衰矣。有大贤者出,吾道其兴矣夫。”[2](卷三十五,P473)
他认为佛教的兴起是由于本土学术的式微。孟子的道没有得到传承,致使老氏兴起。老氏衰微后佛教涌入,“至今而衰矣”显然是陆氏自己的一厢情愿。宋季儒学的复兴使得佛教显得沉寂,并不能掩盖佛教的盛行。陆九渊期盼大贤者能够振兴儒教,是其作为理学家的应有之义。学术的争辩,伴随佛儒两家,陆九渊平时少有论述,源于此问题的复杂和争论者的主观求胜心理:
“儒释之辨,某平时亦少所与论者:有相信者,或以语之,亦无所辨难,於我无益;有自立议论与我异者,又是多胜心所持,必欲己说之伸,不能公平求是,与之反覆,只成争辩,此又不可与论”[2](卷二,P19)
此番见解显然是陆九渊有此类佛儒辩论经验的亲身经历。在《与王顺伯》的信中他开篇阐明了自家观点。“大抵学术有说有实,儒者有儒者之说,老氏有老氏之说,释氏有释氏之说,天下之学术众矣,而大门则此三家也。昔之有是说者,本於有是实,后之求是实者,亦必由是说,故凡学者之欲求其实,则必先习其说。”[2](卷二,P16)陆氏把三家学术放置在“有说有实”的衡量标准之下,要想求实,必须习得学说,只在外部指责批评是毫无见地的。他同时认为“得与不得,说与实,与夫浅深、精粗、偏全、纯驳之间,而不知其为三家之所均有者,则亦非其至者矣。”[2](卷二,P16)作为一种学说自然存在内部的是非争论,三家学说都是如此。陆九渊站在三家学术的高度作出这样的论断,正是以“天下正理”来思考论争,同时给予三家学术同等的地位评价。
在评价佛教的学术地位上,他又以“理”来权度其学术的正邪。“问:‘作书攻王顺伯,也不是言释,也不是言儒,惟理是从否?’曰:‘然’。”[2](卷三十五,P447)不管是针对佛教还是儒教都是从“理”上进行权衡,因此他虽然认为佛教是三家学说之一,但就其性质而言,佛教教义不符合“理”。
“诸子百家,说的世人之病好,只是他立处未是。佛老亦然。”[2](卷三十五,P454)
“佛老高人一世,只是道偏,不是。”[2](卷三十五,P467)
陆氏认为佛教虽然能够劝化世人,立论足够高远,但所“立处”不在正理上,不具备对“仁义礼智”进行诠释的资格,自然无法与儒家相争持。“立处未是”、“道偏”是陆九渊对佛教的基本评价。
此处另一则师门问答:
“定夫举禅说:‘正人说邪说,邪说亦是正,邪人说正说,正说亦是邪。’先生曰:‘此邪说也。正则皆正,邪则皆邪,正人岂有邪说?邪人岂有正说?此儒释之分也。’”[2](卷十五,P460)
陆九渊认为学说“立处”所在,决定了学说的正邪,不因人而异。佛儒之分正邪,更需要加以从“立处”辨析,因此陆氏提出“公私义利”。
四、儒释“公私之辨”
程朱理学与心学皆有儒释之辨,朱熹提出自己的判别理论,“释氏虚,吾儒实;释氏二,吾儒一。”[7]陆九渊对此颇有微词,以致引起朱熹及其门人弟子们的回应,此处不容赘述。朱熹一派从虚实上判别儒释,注重儒家最后的归宿在于仁义礼智,批判释教所标举的空虚;陆氏心学一派注重儒家的人道,批判释教所追求的超脱轮回的最后境界。两派出发点不同,分歧自然产生,但所归皆在儒家的世俗人生价值观。
陆九渊在门庭传授中,特别重视儒释之辨。“凡欲为学,当先识义利公私之辨。今所学果为何事?人生天地间,为人当尽人道,学者所以为学,学为人而已,非有为也。”[2](卷三十五,P470)为学的目的在于为人,为人应该尽人道,“公私义利”之辨的目的在于使世人知晓为学的大旨,不至于误入歧途。
义利之辨是儒家特别关注的话题,孔子以此来分别小人、君子,孟子也同样有舍生取义之。陆九渊把这一命题放置在佛儒的判别中,立足于儒家传统的学说观念,解释新的佛儒关系。他批判世人认为佛儒相同的学说,提出自己的辩解:
“兄前两与家兄书,大概谓儒释同,其所以相比配者,盖所谓均有之者也。某尝以义利二字判儒释,又曰公私,其实即义利也。儒者以人生天地之间,灵于万物,贵于万物,与天地并而为三极。天有天道,地有地道,人有人道。人而不尽人道,不足与天地并。人有五官,官有其事,于是有是非得失,于是有教有学。其教之所以立者如此,故曰义、曰公。释氏以人生天地间,有生死,有轮回,有烦恼,以为甚苦,而求所以免之。其有得道明悟者,则知本无生死,本无轮回,本无烦恼。故其言曰‘生死事大。’如兄所谓菩萨发心者,亦只为此一大事。其教之所从立者如此,故曰利、曰私。”[2](卷二,P17)
陆氏以“义利”二字来判别佛儒,认为儒家注重人道,要求人有教有学,所立足之处是着眼于世俗个人价值的实现;他同时认为佛教以生死轮回为前提,主张超脱人世,出于一己之私欲,是为利的表现。他继而探讨两家学术的世俗观念,儒家基于尽人道,故而主张经世,佛教以未来、普度为旨归,故而舍弃人世。僧徒同样为人,其所谓的“本心”不应该泯灭。但佛教所追求的不是这些,最终还是回到私利的层面上。
陆九渊虽然对佛儒之异进行了辨析,其观点也有偏颇之处,在把佛教归为私利的态度上,不免牵强。但是,作为基于儒教道德观念的理学家,陆氏站在宏观学术背景下对佛儒进行判别考察,在宋际士大夫群体中颇独树一帜。
“吾儒之道乃天下之常道,岂是别有妙道谓之典常,谓之彝伦,盖天下之所共由,斯民之所日用,此道一而已矣,不可改头换面。前书固谓今之为释氏者,亦岂能尽舍吾道,特其不主于是,而其违顺得失,不足以为深造者之轻重耳。”[2](卷二,P20)
儒家之道是天下恒久之道,是唯一之道,不可被改变。陆氏强调儒家之道的地位,是道学兴起之后士大夫所普遍认同的,因此佛教僧徒也不能放弃仁义道德。换言之,佛教的存亡系于儒家治世的前提。
五、刘淳叟、陈正己“溺佛”案
前文从力辩“异端”、以“理”衡量佛教、佛教的学术地位上,系统阐述了陆九渊对待佛教的态度。此处以陆九渊门下弟子“溺佛”一事作为切入点,从具体事件中认识陆氏的态度。
刘纯叟、陈正己二人曾求学于陆九渊,在陆氏门下也是颇为自励:
“淳叟、正己初向学时,自厉之意蔚然可观,乡里子弟因之以感动兴起者甚众。曾未半途, 各有异志。淳叟归依佛乘,正己慕用才术,所托虽殊,其趣则一。此其为蔽,与前所谓以学自命者又大不侔矣。正己比来相与礼貌,然视其朋游,观其文辞,验之瞻视容色,以考其指归,未之有改,此尤可念也。”[2](卷九,P128)
乡里子弟为此二人的自励而感动,说明二人向学的热情甚为高涨。然而半途,刘淳叟皈依佛教,陈正己慕用才术,放弃儒教的学术,与陆九渊所要求的显然悖离。但是陆九渊依然没有对其口诛笔伐,在看到陈正己“朋游”“礼貌”“文辞”“瞻视容色”都合乎法度,说明他的“指归”未曾改变。同样是在孜孜求学,陆氏充分肯定刘、陈的为学心态和积极作为,但他又在另一面做出批评:
“虽然,诚使能大进其道,出得阴界,犹为常人之私利不细,政恐阴界亦未易出耳。如淳史、正己辈,恐时僧牢笼诱掖,来作渠法门外护耳。若著实理会,虽渠亦未必知其非,所敢望于公等也。与正己相处之久,不敢不直言。”[2](卷十二,P163)
佛教的私利性质仍为陆氏指摘。他认为刘淳叟、陈正己被佛教诱掖,没有对教义进行着实理会。即便是在佛教参禅之事上能有所进益,终究是带有私利性质。他期望门人弟子引以为戒,能够昌明儒学,不至于误入佛教的歧途。而另一则问答中刘淳叟以参佛者道出其中差异:
“淳叟参禅,其友周姓者问之曰‘淳叟何故舍吾儒之道而参禅?’淳雯答曰:‘譬之于手,释氏是把锄头,儒者是把斧头。所把虽不同,然却皆是这手。我而今只要就他明此手。’友答云:‘若如淳叟所言,我只就把斧头处明此手,不愿就他把锄头处明此手。’先生云:‘淳叟亦善喻,周亦可谓善对。’”[2](卷三十四,P408)
刘淳叟对佛儒两者譬喻,认为两者都是工具,只要“明此手”皆是为学路径。在陆九渊的评价中,他认同了佛儒两家的学术工具性。但就其立足处,他肯定周姓友人的回答,“把斧头处明此手”,即是在儒学处求道问学。
以上看来陆九渊对待门下弟子向佛参禅并未苛责声讨,只是在情理上予以劝勉,可见其人格之伟岸。在对待佛教的态度上,批评当时妄说者,要求在“理”的层面上对佛教做出判断,陆氏有以下论断:
“虽儒者好辟释氏,绝不与交谈,亦未为全是。假令其说邪妄,亦必能洞照底蕴,知其所蔽,然后可得而绝之。今于其说漫不知其涯挨,而徒以名斥之,固未为儒者之善,第不知其与楼楼乞怜于其门者其优劣又如何耶?”[2](卷十二,P163)
他完全不赞同儒者杜绝和佛教僧徒的来往,也不认同无根据攻讦释氏学说。陆氏本人同样与僧徒有所交游,在《赠僧允怀》中,他评价允怀上人:
“怀上人,学佛者也,尊其法教,崇其门庭,建藏之役,精诚勤苦,经营未几,骎骎乡乎有成,何其能哉使家之子弟,国之士大夫,举能如此,则父兄君上,可以不诏而仰成,岂不美乎?”[2](卷二十,P245)
他认为僧徒若能遵守法教,为世人做楷模,同样可以教化国家乡里风俗。另外陆九渊说道:“虽不曾看释藏经教,然而《楞严》、《圆觉》、《维摩》等经,则尝见之。”[2](卷二,P19)佛家的这些基本教义经书,他也是泛览的。在对待佛教态度上,他并未过于激进,只是在事理上偏向儒家。
总之,陆九渊在对待佛教的批判辨析中,申明己意,以宏大的学术背景为参照,承认佛教的学术地位,以“天下正理”将佛教归为偏道,体现了其担当道学重任的魄力,其立足点仍是儒家孔孟之道。陆九渊及其心学一派对待佛教保持明显的距离,不存在完全接受或肯定佛禅思想的可能性。另一方面,就其读释家经书和僧徒交游上看,或许在学说思维逻辑方式上对佛禅思想有所吸收。
[参考文献]
[1]祁润兴.陆九渊评传[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1998.
[2]陆九渊.陆九渊集[M].北京:中华书局,1980.
[3]焦循.孟子正义:卷二十二[M].北京:中华书局,1987.
[4]余英时.朱熹的历史世界:宋代士大夫政治文化的研究[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1.
[5]〔日〕高雄义坚.宋代佛教史の研究[M].京都:百华苑,1975.
[6]陈垣.清初僧诤记[M].北京:中华书局,1962.
[7]黎靖德.朱子语类:卷一百二十六[M].北京:中华书局,1986.
责任编辑:思动
[收稿日期]2014-12-28
[作者简介]韩兴波(1990-),男,山东聊城人,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中国古典文献学和唐宋文学研究。
[文章编号]1004—5856(2015)09—0076—06
[中图分类号]I206.21
[文献标识码]A
doi:10.3969/j.issn.1004-5856.2015.09.017
Criticism on Buddhism
——LU Jiuyuan’s Attitude Towards Buddhism
HAN Xing-bo
(Chongqing Normal University,Chongqing 401331,China)
Abstract:Lu Jiuyuan employed Confucian idea to examine paganism and believed that it was not specially for Buddhism. He proposed the “real truth” and thought that Buddhism was biased. Confucius and Buddhism are examined from the aspects of “public and private,justice and benefit”. The mistakes that Buddhism made on the mundane issues were pointed out while an objective attitude was expressed toward the incident that his disciples “drowning Buddha”. He hoped that they could return to Confucius.
Key words:LU Jiuyuan;Buddhism;the philosophy of the mi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