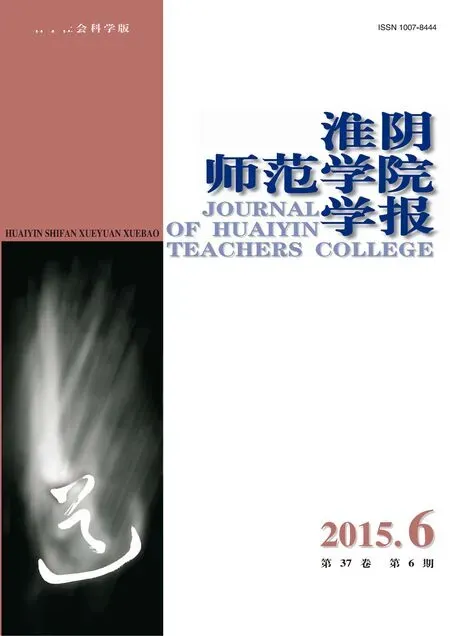论演出叙述中两种时间“空间化”方式
胡一伟
(四川大学 文学与新闻学院, 四川 成都 610064)
论演出叙述中两种时间“空间化”方式
胡一伟
(四川大学 文学与新闻学院, 四川 成都 610064)
叙述是人们感觉时间、整理时间经验的基本方式。不同叙述体裁,会用不同方式将时间性因素转化为某种空间性存在,即呈现出时间的“空间化”现象。当今,演出作为文化产业的核心体裁,有诸多构成时间“空间化”的方式。本文以演出叙述为研究对象,对其时间“空间化”方式进行讨论。由于演出的被叙述时间具有较为明显的空间性特征,所以本文主要就叙述行为时间的“空间化”方式展开论述。演出叙述中情节时间性展开的“空间化”,以及演出场面时间性展开的“空间化”,本文对这两类时间“空间化”方式进行具体分析。
叙述行为;时间;空间;结构情节;演出场面
叙述是一种具有时间表意性的文本,在不同条件的作用下,时间性可以被“空间化”。譬如,可以经由图像化处理(包括认知图式想象)形成空间性的存在,可由反复叙述构成空间性结构,或文本本身作为一种空间的存在,等等。演出作为当今文化产业的核心体裁之一,其时间的“空间化”方式更甚。表现在多个方面,如演出需要向观众展示,需要有空间承载演出;演员、道具、布景等演出因素本身就以空间化形态存在着;对时间的表现也需要借肢体动作等非特有媒介呈现出来。可以说,正在进行的演出本身就是一种空间式的描述。本文以演出叙述为研究对象,具体分析其时间“空间化”方式。需要说明的是,由于演出文本本身的空间性就十分明显(同时,演出的被叙述时间也具有较为明显的空间性特征),本论文对时间的讨论主要指叙述行为时间*“叙述时间”是个伞形概念,学界对“叙述时间”的研究多集中于被叙述时间、叙述行为时间、叙述文本内外时间间距等方面。可参见赵毅衡:《广义叙述学》,四川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145-147页。这一时间层面,而“空间化”则主要指抽象的空间性结构。其中,通过情节—时间逻辑上形成的空间结构,以及通过演出场面呈现出空间结构,属于两种较为典型的叙述行为时间“空间化”方式。故而,本论文将对演出叙述中情节时间性展开的空间化结构(简称为情节的“空间化”)以及演出场面时间性展开的空间结构(简称为演出场面的“空间化”)这两类时间“空间化”方式进行分析。
一、情节时间性展开的“空间化”
被叙述情节的时间性可以通过文本中的各种符号标明出来,也可以由情节的展开以及叙述节奏为人们所感知。常用的“空间化”方式有反复叙述(可造成“空间并置”)、嵌套叙述(可造成“空间套层”)、插入式叙述(可通过隔出空间促成“空间回环”)等,它们可以将线性的、连续式的时间性展开方式转向多层次的空间性结构。与演出场面“空间化”方式相比,情节时间性展开的“空间化”方式没有演出场面的空间结构效果明显——情节时间性展开的“空间化”不一定能在刚上演时就被接收者意识到,大多时候需要看完整场演出。更进一步地说,二者都是故事与形式的融合,但前者侧重于故事情节结构上的“空间化”(需要被理解后形成的空间结构感),而后者侧重于风格形式上的“空间化”(直接作用于感知渠道的空间存在),前者以不同时间下同一空间(同一场景或同一演出区域)的展示为典型,后者以同一时间下不同空间的展示(“共时态”)为典型。下面试举几类情节时间性展开的“空间化”方式,以进行具体分析。
通过插入式叙述手法(一般表现为隐身叙述者显身点评、话语或声音突然“飘入”舞台)隔出空间,串联空间,甚至造成空间回环。此类“空间化”方式十分常见,赖声川在其舞台剧《乱民全讲》*《全民乱讲》(2003年11月28日在台北国家戏剧院首演),由赖声川与丁乃筝合作编剧导演,该剧为赖声川“表演工作坊”二十周年前夕彻底自我颠覆的全新剧型,回归到赖声川早期在即兴创作之中引用的“天马行空”的随机原理。中就采用了插入式的手法。该剧用一些看似有联系,以及一些相互独立、毫无关联的情节或片段表现当时大多数台湾人所共同呈现的精神状态与焦虑处境,影射台湾社会的种种乱象。人们在台上的讨论、对话以及偶尔被插入进来的独白在结构上杂乱无章,使整个舞台呈现出一个支离破碎的空间格局。尽管对话的打断以及个人独白的混杂,是为了暗示现代都市居民生活的混乱与生存空间的变异。但让人感觉该叙述文本毫无章法可言,四分五裂的空间结构不易于向观众表达该剧的主题,使之成为一出有机的戏剧,引发观众对当下社会困境、人类精神状态的关注及其思考。对此,赖声川特意安排了一些角色穿插在散乱无章的片段之中,角色的穿插出场以及演出行为所传递出的意义与散乱片段所传递出的含义形成了鲜明对比,让碎片化的片段组成了有机整体。于善禄分析赖声川该剧的叙述手法时也就此提出了相关论述——该剧“偶尔在过场时让美声女子的清唱歌声,涤化戏里头那一波波的泛政治骚动,甚至到了戏的结尾,所有的演员或站或坐在舞台四处,一旦有人想开口再说些什么,都会被嘘噪,因为不需要再讲话舞台天幕同时也出现满天的繁星不要再吵了,只要聆听那美妙的歌声就好,在浩瀚的星空之下,所有的争辩与嘈杂都是多余的”[1]。可以说,穿插式的叙述手法(包括隐含叙述者通过评论显身)、片段里与片段外的鲜明对比(戏谑氛围)让情节在时间性展开时有了较为齐整的“空间化”结构。而该剧恰恰体现了插入式手法的多重功能:首先用个人独白、独语打断人们的对话、讨论,属于用插入式手法隔出空间的一类;其次是用特殊的角色功能穿插于散乱五章的片段之中,通过戏谑比照,将毫无关联的片段连接起来,也把破碎的空间串联了起来。侯淑仪将其归为赖声川早期即兴创作的一种随机原理,它“不预设结构和内容,把整个创作过程视为一种有机的探索和发现,最后才到达演出的形式和内容”[2]。实际上,随机插入、随时打断恰恰是演出体裁所特有的品格,此处所论主要是就文本本身(创作的过程)来看,未涉及观演现场的即兴插入与打断。
通过反复叙述造成的空间并置。对同一件事的反复叙述在戏剧演出中最为常见,它主要是由不同次叙述者对同一件事情的不同阐述构成情节结构上的空间并置。其中,较为典型的是由次叙述者叙述同一件事情。例如,在皮兰德娄《你是对的——如果你这样认为的话》(1917年)一剧中,次叙述者费罗拉太太、女婿彭查先生以及他的“妻子”对彭查先生的妻子的解释也是一种重复叙述。此外,还可以利用慢动作、音乐、乐章的特质将情节时间性“空间化”。音乐、慢动作本身就具有时间延展性,而重复的动作、乐章交响恰恰能够将延展着的时间带上“空间化”构造。诸多导演和编剧注意到了这类媒介的特殊属性,或将音乐贯穿于整场演出之中,或者按照乐章重新结构构架演出形式。由于赖声川的《变奏巴哈》*《变奏巴哈》是赖声川集体即兴创作的作品,台北国立艺术学院戏剧系于1985年6月11日在台北市立社教馆首演,此后搬演两场。2012年,其学生杨景翔在内陆搬演该剧,名为《变奏巴哈——末日再生》。在这两方面都有所表现,这里就以《变奏巴哈》为例进行具体分析。该演出贯穿了巴哈(J.S.Bach)的赋格曲(Fugue),即情节随着巴哈赋格曲的展开而展开,演员在时间性延展的音乐中即兴演出。在创作之前,赖声川为集体即兴设定了规则:演员分别躺在舞台上画好的24个格子中,随着音乐的响起,演员需要展开其动作。可以抓痒、可以转动,但都以缓慢的速度进行,同时还要保证与位于相邻格子里的演员动作不相一致,不管演员如何行动,每一格均有一人。大幕拉开,灯光渐亮,格子中的演员随着巴哈“十二平均律”第一首C大调前奏曲和赋格曲开始缓慢舒展开来,犹如同胚胎中的人慢慢起身,在格子中各自活动。此时,受演员片段化的语言、重复的机械化姿势(抽象移动的躯体)和反复音乐节奏的影响,情节时间性的展开被“空间化”了。更值得一提的是,《变奏巴哈》三幕均按照巴哈赋格曲的结构分为《第一乐章》《第二乐章》《第三乐章》,也就是说,故事的发生发展与乐章的节奏结构(呈示部——主题依次在各声部作最初的陈述;发展部——主题的进入比较自由,可随时变奏答题,进入此处也无规定性;再现部或结束部——主题在主调上进入,并与答题构成主调—属调—下属调的布局)相呼应,动作的反复、主旋律的一再重现(或正或反,一而再,再而三地强化主题)、每一场主题的重复等反复叙述的方式,让按时间性展开的情节呈现出了“空间化”结构。概言之,赖声川借用赋格曲种的音句性质——《主题》(Subject)、《答题》(Answer)、《对句》(Counter subject)来统合全剧的情节线索,巧妙地应用了赋格曲的乐理结构构架情节的空间结构,在丰富演出的空间结构时,呈现出舞台上的人生剧码犹如赋格中不断变形、无常又不可预测的主题。然而,巧用肢体动作、音乐等演示媒介来制造空间感(包括让故事情节显出其“空间化”结构)的方式还有多种,在哑剧、音乐剧中则更为明显。
通过嵌套叙述造成的空间套层,属于空间并置的一种变体。它与插入式叙述极为相似,但不同之处在于,嵌套叙述“插入”的是另一个故事而不是单纯的评论或乐音。嵌套叙述造成的空间套层现象在“戏中戏”中较为常见。在西方,“戏中戏”的历史最早可追溯到1497年亨利·麦德瓦尔的戏剧,直到文艺复兴时期,“戏中戏”成为普遍手法,莎士比亚的《仲夏夜之梦》《哈姆雷特》和卡尔德隆的《人生如梦》等剧均是人们所熟知的“戏中戏”。汤姆·斯托帕德(Tom Stoppard)就曾对《哈姆雷特》“戏中戏”舞台前后情节的一个完整补充,做了另一场“戏中戏”(或者说是对莎剧的改写)——《罗森克兰茨和吉尔德斯特恩已死》(简称“《罗》”)。该剧详尽叙述罗森和吉尔在宫廷路上与一群戏子的相遇,以及陪同哈姆雷特坐船赴英格兰的过程,并直接引用莎剧中与两人有关的片段(大多在舞台后半部演出区域上演),巧妙地嵌入自己的剧目。但《罗》剧与《哈姆雷特》一剧不同之处在于,《哈姆雷特》剧中两个小人物罗森和吉尔成了《罗》剧中的主角,而哈姆雷特则为戏中的配角,二者的命运发生了转变。其次,戏中之戏,或者说被嵌入的故事有所不同。该剧第一幕为国王召见罗森和吉尔,二人在遇到一群悲剧演员后,终于见到国王。第二幕则是二人再次遇到悲剧演员时,演员给他们上演了一出戏,而演出的戏实际上就是他们的命运。第三幕,二人陪同哈姆雷特前往英国,哈姆雷特将交给英国国王的信掉包后脱身,致使二人性命不保。这里,戏中嵌入的故事不同(悲剧演员的排练和演出),而且,《罗》剧还将《哈姆雷特》剧中的片段直接引入其中,再度形成一种包裹与嵌入的关系。也就是说,该剧所嵌入的片段或故事,使得情节的延展“立体”了起来,即情节时间被“空间化”了。而被嵌入的两个片段又形成了一种并置的关系,通过两段不同命运的比照,传递出人生之荒诞的意味。另外,该剧在演出之时,斯托帕在灯光转换、舞美设置、演员表演上有意区隔了叙述上层与下层,这也使得故事情节时间性展开的“空间化”与演出场面的“空间化”情况相重合。这在下文会具体论述。
实际上,反复叙述、插入式叙述还是嵌套叙述所造成的并置的、嵌入的空间结构情况,是相互关联的,可以达到同一效果。譬如,当插入叙述文本中的片段具有一定规律性——将另一个故事分成片段间隔插入同一叙述文本,打断原有叙述文本中的情节线性展开的方式,且该故事与原叙述文本所讲故事有因果逻辑关系等,可视为反复、插入式或嵌套叙述,而情节的空间结构既可看成是嵌入式的空间结构又可归于并置式的空间结构。以汤姆·斯托帕德的《阿卡狄亚》(写于1993年)为例。该戏共分两幕七场:第一场戏发生于1809年,第二场戏发生于当前,而第三场戏又回到1809年,情节就第一场戏继续发展……依此类推。1809年所发生的事件穿插在当前的故事中,形成有规律性的隔场跳跃。有意思的是,该剧依旧是在不同时间(1809年和当前),同一地点(英国德比郡乡间的一个贵族庄园)中上演,该剧第一幕第二场的舞台提示中写道:
本剧的剧情在十九世纪和当前之间来回转移,但始终在同一个房间内。两个时期必须共用室内的器物,无通常预料中的增减。这个房间予人的总体观感与两时期都不抵触。
也就是说,隔场插入的情节事件将空间隔开之余,又将隔开的片段串联了起来,而不同时间内故事所发生的地点相同这一特殊情境,又让隔开的片段构成了空间性的结构——并置或回环。我们均可通过隔场展开的两个故事获知:1809年4月,塞普蒂莫斯正在给13岁的女孩托马西娜上数学课,早慧的托马西娜已经预料到了热力学第二定律的意义。此时,三流诗人查特闯进来,指责塞普蒂莫斯曾经企图非礼查特夫人。180年之后的现在,克洛伊、瓦伦丁、格斯仍然住在这个庄园里,另外还有两位客人——园艺学家汉娜和学者伯纳德。其中,汉娜研究庄园的历史,想要确定谁是隐士,伯纳德想要证明诗人拜伦曾到过庄园并杀死了诗人查特。而瓦伦丁则在破解塞普蒂莫斯和托马西娜所思考的问题。当前的这些人物都努力想通过极其有限的线索去推断1809年在这里所发生的事情。可以说,斯托帕德试图将两条时间线平行展开,造成了情节结构的并置。而两条时间线交隔上演,打破了原有的时间线性,有相互嵌入之效。而对不同时间、同一个地点、同一件事情考证或寻求答案又有反复叙述之嫌。这样的设置使得该剧悬念意味步步增强,直到最后水落石出:拜伦的确到访过庄园,但不曾杀死查特,查特是在西印度群岛被猴子咬死的,托马西娜死于一场火灾,受刺激而变疯的塞普蒂莫斯从此在隐居室中耗时几十年奋力计算。
纵观上述情节时间性展开的“空间化”方式,空间性结构的隔出实与叙述层次有关。换言之,叙述区隔在叙述中的分层作用可以造成齐整的、并置的、嵌套的空间结构——它们在隔出多个空间之时,又将彼此隔开的空间相互勾连了起来,造成了叙述的上下层次关系,使得不同空间层次形成了嵌套、并置的空间形态。与形成演出场面的“空间化”结构情况不同的是,构架故事情节时间“空间化”情况中的区隔或不可见、或不易被察觉,多数没有演出中的明显,下面将具体展开而论。
二、演出场面的“空间化”
在演出中,对时间的表现需要以舞台空间的符号化为前提。如,演员迈了几步或转了个圈代表跑了许多路程。此类标明时间的空间符号有诸多类型,这里则主要就演出场次、场景时间性展开的“空间化”现象而论。需要明确的是,相较于演员的姿势动作等具象的、单一的空间符号,本论述所说的演出场面(包括片段、场景、场次)属于大局面文本的“空间化”方式;相较于情节时间性展开的“空间化”方式,演出场面时间性展开的“空间化”研究偏重于由演出风格形态造成的“空间化”结构——演出的形式不是内容的装饰,不是内容的容器,而是事物的本质[3],因此对演出风格形态的研究更显重要。这种“空间化”结构是人们可以直接通过媒介渠道呈现并感知出来的,但并不一定都与叙述的层次有关。演出场面的“空间化”同样可以以多重方式呈现出来,这里试举两类依次进行分析。
可以通过多种戏剧风格的同时呈现及故事所处的不同文化背景、不同年代的同时比照,将空间层次感突显出来,其中最明显的是将不同风格的剧目拼贴在一起。中国当代话剧导演林兆华的舞台剧《三姊妹·等待戈多》就是一例。该剧为了反映出两个不同时代的社会文化心理,表达人类的命运在于永恒等待、长久追寻的主旨,大胆地将契诃夫的《三姊妹》与贝克特的《等待戈多》这两部风格相去甚远的话剧作品拼贴在了一起。舞台上两种风格——一静一动,优美沉郁与荒诞怪异的呈现,不仅将演出的空间感突显了出来(使得舞台空间更为立体),还将两部西方经典剧作平行并置了起来,俨然一出结构谨严的二重奏。可以说,该剧演出场面(片段)的并置是消解了整个话剧的旋律性的,也即打断了时间性地向前推进的故事情节,促成了一种动静交错、回环往复的节奏形态。林兆华为增强演出的画面感(空间立体而充盈)而将两部西方经典剧作拼贴“并置”起来,为的是促使观众以更为理性的方式比照两部西方剧作背后的文化隐喻,领会二者互为指涉的思想内涵。而瑞士剧作家马克斯·弗里施(MaxFrisch)的《中国长城》则是将不同年代、不同文化背景的人物置于一个场面之中。该剧以公元前200年,秦始皇在顺利打退北方蛮族,并且命令举国上下修建万里长城之后,举办盛大的聚会为基调展开,通过不同国家、不同时代的人物,古代与现代场景的比照,讽刺那个用武力修筑长城、独裁专政的闹剧的时代。舞台一开场呈现的是两番场景——右侧是一段中国风格的露天台阶,左侧前方则是几张现代派风格的靠背椅。无疑,演出已将两个不同的时间场景并置在一起了。更有趣的是,光临这次宴会的人物又是从各种历史时段走来的:法国皇帝拿破仑、埃及艳后克娄巴特拉、美洲大陆的发现者哥伦布、文学人物唐璜、戏剧人物罗密欧和朱丽叶、腓特烈大帝、华伦斯坦,还包括一位现代人,也即,同一舞台上被隔出的左右两边,会频频发生人物“闪回”“穿越”的情状。譬如,在宴会开始之前,现代人就闯入了秦始皇之女美兰的闺阁之中,大谈两千年之后的未来社会(秦始皇所做的一切在二千年之后的世界里已经不可通行了,因为未来人类会处在一个氢弹或者原子弹时代,而独裁统治在现代社会是极其危险的,一旦成为暴君,就是整个人类的暴君,会使整个人类都同归于尽)。尽管现代人的言论引发了美兰的好奇,但在秦始皇这位强权专制者眼里却显得苍白无力(秦始皇对于现代人的说法不屑一顾,只把它当作一种雄辩术,并调笑地颁给他一个“孔夫子大奖”)。舞台上,古代与现代的场面拼贴并置,两个相去甚远的时间维度共生于一时,凸显出了场面的“空间化”结构,在展现一个从古代中国到20世纪西方的广阔的历史背景之时,表达了反战和反对独裁的意旨。
可以通过非特有媒介区隔出多重空间,以显出演出场面的空间结构、层次。最为直观和常见的方法是利用具象的物体将空间分割开来——将演出区域分为舞台前/后部,上/中/下,左/中/右部分,等等。譬如,利用楼房的特殊结构,向观众展示一栋楼的横切面,亦即多个楼层、多个家庭生活居住的空间;向观众展示某一层几户人家的横切面,亦即一个楼层,多个家庭私有以及公共的居住空间;向观众展示一户人家多个房间的横切面。又可以将演出区域设计为可移动形式,根据演出情况而移步换景,或将演出区域分为内环和外环层叠关系(如,赖声川的《十三角关系》等戏中就有对旋转舞台的运用)。除了利用实物道具进行特殊设置或隔断之外,由于叙述框架的作用——不仅能把身体和物件这些日常物品转换成演示媒介,还能将演出空间被“特用”的情况呈现出来[4],灯光、演员姿势这类塑形极强的媒介配合演出情境,也可形成演出场面的“空间化”结构。这在呈现人物心理、意识流方面较为典型。如用不同色调的灯光将人物的内心独白或意识流凸显出来,此时人物的追光与周围的灯光色调或者场景色彩基调出现了差异,演出场面的空间化结构显现了出来。此类效果时常需要与静场的方式相互配合,即有时舞台上没有其他人,或者其他在舞台上的人都不说话、静止不动,等等。以林兆华执导的《野人》中幺妹出嫁的一个场面为例。幺妹深爱生态学家,但被他拒绝之后,被迫嫁给他人。剧中幺妹出嫁的场面十分隆重,当媒婆和一群人抬着轿子载歌载舞、喜气洋洋地通向目的地时,所有的演员突然停了下来,止住不动,而唯有头上披着大红纱巾的幺妹从轿子里下来,缓缓地走向舞台中央。她慢慢地掀开红头巾,神情复杂地望着前方,随后又缓缓地披上红头巾,往人群走去。她一跨进轿子,作静止状的人群马上继续前面的歌舞动作,仿佛没有间断似的,吹吹打打,欢歌曼舞地涌向舞台深处。这一静一动将人物的心理空间“前推”了,大伙的喜庆场景与幺妹悲怨的心境恰恰形成了鲜明对比,赋予了演出场面“空间化”的结构。与此相类似的还有,在徐晓钟执导的《大雪地》一剧中,黄子牛与秀玲互相表达爱慕之心之后的场面——秀玲要用自己的棉帽子为黄子牛的手取暖,两人在音乐中夸张地扭捏推拉也采用了一静一动的效果。不过,导演对他们一瞬间发生的几个动作做了另一种特殊处理——“定格”,也即两人在推拉时,多次地停顿或静止了几秒。与此同时,舞台灯光与场景氛围也伴随人物动作的停顿而发生变化。这个演出场面的特殊设计在短暂的时间内将人物内心的情感、情绪呈现了出来。人物动作瞬间的静止、定格中断了人物外部环境以及事件、情节时间性地展开的进程,从而使该场面呈现出了一个被结构化的空间——人物心理空间被前推,而人物所处的环境、共享的事件等被后置。王晓鹰导演曾对定格与前推人物的心理空间所达到的效果做出了评论,认为它“中止了外部的现实时间的进程,而恰恰是因为外部时间的短暂停滞,使得他们相互间的姿态造型所显露的情感含义,特别是他们与此时的舞台灯光气氛一起变得格外明亮开朗的面部表情所显露的情感含义,鲜明而富于美感地向观众揭示了两人心中初次萌发的美好恋情给他们带来的内心欢乐”[5]。本文认为,上述定格、静场等方式也会造成“展面”与“刺点”*“Studium/Punctum”为巴尔特《明室》一书中不好理解的两个拉丁词,本文采用赵毅衡教授在《符号学原理与推演》一书中的翻译“展面与刺点”。赵毅衡:《符号学原理与推演》,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167页。之间的空间结构(场景环境的静止与人物的运动;人物的运动与动作的定格),而“刺点”的形成恰恰可为演出增色不少,有时会产生极为强烈的舞台效果。
除了通过静止与运动的状态凸显出场面的空间结构,慢动作与概述性动作、日常生活中常见的肢体动作的比照也能够形成场面的空间结构。赖声川的《变奏巴哈》中就有对慢动作的运用,徐晓钟所执导的几部作品(《培尔·金特》《桑树坪纪事》《大雪地》)还特别运用了转台来强化这种慢速的动作。以《大雪地》中“抓强奸犯”这出戏为例,大翠与大海半夜幽会被抓,来不及逃的大翠在情急之中谎称被人强奸。于是,保卫科干部便集合全体工人,让大翠当众指认“强奸犯”。当大翠迫于无奈而向大海走去时,其他工人消失了(静场)。舞台顿时静止了下来,唯有大海一人站在台口处,向大海走去的大翠因为转台的缘故(与大翠走去的方向相反)让大翠一直处于走动的状态。此刻,二人之间的距离被慢动作以及转台的作用拉远了。同时,也巧妙地将人物的心理状态呈现了出来——缓慢的步速说明大翠内心在犹豫,而越走越远的距离则意味着她深知这一举动将使得她永远走不到被她亲手毁掉的爱人身边。舞台上,全体工人寻常的肢体动作与表现大翠指认“强奸犯”犹疑不决的步速,大翠平日的肢体动作与表现内心越走越远的更缓慢的动作形成了比照,二者并置了起来,形成了结构化的空间场面。然而,对慢动作运用得最为极致的是将其意象化。罗伯特·威尔森(Robert Wilson)的意象式表演便是其中一类。这种表演剥去了人物的性格,演员只需要按导演的指令缓慢移动,形同傀儡。譬如,其代表作《沙滩上的爱因斯坦》(1976年)一剧,演员在舞台上的缓慢行动状态,营造出了一种梦境式幻觉感受,与日常生活琐碎的状态形成极强烈的反差效果。而正是因为人物性格的扁平化,人物行为的机械化,反反复复的慢动作恰好将舞台场面的空间结构化了(即由意象与意象的重复、同一符号的复现使空间仿若隔出了多个层次)。
实际上,通过不同戏剧风格的比照,故事中不同时段、情境的比照,以及非特有媒介隔出的多重空间让演出场面空间形态结构化的几例,均属于通过“共时态”下不同空间区域的相互比照而形成的空间结构化态势。只是它们结构化空间的方式不一样,即分别呈现出“前推”与“后置”、左右并置、上下分层等空间的排列组合情况。
小结:两种“空间化”方式的“重合”
诚然,前文分析的两种时间“空间化”方式均是对时间的空间结构化与展示场面的空间结构化现象的一种论述。因为情节的展开是具有时间延展性的(即时间与情节的关系紧密,任何叙述都离不开情节—时间,因果—道义的逻辑关系),对情节时间性展开的“空间化”方式进行研究也就是对时间的空间结构化方式进行研究。而由于演出本身就需要空间来呈现,因此对展示场面的研究着重于被结构化的空间现象。尽管一种是就时间谈空间结构(这类情况在传统戏剧中较为常见,如古典戏曲多按照一折一幕的线性时间进行叙述),另一种是就空间展开论空间结构(这类情况在现代戏剧中经常出现,如现代戏剧偏重于打破线性时间观,多线并进),但它们之间是相互联系着的——都存在时间性的展开以及空间的结构化。换言之,它们可以同时出现在一场演出中,两种方式所产生的效果也有其相同之处。下面试举几例:
两种方式共存于同一演出文本中,但产生的效果不同。以赖声川执导的舞台剧《暗恋桃花源》为例。该剧由《暗恋》(讲述在1948年,青年男女江滨柳和云之凡在上海因战乱相遇,也因战乱离散;之后两人不约而同逃到台湾,却彼此不知情,苦恋四十年后才得以相见的故事)与《桃花源》(讲述魏晋时期的武陵人老陶因为其妻春花与房东袁老板私通而离家出走桃花源;等他返回武陵时,春花已与袁老板成家生子的故事)两剧拼贴而成,即在同一个舞台上同时呈现了的暗恋故事和古代魏晋时期女子出轨的故事。该戏中特殊情境的设置——“暗恋”与“桃花源”两个不相干的剧组意外地在同一个剧场里相遇,由于演出迫在眉睫,无法更换彩排地点,两个剧组只能同时彩排,将两种不同风格类型(现代悲剧与古代戏剧)的戏剧拼贴在一起。该剧开演时,戏中两个剧组的排演时不时地被剧场工作人员以及对方剧组打断,这时古代戏曲的排演与现代戏剧的排演是相互交织的,形成了情节时间性延展的空间化结构。直到第十幕,在十万火急的情况下,两个剧组不得不共用一个舞台各自排演时,现代与古代两个类型风格不一的戏剧形态于同一个演出场面的对照,将场面空间结构化了。可以说,整出戏在纵向和横向上都存在空间结构化的现象——纵向的情节时间性展开的空间并置,横向上演出场面中的空间并置,而这一并置恰恰将爱情的各种状态(暗恋、离散、寻找、婚姻、出轨、重聚等)一同呈现了出来。同时也满足了台湾人民潜意识的某种愿望:“台湾实在太乱了,这出戏便是在混乱与干扰当中,钻出一个秩序来。让完全不和谐的东西放到一起,看久了,也就和谐了。”由此可见,戏剧的拼贴与空间的并置,能够让本不相关联的、破碎混乱的情节“和谐”地共生,在强烈的比照中,重新建构起其独有的时间秩序。
两种方式共存于同一演出文本中,但产生的效果重合,该类情况在前文所举的例子中已有涉及,这里先就《变奏巴哈》来论。赖声川的《变奏巴哈》中多处出现了反复重合的现象,如第一幕中,24个格子将舞台空间划分开来,演员在格子中站立、转向、前进、后退等机械化、缓慢的重复动作构架了演出场面的空间结构。而在第二幕、第三幕中,多名演员围绕一个主题的反复叙述也在无形中划分出了演出场面的空间结构。这三幕对人生无常、百无聊赖、难以掌握的主题的重复,又组成了情节时间的空间化结构。而几乎贯穿了全剧主旋律的“流水席”则更能体现时间的空间化结构与展示场面空间结构化的重合。剧中多重时间按照“流水席”依次在舞台上上演,人来人往,匆匆过客与主旋律相互呼应(如,第二幕中舞台不同方位多个破碎场景的同时呈现与正在进行的主旋律的呼应),使得时间与空间的机构化在同一幕中出现。当然,这是一类较为复杂的情况,体现了对多种媒介的巧妙使用。而在阿瑟·米勒执导的舞台剧《推销员之死》(1983年)中,也出现了两种“空间化”效果有所重合的情况。该剧采用双线并进的方式,将老推销员的意识流回忆以倒叙的方式间隔插入现在正在展示的故事中,演出场面中人物心理空间的“前推”(空间被结构化了)与不断间隔插入、不断重复以打断情节时间性延展的情况(时间被结构化了)同时出现,属于两种“空间化”方式重合的一种用法。
其实,对两种“空间化”方式在演出这一体裁中的运用及二者关系的讨论(重合与分离),也在某种程度上揭示出情节与场面时间性展开的关系。首先,情节与场面并非对等(它们的差异可以通过同一戏剧的剧本和演出文本比照出来)。情节由具有可述性的事件组成,而场面未必构成一个情节,它可以是事件、情节、故事发生的背景,也可以是某一情节片段等。当二者“重合”(尤其是在独幕剧中),两种“空间化”方式所达效果一致。其次,对演出场次或场面的划分并不一定以情节发生发展的原有逻辑为依据(现代戏剧时常会打破传统戏剧的时空观念)。因此,当场面与情节所展示的事件一致,或二者具有同一步调时,两种“空间化”方式可能会引发同一种效果。
需要注意的是,无论是受何种时间“空间化”方式的作用,并不意味着叙述时间的停止。也就是说,尽管原有的情节时间被打断了,但随着空间的结构化,新的时间也重新被建构了起来。另外,两种“空间化”方式之区别常会被有意地模糊(如置于不同文化空间中),以产生“陌生化”的效果。尤其当某些被试图取消戏剧时空以达到剧场时空和戏剧时空统一的演出来说,演员和观众共享同一个空间(可以是剧场时空也可以是叙述时空,因为二者合一了),却受不同文化空间的影响,则会使时间“空间化”方式更为复杂。
[1] 于善禄.后记:不需要再讲话[M]//赖声川.拼贴.台北:群声出版有限公司,2005:232.
[2] 侯淑仪.天马行空的随机原理[M]//赖声川.拼贴.台北:群声出版有限公司,2005:10.
[3] 赵毅衡.回到皮尔斯[J].符号与传媒(第9辑),2014.
[4] 埃罗·塔拉斯蒂.表演艺术符号学:一个建议[J].陆正兰,段练,译.符号与传媒(第5辑),2012.
[5] 王晓鹰.戏剧演出中的假定性[M].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1995:69.
责任编辑:刘海宁
J0-05
A
1007-8444(2015)06-0752-07
2015-08-20
2013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重大课题“当今中国文化现状与发展的符号学研究”(13&ZD123)。
胡一伟(1988-),博士,主要从事演出符号学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