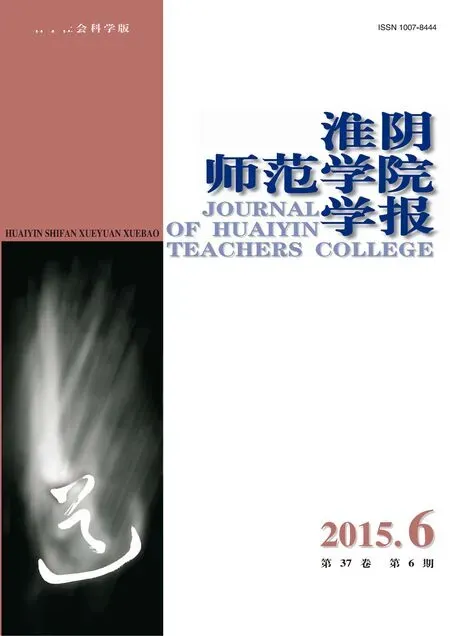“如何认识科学”(十二):科学的世界与感观的世界
——大卫·凯里对大卫·艾布拉姆的访谈
大卫·艾布拉姆, 大卫·凯里
“如何认识科学”(十二):科学的世界与感观的世界
——大卫·凯里对大卫·艾布拉姆的访谈
大卫·艾布拉姆, 大卫·凯里
大卫·艾布拉姆认为,我们都生长在一种深深地决定和约束我们判断力的文化中。我们被一种非常深层次的科学理解所决定,并且这种决定的主要作用会使我们不相信我们的感觉。对于处于技术科学共同体中的公民来说,真实的世界并不是我们可以触摸和体验的;它是一个通过粒子物理学或射电天文学所揭示的世界。艾布拉姆相信,我们应该从对技术的着迷中摆脱出来并如实地回到感官世界中;真实的世界是我们可以触摸、感受、听到、闻到和看到的;科学只是它的抽象或图解,除非回到感觉的体验,否则我们无法了解科学。他认为,这种对感觉不信任的根源深深地根植于科学史中,它实质上定义了我们所称为的“科学革命”。艾布拉姆想要恢复科学的卓越并把它作为有能量的、有用的但仍然是第二位的知识形式放到它恰当的位置上,认为科学作为一种立场,有它的地位和益处。他反对这样的一种方式,在其中科学超越感觉经验并使我们疏远于自然的世界。他希望最终回到感觉世界的家中。
理解科学;科学的世界;感观的世界;科学立场
肯尼迪:我是保罗·肯尼迪,这是关于科学与感觉的《思想》栏目。
艾布拉姆:无论我们是科学家或逃避工作的人,无论我们是农民或物理学家,我们都生长在一种深深地决定和约束我们判断力的文化中。我认为,这种文化深深地决定着其所有成员,使我们不能真正注意到环绕在我们周围世界中的神秘莫测的奇迹,没有真正注意到世界事实上就在那儿。
肯尼迪:研究者有时会测试大众对科学的理解程度,其可以预见到的结果是令人悲哀的无知:有20%的人认为月亮是由鲜乳酪支撑的,有30%的认为一个电子比一个分子大,等等。但是,对大卫·艾布拉姆来说,这种明显不可靠的对细节的理解漏掉了关键点。他认为,我们被一种非常深层次的科学理解所决定,并且这种决定的主要作用会使我们不相信我们的感觉。他说,对于处于技术科学共同体中的公民,真实的世界并不是我们可以触摸和体验的,它是一个通过粒子物理学或射电天文学所揭示的世界。大卫·艾布拉姆是一名教师和作家,他的书《感观的魅力》,已被广泛地阅读并获得很多赞誉。他相信我们应该从对技术的着迷中摆脱出来并如实地回到感官世界中。今天,在《思想》栏目中,他把他的思想作为“如何认识科学”节目的内容奉献给我们。《思想》栏目的制作人是大卫·凯里。
凯里:在最近的一篇论文中,大卫·艾布拉姆回顾了20世纪70年代在美国纽约州的长岛,他作为一名热爱自然的孩子在成长中所经历的高中科学教育。他的科学教育始于这样的课堂,一位最敬业的物理学教师在课堂上宣称:他坐在其上的、表面坚硬的桌子是一种错觉,桌子事实上是由发射微小的旋转粒子的真空组成。此外,他还学了一门生物学,它完全是在一个不涉及学校周围鲜活世界的、像实验室一样的教室中进行的。在那个教室里,老师解释说,动物的行为在其各自物种的基因中是“程式化的”;教室里的红衣凤头鸟、画眉、乌鸦的鸣叫声过去一直让年轻的艾布拉姆着迷,而在教室里,它们“呆若木鸡”——如他所说的,它们实际上是用羽毛装饰的自动机,听命于编码指令的动物标本。大卫·艾布拉姆对这一常见的科学教育形式难以接受。对他而言,通过他的感官所展示的那个会唱歌的、会说话的世界,是非常重要的。当发现他的老师仅仅把世界看做一个空洞和机械的外观、一团从数学方程和高能量的仪器中发出的鬼火时,他犹如挨了一拳。
不过,他认为,他在学校里所学到的东西是特有的。在他的观念里,我们中的大多数人会假定,不管怎样,世界正如科学所揭示的,它在某种程度上要比我们体验到的世界更为真实;但对他而言,这样所获得的关于事物的知识是完全颠倒的。真实的世界是我们可以触摸、感受、听到、闻到和看到的。科学只是它的抽象或图解;除非回到感觉的体验,否则我们无法了解科学。
大卫·艾布拉姆想要恢复科学的卓越并把它作为有能量的、有用的但仍然是第二位的知识形式放到它恰当的位置上。在今天的节目中,他要讲述现代科学的技术文明是如何在意识的土壤里失去其根基的,以及如何重新获得它。谈话来自新墨西哥圣达菲位于他家附近的一个无线电播音室。他告诉我一些他是如何理解如下观点的:通过我们的感官,我们在世界中和世界在我们中。他说,他的学习所采取的方式之一是,首先让他自己通过熟练手法魔术师职业学院的培训而成为一名职业魔术师。
艾布拉姆:伴随着这种手艺、魔术和熟练手艺魔术的实践,我变得对知觉和我们关于世界的一般感知体验非常感兴趣。知觉对于一个魔术师来说,实际上是媒介,就像颜料对于一个画家是媒介一样。魔术师的工作带有非常可塑的和相当神秘的元素,我们称为知觉、知觉的体验。不管是一个当代的熟练技法魔术师还是传统的魔术师、本土的巫师或江湖医生,还是用知觉自身的一些不固定的特性进行表演,魔术师是那些精通于改变或转变其团体中公认的、惯常的知觉体验的人,不管是为了同另一种智力状态(比如蜘蛛、狼或者鲸鱼)和睦相处与沟通,还是仅仅出于娱乐——当今社会魔术行为就是这样一些类似的事情,这是魔术行为深层含义的一种退化。于是,作为一名熟练手艺魔术师,从我的技艺的角度来看,感官体验,我们的眼睛、耳朵、皮肤如何感受并与周围的广大世界建立联系,以及它们如何带我们进入与我们赖以生存的鲜活世界之间的互惠,这些都深深地吸引着我。
凯里:对于大卫·艾布拉姆来说,以上述方式进入鲜活世界的事情之一是他在亚洲一年的经历,可以说,相对于过去的魔术师生涯,它是值得记录的。在这之前,他在美国的一些俱乐部和餐馆表演他的技艺,以他的方式作为一个街头魔术艺人在欧洲各国巡演;而且作为特立独行的精神病医生R.D.莱恩的费城协会的一部分,他在那里花了几个月的时间探索魔术在精神治疗法中的使用。然后,他决定去印度尼西亚和尼泊尔游历,在那里,他的才能让他融入那里的巫师或江湖医生及其文化中。这次经历对他的改变如此之大,以至于回家后他感到很震惊。
艾布拉姆:当我首次从传统的、本土的人群和团体中游历回来时,当我回到北美时,在我自己过去关于事物的感受体验中,它完全是一种歪曲,因为我不再能以过去的方式去感受我周围的具体活动、地面上事物的自身活动。在与传统魔术师生活期间,我发现,我的各种感官正在以某种方式被唤醒,而它们从我还是个孩子的时候起就从没在我自己拥有的文化中存在过;我成长在这样的一种文化中,它把感官的周围事物基本上解释为一组呆滞的、无生气的或至少是确定的客体和客观过程。我的感官变得迟钝了,我的眼睛呆滞了,我越来越生活在一组抽象概念之中。
但是,在与那些传统的人群特别是那些传统的、用宗教迷信的方式给人治病的人和江湖医生生活和交谈期间,我不得不学习这样一种说话方式,以便让每样事物自己主动行事、自己生存;并且,当我采用这种方式说话时,我自己的感官对我自己所处的状况变得更有意识。于是,我开始注意到围绕在我周围四面八方真实世界的惊艳。石头、小植物、狂风、一块地衣在鹅卵石上慢慢地伸展——每样事物都变得不可思议地迷人、奇妙、神奇,每样事物都以它们自己的方式展现,因为我现在正用一种体验的方式去听和看,听它们所在做的,不再把它们仅仅解释为呆滞的或无生气的过程。我正在感知到有一个他物在现实世界的每个要素方面呈现;并且,对我而言似乎是,对于他物的预期之一是,所有事物都有其自身的内在自发性,每一事物都有其自身的生活方式——这种说话方式就是一种与人的感官和人关于世界的直接感觉体验相一致的表达方式。它是这样的一种表达方式,保持人的感官的清醒以及对最接近的周围事物的意识。
凯里:大卫·艾布拉姆说,世界是鲜活的,而我们的感官作为我们定义的结果变得迟钝了。世界不能让我们感到惊奇,是因为我们生活在他称为的“一组抽象概念”之中。感官被更为普遍的计划和范畴压倒。而且他认为,这一趋势以许多方式被构建到当代的文化中。
艾布拉姆:无论我们是科学家或逃避工作的人,无论我们是农民或物理学家,我们都生长在这样的文化中,它深深地决定和约束我们的判断力在面对感官领域时进入特定的模式之中。我认为,这种文化深深地决定其所有成员,使我们不能真正注意到围绕在我们周围世界中神秘莫测的奇迹,不能真正注意到世界事实上就在那儿。我们以远离我们周围所有声音的方式来界定事物,认为鸟的声音和其他发声的动物不是真正的声音。确实,它们不说什么。它是程式化在它们基因中无意识的发声,好像其他有机体仅仅是自动机一样;并且,随着一些计算机程序的发展而给它们插入新的软件。这就是为什么它们会如此活动的原因。因此,在它们那里,没有什么神秘的东西迫使我们的耳朵去更为深入地听,没有什么事情要通过那些鸟说出来。于是,我们的耳朵对没有用语言说的事物变得有些失聪。我们的眼睛对不是人类的或人类发明的事物变得相当盲目,因为我们生长在一个共同的话语中,在其中,我们把我们之外的动物的自然界当作客观和客观过程一类的东西相当随意地加以谈论。在那里没有创造。一只乌鸦或蜘蛛的活动不是对在那一时刻围绕在它周围事物的一种创造性反应。所以,我们的眼睛变得呆滞了,我们有时变得盲目了。我认为这是我们今天的公共遗产。无论我们是否沉浸在这样的科学中,或者无论我们是否关注它们,它是我们时代共同话语的一部分,一种深深地影响我们看的方式和听的方式、甚至体会周围世界方式的说话方式。
凯里:大卫·艾布拉姆论述说,现代人的官能已陷入一种自满中。其他生命不对我们发言,因为我们事先已决定了它们没有什么令人惊奇的东西要说。这种预期起因于他所命名的“一种共同的话语和一种共同的遗产”。我们都持有这样的官能,不论我们是否精通科学。大卫·艾布拉姆说,不过,科学,在一个非常宽泛的意义上,是它的来源,因为正是科学,几个世纪以来一直告诉我们世界似乎不是我们的感官感知的样子。
艾布拉姆:我认为,我们时代科学的话语背景中的一个主要因素是这样的教育:我们不应该相信我们的感官。每一个孩子天生就有一种生机勃勃的感觉器官,想去参与到感觉的周围事物的每个方面。但是,很快,在初级中学和作为我们经历过的教育系统中,我们所学习和接纳的是,在所有的方面,明确的和不明确的,我们都不应该相信我们的感官:感官是迷惑人的,是骗人的。这正是当下被视为理所当然的事情。
凯里:从大卫·艾布拉姆的观点看,这种对感官不信任的根源深深地根植于科学史中。事实上,他认为,它实质上定义了我们所称为的“科学革命”。
艾布拉姆:科学革命的关键方面是这种从我们感官的知觉体验中的疏离和分离。伴随哥白尼革命的令人吃惊的披露,是地球在转动而不是太阳围绕地球在转动。太阳作为一种存在物,从我们对它直接的感觉体验看,它在我们面前弧形地飞过我们头顶上的天空,在傍晚的地平线之外落下,然后每天早上从东方的地面上爬出来并再一次弧形地飞过天空。这是我们关于太阳的永世的感觉体验;而我们突然接受一种新的说话和思考方式说,这不是真的,因此,你不应该相信你的感官。真理隐藏在感官的背后。这就是那些专家用他们可以使用的非常高能量的仪器(像当代的新望远镜一样)必定传递给我们的观念。如伽利略所说,世界的真理是用数学的语言书写的,我们的感官带给我的是一个关于世界如何运动的虚假故事。所以,科学革命带来了这种与我们感官的巨大疏离。雷内·笛卡尔关于身体与思考的理智之间区别的思想还没有被很好地承认;他从无意识的身体中切出思考的东西、从感觉的身体中分离出思考的智力,以便建立因事物的新形态所需要的本体论,在其中,我们完全不应该相信我们的感官,而应该真正地把我们自己交给对世界的理智研究,因为本体隐藏在感官的背后。
凯里:雷内·笛卡尔把事物与理智切开,从某种意义上说,是一种防御性的操作。它是为了理智免于受到身体和自然的欺骗。但是,这种把人类定位于自然之外和之上的企图,也有他认为的深刻的宗教根源。大众对科学革命的解释,时常强调宗教与哥白尼和伽利略新自然哲学之间的紧张。但是,大卫·艾布拉姆认为,在更深层的意义上,新科学是长期建立起来的基督教思想习惯的补充。
艾布拉姆:于是,我们许多伙伴和同事按照已代替了宗教的科学的方式说话;但是,对我而言,这似乎是非常错误的。在我们时代的世界中,太多现代的东西和特殊的科学话语是某种更为深刻宗教的一种继续,许多是基督教的,是关于人类与其余的自然保持距离的假说,也是自然世界堕落的特征。当然,虽然我们不再用“堕落的”“罪恶的”和“恶魔的”来谈论物质的自然,我们现在用“惰性的”“机械的”“确定的”以及在许多方面用“死的”来谈论它。但是,对我而言,它不过是同样的、更深宗教偏见的一种继续,只不过是被转化为一种新的、更为现代的术语。
凯里:按大卫·艾布拉姆的评价,现代科学本质上在延续着人类疏远自然和自然疏远上帝的宗教主题。从他的观点看,17世纪的新自然哲学还是在寻求一种与官方宗教明确的和解。他说,在文艺复兴期间,后来作为科学特征的实验的实践仍然与点金术的描述缠绕在一起。在1600年被罗马宗教法庭烧死在火刑柱上的焦尔达诺·布鲁诺是一个典型的人物。一方面,他是科学家的典型并且是哥白尼的追随者;但至少,按照我们今天的说法,他是个万物有灵论者,是因其“魔法和占卜行为”而被罗马法庭指控的。大卫·艾布拉姆认为,教会受到像布鲁诺一样的、相信一个活动的和无意识的自然人的威胁,但这容易使它与像一个无生命的钟表装置的自然图景之间达成和解。
艾布拉姆:科学的现代实践是在寻求一种新的术语,以便缓和教会的戒心和敌对,其机制——把世界比喻为一个巨大的机器——是这个时代形成的完美话语;并且它作为一种谈论方式,被许多科学的早期从业者抓住不放,以便进行他们的研究;然而,与此同时,它也隐含着:如果世界是一个大的机器,那么某些人一定能制造出这样的机器。其中仍然需要有一个根本上超越于物质世界的超凡源泉,如果你愿意,可以称之为“一个超凡的创造者”。于是,当这种机制变成现代科学的话语时,它发现自己与时代的宗教处于一种更为流畅和更容易相处的关系中,而不再处于一种难以相处和敌对的关系中。所以,我认为,为什么机械的话语席卷现代的东西并变成一种视之为当然的术语——它如此强大以至于现在大多数人甚至不承认它是一个比喻,以上所说的是一个关键性的理由。世界当然并非一部机器。它不是由外来的东西建造的。它似乎是出自宇宙自身的创生。这个宇宙处于一个持续的创造过程中,它就是自我创造。所以,我认为这是应该指明的。
凯里:根据大卫·艾布拉姆的观点,机械哲学与把上帝看做一个强有力的统治者和立法者的专制主义宗教是极为契合的。教会主张最终的实在只有通过它的仲裁才有效,而对于自然,科学制造了一个相同的论断。《圣经》告诉你如何进入天堂,正如伽利略所说的,科学告诉你天堂如何运转。
艾布拉姆:在这一意义上,对物质自然的机械描述与对作为从本质上超凡于感官世界的真正源泉中堕落的第二领域的自然传统的基督教理解之间有一种缄默的联盟。即使科学领域内的那些兄弟姐妹们公开把自己说成是无神论者,然而他们还是倾向于把围绕在他们周围的物质或者感觉的世界即我们直接体验的世界,看做从一个更为根本的领域中派生出来的第二位的衍生物,并认为我们所体验的世界几乎不如隐藏着的亚原子粒子、夸克、胶子和介子那样真实。然而,还有其他的研究者会说,“是这样的,但是,我们对事物的体验同样是由深陷于原子核中的偶发事件的展开而引起的,不只是原子,而是深陷于我们自己的原子核中、基因组中,以及不同DNA链的相互影响中,我们只有通过高性能的、昂贵的设备和仪器才能够接近这些”。所以,在他们那里以及许多其他方面,现代科学的话语仍然持续地告诉我们,不要相信我们的感官和我们对真实世界的直接感觉体验,而要去假定我们居住和体验的世界是通过隐藏在某个地方的某种规模的东西而被真实地解释的;并且,在许多方面,这是一个永恒的理论推测,物质的自然是自己通过参考一个完全隐藏起来的、在所有身体范围之外的超凡源泉而被解释的。
凯里:科学,在大卫·艾布拉姆所说的时代,是一种为建立自己的合理性而抗争的新哲学。进入20世纪,它的假定已经变成新的常识,它关于自然的观点达到这样的程度,正如大卫·艾布拉姆刚才说的,以至于人们甚至不再注意到机械论仅仅是一种隐喻。科学开始支配现代社会,并且正是这一支配导致一个哲学学派——现象学——的产生,该学派激发了大卫·艾布拉姆的许多灵感。该学派的创建人是一个生活在1850至1938年间说德语的哲学家埃德蒙·胡塞尔。
艾布拉姆:作为现象学的创建者,胡塞尔认识到,到20世纪早期,科学已变得如此彻底地疏离于我们直接的体验,以至于通过他们所从事的研究它们正威胁乃至毁掉这个世界,他们同样正在带领我们进一步地远离我们对事物感觉的体验。于是,胡塞尔着手发展一种哲学,为依据一种知觉科学而建立的另外一种科学充当基础;这种知觉科学是经验自身的一门科学,从它出发,其他更为抽象的科学可以开启它们自己,而无须在反对我们感觉经验中确立它们自己。所以,现象学对世界的研究是以我们经验它的方式进行的。先于反映的、先于数学和科学主体化的是,当我们只是注视这个直接的世界时,我们该怎么做?
凯里:埃德蒙·胡塞尔想要恢复对还没有被分析的头脑完全切掉和榨干的事物的经验。但是,按照大卫·艾布拉姆当年的观点,胡塞尔在某些重要方面依旧持有远离自然的人类观点。对于胡塞尔而言,感觉或意识对世界的自我呈现依然是外在的自然,是独立于身体的。在这个意义上,他依旧是个笛卡尔信徒。这就为他的学生、法国现象学家莫里斯·梅洛·庞蒂采取下一个步骤留下了余地。庞蒂论证说,身体不仅仅是知觉的居所,它还是知觉自身。
艾布拉姆:梅洛·庞蒂迈出了重要的一步而完全超出了笛卡尔主义。他说,胡塞尔提及的、正在经验的知觉,这一赤裸裸的意识,不是别的,正是身体自身;这一身体是经验的主体,一个正在经验的存在。这是迈出的极为重要的一步。在某种意义上说,梅洛·庞蒂不得不发展、创造一种全新的说话方式,以便开始走出我们同时代话语中的笛卡尔哲学的偏见,去打开另一种说话方式,这种方式不再继续把我们拉扯出感官、运出我们的身体。
凯里:谈到梅洛·庞蒂,我们就来到了大卫·艾布拉姆在他自己的著作中已经开始从事并向前推进的事业。梅洛·庞蒂克服了笛卡尔哲学中的理智与身体的分离并重新在自然中安置理智。他说,我们的思想是世界的思想,我们的身体是世界的身体。如果我认为天空是蓝的,那么——举大卫·艾布拉姆著作中的一个例子——天空通过我而同样地认为自己是蓝的;如果我谈论世界,那么世界也谈论我。在大卫·艾布拉姆的观点中,甚至一而再再而三地被看做人类独一无二的王冠和标志的语言,也不是我们专门拥有的,也属于我们给予其声音的世界。这是大卫·艾布拉姆对梅洛·庞蒂的思想特别加以拓展和丰富的一个方面。
艾布拉姆:梅洛·庞蒂现象学的核心发现之一是承认,对于感觉和有感觉力的人类动物而言,在某种意义上,它不仅仅是有生命的和活着的每一个事物,而且每一事物所发出的任何声响都可能是一种声音,任何活动都可能是一个姿势,一个有意义的表达;这种表现就是世界自身的一种性能。我周围的每一件事物至少具备有意义表达的能力。甚至在天花板高处上的荧光灯发出的嗡嗡声也是一种声音,因为在它自身的声响中有一种意义出现。它必定不是一种口才好的意思,而是把轿车轮胎发出的特殊声音视为轮胎在雨夜里呼啸地通过潮湿街道的意思。这是一种影响我们身体的听力器官的声音;它使我们滑入某种情绪,就像鸟的歌声影响我们的情绪或者影响我们思想状态一样,这些声音影响我们,而我们做出反应。并且,在某种意义上,我们自己人类的语言都产生于一种呼叫并用我们习惯的发声表达形式做出的反应。这是相当清楚的,比如,我们固有的祖先、我们狩猎和采集的祖先,是极为依赖他们参与听、学习、甚至模仿其他动物声音的能力的。为了接近那些动物,一个人有时不得不制造非常像那些你想足够接近去杀死的松鸡的声音或者野兽的喊叫的表达方式。当然,这是在我们有像枪一样的东西之前。如果你想猎取它作为晚餐,你不得不尽可能地接近其他生物。对于我们拥有巨大延伸性的现代人,我们与那些我们至少依靠其生存的其他生物之间,处于一种非常紧密的、亲密而注重协调的关系中。并且,我们自己的语言似乎深深地被那些其他生物的呼叫和喊叫声所表达,就像通过鸟的歌声甚至柳树林中的风声所表达一样;因为这也似乎是声音的一种,每一存在有它自己的雄辩,而我们的讲话方式仅仅是我们非常广泛交往的一部分。
凯里:那么,对科学语言学持有“我们的语言基本上是专制的规范”的观点,我们能说些什么呢?
艾布拉姆:当然,如果你继续把语言看做一种人类特有的性能,那么你必须做的是如何思考语言。你不得不从我们的声音中分出所有的感觉意义并真正聚焦在作为一种代码的语言的感觉上,其中每一术语相当武断地代表一种拥有特殊意义的符号。但是,语言当然不是严格的一种符号,我们的所有术语都带一种在其中我们永远无法完全砍掉的诗意的共鸣。我最近思考了一个简单的例子,它是关于我们的语词“雷声”(thunder)和“闪电”(lightning)——我们的、代表在我们听到雷声之前划破天空的、锯齿状的、闪烁的光的词语;而有震动的声音,我们称之为“雷声”。假使一个人试图颠倒这两个词语的使用并把雷声说成“闪电”,结果会怎样?声音与意义之间的关系恐怕是武断的,如果我们称锯齿状的闪烁的光为“雷声”并称低沉的、轰隆隆的声音为“闪电”,那么,显然这不会为人们所持有。你可以在你的群体中尝试并实践几天或几周,但是它自己很快会再一次颠倒过来,因为重复“雷声”声音这个词有某些不在任何直接地、明显地和单纯地模仿习惯中而感到的合适。当然,比起把雷声说成“闪电”的说法,不倒置的说法感觉上更为合适。所以,我们过去常常用来谈论的、当一条河流冲刷过它的堤岸而发出的声响的词语,像“冲刷”(wash)或者“飞溅”(spalash)、“涌出”(gush)等词语,这并不是偶然的;因为那些词语都拥有“sh”的声音正是河流翻转过岩石河水发出的声音。所以,我们人类的语言是由除了那些我们自己拥有之外的许多其他种类的语音和声音构成的。于是,当我们阻断所有的河流并越来越明确地控制剩下的森林时,当由于它们的湿地和在赤道适于它们过冬的地域被毁而使得周围的鸟鸣越来越少时,由此当然可以推断,我们自己人类的语言越来越多地失去它们的意义,因为它们不再通过那些被阻断河流的飞溅水声或鸣鸟和鹪鹩的韵律所形成并被影响。
凯里:大卫·艾布拉姆说,如果我们对周围事物保持缄默或者用机械制造的声音取代语言,那么语言将萎缩。并且他认为,越来越多地与他同时代的人的确生活在一种技术的围场或是技术科学的第二世界中。科学的抽象代替了经验,数字技术把我们设计进埃布拉姆所称为的“无身体的空间”中。他的回应是不断地提醒人们,在科学和技术二者的下面,在人类有机体和它的世界之间,仍然有他称为的一个“更为根本的相互作用”。
艾布拉姆:今天,我们被一种技术的蚕蛹所包围,并且似乎时常找不到直接通向更为人性的生活领域的入口。似乎每一样事物都是人造物。在这间屋里,我所能注视的每一样事物似乎都是我们同类的精致发明——直至我近距离看到的、我自己坐在这儿意识到和呼吸到的空气;而在我和麦克风之间流动的空气中,含有由所有这个录音室周围绿色的和生长的事物、室外的草地和树木一直在呼出的氧气。我正在吸入它们呼出的,而我吸出的是它们吸入的。我坐在这儿依然受到引力的影响。维持我的身体在地球上的引力,依然是一个巨大的和陌生的神秘之物,如同它曾经是的那样。在科学革命的开端,引力对于我们的兄弟姐妹们来说是一个可怕的神秘之物。但是,一旦它开始被说成是一个定律、引力定律,一旦我们把它当作一个定律来谈论,那么,我们就不再注意它;因为它是机械地发生的,所以在那里没有什么真正神秘的东西。但是,神秘是什么呢?即使在今天我们还是把它解释为有一定距离的物体之间的相互吸引,就像我知道的关于性欲的一个恰当解释一样,我的身体对地球身体的吸引和地球的肉体对我肉体的吸引。我每一时刻都处于与地球的一种性爱之中,如同我把一块石头抛到空中一样,它就会正确地找到回到与之有联系的地面的路线。如果我们承认引力是性欲,那么我们的体验又会有什么不同呢。所以,这对我来说似乎是,只要稍微注意一下,就像小心地专注我所说的那样,我们就可以开始注意到并再一次使之明显的是,在我们的有机体与一个既不是我们创造也不是我们发明却创造了我们的巨大世界之间,有着多么狂热和令人吃惊的相互作用和互惠啊!
凯里:对于大卫·艾布拉姆而言,属于世界的我们、我们与它的互惠,是所有我们被制造出来的科学和技术的基础;并且它也是道德的基础。在最近一篇叫做“日蚀中的地球”的论文中,他对几年前发生在克罗拉州的科隆比纳中学的群体杀戮事件,有一段相当令人恐惧的描述。在该段描述中,他引用了一个他一生的朋友——作为其中之一的杀手——告诉一个记者的话,我在这里加以引用:“他们所做的不是因为愤怒和仇恨,而是他们生活在那样的时刻,就像他们在一个视频游戏中一样。”埃布拉姆继续思索到,也许这两个年轻人花费超乎寻常数量的时间在虚拟的空间中,以至于失去了与既不是他们也不是被他们杀害的人们之间的整个真实存在的同情心的整体联系。大卫·艾布拉姆说,因为我们的同情心来自身体和地球的身体。
艾布拉姆:伦理学首要的不是我们从书本或老师那里学到的一套规则和原理,它首先是我们内心深处的一种知觉。在这个意义上,伦理学是在这个世界中的一种感动能力,这种能力无须对其他主体以其自身方式呈现的感动能力给予不必要的违背。这是一个如何给予其他生物空间、如何在某些情况中约束我自己激昂的言行和愤怒以免妨碍另外一个正处于激昂言行中的人的问题。伦理学如同如何不做冒犯的事一样,它对于我来说似乎首先是我们把它作为身体的存在而加以学习的东西。在某种程度上,我们今天生活在一个通过技术来调节的世界中,它切断了我们与我们的感觉之间的联系,并使我们生活在一个抽象的领域,几乎遗忘了我们身体的感觉和在我们周围感觉到的地球。我认为要合乎伦理是极为困难的。我们很难知道什么是与其他(包括其他人和我们世界的其他形状和形式的事物)处于正确的关系中的生活。对于关心环境的积极分子而言,像我自己,要调动人们为另一个将要被砍伐光的森林、另一个将要被铺路和发展的湿地或者甚至反对目前全球气候变化而采取行动,也是相当困难的;因为人们感觉不到与他们居住的地球世界的任何真正深刻的密切关系。身体是我们接近这个世界的基本通道;并且在某种程度上,我们过着如此空洞的生活,我们也把关于事物的最深处的真理投入到完全超然于感觉的某一维度的世界中,无论它是隐藏在繁星背后的天堂,还是隐藏在原子核中的亚原子世界,我仍然没有利用我全部的智力真正生活在这个世界中、真正参与到这个世界中。所以,当我听到其他物种以空前的速度在走向灭绝或者甚至气候在急速地变化时,我没有感觉到与这个世界的任何深厚的密切关系。这很有趣,但它对我没有深刻的影响,因为这不是我真正的家。我的更为真实的、更为真切的家,在另外某个地方。
凯里:这一真实的“生活在别处”的感觉是由部分的科学世界观引起的,正如大卫·艾布拉姆在今天的节目中几次强调的。但是,这个问题对于他而言,不在科学本身。他认为,科学作为一种立场,有它的地位和益处。他只是反对这样的一种方式,在其中,科学超越感觉经验并使我们疏远于自然的世界。而最终他所希望的就是回到感觉世界的家中。
艾布拉姆:我绝不是毁谤科学或者技术,我试图论证的是,有一个世界,一个经验的领域,一个我们需要作为我们真实的家、作为人类生活、经验和联系的基本范围加以开拓的领域。并且,这是我们直接肉体的、感觉的、经验的世界,共同体的世界;不是那些在线对话的人,而是那些亲身经历的、在我自己周围面对面会面的人。我想赋予述说同样事物的另一种方式或者感性地述说同样事物的方式一种首要地位,并开始对赋予这种首要地位的那种叙述方式进行实践。这不是说,我们不应该同样地关注在星球的另一边所发生的事情,或我们不应该与互联网打交道;而是说,我们应该认识到,有这样的一个领域,它是土壤、是土地,在其中,所有其他的、更为抽象的各种大小的事物依然根源于其上并仍然默默地或秘密地从中吸取营养。
(淮阴师范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王荣江译,标题、摘要和关键词为译者所加。)
责任编辑:王荣江
N0
A
1007-8444(2015)06-0725-07
2015-08-25
2013年度江苏省社科基金项目(13ZXB003)。
大卫·艾布拉姆((David Abram),魔术师,独立学者,新墨西哥圣达菲“野生伦理学联盟”创办者,《感观的魅力》(ThespelloftheSensuous)一书的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