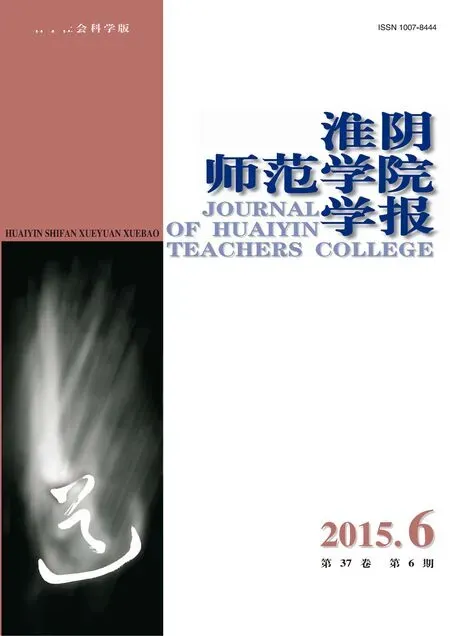“如何认识科学”(十一):科学与常识
——大卫·凯里对萨耶·塞缪尔的访谈
萨耶·塞缪尔, 大卫·凯里
【科学哲学·如何认识科学】
“如何认识科学”(十一):科学与常识
——大卫·凯里对萨耶·塞缪尔的访谈
萨耶·塞缪尔, 大卫·凯里
萨耶·塞缪尔试图复兴一种对科学服从常识判断的理性说明。他认为,我们理解世界是通过我们的感官,感官也是我们维系于所予世界的方式;并且,只有承认我们拥有共享周围世界的天性,我们才能够发现我们的本性。常识是连接世界与我的心灵之间的通道。我们的思想,无论怎样抽象,总是建立在我们感觉经验的基础上的。科学在知识和经验之间造成了一种破裂。科学知识是创造性的、建构性的、有意而为之的,这些属性使得科学知识完全不像人们以前所依靠的常识并取代了常识。科学认识变成理性和所有恰当知识范式的象征。在塞缪尔看来,政治应该是每个公民都可以理解和体验的东西,否则,如果只有专家有资格发表观点,那么普通公民就被剥夺了运用判断力的任何机会。我们急需一种所有公民都能参与“什么对于我们是好的”问题讨论的语言。萨耶·塞缪尔想要挑战科学对理性的垄断,恢复常识的尊严并限制科学的应用。
科学;垄断;常识;公民;语言
肯尼迪:我是保罗·肯尼迪,这是《思想》栏目中的“如何认识科学”节目。
塞缪尔:我们理解世界是通过我们的感官。感官也是我们维系于所予世界的方式;并且,只有承认我们拥有共享周围世界的天性,我们才能够发现我们的本性。所以,除非我们保持与世界的联系,就是说,将我们的手指插进泥土,否则我们将永远误解我们的本性。常识是连接世界与我的心灵之间的通道。
肯尼迪:1543年,尼古拉·哥白尼出版了《天体运行论》一书,该书将地球从宇宙的中心移开。90年过后,伽利略在《关于两个世界体系的对话》一书中,赞扬了他的前辈哥白尼的成就。他说:哥白尼使“理性战胜了感觉”;如果我们要理解事物的真实本质,科学要求我们必须拒绝我们感官的证据。这在今天已经是一种老生常谈了。真理隐藏在事物外观的后面或下面。根据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教授塞缪尔的观点,这一感觉的丢失有致命的后果。他说,没有常识,科学就会蒙蔽我们全部的眼界,使我们在科学之外没有立足之地,使我们失去用以判断科学应该产出什么问题的根基。今天,在《思想》栏目中,作为我们系列节目“如何认识科学”的继续,他与我们分享他在科学与感觉问题上的反思。该系列节目由大卫·凯里主持。
凯里:塞缪尔有关科学与常识方面的研究工作,开始于他与已故伊凡·伊里奇(Ivan Illich)之间持续多年的一个对话。伊里奇是有关专业人员和专家权力的一个批评者。在诸如《反学校教育的社会》(DeschoolingSeciety) 和《医学的报应》(MedicalNemesis)这些书中,他挑战这样的思想:生活在现代社会中的人,不可避免地必须服从于那些声称拥有科学知识的人。塞缪尔遇到伊里奇几乎是在20年前的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他从他出生国印度到那里去做商业管理方面的毕业论文。伊里奇的教学给他深刻印象;他们建立了友谊,然后是接下来的一个紧密的智力上的合作。伊里奇2002年去世后,塞缪尔继续他们一起从事的工作。他特别聚焦于科学判断是如何被判定的问题。他想知道,有一种人们可以对借以证明专家规则是正确的科学知识进行质询的常识吗?
通过我们俩多年共同的朋友伊凡·伊里奇,塞缪尔和我认识多年。2006年的夏天,在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他家的藏书室里,我支起麦克风,邀请他与我谈论关于科学与常识的问题。他通过描述他一直在从事的探究活动的一般概要开始他的谈话。
塞缪尔:我开始好奇于我所探寻的科学或科学知识与常识之间的区别,是否允许我在不至于陷入一种新世纪的浪漫主义、一种情感主义和非理性主义的情况下谈及科学知识的界限。我好奇于以某种历史主义方式研究科学知识与常识之间的区别(如果有的话),是否允许我对科学给予某种合理的批评——科学伴随着理性呈现自身——并因此让科学之外的理性没有存在的空间。如果如人们所说的那样,科学是理性的和科学是知识,那么,对科学的唯一批评就只能是非理性的;并且,如果你拒绝批评科学或者你不能批评科学,那么,你只能得到客观化的科学知识,因为科学知识——如果你愿意的话,你可以说,从我们的中学课本中知道它——是一种根植于数学中的知识。但是,我们的直觉、我们所有的直觉告诉我,我们是不可能将它们全部写入某个公式中或某一理论中的。所以,人们开始发现这样的悖论:如果我把科学理由当作所有的理由,那么,这就意味着,我的鼻子撞上墙是必然的,因为我把自己当成一个物理定理中的人。我知道,情况并不是这样的。
凯里:在塞缪尔的观点中,科学在知识和经验之间造成了一种破裂。他说,当我撞到墙时,我把自己看做一个有感觉的主体;但是,科学把我看做一个客体、一个理论,并且科学声称它是理性自身的皇冠。浪漫主义对科学的回应一直是拒斥理性并重新主张经验的首要地位。塞缪尔采取了不同的行动方针。他试图拓展理性,并且这导致他去探求在现代科学发明之前人们理解事物的方式。他的一些优先发现之一是,以前的常识有一个完全不同于今天的含义。
塞缪尔:常识,自亚里士多德那里就存在的以及之后2000年中所具有的含义,不是指每个人试图知道的内在能力,而差不多是指人类认知的一种哲学维度。常识是综合由你的五种感官获得的分散感觉并把你看到的、听到的、闻到的和触摸到的融合成一致整体的能力。简捷地说,如果我给出一点漫画式描述的话,那么,根据亚里士多德和亚里士多德主义的观点,当我看一扇门时,门散发出它的特性。眼睛看过去并抓住它所能抓住的——每种感官只能抓住适合于它的东西——于是,比如,它捕获了门的颜色。但是,这还不是整个门的全部,它只是门的颜色。对于门而言,还有更多的东西:大小、形状、当你击打它时它发出的声音,等等。所以,我们怎样做才能获得门的一致图像呢?不同的感官获取门的不同方面的特征,这些特征在常识中被综合,于是,常识允许我们产生一个关于那扇门的判断。“sensus communis”(常识的拉丁语)或者按亚里士多德的方式理解的“常识”中的关键点,是一种对被理解了的事物允许做出判断的能力或者通过感官理解世界的能力。这样的话,所有的思想,都是对这种领会世界的原型的一种反映。它是不能被砍掉而与世界分离的;它是不能与世界分开而出现的。通过常识的综合活动,你的思想、无论到最后你有什么样的思想,都是根植于常识这一世界中的。
凯里:亚里士多德写道,如果不首先在感觉中,就不可能在智力中。他的话成为中世纪的共同智慧。根据萨耶·塞缪尔的观点,其意思是指,我们的思想,无论怎样抽象,总是建立在我们感觉经验的基础上的。
塞缪尔:在笛卡尔之前,一个人不得不识别思想中思想的客观性,这种思想不是虚幻地由头脑或为了头脑而形成的,而是被理解为世界所固有的。我认为,对于像亚里士多德一样的某个人而言,情况不是这样的:正义是我们头脑虚构的事物。正义是世界的性质。比如,当我看见两个人共享或分割一块馅饼时,正义的思想就出现在我的面前。看到这一事实,就赋予我什么是正当的或合适的分割的基础知识。你还要更多的东西吗?我少了什么东西吗?这是清楚的,没有疑问。你是谁?你需要多少?这就是我们所发展或者显现的正义的思想。一个经典的例子是,当阿基里斯——当然这是在亚里士多德之前——想去分配从一次袭击中获得的战利品时,他让每个人围坐成一个圆圈,战利品被放在圆圈的中间。那么,现在,我们不得不进入如何分享这些战利品的思想——一个关于形成中的正义的实际例子。所以,在亚里士多德的传统中,常识让智力通过感官维系于世界。如果你愿意的话,你可以说常识是“塔桥”,它是世界与智力联姻的必经之路。
凯里:智力与感官之间的联姻终结于现代科学的发明。塞缪尔追溯一种类似于制造伽利略新看法原型的科学史家和科学家的长期传统。
塞缪尔:伽利略的科学以“自然之书是由数、重量和测量而被书写的”命题开始;这就是说,当你思考一朵玫瑰时,它不是红的。红的只是你看到的,红的只是事物的第二特征;真实的玫瑰是以几何学的方式被描述的。伽利略歪曲了你的感觉。事物的真实性质成了三角形、圆——数学的、几何学的形式。一个先在的形而上学承诺让他采取了他的步骤。他开始于“自然是数”这样的命题,而正是这一先在的形而上学承诺让他否认他所看到的是真实的存在。
凯里:萨耶·塞缪尔说,伽利略歪曲了感觉。我们看到的,似乎不是那里有什么,而是头脑建构了什么。伽利略的同时代人雷内·笛卡尔持有相同的观点。作为一个例子,萨耶·塞缪尔描述了笛卡尔的想象力理论。
塞缪尔:笛卡尔坚持认为有原子,即很小的球体。这些小球相互碰撞,它们旋转的速率——它们转动得如何快——形成一定的颜色,并且正是这种在移动中的事件允许你看。看是小球碰到你的眼睛、快速旋转、形成颜色的结果——当然这是一种漫画式的描述——如果你愿意这样说的话。这与前现代时期看一扇门的客体、可以说就是看从那扇门放射出它的形式、它的性质的说明是相反的。客体不是呆滞的,物体不是无生命的。门放射出它的形式,而眼睛看过去并抓住它们,这就是看的存在方式。那扇门不是我的想象力的虚构物;它实际地在那里,并且它放射出我能从感觉上理解的它的性质。而相反的情形是:那里没有门;它是一串分子和原子,微小的、相互碰撞的圆球,极为快速地旋转并形成我的关于一扇门的想象力。
凯里:对萨耶·塞缪尔来说,两种观点之间关键的不同在于,我们的思想是源自作为是其所是的事物,还是源于由我们加给事物的头脑?我们与我们的世界是同一性质(就像伽利略所说,我们能够看到太阳是因为我们的眼睛类似太阳)?抑或我们从没有内在意义的数据中建构独立的实在?
塞缪尔:心灵从世界中剪取思想。在过去的观点中,世界以某种形式、某种方式明白地呈现自身,你理解这一点;理智组建起关于世界的概念,并且这些概念是真实世界的观念。但是,如果你像伽利略所做的那样坚持认为,真实的世界不是你看到的、你的感官抓住的,而是相当于不受时间影响的三角形、圆和正方形的几何学的形式,那么,真正的世界就是你想象的样子。你在世界中从来没有看见过完美的正方形,那是某种你在你的头脑中虚构的东西,然后强加给世界的。理性以一种它好像是真的方式被对待。你在你的头脑中建构了一个正方形,然后你说,世界就像一个正方形或者是一个正方形,或者一束玫瑰可以用正方形、圆和三角形加以刻画。这一观念的翻转对我而言,似乎是个关键时刻。你离开反映头脑和世界之间一致的观念去“建构”——在你的思想之光中重铸世界。并且,这些思想被自由地创造,它脱离任何事物,类似于上帝一样创造。
凯里:塞缪尔说,数学的思想是头脑的自由创造。显然,这并不意味着,数学在世界上没有它的现实基础。数学的思想神秘地与宇宙相一致,它从古代就为人们所知。在17世纪,新的思想是,那些不受时间影响的形式可能被应用于鲜活的、永远变化的、尘世的自然世界。并且,塞缪尔认为,达到这样的思想要迈出勇敢的一步,因为在中世纪期间,数学的知识、特别是几何学,一直被认为是类似于上帝的东西。
塞缪尔:几何学、几何学的思想并非源自自然,而在相当程度上来自心灵。它们是无形的和不受时间影响的,是由心灵虚构的;并且它是心灵的、想象力的生产性行为,是形成那些被用来作为理解像上帝的创造力一类事情的形式的生产性行为。上帝可以从他自身之内的虚构进行创造,而他思想的产品就是创世之谜(the Creation);所以,存在跟随在他的思想之后。这就引出我的一个观点——虽然我对这一观点有些犹豫不决但仍认为它是正确的:像笛卡尔、伽利略、培根一类的人和其他一些人,都坚持世界的几何学性质,因为几何学的形式是通过人类心灵所虚构的,然而,如果把这种思路具体化到现实中,就允许人类在同样强烈的感官中与上帝一样勇于创新。如果你愿意的话,可以说它是一种模仿。我认为,如果你问这样的问题:“为什么这种形而上学转换发生了?”答案一定与这种过度地渴望根据理性制造真实有关系。想象力创造了数学的形式。我坚持认为,世界遵从那些数学形式的想象力,然后再创造世界以便我们去适应。并且,由于那些数学形式的位置隐藏在现象的下面,我必定迁怒于自然。我必须揭开它的秘密,这是做实验的姿态;我必须“筹划”世界以便解释在我的实验和通过我的实验所发明和发现的数学关系。我唯一能做的就是“筹划”世界以便使它适合于我的询问。
凯里:依照塞缪尔的观点,最初的科学家,模仿了他们的、作为发明创造的超智力者的上帝观念。就像上帝通过制造世界而认识世界一样,科学家通过重新制造自然而认识自然。为了理解这种通过实验获得新知识技法的性质,塞缪尔使用了“筹划”这一具有夸张意义的比喻说法。但是,他一直使用的几乎所有的术语——建构、发明、强加、虚构——都表明这种类似的看法:科学知识是我们制造的某种东西,而不是简单地给予我们的某种东西。不过,有人可能会问,这种科学知识难道不是真的吗?因为它明显地在起作用。如,我们数学的钥匙恰恰非常适合自然的锁,为什么我们要持续不断地对科学知识的人造性质喋喋不休呢?塞缪尔通过刻画他在科学史家皮特·蒂尔(Peter Dear)著作中发现的一个差别开始他的回答。
塞缪尔:蒂尔解释道,我们今天谈论科学,有两种方式。一种是告诉我们一些世界是其所是的知识部分;然而,我们也谈论作为一种改变世界、改进世界——疫苗、炸弹、小汽车——的手段的科学。所以,科学有一种使用其语言工具的外表和一种自然哲学的外表——自然科学,它们分别以研究世界运转的方式和研究世界是其所是的方式存在。当你问“为什么科学是真的?为什么某一理论是真的?”的时候,就是倾向于说,因为它起作用,因为飞机在飞,因为疫苗预防了疾病,因为原子弹……这些都作为科学是真的断言的证据而为人们所持有。如果科学是错的,如果由科学制造的真断言是错误的,那么,这种疫苗就不会起作用。如果你问“为什么这种疫苗起作用?”这样的问题,那么其答案是:因为科学是真的。所以,在这一证明中有一个循环论证:科学是真的,因为它起作用;它起作用因为科学是真的。蒂尔称它为一种意识形态。我认为,他这样称呼科学,部分原因是因为科学可能被歪曲了。以无限电波为例,这是他列举的两个例子之一。我认为,1880年无线电波的预言,是赫兹根据麦克斯韦针对以太问题所提出的科学理论而得出的:空气是由传播无线电波的以太组成的。是的,无线电波是真实的——预言是可靠的;它起作用——但是理论不是——完全是错误的。他给出的另一个例子是有关航海员的,即使在今天,航海员还是使用老的以地球为中心的天文学,而不是使用以太阳为中心的天文学。这又一次说明,你可以拥有一个涉及世界是什么的完全错误的理论而它却是有用的,你可以用它来把事情做好。所以,这无可争议地证明——为什么某一事情是真的?因为它起作用;为什么它起作用?因为它是真的——这可能很容易被歪曲并仍然为人们所持有。我们并不注意去询问知道某一事物与制造它之间的关系。被制造的事物与真的事物是相同的,通过建构而得到知识的建构主义可以被理解为现代性的标志。
凯里:正如萨耶·塞缪尔在这里所描述的,科学知识是创造性的、建构性的、有意而为之的,因此,在某种意义上说,它是上帝般的。这些属性使得科学知识完全不像人们以前依靠的常识。并且,历史地看,塞缪尔对这种科学所关注的,不是它恰好作为常识的补充,而是它代替了常识。科学认识变成理性和所有恰当知识范式的象征。术语“常识”继续表示合理的判断,但它也开始引起对事物真的是怎样的某种无知。在这方面,特别典型的是阿尔伯特·爱因斯坦时常被引用的评论:“常识无非是孩童期的头脑中遗留下来的偏见的沉淀物。”
萨耶·塞缪尔想要挑战科学对理性的垄断。他想恢复常识的尊严并限制科学的应用。两个区别对于他而言是决定性的:他说,数学知识必须与判断相区别;实验必须与经验相区别。
塞缪尔:实验与经验之间的区别是首要的。人们不得不明白这一点。从亚里士多德到霍布斯,经验被理解为在记忆中积累的感觉印象重复的结果。直到那时,我们才可以说我们拥有经验。即使在今天它也被理解为:“他是一个有经验的人。”这意思是说,他一直重复地经历某些事情。这就是我们所指的“经验”的含义。
“实验”可能是一个一次性的事件,一个单一事件。实验不仅可能是单一的事件,而且它需要对自然的“谋划”。你必须打断、切割、捆扎、改变、安排,以便于你可以研究自然,以便于你可以询问“她”。它不是在正常的过程中所获取的东西。实验“筹划”自然,然后从这种“筹划”中将其一般化,好像它是经验并且任何人在任何地方都可以重复这个过程似的。这不是真实的。它使用许多仪器去重复许多实验。所以,这些实验结果,由于其本身的性质,是一次性的事件、单一性的事件或在高度程式化的装置中重复的事件,是很特别的。但是,它们作为自然的一般过程的证据,被呈现给我们。
所以,我在经验和实验之间做出区别:经验是指所有我们时常在与处于正常过程的自然相互作用中所经历的;而实验是指对自然“筹划”的结果,是典型的生产的结果:不是普通地可以看得见的,而是把结果当作普通的存在并在修辞学上加以证明。
凯里:塞缪尔所称的科学修辞学是指,从1660年罗伯特·波义耳首次公布他的实验到现在的时间里,一直呈现在公众面前的科学形式。这种修辞学试图说服我们实验应当被视为经验,我们应当把科学知识视为犹如我们可以体验和触摸一样真实的东西。塞缪尔试图小心地在他们之间做出区别,并且他对数学证明和常识判断之间在并行的性质上给予同等的权重。
塞缪尔:计算机处理所给出的回答是数字:0和1;真与假。如果我说这个桌子6英尺长,那么,这要么是对的那么是错误。只有一个答案。甚至当人们谈论统计学的可变形式时,也只有一个正确的答案。我们不能在我们想要的精密程度上彻底了解它,但是,确有一个正确的答案。所以,所有数字的测量都具有这一特征。
还有另一种测量,比如在柏拉图那里就有。它是太多、太少或者正好的测量——并且它确实是一种测量。不过,如果你愿意的话,可以叫它是第二类别的测量,是一种非量化的判断。它视情况而定。它依据情况做出判断,它依赖于人类的意图,它依赖于谁在问他、出于什么目的。答案不是精确的6.5英寸。
在数学测量和我们称为判断的测量——有关太多或者太少的问题的回答——之间的这种区别,出现在我们之前经历的或我们现在正在面临的问题中:比如,全球变暖问题。全球变暖是一个科学假设,它要么是真的要么是假的;含碳值要么是0.2要么是0.5。但是,无论这个值是太高或太低,它都是一个判断的事情。它视情况而定,它依赖于人类的意图,它依赖于人类的目的,等等。对这一问题没有科学的答案。
我们可能会更深入地问,我们能以这种方式理解自然吗?并不仅仅是我现在谈论的全球变暖问题。有这种太多或到少的科学或者这种认识的科学方式吗?这完全是一个合理的问题,并且它没有科学的回答。就是说,经验和判断,在原则上是否有优于科学知识等级这一问题上,没有科学的答案,因为我们总是能问,科学提供太多的东西了吗?对于这样的问题没有科学的答案。当科学自身的合法性问题被提出时,科学的无语和沉默说明,在这一点上要有一个更高的权威来做出判断:常识。这正是我要强调的一点。我们的意识形态对科学与理性之间同一性的奴役——视科学论证为唯一的论证形式——可以通过注意这一根本的缺点而被颠覆:科学不能回答自身合法性的问题。这提供了一个杠杆,以便我们从我们意识形态的、盲目的对科学和理性的认同中摆脱出来。询问科学的合法性,是认识科学的无知并因此把它放到它合适的位置上的一种非常合理的方式。
凯里:塞缪尔想建立两种主要的区别:实验与经验之间的区别,数学维度与常识判断的区别。通过这些区别,他认为,正如他所说的,科学可以被放到它合适的位置上。他认为,这也可以中止对理性自身的伪装并适应科学之外的权威,否则我们将无穷无尽地在这同一循环中兜圈子,在这一循环中,对科学产生问题的回答总是要更为科学。关于把科学放到它合适的位置这类事情,我们能做些什么呢?首先,在塞缪尔的观点里,广义地说,因为科学现在完全支配我们大众和政治生活,所以,在我们考虑什么和我们做什么这两个方面,应做出明确的规定。
塞缪尔:政治话语的主题是什么?它是全球变暖,是京都协议,是汽车;它是经济布局和失业;它是性政策;它是对外援助,是贸易往来,等等,等等。这种政治话语的主题事务是由经济科学、生物化学等所制造的对象组成的。之后,在思考这些事件、这些主题中,思考的工具和形式所造成的冲击,是它们自己的科学式提问方式。政治问题是通过公共政治学被处理的,并且公共政治是政治科学的一个分支。所以,今天的政治学所传递的——如果你愿意的话,你可以说,在它的主题和它的解决方案两个方面——是在科学术语中被建构的东西。好争辩的一方会说,这就是由“polis”即“人们的科学管理”的实验所构成的公共政治。
凯里:根据萨耶·塞缪尔的观点,现代政治生活在两种意义上是科学的生活。首先,它的内容是科学地建造的,甚至一个普通的新闻广播都不拘礼节地涉及不妨说是天使或半狮半鹫的怪兽的事情,以至于大多数的听众认为:那不过是一个发射性同位素的临界短缺或者比如说一个许多货币利息基本点调整的事情。其次,人们通过投票、公众关系、保健等艺术的形式科学而被管理。萨耶·塞缪尔说,这就是现在国家政治大部分的状况。
塞缪尔:如果你研究“政治”这个术语,你会发现,它由“警察”和存在于服从命令的政治空间的监督科学而产生。所以,它成了盔甲,它成了你用来管理政治事务的航标。这就是公众政治的角色和目的。现在,它对我而言似乎是,它是在科学、社会科学的范围内被告知的东西,它只不过是在人们身上所做的科学实验。
凯里:如果有人采用你上面关于政治的定义——也是伽利略着力创立的“重塑理性的真实”,那么,这似乎很难反驳你刚才所说的现代政治的运转方式——为了人们的制度、进步等目的而使得他们与理性设计保持一致。我们还能有其他诠释政治的方式吗?
塞缪尔:亚里士多德有一个有趣的理解方式。他说:“相对于自然,人是一种政治动物。”并且他论证说,所有的动物、包括人,都有嗓音。嗓音是用来表达愉快和痛苦的。当你拍打睡在你床上的猫的尾部时,它的叫声以一种不是你在喂它时发出声音的方式表示它的委屈。我们和动物共同享有这一点。但是,只有人有说话能力;并且说话是人表达他对正义和非正义、什么是好和什么是坏、什么是合适和什么不是合适、什么是恰当和什么是不恰当的关注方式。
对人的科学管理——如果我们同意科学所说的——就是冰冷地对待公平和不公平、恰当和不恰当的问题。其实,那些是判断的问题,需要你去理解什么是太多和太少、什么是正好。事实上,科学家自己也承认这一点。他说:“那是价值领域。”但是,价值完全是非理性的,而且这就是我为什么反对确立这种问题的整个方式的原因。科学与价值之间的区分,因没有为对科学的合理批评留有空间,所以是错误的。价值对于做出决定,是一个主观的、非理性的承诺。为什么我做某事?因为我想做;但是我对此不能给出理由。所以,回到我的观点上,由亚里士多德发现的、赋予人的政治动物特性的讲话能力,在公共政治世界里是没有生存土壤的。
萨耶·塞缪尔对政治学使用科学技术的方式设法科学地框定问题的反应,是退回到以前的情况。这不是由于冷漠,也不是由于知识分子的傲慢,而是因为他相信,仅仅通过抵制政治学对常识的免疫力就能让政治判断重生。
塞缪尔:对我而言,首要的一步是,在识别因政治学而经历的冷漠中,认清什么是应被尊重的、恰当的政治话题——即,公正与否的问题,适当与否的问题。并且,识别冷漠这首要的一步,将使我们与用纯粹的科学术语所提出的问题保持距离并拒绝接触这些问题。我们不得不问,是否在政治学中有太多的科学以及科学的谈论和陈述方式——这是我们的第一步,而不是我们现在被邀请来做对所谓的“政治问题”仅仅进行袒护的事情。所以,要么你赞成转基因生物,要么你反对转基因生物;要么你赞成全球变暖,要么你反对全球变暖;要么你赞成外购,要么你反对外购。并且,通过这种你宣布支持争论的某一方的盲目决定,你被赋予作为一个所谓的“政治动物”的凭据。但是,这是在完全不理解的情况下做出的。我们不能在明白事理的方式上懂得或者理解这些问题。最后,我们应无条件地相信涉及那些问题的真理。所以,应该按传统说法去做,而不是仅仅去当无政治意义的噪音发生器——为了赞成或反对这件或那件事情而站在队伍中擂鼓助威。我建议我们首先要问这样的问题:我们是否能够后退并摆脱某种不介入主要政治问题(如公正与否)的讨论、并且不允许我们对某一事情太多或太少作出判断的言论方式?
为了把上述问题具体化,我做过大量的阅读(尽管可能没有太多的必要),但是我还不能直接进入气候变化问题的讨论。我丝毫不想否认,人类掠夺了他们的故土、践踏了自己的家园。这一点毫无疑问。但是,我们面临的难题是:当它变成了科学的实在时,其解决方案将是科学的,并且需要人们的科学管理,无论它是通过污染信用的方式、增加燃气价格的方式、重新设计城市空间的方式,还是其他任何方式。工业化是给人类今天带来所有那些麻烦的直接原因,人类在工业化的道路上已经走得太远,这种思想在尚无科学的很早以前就已经被人们理解了。并且,那时解决此类问题的方案也是非科学的和常识性的方式。现在这没有用,我们走得太远了。无视常识并赋予科学特权的历程恰恰导致我们处于目前的状况。我认为,除非回到常识,否则我们无路可逃。否则,你将伴随更为科学的管理方式而终结。我们只能在目前已有的状态中终结,别无选择。
凯里:萨耶·塞缪尔面对作为政治问题的气候变化而沉默寡言,有两点根据。第一个是他不愿采取远距离观察的气候分析员的立场,即从很高的位置审视地球、从地球的每个时期的每次天气及其周围的变化来分析气候变化。第二是他的感受,正如他所说的,气候变化的讨论,时常并不是关于人类活动的恰当限制和关于在我们开发自然中我们应该走多远的话题,而几乎总是关于生物圈在它反弹之前可以安全地向前推进多远的话题,也就是说,是关于我们干什么可以侥幸逃脱的话题。
塞缪尔:我们可以问,从事建构那些气候变化模型的目的是什么?请注意,我毫不怀疑——并且我还想强调这一个事实——地球一直通过工业化被掠夺。比如,在印度我的家里,所有我不得不做的事就是出去走走并呼吸空气。这是明显的,这是常识。所以,我对此没有疑问。让我们回到问题:为什么是这些气候变化模型?它对我而言似乎是,被提出来的问题是,在地球采取它的报复之前我们能掠夺它到什么程度?它是一个正在被问及的、突出的实践问题。在地球反咬我们之前,我们还可以掠夺它多少?但是,它对我而言似乎是,要问的先在问题是:甚至那些最平庸的人都可以明白,他们自然界的临界值是否应该被超越?你从骑自行车到开汽车的时刻,就是你超越你能力的时刻,你已经打破了某一自然界的临界值。在打破临界值或界限时,这不仅很有可能意味着你掠夺地球,更为重要的是,这更有可能意味着,你将从你能看见的、你正在掠夺的地球中失去中心位置。我认为这是非常重要的。我们越是给予用科学的方式提出问题的必然性以信赖,我们就越是“入股于”用科学的方式进行管理的必然性。
凯里:在塞缪尔的观点中,政治学应该是每个公民可以理解和经验的东西。他说,只有专家有资格发表观点,普通公民就被剥夺了运用判断力的任何机会。有多少公民对空气中的二氧化碳恰当浓度有能力做出判断呢?当技术问题支配公共讨论时,大多数人被剥夺了公民的权利。并且,萨耶·塞缪尔说,结果,无知和不能胜任,连同专家的意见一起被强化。
塞缪尔:在理性、启蒙时代,技术—科学的理性主义已达到缺乏文明的人类历史的最高点,有许多各种各样的无知。法国人类学家马克·奥格(March Augé)注意到,今天的美国人看待其他美国人和欧洲人看待其他欧洲人,如同曾经的英国人看待印度人和法国人看待北美洲人一样感到陌生。美国人已经开始对自己进行人类学研究,于是,曾经被用于陌生的、未开化人的人类学,现在被用到身边熟悉的人身上了。美国人对待他们自己的方式似乎有点让人看不懂。不必去谈论在政治认同和寻求认同中表现出来的别的各种无知,就我自己而言:我不认识我自己,我想弄明白我是谁——这事实上是对自己的看不懂。不过,比这更糟糕的是,严格地说,我们被为我们所建构了的一个魔法世界的技术—科学客体所包围;在这样的世界中,事物在运转,但其原因是难以理解的或者是隐藏着的。我走到自动取款机前,插入银行卡,输入密码,于是取款机“吐出”钱来。它如何工作的和为什么是这样的,我不知道。我去过法国,事情也是这样发生的。我用手机呼叫我母亲,即使某人告诉我没有电线、没有什么东西,它就是在某个地方跳出的空气,但她能听到我的声音。这好像是说,在严格的意义上,我们生活在一个魔法时代,被正在起作用的但不理解其原因的客体所包围。在事情如何运转问题上,我们有看不明白的地方。
最后——并且我认为这是特别值得说的——科学的产品已经达到如此复杂的程度,以至于一位科学家或者一类科学家们,根本不知道其他科学家们正在做什么。对我而言,当大卫·吕埃勒(David Ruelle)在《机遇与混乱》(ChanceandChaos)中用5 000页的篇幅对所谓的四色理论的解决方案或者所声称的证明进行报告时,没有一个数学家能理解它——它甚至是位于数学中心地带的一种晦涩,这一问题达到了危机关头。就是说,理性主义达到了这样的阶段,在其中无知似乎成为一种普遍现象。如果这不是对重新发现或者找出对技术—科学文明的合理批判的呼唤,我不知道它还能是什么。在这种文明中,享受被看做理性最高和最丰富的果实;在被表述为“敢于求知”(dare to know)的理性时代中,300年后,我们达到了一个几乎是系统的无知的状况。没有一个人知道得很多;每一事物似乎都在运转;我们表现出越来越多的非理性行为。当我问:“自动取款机是如何工作的?为什么这样工作?为什么那样发生?”答案是很难得到的;然而我期待行动。我期待被签约雇佣去做一些事情。我们正处于行动被建立在不合理基础上的世界之中。
凯里:萨耶·塞缪尔一直强调,科学对自身不能做出判断,不能发现它自己恰当的限制,不能告诉我们什么是足够了。所以,对科学而言,通过呼唤对相同事情的更精细或者更综合的版本来回答科学的每个失败,是愚蠢的。在他的观点中,我们急需的是一种所有公民都能参与“什么对于我们是好的”问题讨论的语言。所以,他打算复兴一种对科学服从常识判断的理性说明。但是,我问他,这如何才有可能甚至被想象出来呢?我们的公众和私人生活充满着科学的客体,并且我们的表达充斥着来自科学的移居者的似懂非懂的语言。回到常识如何可能呢?他的回答诉诸加拿大哲学家乔治·格兰特曾经称为的“剥夺地告知”,就是这样的感觉:某些事情在现代社会正在失去,某些事情我们必须重新发现以便排除对科学恒常的依赖。
塞缪尔:与科学的术语和视之为当然的术语、词汇保持距离的方式之一,是开始着手查明它们进行取代的行进过程。并且,在试图从事这项工作中,我重新发现了残渣、剩余,某种剩下来的东西,它允许我表达——不管它怎样无条理地、摸索着地表达——一种对科学术语的不满,一种它们对我们正在问的问题不能加以确切表达的识别。在打算去说的术语和我们承认的它不能确切表达的术语之间,有差距;并且,这种差距提供了某种刺激、诱因,以便承担必要的历史研究。你可能会问,在充满那些科学术语的表述中,我们失去了什么?我认为,可以说,这个问题的最好表达方式是通过一个引证来进行。我引证的书叫《政治学的解释学》,作者是斯坦利·罗斯(Stanley Rosen)。他写道:“如果知识是启蒙并且科学是知识,顺理成章的是,为了被启蒙,要么承受自我无知,要么经历物化。”如果知识是启蒙并且科学是知识——这与我们之前说的是等同的——那么,被启蒙将遭受自我否定(因为科学不能影响我)或者变成一个客体并经历物化。你可能会问,为什么我们被科学的术语所包围这一点是很重要的?如果通过科学的术语我们理解了我们自己,那么我们就以客体的方式来对待我们自己;或者说,如果我们认识到科学的术语不能帮助我们理解我们自己,那么,我们将永远对我们自己是不清楚的,我们是无知的。并且,到目前为止,科学的环境没有改变,我们被谴责为是物质的。人类,作为理性的动物,最终将变成真正的动物。对我而言,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的赌注是如此之高的原因。
凯里:萨耶·塞缪尔通过指出科学使我们的感觉失去人性开始今天的节目。它展示给我们的世界,不是我们感知到的它的样子;并且,他是要回到我们感官的世界,这种感官世界是塞缪尔看做摆脱他刚才描述的进退两难境地——在科学规则的控制之下,我们必须要么将我们自己看做客体要么永远保持对我们自己的不理解——的方式。他说,正是通过我们的感觉,我们最终属于世界并且世界也属于我们。
塞缪尔:如果通过我们的感官我们理解了世界,那么,感官也是我们维系于所予世界的方式;并且,只有承认我们拥有共享周围世界的天性,我们才能够发现我们的本性。所以,除非我们保持与世界的联系,就是说,将我们的手指插入泥土,否则我们将永远误解我们的本性。常识为什么重要呢?常识是从外部将世界和我的心灵联系起来的通道。如果我谈论作为界限的自然的临界值,那么这种联系就是核心或关键。我不得不保持与泥土的联系,以便了解、认识自然的临界值。这恰恰是因为我们已经被连根拔起并随意地到处漂流;在极大程度上,在肉体的、可意识到的方式上,我们再也不能领会在走路和踩脚踏车兜风与进行联邦快递之间有什么不同了。当你进入小轿车时,你就成了一个联邦快递包裹,就像我一样。并且,我们把走路和驾车仅仅看做可供选择的运输模式的这一事实,作为我们已经走得何其远、我们已经变得何等背离常识的一个指标,一条线索。
凯里:你认为任何人都可能采取的、首要的一步是承认不同,即使人最初不能对此做任何事情?
塞缪尔:我认为需要行动,造成一种几乎是遭遇抢劫者的紧急状况——要么你行动,要么你死——以免造成自我的进一步迷失。还有足够的时间。虽然我不能做任何事情;但是,正确地思考,试图正确地思考、研究、工作、澄清,是我做事的形式。用了300年的时间才加以根除的东西,如今要再现它,绝非一日之功。
(淮阴师范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王荣江译,标题、摘要和关键词为译者所加。)
责任编辑:王荣江
N0
A
1007-8444(2015)06-0717-08
2015-08-20
2014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项目(14BZX023)。
萨耶·塞缪尔(Sajay Samuel),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商学院临床教授,科学和常识方面的随笔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