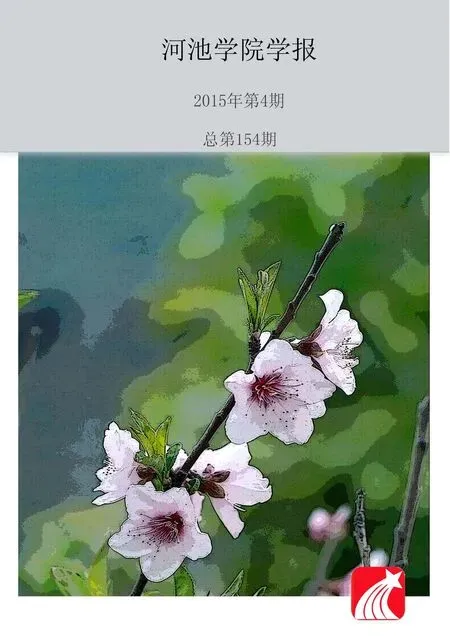“母亲”的勇敢与抗争——析赛珍珠《母亲》的女性主义意识
李秀梅
(江苏科技大学 外国语学院,江苏 镇江 212003)
尽管赛珍珠从未参加过任何妇女解放组织,并自称不是什么女权主义者,但其在中西方世界独特的生活经历和天性的敏感使她对女性的命运极为关注。1938年赛珍珠凭借书写中国农村和农民题材的两部长篇小说《母亲》《大地》三部曲以及两部纪念父母的传记作品《异邦客》和《战斗的天使》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引起了世人的瞩目。其中《母亲》被认为是“赛珍珠的中国女性形象中最完美的,这本书也是她最好的一部”[1]951。但这部作品的译本由于出版年代久远,并不为广大读者所熟知,“一般的中美读者和小说评论人看赛珍珠的小说,都止于《大地》,多半忽略了这本更具感情和含有心理分析意义的好书”[2]9。近些年随着赛珍珠研究的不断深入,以及夏尚澄修订,万年绮翻译的《母亲》再度出版,《母亲》重新走进人们的视野。即便如此,《母亲》的关注度远不如其他获奖作品。对《母亲》进行多角度、多侧面的研究并探讨其深藏的艺术价值和社会意义是十分有必要的。本文拟从女性主义视角分析《母亲》,探究赛珍珠的女性主义意识,以期更好地把握赛珍珠的文学创作思想。
一、“母亲”对情爱的大胆追求
旧中国深受儒家封建礼教的影响,将女性视为男性的附属品。女性在社会和家庭中无地位、无尊严,遭受丈夫的奴役和支配。女性的形象也一直被传统男性作家忽视或丑化,在他们的作品中,女性要么呆傻,要么妖媚,甚至撒泼,总之难登大雅之堂。赛珍珠看到女性在封建旧社会遭受的种种不幸,关心她们内心需求,“细腻诚实地描写了‘母亲’的身心情感成长,以及情欲收敛、压抑、迸放、悔伤的过程”。[2]24为读者刻画了一个身心完整的女性形象。
文章一开始就给读者呈现了一个温柔善良、勤劳能干的“母亲”形象,她深爱自己的家人和现世的生活,“对日子的轮转感到非常的满足”[3]15。这跟一些男性作家笔下没有思想、没有意识、没有欲望的乖顺羔羊相比,“母亲”的形象是鲜活的,她有血有肉,有七情六欲,并且敢于追求自己的情感。“母亲”用心地疼爱自己的丈夫,但并不唯唯诺诺,她既敢于向丈夫发脾气,也敢于表达自己的情欲。她的内心有“克制不住的强烈的情欲,激动起来像狂风暴雨一般,会把所有无名的怨气和爱意尽情地向她的男人发泄”[3]75。但不幸的是,在她生了3个孩子之后,丈夫就抛下一家老小,一个人带着所有的积蓄离家出走了,“母亲”的情欲再也无处发泄。在男权当道的封建社会,男人可以在外寻花问柳,在家三妻四妾,女性却只能从一而终,在内心孤苦中煎熬着老去。“母亲”无比地嫉妒对街堂嫂一家,心里又“激起了渴望的情欲”[3]81。感情上得不到满足的“母亲”情绪会起伏不定,她会突然有一天“感到极度愤怒,她的心又凉又痛,就像有人拿拳头打着她一样”[3]84。乐黛云认为,分析女性意识的文化层面应该以男性为参照,了解女性在精神文化方面的独特处境。赛珍珠对母亲潜意识里欲望的窥探体现了她对女性意识的关照。
空虚失落的“母亲”太需要有人来抚慰了,就在这时地主的收租人出现了。他开始勾引“母亲”。“母亲”不但没有感到任何的羞耻和愤怒,反而在不知不觉中“眼里竟然流露出那深切、渴望的热情”[3]85,得到回应的收租人更加的大胆,直接摸了摸母亲的手,“母亲”的身体立刻有了别样的本能反应,她的“血液里像燃起了火焰一般的燃烧着”。弗洛伊德认为,下意识对人的心理、行为和性格都有很重要的意义,它能够反射出一个人的内心世界。“母亲”的这种下意识的情欲正是她身心忍受着煎熬和思念的展现。“母亲”虽感到羞愧,有所回避,但她的心里有了一份“既温暖又不正常的渴望,”[3]86收租人走了之后,她在心里还在不断回想着刚才“充满刺激般甜蜜的激情”[3]87。渴望最终压倒了一切,勇敢的“母亲”将封建枷锁全都打翻在地,无法抑制内心的冲动跟收租人苟合了。“母亲”再一次成为了母亲并勇敢的接受了收租人的爱,她“停不住对他的思念”[3]105却又不好意思去寻他。此时,收租人对她的热情却突然不见了。当他不再看她的时候,“母亲”很快就明白了一切,但是,“母亲”并没有轻易放弃,努力地想让他回心转意。在收割后招待收租人宴席上,“母亲”打扮的很漂亮,并有意在他的眼前忙来逛去,可是他的一眼都没看她,“母亲气得浑身颤抖着”。[3]106却还是不死心,又把收租人送的首饰戴上,最后依然无法改变他对她的冷漠。“母亲”再度出击,她不顾封建社会旧俗陈规的束缚,主动找到收租人婉转地向其求婚,不料遭到了断然拒绝。“母亲”再次被抛弃了。内心强大的“母亲”“忍住不哭”[3]111。她不顾一切地私下打胎,再一次坚强地挺了过来。透过赛珍珠细腻的笔端,读者结识了一个内心有欲望、有胆识的“母亲”,她勇敢地追求自己的幸福,敢于打破封建的“三纲五常”。林中明认为赛珍珠对“母亲”的这些描写“在当时的社会环境里,算是大胆的文笔”[2]24。
二、“母亲”对命运不公的抗争
“母亲”的勇敢不仅表现她敢于表达自己内心的渴望和需求,更体现在她不屈从命运的摆布,像一个硬汉一样坚决地与困境抗争到底。在男尊女卑的传统社会中,女人依附于男人而存在,她们不但在社会生活中毫无地位可言,在经济上也得不到独立,只好退守到家庭生活中沦落为男性泄欲的对象和生育的工具。离开了男人的女性无法在社会上立足,备受社会的歧视和冷落。但是“母亲”没有被吓倒,她用智慧勇敢地对付这些偏见。当发现丈夫携钱财离家出走之后,所有人都没了主意,只有“母亲”很镇定。“母亲”先安慰婆婆“老妈妈,没事儿!他明天就会回来的,你去睡吧”[3]47。她又安慰孩子们“没事,爸在镇上,明天或者后天就会回来了”[3]47。面对好事者的猜疑,“母亲”很镇定地告诉他们“他到镇上有事儿,所以迟了,我想……明天才会回来呢”[3]46。“母亲”的镇定打消了所有人的疑虑,大家都在“母亲”的庇护下安心地去休息了。只有“母亲”自己的心里很明白:他不会回来了。
在男性为中心的社会价值体系中女性被推到道德、正义的对立面,成了祸水和灾难的始作俑者。男人的离家出走并不能为“母亲”换来同情的眼泪,反而成了指责“母亲”不够贤良淑德而遭受唾弃的证据。然而机智的“母亲”开始精心编织谎言,为了安慰一家人焦急等待的心、堵住好事者的好奇心,她编了一个男人在城里做工的故事。为了证实故事的可信,她伪造书信,并拿出家里的余钱佯装是男人捎回来的。在人前,“母亲”从来没有流露出一丝一毫被抛弃的幽怨,只有在夜深人静一个人时,她才会流眼泪。男人的抛弃并没有让“母亲”倒下,她挺直了腰杆,坚强而又自尊地活着,继续履行她为人母、为人媳的责任,可见“母亲”是多么地坚强。此后,管家的羞辱、宝贝女儿和心爱的小儿子的相继离世都没有将“母亲”打垮,“母亲”像一个勇敢的斗士,在孙子呱呱坠地声中复苏过来,继续骄傲而坚强地活着。
此外,“母亲”敢于谴责神灵不公。在封建社会,由于社会生产力的低下,人们对自然现象和人类命运的不可把握充满恐惧,陷入封建迷信的神坛中,对超自然的力量膜拜不已,以祈求获得庇佑。“母亲”也对神灵充满了敬畏,她虔诚供奉神灵,祈求多子多福、消灾免难。男人出走未归,“母亲”“做了糕饼,买了香烛,放在神前为他祈祷”[3]60,求神保佑丈夫平安回来;跟收租人发生关系时,她从地上捡起衣服,“蒙在土地公公的头上,好遮着他那双凝视的眼睛”[3]99;当女儿眼疾越来越严重、几近失明时,她迎着很大的风,走了整整一天到观音庙去为女儿祈祷。可是,祈祷并没有换来安稳如意的日子,苦难还是一重接一重地降临:丈夫出走五年至今未归,小女儿眼睛彻底瞎了,嫁为人妇后被虐待至死,小儿子被抓走枪毙,大儿媳婚后一直未育。“母亲”不再沉默地祈祷,她勇敢地站起来控诉神灵的不公。她一次次地责问神灵“我所受的惩罚难道还不够包容我犯的那一点罪恶吗?”[3]200“我一生的痛苦,一生的穷苦,难道还不够吗?但是菩萨您却好像不是怎么公平呢!”[3]200-201“到底哪里才能找到一个完美无缺的女人,不曾犯过一点罪过,为什么我就该受这么些苦难呢?”[3]206她甚至怒喊“难道这就是我应得的报应吗?难道这么多罪还不够我受的吗?”[3]219“母亲”的控诉字字带泪,淋漓尽致表现了她对命运不公的不甘与反抗。
三、“母亲”对话语权的争夺
话语包括两层意思,一种是人们在实际生活中运用的言语,二如福柯所描述的话语(discourse),它与权力相交织,是“一种社会工具,是权力施展与再现的一种形式,也是社会文化构架中的必要因素之一”。[4]103“任何人际关系在某种程度上都是权力关系。我们是在一种拥有永恒战略关系的世界中行事的。”[5]男女关系当然也不能例外,它体现了两性之间支配与被支配的关系。在传统的家庭和婚姻关系中,男性操纵了话语权,建立起社会主流话语霸权地位,女性则丧失了话语权的主导地位,对男性的统治要么沉默不语,要么随声附和。然而“母亲”没有唯唯诺诺地应对男人的指责,而是不断地跟丈夫进行针锋相对的抗争。当丈夫把她停下手中的活儿去喂奶看作是一种偷懒行为进而训斥她时,她大声地辩解“难道你不该稍微补偿一点我的痛苦吗?你在干活的时候,难道有像我一样挺着几个月的大肚子?你有尝过生孩子的痛苦吗?”[3]5当丈夫想进茶馆、逛赌场时,“母亲”会用白眼来制止他,而他的男人则“不敢在她妻子的气头下进行反抗”[3]10。当男人花钱买些没用的玩意儿回来,或者在镇上喝了酒,醉醺醺的回来的时候,“母亲”就会向他大发脾气,他的男人则有点害怕她。当男人抢夺“母亲”陪嫁的3块银元给自己做新长衫时,“母亲”愤怒地同他争夺、扭打。赛珍珠呈现给我们的“母亲”是一个不甘于被父权压制和奴役的女性,虽然她的发展空间和生存的境况在社会各种苛刻条件的盘剥中越来越糟糕,但她勇于斥责男性话语的统治模式,不断挑战男性的权威。
“母亲”虽然没有鲜明的解构父权制的意识,但“女性争取话语权的抗争过程实际上是自我建立的过程”[4]。她的勇敢、无私和担当一定程度上解构了大行其道的男权文化。美国社会学家约翰逊认为男权社会是“男性中心主义社会,指一个社会由男性统治,是认同男性的,以男性为中心的。”[6]在男权的社会中,男性制定社会的价值标准,掌握生杀予夺的大权,在社会和家庭中享有绝对的权威和话语权。《易经·说卦》中的“乾,健也;坤,顺也”很好地说明了封建统治下的男女关系,在传统文学作品中,男性往往是歌颂的对象,他们体格健硕,骁勇善战,身手不凡,是正义的化身;他们有智慧,能够运筹帷幄、决胜千里之外;他们有责任感,能够铁肩担道义、一掌定乾坤。相形之下女人则是可有可无,她们渺小、柔弱,需要男性的保护;她们愚昧无知,被“女子无才便是德”的训诫困住无法翻身;她们毫无主见,听命于男人,奴性十足。西蒙·波伏娃认为“女人是男人用确定自己存在的参照物,是一种补偿性的事物,是男人的理想和神话,而唯一不是的便是她们自己”[7]23,可见男性之于女性的权威地位。但是,男性的权威、高大形象也并不是牢不可破的。在女性文学作品中,女性往往能够在关键时刻展现出超越男性的智慧和勇气,她们的形象有时比男性更光辉、更伟大,体现了女性文学对男权文化传统的抵制。
小说中,“母亲”的男人虽是一家之主,却并不愿意承担为人夫、为人子、为人父的责任。相反,他自私自利,不爱任何人。他是家中的独子,承担着赡养老人的义务,理应为老母养老送终,可他在厌倦了“干活,睡觉,干活,睡觉”[3]11的日子之后抛弃了家庭,带着所有的积蓄到外面逍遥快活去了,将赡养老人和孩子的任务扔给了“母亲”一人。他不疼爱他的孩子。女儿害眼病需要诊治,他冷酷地对“母亲”道“她不会痛死的,为什么要用我们好不容易剩下的那么一点钱给她医眼睛呢?”[3]14。这个男人不爱“母亲”,对她充满抱怨。他对“母亲”怀孕生子的辛劳毫不体谅,反而在心里埋怨她太会生了。他对“母亲”很粗鲁、暴躁,经常开口骂她。他也很吝啬,“从来没有像别的男人对他们的女人那样,给她买过任何首饰”[3]27。但他对自己则相当的大方,他花重金为自己买些中看不中用的东西,完全不顾念家里的穷日子。实际上,他“看见替他生孩子的女人和一群需要他养活的孩子们,就会突然觉得有一种重压在肩头上。这种责任好像就是他最大的梦魇。”[3]24他甚至对“母亲”说他的工作足够养活他自己了,仿佛照看老人和孩子都是“母亲”一个人的事,他不需要承担任何的责任。
跟男人相比,“母亲”更像一家之主。她挣扎在社会的最底层,虽目不识丁,却是生活中的强者,是家里、地里样样能干的多面手。作为家庭主妇,她总是天还没亮,别人都在睡梦中时,就开始了一天的忙碌。白天,她与男人一起在田间劳作,没有一刻休息。晚上,她还要接着操持家务到深夜。即使是在夜里,“母亲”也不能安心歇息。“母亲”关爱家人。她不但是3个孩子的母亲,还把婆婆和老公都当孩子一样地仔细照顾。“母亲”疼爱孩子。“她不忍听到孩子的一点点哭声”[3]5。“她宁愿把自己多余的钱让孩子们长胖些”[3]7,也不为自己添置那些喜欢了很久的首饰。“母亲”对男人充满爱。她总是哄着自己的男人,“无论他俩怎么争吵,当母亲看到他吃的舒服,心里总是很安慰。”[3]9当丈夫离家出走之后,“母亲”毫不退缩,她勇敢地担起照顾婆婆和3个孩子的重担,尽自己所能为家人忘我付出。《老子》中说“无名,天地之始。”小说中的“母亲”虽无名无姓,但却极其温柔、坚强、伟大。她像世上的大多数母亲一样,用无私的普世之爱照拂家庭,像母鸡一样把家人庇护在她的羽翼下,时刻守护着。她那不务正业、游手好闲、好吃懒惰的丈夫在此等高大形象的衬托下显得渺小而猥琐。
四、结语
赛珍珠笔下的“母亲”生活在黑暗的旧中国,“处于多重压迫系统的最底层,肩负着种族、阶级和性别的压迫”[8],她命运坎坷、身份低微,却并没有唯唯诺诺地屈从于父权的压制和奴役。她敢于打破封建礼教对妇女的束缚,毫不压抑自己的内心渴求,大胆地寻求情感的归宿,并能勇于面对男人对其一而再的抛弃。她的勇敢反映了赛珍珠对女性情感意识的格外关照;此外,“母亲”积极地同命运及封建男权统治进行不懈地抗争,她不甘于做命运的棋子,不断挑战男性话语权及男性权威,毫不畏惧男人的种种无理指责,大胆解构男性话语,独自担负起男人不愿承担的家庭及社会责任,显示出其不输于男性的、坚强的性格,反映了赛珍珠对“母亲”身上显现的女性自我建构意识的精妙捕捉。
[1]瑞典文学院常务秘书.授奖词[M]//赛珍珠.赛珍珠作品选集——大地三部曲.桂林:漓江出版社,1998.
[2]林中明.序二[A]//赛珍珠.母亲.夏尚澄,编译.上海:东方出版中心,2010.
[3]赛珍珠.母亲[M].夏尚澄,译.上海:东方出版中心,2010.
[4]马红梅.18世界英国女性话语的丧失-以丹尼尔·笛福的《罗克珊娜》为例[J].外语研究,2010(4):103-106.
[5]冯永朝,王颖.解构男权:肖红小说中男性形象解读[J].广西社会科学,2009(9):84-88.
[6]王艳玲.后殖民视角下的赛珍珠小说再研究[D].沈阳:吉林大学,2014.
[7]西蒙·波伏娃.第二性[M].桑竹,译.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1986.
[8]李秀梅.赛珍珠的后殖民意识初探[J].江苏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3):51-55.